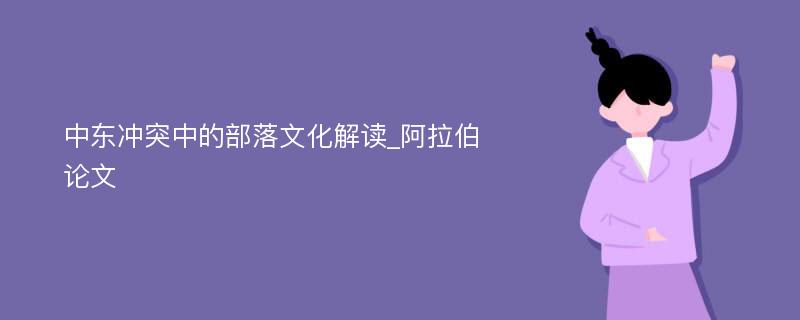
中东冲突的部落文化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东论文,冲突论文,部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东内部冲突无法与中东地区部落文化相分离。后冷战以来,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愈演愈烈,尤以中东地区动荡局势更为凸显。这里既存在阿以冲突,又有阿拉伯人的内部冲突,还有阿拉伯人与伊朗人、库尔德人的冲突等,构成了错综复杂、积重难返的中东地缘政治景象。很多学者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间的冲突视为政治、经济及至宗教的纷争。①鲜有从阿拉伯部落文化根源去探讨中东冲突。实际上,中东内部冲突与该地区部落文化有密切的关系。部落文化,是拥有一定血缘关系及其共同经济利益(特别是地理环境资源)的社会群体习得且共有的一切观念和行为。作为阿拉伯世界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部落文化“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沉淀”②。由于社会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因而中东部落文化对中东社会具有潜在而持久的影响。部落文化不仅影响着伊斯兰教,还影响着穆斯林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今天,部落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一道影响着阿拉伯国家的对外交往。
部落文化与贝都因人的劫掠性扩张
阿拉伯人通过“平衡对抗”原则来确保自己的安全。阿拉伯人与阿拉伯民族并不是一个等同的概念。历史上,阿拉伯人的出现早于阿拉伯民族的形成。狭义的阿拉伯人是指在蒙昧时期居住在阿拉伯半岛中部和北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贝都因人。③“阿拉伯”一词的原意是指沙漠。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里,贝都因人既要与自然界抗争,又要对付以农耕为主的南部定居居民和北部其他游牧民。显然,仅凭个人力量是不够的,家庭的力量也十分有限,只有联合才是出路。家族的重要性便显现出来了,在家庭的基础上形成了氏族,进而发展成部落。这样,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构成了社会的基本单位和组织形式。早期贝都因人就往往生活在这种松散的社团里,过着紧缩、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在部落里生活,当然也要为部落而生存,完全忠实并献身于自己的部落,因为脱离了部落也就等于失去了生存的条件。为了生存和发展,贝都因人通过“平衡对抗”秩序来维持安全稳定。 “平衡对抗”作为一种部落的组织形式,既是部落自我管理的基础,又是建立在分权和自治基础上的区域组织。在这一秩序中,部落不论大小,基于血亲关系,每个部落成员都有责任保护本族成员,并攻击外敌。假如发生了一场家庭与家庭、宗教与宗教、部落与部落、教派与教派、穆斯林与异教徒之间的对峙,这种“平衡对抗”就能平衡双方敌对关系。任何潜在对手都知道其敌人并非力量薄弱,至少是势均力敌。
恶劣的沙漠环境和部落组织形式也决定了男子(父亲)在家庭中的支配地位。人类学家认为,大规模父系氏族的出现正是得益于家畜的积蓄饲养,尤其是游牧生活的出现和骆驼的成群移动。其实道理很简单:父系家族游牧生活的能力和社会地位主要取决于可参与其中的男性数量,父系群体越是庞大,就越能打败其他部落,从而保护和扩大自己的领域范围,拥有的驼群也会增加,其生存能力也会增强。家族间的世仇是导致部落社会地位不断变化的主要机制,规模相同的家族都致力于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长期的不和又导致他们之间不断的冲突。每个父系家族都倾向于扩大本家族的规模。他们通过一些有效策略,如生养许多儿子,和同族人家联姻,以及实行一夫多妻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父系家族结构暗示了他们倾向于同亲属联姻,尤其是父亲的堂表兄弟。当一个男人娶了他叔伯的女儿时,她生的孩子仍是她本家族的后代,而不是外族的。当自己的女儿因家族内部联姻出嫁后,他们就希望家中的男子能够出去娶一个相对弱小家族的女儿,而且极有可能是一夫多妻制的婚姻。普遍的内部联姻,以及一夫多妻制婚姻为这些家族提供了快速的方法去扩大其家族的相对规模、相对力量和社会地位。
劫掠、族际仇恨成为游牧部落生活的必要补充。虽然部落的成功取决于儿孙满堂,但驼、羊成群和丰美牧场也是贝都因人生活的必要条件。逐水草而居的贝都因人饲养骆驼、马、羊等家畜,尤其是骆驼对他们的生活至关重要。骆驼皮可制衣、织帐篷,骆驼粪可作燃料,骆驼奶是主要的饮料来源;此外,骆驼适于长途跋涉而成为主要交通工具;此外,骆驼还有重要的社会沟通因素。结婚时,贝都因人将骆驼作为聘礼;也可以通过赠与或租借牲畜建立和巩固同其他家族的联盟,从而获得劳动上的帮助和政治上的支持。正因如此,“新娘的彩礼、凶手的赎金、赌棍的赌注、酋长的财富,都以骆驼为计算单位的。”④但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人口以及牧场的干旱,通过掠夺来获取资源就成为必要。通过侵袭来掠夺牲畜、侵占牧场和水资源,这种方式经常吸引那些部落的男子,他们视此为独立和卓有成效的方法。因而劫掠成为游牧部落的生活补充,对于贝都因人而言,劫掠和游牧同等重要。与劫掠相关联的就是族仇(血亲复仇)。家族间的仇恨仍将存在,因为已被当做一种机制来考验他们的家族团结与否。父系家族导致了等级制度的产生,他们也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两个年轻人的小争执很可能波及成人,最终导致大范围的混乱,影响到住在城镇和家族起源地所有人的生活。通过部落战争,可以增强部落内部的凝聚力,对外增强仇视感和抵抗力。
荣誉产生于劫掠和战争,反过来荣誉又进而为劫掠和扩张提供了精神支柱。劫掠和战争不仅被视为正常,而且能获得某种满足感——荣誉。在贝都因部落文化中,失败者、受害者受到鄙视。相反,胜利者则被推崇,赋予无尚的荣誉。可以说,荣誉与劫掠、征服相辅相成。赢得荣誉成为对外劫掠的重要使命。首先,忠于部落团结,实现使命就会获得荣誉;其次,在双方冲突中取胜就会赢得荣誉;再次,在部落矛盾中,成功者带来荣誉。对于贝都因男子而言,对外部的武装斗争是寻求荣誉的传统方式。
部落通过“平衡对抗”原则确立了部落内部的团结、和谐,并为劫掠、扩张提供了有力保障。在这个原则下,父权制、劫掠与族仇,以及荣誉等部落文化一起使贝都因人获取生存资源的首要能力和缔造其精神生活变得简单,也使他们更易掌控他人及财产。通过联盟,亲近疏远,在部落内外都可以采用。小家族被迫联合其他家族与另一家族抗衡;当部落人发生冲突时,部落内外的所有成员都联合起来,组成统一战线,并提供物质支持,以一致对外。⑤
部落文化与伊斯兰教
公元7世纪前,阿拉伯半岛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首先是南部以农耕为主的定居居民和北部以游牧为主的贝都因人的矛盾。后者常常劫掠南部农业区,南部诸王国则不断向北进犯贝都因人部落;其次,贝都因人部落血亲复仇比比皆是。各部落之间正忙于为争夺牧场、牲畜以及荣誉而争斗,加之多神教的存在,则进一步加深了部落间的矛盾,增强了他们的狭隘性和排他性,不利于阿拉伯半岛社会经济的发展。具备将贝都因人的血亲复仇转化为团结互助天赋的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后,阿拉伯半岛的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改观。在《古兰经》里,阿拉伯语“伊斯兰”的本义在于服从唯一的神“安拉”。这种一神教的统一性打破了氏族部落和各个小酋长国的狭隘性与排他性,并以地域关系逐渐取代血缘关系。此外,伊斯兰教又通过集体礼拜这种仪式促进了教胞间的兄弟关系,把阿拉伯人过去对部落的狭隘忠诚转到对宗教事业的忠诚,并异常团结,一致对外。这使阿拉伯各部族男子更加团结,他们共同组成了穆斯林群体组织——乌玛。
在部落体系基础上,穆罕默德架构了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结构。在此架构内,乌玛和部落具备同样共有的、神赐的特性,这使彼此排斥的诸部落有了共同利益和美好蓝图。但只有扩大“平衡对抗”这一基本的部落准则,统一才成为可能。穆罕默德通过这一准则来使穆斯林反对异教徒,从而把均衡状态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结构层面。初期的伊斯兰教试图把阿拉伯原始的部落忠诚意识加以改造,以忠于更广泛的兄弟情谊和一部内容广泛的法典《古兰经》,来打破狭隘的部落意识。在异教徒面前,具有共同信仰的各个穆斯林部落得到统一。贝都因人的劫掠与征战又因这一宗教而变得神圣。在每一场与非穆斯林的战争取胜后,越来越多的贝都因人加入到乌玛。一旦联合起来,贝都因人的枪口一致对外,赋予战争以神圣的意义。
然而,通过“平衡对抗”而在伊斯兰教中建立新的忠诚、荣誉之际,忠于旧部落的潜流依然存在。随着阿拉伯帝国急剧扩张和伊斯兰教影响迅速扩大,忠于旧部落的潜流一再泛起,以致破坏和谐,制造分裂。分化来自早期穆斯林的个人、家族、部落、教派,以及朋党之争,不过也牵涉其他因素。可以说,在伊斯兰教时代早期,足以严重威胁到阿拉伯国家稳定,以及乌玛社群的最凶险的冲突,并不在于穆斯林是否是阿拉伯系的分野;穆斯林与异教徒之间的分歧也没有那么严重,症结在于阿拉伯本族人之间的对立——出身北阿拉伯与南阿拉伯的部落者的相互对立、先来者与后到者之间的相互对立、勤奋有成者同事与愿违者彼此对立、父母两系都是阿拉伯自由人者与父系为阿拉伯自由人而母系为外邦妻妾者也彼此对立。⑥基于胜者对败者行使各项天经地义的权力,于是阿拉伯混血儿的人数也随之剧增。不同流派的阿拉伯人之间,存在连绵不断且往往是积怨深重的敌意,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内战。人数日增的非阿拉伯人穆斯林也被排斥在社会主流之外而感到愤恨与不平,因而也卷入内部纷争之中。在这些内战中,各派系纷纷为自身的悲情与诉求寻找宗教上的措辞。随着伊斯兰教疆域的急剧扩张,进一步带来了这种紧张现象。维持和治理这个国家与这个帝国的工作,尤其被上述这些差异与冲突弄得复杂不堪。在四大哈里发时期,除第一位之外,其余均丧生在穆斯林异己分子手中。先知去世才20余年,他的乌玛社群就被激烈的纷争撕裂了,并陷入了乱世与内战之中——更多的是阿拉伯人相互对立。
从政治角度讲,伊斯兰教将部落社会推向一个外延更大的层次,构建了穆斯林与异教徒相互“平衡对抗”的秩序。但不能代替部落政治文化的核心地位。作为部落政治,对抗意味着团结和忠诚。“我们与他们”相互对抗的基本部落框架在伊斯兰教里仍旧存在。任何试图超越这些普遍被接受、认可的规则是难以存在的。伊斯兰教派的出现与哈里发国家内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密切相关。而教派产生后在教义上的不同争论,又使各派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和复杂,并贯穿于伊斯兰教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⑦当前,伊拉克教派冲突是两派数世纪以来的战争的一种延续。⑧当然,伊斯兰文化也并非一成不变,它像部落政治结构的每个层次一样随时变化。人们只有在对抗异教徒时,才会从更高层面紧密地团结为穆斯林,而在内部,则以派别依据来发动群众,就像逊尼派与什叶派相抗衡。在两大教派内部,各自又分为不同的部落,且彼此对立。
因此,部落文化中的部落纷争使社会难以团结。不同组织的成员形成对抗。没有一个普遍的关系囊括所有的组织,正因如此,对抗主义变成了文化冲突。建立在“平衡对抗”基础上的部落体系又有效地促成游牧部落各自为政,前者进一步抑制了社会融洽,使纷争难以通过区域性法律手段来解决。
部落文化与阿以冲突
当代中东地区的诸多冲突依然深受部落文化观念的影响。对族际仇恨的推崇也会为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埋下隐患。中东国家之间在边境交火的频率亦很高,这些都与私人的族际仇恨有关。政府,也相当于一个家庭,十分看重诸如男性亲属、荣誉、报复等此类问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些问题已成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冲突的部落文化根源之一。阿以冲突使双方立场截然对立,然而,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只关心双方冲突本身,而鲜有考虑部落文化是如何形成和影响冲突的。
在没有深入了解阿以冲突根源的情况下,人们大都会对阿拉伯人不屈不挠地反对以色列而感到震惊与困惑。同样,人们对那些努力与他国交往,却没有热情与近邻以色列改善关系的阿拉伯国家的行为感到费解。与中东强国以色列相比,阿拉伯世界局势惨淡。除宗教以外,阿拉伯社会文化各方面,其重要性和影响力均有所下降。在与其他社会文化的全球竞争中,阿拉伯文化远比不上昔日的辉煌。另一方面,作为自由民主制国家的以色列,凝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还接受了贝都因人和阿拉伯人,既有穆斯林,又有基督徒。尽管其融合并不完美,但总体冲突较少。以色列的高科技发展显著。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互联网(INTEL)在以色列均有研发中心,微软也在此设有机构,摩托罗拉在以色列有海外最大的研发基地。此外,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有很近的血缘关系,双方的语言同属闪族语,甚至在宗教上也有一定的联系。
面对这个具有血亲关系的富裕而发达的近邻,阿拉伯世界不要说接受以色列的帮助,几乎是拒绝了以色列。甚至连与以色列和平相处的阿拉伯国家都拒绝接受犹太国家给予的灾难援助。⑨阿拉伯世界这种拒绝主义的普遍存在有其深刻的根源:(1)资源利益的冲突;(2)阿拉伯领导人利用以色列为外敌转移国内不满情绪;(3)阿拉伯基于“平衡对抗”的组织原则;(4)阿拉伯的荣誉观。最后两个因素可能尤为值得关注。
建立在诸如土地和水等自然环境基础上的资源利益冲突固然是重要因素,在世界各地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但鲜有像巴勒斯坦地区如此凸显。此外,阿拉伯各国将国内不满情绪转向以色列也是重要因素,但萌生于部落文化的“平衡对抗”更加深了彼此关系的不和。阿拉伯谚语“我反对我兄弟,我和我兄弟反对我堂兄,我、我兄弟和堂兄反对全世界”正是对“平衡对立”极好的写照。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头几年利比亚的形势为例:1911年意大利入侵利比亚之前,阿拉伯贝都因人正在与土耳其打仗,但意大利出兵土耳其帝国后,贝都因人并未中立或与意大利联手,而是与同为穆斯林的土耳其人一起对抗意大利。与此相同,阿拉伯人会联合其敌人对抗任何非阿拉伯人,更不用说非穆斯林。
在与以色列的冲突中,阿拉伯社会最基本的原则是联合近亲抵抗远族。“对”与“错”经常与“我们”和“他们”相联系。道德标准是一个人必须为有利于自己的集体而战。阿拉伯穆斯林和犹太人的这种对抗正是基于站在伊斯兰一方的“我们”和站在异教徒一方的“他们”之上。由于“他们”“错误”的宗教道德,一种道德力量迫使“我们”开拓神的正确道路,那就是伊斯兰教。对阿拉伯人而言,虽然犹太人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以色列,然而后来阿拉伯人征服了这块土地。正如霍普斯金大学福阿维·阿加米所言:“在现代的外壳下,那里还保留着种族教派和宗派的古老现状”⑩。在这种体系下,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穆斯林和犹太人是无法形成共同利益的。他们缺乏一种来自远方势力不可预期的冲击。在这种对立框架下,没有寻求或发现共同利益及其存在的可能性。
贝都因部落文化的另一核心价值观就是荣誉。贝都因阿拉伯式的荣誉是由战士在抗敌斗争中取胜而形成的。只有胜利才有荣誉。败者被击败得越惨,胜者得到的荣誉就越丰厚。在阿拉伯世界,“胜利从不与节制或同情相伴”(11)。阿拉伯人受到的刻骨铭心的教育就是荣誉比财富、名声、爱、甚至死亡更重要。现代阿拉伯人同样满怀这种意识,却发现自己处在一种无法立足的境地:将近代历史和阿拉伯帝国的繁荣相比,阿拉伯人看到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与挫折。在其中如何寻找荣誉?没有荣誉的阿拉伯人如何寻找自信?在这个充斥失败的世界里,只有反抗才能找到自信。阿拉伯的自尊要求他们不惜代价地起来战斗,去寻找荣誉。正如阿拉伯一家报刊主编塞克赫(Sheikh)所言:“很明显,因为我们总是输给以色列,像它这样一个只有700万人的小国,能打败拥有3亿多人口的阿拉伯民族,这令我们寝食难安。这伤害了我们的尊严,巴勒斯坦问题与我们息息相关。”(12)黎巴嫩诗人克哈里·哈威在其《受伤的闪电》诗中哀叹道:“这是多么深重的羞耻啊!”(13)
基于资源利益的争夺、内部矛盾的对外转移、维护荣誉,以及“平衡对抗”原则,这些因素孕育了阿以冲突和阿拉伯人不屈不挠的拒绝主义。荣誉和对抗这两个部落文化因素才是深刻渗入阿拉伯人国民性格中的历史积淀。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部落文化与国家统治
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独立解放浪潮中独立的大部分阿拉伯国家走上了民主、独立的发展道路,但仍有一些从摩洛哥到伊朗的穆斯林中东国家并非完全实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国家权力集中在统治者手中。(14)这种统治方式与其部落文化有深刻关联。人类学家萨尔兹门(Salzman)指出,历史上曾经有两种方式统治着中东:部落的自治和君王的中央集权制。前者是这个地区的特色,也是理解该地区的关键。(15)基于这一机制,贝都因人靠本部落的长期扩展来保护生命和牲畜免受伤害与劫掠。部落自治推动了中东历史进程。当一个政权摇摇欲坠时,大的部落联合就会形成,族人们离开他们贫瘠的荒地,占领城镇和农业耕地。然而农牧民之间固有的区别也给部落首领们的统治带来了挑战。农民是定居的,他们牢牢地与土地相联系,而牧民和他们的牲畜则一起四处迁移,可以到达很远的地方;农民密切关注那些有河流或灌溉系统完善的水源充足之地,与此相反,牧民则在平民、沙漠等地域上扩张与劫掠;无法脱离农耕的生存方式、固定的播种、收获作息等决定了农民的脆弱性。对于国家统治者而言,农民虽然本身较为脆弱,但对国家却是贡献较大的群体;与之相比,牧民没有农民那么脆弱。他们的主要资产、牲畜和帐篷都是可移动的,而且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牧民们需要不断做出决策,这使他们独立而勇敢,同样,迁徙过程使牧民不像农民那样脆弱和易受人控制。农牧民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区别,使得部落首领们用残暴、专制的方式统治民众。
现代中东国家为了维持统治,获得贡赋,必须对牧民实施有效管理,让牧民成为农民。因为政府无法从牧民那里收税征兵,但可以从农民那里取得。部落问题是国家权力机构在对牧民实行管制中面临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府在解决游牧部落问题时通常以下列两种结果出现:在某些国家,政府通过对部落的严厉镇压而巩固了中央政权。如20世纪20~30年代,伊朗的礼萨汗暴力征服和镇压了包括西北的库尔德人、东南俾路支在内的许多伊朗游牧部落。萨达姆执政时期严厉镇压北部库尔德人部落以加强中央集权(16);另一种方式,像利比亚和海湾地区的一些酋长国,部落归属了政府,部落组织变为管理组织,部落长老不是成为政治领袖,就是成为地区显贵,如海湾国家。于是,一个固定的管理体系就这样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结语
部落文化在当代中东生活中扮演着何种角色?从国家的外部形态而言,部落文化对现代中东社会的影响较为薄弱。毕竟,中东已建立起国家政府机构、官僚制度、警察、法院、军队和政治团体。然而,仅仅从现代组织机构的形式而言,就想当然地认为中东部落生活及其文化作用甚微、甚至不复存在,则过于肤浅和简单化。部落文化在部落形成中有助于创建一个极具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会,但如今它却是一个极大的障碍,阻碍了中东进入现代文明生活。作为部落文化的核心原则“平衡对立”,从积极层面看,部族间的团结让他们可以完全独立于暴力机器的国家之外;从消极层面讲,这暗示了一场无休止的冲突;每一团体都有多个敌人,且这种斗争祖祖辈辈长期存在。族际仇恨的后果牵扯到的远远不止那些直接卷入其中的个人,它们还会造成对社会的破坏和浪费,剥夺个人其他潜在经济利益的取得和社会关系的形成,阻碍个人思维的发展,不利于社会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进程和发展。(17)当前中东诸多冲突和复杂局势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作用的结果,既有现实政治的动因,更有宗教文化、部落文化的历史渊源。中东文化中渗透着部落文化和组织形态,“平衡对立”潜伏在现代中东生活的各个角落。尤其是当前中东国家普遍处于社会转型初期混乱和动荡的大背景下,部落文化的灵魂在并不“现代”的中东社会一再浮现,折射出阿拉伯-伊斯兰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长期冲突和碰撞中的新一轮交锋。(18)
注释:
①参见[美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另参见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②[美国]E·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
③参见纳忠著:《阿拉伯通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页。
④[美国]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上),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2页。
⑤See Marshall Sahlins,"The Segmentary Lineage:An Organization of Predatory Expansion",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63,1961,pp.322-343.
⑥参见[美国]伯纳德·路易斯著;郑之书译:《中东——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77页。
⑦参见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页。
⑧See New York Times,Feb.23,2006.
⑨See Philip Carl Salzman,"The Middle East's Tribab DNA",Middle East Quarterly,Winter,2008,pp.23-33.
⑩Fouad Ajami,The Dream Palace of the Arabs,New York:Vintage,1999,p.155.
(11)Ibid.,p.134.
(12)Pierre Heumann,An Interview with Al-Jazeera Editor-in Chief Ahmed Sheikh,World Police Review,Dec,7,2006.
(13)Fouad Ajami,op.cit.,p.97.
(14)See "2007 Subscores",Freedom in the World,Washington,D.C:Freedom House,2007.
(15)See Daniel Pipes,"The Middle East's Tribal Affliction",http://zh-hans.danielpipes.org/article/5417.
(16)See Hassan Arfa,Under Five Shahs,London:John Murray,1965,pp.253-257.
(17)See David M.Hart,Traditional Society and Feud in the Moroccan Rif,Rabat:Editions La Paste,1997.
(18)参见李伟建:《伊拉克教派冲突背后的宗教文化博弈及对地区形势影响》,载《西亚非洲》,2008年第3期,第48页。
标签:阿拉伯论文; 贝都因人论文; 中东历史论文; 中国伊斯兰教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非洲部落论文; 中东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穆斯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