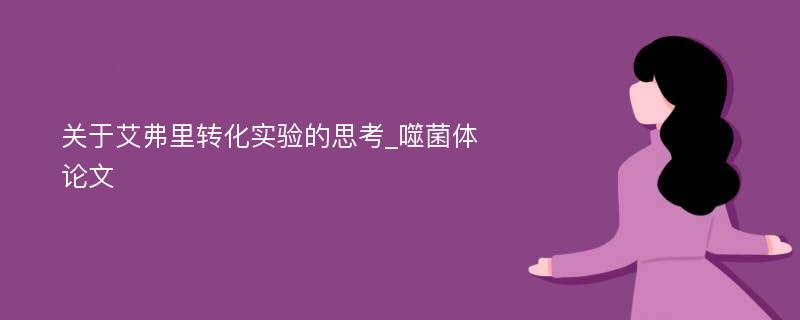
艾弗里转化实验引发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弗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462(2013)03—0031—06
由于“四核苷酸假说”等因素的影响,DNA一度被剥夺了遗传物质的候选资格。在人们向几乎默认为遗传物质的蛋白质投以极大热情的岁月里,DNA在黑暗中孤寂地等待着。格里菲斯不经意间发现的转化现象,给了DNA“重见天日”的机会。艾弗里等人长期致力于肺炎球菌的转化现象研究,无数次的实验终于证实了DNA是引起转化现象的物质而非蛋白质。艾弗里的转化实验结论对“四核苷酸假说”提出了强有力的质疑,更重要的是,他让更多人重新审视DNA作为遗传物质的可能,揭开了20世纪生物学革命的序幕。由于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艾弗里的转化实验结论公布后引起的反响是耐人寻味的,至今仍能引发人们的思考。
1 艾弗里生平及其转化实验
艾弗里1877年10月21日生于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1955年2月20日卒于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他是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卓越的细菌学家和免疫化学的先驱。1887年,10岁的艾弗里随父母由哈利法克斯移居纽约,在当地一所普通中学就读,1893年毕业后进入纽约的科尔盖特学校。1896年艾弗里进入科尔盖特大学,于1900年获文学士学位。在大学期间,艾弗里主修人文科学,也选修一些自然科学课程。他在文学、演说、辩论方面表现非常出色。1900年,艾弗里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学习,那是当时美国最负盛名的医学院。1904年艾弗里获得医学博士学位,随后成为临床外科医师。1907年艾弗里来到位于纽约南部布鲁克林的霍格兰实验室工作,这是美国第一家由私人资助建立的细菌研究机构。他在那里教授课程,并学习实验技能和细菌的生物化学。正是从那时起,艾弗里对致病菌的生理化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13年,艾弗里受邀去往洛克菲勒研究所医学院从事肺炎相关的研究工作。他在这里工作了35年,直到科研生涯结束。1913—1915年艾弗里任医学部助理教授,1915—1919年任副教授,1919—1923年为准成员,1923年转为正式成员,直至1943年退休。退休后的艾弗里成为荣誉成员,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直至1948年。在这里,艾弗里与他优秀的同事们一起对肺炎的致病菌——肺炎球菌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艾弗里1917年曾在美国陆军医疗团服务,后被授予上尉军衔,1918年加入美国籍。1944年他被任命为军队流行病学局成员,两年后退出。1948年他离开纽约,迁居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1955年艾弗里因患肝癌去世,享年78岁。艾弗里一生获得许多荣誉,唯一的令人感到遗憾是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他所获得的主要荣誉如下:美国医师学院约夫菲利普纪念奖章(1932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33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保罗艾利奇金质奖章(1933年),当选美国细菌学家协会会长(1941年),伦敦皇家学会科普利奖章(1945年),美国内科医师协会科伯奖章(1946年),美国公共卫生协会拉斯克奖(1947年),帕斯诺奖(1949年),瑞典医学会巴斯德金质奖章(1950年)[1]。
1923年,英国卫生部的医学官员格里菲斯证实粗糙品系(R品系)和光滑品系(S品系)肺炎球菌均存在一系列类型(Ⅰ,Ⅱ,Ⅲ,Ⅳ等)。R品系是非毒性的,在显微镜下观察菌落粗糙而不规则,S品系有毒性,菌落光滑而有光泽。格里菲斯发现R品系和S品系能够在生物体内和实验室条件下实现对应的相互转变。格里菲斯的发现与艾弗里对毒力的理解相互吻合。艾弗里早年就指出S品系之所以有毒性是因为外部有荚膜包被,而R品系丧失了荚膜包被所以失去了毒性[2]。1928年,格里菲斯同时给小鼠注射两种不同的肺炎球菌,分别是少量的有活性的R品系Ⅱ型菌和大量的热处理灭活后的S品系Ⅲ型菌。注射的结果令人惊奇:许多小鼠死了,并且在死亡小鼠的心脏血液中存在同时具有活性和致病性的S品系菌。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这些新出现的S品系菌,不是Ⅱ型的,而是Ⅲ型的。格里菲斯将这些菌进行连续几代的培养,都只产生了致病性的Ⅲ型菌。并且,用其他类型的肺炎球菌重复上述实验可以得到类似的结果。格里菲斯公布了这一发现[3],引起了人们的猜测和怀疑。
艾弗里起初对格里菲斯的发现表示怀疑[4],他认为是实验控制方面存在问题才导致那样的结果。但是过了不久,格里菲斯的实验结果被德国的弗雷德?纽费尔德(Fred Neufeld)和洛克菲勒研究所的道森(Michael H.Dawson)等人分别证实。1929年道森创造了一种体外实现转化的实验方法。1930年道森离开艾弗里的实验室后,阿洛维(James Lionel Alloway)将他的研究工作更进一步。他将S品系细菌破碎以使其内部成分被释放出来,然后用过滤器将细胞壁碎片连同未被破碎的细胞一同去除。当这种无细胞提取液被加入生长中的R品系细菌的培养基,转化发生了,将酒精加入到提取液中,可观察到糖浆状的固态沉淀物。阿洛维认为在这种无细胞提取液中应该存在一种称为“转化因子”的物质,是它引起肺炎球菌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的转化。艾弗里认识到这种现象不仅仅在细菌学和遗传学上,而且在普通生物学和医学上有深远意义。阿洛维1932年离开了实验室,次年艾弗里的实验室发表1944年那篇里程式文章发表之前有关转化现象的最后一篇论文。1934年麦克劳德加入艾弗里的研究组,继续转化因子的研究。在1934至1937年间,麦克劳德从Ⅱ型光滑菌株转化得到一株可以稳定存在的粗糙品系菌,这株粗糙品系菌日后广泛地用于转化研究。麦克劳德经过努力在转化活性的测定和抽提物的处理技术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由于自感遇到研究瓶颈,1937年他暂停了关于细菌转化的研究。到了1940年,艾弗里与麦克劳德又重新开始了关于转化因子的鉴定研究。同年晚些时候,麦克劳德去往纽约大学任职,1941年麦卡蒂加入实验组,协助艾弗里研究转化因子。他们的初步目标是改进转化活性物质的制备、纯化以及它的活性的定量测定。在开始阶段,艾弗里的实验经常失败。转化试验的重复性差,但是他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并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去完成它。艾弗里和麦卡蒂将S品系突变得到的R品系肺炎球菌培养了30多代,向其中加入高纯度的S品系Ⅲ型DNA,在第二代得到了S品系Ⅲ型的菌,菌落大且生长状况良好。将这些新产生的菌继续培养数代后,其遗传特性保持稳定。掌握了转化的实验技术,艾弗里开始全神贯注解决转化现象是否单独由DNA引起。艾弗里和麦卡蒂对转化因子进行化学分析。他们发现用蛋白酶和脂酶处理无细胞提取物均不能使转化因子失去活性,由此认为转化因子不是蛋白质或者脂类。而且,它也不可能是类似荚膜多糖的糖类,因为糖类不能用酒精来沉淀而转化因子却可以。艾弗里由此认为转化活性物质一定富含核酸。当他们用RNA酶去处理转化活性物质时,仍然不能使其失去转化活性。而用那些降解DNA的酶却可以将转化因子的活性完全破坏。他们测定发现纯化样品与DNA有彼此相当的高分子量,并且对二苯胺反应(检测DNA的化学反应)很灵敏。艾弗里和麦卡蒂得出结论:在肺炎球菌内部引起其发生转化的物质是DNA。
1944年,艾弗里、麦克劳德和麦卡蒂在实验医学杂志(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上发表题为《关于引起肺炎球菌发生转化的物质化学性质的实验研究》的论文,向世人宣布了他们多年来的研究结论:肺炎球菌的转化因子是DNA[5]。虽然他们的发现具有明显的革命性,他们在论文中提出的结论非常谨慎[6]而且给予实验结果几种可能的解释,但还是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批评。大多数的生化和遗传学家仍然相信遗传物质是蛋白质而非核酸。直到1952年,赫尔希和蔡斯用同位素标记的噬菌体侵染实验结果[7]公布于世,人们才最终认定DNA是遗传物质。
2 艾弗里转化实验与格里菲思转化实验的关系
艾弗里实验与格里菲斯实验的对象都是肺炎球菌,研究的也都是转化现象,两者之间有明显的承接关系。艾弗里很早就开始研究肺炎球菌,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针对肺炎球菌发表了系统的研究结论[8],包括荚膜的化学组成、荚膜与毒性的关系、荚膜的结构与肺炎球菌免疫学的关系机理等方面,开拓了用生物化学的手段描述和解决免疫学问题的领域。但是,由于在研究中未曾发现偶然的转化现象,因而不可能将其作为研究目标。格里菲斯是英国卫生部的医学官员,对肺炎球菌并没有系统的研究,他在研究肺炎球菌的毒性时意外发现了转化现象。格里菲斯自己并没有认识到转化现象对于遗传学研究的意义,他对于这个奇怪的“0+0=1”的现象的解释是S品系Ⅱ型的死菌刺激小鼠体内产生免疫物质,这种免疫物质可以激发R品系Ⅰ型菌的毒力,使其转变为S品系Ⅱ型菌。当时,一些免疫化学家推测S品系菌的荚膜多糖导致了转化的发生[9]。不过,很快就证明引起转化的物质既不来自于小鼠体内,也不来自与肺炎球菌的外部,而是来自其内部。艾弗里等人将体内转化发展到体外转化,这是转化实验的一大进步。体外转化实验排除了一系列的干扰因素,能够更加清晰和准确地定位引起转化的物质,并将其称为转化因子。而后,艾弗里等人通过一系列排除实验否定了转化因子是蛋白质、脂类、多糖以及RNA的可能性,并用专一性很强的实验确证转化因子就是DNA。从发现转化现象到鉴定出转化因子的化学本质,前后历时15年,完成了生物学领域具有革命性的一件大事,奠定了分子生物学的基础。艾弗里等人能够在格里菲斯发现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其背后蕴藏地深意,最终取得极其重要的成就,是难能可贵的。两个实验之间很好的承接关系体现了科学研究发展的一般规律。
3 艾弗里转化实验与噬菌体侵染实验的关系
艾弗里实验与噬菌体实验一般被认为是递进关系,即噬菌体实验比艾弗里实验更进一步确证了 DNA是遗传物质。当赫尔希和蔡斯将总结噬菌体侵染实验结果的论文发表在1952年美国的《普通生理学杂志》上并公诸于世后,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为遗传物质的化学本质之争画上了句号。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1944年艾弗里转化实验的结果公布时,尽管已经对结论进行了十分谨慎的处理,但还是遭到一片反对之声。颇有意思的是,赫尔希和蔡斯所在的噬菌体小组也是艾弗里转化实验结论的质疑者。噬菌体小组的领导者德尔布吕克和卢里亚虽然认为艾弗里的实验结果很重要[4]28—32,但由于观念上长期受到“四核苷酸假说”的影响,还是坚持认为无法排除 DNA中有少量蛋白杂质存在的可能性,而这些蛋白可能是真正起作用的物质。这些看起来具有“臆想”特点的看法,当时却占据了主流。噬菌体小组的侵染实验最初几乎是为了证明DNA不是遗传物质,未料到却得到了和艾弗里实验一致的结果。赫尔希和蔡斯用放射性同位素32P和35S分别标记大肠杆菌T2噬菌体的DNA和蛋白质,让T2噬菌体去侵染大肠杆菌,而后进行放射性检测,发现新产生的子代噬菌体都不含35S,却有约30%的32P出现在其中,由此证明遗传物质是DNA而非蛋白质。噬菌体侵染实验采用了同位素示踪技术,较为直观地演示了遗传信息的传递过程,但在分析论证上还是有明显的漏洞[10]。根据实验数据,大约30%的32P出现在子代噬菌体的 DNA中,那么剩下70%去往何处没有合理的解释。同样,只有大约30%的35S留在了大肠杆菌外表面,剩下的35S不知去向。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约有10%的噬菌体蛋白质不含S,因而无法被35S标记,如何证明这些蛋白质没有发挥遗传物质的作用[11]?照此分析,噬菌体实验存在的疑点似乎不比艾弗里实验那不足1%的蛋白杂质小,何况艾弗里后来又改进了纯化方法,将杂质含量降低到不足万分之二,大大增强了结论的说服力。根据上述分析,两个实验之间并不存在递进关系,而应该是并列关系。噬菌体实验只是用一种新方法重新论证了艾弗里实验的结论,在思想上是源于艾弗里实验的。两者受到的截然相反的待遇,主要是缘于1944—1952年间学界对DNA能否作为遗传复制看法的逐渐改变,而不是实验数据的精确性和论证的严密性。
4 艾弗里缘何未获诺贝尔奖
艾弗里等人的文章发表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战争阻碍了国际学术交流。刊登艾弗里文章的实验医学杂志读者范围有限,许多遗传学家和一般的生物学家通常无法看到。而艾弗里的文章大部分都发表在此杂志上,这就使得许多人无法领会到其发现蕴含的深刻意义。但是到了艾弗里去世的时候,1944年的那篇重要论文已经广为流传并被引用了几百次,并被广泛认为意义重大。尽管如此,艾弗里还是没有获得诺贝尔奖,这着实令人深思。当艾弗里等人的文章发表之时,“四核苷酸假说”在核酸研究领域仍占统治地位,影响广泛。遗传学和生物化学领域的权威学者大多坚持认为DNA因不具有化学结构上的复杂性而不可能充当遗传物质,由此产生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即使活性转化物质是 DNA,也很可能只是通过对荚膜的形成有直接的化学效应起作用,并非作为遗传信息的载体而起作用。第二种意见则否认DNA是遗传物质,认为经多次纯化的DNA中可能残留微量蛋白质或其他成分,而后者才是真正的转化因子。第一种意见由于泰勒(H.Taylor)和哈赤基斯(R.D.Hotchkiss)一系列的实验研究,于1949年被彻底否定了。为了否定第二种意见,艾弗里和麦卡蒂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不断地提高样品的纯化程度并采用更加灵敏的手段进行检测,但终究无法彻底说服反对者。第二种否定观点今天看来是有些吹毛求疵的,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还是情有可原。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德国著名的有机化学家,酶学领域的权威威尔斯塔特曾经宣称制得不含蛋白质的酶样品,改变了人们长久以来认为酶的化学本质是蛋白质的看法。但1930年,洛克菲勒研究所的诺斯罗普(John Howard Northrop)成功得到了胃蛋白酶的晶体并证明其化学本质是蛋白质。后来,他又采用精密的测量技术证明威尔斯塔特的实验结果是错误的,而产生错误的原因就是样品中的微量蛋白质污染。由于这个历史原因,艾弗里所在的洛克菲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情不自禁地将艾弗里与威尔斯塔特类比,从而产生了反对意见甚至流言。艾弗里的同事迪博在回忆威尔斯塔特的留言对艾弗里的影响时说:“当时每个人的头脑里都有这个错误观念!”[4]16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连艾弗里本人在对待实验结论的态度上也表现得过于谨慎,他不主张将DNA看作生物普遍的遗传物质,并且指出了样品存在污染的可能性。不过,他在给自己的弟弟,范德比尔特大学的细菌学家罗伊一封长达14页的信中详述了自己的实验并指出“DNA很可能是遗传物质”[4]15-16。可见,从他的内心里还是倾向于相信自己的实验结论的。在1950年召开的孟德尔定律再发现50周年的纪念会上,会上的26位遗传学家仅有米尔斯基(Alfred Ezra Mirsky,1900—1974)在发言中谈到了艾弗里的工作,但他并不是支持其实验结论,而是对转化因子是DNA的观点提出强烈质疑。而著名遗传学家缪勒(H.J.Muller)也在会后指出:“基因的化学结构与作为基因特性的自我复制的功能之间还未建立起联系。[12]”暗示DNA作为遗传物质无法说明基因自我复制的问题,因而无法接受 DNA是遗传物质的结论。据美国著名微生物学家杜博斯(Rene Jule Dubos,1901—1982)所著的艾弗里传记《教授、研究所和DNA》一书[13]记述,艾弗里性格内向稳重,处事小心谨慎,为人低调,很少作自我宣传,这或许也是其研究成果早期未被给予充分重视的原因。但论及艾弗里为何未获诺贝尔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而且是最直接的原因,那便是诺贝尔奖评议委员哈马斯藤(Hammarsten)怀疑艾弗里实验的样品DNA已被蛋白质污染。主要原因是他受基因是蛋白质而DNA仅在基因复制提供结构支撑的观点影响太深,从而无法接受基因是DNA的结论[14]。从解密的诺贝尔奖评选资料来看,从1932年起到艾弗里逝世的1955年,他不仅没有像先前一些观点认为的“未被提名”,相反却是被多次提名,甚至经常连续数年被提名[15]。在他逝世的前几年,未能赶上“末班车”主要是由评奖程序上存在的问题以及运作机制上的缺陷所致。如果艾弗里能够多活几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多年后,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在谈到艾弗里的工作时不得不承认:“艾弗里于1944年关于DNA携带遗传信息的发现代表了遗传学领域中一个最重要的成就,他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是很遗憾的。[16]”艾弗里的转化实验结论没有能够获得诺贝尔奖,令人不禁想起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爱因斯坦的狭义和广义相对论是20世纪物理学乃至整个自然科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极强的革命性。相对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爱因斯坦并没有因此获奖,而是因影响力不及相对论的光电效应而获奖,据说是为了补偿相对论没有获奖的损失。艾弗里和爱因斯坦是同龄人,艾弗里生于1877年,爱因斯坦生于1879年,两人均逝世于1955年。他们的一生都献给了科学事业,直到晚年还在默默地奉献。爱因斯坦的成就主要是在其青年和中年时期取得的,这和许多著名科学家一样。而艾弗里与此有很大的不同,他的成就主要在中年和老年取得,尤其是转化因子的研究成果,更是在67岁的高龄时取得,被公认为科学史上的奇迹。除了年龄的相仿,两者最大的相同之处是,都取得了各自领域的划时代成就。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艾弗里的转化实验结论都具有很强的革命性。相对论冲破了牛顿绝对时空观对物理学思想长达数百年的束缚,直接参与引发了20世纪物理学革命;艾弗里的转化实验证明了遗传物质的化学本质是DNA,纠正了长期以来被信奉为教条的遗传物质是蛋白质的错误观点,引发了20世纪生物学革命,对分子生物学的诞生起到重要的奠基作用。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相对论还是艾弗里转化实验结论都未能获得诺贝尔奖,这其中的原因或有相似之处,但又与各自的背景紧密结合。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相对论没有获诺贝尔奖是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第一大遗憾,那么转化实验没有获诺贝尔奖无疑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第一大遗憾。
5 艾弗里转化实验给我们的启示
艾弗里转化实验是证明DNA是遗传物质的第一个直接证据,实验方法得当,实验数据精确。根据上文分析,艾弗里转化实验的说服力甚至强于后来被公认为“具有最终决定意义”的噬菌体侵染实验。然而,从反响上来看,两者差异甚大。艾弗里实验受到的是广泛而激烈的批评,噬菌体实验却受到热烈的欢迎和拥护。试想两者结果公布的时间互换,会不会使结果也相应互换?我们认为是极有可能的,因为两者结果公布相隔的时间里学界对遗传物质化学本质观点的逐渐改变时造成结果不同的主要因素而非实验本身的设计。艾弗里实验结论受到“委屈”的事实给我们以启示:面对科学新发现,要尽力摆脱固有观念和思维定势,以开放的眼光进行审视。自从布里吉斯(Bridges)在1916年实验证实了基因的物质实体位于染色体上[17],越来越多的生化和遗传学家投入到遗传物质化学本质的研究工作中。1924年,福尔根(Feulgen)用自己发明的染色法证明了DNA是染色体的主要组分之一[18],这更加激发了人们的研究热情。然而,恰在此时,核酸化学权威列文提出了“四核苷酸假说”,通过结构的简单性否定了DNA作为遗传物质的可能。
“四核苷酸假说”很快成为核酸研究领域的规范,上至顶尖科学家,下至一般研究人员普遍将其作为信条,由此造成了DNA遗传学相关研究的长期停滞。即使在列文晚年,DNA已被证明是生物大分子时,“四核苷酸假说”也只是简单修改为四核苷酸单位重复组成的聚合物,和简单的小分子没有本质区别,仍然不可能具有遗传物质必需的多样性。同时,由于当时已知蛋白质由20种氨基酸组成,排列顺序无法计数,具有极大地多样性,又位于染色体上,便自然成为被学界默认的遗传物质,许多人甚至直接开始寻找其自我复制以传递遗传信息的奥秘。艾弗里的转化实验结果公诸于世,本是为广大研究者指明了正确方向,可却被误认为是歧途,这与“四核苷酸假说”的巨大影响力不无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绝大部分学者对于遗传物质的化学本质的看法受固有观念束缚太紧,形成了思维定势。在面对艾弗里转化实验的“惊人”结论时,他们往往先入为主地给予否定结论,而后便是想法去证明否定是正确的。这样对待新的发现,难免会故步自封,扼杀可贵的创造力。即使是一些大牌科学家,被束缚在这个固有观念的怪圈里,也难免看不清事情的真相而错失良机。极少数“识破庐山真面目”的学者由于摆脱了固有观念的束缚,充分认识到了艾弗里实验结论的重大意义。如果不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新事物,就很难产生出新的真知灼见。此外,艾弗里在数十年的研究工作中,兢兢业业,淡泊名利,带着对问题强烈的好奇心去从事科学研究,值得每一个科研工作者学习。在67岁的高龄取得辉煌的成就后,艾弗里的表现很平静,为了将研究进行到底,他毅然成为洛克菲勒研究所得荣誉成员,继续参加相关课题的研究。这种持之以恒的宝贵精神不正是许多取得重大成就的人所共有的吗?艾弗里和他的转化实验永远是人类精神的宝藏,值得人们去认真发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