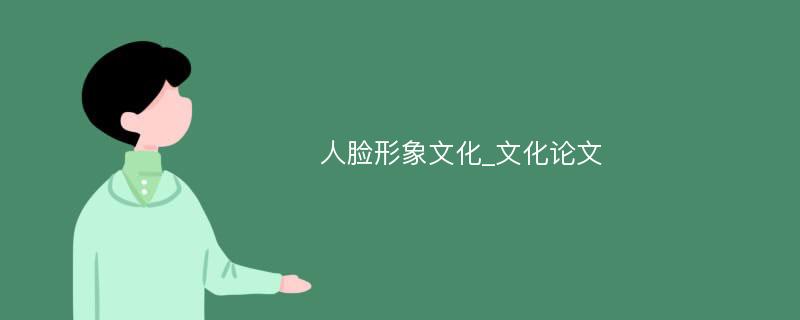
面对图像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像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当代社会正由文字文化向图像文化转变,以摄影、电影、电视、多媒体为代表的新科技正孕育着一场新的视觉革命,对图像文化、视觉革命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并加以认真研究。本文只是对图像文化的粗线条描述,许多问题尚待展开。
Summary
Modern world is changing from words to graphics.Newtechnology represented by photos,films,TV and multi- media isbringing about new visual revolution.It is important to studygraphics and itsissues.
世纪之交的文化艺术现象纷纭繁杂、瞬息万变。正像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那样。在我们的研究工作由宏观领域进入微观领域时,会遇到一个矛盾:我们的观测仪器是宏观的,可是研究对象却是微观的。宏观仪器必然对微观粒子产生干扰,这种干扰本身又对我们的认识产生干扰。用任何一种理论都无法对待当今出现的图像文化,当代的商品求新求异,并且是不保值的,当今的图像同样如此,犹如精美时装店中的时装,不断更换,眼花缭乱……。当今我们文化人处的地位同样是如此的困惑与尴尬,有点象盲人想知道雪花的形状和构造,雪花一碰到他的手指或舌头就迅速溶化了。但人类充满着好奇与探求的欲望,明知雪花会溶化,却仍然不断地用手指去摸,用舌头去舔……。
一)谈到图像文化不得不提到本雅明,本雅明认为现代社会正处于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期,由手工劳动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这个转变也使与手工劳动社会相对应的以叙事艺术为主的古典艺术走向终结。本雅明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的这个重大历史转变,具体表现在人的传播方式的变化上。手工劳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主要传播方式是叙说,与之对应的是以叙事性为主的古典艺术。而现代信息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方式则由叙说变成了信息,与之对应的则是以机械复制为特点的艺术,如摄影艺术、电影等等。本雅明的奠定著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揭示了图像文化的来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认为机械复制艺术,特别是摄影、电影丰富了我们的视觉世界,展示了我们日常视觉未察觉到的东西。“电影摄影机借助一些辅助手段,例如通过下降和提升,通过分割和孤立处理,通过对过程的延长和收缩,通过放大和缩小,便能达到那些肉眼察觉不到的运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第11节)并且认为整个传统艺术是以对物和世界的韵味经验为前提的,而机械复制艺术则主要以技术复制手段进行大量复制的艺术。“机械复制的艺术品越来越广泛地成了对为可复制而设计之艺术品的复制,如人们可以用一张照相底片复制任意数量的相片,而要鉴别其中哪张是‘真品’。则是毫无意义的”。(同上)本雅明的高明是他把艺术的演变放在科技发展的背景中来论述,积极推崇由艺术生产力的发展所导致的艺术革命。随着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证明本雅明的论述是对的。本雅明之后的麦克卢汉讲过一句名言:“媒体即信息”。其基本含义是文化内容要受到交流方式的制约,什么样的传播手段承载什么样的信息。事实确是如此,信息对于媒体有它的依附性,传播媒体不同,确会使传播内容产生极大的弹性。众所周知,文字与图像,静止的图像与动态的图像对于接受者来说显然是不同的。媒体不一样,同样的信息内容会有不同的状态。特别是电视的出现,使得图像文化更为普及。当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更把图像文化推到了前台。计算机的发展从另方面强化了图像文化。尤其是多媒体电脑将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管是图片族还是多媒体族的出现决不能仅仅把它视为只是科学技术的革命,实际上它将预示着整个文化艺术的革命。
二)以电视为代表的图像文化正迅速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中国在迈向商品社会的进程中,电视与图像文化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溢出所有艺术,灌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行为准则,甚至举止言谈衣着打扮。在当代文化的研究中,应该把图像文化凸现出来,作为一个大题目,认真的加以研究。
三)众所周知,文字文化与图像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人们用文字进行思考时常把对象从整体的具体的事物中割取出来,从变化的动态中固定下来,使无限变成有限,使过程变成片段,使具体变成一般,它抛弃了对象存在的丰富性与运动的多变性,语言文字抽象的结果使符号实物之间发生了错动,产生了假言现象。而图像文化是直观的,瞬间的,有人称之为“短路符号系统”,因为图像文化与它所指的那个事物现象几乎是重叠的,能指和所指是重叠的。当代科学证明,图像文化极有利于开发人的右半脑。视知觉语言和直觉观照是文字语言和分析思维的平行物这一观念到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罗杰·斯伯尼对人脑认识功能双轨系统作用的发现才从根本上得到认识。如果说人类寻找失落的感觉的努力需要什么方式的话,那么图像文化的发展就是最好的途径。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马尔库塞早就想用新感性来重建世界,他的理想是通过对新感性的造就,重建一个新的世界。实在讲,图像文化是与文字文化平行不悖的两种文化,谁也离不开谁。但是图像文化的出现与发展是商业社会发展的必然,它广泛地缓解了社会的深层焦虑,稳定了已经开始动摇的主流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释义与解释的重负,从轻松的感性层面上冲淡了沉重的理性思维。生动直观、色彩丰富、图像逼真的画面成为当代人视知觉的关注与注意中心。正如马尔库塞所说:“艺术只有作为艺术,只有以其破除日常语言、或作为‘世界的诗文’这种它自身的语言和图像,才能表达其激进的潜能。艺术解放的‘信息’还超越着解放中可以达到的具体目标,就像它超越着对社会的具体的批判一样。”(转引自《纷花怒放》)应该承认图像文化在轻松感官,愉悦感官,冲击我们的视知觉方面是文字文化无法替代的。
四)苏姗·桑塔格曾经提出过“反对解释”,主张用各种感官而不是释义去感受艺术品,并主张用对“艺术的性爱”取代对艺术的解释,这无疑是快感具有积极意义的论点。艺术讲到底是生命的体悟,感性力量的发挥。可是长期以来我们把艺术的主要功能淡化了。以图像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绘画为例,我们面对一幅绘画作品首先不是相信自己的感官直觉,而是发问:“它是什么?”这幅绘画作品的意思是什么,“什么”不是指作品内在的绘画语言本身,而是指作品的造型内容所指称的外部世界的意义。绘画作品往往被赋予外指的文字意义,却恰恰忽略了绘画艺术的根本的形式构成语言。有人把以追问外指意义为目的的解读方式称为“语义向心主义”。实际上是文字语言长期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积淀产物。在面对丰富、生动、具体、五光十色的艺术作品时,越来越失去了人们原本就具有的灵敏的感官系统。所以以第五代电影导演拍摄的《黄土地》作为中国视觉艺术的革命。《黄土地》通过视角的变换,色彩的配置,画面的构图,动态的图像,用图像本身来述说一个古老的故事。难怪当时许多人看不懂,不理解。因为用文字很难去解释。当今出现的许多艺术现象,尤其以图像文化为表征的艺术常常难以释义,许多画面精致、节奏很快、色彩艳丽的MTV,对人们的视知觉冲击力是无法否定的,人们从中获得的快感也是无法言说的。应该承认“快感”是人们正常生理心理反应,快感历来存在,但历来对快感有不同的认识。应该说,弗里德里克·杰姆逊有关快感的论述更为合理,他既反对毫无束缚的快感说,也反对对快感的全盘否定。与古典艺术过于强调的“升华”相比,应该承认,快感的确更具有某种当下的渲泄解放作用,它使人们审美自由得以从解释、地位、政治、经济和其它因素中挣脱出来,它只以感官为唯一标准,以“过瘾”的形式来体验艺术的真谛。尤其在商品社会,紧张的工作之余,图像文化作为调剂人们身心的艺术形式是应该肯定的。
五)在当代大众文化中,由于图像在现代传播手段中日益成为主要媒介,因此对各种“图”与“像”进行认真的分析与研究就变得十分必要。在图像文化中,女性视像的普遍存在已成为一个敏感的问题。看与被看是两性文化的基本构架。而在两性文化中,“性”与“文化”又是两个重要元素,它们彼此渗透,相互影响。而当代文化中女性视像的广泛存在确实与当代男权主义文化结构有关,是以男权中心为原则的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的结果。它不仅表现为“主从”的关系而且在艺术上表现为“看”与“被看”的关系。同时还必须承认:“从18世纪以来一直贯乎历史主脉的情感解放思潮。感性、肉体、情欲、生命等等,成了这一思潮中对传统道德体系最直接,最强有力的颠覆力量,‘性’在这其中,更是担当着一个首当其冲的先锋角色……她们作为整个男权文化所认可的性角色,以及其形体所显示的特有的自然感性美,实际上已担负着一种否定原罪观念,重估一切价值,向传统和理性挑战,恢复生命存在的本体地位的崇高历史使命。她们用自己整个的肉体生命作了这一时代意识的神圣祭品。”(引自《美学与两性文化》)
六)“性”在当代图像文化中是一个无法避讳的问题。“性”与文明的进程有关,“性”在不同的国度与民族民俗中又有极为不同的表现。如何在图像文化中把握好它的尺度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应该承认“性”在图像中的表现不仅是一个技术技法的问题,更应该从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乃至美学、艺术等方方面面去考虑,去研究。当然应该考虑它的负面效应,实际上过分的泛滥必然会出现信息的递减效应。但是应该承认“性”在图像中的表现具有心理学与生理学的依据。
七)在图像文化中,与“性”同样敏感的是“动作”,或称为“打斗”。图像文化实则也是商业文化,大众文化。图像文化中的许多动作片(当然动作片中仍有某种意义,给人以教益)恰恰不愿意走上因“理解”而放弃“奇观”。它们无须以“理解”为基石,但它们却是对荒诞世界的荒诞呈现。应该承认“社会,历史及艺术中一场又一场的革命和变迁,使艺术家们再也没有固定的艺术标准可资遵循,在种种主义和流派使已经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复杂化了的心灵更加更杂之后,艺术家们发现自己总是单身一人面对无数个声音和画面的鼓噪和诱惑。他们再也难以像从前的先辈一样自信而明确地回答自己和告诉别人:“什么是艺术?”,“艺术的过程是怎么样?”(引自《纷花怒放》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宽一些,应该承认当代图像文化中的许多“奇观”如果没有九十年代高科技的支持是无法实现的。或者讲得更绝对一点,它完全是与现代高科技手段紧密相关的,某种程度上就是现代高科技本身的展示。
八)对图象文化的“读解”和“体悟”需要长时间的学习与实践。由于种种原因,在我国并没有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我们的教育仍然以文字、理性、逻辑为主。由于图像教育的断层造成领悟图像的困难,反过来又使图像教育陷入困境。图像作为一种文化当然有它特殊的语言。从文字文化进入到图像文化,许多人准备不足,大家还是以文字的抽象语言来对待图像,还是以抽象思维来对待形象思维。我们常常可以在许多故事片或电视剧中看到如下现象:①用变焦来代替摄影机的推拉;②用望远镜头吊的近景来代替摄影机靠近被摄体获得的近景;③用全堂亮的光效来代替立体空间的具体光源的照明;④用演员站在话筒前念台词的后期配音来代替同期录音;⑤用随意变换的声音前后关系来代替立体空间的声音关系。⑥用录音棚的声音来代替空间的混响,混响当虚的来用。正如周传基先生正确指出的:“这是技巧使用不当吗?我们从这六种技巧的用法所造成的效果来看,它们就变成了:平面+平面+平面+平面+平面+平面!”,显而易见,这是线性思维的观念,这是人们长期使用的习惯语言,长期进行的文字训练导致的结果。图像文化首先是视听四维语言思维的文化。按照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体即信息”。媒体发生变化,传递信息当然会发生变化。遗憾的是我们对当代正在发生的媒体革命重视不够,还停留在文字叙事层面上,不太重视“如何拍”、“如何画”、“如何设计”,忽视媒体的特殊的表现手段。(顺便提一句,国外艺术院校将“材料课”作为表现肌理效果的重要必修课,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媒体的应用)应该指出人类的信息传递除了自然语言(讲话),文字语言(书写)以外还有大量的表情语言,体态语言,装饰语言等等。平心而论,我们对这些语言还相当陌生,更缺泛必要的认真的研究。当代媒体革命所引发的技巧又常常在传递文字语言无法言说的信息,它的直捷性,具像性,丰富性,多变性,动态性日新月异,不断发展,更是与文字语言无法比拟的。更为困难的是图像文化传递的信息只要经过人的主观思维加之以意识又配以动机再加上不同民族民俗的差异,那么就会在这个层次上变成无数的“信息”。人们所看到的不仅依赖于他看什么,而且也依赖于他以前的视觉概念的经验教会他去看什么。
九)从文字文化走向图像文化的重要环节就是对美术概念的理解。应该指出,在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纯美术与社会大美术(设计)是相辅相成的,是一种同步反馈机制。对纯美术中的形式分析,色彩分析,构成分析越深刻,则越能促进社会大美术的发展,越有利于图像文化的发展。国外发达国家已经提供了这方面的有益经验。许多欧美国家似乎更强调美术的社会实用价值,他们在发展纯美术的同时,更加注意艺术设计,更加重视设计教育。他们把美术作为一项工程来对待,他们常常把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美术、电影电视美术以及现代工业设计等作综合的系统的考察。他们对美术教育的基本原则是延伸了“包豪斯”的传统,强调艺术的整体观念,强调艺术的制作与绘画性同步训练。即使在中小学乃至大学仍然十分重视美术修养的训练与教育。许多大学把艺术史、电影电视编入课程也并非是要培养未来艺术家或影视制作者,而是让他们充分了解并熟悉当代新的图像文化,新的四维视听语言,更好地开发人类的右半脑,更好地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设计与设计教育是提高图像文化整体水平的极为重要的环节。设计新概念已经超越政治、经济、社会,成为全球性的人类造物活动。
十)图像文化的出现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需要我们认真的加以研究。当代画家D·萨勒有一幅《瓦解压皱的一片》,以艺术形象再现了当代图像文化的杂乱性和无章可循性。该作品由两个被挤压在一起的意象群构成,左边是一组奇怪的略具花型的抽象结构支架;右边画了一个粗俗的裸体,然后在其上画了一个更粗俗的卡通图形;最后他补上了一些抽象的近乎椭园形的图案。人们要想在画中找寻正常的叙事关系十分困难,类似达达、波普的拼贴画,正如莫道夫分析的:“此画在意象结构上,故意杂乱无章,使观画者为之困惑不已。……此画又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在大家疯狂进步,变了又变的生活里,我们所了解的意象,也是横遭砍切,压平挤扁的,我们的文化正如此画,也成了被‘瓦解压皱的一片’”。(转引自《扑朔迷离的游戏》)莫道夫的结论是:“我们目前的时代”是由支离破碎的片断“组成的”。我们已远离本真的世界,世界已由图像符号组成,我们通过电影、电视、录像、图片、广告等大众传媒的过滤,接收到的是一个被解体、并置、杂乱的图像世界。在电视上前一个图像是香水广告,接着报道在世界某地发生地震,时间的连续发展遭到切断。每天各种五光十色的图像冲击着我们的视觉感官。大众传媒中以图像文化为主要特征的视觉化倾向和泛视觉化倾向对社会性格的引导作用尤为重要。由于大众传媒造成人际交往的扩大,使人们受他人的影响增大直到左右着每个人的人格发展。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把当代美国社会称作“一个充满形象的社会”。他认为这是一个没有根,浮于表面的感觉,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一个特征。电视作为图像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在不知不觉地引导着人们社会性格的形成。
国内外一些对图像文化中,在电影、电视中出现负面效应表示忧虑的学者们创造了“视觉污染”这个新词。因为过份毫无节制的图像泛滥将破坏自然环境而大煞风景……。它确实指出了当今图像文化中的负面效应,应该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
十一)贝尔在分析了后现代以视觉美学为表征的文化特征后,对其文化混杂倾向和所谓“反文化”的偏激冲动表示出深切的忧虑。他认为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而后现代社会中人们具有的两种体验世界方式:外部世界的迅速变化导致人在空间感和时间感方面的错乱,而宗教信仰的泯灭,超生希望的失落,以及关于人生有限,死后万事空的新意识铸成自我意识的危机。后现代艺术的冲动原是想超越这些苦恼:超越自然,超越文化,超越悲剧去开拓无限。可惜它的动力仅仅出自激进自我的无穷发展精神,因此,当它以破碎的艺术拼贴的图像去对抗破碎的世界时,就已注定它最终无法将心灵的碎片重新聚合起来。这样,人们走到了一个生命意义匮乏的“空白荒地的边缘”。因此贝尔的结论是重建人类新的宗教或文化科学。当然贝尔的新宗教似乎并不能解决后现代文化的失落以及图像文化飞速的发展。但它的分析仍可引起我们的注意。图像文化似乎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即“性”,“快”,“感”。“快”,“性”,“感”,“感”“性”,“快”三个字任意组合、排列,仍不失对图像文化的描述。正如有学者明确指出的那样如昆德拉所说的:人处在一个真正的缩减的旋涡之中。爱情缩减为性;友谊缩减为交际、公关;读书思考缩减为看电视;大自然缩减为豪华宾馆,室内风景;对土地的依恋缩减为旅游业;真正的精神冒险缩减为假冒险的游乐设施;一切精神价值都缩减成了实用价值;永恒的怀念和追求缩减成了当下官能享受;文化缩减成了大众传播媒介……一句话,生活变成了图像,重变成了轻。难怪昆德拉的一本小说的书名极富象征意味——《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对此,当今出现了“茧居”一词,“茧居”的定义是:我们渴望寻找一个安全的壳或城堡来保护自己,以使我们不再受外在各种低劣视像、信息噪音的污染,与此同时“回归大自然”的呼声此起彼伏。所谓的“绿色设计”“生态设计”等等成为设计中新的热点。
十二)有一则新闻报道传递了这样一条信息:我国著名心内科专家曾昭耆教授最近撰文指出,现在外国有许多医生主要靠仪器看病,看仪器上显示的图像,很少动脑筋思考。许多人对自己的直观检查产生了怀疑却依赖于仪器与图像。当然这样说不是否定现代设备图像的积极作用,但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临床观察,分析思考、正确判断、用自己手、眼与脑的能力。曾教授实际上同样道出了对当今一切都图像化了、符号化了的世界表示的关切。人必须找回失落的自我,充分相信自我的能力,自我的本真。就“图像”而言,我们首先必须认清图像的“真面目”。历来对“图像”的认识经历了表现的,摹仿的和后现代的诸种对待图像理论的态度。表现的图像理论的核心论点是,摄影机实际上并不再现现实,而毋宁说是生成或结构现实。现实并不存在于经验论者所谓的客观性之中,而是话语的产物,摄影艺术只是对现实的译解而非记录。这种译解制造出对现实的看法——它是意识形态的;因此,被再现的不是现实,而是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煽情效果被摄影之肖似性加强了。摹仿论则依据这样一种假定:一个影像是,或者至少应该是,它的被摄对象的映像。这种假定建立于一种有关透明性的隐喻基础上,即把摄影机镜头建构为可以由之观察世界的窗口。然而由于这个魔术般的窗口能够广泛记录和传播我们从中所见之物的视像,它颠到了视像与其对象之间真实的,或者说逻辑上正确的关系:它使得视像比其对象更为重要。这种情形的结果,是一个完整的“影象操纵”工业(即所谓文化工业——图像文化工业)迅速发展——它只盯着视像的再生产和传播,这种视像的“真实性”常常被那种为视像效果而搬演现实的实践直接颠覆。这样的“非真实化”实践使得处于视像文化中的人们更加难以在视像和(它的)原对象之间作出区分。后现代主义理论认为:“视像与现实并无不同的本体论身份。他们不相信“原本”,既然“原本”不再存在,也就无所谓摹本了”(德里达语)。实际上他们并非彻底否定原本、对象的存在。他所要用他们的解构主义对原本与摹本(现实与视像)的二元对立的等级结构实施解构。确定广义的摹本概念——一种包括原本于自身之内的摹本,它既是摹本又是原本,本质上是一种差异。应该说,关于视像的三种观点都在某些方面把握到了视像的某些意义,但他们的共同点仅把着眼点落在作为对象的视象一方面,不同程度地忽视了视像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接受的一方,因为接爱一方具有自主的能动性。约翰·菲斯克博士在《具体现实的视像》一文中认为接受者既非消极被动地任凭表现论者所言强加某种意识形态意义,但又非只消费视像本身而拒斥消费意义。菲斯克博士认为,在媒介工业生产的视像和消费视像的大众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性关系,一种并合和离折的关系。视像意义的产生与大众在社会历史背景中的特定处境及他们生活在其中的日常生活情境密切相关。意义是动态的,它会生成和创造,并且视像是大众文化和商业文化交互建构的产物,是一种本文/文化实践的力场。实际上菲斯克博士的观点类似于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观点,认识是一种建构活动。菲斯克提出了被以上三种理论忽视的地方,强调视像意义生成过程中大众的能动性所带来的积极作用,当今许多学者都指出图像制作者与接受者个性的差异性以及文化背景的多样性与差异性都会影响图像本身,这些观点无疑具有建设性的启示,对我们认识“图像文化”的“真面目”提供了多方面的视角。
十三)图像与现实,视像与本真世界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图像作为一种语言,当然也有其自身的话语系统,并且应该是逐步为接受者可识别、可理解。世界在变化,当然图像也在变化,作为一种文化,必须是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正如赫伯特·里德在《现代绘画简史》中所说,整个艺术史,是一部视觉不断变更,视觉方式不断发展的历史。任何静态的描述都是徒劳的。现代系统论提示我们,只有把现实、图像与图像的制作者与接受者作为系统的、动态的不断反馈的网络结构来分析,才能比较好地把握它发展的走向与内在机制。要用有机的对待生命现象的复杂性,动态性,整体性来对待不断发展着的图像文化,才能比较清楚地廓清图像文化的真面貌。皮亚杰有关“图式”,“同化”,“顺应”的理论对于理解图像文化颇有一点启发意义。皮亚杰的“图式”是一个对外界信息的接收器,加工器。图式在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发展。皮亚杰将这种图式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称为“建构”。图像文化中的“图像”在不断改变着我们的“图式”,同样我们也在不断地“建构”着“图像”。“图像”与“图式”是相辅相承、相互反馈、不断发展的——不断“建构”的。
与其说我们在述说图像,不如说我们在拼贴图像。拼贴的图像与图像的拼贴已介入、包围、构造着人们的生活,同时也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无论你愿意与否,赞成与否,它已无可挽回地侵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正也,图像;负也,图像;喜也,图像;骂也,图像。正确的态度是认真地对待它。我们既要面对历史条件所形成的历史性格,又要面对当前历史条件所形成的处境,更要面对现代图像文化隐藏的操纵本质,从而积极寻找对策,寻找在图像文化日益泛滥下复兴人的自主性、批判性与创造性……我们只能面对,不能拒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