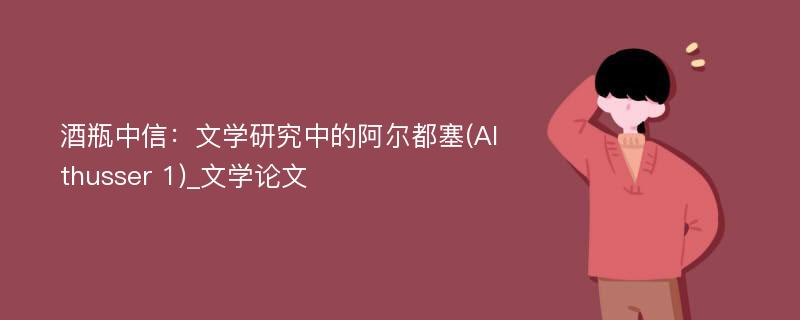
瓶中信:文学研究中的阿尔都塞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尔论文,瓶中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据说,路易·阿尔都塞在谈到国际性的“阿尔都塞主义”现象时,曾经伤感地说:写书就像发送储在瓶中的信息,你根本没法知道你说的话会被谁碰上,又会被他们用作什么意义。
在阿尔都塞比较关注的文学研究领域,这些信息很快就被人们发现和阅读。经验(一个最近略带宿命感的词)是让人气馁的,但也有让人兴高采烈之处:对于许多人来说,它似乎是让人感觉获得解放的重要时刻。但是,就像其他所有的时刻一样,它也只是一个开始,在经历将近30年的注释和说明之后,它的意义似乎显得越发含混和难以捉摸,已不像它当时曾经显现的那样简单了。②
阿尔都塞提出的“保卫马克思”这一理论,既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也涉及它的地位。③ 他强调,马克思的革命留给后世的不只是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这种新理论抛弃了旧哲学假定的表现主义,而代之以一种本来就很复杂的社会整体观念: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实存机构(instances)在其中是“相对独立的”“有各自效能的”,且“归根结底”是受经济决定的。在这种概念图式中,“决定”一词的含义也是很复杂的,既不指单个的(singular),也不只是指复数的(plural),可以说,它的运作是非常特殊的。任何一种矛盾总体上是由构成其存在条件的多个矛盾从内部标示出来的(internally marked),处于各种不能简约的“多重决定(overdetermination)”④ 状态和过程当中。一个复杂的整体以及同样复杂的时间——心目中的历史,不能依照单一的、规范的节拍前进;相反,历史必须被看作一种具“差异的(differential)”暂存性(temporality),会出现由那些独特事态(conjunctures)所构成的无节奏的连续性。
对于阿尔都塞来说,在历史唯物主义彻底摆脱了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之后,以上这些观念都是构成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要素。针对历史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一种解中心的(decentred)、非表现的过程;针对人道主义,它强调结构和实践先于诸多具体的个体而存在,而之前个体一直被精心设想为他们自己的承载者(bearer),在这两个方面,它与那种将“主体”看作历史创造者和源头的哲学思想框架产生了根本的决裂。“主体”这一范畴在阿尔都塞为历史唯物主义领域所做的最主要的独到研究——全力探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当中起着关键作用。这一术语及其相关意义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引领了一种不符常规的、雄辩机智的做派;在阿尔都塞的思想中,它承担了一个永恒的、压倒一切的角色。意识形态在此是一种相对自足的(autonomous)实践,它的首要作用是确保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其被普遍接受的诸如错觉、神秘化、虚假意识以及被精神化的趣味(interest)等观念,均无法传达出这一概念实际存在的影响。不是主体们在工作,而是意识形态在使他们工作,是意识形态将那些被称为“主体”的社会个体“询唤”为将自己看作社会行为人的各种身份认同(identities)。这些身份认同与真实状态维持着一种“想象的”关系,而且无论是在现在还是将来,这对人类都是不可或缺的:在任何情况下生活都是在意识形态当中生活。
严格来说,知识应该是科学的知识,是对各种混杂的经验材料——意识形态——进行非主观主义的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这是阿尔都塞在探讨马克思的开创地位时提出的一项补充声明,也是他进行的理论干预的第二个方面。作为一门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将自己建基于同意识形态的决裂之上,它建构的理论对象、进行的精心分析,都应该取决于理论实践自身的标准,而不应受经验世界(意识形态)的暗示所支配。
阿尔都塞对于理论实践的期待可能有些过高了,在某些重要方面的确如此。类似于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他的证伪主义具有一定的可比性,阿尔都塞不但给科学授予了独有的认识特权,而且赋予了英雄主义的同情。因此,毫无奇怪,这就容易引起人们对新实证主义和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怀疑。但是,尽管阿尔都塞的写作中出现过马克思主义必胜论的主题,但他所说的“回到马克思”并不是要从知识上返回到党派。他对于科学完整性的强调,并不包含排斥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他不是在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领域来讨论马克思的科学,而是在各种研究人的科学(human sciences),尤其是新“四艺”——历史学、文化人类学(ethnology)、精神分析学和语言学⑤ ——以及它们的混合物——“结构主义”当中思考。⑥ 在这里,对于科学性的追求,意味着要抛弃学术上的闭关自守。
对于英国从事文学研究的左派来说,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的普遍主题和指向本身就足以带来强大的吸引力,因为在英国左派当中根深蒂固地保持着知识非法性(intellectual illegitimacy)的观念。他们从经典著作中继承了普遍理论的大纲和一些著名的思想片断,后者涉及古典艺术或巴尔扎克小说和戏剧当中的政治和现实主义。第二国际的那些伟大的体系化论者,不论他们每个人的文化特征如何,都倾向于将艺术看成一个可用来测试他们一般阐述的各种主张的重要例证。他们将艺术带回到现实当中,但以后就置之不理了。以列宁和托洛茨基而闻名的布尔什维克一代,发现了意识形态介入文学生活的种种机会,但也没有写出可适用于各种通用目标的观点。1930年代,以艾里克斯·威斯特(Alick West)和拉尔夫·福克斯(Ralph Fox),尤其是克里斯托夫·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也处在集体的困窘状态。⑦ 它的诸多直接继承者在人们熟悉的“文学—学术”程序当中倡导一种非强制性的共产主义变体。雷蒙·威廉斯的漫长革命所能扩及的最终范围,依然没有受到重视。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的著作为当代思想提供了无法避开的参照点,他的继承者卢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随后也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这两位思想家提供的观点成了分析遵循的思想路线,尽管这些思想相当深刻而有力,但在对待历史和文本时,尤其在卢卡奇那声名狼藉的分析实例中,就会无可救药地陷入图解化,同时容易滑向美学教条主义。与此同时,尽管法兰克福学派,或者说当时英国所理解的法兰克福学派,提供了一种更丰富、更现代的学术(intellectual)文化,但这也免除不了人们对于总体化建构的普遍怀疑。人们尽管可以彻底地学习、认真地实践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新样式,但却不可能平息主流传统的内在指责,后者一直倡导要忠实于文本的经验记录和详尽生活。⑧
之后出现了阿尔都塞(《矛盾和多重决定》一文1967年出现在英国;完整的《保卫马克思》出现于1969年;《读〈资本论〉》出现于1970年),这预示着一个新的开端。得益于这些新的历史概念,那些明显扎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当中的种种决定论和图解化倾向,可以用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来批判和克服。对于意识形态的新理解,及其对“经验”所做的至关重要的重新评价,扰乱了主流批评传统的第一指导原则。如果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和自由—人道主义的“经验主义”所带有的种种错误,就有可能,也有必要提出一种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作为不可简约的社会实践的艺术概念,设想一种有明确具体对象的合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阿尔都塞本人对艺术的兴趣激发他写下了两篇令人注目的偶发性文章:一篇讨论在巴黎上演的由乔尔焦·斯特雷勒(Giorgio Strehler)导演的话剧《我们的米兰》(El Nost Milan)⑨;另一篇讨论西班牙画家莱昂纳多·克勒莫尼尼(Leonardo Cremonini)的绘画。⑩ 这些文章超出了对具体对象的讨论,显示出阿尔都塞对于理论和方法等普遍性问题的敏锐觉察。两篇文章都把物质事件(戏剧和画布)和事件显示实践放在分析的第一位。文章虽然也提到了这些实践的“主体”(作家,导演,画家,观众),但却替换了他们:对于克拉莫尼尼画布的阅读并不受画家主观意图的迹象所限制;布莱希特对于移情(共鸣)戏剧的责难,显示出对观众反应的非心理学的(nonpsychologistic)理解。此外,这两篇文章被看作是与批评“烹饪术”(gastronomy)的论战,后者已经成了阻挠批评成为知识的障碍。
但是,这两篇文章不能被当作这样一种批评的引领者。阿尔都塞之所以要抓住由斯特雷勒执导的贝尔多拉西(Carlo Bertolazzi)(11) 的剧作不放,是因为该剧奇异的双重节奏戏剧化地表现了阿氏自己对于意识形态的某种相似的理解。克勒莫尼尼所用的垂直线和圆圈之所以让阿尔都塞感到兴奋,是因为他从这些图线中看到了他自己反人道主义的思想形态。这两篇文章好像反意识形态“认可(recognition)”(一个不可缺少的词)的一些瞬间,但更多是对感受瞬间进行的令人陶醉的阐述,而不是对于勾画一种新理论或实践的指导。
然而,阿尔都塞唯一一篇论及美学的纲领性说明——《给安德烈·达斯普尔(André Daspre)的信》,显示出他赞同将理论详述和美学偏爱合并起来的努力。阿尔都塞的目标是获得“真正的艺术知识”;他的意思是对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进行严密反思”——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道路”。他想在此阐明他的“第一观念”:艺术在范畴上有别于科学,它不生产严格意义上的知识。然而它并不是一种中立的意识形态方式。因为艺术与知识保持着一种特异的关系,它能“使我们看到”它所“暗指”的“真实”,这是由于艺术在意识形态内部建立了一种“内在的距离”。当然,他在这里说的是“真正的艺术,而不是那些平常的、中不溜的作品”(12)。如果这是对新理论的诉求,那么这条思路似乎又是循环的。确立“第一观念”通常都是非常棘手的(阿尔都塞提到过在已接受的成语中进行创新的艰难斗争),但阿氏的这个“第一观念”似乎又太过确定了。艺术在范畴上不同于科学,它扎根于日常语言当中,但却具有特许的洞见。实际上,美学作为对艺术伟大性的阐释,不是一种具体实践的知识而是一种详尽的辨别协定——这些已成为文学学术的老生常谈。在这一点上,我们很难看到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反思(在这个场合并不鼓励它与其他批判性的知识相互交流)能够将它们转变为科学。
在给达斯普尔的信中,阿尔都塞声明,他的谈话背景源于他年轻的合作者皮埃尔·马歇雷(Pierre Macherey)的著作,后者所写的《文学生产理论》(出版在同年,即1966年)在文学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做出了开创性的表述。马歇雷的著作是双重意义上的形态学研究。它首先关注的是确定已有文学批评——及其意图形式——的特有形态,然后推断出有可比性的、科学的替代草案。在详述了这一科学的基本论题之后,呈现的主题就是处于意识形态当中的文学形式的活动。在他看来,已有的批评似乎扮演着在文学“领域”调节写作和阅读之间关系的角色。作为一种“规范的”实践,这种批评裁定了可资比较的成就;作为“阐释”,它试图去裁决和调停意义。在这两种方式当中,批评都在继续干着骗人的勾当,实际上在用幻想的他者——作品中似乎有过或者在“完满的”意义上会有——来“代替”它宣称要分析的东西。相反,科学的批评将是一种知识话语,是对这一理论上特定的对象—作为在意识形态当中有明确限定的物质实践活动的文学“生产”——的“种种规则”进行的系统化质询。
马歇雷进而指出,文学生产的成果与批评传统所肯定的那些东西正好相反:不是冷静(composure)和完满,而是不完整、不一致和不在场。这些都是文学形式所产生的作用。因为尽管文学不是科学,但它“从本质上也蔑视轻信的世界观”;由于文学处在意识形态内部,它“特定的不充分性”反而可以戏仿意识形态并使其漫画化,这就提供了对于意识形态的“暗含的批判”。(13) 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任务就是去描绘这些创造性的无序(disorder)的运作方式,并对其进行解释。
从各个方面来看,马歇雷的理论扩展都有阿尔都塞主义的色彩,但这决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这本书的写作从正式的形式上看是受到了列宁的启示——同在别处一样,以不受限的客套话求诸于列宁,但更根本的(尽管未曾明言)知识资源则来自弗洛伊德,弗氏所举的例子在阿尔都塞圈子内已经成为流行的规范。在马歇雷的话语中,文本和批评家的意象(image)成了症状和它(精神)的分析学家。文学作品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分裂的集体(collective)主体性所产生的梦幻、玩笑和倒错。这种类推是有效的(实际上,对此作进一步调整,就可以改进马歇雷对于阐释的这种不加区别的批判),但却无法推出下一步的假定——文学有不同于它者的特定的(differential)批判价值。弗洛伊德列举的种种症候文本作为分析的证据很有价值,但这些文本自身就处于未知的、否定的和困惑的状态。但是依据马歇雷的观点,认识的特权属于这类文学作品,而不只属于能够阐释作品形态(figuration)的那种理论。像阿尔都塞一样,马歇雷在文化等级体系当中授予文学与科学以同等重要的地位。
马歇雷后来打算采取完全不同的思想方向,(14) 但直到现在,阿尔都塞主义独有的问题框架还保持着强劲的影响力:适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对象应该是“意识形态和文学形式”。后者是英语文学研究界在阿尔都塞的全面支持下所取得的第一个创造性成果——特里·伊格尔顿的《批评与意识形态》——中具有引领意义的一篇文章的标题。理论实践的模式明显表现在伊格尔顿的探索形态当中。对于已有的(以利维斯和威廉斯各自代表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批评文化进行的探索性评论,促成了一种关于文学在社会整体结构中所处位置的普遍的理论建构,由此达到一个顶点:“文本的科学”。这部书的几个核心命题大家非常熟悉:“唯物主义批评”作为反人道主义、反历史主义的实践,推进了与意识形态的决裂;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唤起了另一种权力”;弗洛伊德作为示范性的理论家和读者,推动了自我分裂性的文本生产。伊格尔顿通过对这些主题的详尽分析和改变,对阿尔都塞和马歇雷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他注意到阿尔都塞在给达斯普尔的回信当中那些带倾向性的限制,并反对马歇雷的观点,指出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必然都是颠覆性的。在他看来,这两人似乎认为文学应该被免除“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羞耻”,“美学应该依然被授予神秘的优先地位,但现在呈现为尴尬的躲躲闪闪的(oblique)状态”。事实的确如此。但阿尔都塞和马歇雷并不是唯独受到这种诱惑的两个人。伊格尔顿担心的正是他在自己的文本中最终无法消除他自己。《批评与意识形态》的核心章节记录了一个斗争的进程,一边给文学指派了特殊的权力,另一边又将这些权力留给了(足够严厉的)读者,而且从未放弃过这种信念——在阿尔都塞和马歇雷心中也很稳固,即存在一个需要人们去认识的所谓“文学”(或“形式”)的稳固实体,存在一个等待适当概念来表述的真正客体。
在伊格尔顿的研究结论一章,这种无法摆脱的本质主义产生了相应的结果,他试图抛开阿尔都塞和马歇雷的先例,从理论上概括特定的文学价值。伊格尔顿相当正确地肯定了这种理论的必要性(尽管特定的判断用于许多无关甚至偏离的纯粹分析目的,但在日常文化领域,不可避免地要区分文学价值),还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价值的解释是相互关联和变化的:一个文本的价值不在它于自身,而在于处于具体情境中的一些使用者(在此具有指导精神的是布莱希特)。然而,他的讨论陷入了相反的结论:在文本生产的历史条件中去探求价值,以此显现一种有原创力的、永恒的创造卓越或平庸的天赋;文学价值最终还是一种本质范畴(essential category)的内在(immanent)变体。
在这些文本中,阿尔都塞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计划被大胆地付诸实施,也毫无疑义地遭受了挫折。它们的主导性问题框架,就像阿尔都塞说过的那样,是“模棱两可的”:旧的范畴被重新描绘为新的概念,企图为无法克服的哲学难题提供一种科学的答案。(15) 马歇雷本人继续拒绝“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对于自主理论空间的不正当侵犯。他后来的著作重新描绘了文学的理论形象,转而强调文学在生产意识形态和解(compromise)中所发挥的作用;更进一步,从强调作为文本的文学转而强调作为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意识形态实践的文学文化及其在阶级国家的教育机器当中显现出来的“文学效应”(16)。伊格尔顿注意到了那些修改过的分析路线的可能性,但并没有继续推进它们,他随后的著作放弃了《批评与意识形态》的那种体系化的提纲,转而赞同一种干涉主义的“政治”批评,尽管并不缺少理论性的介入,依然强调马克思主义,但已经不能被称为“阿尔都塞主义”了。(17)
与此同时,另外一种首创精神也迸发出旺盛的活力。以菲利浦·索勒斯(Phillipe Sollers)和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为核心、发展迅猛的《泰凯尔》(Tel Quel)小组的合作著作,早在阿尔都塞最具影响力的时代已经成形,并在1968年的五月事件之后数月,到达了自我定位(selfdefinition)的决定性时刻。(18) 阿尔都塞的圈子成员与《泰凯尔》小组保持着明显的距离,似乎处于一种既热望又不愿主动结为同行的尴尬感觉当中。(19) 阿尔都塞同拉康一样,是该杂志的权威参照,是被公认的杠杆(levier)、水准或影响力的人。(20) 同这一小组有紧密关系的指导顾问是罗兰·巴特、德里达和福柯,他们开始编写一本集体性的册子《协作的理论》(Théorie d'ensemble)。(21) 《泰凯尔》小组不遗余力地试图恢复法国艺术的先锋传统,并在此刻投身于文化革命的毛主义(anarcho-Maoist)计划,并将自己的理论方向置于学术网络当中(网[reseau]是一个有意义的隐喻),这其实接纳了阿尔都塞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他,但他们却具有迥异的学术和政治出发点。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因此被限定、被替换了,在这里只是作为一种处在既熟悉又奇异的语境中的权威引文而发挥作用。
如果对这种发展持较为乐观而不是消极的评价,那么可以说,《泰凯尔》小组在相当程度上理解了阿尔都塞的观念,将非自足的(non-autarkic)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理论领域的发展看作一门科学。实际上,这种态度推动了英国,尤其是《银幕》杂志(Screen)所开展的类似研究。
“《银幕》项目”以一种常见的方式唤起了合作研究,而且机智地避开了简单的概述。这份杂志在知识方面从没有显示出同质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它们的母体组织——影视教育协会——当中有各种不同的关注在相互竞争。在70年代这一关键阶段,这一杂志的主导学术倾向本身就不稳固,部分原因在于进口型先锋文化的特征——迅疾的节拍和变化的节奏,部分原因在于在当时涌现的种种理论兴趣之间缺乏预先协调。“《银幕》项目”不是一个严格的单数,而且也没有权威性的看法。然而,由于具备这些条件,也就不会误解这一个与另一个观点之间的差异,就会对阿尔都塞思想的潜在价值做出比较精确的规范性阐释。
由此开始,情况出现了重大改变。人们不能轻视如下事实——《银幕》确定的活动领域现在已是电影而不是文学了。电影作为工业、技术实践和经验,具有纯粹的物质性,同文学体制(institution)相较,它更不容易被神圣化。文学体制的保守信徒们,正好愿意确认这一点,他们完全知道一个集会和一群乌合之众之间的差异。现代批评文化的诸多战略主题并不是已被澄清的真理:导演主创论可能还在重复传统主义者的创作和阅读观念,但它也有助于拆除“艺术”和“娱乐”之间的强制性隔离;本质主义的“电影”理论被提出时,会面临已有电影剧目的现存复杂性的顽强抵抗,后者具有多样的和易变的规范表现内容。此外,一种多变的、对抗的电影制作文化——该杂志的一些编辑也正好热衷于此——的可行性,必然会完全改变理论思考,像本雅明(Benjamin)所认识到的,从生产角度看每一个对象都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
阿尔都塞要求分析具体的、相对自足的实践,并将意识形态阐释为体制化的物质实践,这为确保从历史的、结构的复杂性方面对电影进行不受强制的阐释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与此同时,主流电影和批判电影的整个历史,都与《致达斯普尔的信》中呈现的那种概念惰性不相符。《银幕》对于电影实践的形态、功能和倾向效果所进行的探索,最初比照《泰凯尔》小组关于意识形态、主体和文本的交互理论话语的思想方法来进行,但不久就与后者趋于一致。
符号学批判性地吸收了现代诗学和语言学的科学创造——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及其他成果,它为对文本形式和功能进行后美学的、唯物主义的分析提供了可依赖的概念和知识类别。精神分析不仅显现为一种有说服力的推论,而且对理解主体性有极其重要的贡献。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历史理解的条件,也限定了文本和主体的政治。学术界对于这种理论结合,有不止一种的概括。彼特·沃勒(Peter Wollen)认同一种元理论的目标联合:“每种理论都关注可以用社会历史说明自然的一个人类行为领域”——符号、劳动和性行为。斯蒂恩·希斯(Stephen Heath)试探性地提到“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学在符号学领域相遇”(22)。在这种思想支持下写出的著作,同样缺乏均衡的规律性。沃勒的著作没有采用他的基本陈述所应显示的总体化思路,而是从一个话题转向一个话题,平静地变化着强调的重点和理论参照。希斯实际上更倾心于探析普遍策略运用于具体的分析操作时的意义。因此,在《银幕》的圈子中,促生了多种理论的变体。虽然它们符合自身的批评主题,但这是一个“不纯粹”的项目,缺乏一个本质(essence)。(23) 理论的产出量引人注目,但只证明了阿尔都塞开创精神的二次翻版——尽管更宽泛、更大胆,同时也更谦逊——并不比第一版更可靠。这是为了适应对话性的理论话语而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自足体系,虽然能够提高理论的生产力,但并不会因此产生更多可预见的分析成果。这不是一个关于从不完善到概念充分的科学进步的故事。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需要那种必需的关联,但对话只有在不对理论进行虔诚模拟的时刻才会出现,各种理论有一种反驳的方法,最终把某些事情更多归功于理性的争论而不是环境的压力。
在整个七十年代,阿尔都塞都是英国文学研究的一种智慧参考。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日益强劲的影响,也有他的一份功劳。伊格尔顿和马歇雷的名字确定了批评的整个趋向。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作家——如科拉·卡普兰(Cora Kaplan)和彭妮·布莫拉(Penny Boumelha)等——将阿尔都塞的历史概念看作一种在文本分析中阐释阶级和性别决定性的方法。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着手去肃清马克思主义对本质主义的文学和价值概念的深层依赖,尽管这一思路与伊格尔顿和马歇雷的分析有明显的分歧且对他们持批判立场,然而在精神上却分明沿用了阿尔都塞的思想。环顾一下,人们很容易相信理论实践的前景是美好的。
回首往昔,七十年代可以被看作是阿尔都塞思想剧烈膨胀的时代,然而在这个引人注目的进程当中,持续强烈的话语流通掩盖了概念意义的流失。这里至少有三个中介(agencies)在起作用。其一是平庸化过程,任何一种有影响的思想都容易受到损伤。其二,也是比较根本的一点,在于阿尔都塞引领其英国鼓吹者的进程。阿氏对于精确的追求引导他的鼓吹者将其导师的一个又一个哲学提议,非强调到自我毁灭(self-destruction)的程度不可。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更普遍的、更纯粹的政治因素: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求人们关注知识和政治利益的整体图景,除了因为后者在任何领域(即使那些不产生多少影响的领域)都具有理论说服力和规划力量而外,还因为政治是激进思想和行动不可脱离的背景。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运动的意识形态旗帜,有成功的记录,有现实的或潜在的支持者(工人运动),在所有全球性的场所都有它的直接显现。得益于这些历史的馈赠,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经受住任何单个的挑战。如果没有这些实践的支持,理论产生的直觉吸引力就会小得多,尽管这种必然结果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我们无法回避它最终显现出的影响力。
即便如此,在这个对马克思主义日益漠视甚至非常无知的时代,阿尔都塞的名字却依然能够被继续唤起。这是因为,正是他提出的相对自足的概念审慎地开启了向社会理论转换的道路,使后者不再被那个建基于经济决定论之上的封闭的总体性教条所束缚。正是他的意识形态理论(一旦消除了他的功能主义困窘),将文化分析重新集中到主体及主体的建构问题之上。正是他助成并培养了理论间的对话,后者现在正走向完备。的确,或许有些理论家让自己相信,阿尔都塞实际上已经是一名后结构主义者,是先锋派(avantgarde)中的茹尔丹先生(Monsieur Jourdain)(24)。安东尼·伊斯霍普(Antony Easthope)作为理论战争中的一员老兵,对反人道主义的宏大叙事有系统完整的揭示。他的《英国后结构主义》,是对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一系列评论,具有浓烈的、令人愉快的世俗味和坚定的社会主义思想。然而,作为一种理论史的建构,它已经被辉格党主义(Whiggish)的进化论所改造,从而将许多先前存在的优点都吸收到阿尔都塞那里,然后再将它向前推进到后结构主义的光辉时刻。《新左派评论》讨论英国的葛兰西论题,受到了杂志后期对于阿尔都塞的关注的影响,在(相对独立性)这一与恩格斯一样古老的论题上,阿尔都塞现在被授予了唯一原创作者的功劳。伊斯霍普告诉我们,“阿尔都塞至少通过三条思想路线进入了英国……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称他为后结构主义者:将历史构成阐释为解中心;断言来自于理论实践的知识是以话语方式建构起来的;将主体解释为一种结果而不是起因”。那么,(就第一条思路来说)达尔文也不过如此,(就第二条来说)波普尔也不过如此,(就第三条来说)弗洛伊德也不过如此。阿尔都塞也不过如此,他的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自我召唤,“现在正好可以被看作是进入到后结构主义当中的结构主义”(25)。过分的事后聪明,目的论的(teleological)复原,理性化:伊斯霍普的描述激起了这些异议。无论这种描述出于何种动机,把其作为过去30多年左派理论文化的总结是站不住脚的。然而,它的确以自己的方式证实了这种强烈的印象:到80年代末,阿尔都塞的名字连同他思想的某些痕迹,在很大程度上几乎仅仅作为一件纪念品,存活于一种已经忘记了他的学术和政治目标的文化中。
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变,就目前作为普遍化的话题流行于后马克思主义学术左派这一点来说,并不是一个独立的(autonomous)批评过程,而更多是多重政治去魅(disenchantment)的结果——尽管这种结果以前未曾料到,但肯定不是阿尔都塞逻辑的成功,而是对它的背弃。这么说并不是要对那些创立了后结构主义口号的各类思想家做总结性评价,也不是对那些目前以他们几个人共同署名流通的各式各样的著作进行判断:新的颠覆文化是一个远弱于其各部分之和的整体。它们都没有说明存在一种原初的理论实践——被多年的误用(misappropriation)所遮蔽但还未被彻底毁灭。我们现在必须像当年阿尔都塞重返马克思那样,重新开启这种理论实践。事情远为复杂,前景远不明朗。总之——尽管这不是个理想的词——很值得对阿尔都塞的核心思想进行一些详细的论述,并为这些思想提供适合时代的现代评价。
意识形态是阿尔都塞在激进的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得以闻名的主题,他的思想路线显示出这是他最具雄心的理论探险。从一方面来看,阿尔都塞的观点并不陌生:意识形态的概念隐含着认识上的缺陷与社会利益之间存在着一种限定关系。用他的权威英译者的话说,是一种“社会实践……支配理论和知识”(26) 的模式。但是,从未有人如此坚决地强调过知识同社会实践的矛盾。意识形态是在这个社会或所有社会里无处不渗透的、人们心照不宣却不怀疑的自发的人类体验。(27) 阿尔都塞没有放弃这一概念较为熟知的第一种意义,而去追索他要考察的第二种意义。意识形态的“想象关系”是一种存在模式,人的意念—情感(ideo-affective)生活在其中,会把社会认可的形式当作自己的身份认同(identity):意识形态“将个体召唤为主体”。阿尔都塞以这种论证方式,实现了两个不同问题之间的极端而有破坏性的融合:从大家比较熟知的意义上讲,意识形态既作为一种由社会推动的区别于知识的关系发挥功能,又作为人类主体建构(subject-formation)的普遍机制而发挥作用。从这一点来说,意识形态能否被认识或替代?阿尔都塞提供的应对办法是:通过科学和艺术。但如果意识形态现在就等同于身份建构的人类学恒量的话,那么如何能够将这些概括为日常的历史实践?反之亦然,如果它们仅仅被作为想象界里不可思议般的(quasi-miraculous)介入而保留,或者说,如果它们根本不能被保留,而必须被当作理性主义和空想的神秘化而抛弃的话,那么,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批评概念还能保留什么?这些以及类似的异议来自那些赞同的或有敌意的评论家们,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文章是持后结构主义立场的人所写,在后者那里反建构(counter-construction)已经出现了。阿尔都塞的“科学”概念与元话语(meta-discourse)特有的否定性有深层关联,而元话语让自身从那些给它约定对象的存在条件中得以豁免。对于主体建构的解释,要么是错误的,因而不充分,要么是正确的,因而又对它自身关于最终合理性(final rationality)的宣称构成了颠覆性的挑战。在任一种情况下,科学性的理念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从科学性理念推定出的其他观念——辅助的意识形态虚构,同样也没有事实根据。“科学”是“真理政治”的开局策略,是各种话语及其话题争论中的强权表演(power-play)。
这种事实上不成立的(destructive)回应证明对当代趣味最有吸引力,但是还有其他的回应,至少包括一份阿尔都塞的思想启示。戈兰·瑟伯恩(G·ran Therborn)指出了一种内在于意识形态的机制,由此主体化—服从(subjectification-subjection)的宿命论统一将陷入自我矛盾,产生认同和信仰危机并带来不确定的结果,换句话说,正好陷入阿尔都塞试图抵制的那种具体的(material)“意识辩证法”(28)。瑟伯恩从阿尔都塞手中接过来的分析局限性,就是将科学(及艺术)归为一种特殊的个案。正像阿尔都塞对于主体化过程的形式主义分析排除了如下事实——所有意识形态都在提出真理宣称(truth-claims),瑟伯恩也支持一种镜像式的推论,认为知识承载型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与主体建构没有内在牵连。但是,在真正的话语领域并没有这种分工,逻辑和修辞产生效果时不但是不可分离的,也很少依据反比例(inverse proportions)规则。如果主体建构理论确实有效,那它也应该适用于所有的话语实践。阿尔都塞的推理如果没有对这类话语的抽象,就不能确保它从哲学上捍卫科学性的合法性,因而激起了不可知论者和非理性主义者的反击。在对科学进行反现实主义阐释时出现的这种困境,有纯粹认识论的因素:后者在将文化错误地简缩为意识形态的过程当中,找到了自毁式的(self-destructive)确信。
雷蒙·威廉斯长期被视为阿尔都塞之感受力(sensibility)的人文主义对立面,但是由他发展的文化理论,由于远离了科学/意识形态的区分所带来的矛盾,证明有更可靠的理论框架。在威廉斯看来,文化通常是构造感觉和主体二者的整体的历史过程。它的实质是物质性的实践活动——修辞和惯例。文化并不构成一个表现的总体性:它的对立面(antagonisms)是复杂的,时代不同,它的意义也就有差异和变化。(恢复到作为社会决定的神秘化的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和(被理解为较弱英雄色彩、对于真实进行可能出错的理性探索的)科学都会出现,但它们是作为从事文化实践的临时教员(contingent faculties),而不是作为它的原初本质而出现的。当然,文学也会出现,但它的功能明显更接近于后期马歇雷而不是阿尔都塞的观点,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形式出现在写作和阅读的历史当中。然而,马歇雷的分析由文本转向了惯例(institution),虽然有所创新,但还远远没有解决他早期的理论困惑,相反倒是在逃避问题。对本文的形式和功能的探究,虽然常常会肯定呈现出形式主义,但依然会在所有配得上文学理论之名的文学理论的核心位置上。检讨过去,我惊奇地发现,威廉斯对文学形式的理解,在很早的时候已经摆脱了困扰阿尔都塞和马歇雷的本质主义,因为后者确实已经挫败了大部分将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化的努力。
意识形态在一个根本上只受经济决定的复杂整体中,享有相对自主权(relative autonomy)。这可能是阿尔都塞提供的信息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在这一名义下所取得的丰富成果,证明了这一范畴的学术价值。但是作为一个概念,它也显示了一种向负面发展的倾向。“相对自主权”作为调节教条的历史哲学与批判的、唯物主义的实践概念之间对立的折中形式,很快会受到怀疑。它被提出来本是作为解决马克思的社会地形图(topology)的一种办法,后来却被越来越多地用为通向其他理论空间的通道。阿尔都塞的理论表述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再次助长了这种不请自来的后果,尽管它远非意识形态概念所招致的不断攻击那么严重。“相对的”这一术语,实际上通常被用作一种特殊润滑剂来化解互为前置词(inter-prepositional)所产生的摩擦。但是,那种带有严肃的唯物主义色彩的反对理由——意识形态不是被决定的就是自主的(除此之外无第三种方式)——也是站不住脚的。(29) 有条件的自主(一个更准确的称谓)是各种综合体系的典型状态,只有人道主义者的假设——社会生活完全有别于其余的现实——才给阿尔都塞继承者的那些自负的选言命题(disjunctions)提供了证据。还有一个事实,或者说我愿意这样认为,阿尔都塞对于“归根结底(the last instance)”的表述是有缺陷的,把概念的时间意义和结构意义合并在一起会带来不利的后果。(30) 但是,从一种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修正这一分析现象并不存在很大的困难。的确,在其他地方明显存在更具原创力的关于阿尔都塞论述的争论之时,“相对自主权”和“归根结底”却吸引了那么多的关注,这显得有些奇怪。他文章中最有名气的概念并不是这两个,而是“多重决定”这一概念。阿尔都塞的目标不是——或者不仅仅是——去松开机械主义者的坏整体和表现主义者的论证,重新分配因果关系之源,将原因从经济基础上推到上层建筑,而是要替换一种将社会作为整体的选择性的(alternative)观念。“多重决定”这一概念不只指明了相对独立的功效的结果,还提出要明确说明社会进程一贯性的典型形态,要显示一种实践如何从那些构成其存在条件的其他各实践内部被标示出来,并且因此——尽管必然显得有点黑格尔主义色彩——去反思而不是抛弃以所有部分呈现整体这一观念。
如果说“相对自主权”是阿尔都塞授予激进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许可证,那么“多重因素决定”则是让它们接受相应的义务或挑战。从运作层面上看,它几乎没有限定:这是一个概念工具,正好适合局域化的文本分析,适合有关时代和流派的大规模的历史阐释。它把精神分析(实际上是这一术语的来源)和符号学授权给生产劳动关系,诸如克里斯蒂娃的“文本间性”等概念在此提供了支援和规范;它清除了一个可以用非还原论(non-reductionist)方式来考察阶级之外的重要社会决定因素的概念空间。但它是阿尔都塞思想体系当中特殊的马克思主义元素——不像那些和它关联的概念,可以在任何一门冷淡的文化社会学内部被接纳,而且未能幸免于随时代变迁的普遍贬值。“多重决定”是阿尔都塞在英语世界许多子孙提到他时所说的第一个词,它的意义依然处在探究当中(under-explored)。
一个概念及其命运的这种简短经历,可以当作一则寓言,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在宽泛的理论文化当中的状况。阿尔都塞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限定性定义和对马克思主义历史概念的修订说明,是互补的两个方面,共同为了一个专一的、基本的决断,即否认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处在发展中的宇宙论的观点,并随即拒绝其在理论上的自闭性。只有经过实践使普遍的科学探询达成批判性的一致时,回到马克思才是合理的。阿尔都塞对于拉康的辩护——在理论上反对他自己学派的日丹诺夫传统,在政治上反对精神分析的官僚作风——为他所献身的这种修正的道德规范和文化政治提供了最有力的理由。(现在人们都知道,他在理解“差异的暂时性”和精神生活的“特定效能”时,这段经历为他提供了一种非常有深度的认知优势)他伟大的关注文本物质性的“阅读”工作,既从精神分析学也从当时的结构主义汲取了灵感,这种“阅读”就是一种适合于对学术行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实践形式。
这是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最重要的独到贡献,但由于它不只是出于虔诚,因而也不仅仅是一件礼物。在比较愉快的时刻,人们会相信一种新的理论综合——反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是可期的。但这种受优待的措辞实际上非常微弱(“唯物主义”并没有明确说明任何真实的物质世界,“反人道主义”只是一个粗糙的论辩主题),以至于实际上它支持了理论综合的对立面:一种新的,或者说不太新的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在我看来,阿尔都塞的倾向弱于第一方面(唯物主义),而强于第二方面(反人道主义)。
一项合成计划可能无法帮助但可以重新点燃旧的宇宙论梦想,而且通过这么做,来抑制而不是帮助理论探询。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感觉和主体性的建构是通过有限定性的生产方式及其相关的阶级关系组织起来的。精神分析学认为这种建构显现出最初以或多或少不同于经济制度的形态进入社会性的持久影响。二者均不能充分说明文本例证(textual evidence);然而,要认真接受这些意见并且同时相信还有一些更高级的解决办法好像也有困难。一个很小的例证就可以具体说明这个问题。福楼拜的《情感教育》戏剧性地表现和证明了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这段特定时期里资产阶级政治失望的过程,我们承认这是事实。同时,福楼拜对人物及其关系的形象描绘受到母亲意象的控制,这似乎也是真实的。这部小说浓缩了这些不同的事情,这些事情既不是分离也不是协作(co-ordination)地并存于一种本质和表现关系。福楼拜的文本空间似乎被两倍的内容占据,同时被某一时期法国的社会意义和某种无意识欲望的形态所填满。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它概括了所有文化的状况,即社会的和精神动力的意义总是在其中共同起作用,不只在它们共享的符号学领域,还在它们彼此的内部进行,并且遵循一种既不排除协作形态也不依赖于它们的逻辑。
然而,推论这一点不是去提供对“文化多元主义(pluralism)”观念的简单支持,这个词内含的有害的含混性已经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文化多元主义作为一种承认所有学术倾向的制度性的原则,是产生丰富研究成果的必要条件。但是,这一词语的这种含义经常有意或无意地被用来限定另一种意义,后者更明显地显示为相对主义者或视角主义者。这些人有他们的权利,但是作为学术立场,他们没有模仿制度优点的特权:集体的文化多元主义不主张——更不要说去命令——个体的折衷主义。而且,尤其不能通过诉诸阿尔都塞的名字来验证他们的观点。说没有任何理论可以宣称对社会知识的垄断权,并不是说真理就是相对的,或者是分解的(parcellized)。阿尔都塞肯定了第一个命题但已经反驳了它带来的谬误结论。马克思主义不能以英雄般的隔离姿态去收获我们可能的社会知识成果。但是只要它提出关于社会普遍结构的观点,它就不仅要反对同一领域中其他猜测性的观点,而且要批判地考察那些缺乏创见的应用观点。这是一种合理的继承,通过这种途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有条理的有理性的理论得以幸存或消失。(31) 理论在视角主义的分析清单中被简缩到只考虑“阶级因素”,正是要成为某种列宁精辟地定义的东西:文化研究中的“工会意识”。
为拒绝旧的宇宙论(尽管他的语气有时掩饰这种姿态),抵抗错误的视角主义的选择,路易·阿尔都塞草拟了一条大胆的、易受攻击的提议:用他自己的话说(此处顺序上做了调换),一种受多重因素决定的理论行为的一致性,它的构造形态可以无限多地新奇,但归根结底还是受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所决定。这一提议究竟有怎样的启示意义,究竟怎样容易被简化或改写,最近的20年已经表明了。今天,这一提议虽然被时光所操弄而大大磨损,但依然清晰可辨,它依然是一条需要我们去阅读、去思考、去依照它行事的信息。
注释:
① 译自《阿尔都塞批评读本》(Althusser:a Critical Reader,Gregory Elliot ed.Oxford UK & Cambridge USA:Blackwell,1994),作者弗兰西斯·马尔赫恩(Francis Mulhern)是英国米德尔塞克斯大学(Middlesex University)艺术学院教授,主要领域研究为马克思主义批评和文化研究,是《新左派评论》的核心成员之一。译者单位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译注。
② 由于缺少更好的措辞,这几页文字只能提供所谓的理论纪要。这些文字并不打算提供体系化的批评成果或严格意义上的历史重构,它们的背景更个人化一些,而且在均衡和范围方面可能显得比较特殊。正因为这个原因,这篇文章也有点英国中心论的色彩;这是我在此无法超越的一种局限,不过我希望承认这一点。感谢格雷戈里·艾略特(Gregory Elliot)的鼓励和批评。
③ 这一点在《保卫马克思》(For Marx,Allen Lane,London,1969),《阅读〈资本论〉》(Reading Capital,New Left Books,London,1970),《列宁和哲学及其他论文》(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trans.by Ben Brewster,London:New Left Books 1971)等书中随处可见。
④ “Overdetermination”是阿尔都塞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借用的范畴,国内学界普遍译为“多元决定”。弗氏原指梦境虽然来自现实,但必须经过心理过程的扭曲、割裂、重组,最终呈现出真幻交织的复杂形态。阿氏借用此概念旨在批判经济决定论的前提假设(经济是唯一且直接的原始决定因素),他把一个时期的社会结构形式重新定义为多种实践(如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理论等)的共存状态,强调各种实践之间相互渗透、相互改造的动态运作以及最终呈现出的各种意识形态交织展现状态。值得注意的是,阿氏并未否认经济实践的“最终”决定性,只是认为这种决定性是一种由处于背后、处于远处、既在场又未在当下显形的多层制约因素共同构成的一个有中心、不均衡的决定性结构。显然,泛泛而谈“多元决定”,无法确切传达阿氏的意图。此处暂拟译为“多重决定”(中国台湾地区学者陈信行译为“泛层决定”),以期引起大方之家进一步推敲。——译注
⑤ “四艺”(Quadrivium):中世纪的大学开设的四门基本学科,指算术、几何、天文、音乐。
⑥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也提到过“领航的四门科学”,但他将经济学而不是将精神分析学与其他三门科学列在一起。参见《符号学的要素》(Elements of Semiology,Hill and Wang,New York,1968.P.101-02,n.55)。
⑦ 我本人讨论这种处于困境中的文化的文稿“克里斯托夫·考德威尔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见New Left Review 85,May/June 1974),代表了用“阿尔都塞主义”清除本土理论遗产的愿望。尽管我在此文中支持否定性(destructive)的分析,但我很久以来就认为考德威尔值得我们进行更用心、更深入的(即,更纯正的批判)阅读。
⑧ 威廉斯对于考德威尔的著名判断归纳出了左派文学批判情感的整个结构:“他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还不至于达到错误的程度”(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Penguin,Harmonsworth,1961.P.268)。
⑨ 乔尔焦·斯特雷勒(Giorgio Strehler,1921-1997):意大利著名戏剧导演,1947年与巴乌罗·格拉斯(Paolo Grassi)和尼娜·芬奇(Nina Vinchi)创办了意大利第一个公立剧院——米兰小剧院,1991年他创立了巴黎的欧洲剧院。一生导演200多部剧作,发展出一种形式严谨、富有政治使命、服务于公众的戏剧。
⑩ 前者(“Piccolo Teatro:Bertolazzi and Brecht”)见《保卫马克思》,后者(“Cremonini,Painter of the Abstract”)见《列宁和哲学及其他论文》。
(11) 卡洛·贝尔多拉西(Carlo Bertolazzi,1870-1916):意大利戏剧家和记者。他于1893年发表《我们的米兰》(El nost Milan),该剧由两个小节构成:《穷人》(La povera gent)和《绅士》(Il sciori),1900年发表了《自我主义者》(L'egoista)。
(12)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trans.,by Ben Brewster,London:New Left Books 1971.P.207.204.
(13) Pierre Macherey,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78.P.133,159.
(14) 参见他与巴里巴尔(Etienna Balibar)合作的文章《论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形式》,英译文见《牛津文学评论》1978年3期,后又重印在Francis Mulhern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Contemporary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London:Longman 1992。
(15) 美国迈克尔·斯布瑞克(Michael Sprinker)的著作倾向于反对这个问题。对他而言,美学和意识形态形式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我们“目前的理解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肯定还处在阿尔都塞的问题框架之内”。然而他补充说,美学的概念比资产阶级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更难以把握。见《想象的关系》(Imaginary Relations,London:Verso 1987.P.2,3.)。
(16) 《论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形式》,第35页。
(17) 参见特里·伊格尔顿《批评与意识形态》(Criticism and Ideology,London:New Left Review 1976.P.56)。伊格尔顿对于阿尔都塞的回顾性评论出现在他的《反本质:1975—1985年文选》(Against the Grain:Essays 1975-1985,London:Verso 1986)一书的“前言”中,P.2-4。
(18) Tel Quel,Théorie d'ensemble,Editions du Seuil,Paris,1968.
(19) 巴里巴尔和马歇雷认为《泰凯尔》与一种“反自然”和“违反秩序”的艺术观相关,即艺术具有“颠覆……保守意识形态的特征”。见《论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形式》,P.54,n.10。
(20) Théorie d'ensemble,P.8.
(21) See Foucault,‘Distance,aspect,origine’; Barthes,‘Drame,poème,roman’ and Derrida,‘La difference’,Théorie d' ensemble,P.11-24,35-40,41-66.
(22) Peter Wollen,Reading and Writings:Semiotic Couter-strategies,London:Verso1982.P.211; Stephen Heath,Questions of Cinema,London:Macmillan 1981,P.201。沃勒的这种三合一的观念通常牢牢依赖于一种致力于科学的信念,他相应地与《泰凯尔》小组的关系比同希思的关系要更疏远一些,希恩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这一杂志的积极合作者。希思的书《时代的符号:文本符号学导读》(Signs of the Times:Introductory Readings in Textual Semiotics,与Colin MacCabe及Christopher Prendergast合著)标志着《泰凯尔》杂志进入了英国左派文化。
(23) Rosalind Coward和John Ellis的《语言和唯物主义》(Language and materialism,Routledge and Kegan Paul,London,1977)一般被当作《银幕》的思想大纲,但并没有明言这一状况。
(24) 茹尔丹(Monsieur Jourdain):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的戏剧《贵人迷》(Le Bourgeois gentilhomme)中一位附庸风雅的暴发户,一心想通过学习艺术赢得贵族的认可。
(25) British Post-structuralism since 1968,London:Routledge,1988.P.17,21.
(26) 见《保卫马克思》“术语表”(由英译者Ben Brewster收集,阿尔都塞本人修改),London:Allen Lane,1969.P.252.
(27) 这一论题的绝对性被阿尔都塞的一种试图限定的努力所确认。他写道,意识形态是“一种贯穿整个历史的(omni-historical)的事实,在这一意义上,其结构和发挥功能是永恒的,呈现在我们所称的全部历史的同一形式当中,在这一意义上,《共产党宣言》才把历史定义为阶级斗争史——即阶级社会史”(《列宁与哲学》,第151—152页)。如果这一假设的限定是有效的,那么基本的论题就失灵了。
(28) 《权力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权力》(The Ideology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Ideology),London:Verso,1980.
(29) See,for example,Paul Hirst,On Law and Ideology,Macmillan,London,1979,P.52-53,71-72 and passim,and for the settled retrospect,Easthope,British Post-structuralism.P.213-214.
(30) Cf.the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p.25.
(31) 斯蒂芬·瑞斯尼克(Stephen Resnick)和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Woolf)在我看来试图规避——或者想删改——这个不肯通融的(unaccommodating)结论,他们首先强调,对阿尔都塞来说不能只有一种社会真实,而只能有复数的真实(a plurality of truths);其次,马克思主义应当接受还是拒绝外源性的理论主张,应依据对这些主张的“社会条件和后果”的评估(《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放》,见The Althusserian Legacy,P.65,67)。
标签:文学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意识形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