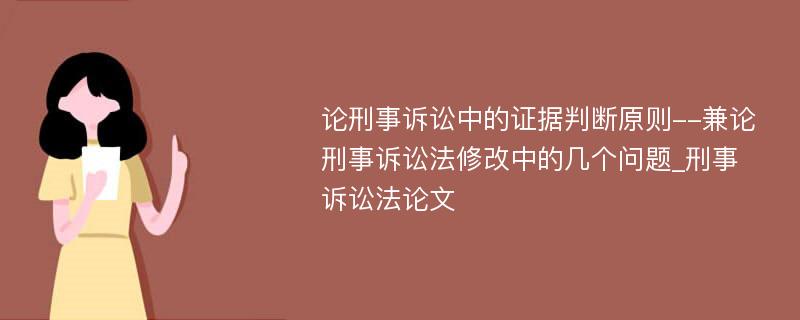
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裁判原则——兼谈《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刑事诉讼法论文,刑事诉讼论文,若干问题论文,裁判论文,证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现代法治国家证据制度基石的证据裁判原则,是指诉讼中司法人员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虽然都体现了证据裁判原则的基本精神,但对该原则都没有明确加以规定。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以下简称两院三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2条明确规定:“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正式确立了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裁判原则。对于证据裁判原则,无论理论上的认识还是实践中的运用都存在较多争议,有待深入研究,本文仅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证据裁判原则的历史发展考察
欲探究证据裁判原则的真谛必须以对其历史发展的考察作为起点。从人类社会诞生之时起,纠纷的解决就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而要合理解决纠纷,裁判者就要力求发现真实。随着社会的进步,发现真实的模式、原则和制度也呈现阶段性的演进。我国诉讼法学者对于证据制度沿革的传统观点往往以欧洲大陆为视角,认为证明方式的演进主要经历过三个阶段:神判证据制度阶段、法定证据制度阶段和自由心证证据制度阶段。笔者认为,这种以欧洲大陆国家证明方式的演进作为人类社会证据制度历史阶段划分的观点有一定局限性。如果突破欧洲大陆的地域限制,将视野扩展至世界范围,将三个阶段分为神明裁判、口供裁判和证据裁判阶段则更为准确,这三个阶段也是人类对诉讼的认识由非理性走向理性的过程。
(一)神明裁判阶段
神明裁判即以神示证据作为裁判的依据。在生产力落后和人类认识水平较低的历史阶段,人们发现案件真实的能力较弱,因此往往借助于神的力量进行裁判。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神意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诉讼活动也不例外。诉讼中如果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存在争议,而又无法证明各自的主张,就将“神的指示”作为裁断的最终依据或唯一依据。神明裁判是一种非理性的证明方式,但又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世界各国古代社会均存在神明裁判,但其方式繁多,各不相同。较为常见的是火审和水审:火审通常以烈火或烙铁是否导致灼伤以及伤口愈合方式判断是非;水审则包括冷水审判法、沸水审判法等等。欧洲大陆曾经盛行过水审和火审,如在古代日耳曼地区,冷水审判是将嫌疑人投入水中,若其身体漂于水面上,则证明其罪恶的身体无法为水所接受,故而应被判有罪;而热水审判则是让嫌疑人将裸露的胳膊或腿放入沸水中,若其能够不受伤地拿出来,则证明其无罪。法兰克王国的《萨利克法典》第53条规定:“如果有人被判处(把手放入)沸水锅的考验,那么,双方可以达成协议,使被判决者可赎回自己的手,并须提出共同宣誓的证人。”①而火的审判之典型可见于公元9世纪法兰克人的《麦玛威法》中:“凡犯盗窃罪必须交付审判。如在审判中为火所灼伤,即认为不能经受火的考验,处以死刑。反之,不为火所灼伤,则可允许其主人代付罚金,免处死刑。”中世纪的欧洲盛行“热铁审”,即牧师先给烧红的铁块洒上圣水并说道:“上帝保佑,圣父、圣子和圣灵请降临这块铁上,显示上帝的正确裁判吧!”再让被告人手持热铁走过9英寸的距离,最后被告人的手被包扎起来,三天后进行检查,若有溃烂的脓血则视为有罪。古代欧洲大陆还存在宣誓裁判、决斗裁判、食物吞咽裁判、卜筮裁判和十字架证明等多种神明裁判方式。②在欧洲大陆之外,英国王室法院也盛行神明裁判方式,这一古老的方式直到1215年才由拉特兰咨议会废除,但在此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人民依然“会把一个巫婆扔到水里接受上帝的裁判”。③
古代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包含大量神明裁判的内容,如第2条规定:“无故以符咒蛊惑他人时,受蛊人应至圣河;投入河中。受蛊人溺毙圣河中时,加蛊人取其房屋。圣河若以其无辜而不加伤害时,加蛊人处死刑。跳入圣河者取加蛊人之房屋”,④第227条规定:“以诈术使烙印者烙不可让与之奴之印者,处死刑,埋于己屋中。烙印者应宣誓‘余非有意烙之’无罪。”⑤《苏美尔法典》第7条规定:“引诱自由民之女离家外出,而女之父母知之者,则引诱此女之人应对神发誓云:‘彼实知情,过应在彼’。”《中亚述法典》第8条规定:“如果有人破坏他的同伴间的大片田界,有人以誓言揭发他并证明他有罪,那么,他应加倍交还他破坏而取得的田地;他应斫掉一指,受一百杖责,并应服王家劳役一整月。”⑥
中国虽然史籍上没有神明裁判的确切记载,但在最古的传说中还可以看到神判法的痕迹,例如,《说文》云:“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论衡》中亦有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的记载。⑦《墨子》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齐庄公下面有两个臣子王里国和中里徼,打了三年官司,案件无法判决,齐庄公想把他们都杀了,却怕冤枉了无辜者,想把他们都放了,又怕放纵了有罪者,于是他让这两个人准备一头羊,到齐国的神社去宣誓,宣誓时,刺羊出血,洒之于社,同时让他们两人读誓词,王里国顺利地读完了自己的誓词,而中里徼的誓词还没有读完一半,羊就起而触之,先触断其脚,最后把他触死了。⑧这些文献记载说明中国古代曾经存在着神明裁判的方式,只是由于消失得比较早,因而在古代法典上没有找到明确的规定。由此可见,神明裁判制度是各个民族共同经历过的证明方式,具有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
(二)口供裁判阶段
口供裁判是指以被告人的口供作为定案的主要依据的证据制度,口供裁判是一种半理性的证明方式,从神明裁判走向口供裁判是伴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和认识能力的提高而实现的,这一制度之典型可见于中世纪欧洲大陆和封建专制主义时代的中国。欧洲大陆的法定证据制度可以被划归入口供裁判阶段中。法定证据制度主要盛行于中世纪的欧洲大陆国家,主要代表性的法典有1532年神圣罗马帝国查理五世制定的《加洛林纳法典》、1853年《奥地利刑事诉讼法》和1857年《俄罗斯帝国法规全书》。法定证据制度的基本特点在于:第一,法律预先对各种证据的证明力大小以及其取舍运用作出详细而机械的规定,根据证明力的大小,证据被分为完善的和不完善(或完全或不完全)的证据。例如1857年《俄罗斯帝国法规全书》中规定受审人的自白、书面的证据、亲自的勘验、具有专门知识的人的证明、与案件无关的人的证明等证据被认为是完善的证据,而共犯的攀供、询问四邻所得知的关于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和表白自己的宣誓等被认为是不完善的证据。第二,口供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证据,《加洛林纳刑法典》是规定口供至上的代表性法律,其规定被告人在法庭上的供认是完全证据中的最好证据,被告人的口供被看做“证据之王”。⑨第三,采用合法的刑讯手段以得到口供,例如在日耳曼的刑事诉讼中,刑讯是刑事诉讼“整个大厦的中心”,《加洛林纳法典》和法国1670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敕令都规定,调查官为查明“事实真相”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包括对嫌疑人和证人实施秘密的或公开的刑讯逼供;在14世纪法国逮捕和审判圣殿骑士团的过程中也大量授权官员对圣殿骑士团成员使用刑讯。⑩
在欧洲大陆之外的英国,当时没有形成法定证据制度,但却出现过口供裁判方式。根据西方学者的考察,在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通常在审理之前被关进严密的禁闭之中。他受到治安法官或者其他地方官员的盘问,而且他的回答都被写下来而且供在审理时起诉之用,但是不给他任何机会来准备自己的辩护。”(11)此外,在英国也同样盛行刑讯,例如16世纪英国曾发生过大规模迫害女巫的运动,许多人受到诬陷被作为女巫受到审判和定罪,女巫审判的依据往往主要是被告人供认自己有罪的忏悔书,而该忏悔书通常是通过恐吓诱骗的方式和刑讯的办法获得的。(12)可见,在封建时代的英国,以刑讯逼供为重要内容的口供裁判也是其重要的证明方式。
中国古代不存在典型的法定证据制度,只有某些法定证据的因素,例如《唐律疏议·断狱》“八议请减老小”条规定,在不允许拷问被告人迫使其招供的情况下,“皆据众证定罪”,而“称众者,三人以上明证其事,始合定罪。”(13)而口供主义始终盛行于古代封建专制主义司法之中,明清两代尤甚,明律“吏典AI写作招草”条王肯堂笺释说:“鞫问刑名等项,必据犯人之招草,以定其情。”(14)清律同条夹注也指出:“必据犯者招草以定其罪”;《清史稿·刑法志》指出:“断罪必取输服供词。律虽有众证明白即同狱成之文,然非共犯有逃亡,并罪在军流以下,不轻用也。”(15)在古代中国,口供裁判又总是与合法的刑讯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秦简《封诊式》“讯狱”即规定:“凡讯狱……诘之极而数訑,更言不服,其律当治(笞)谅(掠)者,乃治(笞)谅(掠)。”(16)唐律规定:“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违者杖六十。”(17)《清律》规定:“强盗、人命及情罪重大案件,正犯及干连有罪人犯,或证据已明,再三详究,不吐实情,或先已招认明白,后竟改供,准夹讯外,其别项小事,概不许滥用夹棍。”(18)口供为主的证明方式加上合法的刑讯构成了口供裁判阶段的基本证明形态,尽管不排斥物证、书证和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但口供是定案的主要依据。
(三)证据裁判阶段
证据裁判制度是一种理性的证明方式,证据裁判与口供裁判的分野不在于口供是否作为定案的证据,而是在于是否以口供作为主要证据。证据裁判是在资产阶级追求民主、自由、人权和对口供裁判制度的激烈批判及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伴随着自由心证制度的确立而建立起来的。自由心证起源于资产阶级大革命后的法国。1790年12月26日,杜波耳向法国宪法会议提出革新草案,建议废除书面程序及其形式证据,只把法官的内心确信作为诉讼的基础,用自由心证制度取代法定证据制度。(19)资产阶级革命后的1808年拿破仑《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42条规定:“法律对于陪审员通过何种方法而认定事实,并不计较;法律也不为陪审员规定任何规则,使他们判断已否齐备及是否充分;法律仅要求陪审员深思细察,并本诸良心,诚实推求已经提出的对于被告不利和有利的证据在他们的理智上产生了何种印象。法律未曾对陪审员说,‘经若干名证人证明的事实即为真实的事实’;法律也未说:‘未经某种记录、某种证件、若干证人、若干凭证证明的事实,即不得视为已有充分证明’;法律仅对陪审员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已经形成内心的确信否?’此即陪审员职责之所在。”这是大陆法系自由心证的经典表述,现行的《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53条基本沿袭了这一规定的主要内容。(20)随后自由心证制度在整个大陆法系得到了广泛的采纳,成为大陆法系的基本诉讼原则。《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61条规定:“对证据调查的结果,由法庭根据它在审理的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内心确信而决定。”(21)1892年俄国《刑事诉讼条例》第119条规定了内心确信原则,苏联《苏俄刑事诉讼法典》沿袭了这一原则,以“社会主义的法律意识”置换了西方自由心证证据制度所要求的“良心”、“良知”,现行《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17条规定:“法官、陪审员以及检察长、侦查员、调查人员根据自己基于刑事案件中已有全部证据的总和而形成的内心确信,同时遵循法律和良知对证据进行评价。任何证据均不具有事先确定的效力。”(22)在此顺便说明一下:我国目前常用的“自由心证”一词沿自民国,源于日本,其实“心证”即是苏联和俄罗斯所用的“内心确信”,此为翻译问题,不要误以为“自由心证”和“内心确信”是两种制度。
由此可见,证据裁判原则正是在从口供裁判阶段转向证据裁判阶段的过程中诞生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欧洲大陆各国的法律条文看,现行的《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德国刑事诉讼法》、《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以及《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均仅规定了自由心证原则及其相关内容,并未将证据裁判作为独立的原则规定于条文之中。当然,这些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中有一些与证据裁判原则直接相关的条文,例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27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犯罪得以任何证据形式认定,并且法官得依其内心确信做出判决。法官只能以在审理过程中向其提出的、并在其当面经对席辩论的证据为其做出裁判决定的依据。”(23)《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44条第2款规定:“为了调查事实真相,法院应当依职权将证据调查延伸到所有的对于裁判具有意义的事实、证据上。”(24)而法国卡斯东·斯特法尼等人所著的《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和德国罗科信教授所著的《德国刑事诉讼法》教科书均未将证据裁判原则作为证据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加以明确阐述。以罗科信的《德国刑事诉讼法》教科书为例,作者在“证据原则”一章中称证据原则乃指调查原则、直接原则、自由心证原则及罪疑唯轻原则,(25)而未曾提及证据裁判原则,这表明欧洲大陆国家学者并不认为证据裁判原则是其法律明确规定的证据法原则。
证据裁判原则固然可以逐本溯源于欧洲大陆国家,但其在法律条文上的真正确立始于日本。日本于1876年制定的《断罪依证律》把《改定律例》规定的“凡断罪,依口供结案”修改为“凡断罪,依证据”,并规定“依证据断罪,完全由法官确定”。(26)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这是法律文件对证据裁判原则的最早规定,将欧洲大陆的自由心证原则一分为二,区分了证据裁判原则和自由心证原则,也标志着证据裁判原则正式在法律上的确立。证据裁判原则的确立实际上也是对法官自由心证的一种限制。这一条文为现行的《日本刑事诉讼法》所继承,该法第317条规定:“认定事实,应当依据证据。”此外,这一规定也影响了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立法,例如韩国与我国台湾地区。
而在英美法系国家,不但法律中没有证据裁判原则的直接规定,甚至英语中也没有“证据裁判原则”这样一个成型的词组。美国不但《联邦证据规则》没有关于证据裁判原则的规定,而且作为州证据立法典型的加州《证据法典》也没有此种规定;加拿大《证据法》、澳大利亚联邦《1995年证据法》、新西兰《1908年证据法》及其十三个修正法案均没有规定证据裁判原则。(27)著名的证据法学专著或教材,如《麦考密克论证据》、《墨菲论证据》、摩根教授所著《证据法之基本问题》,以及近年来被大陆学者译成中文的乔恩·R·华尔兹所著《刑事证据大全》、理查德·梅所著《刑事证据》和罗纳德·J·艾伦所著《证据法:文本、问题和案例》等均没有论及证据裁判原则。英美法系国家没有明确规定证据裁判原则并非对该原则的否认,而是认为证据裁判原则是不言自明的。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制度中有大量关于证据关联性和可采性的规则,这些规则与证据裁判原则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事实上表明这些国家非常强调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依靠证据。当然,这一原则在英美法系并非绝对,例如陪审团有不顾事实和证据作出裁判的权利,但证据裁判作为其证据制度实际上的基本原则是毋庸置疑的。
由此可见,尽管大多数国家没有在法律中明确规定证据裁判原则,但通过对其法律的分析,可知证据裁判原则的精神已为民主法治国家所公认。随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证据裁判原则也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民事和行政诉讼中早有证据裁判原则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3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判行政案件,应当以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但是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无证据裁判原则的条文规定,其规定仅体现了证据裁判原则的一些精神。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提出:“坚持证据裁判原则,重证据、不轻信口供。”2010年《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规定:“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表明中国刑事诉讼证据裁判原则的正式确立,这对于反对口供至上主义和刑讯逼供、追求司法真实、保障人权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另外有学者认为历史上的证明方式曾经有过两次重大的转化:第一次是从以神证为主的证明方法向以人证为主的证明方法的转化,第二次是从以人证为主的证明方法向以物证为主的证明方法的转化。相应的,司法证明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神誓和神判为证明的主要形式;第二个阶段以当事人和证人的陈述为证明的主要方法;第三个阶段以物证或科学证据为证明的主要手段。(28)笔者认为其所述的第一次转化和对应的第一、第二阶段当无疑义,但关于第二次转化“物证为主”和第三个阶段“主要手段”的表述值得斟酌。随着司法文明的发展和人类发现真实能力的提高,物证或科学证据在诉讼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科学与司法的良性互动正改变着诉讼方式。但是物证或科学证据地位的提升并不意味着当事人和证人陈述作用的逐渐消失,实际上人证(包括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对案件事实具体的描述是物证或科学证据所无法取代的:交叉询问在英美法系国家仍被认为是发现真实最重要和最有效的途径,即使案件中运用了色谱分析、质谱分析或DNA检测等科学取证方法,法庭科学家也需要作为专家证人在法庭上以言词方式接受交叉询问。因而,从人证到物证的分期有待思量。
二、证据裁判原则的含义和要求
(一)证据裁判原则的含义
就刑事、民事和行政三种诉讼通用的定义而言,证据裁判原则是指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依据证据。但在刑事诉讼中,就实体方面而言,证据裁判原则是指认定犯罪事实必须依据证据。刑事诉讼奉行无罪推定原则,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2项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根据这一原则,被告人有罪的事实需要控方举证加以证明,而被告人无罪的事实不需要加以证明,只要控方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或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充分,就应推定被告人无罪。如果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裁判原则是指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依据证据,其隐含之义即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的事实之认定均需通过证据加以证明,这显然是不符合无罪推定原则的,因此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裁判原则实际上是指认定犯罪事实必须依照证据。
关于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裁判原则内涵的认识,日本立法的演化就表明两种不同的观点。日本1876年《断罪依证律》“凡断罪,依证据”表达的是刑事诉讼中证据裁判原则的基本内涵为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以证据为依据的观点,而现行《日本刑事诉讼法》“认定事实,应当依据证据”表达的是认为案件事实(应包括有罪事实和无罪事实)的认定必须依据证据的观点。这两种观点也影响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如韩国《刑事诉讼法》第307条即采“案件事实说”,规定“认定事实,应当根据证据”,而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154条则采“犯罪事实说”,规定“犯罪事实应依证据认定之,无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
基上,在刑事诉讼中将证据裁判原则表述为认定犯罪事实必须依据证据更合理,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或制定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证据裁判原则之时,可采用“认定犯罪事实,必须以证据为依据”之表述。
(二)证据裁判原则的基本要求
现代法治意义下的证据裁判原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
1.作为认定犯罪事实和作出裁判依据的证据必须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可采性。大陆法系要求证据具备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英美法系通常强调证据的关联性和可采性,要求证据不但在实质上与案件有关联,而且在形式上必须符合法律的要求。我国学界曾长期主张证据需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笔者赞成“三性说”,但将其修正为客观性、关联性和可采性。证据必须同时具备这三方面的属性,也即证据必须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否则就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在可采性问题上,应当明确的是,凡不具备可采性要件的证据应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针对的是非法取得的证据,要求将非法取得的证据排除于诉讼程序之外,这也是证据裁判原则的题中之意。2010年两院三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正式以单独司法解释文件的形式规定了这一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够强化公安司法人员的证据意识和程序意识,有效遏制刑讯逼供,提高案件质量,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正是由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使得按照证据裁判原则的要求保证证据的可采性成为现实的可能。因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必将为正在进行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所正式规定。
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特点:第一,可以进行非法证据排除的诉讼阶段包括审查批捕、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排除主体包括检察院和法院。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其一,我国的检察机关不是当事人化的诉讼一方,而是主要承担公诉职能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它有权监督侦查机关,排除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是其职责所在。其二,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阶段由检察院实施非法证据排除具有有效的隔断作用,由检察机关提前将非法证据排除,可以隔断法官与非法证据之间的接触,以排除非法证据对定案裁判的影响,实现实体正义。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应当将侦查机关也作为排除非法证据的主体,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无论外国还是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基本的意义都在于制约侦查权力和监督侦查行为,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常言的“震慑警察”的效力。非法证据本身往往即“产自”侦查机关,侦查机关固然可以主动放弃使用非法证据,但这与排除规则所含的外部监督的意义不同,因此将侦查机关列为排除主体不符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般原理。第二,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持审慎态度。我国对排除非法实物证据设置了极高的门槛:实物证据只有同时满足“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和“可能影响公正审判”,而且无法进行“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才会被排除,这表明对排除非法实物证据持极谨慎的态度。笔者认为,由于实物证据的不可替代性及其在证明案件事实方面的重要作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均持自由裁量排除原则,但我国司法解释对实物证据的排除标准过高,实际上使得任何非法实物证据均难以排除,这在修改刑诉法时必须加以纠正。有论者认为应当修改为实物证据“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排除,笔者对此表示赞同。第三,被告人一方需要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6条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应当要求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这是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滥用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权,并为司法机关审查是否需要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提供条件,这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加以确认。
2.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必须按法定程序进行审查判断。证据审查判断的过程贯穿于整个诉讼活动,但最为重要的是法庭上依法进行的审查判断活动。作为作出裁判依据的证据必须在公开的法庭上出示,并经过控辩双方的充分质证,由裁判者作出最终是否采纳的决定。凡是未经依法审查判断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依据,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从发现案件真实的角度看,证据的审查判断程序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也是一个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诉讼中难免会出现证明力不强甚至完全伪造的证据,通过审查判断程序,尤其是法庭上的举证质证程序,司法人员能够更好地判断各个证据的真伪以及证明力的大小,逐步地加深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从而最大限度地使其对案件的认识与客观事实相符合。第二,从诉讼权利保障的角度看,证据经过法定审查判断程序也是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重要内容。正因为如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进一步规定:“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3.作为裁判依据的所有证据经过综合审查判断必须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也就是说不但没有任何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或作出有罪裁判,证据因内容或形式上不符合法定要求而被排除的等同于没有该证据,而且证据不充分也不得认定犯罪事实或作出有罪裁判。对此下文将予以详细阐述。
(三)证据裁判原则与口供
证据裁判原则要求的认定犯罪事实必须依据的证据,当然是指《刑事诉讼法》第42条所规定的全部七种证据,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即口供。但笔者认为,据以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主要不是指口供,而是指口供以外的各种证据。理由如下:
第一,从历史渊源和立法目的的角度看,如前文所述,证据裁判原则是反对口供裁判主义的产物。确立证据裁判原则旨在降低口供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地位,提升其他证据在诉讼中的作用。无论在国外还是在中国,证据裁判原则的重要意义不是为了取代神判,而在于防止口供至上和刑讯逼供现象。刑讯不仅可能导致错案的发生,其运用本身也是对人的权利和尊严的严重侵害,证据裁判原则力图削弱口供在定案中的意义,从而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在当代中国,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绝,在这种情况下,将证据裁判原则中所指的证据理解为主要指口供之外的证据,是极为重要的。
第二,从我国的立法情况看,在中国语境下,证据裁判原则中的证据也应当主要指口供之外的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一规定将“证据”与“口供”作了一定剥离,其中证据仅主要指除了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
与上述观点相联系,对口供补强规则在中国的运用应当有自己的理解。西方的口供补强规则通常仅以增强证据证明力为目标,例如在美国“各司法区信奉这样一种要求,就是欲支持一项供认为基础的有罪认定,该供认必须为审理中提出的其他证据所佐证。”(29)《日本国宪法》第38条第3款规定:“任何人在对自己不利的唯一证据是本人的自白时,不得被定罪判刑。”而中国的口供补强规则是指要判定被告人有罪,不能仅凭被告人的口供,尚需其他证据加以补强,并且补强的程度要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当然西方也有学者对补强的理解与我国非常接近,例如墨菲就认为:“所谓‘补强’即要求某类证据以其他的独立证据加以印证或支持,以使该证据反映的事实诸如对犯罪行为的定罪等是足够充分的。”(30)根据口供补强规则的一般定义和原理,其他证据对口供进行印证或支持,以补充口供本身对某一事实的证明,即口供为主、以其他证据补强之。但我国的法律并非如此对待口供与补强证据的关系,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来看,口供与补强证据已不是主次关系了;相反的,补强证据已经超越口供成为定案的主要依据。目前法律对共犯口供是否可以作为其他共犯口供的补强证据的问题尚未作出明确规定,我们认为共犯的口供仍然是“被告人供述”,如果可以仅凭共犯的供述定案,无疑有“轻信口供”之嫌。因此,不能仅仅以共犯的口供作为补强证据,即使共犯的口供相互一致,也应当寻求其他证据来补强。
三、证据裁判原则与证明标准
证据裁判原则要求对全部可采纳的证据的综合审查判断所认定的事实需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证明标准是事实裁判者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所应达到的法定程度。从哲学的角度看,证明标准实际上是法律规定的裁判者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相符合的程度。裁判者的结论永远是主观的认识,而证明标准的设立即通过法律要求主观认识尽可能地符合客观事实。对此,首先有两个问题需要作出回答:第一,案件是否有客观存在的本源事实?对此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案件是否发生、如何发生,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以裁判者的意志为转移,案件事实一旦发生,始终独立于办案人员之外而客观存在,永远只存在一个客观存在的、具有确定性和过去性的特征的案件本源事实。第二,能否通过证明达到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相符?笔者对此的回答也是肯定的。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识论原理和诉讼证明实践,办案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可以达到与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相一致。
笔者认为根据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平衡的理念,在设立证明标准时,要满足以下两个方面的要求:第一,刑事诉讼的定罪标准要达到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标准,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减少错案的发生;第二,在必要情况下要适度降低定罪标准,以适当满足司法的现实需要。在两方面要求的关系上,应当以最高标准为基本要求,以适度降低标准为必要补充。
(一)关于我国刑事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解读
在刑事诉讼中如何设立证明标准事关重大。从国际上看,目前主要有两种刑事证明标准,第一种为大陆法系的“内心确信(自由心证)”标准,第二种为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两者均为主观证明标准。而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的规定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一个主客观相结合的证明标准:其中“案件事实清楚”是主观标准,是指事实裁判者在认识上、心理上对事实已经“清楚”、“明白”;“证据确实充分”是客观标准,要求证据客观上在质和量两方面达到“确实”和“充分”的程度。
我国“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标准的确立是历史的产物和司法经验的总结。新中国建立前在革命根据地颁布的各个涉及刑事案件处理的法令文件就常包含有“事实足信”、“证据确凿”之类的措辞,而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各级人民法院刑、民事案件审判程序总结》指出,在法庭调查阶段,必须把案件彻底查清,取得确凿的证据,被告人的供词,必须经过调查研究,查明确与客观事实相符的,才能采用。(31)1979年刑事诉讼法明确确立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刑事证明标准,这一标准也得到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沿用以及一系列相关司法解释和法律文件的认同。
然而学界对此标准存在着争论与质疑,形成了多种观点,具有代表性的有排他性(唯一性)标准、确信无疑标准和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等。(32)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相关机关曾多次就刑事诉讼的定罪标准作出具体说明和解释。在2006年11月举行的第五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解释“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时指出:“特别是影响定罪的关键证据存在疑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得出唯一结论的,就应当坚决按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裁判标准,果断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33)这里他把“结论唯一”与“排除合理怀疑”加以结合。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对“证据不足”作出解释:“(1)据以定罪的证据存在疑问,无法查证属实的;(2)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缺乏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的;(3)据以定罪的证据之间的矛盾不能合理排除的;(4)根据证据得出的结论具有其他可能性的。”其中第四点可反面推导出,“证据确实充分”是指根据证据得出的结论没有其他可能,即要求结论是唯一的。2010年两院三部《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明确了认定被告人犯罪事实应采用“结论唯一”标准,其第5条规定:“办理死刑案件,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证据确实、充分是指:(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四)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五)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这是“结论唯一”首次出现在司法解释文件之中。
(二)关于“结论唯一”标准问题
笔者赞同将定罪的最高证明标准确定为“结论唯一”,认为将“结论唯一”标准作为刑事定罪的最高证明标准是合理的,不仅可能达到而且有必要达到。首先,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如前文所述,司法人员的认识与案件客观事实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能够达到一致。其次,从价值取向的角度看,刑事诉讼涉及人的生命权、自由权这些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一旦出现冤案错案,则可能对公民权利造成巨大损害,而“结论唯一”的证明标准体现出对这些权利的极端重视,能够避免冤枉无辜,保证实体公正,有效维护人权。最后,“结论唯一”的证明标准也与联合国《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关于死刑证明应该达到“明确和令人信服”以及“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标准的表述一致。(34)
坚持“结论唯一”标准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凸显出其自身价值。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1月1日收回死刑核准权以来,在审核死刑案件中特别强调坚持“结论唯一”的最高证明标准,因而在四年半的死刑复核过程中,至今尚未出现一起事实认定错误的冤案。相反,在一些地方法院,由于没有坚持“结论唯一”,导致出现了多起错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如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等案件,均与没有坚持“结论唯一”标准有关。从这一正一反两方面的司法实践事实可见,刑事案件的定罪标准应以可能达到的最高证明标准即“结论唯一”为标准。
但必须指出,坚持“结论唯一”标准,并不意味着要求所有案件事实的细节都必须完全查明且其结论都必须是唯一的。“结论唯一”是指对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达到唯一的程度,具体而言“主要事实”指:(1)犯罪事实是否已经发生;(2)实施犯罪的主体是否为被告人;(3)从重量刑的情节,特别是据以判处死刑的从重情节。至于案件的某些细枝末节,则不必也不可能按照“唯一性”的标准全部查明。
(三)“结论唯一”与“排除合理怀疑”的立法抉择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5条规定了“结论唯一”标准,第33条规定“依据间接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结论是唯一的,足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就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但“结论唯一”和“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即“排除合理怀疑”是两个层面的证明标准,两者要求的严格程度是有区别的。
关于“排除合理怀疑”,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解释,是指要求“达到接近对有罪确定无疑的主观状态”(35)。尽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直不愿意对“排除合理怀疑”作出量化,但根据对美国联邦法官的调查问卷显示,171个法官中有126人认为“排除合理怀疑”需等于或高于90%的确定。(36)美英的学者认为:“如果我是事实裁定者,我会考虑我自己关于被告人有罪的确信程度,范围是从0到100,除非我确信的程度超过95%的范围,否则我不会赞同裁定有罪。”(37)“超出合理怀疑的证明没有准确的定义。一些法学家认为这是指每个陪审员必须95%或99%相信被告人有罪;另一种意见认为若没有其他对证据的解释是合理的,而起诉方已经完成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38)“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法律寻找的是最大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证据不一定要达到确定的地步,但它必须达到极大可能性的程度。超越怀疑的证据,不是达到没有一丝怀疑的程度。”(39)
由此可见,“排除合理怀疑”与“结论唯一”标准不同,结论唯一即确定无疑、无任何其他可能,量化言之,其确定性为100%,至少应是99.99%。笔者认为,对于主要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坚持达到“结论唯一”的程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刑事判决,特别是死刑判决不发生冤判错杀。这里还有必要指出,如前文所述“案件事实清楚”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状态,和“排除合理怀疑”同属主观标准,如果像有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将“证据确实充分”解释为“排除合理怀疑”,那么“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就成了一个从主观-客观-主观的标准,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和理念上的混乱。
当然,由于英美法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影响,“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为许多国家所接受,一些联合国文件也承认了这一标准。例如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1984年通过的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的一般性意见中指出:“有罪不能被推定,除非指控得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另外,“排除合理怀疑”与“结论唯一”标准虽有不同,但也存在一定的互补性。毕竟要求在每个案件的主要犯罪事实证明均达到“结论唯一”的最高标准并不现实,将“排除合理怀疑”与“结论唯一”标准在实践中互补适用,这也许体现了应然和实然、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但证明标准涉及认识论与价值论的复杂理论问题,也涉及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如何平衡的困难问题,无论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我国现行规定的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否修改、怎样修改,这个问题在理论上的争论和实践中的困惑将继续存在,它像迷宫一般让我们不断探索下去。但我们要牢牢记住一条根本的原则,那就是:保证无辜者不受惩罚的价值远远高于有罪者必须受到惩罚的价值。
注释:
①《世界著名法典汉译丛书》编委会:《萨利克法典》,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②参见[英]萨达卡特·卡德里:《审判的历史——从苏格拉底到辛普森》,杨雄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0页。
③参见[英]梅兰特:《普通法的诉讼形式》,王云霞、马海峰、彭蕾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8页。
④[英]爱德华滋:《汉穆拉比法典》,沈大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⑤同上注,第59页。
⑥转引自陈光中:《陈光中法学文选》第1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1~52页。
⑦[东汉]王充:《论衡·是应》。
⑧参见《墨子·明鬼》。
⑨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修订版),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页。
⑩对圣殿骑士团的审判,参见郭建淮:《圣殿骑士团兴衰论》,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
(11)[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二卷):新教改革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影响》,袁瑜琤、苗文龙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02页。
(12)参见[英]克里斯蒂纳·拉娜:《巫术与宗教:公众信仰的政治学》,刘靖华、周晓慧译,今日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6~37页。
(13)《唐律疏议·断狱》“八议请减老小”条。
(14)[清]薛允升:《唐明律合编》(五),商务印书馆发行《万有文库》第二集七百种之134,第699页。
(15)《清史稿·刑法志》卷一百四十四志一百十九刑法三。
(16)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46~247页。
(17)《唐律·断狱》“讯囚察辞理”条。
(18)《清律·刑律·断狱》“故禁故勘平人”条。
(19)陈光中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0页。
(20)《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248页。
(21)《德国刑事诉讼法典》,李昌珂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页。
(22)《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黄道秀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23)同前注(20),第292页。
(24)同前注(21),第101页。
(25)[德]Claus Roxin:《德国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台湾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129页。
(26)参见[日]松尾浩也:《日本刑事诉讼法》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亦可参见[日]土本武司:《日本刑事诉讼法要义》,董璠舆、宋英辉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310~311页。
(27)这些法律的具体条文可参见何家弘、张卫平主编:《外国证据法选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
(28)参见何家弘:《神证·人证·物证——试论司法证明方法的进化》,《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年第4期。
(29)[美]约翰·W·斯特龙等:《麦考密克论证据》第5版,汤维建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4页。
(30)See Peter Murphy,Murphy on Evidence,Blackstone Press Limited,6th ed.,1997,p.505.
(31)参见李玉华:《刑事证明标准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页。
(32)关于定罪标准的各种观点,具体可参见宋英辉、汤维建主编:《证据法学研究述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5~368页。
(33)王斗斗:《“六个坚持”指导刑事审判 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法制日报》2006年11月12日。
(34)联合国《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条规定:“只有在对被告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
(35)Jackson v.Virginia,443 U.S.307,315(1979).
(36)Lawrence M.Solan,Refocusing the Burden of Proof in Criminal Cases:Some Doubt About Reasonable Doubt,78 Tex.L.Rev.105,110(1999).
(37)Jon O.Newman,Beyond "Reasonable Doubt",68 N.Y.U.L.Rev.979(1993).
(38)[美]爱伦·豪切斯泰勒·丝黛丽、南希·弗兰克:《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陈卫东、徐美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39)[英]理查德·梅:《刑事证据》,王丽、李贵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77~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