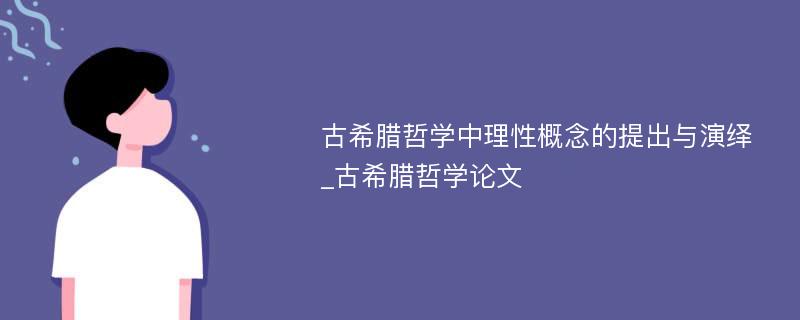
古希腊哲学中理性观念的提出及其演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希腊论文,理性论文,观念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0) 04-0032-08
理性主义传统在西方哲学发展中渊源流长,理性精神构成了西方哲学的主流。古希腊哲学从其产生之日,就把认识整个世界,普遍地把握世界当作自己的神圣使命。无论是早期自然哲学家用水、气等元素解释万事万物的存在与来源,还是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萨哥拉提出逻各斯、努斯以说明世界的运动和变化,亦或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创立理性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其用意都只有一个,即把理性的世界理性地加以解释和把握(胡塞尔语)。理性主义源起于古希腊哲学,经历了几千年演变,其间有关理性概念的理解和把握,无论就其表现形态、特征,还是其内在构成、功能和地位、作用等等,都不断变化和发展着。但是,至今理性的核心内容仍然可以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λóros)和阿那克萨哥拉的努斯(νoνs)加以概括。赫拉克利特和阿那克萨哥拉提出逻各斯、努斯概念,苏格拉底、柏拉图则进一步发展其实质内容,最后,亚里士多德将努斯与逻各斯统一于“目的性”之中,构成了对理性概念的初步理解,由此奠定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基石。但是,古希腊哲学之后的发展却不断地加剧着本属理性自身内部的两种冲动或属性的冲突和对立。进一步说,从苏格拉底开始就种下了这种对立、冲突的种子,乃至于最终演化出极端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对执,尽管其间经历了黑格尔对理性自身逻各斯规范性和努斯的自我超越性的对立统一的深刻揭示和把握。
一、逻各斯与努斯的提出及其对世界的规范性和动源的探寻
古希腊早期哲学家试图从自然中找出某种能产生世界万物及其变化的根据,也即“本原”或“始基”。这就是泰利士的“水”、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或无定形)、阿那克西米尼的“气”。但是,由于其表达的感性局限性,这些元素均无力完成其作为普遍性的始基的使命。毕达哥拉斯的“数”,由于超越了感性经验的质的规定,而实现了对世界本原探究的飞跃,但依然未能真正摆脱感性世界的量的规定。然而,由于“数”的概念包含着“一”的原则,并且是在一定的关系中得以确定的,这就为赫拉克利特提出“逻各斯”概念作了思想准备。
赫拉克利特提出“变”的原则,“一切皆变”,无物常在,仅“一”常存,有与无存在于对立统一之中,存在于万变之不变中。“对立物存在于同一东西中。”(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00页。)赫拉克利特对“变”这个概念的具体阐释,带来了历史转折。他以火作为万物的始基并用火来体现变的原则。火与水、气、无限相比,不再是盲目被动的可塑性,也不再需要外来的力量来给它定形,而是自己塑造或创造自身,并为自己定形。“这个世界对一切存在物都是同一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注:《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页。)火是有定形和无定形的统一,是作为“变的变”,是自己运动的,具有自身的分寸、规律和尺度,这个尺度就是“逻各斯”(λo′ros)。赫拉克利特残篇开头就向世人提出(λo′ros)(逻各斯)。他说:这“(λo′ros)(或译道)虽然万古长存,可是人们在听到它之前,以及刚刚听到它的时候,却对它理解不了。一切都遵循着这个道,然而人们试图像我告诉他们的那样,对某些言语和行为按本性一一加以分析,说出它们与道的关系时,却立刻显得毫无经验。另外还有些人则完全不知道自己醒时所做的事情,就像忘了梦中所做的事情一样。”(注:《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哲史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2页。)在他看来,“λo′ros”(逻各斯)是大家共同享有的,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遵从的共同的东西,尽管大多数人都自以为是,好像都有自己的逻各斯一样,但逻各斯的本性不是多,而是一,即统一性、普遍的东西。
赫拉克利特把这种普遍性,这种在对立中统一(有和无是同样的东西),叫做命运,它是变化的尺度、规律、语法,它既要超越感性世界又要对此加以规范。它是变中不变,是贯穿在全体存在中的绝对关系。它不是抽象的数或量的关系,而是质的关系,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存在与非存在的统一之变就是最基本最普遍的对立统一关系。“我们踏进又不踏进同一条河,我们存在又不存在。”(注:《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哲史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3页。)赫拉克利特将存在与非存在作为变本身的两环节,引入哲学思维,将它们的关系看作是变化的规律、尺度、逻各斯,这种含义的逻各斯最后演变成“理性”的意义,构成理性的重要内容。
赫拉克利特这位“爱哭泣的哲学家”,不管人们像每人都有自己的逻各斯那样行动,但他却仍然坚信逻各斯对所有的人都是相同的,逻各斯是一。赫拉克利特提出逻各斯作为对于世界的安排或结构,同时给变动不居的世界以一“定形”即赋予绝对的不确定性(火)以绝对确定性。逻各斯代表着普遍的尺度、规律、语法。它要超越感性世界来对之加以规范。后人对逻各斯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万变不离其宗,即它是一种精神活动,但却是有客观效准的活动,是展示给人看并能得到别人同意的活动。
阿那克萨哥拉用“种子”取代了爱利亚学派唯一不动的存在和恩培多克勒的“四根”(水、气、火、土),他认为无数在质上根本不同的种子构成世界,自然界的各种事物都是由种子的结合和分离造成的,而努斯(Nous,又译心灵)则是这些多个存在的结合和分离的造成者。阿那克萨哥拉说:“将来会存在的东西,过去存在过现在已不复存在的东西,以及现存的东西,都是努斯(Nous)所安排的。”(注:《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哲史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9页。)他把心灵、思想或一般的心智认作世界的本质、认作绝对的推动者,心灵推动一切。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对于感性世界的超越和规范需要动能,“火”虽然是能动的,但本身还陷在感性世界之中。“火只是过程,还不是独立自存的规定者”,但“在‘心灵’里面存在着普遍性的规定,在心灵中有着目的、善。”(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54~355页。)从心灵中就可以引申出一切事物来。阿那克萨哥拉努斯的提出回应了这种需求,努斯是自身规定的活动性,代表心灵的能动性,它使理性灵魂最终跳出感性束缚,达到自身的目的。努斯的动能不再是感性世界中互相牵制、依赖的动能,而是超越感性世界的,因而(可看作)是终极本质的动能,是世界的原始动能。
阿那克萨哥拉努斯的提出,在一定意义上完成了古希腊哲学家将精神从自然物质中解脱出来的努力,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他说:“别的东西都具有着每一件事物的一部分,但是心灵(Nous)则是无限的、自主的,不与任何事物相混淆,而是单独、独立的、自为的。”(注:《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哲史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9页。)努斯自己规定自己,又规定对方,而进入自己建立的对立中,但却又消灭这对立,统治这对立,返回自身,这个活动就是实现自身的目的,返回心灵、思维的过程。努斯就是在自身规定中保持自身的东西,就是有精神理智活动的生命体。但是,努斯并不只存在于人那里,而且也是世界的真正本体,推动万物的原动力,是世界的普遍精神。潜存于阿那克萨哥拉努斯内的这种特性,对黑格尔自觉理性与绝对理性的和解思想影响颇深。
阿那克萨哥拉努斯的问世,开始以目的论代替物活论,人类的视界不再局限于维系精神自身为“一”,而且要使世界成为一,成为善的、真的世界。努斯是作为推动者贯穿并联结人的灵魂和整个世界的内在活动和目的。一方面,努斯的提出为解决“运动的开端”这一令古代哲学家伤脑筋的问题作了合理尝试和准备,“面对这一困境,阿那克萨哥拉以为在那个自我运动的,一向无所依赖的‘努斯’身上找到了特别的救星”。(注:尼采:《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周国平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5页。)另一方面,努斯的提出是直接针对一与多、无限与有限等难题的,它提示人们,用一般的感觉、理解是无法真正掌握无限的。无限是理性追求的一个对象,它折射出人类精神生发的转迹,必须超出感觉对象的范围在思想上把它作为理性的问题提出来。努斯的最本质的特点就是超越有限的、受束缚的、感性的事物而面对无限目的和自由的追求,它代表精神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这样,逻各斯与努斯的提出,既赋予了世界以秩序、规律,又提供了背后的推动者和原因。理性统治并推动世界,逻各斯与努斯的提出及结合,形成了古代最初的理性概念,也构成了西方哲学的理性概念的两个古代来源,蕴含着理性的逻辑规范性和自由超越性这双重意义的根芽。但是,在赫拉克利特和阿那克萨哥拉的逻各斯与努斯观念中,对于有关世界的根据或动力的揭示、寻求和设定并不是相互排斥、对立的,而是浑然不分的。这种状况,一方面说明这其中缺乏应有的分化、抽象和深究,反映出人类早期哲学思想的素朴性;另一方面,这种对世界的根据与世界的动力的探寻的浑然不分状态,正好折射出作为古人圣哲的赫拉古利特和阿那克萨哥拉面对世界、社会和人性的天然和谐、包容万物的心态,体现出理性自身那种原始的与社会、与世界、与自身的和解功能。而这种可贵的和谐、统一却为日后理性观念的进一步演进所打破,这里有没有其自身内在逻辑必然性,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
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努斯与逻各斯的发展及对逻辑规范性的凸现
苏格拉底由最初对阿那克萨哥拉的努斯抱以希望到痛苦的失望,他摒弃了阿那克萨哥拉只在解释最初的动因时才诉诸努斯的做法,而把努斯原则贯穿到底,发展出目的性概念以进一步解释努斯的作用。他宣称普遍的努斯精神是本质的东西,这种安息在自身之中的意识、不受现实限制,不受意识对现实的关系限制。思想、意识这个固定的东西,这个自在自为的本体、绝对自我保存者,它就是自己的目的,并被进一步规定为真理和善,以及“神”。苏格拉底把客观事物的真理归结到主体的思维、意识,强调人必须从他自己去找他的天职、世界的最终目的和真理,通过他自身实现自在自为而达到真理。这种以自身为目的,自我追求自己、自己实现自己,就是意识复归自己,正是在这种追求自身目的、复归的过程中,意识不断摆脱自己的特殊的主观性,而获得自在自为的普遍性,也即客观性,这并非外在的客观性,真理成了通过思维、意识而建立起来的间接性的东西。苏格拉底解释发展了理性的努斯精神,要求从意识自身中创造出真实的东西,引出真理。从这一方面看,他突出了理性的主体性、能动性和自我超越性。
但是,苏格拉底的所有对话都体现了超越感性的努力,他要通过“讽刺法”和“接生术”等辩证的方法从感性经验之中,从具体的事例发展出普遍的原则,使潜在于人们意识中的概念明确呈现出来;同时利用意识的否定力量瓦解通常被认定的、固定的思想观念,让它们与具体事物相互矛盾冲突。在超越感性世界的努斯冲动中,在意识不断追求自身目的、从有限目的达到无限的、从日常理性上升到神的理性的上升过程中,在这种主观活动中,同时产生和建立一种自在自为的东西、客观的东西,这就是普遍的理性逻各斯、普遍共相。黑格尔指出,根据苏格拉底的原则,“凡是精神不提供证明的东西对于人就没有效准,就不是真理。人之所以自由,就在于他无求于外;这就是精神的主观性。”(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6页。)这种无求于外的“主观性”恰恰构成了事物的“客观效准的东西”。苏格拉底认为人的理性是万物的尺度,并由此开启了寻求普遍的逻各斯的逻辑进程。黑格尔正是把这种思想发挥至极,他认为,凡是不能被言说的,无法通过理性表达的东西都是虚假的,也就不存在,理性是一切根据的根据,应从理性主体中抽绎出现实客体。苏格拉底对于逻辑普通性的凸现与极度的追求,一方面开启了人们对理性的逻辑规范、推演、抽象能力和功能的关注和发展,乃至奠定了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基本原则而成为西方理性主义之父、文明之父。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苏格拉底这种对逻辑普遍性、规范性的凸现和夸张,埋下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种芽,而遭到后人的严厉批判。尼采尖锐地指出:“苏格拉底是理论乐观主义者的原型,他相信万物的本性皆可究,认为知识和认识拥有包治百病的力量,而错误本身即是灾祸。深入事物的根本辨别真知灼见与假象错误,在苏格拉底式的人看来乃是人类最高尚的甚至唯一的真正使命。因此,从苏格拉底开始,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逻辑程序就被尊崇为其他一切能力之上的最高级的活动和最堪赞叹的天赋。”(注: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周国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12月版,第64~65页。)尼采批评苏格拉底将逻辑视作万事万物的本质和人类活动的最后根据,将人生的意义归结为对知识的追求,并将苏格拉底的逻辑中心主义看作是使西方文明误入歧途的罪魁祸首。其实,如果联系到现当代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思潮中对逻辑确定性、精确性的极度追求和夸张这种做法的思想渊源来看,尼采对苏格拉底的指摘并非没有道理。逻各斯中心主义在苏格拉底生后的逐步膨胀,乃至现当代西方科学主义思潮达到极至。尼采对苏格拉底的批判具有一定的“消毒”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逻各斯中心的扩张,维护了非逻辑的东西,如情感、常识等等的权力。逻辑不能包容一切,世界除了逻辑还有非逻辑的东西。
柏拉图把握了苏格拉底基本原则的全部真理,认本质是在意识里,认本质为意识的本质,绝对是在思想里面,一切实在都是思想。柏拉图的许多对话其目的也仅仅在于使一个普遍的表象得到意识,他扬弃了苏格拉底的局限于个人“灵异”之中的狭隘性,进一步认为独立自在的思想不只是自觉的意识之本质和目的,也是整个世界的本质。柏拉图将理念作为世界的本体,理念也即逻各斯,是普遍共相、抽象的实体,理念是思想通过自我运动同时推动万物超越感性世界之努力的结果,也即理性努斯由其自身的困惑、不安、自我否定而不断回忆自己、追求自己的结果。
柏拉图认为学习只是回忆,是这样一种运动,在其学习过程中,没有什么异己的东西增加进去,只是不断地实现自己的本质。这样他揭示出意识的真正性质,“心灵(努斯)即是以其自身为对象的东西,或者自己为自己而存在的东西。”在这种运动中生成的东西即逻各斯,“共相、类本身就是自己的生成。……它只是它自己的运动的起点,它的运动只是不断地返回于自身。”(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83页。)精神、意识通过不断的回忆、自我学习,把自身对感性的不断超越、对真理的不断向往这样一种强烈的努斯冲动,通过逻各斯的共相、理念表达出来;同时,逻各斯的共相、理念也只有通过努斯对感性世界的超越、飞跃才能达到,它们正是努斯冲动的生成和产物,真理的根源就在心灵、努斯之中。
进一步说,学习只是对于心灵的一种回忆。柏拉图强调灵魂是不灭的,因为灵魂是能思维的,思维本身是自由的,灵魂是自身运动的,而自身运动的东西是不死的、不消逝的。这样,自在自为的心灵、努斯的生命本质就在于意识到自我本身的绝对性和自由性。思维乃是共相的活动,但共相并不是抽象的,而是自己反映自己,通过自身的能动性所建立起来的。柏拉图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实际上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只有通过心灵、努斯的回忆、追求及灵魂的超升,普遍的东西、共相才得以实现和把握。因而,理念实际上是以普遍的内容来确定、表达心灵、思维和灵魂的生命冲动、自身活动。柏拉图的辩证法则正是试图在努斯的生命冲动、灵魂的不断回忆、超升中,以普遍、共相的方式把握对立统一的具体理念。黑格尔继承和发展了柏拉图的回忆说,他进一步引申了德语“erinnerung(回忆)的用法,把回忆看作‘探究自己’(成为自己)的问题,而要探究自己(成为自己)就要从外部世界的变化和繁杂中退而进入(自我)同一的意识最深处。”(注:Julian Roberts:German Philosophy - An Introduction,Polity Press in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1988,P75.)黑格尔对于理性矛盾的自我圆圈运动的揭示和对理性矛盾的自我和解之本质的把握,深受柏拉图的辩证法之影响。
柏拉图沿着苏格拉底指引的方向,通过逻辑的道路最终达到了一个纯粹思维、概念和精神的王国,一个逐步失却了感性意谓,没有血肉的阴影王国。同苏格拉底一样,柏拉图对后人的影响亦是双重的。一方面柏拉图观念王国的建立,为后人确定起一个内容丰富有规可循的精神世界,为人类初步确定起一个永远值得追寻的精神家园,使得人们的思想得以身由遨游,不再束缚于感性尘世的羁绊,使得人类的四处游荡的灵魂得以栖息。另一方面,从这里开始了逻各斯与努斯的分离与对立,并确立了影响西方哲学发展的主导原则,逻辑本质主义,从此逻辑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的决定性的标准和依据,理性就是逻辑,逻辑就是理性。但是,世界并不只是逻辑,还包含着非逻辑的东西,而逻辑的东西是以非逻辑的东西为基础的,并通过非逻辑的东西得以体现、展示。说到底,逻辑与非逻辑并非只是水火难容的对立,还有水乳交融的和谐。
另外,柏拉图的努斯的能动原则仍只限于人的灵魂,理念本身不具有能动性,努斯的能动性只限于由感性朝向灵魂(理性)超升的过程,当灵魂、努斯表现出能动性时,它还未达到理念、逻各斯,而当它到达理念、逻各斯时,努斯的能动性便丧失了。此外,他对努斯的能动性也没有具体的分析,更多的是假定和拟人化的比喻;同时,他对目的性的理解流于表面、日常化。因而,黑格尔指正柏拉图的理念“其中缺乏生命的原则、主观性的原则。”(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89页。)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是阴影王国,没有活力、缺乏生命、主体性的原则。努斯与逻各斯尚处于对立之中。
三、亚里士多德综合努斯与逻各斯的尝试及其局限
亚里士多德提出“最高形式”,弥补了柏拉图的不足。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和柏拉图的理念是同一个词(ειδos),形式内就有目的因,是一个事物的本质和目的。柏拉图把理念当作最普遍的共相,是目的和善,亚里士多德却进一步把理念(形式)规定为活动性,或者说亚里士多德把理念也看作是目的,但目的不是静止固定的东西,而是一个由潜能到现实的活动过程,活动性既是变化却保持自身同一,它是作为自身等同的变化而被设定为共相,是一种自己规定自己的活动,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目的概念,目的即隐得来希(ενγελεxειIα),它并非单纯内在(潜在)的、尚未实现的,它本身乃是最现实的东西,凡事莫不包含自身目的并实现其目的。亚里士多德指出:“世上各物并非各自为业,实乃随处相关。一切悉被安排于一个目的。”(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55页。)因此,目的也就是事物的形式(形式因)或本质。亚里士多德目的概念有两个重要特征:其一,它是推动者和被推动者的同一,不动的推动者就是目的本身,永远自身等同,它推动着,却只对自己发生关系,永远只以自己为对象。这便体现出目的作为自我实现的能动性、活动性;其二,真正的目的只能是“思维的思维”,“思辨地去考察一切,把一切转变为思想。”也就是说,真正的目的,是自我意识,是思维与思维的对象的同一,这是内在目的,它不同于以外物为对象的有限的外在目的,即不是目的与手段外在,而是手段就是目的本身。所以,真正的理性、作为理性的理性,也就是内在目的。在这里,努斯能动地建立起目的并借逻各斯而实现之。
在亚里士多德目的概念中形式与活动性的结合,便成了有规律或逻各斯的努斯,成了合乎理性的、摆脱了偶然性的实现过程,目的既是理念逻各斯又是能动的努斯活动,其本身就是本质的原因,又具有自我实现的推动力。最高的形式、最高的目的就是上帝,上帝是完美的努斯,是万物的原因,而人的努斯与上帝的努斯是一致的,通过逻各斯表达自己并以逻各斯的普遍共相将自己确定起来。上帝就是那无所不能的不动的推动者,它按照一定目的理性地、井然有序地、能动地推动着世界万物,使之趋向自己。亚里士多德通过目的概念也即“最高形式”或“隐得来希”进一步解决了古希腊哲学的根本问题:即在变动不居的现象世界的背后,如何思考统一的、永恒不变的存在;如何解答“作为存在的存在”为何物。
亚里士多德目的概念是他对理性概念的具体而全面的揭示和建构,在此,逻各斯成了有生命力的逻各斯,努斯的生命冲动则有内在尺度和规定性。“因此若以理性为至善,理性〈神心〉就只能致想于神圣的自身,而思想就成为思想于思想的一种思想。”(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54页。)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性就是自己以自己为对象和追求目的的“思维的思维”,自己意识自身的自我意识,是作为逻各斯与努斯相统一的“目的因”,或包含目的因在内的“最高形式”。至此,古希腊哲学中理性发展的两大原则:即代表理性本原冲动的生命原则、能动性原则努斯,与代表理性先天(客观)规范的逻辑原则逻各斯就合而为一了。(注:参见邓晓芒:《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6~57页。)亚里士多德这种包含着努斯原则与逻各斯原则的理性概念,不仅是对古希腊哲学的最高概括与总结,标志着古希腊哲学理性概念的完成,同时也奠定了其后西方理性主义发展的基础。其实,亚里士多德理性概念构成了黑格尔绝对理念的原型,而对于努斯与逻各斯矛盾对立统一的进一步深入地揭示和回忆,则构成了黑格尔理性自我矛盾与和解的基本线索。
亚里士多德尽管在目的概念中融合了理念逻各斯与能动的努斯,发展了古希腊哲学的理性观念。但是,在他那里,理性主要被认作为能力,是思想抽象,是“思想”思想自身的能力,一种抽象、判断、推理的思维能力。真正说来,亚里士多德还未能把理性理解为活动性,作为世界本体的活动性加以把握。这样,“如果理性只是被理解为能力,而不是被理解为活动性,则延续不停的思维将会是充满疲劳的,而对象就会比理性优越。”(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56页。)亚里士多德未能将理性真正彻底地本体化,不是将理性主要地理解为活动而是能力,那么,他将理念逻各斯与能动的努斯结合在理性的目的概念中,最终也只能是外在的结合,将这两者看作是理性的两种不同的能力而已。这样的理性观念是既无力实现自身的内部统一,也无力达到与外部世界的和解和统一。这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主要缺点在于:在各式各样现象被他的哲学提高到概念里面之后,这个概念却又分解为一系列彼此外在的特定的概念,那个统一性、那个绝对地把它们结合起来的概念却没有被强调。”(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81~382页.)亚里士多德所缺乏的就是能将一切统摄于自身之内,消解一切、包容一切的绝对统一性概念,亚里士多德所缺乏的也正是将他的目的概念提升、充实为——既为世界的存在运动发展提供根据和规范的逻各斯,又为其提供动能和活力的能动努斯的——这样一种绝对理性。而“这正是后来的时代所必须完成的工作。”(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82页.),这一工作在经历了几千年漫长的曲折劳作之后,终于在黑格尔那里得以真正完成。黑格尔整个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绝对理念(绝对精神),实现了逻辑规范性的逻各斯与自我超越性的努斯的对立统一。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既是对亚里士多德目的概念的继承、发展和完成,同时也是对传统的西方理性主义的集大成。(注:关于黑格尔“目的理性”可参见拙作《黑格尔“目的理性”的确定及其意义》,《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2期。)
四、古希腊哲学理性观念对后世的影响
古希腊哲学在解释、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矛盾关系中,首先要面对一与多、本质与现象、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等矛盾。其中,以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萨哥拉、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为代表的哲学大师,他们倾向于将这些矛盾纳入理性之中,将自然现象中的矛盾、人类社会中和思维活动中的矛盾以及自然、社会、人相互之间的矛盾都内化为理性内部的矛盾,并把理性本体化,视其为万事万物存在、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根据和本源。这样,在古希腊哲学中对于理性的揭示和把握就成了解释和把握其他一切问题的关键,或者说,其本身就包含着对其他问题的解释和把握,其实,这也成了整个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古希腊哲学初步揭示、暴露出了理性观念的内在矛盾结构:努斯代表着理性本原性主观能动的冲动(不确定性),逻各斯代表着理性客观制约的规范(确定性),两者构成了理性的两种倾向和特征。从总体上看,古希腊哲学初步探索到两者的不一致并(本能地)试图加以调合(和),但并未真正地意识到两者的对立矛盾,或者说并未将主客对立真正纳入理性之内作为同一个东西的矛盾的两方面之对立。对于理性的理解处于笼统的原始统一阶段,两者总是不可分地纠缠在一起,虽然各个哲学家各有偏重,但却未出现极端孤立的努斯或逻各斯。尽管如此,古希腊这一对理性范畴的提出却给2000多年西方哲学理性观的发展制定了最基本的框架结构,这一结构在后世各种各样的理性形态中始终于思想深处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并以各种不同的变相,在各种不同的层次上展示自己持久的生命力。
在中世纪哲学中,抽象的逻各斯变成了形式主义的逻辑,努斯在信仰领域越来越与非理性的东西纠缠在一起,淡化了理性色彩。努斯原本是超越感性而朝向理性的上升冲动,但在此却主要成了达到神秘信仰的超越。这样,努斯实际上神秘化了,成了一种神的感召,由此也将上帝本身的逻各斯(道)变成了神秘的创世行为。从这里折射出努斯自身内包含的非理性的倾向。
近代哲学则把这两种精神重新拉回到理性的基础上,使它们再次进入了互相渗透、融合、分化的关系之中。与古希腊哲学的理性概念相比,近代哲学的理性概念也有了质的飞跃,理性内部含糊不清的逻各斯与努斯的差异发展为理性自身的对立,理性自己与自己的对立,进而演化为以思维与存在、理性与现实相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制约性的对立。尽管大多数哲学家都致力于努斯与逻各斯的统一,但是,却因以有限的概念、范畴,以形式逻辑的方法、推理去追求、把握无限的对象、概念,在“理性的通有的驱迫力”下寻求一个无限的东西,但却沉溺、局限于知性的抽象、片面、有限之中,没有能发展出辩证的理解和把握。最终却都陷入冲突、对立的困境,并最终导致了理性的危机。近代哲学在对古希腊理性观念的大力推进和发展的同时,却凸现出理性努斯追求无限性与知性的逻各斯规范、确定性之有限性之间的尖锐对立。解决这种对立,并将这种对立理解、发展为矛盾的对立统一,就引发出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性发展的逻辑进程。
德国古典哲学深入、具体而又全面地发挥出古希腊理性观念的实质内容,它是从理性自身开始的,其原则是:理性认识到它自己就是一切存在的根基。但是,与古希腊哲学、与近代哲学相比,它对于理性概念的把握却有着本质的差别。德国古典哲学不再一般地将理性看作是世界的本原和根据,或者说,它不只是仅仅把理性看作是本原性的存在,而是将理性作为本原性的活动,由理性中推导出一切,“理性为自然立法!”理性成了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根源。这就不再象近代哲学那样,将理性形式化,只用形式逻辑去规定理性,只有理性的客体形式,而没有发展出理性的能动性和主体的形式。德国古典哲学代表着理性发展的崭新阶段,其中突出标志即努斯与逻各斯矛盾体现为主体与客体矛盾。一方面,按照努斯原则从主观能动性中推导出客观的、必然的东西;另一方面,从逻各斯原则出发,由客观的、必然的东西发展出主观精神,返回到自己。确信对于客观的、必然的东西认识和把握,正是努斯原则通过逻各斯的规范性表达自己、外化自己、实现自己,也即理性的自我运动和自我认识,达到主体与客体的绝对同一,并确信主体与客体的绝对同一构成了世界的绝对本体和理性自我认识的最高境界。
古希腊理性观念的核心内容及其所代表的基本原则,在黑格尔哲学中得以彻底的贯彻、完成和全面的发展。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只是阐述理性连续不断地获得明确的自我意识进而达到概念形式的那种无限发展过程。哲学将理性的自我认识当作自己的目标,把人类理性呈现其活动必需的形式和原则自觉表现出来,并把它们从原始的知觉、感情和冲动的形式转化、提升为概念的、逻辑的思想形式。理性就是绝对理念的进程。人的意识在未达到纯粹逻辑概念之前经过了意识、自我意识到理性的发展。人类意识发展到理性阶段便确信:“自己即一切实在这个确定性”(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7页。),主体确信客体就是自身的现实。理性不是僵硬的抽象观念,也不是软弱无力的应该(Sollen),而是具体概念、客观概念,是世界万物的本质和根据,是由其内在的努斯能动性、概念的本性推动而呈现出充满活力的现实运动和过程。它既是一个逻辑上的必然的过程,又是绝对理念自我认识的过程,还是作为客观本体自由地自我发展、外化和展示复又回归于自身的过程。黑格尔整个理论体系都是围绕理性展开和发展的,理性作为本体、灵魂、辩证法构成了一个首尾贯通的圆圈运动。黑格尔继承了古希腊哲学中逻各斯与努斯的理性传统,并通过对整个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批判和改造,将理性的努斯原则作为理性的自我超越性、历史超越性,将逻各斯原则作为逻辑规范性、作为包含着个别性的具体普遍性,而有机地结合在理性概念之中,实现了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制约性的对立统一,由此实现了理性与现实的矛盾和解。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的理性概念。它既是前人艰辛的思想劳作在黑格尔这里的开花结果,又是黑格尔为后人种下的理性的新的种子。但是,不幸的是在黑格尔身后,黑格尔实现了的理性自我和解又被人为地再度打破。更为有趣的是,黑格尔的“不肖子孙”各自掘取黑格尔理性观念中的一部分而将其发展、夸大到极至,却自以为完全地抛弃、逃避了黑格尔。现当代西方哲学中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极端对立正是对这种情形的真实写照,前者将本属完整的理性观念中的逻各斯的规范性、普遍性发挥到顶点,就像后者将本属完整的理性观念中的努斯的自我超越性、历史超越性凸现到极点一样,而陷理性于自我对立之中,并由此折射、引发、派生出人与自然、社会和他人的矛盾对立,乃至于人与自己的矛盾冲突,真可谓,“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令人欣慰的是,将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重新整合、统一在辩证理性之中的重建的努力和劳作,已出现在人类的地平线上。
收稿日期:1999-10-18
标签:古希腊哲学论文; 逻各斯论文; 柏拉图主义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哲学史讲演录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哲学家论文; 苏格拉底论文; 能动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