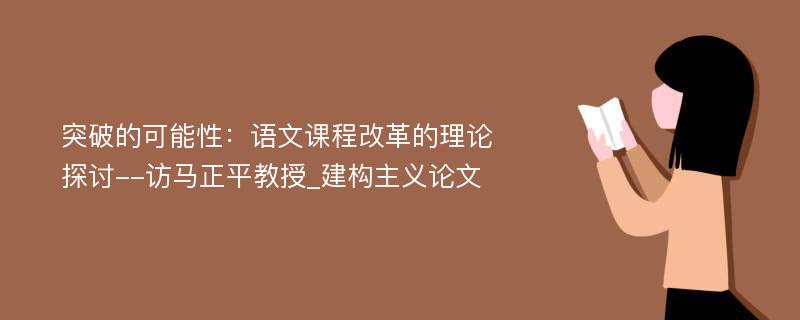
突破的可能:语文课改探究的学理取径——马正平教授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理论文,课改论文,访谈录论文,语文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杨元林(以下简称“杨”):马老师您好。我们有种感觉,好像语文新课程改革正进入了“高原反应期”。您怎么看待目前语文课改碰到的一些现实问题? 马正平(以下简称“马”):我以为主要的原因在课程本身。根本的问题是语文新课程的“课程内容”的“空缺”或者说“含混不清”,语文教师并不清楚自己到底应该教什么,学生自然也不清楚自己在语文课程中究竟应该学什么。 杨:教学内容的不确定性,确实是当前中学语文教学存在的严重问题,也是一线师生挥之不去的困扰。就这一点看,语文新课程好像还不如以前的“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的内容让人觉得踏实。请问,中学语文新课程的“课程内容”为什么会空缺呢? 马:原因有三:第一是“语言学语文知识的陈旧”;第二是“心理学、教育学的僭妄”;第三是语文新课程改革学科专业机构及学科专家的缺位。 首先说第一点。20世纪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基础上的“语、修、逻、文”的语文知识是关于语言、文学的结构的知识,而并不是语文交际行为的技能知识,而新课程所迫切需要的是关于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交际行为的技能知识,而这种知识当时没有产生出来,所以这次语文新课程改革真正所需的“言语学”(不是“语言学”)语文知识是缺席的。 第二点,各个学科新课程改革基本方案是由教育学界课程教学论专家设计出来的。这里就存在课程理念如何接得教学实践之地气的问题。真正的教学方法的创新来源于真正科学有效的学科知识的创新发展,离开了科学有效的学科知识,仅仅运用教育学、课程论的知识是不能进行学科课程改革与教学方法改革的。由于心理学、教育学的课程与教学理论在课程改革中“占据”理论“高地”,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具体学科知识的更新在课程改革中的重要性,造成心理学、教育学的僭妄。 第三点,我觉得理想的“语文新课程改革”应该建立在实践论哲学和默会性语文知识体系上。语文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建构者都是著名大学的语言学、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专家,他们在课程上位为我们梳理了相对完整、严谨的学理方向,他们的专业学术眼光和视野在课程改革中发挥着高屋建瓴、鞭辟入里的引领作用。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正视这样的现实:语文新课程改革的“课程工具”的设计、建构与宏观指导、示范、引领是需要守望着语文的原野、拥有实践性经验的学科专业机构和学科专家的“在场”的。 杨:作为一线教师,我们迫切希望语文课程改革迈出更为科学而富有践履价值的步伐。大家都知道您在语文学科上研究很深很多,取得了丰硕成果。您认为,目前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性质的“语文新课程体系”?如果要让您来主持下一轮语文新课程改革,您会做些什么呢? 马:通过30多年来非构思写作学、行文措辞学、言语学、时空美学、阅读学的研究与建构,我以为,现在已经完成了语文新课程改革所迫切需要的语文新知识的建构,在这种语文新知识背景下,进行真正科学有效的语文新课程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我认为,目前我们国家需要一种建立在“新现代主义”或者说新哲学观、新知识观基础上的“语文新课程体系”。如果我有机会来主持国家语文新课程改革,我建议做好“务虚”的三件事。 首先,建议变革目前新课程改革的哲学基础;其次,试图树立新的知识论理念;最后,纠正对“建构主义”的误解。 要想建构新的“语文课程体系”,我以为首先要进行“哲学基础”的变革。我们必须明确,语文交际(写作、阅读、说话、聆听)活动本身是一种实践活动,即创造言语作品、作品意义和美的实践活动。中国几千年来的语文教育活动都是以培养这种实践活动的思维操作模型为使命的。例如,明清时期,语文教学的最高理想就是进行“起—承—转—合”的写作章法规范的培养,其实质就是非构思写作学中所谈的“重复与对比”的赋形思维。实际上,陆机的《文赋》和刘勰《文心雕龙》里“文之机枢”的《原道》《宗经》《征圣》,以及严羽的《沧浪诗话》思考的就是这些东西,而王夫之的《姜斋诗话》把写作赋形思维阐释得更加清楚。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将西方建立在认识论基础上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文艺学、修辞学等思想引进之后,就将语文教学搞成一种认识活动,我们进行语言教学就去分析语言的结构,阅读文章就去分析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课改以前的语文教学就是这种认识论的语文教学观的典型形态。而这次新课程改革并未能清算认识论语文教学的哲学基础,而是将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基础作为新课程改革的哲学基础和思维方式。后现代哲学由于反现代主义的理性,所以排斥知识、理性,强调感性、经验、体验,强调方法的生活建构主义,这样后现代主义就走到了现代主义哲学的另一个极端:反理性主义。殊不知,学科知识、技能知识、素养知识,尤其是语文知识,既不是理性的又不是感性的,而是“类理性”的实践技能知识,因此,当代哲学必须从认识论理性哲学转向追求实践行为的类理性知识的实践论哲学,这样的哲学就是一种“新现代主义”或“新后现代主义”哲学。只有这样的实践哲学对于语文课程改革才是有意义的和有效的哲学基础、思维方式和知识范式,建立在实践论哲学基础上的语文课程改革才是科学的、有意义的、有效的。 杨:实践哲学,这个提法很好。实践性很强的语文学科,需要有对实践行为的深入理解。听您这么讲,语文新课程的问题及其根源就非常清晰了。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说,语文教学的重点是语文行为素养、技能的培养而不是文章、作品的结构知识的灌输?藉此,您为什么又提出要进行“语文知识观”的彻底转向呢? 马:是的,“语文教学的重点是语文行为素养、技能的培养而不是文章、作品的结构知识的灌输”,你的理解非常准确到位。由于语文行为的知识是默会性的“类理性”的知识,因此进行语文新课程改革必须转变传统的理性主义、明言性、概念性的语文知识观,建立“类理性”的“默会认识论”的语文知识观。这是由于语文交际行为的技能知识是将附带觉知整合到焦点觉知之中去的默会知识。我提出的非构思写作知识、言语学知识、时空美学审美思维知识无一不是对语文交际行为的默会知识的显性化描述,它具有“类理性”的特征。30多年来,这种类理性的默会性的写作知识、审美知识具有高度的可操作性、有效性。因此,我们必须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建立起这种默会知识体系,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接受新的语文知识。非构思的课程改革范式,既不是笛卡尔、牛顿、布鲁纳的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哲学的世界观的现代主义范式,也不是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既不是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建构主义,也不是多尔的经验的、差异的、相对的、多元的感性主义后现代哲学的世界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杜威的实践主义哲学、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和普利高津的演化生长的新哲学有点联系,但却是对其深化的默会认识论、实践哲学、思维哲学的新现代主义,而这种新现代主义正是对中国古典处于“意会”、“默会”(庄子)、“缄秘”(王夫之)的默会性经验性语文教学的现代转化、深化。 杨:您说的知识观转向,是由理性的、概念性的知识观转为默会知识观,默会知识是关于行为和技能的知识,这与语文学科的实践性和行为性特点是一致的。您刚才讲到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对“多元解读”“读者至上”的理念很感兴趣,但是从常识上看文本理解应该具有一致性,而且从教学实际来看,也需要有个确定的理解用来检查阅读效果,指导阅读方法和思路。究竟有没有方法和可能理解文本意义?对文本需不需要确定的解读?在后现代语文教学观和哲学阐释学那里,答案是否定的。马老师,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马:我一再讲,正如现代主义哲学一样,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发展的,后现代教育思想也是发展的。在没有发现写作赋形思维原理之前,我们对作品的本意、原意确实是很难把握的。现在语文新课改的课堂上流行的所谓多元解读,更多是寻章摘句的断章取义、自说自话的随意发挥。但是当写作赋形思维的原理、规律被发现之后,作品中作者的原意、本意就可以被赋形思维模型所证实、确证了。我以为,作为传承优秀民族文化重要载体的中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是不同于思想家对文章的批判性理解的,后者的阅读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的借题发挥的思想创造而已,前者的阅读就是要尽量去把握、理解作品的原意、本意,并受其影响。这才是真正的语文阅读教学中的理解的本意。 杨:马老师,我们该怎样看待新课改对培养学生批判意识、质疑意识、创意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强调呢? 马:当代语文教育肯定要强调批判意识、质疑意识、创意意识和创新精神。有效的批评、质疑、创意应该是建立在对课文本意、原意真正确切的实证性的理解之上才可以开始的,才是有意义和有效的。也就是说,学生的批判、质疑、创意是在课文的作者本意、原意的基础上的独立思考、质疑论难,这才能培养真正有效的批判意识、质疑意识、创意意识和创新精神,否则就是恶性、消极的“误读”“误解”。显然后者对于民族时代文化的传承和创造是没有什么积极价值和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我历来坚决反对。 杨:马老师,您这个论述我们完全赞同。但这次课程改革十分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建构性、生成性、多元性,这有什么问题吗?强调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也不对吗?您前面说要纠正对“建构主义”的误解,新课程强调的这些东西,是误解了建构主义吗? 马: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是很多有顾虑的人向我多次提出的问题。其实,在我看来,“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建构性、生成性、多元性”,“强调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从字面上讲,这种“建构主义”教育思想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新课程改革讲的是在离开具体学科的有效性学科知识的创造前提下,而仅仅从教育学、心理学的角度来推行这些心理学建构主义、生活行为结构的建构主义。我们知道,建构主义教育的思想基础来源于皮亚杰心理学的“发生认识论”,皮亚杰所谓“建构”之“构”是指儿童的日常生活行为实践的能力结构,并不是指学校学生的专业学科知识和专业能力的专业行为技能结构,后者这种结构的建构是不能离开具体学科的有效性学科知识来进行的。而本次新课程改革是由非具体学科的教育学家、课程论专家来设计的课程改革思路,而他们是不管具体学科的有效性学科知识的,离开了具体学科的有效性知识来推行建构主义,来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建构性、生成性、多元性”,“强调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是很难有什么效果的。因为语文教师、学生不太清楚究竟会“建构”“生成”什么样的有效性语文知识、技能,也不知道怎样进行“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其实,我们也赞赏建构主义,我们也主张“生成”。但是,我们是在默会性、有效性的新语文知识——非构思写作学、言语学、时空美学——背景上的建构主义,我们是将这些语文行文技能的默会知识通过讲授、训练、实践,最后建构起语文行为的专业性思维操作模型、审美思维模型。显然,这并不是“在生活中学语文”的“生活建构主义”语文课程教学。我们所主张的是一种有效性学科知识的“学校建构主义”或“语文默会知识建构主义”的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而后者将心理学的建构主义运用于这种学科有效性知识的建构主义上来,其实这就是将有效性的语文行为知识转化为真实的语文行为的语文素养和能力的最高课程理想和唯一正确教学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