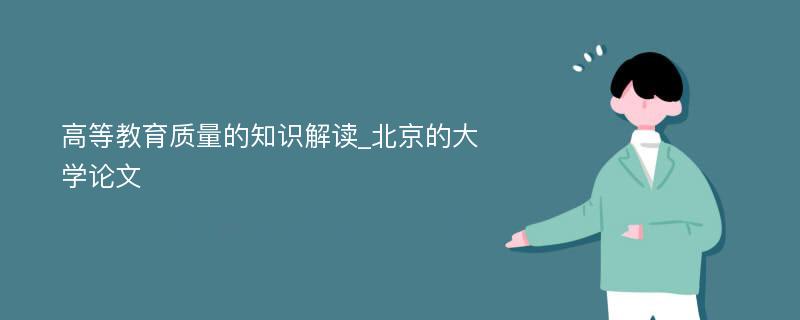
高等教育质量的知识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质量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09)06-0016-07
尽管人们尝试从不同的角度、依凭不同的实践经验对高等教育质量进行阐释、分析、评价、建构模型、提出措施;尽管有席卷全球的关注热潮,汗牛充栋的大量文献;高等教育质量研究进程依然缓慢。从现有的相关文献来看,在理论层面并未有重大突破,在实践层面上也面临着诸多困难。艾彦曾指出:“对任何一个时代问题作出适当的解答,都绝对不能只靠迫切的愿望和渊博的知识,还需要真正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的根本创新。”①从知识的视角来研究高等教育质量,正是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转换。在高等教育质量已有的诸多研究中,不仅缺少对知识的关注,知识质量观甚至成为被批判的对象。然而,高等教育质量与知识有摆脱不了密切关系。
一、高等教育质量的知识视角
高等教育机构是“控制高深知识和方法的社会机构”②。“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也。”③无论我们怎样讨论高等教育质量,都离不开知识这个核心内容。“如果有什么东西对于高等教育是基础性的话,它就是知识的中心概念。”④高等教育中的教学、科研、服务都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不关注或者忽视知识的特性与变化,使得许多有关质量的讨论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知识的角度研究高等教育质量,不仅在理论上找到了高等教育质量合法性最坚实的基础,也为高等教育在实践中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南。然而,不仅高等教育质量的相关讨论大都忽视了对知识的研究,就是在整个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也缺乏对知识的关注。“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很少有聚焦于知识的分析。”⑤
从知识的维度来论述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另一个理由是,知识社会的来临使得知识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心,高等教育机构随之成为社会发展的轴心机构。近年来、知识经济、知识资本、知识社会等概念不断涌现在学术专著与大众资讯之中,知识受到人们空前的关注。彼得·德鲁克认为,“知识是今天唯一有意义的资源”⑥。丹尼尔·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意味着出现了新的轴心结构和新的轴心原则,“社会正在从一个商品生产社会转变为一个信息社会或知识社会”⑦。由于知识对于现代社会的重要性,高等教育机构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迈向知识社会》的报告中提出,“高等教育机构应在知识社会中发挥根本性的作用”⑧。这样,在知识社会的背景下,高等教育质量变得尤其重要。
二、知识的扩展与高等教育质量
传统的知识质量观之所以受到批判,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知识概念的狭窄。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概念已得到极大扩展。知识的扩展带来高等教育质量的变革。
从以学科为基础的知识到操作主义的知识。英国学者贝内特指出,现今高等教育领域中,出现了知识范式的转换。传统的以学科为基础的知识不再能够包括所有的知识,相反,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操作主义。象洞察力、理解力、反应力、智慧与批判力被忽略,现代社会支持的是技能、能力、结果、信息、技术与灵活性。⑨贝内特还强调,象经验学习、迁移技能、问题解决、小组工作、基于工作的学习这样的词,不仅仅指新的教学方法,而是知识界定正在发生变化。合法知识至少被扩展到包括知道怎样(knowing-how)和知道那样(knowing-that)。⑩利奥塔也指出,由于这种操作能力的知识,“一个辽阔的操作能力市场展现出来了。不论现在还是将来,这种知识的占有者都是收购的对象,甚至是政治引诱的赌注。从这个角度看,知识的末日不仅没有来临,而且正相反”(11)。
4W与6W的知识。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将知识分成四类:知道是什么的知识(know-what),知道为什么的知识(know-why),知道怎么样做的知识(know-how)和知道是谁的知识(know-who)。(12)我国学者吴季松在此基础上,提出知识的六个W:知道是什么(know-what),知道为什么(know-why),知道怎么做(know-how),知道谁(know-who),知道是什么时间(know-when)和知道是什么地点(know-where)。(13)知识的4W与6W既是一种对于知识的分类,也是一种对传统知识观的扩展。单一的知识观已被一种多样化的知识观取代。
企业化知识。亨利·埃兹科维茨等人指出,一种“企业化科学”正在兴起,并对传统科学形成冲击。传统观点认为,科学家最深刻的价值在于扩展知识,对这一点的追求是科学家的最高奋斗目标,而“企业化科学”正在致力于建立“扩展知识”与“知识‘资本化’”之间的相容关系。企业化科学的发生是认知条件、科研机构的重新调整以及科学规范的变革带来的结果。反过来,它又给未来的科研带来了认识论上的影响。逐渐增多的学科和科学领域里发生的认识变革为科学家们同时达到这两种目标提供了机会:对真理的追求与对利润的追求。(14)企业化的知识强调知识的生产性,强调知识的生产重在应用,强调一种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知识,强调可以产生利润的知识。
实践知识。彼得·贾维斯详细分析了实践知识,认为实践知识包括内容的知识(content knowledge)、过程知识与技巧(process knowledge and skill)、信仰与价值(beliefs and values)、缄默知识(tacit knowledge)。贾维斯认为实践知识是:在实践环境中学习到的与合法化的;实践的,不仅仅是运用一些“纯粹的”学术原则到实践环境中;理论化的,因为它包括了内容知识;动态的,由于它仅仅在它工作的时候保持;整合的,而不是分成学术性学科;不是如同科学或社会科学一样的一个学术学科,尽管特定的实践领域如教育与医学宣称是一个学术性学科;主观的,不是价值无涉的。(15)贾维斯对于实践知识的研究表明,实践知识不仅是实践的,也是理论的;它是动态的、整合的、主观的,不同于一般学术学科知识。
复数的知识。知识的扩展表明,知识不再是单数(knowledge),而是复数(knowledges)。对此,德鲁克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德鲁克认为:“我一直在谈论知识。但是,准确反映我意思的词应该是复数的知识。因为知识社会中的知识与以前社会中所认为的知识(与事实上目前仍然广泛认为的知识)具有根本的区别……在知识社会,知识只有在应用中才能生存。”(16)利奥塔也明确指出:“人们使用知识一词时根本不是仅指全部指示性陈述,这个词中还掺杂着做事能力、处世能力、倾听能力等意义。因此这里涉及的是一种能力。它超出了确定并实施唯一的真理标准这个范围,扩展到了其他的标准,如效率标准(技术资格)、正义和/或幸福标准(伦理智慧)、音美和色美标准(听觉和视觉)等等。”(17)
以上关于知识扩展的研究表明,当代知识的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从单数的知识到复数的知识;从静态的知识到动态的知识;从客观的知识到主观的知识;从价值无涉的知识到价值关联的知识;从理论化的知识到操作化的知识。
知识的扩展带来高等教育质量范式的转换。从高等教育质量观来说,由于知识从单数变为复数,一元的质量观必然变为多元的质量观;由于知识从静态变为动态,必然要求发展的质量观;知识从客观到主观,要求人文的质量观;知识从价值无涉到价值关联,要求适应性的质量观;知识从理论到操作,必然要求实践能力的质量观。
三、知识特性与高等教育质量
知识概念的扩展导致知识特性发生重大变化,具体表现为知识的生产性、知识的公共性、知识的自主性。知识的生产性导致了知识的商品化;知识的公共性引起知识的权力化,各种权力尤其是政府的权力介入知识生产传播运用,与此同时知识本身也变成了权力;知识的自主性曾是知识的古老特性,但知识概念的扩展赋予其新的意义。
1.知识的生产性
知识在生产领域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知识的生产性具体表现为两点。一是知识变成资本,知识资本可用于投资,人们对待知识的态度从闲逸的好奇变成资本的投资,从“爱智慧”变成“爱回报”。从物质资本到人力资本再到知识资本的变化轨迹,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二是知识变成商品,可以自由交易,知识从无产权变成有产权,从装饰门面变成流通商品,从交流思想变成交易知识。由此,知识的评估从内在价值转变为外在价值,从智慧的价值变成金钱的价值,从理论的价值变成实践的价值,高等教育相应地也就从“社会中的高等教育”变成“社会的高等教育”(18)。效率、效益、成本—收益、金钱的价值等变成高等教育评估中最常见的口号。知识的生产特性决定政府与社会介入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是必然的,象牙塔必然要被打破。政府与社会必然关注应用与效率,对高等教育质量有更多的要求。
更为严重的是,高等教育的知识生产尽管越来越重要,但是知识的生产机构却远非高等教育机构一家。各种各样的政府研究机构、大公司大企业的科研开发机构、各种社会组织的研发机构等如雨后春笋,大学成了众多知识生产机构中的一家。大学正在丧失作为知识生产者的垄断权。由此,大学面临着知识生产的巨大压力。因此,高等教育自身也开始对质量保障重视起来。
2.知识的公共性
知识的公共性不仅表现为知识从个人知识到公众知识,还表现为知识变成一种公共产品,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度,涉及到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整个社会变成了知识化生存。“知识一直是一种个人利益。几乎一夜之间它变成了一种公共利益。”(19)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大学从象牙之塔变成公众之地,从培养精英到训练平民。因此,原来接受高等教育只是少数人的事现在变成了多数人的事,高等教育从高质量的符号象征变成质量本身成了问题而受人质疑,“大学和教授从令人敬畏的目标开始慢慢沦落为问责的对象”(20)。高等教育从自给自足变成必须满足公众的需求,从训导变成了服务,学生从接受者变成服务对象,高等教育科研与工业、政府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知识的公共性导致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发生几个变化。一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从内部到外部,各种利益相关人对高等教育质量提出不同的要求,同时也提供了不同的监督。绩效与问责成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一种常见形式,各种权力渗透进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特别是政府通过评估、问责、拨款等各种方式对高等教育质量进行监督控制,高等教育质量从自我保障到外部保障,从游离于权力到陷入权力之网。二是高等教育质量从“黑箱”状态变成透明状态。高等教育质量的社会问责导致高等教育的公开化,高等院校的物质条件、师资力量、学生水平、资金状况等从原来的秘而不传到现在公开化、透明化。各种媒体的大学排名以其广泛的影响,将高等院校的各种信息呈现于公众面前。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更是加强了高等教育质量的透明化、公开化。
3.知识的自主性
尽管随着知识的发展,知识与社会、知识与权力、知识与利益、知识与控制不断地结盟,知识的自主性逻辑受到外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但知识自主性逻辑不会消隐,特别是高等教育机构作为高深知识之所,学科发展前沿之地,其特殊的自主逻辑表现得更为突出。高等教育领域中,知识的自主性主要表现为:
高深知识。高等教育机构是研究高深知识的地方,高深知识所涉及到的譬如真理的追求、思想的深刻性、学科发展前沿与未来走向、新知识的创造等,不仅是局外人难以发言,就是局内人有时也因研究方向不一致而难以言语。在高等教育领域中,谁有知识谁才有发言权。这点与其他领域是不同的。高深知识形成一种天然的障碍,阻止外来者的横加干涉,并且形成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经典大学理念。
分化知识。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是以学科为单位建立起来的。尽管在后现代视野中,知识的跨学科性表现突出,但是知识的跨学科性却表现为新的学科的产生。各学科之间又有不同的知识发展逻辑,有不同的学科研究对象,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有不同的学科理念,有不同的学科学习研究模式,这些学科之间的差异形成所谓的“范式”。不同学科之间不同的范式导致了隔行如隔山,导致了大学组织的松散联合结构与权力的底部厚重。
缄默知识。一般来说,显性知识是可以编码、传授、流通的,因而也就更具有资本性、商品性。然而,缄默知识是难以编码、传授、流通的。缄默知识的存在使得知识的自主性凸显出来,大学成为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追求真理与精神交往的自由家园(21)。在这种自由地追求真理与精神交往中,缄默知识才得以领会、融合、相互影响、内化,才会成为学生与教师知识结构的一部分。由于这种缄默知识难以编码、量化、觉察,其质量保障就难以采用显性知识的评估方式。
批判知识。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大学作为知识分子最后的避难所,是生产批判知识的最佳场所。因为批判知识的存在,所以大学需要与社会保持距离,正如弗来克斯纳所说的,大学不是风向标。相反,大学需要批判社会、引领社会。对于批判的知识,由局外人、社会或被批判者来评价,显然是不合适的。这样,批判的知识就游离于质量保障的边缘。“我们可以接受怀疑论者的告诫,但还是要在知识领域中为那些无法量度的东西保留一席之地,即价值观和选择的领地。”(22)
不确定知识。对知识投资的价值一直是难以测量的,结果也可能与预期的大相径庭。换句话说,拥有知识资源不能保证创造出价值,具有知识的使用能力,才是其中的关键。在知识资源的评价方面还存在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知识还未公开前,无法判断其价值,一旦公开以后,对行家来说,其价值就已经不存在了。但对整体来说,情况刚好相反,公开的知识经过交流与融合,反而会产生更多的知识资源。而且知识的收益具有不确定的利益分成。即使知识投资能获得巨大利益,我们也很难确定谁将获得利益的大部分。
总而言之,知识的自主性决定了知识领域许多东西难以量度、难以测评,因此要求高校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主体,要求同行评估不可缺少,要求评估的专业化,要求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不可能有统一的模式。知识的自主性最终表明,高等教育质量要由高等学校自身来保证。
四、知识生产与高等教育质量
知识生产模式对质量控制的影响论述中,最为著名应属吉本斯的“模式2”。吉本斯将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称之为“模式1”,而将新的知识生产模式称为“模式2”。相对于“模式1”来说,“模式2”具有一些新的特点:知识在应用的背景下生产;跨学科;异质性与组织上的多元性;提高社会责任;更广泛地以质量控制系统为基础。
由于知识生产模式的变化,质量控制面临着新的问题,吉本斯指出:(1)在“模式2”中的知识,科学同行评估不再是可靠的鉴定,因为不再有可编码学科的稳定分类。(2)简化的质量控制形式不能容易地应用于更加广泛结构的研究问题:研究游戏正被越来越多的玩家参与,并非只是简单地扩大了文化生产者的范围,还有管弦乐队、经纪人、传播者与使用者。(3)清楚的与未受到挑战的标准,通过它来确定质量,将不再是可用的。相反,我们必须学会忍受多方面的质量界定。政策制定者与资助机构依赖使区分、优先性、选择性的过程复杂化。(23)
吉本斯关于知识生产的“模式2”与质量控制的相关论述为我们理解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提供了理论基础。简而言之,吉本斯的理论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来说具有以下意义。第一,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的多元化。由于知识生产从单学科到多学科,从理论性到应用,从同质性到异质性,知识质量的标准多元化,高等教育质量标准也面临着多元化。第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方式从内在保障到内外并重。由于知识在应用的背景下生产,知识生产机构与知识服务的对象都不断扩大,知识质量从学科的控制转向其它控制,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高等质量保障中来。第三,高等教育质量的同行评估方式受到挑战。学科分类不再稳定,从单学科到多学科的发展表明,同行评估不再是可靠的质量评估方式。第四,高等教育质量的社会问责。随着原来的“社会中的高等教育”转变为“社会的高等教育”,高等学校从社会的边缘进入社会的中心,高等教育必然面临着众多的问责,高等学校必须就质量问题向社会说明责任。
五、知识传播、知识分配与高等教育质量
知识传播由原来的单向变成双向甚至多向,从文本方式转向超文本,从线性到非线性。知识传播方式的改变进一步引起了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关注,比如网络大学的质量、开放大学的质量等。“知识经济的标志之一,是承认知识的扩散与知识的生产同等重要,这使得‘知识传播网络’和‘国家创新体系’更加受到重视。”(24)随着知识传播由封闭变得开放,原来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价有所改变:“知识变成开放的,这很重要。广大社会产生出他们自己对合法知识的界定,更操作性的、更相互作用的、更基于多种的表述形式。高等教育与广大社会的互相渗透,因此提出尖锐的认识论问题:什么是大学用于定位自己的合法知识的标准?这些标准是广大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提供的吗?在这样的环境下,有牢固的知识标准吗?”(25)
知识分配方式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知识分配的对象发生变化。知识分配从少数人到多数人,从精英到大众。知识从原来精英们的装饰与点缀变成了平民百姓的空气与面包。知识分配对象的变化引起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变化,原来的高等教育本身代表着高质量,是少数人的特权,本身就是精英的组合。因此没有也不必要进行全方位的质量保障措施与保障体系。但是,在大众化的高等教育中,高等教育变成普通百姓的权利,关涉着大众生活,高等教育质量的高低决定了大众的生活质量的高低。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使得原来的高等教育质量的“学术金标准”已不再适用,重建高等教育质量观,构建大众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成为必然。另一方面,知识的分配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在精英阶段,知识分配是无偿的,高等教育被看成是公益事业。然而,在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按照成本分担原则,知识的分配方式从无偿变成有偿,从公益事业变成了人力投资,知识本身成了资本,成了商品。知识分配方式的变化导致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高度关注。纳税人纳税、学生付学费、政府投资都希望能从高等教育中得到回报,因此对高等教育质量也就更加关注。
六、从传统知识质量观到新知识质量观
曾几何时,高等教育的知识质量观成为一些学者批判的对象。任君庆、苏志刚认为知识质量观是一种以学生掌握理论知识的深度、广度及学科理论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来衡量教育质量的质量观。在这种质量观的观照下,容易产生重理论、轻实践,重科学、轻技术应用的教学思想。(26)传统的知识质量观确实存在着诸多缺陷,但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人们对知识理解在不断扩展。建立在扩展知识基础上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才能真正反映新的知识质量观。
新的高等教育知识质量观以知识为中心。由于知识概念的扩展,知识不仅是静态的,也是动态的;不仅是理论的,也是操作的;不仅是显性的,也是隐性的;不仅是支持的,也是批判的;不仅是自主的,也是公共的。因此,新的高等教育知识质量观提倡以知识为中心,与传统的知识质量观是截然不同的。
新的高等教育质量观要求以知识为中心,要求培养现代知识人。高等教育历史经历了从培养“自由人”、“绅士”到“学科人”、“专业人”再到“知识人”的路径。知识社会中的知识人应该“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具有知道是什么的知识、知道为什么的知识、知道怎么样做的知识和知道是谁的知识。
新的高等教育知识质量观是多元化的知识质量观。从知识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质量必然是多元化的。知识从单数变为复数,导致不同的知识有不同的评价标准,有不同的质量保障模式;不同知识的不同特性使得高等教育质量观不尽相同,有的知识其主要特性是自主性,而有的知识则主要表现为生产性或公共性,其质量评价标准也不一样;知识生产、传播与分配的不同也导致了高等教育知识质量观的多元化。
新的高等教育知识质量观是政府、社会、高校共同分享与对话的质量观,是利益相关人博弈的质量观。这种质量观强调适应,不仅高校要适应政府与社会对于知识质量的要求,政府与社会也要适应高校知识的自主性,尊重学术发展规律,从而达到权力的分享与利益的双赢。利益相关者对于高等教育质量的不同观点,实质上反映了利益相关者不同利益与权力的要求,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其实是在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与权力之间寻求一种博弈均衡。
注释:
①马克斯·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6.
②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1.
③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72.
④Frans Van Vught."The New Context for Academic Quality," in Emerging Patterns of Social Demand and University Reform:Through a Glass Darkly edited by Daivid D.Dill and Barbara Sporn(IAU Press,1995),202.
⑤Patricia J.Gumport.Academic Pathfinders:Knowledge Creation and Feminist Scholarship(Greenwood Press,2002),3.
⑥彼得·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45.
⑦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5.152.
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迈向知识社会[M].教科文组织出版,2005.91.
⑨Ronald Barnett.The Limits of Competence(SRHE 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4),15-16.
⑩Ibid,47.
(11)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07.
(1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7.6.
(13)吴季松.知识经济——21世纪社会的新趋势[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16.
(14)李正风.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及其演变[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21.
(15)Peter Jarvis.Universities and corporate university(Stylus publishing Inc,2001),49.
(16)亨利·埃兹科维茨,劳埃特·雷德斯多夫.大学与全球知识经济[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6-9.
(17)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41.
(18)Ronald Barnett.The Limits of Competence(SRHE 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4),21.
(19)彼得·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21.
(20)Joseph C.Burke and Associates.Achieving Account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Balancing Public,Academic,and Market Demands(San Francisco,Jossey-Bass,A whey Imprint,2004),6.
(21)黄启兵.追求真理与精神交往的自由家园[J].复旦教育论坛,2005,(5):42.
(22)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5.73.
(23)Helga Nowotny,Peter Scott And Michael Gibbons."Introduction 'Mode 2' Revisited: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Minerva 41(2003):187-188.
(2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7.22-23.
(25)Ronald Barnett."The Purpose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Changing Face of Academic",London Review of Education 1(2004):63.
(26)任君庆,苏志刚.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标准和质量观[J]职业技术教育(教科版),2003,(2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