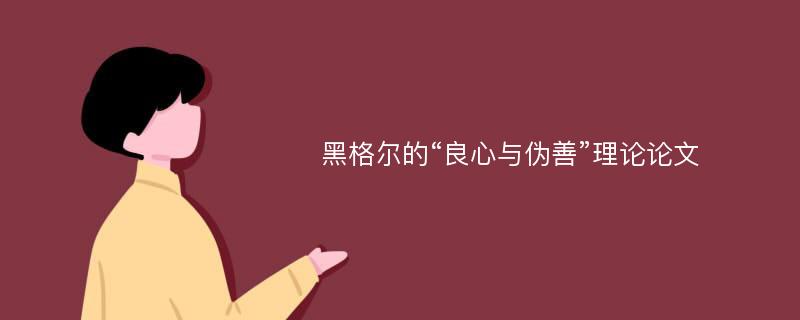
黑格尔的“良心与伪善”理论
冉光芬
(上海海事大学,上海 201306)
摘 要: 黑格尔的“良心与伪善”理论,是在批判康德“良心与伪善”理论“形式主义”缺陷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通过《精神现象学》及《法哲学原理》相关章节,黑格尔建构了“良心与伪善”理论的完整体系,阐述了“形式的良心必然导致伪善”的观点和立场。黑格尔的这一理论在打破中国传统文化中良心理论的定势和偏见方面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存在纯思辨纯逻辑却缺乏现实关切的历史性局限。
关键词: 黑格尔;康德;良心与伪善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完美演绎了自由从抽象概念经由设定他者与定在后回到概念自身,最终实现为理念的心路历程。藉其博大精深的思辨思维,黑格尔赋予每一个环节以现实性及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同时又断定每个环节都存在缺陷与不足,从而必然为下一个阶段所扬弃和超越的宿命。“良心”作为自由意志理念展开过程中的以主观和内在为规定性的环节及阶段性存在,必然不能成为“自由”理念演绎的最终完成,更不是以自由为规定性的绝对精神本身。但是“良心”作为独立的理念,必然也有一个从“无规定性的、抽象的概念”到“设定他者及定在”,再到“突破定在的有限性后回到概念自身”的辩证体系和发展过程。在自由意志理念发展到要从主观和内在寻找根据的道德阶段,以“普遍善”的实现为目的的“良心”却有了恶的规定性,并导致“伪善”的后果。这就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及《法哲学原理》“道德”章所建构的“良心导致伪善”的理论打破人们“良心即善”定势思维的微妙之处,也是对康德“良心与伪善”理论的超越之处。因此,作为彪炳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史册的前后相继的两位伟大人物,黑格尔“良心与伪善”理论是在德国古典哲学相同使命之下对康德伦理体系的补足和完善。基于此,黑格尔认为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通过费希特和谢林直到他自己的发展是一个从开端(在那时,它还不可能理解康德立场的基本含义)到终结(到那时观念论哲学成为连贯的和普遍的)的必然发展。[1]80
一、黑格尔对康德“良心与伪善”理论形式主义缺陷的批判
作为启蒙运动倡导者和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既要充分肯定理性权威、重塑人的主体地位,又要避免理性在工作过程中的僭妄和独断。因为僭妄和独断恰恰会取消理性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认为理性只能认识存在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且与主体的表象不可分的东西,即只能认识现象,不能认识独立于主体表象之外的物自身,这就是理性理论运用的边界和范围,是思辨理性;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实践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学》以及《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康德讨论的则是理性在情感意志等驱使下的实践过程中的运行机制和规定根据。因为理论理性的界限和范围是现象界,越界就会独断和僭妄,从而承认自己对认识超验领域的无能为力,但是基于重塑人之自由和尊严的目的,思辨理性会催促理性用实践依据充实超验世界的物自身[2],从而创造出一个“德福一致”的至善世界,此即为理性的实践活动或实践理性。理性的实践运用分为一般实践理性的活动和纯粹实践理性的活动,在前者中是行动取决于对象,后者则是行动则取决于先天法则。由对象所决定的活动是一般理性实践,不具有善恶评判的价值;只有以先天法则和摈弃一切偏好的绝对命令为意志规定根据的行为才具有善恶价值,是道德实践。但是,行动的意志如何能够只为先天法则所规定,而不考虑目的和对象?换言之,理性如何能够直接就是实践的?
康德对“理性如何能够直接就是实践的?”这一问题的系统性回答,夯实了人类至上尊严的基础,成就了“但问动机不问结果”的义务论伦理学,实现了伦理学与形而上学传统关系的重大颠覆:不是伦理学要以形而上学为基础,而是形而上学只有在伦理学中才能最终得以完成。因为“上帝、自由、灵魂”作为本体界实存、形而上学对象、作为“物自体”,根本不能通过感性直观和逻辑思辨获得确定性和实在性,只有在理性存在者的实践中才得以证成。实践理性之所以能够直接就是实践的,是因为具有自由意志但仅为有限理性存在者的人,为了自己至上尊严而始终坚持实践法则和绝对命令从而形成“善良意志”的缘故。这就是康德伦理思路的内在逻辑。“善良意志”是康德在其伦理体系中提出的一个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意义的概念,是审查并执行绝对命令的“良心”,是无限制的善。康德说:“在世界之内,一般而言甚至在世界之外,除了一个善的意志之外,不可能设想任何东西能够被无限制地视为善的。”[3]“善良意志”不仅是善的意愿、一种静观,还是克服善之障碍物的行为和驱动力。换句话说,善良意志就是坚持依循普遍法则或绝对命令(纯粹义务)而行为的意志,是单凭理性本身颁布给行为主体的普遍的道德法则。只有出于对普遍法则和绝对命令的遵从而发生的行为,才是具有道德价值的道德行为。
在康德看来,意志自由的理性存在者拒斥一切偏好,只依理性给自己颁布的绝对命令的行动才是道德行为,自由的但却只选择普遍法则来遵守的意志就是善良意志,在偏好和普遍法则混杂的世界里,独独识别出作为普遍法则的善的能力,就是das Gewissen,即“良心”或“良知”。良心在康德这里具有“意、情、知”三个方面的内涵[4]:即用法则而非偏好规定行为的善良意志,基于对法则之崇拜而产生的道德情感,辨别善恶的能力。良心的这三个方面必须要具有时空的共在性,是一个整体性的存在。任何行为缺一则不足以成为道德行为,甚至会导致不道德的结果。在《道德形而上学》及《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谈到《圣经》所记录的有关内容时,康德将“说谎”视为比该隐谋杀兄弟更为恶劣的行为,因为说谎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伪善”倾向,是对他人“把恶主张为善”和“把善主张为恶”的人性之恶,是根本恶。是能辨善恶却不择善而从,不崇敬法则的结果。由此看来,在康德这里,良心本身没有问题。良心和伪善之间没有逻辑或自然上的因果关系,伪善的存在只是良心非整体性出场所导致的后果。
康德所面对的是基督教信仰遭遇危机的现代自由社会,在原子式个人基础上建立“道德共同体”成为不可能。无论是孟子的“四心说”还是情感主义伦理学,都不能解决“现代社会道德何以可能”的问题。但是,现代性的基础—自由—要通过道德才能得到辩护,人的至上尊严唯有通过道德才能证成。康德需要着手解决如何在自由主体中建立普遍而可靠的伦理规范这一问题。这就是康德“良心与伪善”理论的鹄的。
做好河道驳岸的虚实处理工作。一般情况下,做好城市河道驳岸的景观设计,需要从实景和虚景2个方面着手进行。实景就是要通过一定的硬性景观将河道的景观表现出来,比如,园林建筑、富有创意的空间景观等,其能够表现出河道景观的功能性和尺度性。
1.5统计学方法: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19.0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s)表示,计量资料采用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二、黑格尔“良心与伪善”理论的内在逻辑
第二种伪善的特点在于强调主观动机的善。较之于盖然论的伪善,这个阶段伪善的层次更高,因为行为者有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伪善。这就造成了一种更加隐晦的伪善,即只要动机是好的,则一切都是好的,或者说,行为及结果的性质在出发点就被规定了。人们甚至理直气壮地把这种说法当作自己行为的公开原则,也许不是主观上要为恶,但却形成了一种伪善人格:他认为只要主观上没有恶意,那么造成了再大的恶果他也不会有丝毫悔意,甚至觉得自己在干最好的事。在黑格尔看来,康德自己的伦理学就属于这种伪善,即只强调主观善良意志的动机,并以主观理念中臆想的“应当”来遮蔽在现实中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第一种伪善,它的形态以“盖然论”而为人们所知。其原则是:“只要行为人能替某种行为找到任何一种好的理由,无论这种理由只是某一神学家的权威,而且行为人也知道其他神学家对这一权威的判断在意见上有极大分歧,这种行为就是许可的,行为人也可感到心安理得。”[7]148这个原则的合理之处在于,任何一个有好的理由的行为都有其他同样好的理由使他不做这件行为,所以任何一件行为总是可以为它找到好的理由的。但行为者觉得哪怕这理由只是“盖然的”,它却足以使自己心安理得。既然行为的理由是可以随机找到的,那么行为的真正动机实际上只在于主观任意性,但行为者却把它说成是客观上可靠的,或者是某个道德权威命令他做的,他自己可以不担责任,这就是伪善。这种伪善大致相当于康德所描述的在纯粹道德原则里面偷运进感性动机、打着道德幌子为个人偏好服务的行为。这种行为就是道貌岸然式的伪善。
①观察统计患者术后切口感染发生情况,以浅表感染、深部感染和腔隙感染的发生情况为进行评估;②调查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以自制的《手术室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进行调查,计分范围为0~100分,按照评分结果将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分为完全满意,得分≥90分,基本满意,得分为60~89分,不满意,得分<60分。其中的护理总满意度=[(完全满意+基本满意)/总例数]×100.00%[3]。
首先,黑格尔用自己的语言,全面梳理并批判了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设定的纯粹义务与感性偏好对立的道德世界观,指出这种道德世界观存在一个道德意识和自然偏好二元存在的逻辑预设。即康德既确定了只以纯粹义务为规定性的个人意识的必然性,同时也假定了感性偏好的实在存在。在黑格尔看来,这种二元假定必然会导致二律背反。因为作为善良意志的良心,要通过行动才能体现它的现实性。但是给予良心以唯一规定性的绝对命令,又是绝对普遍从而超越于一切现实的行为之上的。于是,善良意志驱使下的行为一经启动,绝对命令这一纯粹义务就不再是绝对的,其本质就不再是本质。良心和自然偏好在意识发展过程中会交替成为本质,甚至会出现把非本质、非道德的东西宣称为本质和道德的情况,从而出现颠倒和混乱,这种状态持续存在就会导致“伪善”。于是,道德意识开始厌倦这种颠倒和混乱的道德世界观,并从对象性的存在中返回自身。此时的良心就是在自己本身中简单的自身确信的精神,这种精神无须中介而只凭良心行动。这时,那以居于彼岸的纯粹义务为其本质的道德意识(良心),就发展成了道德阶段的“优美灵魂”。[5]147其次,黑格尔还指出由于康德对人类精神世界及相应“自我”未加区分从而导致“良心与伪善”之纠缠状态无解的困局。在黑格尔看来,人类精神世界在不同阶段分别呈现为三种样态:第一种精神世界为伦理世界,其自我是法权状态下的原子式个人;第二种精神世界是教化世界,相应的自我是经过启蒙而反宗教、重功利、争自由的自我;第三种是道德自我存在于其中的道德世界。[5]148-149康德道德世界观的二律背反,就在于本该进入道德世界的自我意识没有把纯粹义务与自然都一同扬弃掉而成为自身直接确定性的良心。道德自我意识从自在进入了自为阶段,道德世界观里因为设定区别而产生的矛盾就会自行消融。据此,“良心”具有如下含义:1.良心是一种认知。良心在对待行为发生于其中的那种现实时,就必须要把这种现实搞清楚,从而确信其中的普遍性环节;2.良心是一种行为。即王阳明所说的“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状态。此时的良心将道德世界观的矛盾和区别予以消融,而把自身建立为唯一存在着的东西。此时良心的规定性在自我意识本身,良心完全不受约束,完全独立自由,可以任意取舍和增删。于是“伪善”这一“根本恶”的产生就有了条件和土壤。这就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良心与伪善”理论的内在逻辑。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有关良心问题的讨论,是在批判康德现象界与物自体不可通约观念的基础上以自由理念的发展为主轴而展开的。“在黑格尔这里,随着自在之物和现象之分的取消,康德的三种自由即可能的自由(先验自由)、必然的自由(实践的自由)和现实的自由(自由感和自由权)便融为一体,成为了同一个自由概念本身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并且这三个阶段不但体现了自由概念本身的逻辑层次,而且展示为人类自由精神发展的历史过程[6]。“良心与伪善”的问题就是自由理念发展过程中历史性阶段的一个产物。黑格尔将良心分为“形式的良心”和“真实的良心”两个阶段。“形式的良心”是自由从外在定在(所有权)回到以主观性为定在的表现形式。这种以善为“纯粹义务”、一心向善的“形式的良心”产生了以“伪善”为表现形态的恶,从而陈述了“良心导致伪善”的逻辑必然性。
黑格尔认为,在以主观性为基地的“形式良心”的阶段,一切外在标准与评价机制都消隐,良心是自己与自己相处的最深奥的内心孤独,从而与外在于主体的自在自为的善本身处于对立状态。个体的自由意志在摆脱掉外在原则或权威(自在自为的善)的束缚之后,对作为行为的“良心”进行规定的就只能是个人的偶然和任性了。感性时代的宗教和法等等一切外在的东西和限制在形式的良心阶段通通归于虚无,主体的良心便成为“特殊性的设定者,规定者和决定者。”[7]139这个良心表示:主体的自我意识在自身内并且绝对能够知道什么是权利和义务。它只把它自己认为是义务和善的东西当作义务和善,其它的一概不予承认。在一切外在约束和限制都消隐后的特定个人的良心中,就会发生如下问题:特定个人的良心是否符合“良心”这一理念?只以善为义务的良心所认为和履行的善是不是确实就是普遍的善?一旦特定个体的良心不符合良心的理念,它所认为和履行的善也不确实就是善的内容或普遍的善,并且由于此时的良心把一切有效的规定都贬低为空虚,而只具有纯内在性时,恶就产生了。如果主体对他人把善曲解为恶,就是彻头彻尾的恶,把恶曲解为善,就是绝对的“伪善”。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140节中对“把恶曲解为善”这种“伪善”现象进行了分类和批判。
作为人类精神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个人意识达到绝对精神的一个历程,黑格尔将良心问题放在《精神现象学》第六章“对其自身具有确定性的精神、道德”部分进行全面论述。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在古典哲学语境中建立了庞大的思辨哲学体系。由康德所创立的德国古典哲学所关注的所有主题,在黑格尔思想体系中都得到了回应与处理。“自由”既是社会现代性的必要基础,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核心议题。人类精神的进化史及自由理念的发展演变过程,分别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及《法哲学原理》中的主题。
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良心与伪善”理论存在如下问题:一方面,绝对命令作为纯粹义务和普遍善是没有规定和限制的,因此是缺乏对立面的抽象概念。“普遍善”一经成为个体行为的规定根据,就有了限制和不同,从而成为“非普遍的”了。抽象的良心和行为相结合成为现实,就不再是超越的维度。作为有限理性存在者的主体,何以能够不关照感性偏好而只依循绝对命令?另一方面,自由的意志既可以选择只听从道德法则的命令,亦可以选择服从感性偏好的驱使。作为根本恶,“伪善”就是感性偏好完全得不到良心照料的产物。“伪善”的出现是良心“形式主义”地规定行为所必然导致的恶果。黑格尔认为康德对执行“善良意志”的主体及人类精神世界不加区分的做法,以及拒斥一切感性偏好的道德动机的设定,都使其实现“至善世界”的美好愿景流于单纯的概念抽象,也无法解决“良心导致伪善”的悖论和难题。
第三种伪善是前面两种情况的合题,即外在权威和主观动机的统一,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把主观自由意志的“准则”通过实践理性推广为“普遍法则”。康德也常常将这种道德法则视为“客观的”,甚至称之为“理性的事实”,作为我们信仰的对象;但这种“客观”和“事实”并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经验的客观事实,而只是实践层面的逻辑必然性,这种伪善更难对付。因为单凭没有恶意的动机和随意的外在的神的权威,就可以宣称自己的行为是善的。
与《精神现象学》要考察人类精神进化史不同,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要解决的是“自由理念”历史性展开的过程。但这两本著作在“良心与伪善”的问题上都着墨不少,且有相同的论证逻辑和运思方式。其差别只在于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精神现象学》中讨论“良心与伪善”的问题,是精神从教化世界的异化状态回归之后,个人意识思考道德世界观的结果;《法哲学原理》中,“良心与伪善”的问题则是放在自由的规定性从客观回归主观的道德阶段来讨论的。第二,在《精神现象学》中,“良心”只是精神发展史的一个环节,只是片面性的存在,没有把良心理念的展开过程体现在其体系中;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则区分了“形式的良心”和“真实的良心”的两个环节。并指出“良心导致伪善”的逻辑悖论是在良心的形式阶段发生的,到了以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为规定性的阶段,“良心导致伪善”的悖论就会得到克服。这个阶段的良心就是“良心”作为理念的实现,是以“普遍善”为规定性并最终实现了“普遍善”的真实的良心。第三,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将“伪善”这一“根本恶”放在批判康德道德世界观所造成的颠倒这个环节来进行讨论的。黑格尔谈到超越于道德世界观之上的良心具有“完全独立自由且可以任意增删”的属性,但并没有言明这种属性与“伪善”的辨证关系,在《法哲学原理》中,“良心导致伪善”的吊诡逻辑是在形式主义阶段的良心中演绎的,黑格尔在此阐述了没有规定性的“形式的良心”必然导致“伪善”的观点,且全面论述了作为“根本恶”的“伪善”的种类、特征等问题。
为了既坚持康德把自由视为道德基础的现代立场,又圆融康德在自由之下建构普遍性的捉襟见肘,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分别从不同侧重点做了补足。费希特通过“自我”的本体论建构,在康德严苛的绝对命令中植入心理学的道德动机。作为启蒙运动自我反思成果的浪漫派的谢林认识到,以自由为基础,不仅导向善,也会导致恶,它仅仅表现为既可致善,也可致恶的可能性。在费希特和谢林基础上,黑格尔对康德“形式主义良心观”及“良心对伪善的产生难辞其咎”的辩证关系的反思与批判更为系统和彻底。其在《精神现象学》第六章的“对其自身具有确定性的精神、道德”以及《法哲学原理》“道德”章中“良心与伪善”辩证关系的理论,就是对康德伦理学“形式主义”缺陷的系统解决。
3.3.1 海马组织DG区病理检测结果 光镜下观察小鼠海马DG区神经元,对照组神经元呈颗粒状,细胞排列整齐有序,胞体饱满,间隙正常,边缘结构清晰。与对照组比较,乳腺癌组神经元未见明显异常;抑郁症组细胞出现萎缩,有一定程度的核深染,而BCRD组神经元出现胞浆浓缩,细胞核体积变小或者消失,核深染程度加重,甚至出现破裂状态。结果见图3。
术后询问患者治疗过程的感受,采集两组患者的主诉情况和躯体反应情况,其评价标准如下:患者主诉身体感觉良好,表示愿意再次接受治疗为良好;患者主诉过程痛苦,表示不愿意再次接受治疗为差。躯体反应评价标准如下: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保持安静,无呻吟和肢体活动为优;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出现呻吟和肢体活动,但未对检查治疗产生影响为良;均不符合上述描述,严重影响诊疗为差,优良率=(优+良)/55*100%。
三、黑格尔“良心与伪善”理论的意义、价值及局限性
黑格尔的“良心与伪善”理论,是在对启蒙哲学“知性思维”及康德“纯形式的善良意志”进行批判与反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合理评价黑格尔“良心与伪善”理论的意义和价值,必须从如下两个方面来立论:
一方面,从黑格尔对启蒙哲学“知性思维方式”及康德“善良意志”进行批判的角度。首先,黑格尔指斥启蒙哲学作为“抽象理智规定”的“知性”不能教会人们如何向善,只能指导人们如何通过辨别和判断更好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即只能教导人们如何更加聪明,却不能教导人们如何更加有德。黑格尔意识到,启蒙哲学所倡导的奠基于自由之上的现代性,其根本特征就是主客体的二元分裂,但这是主张客观精神和主观精神最终统一于绝对精神的黑格尔所不能容忍的。通过摧毁现代性、重回基督教信仰来克服这种二元分裂的做法也是黑格尔绝对不可能做的选择。在“现代性必须继续”这个不可逃避的前提之下,对作为现代性之基础的“自由”进行考辨和规定就是唯一途径。从《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中,我们清楚的看到,对现代性进行诊断,得出“现代性不能促进道德”这一结论的黑格尔并没有抛弃作为现代性基石的“自由”。黑格尔意识到,自由是现代性的立论基础,为道德奠基是现代性的根本宗旨。换句话说:现代性从根本上说就是一项道德的事业。自由是现代性的基础,故也是道德的基础。但自由不能停留在抽象理智规定的阶段,必须要在人类精神历史及生活世界中展开。其次,黑格尔指责康德伦理学是“形式主义”,认为“义务能够作为行为约束力”的前提是因为假设了上帝和灵魂不朽。黑格尔开始反思:如果没有代表世代轮回和末日审判的不朽灵魂与上帝的假设,义务还能够有约束力吗?道德法则始终有效吗?面对这些问题,作为政治哲学家的黑格尔,把道德实现纳入其政治体制的设计和建构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黑格尔认为,“良心导致伪善”这一辩证关系的克服,不能寄望于私人的修养和教化,必须要放在具有普遍约束力(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伦理政制的设计与建构之上,从而开辟出一条从道德上的“绝对应该”变成社会政治的“绝对现实”的道路。但是,从对康德伦理学“缺乏现实性和约束力、从而是形式主义的”这一判断结果来看,黑格尔的结论仅仅是局限于从康德“善良意志”这一前提性问题展开立论的。康德在其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本著作《道德形而上学》中,对他在前几本伦理学著作(《纯粹理性批判》的“法规论”、《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实践理性批判》)中“提纯萃取过的道德原则如何应用在可经验的人类学中”这一问题进行过有益的探讨。尽管这一探讨并没有成功解决“普遍法则如何能够有效应用于‘有限’理性存在者的人类”这一伦理学中的关键性问题,但并非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康德伦理学是不思应用的,“良心与伪善”辨证关系不能得到克服的“形式主义”的伦理学。由此可以推断,黑格尔并没有读过,至少是没有认真对待《道德形而上学》这本著作。因此,他对康德的评价有“断章取义”之嫌。
梅先生平静地说:“我始终相信,天才在世界上只是极少部分,大多数人是站在同一水平线上的,差异只是在于刻苦的程度、坚持的时间以及自身的责任感而已。”
另一方面,从黑格尔“良心与伪善”理论对其后的西方思想的影响及儒家伦理的启示性原则的角度。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人类精神进化史的展开和铺陈,体现出其哲学的主体性特征,并由此获得了“主体性哲学集大成者”的美誉。但一如其博大精深的辩证法,黑格尔体系本身也是一个充满辩证吊诡的困局。首先,黑格尔在其伦理思想中将道德实现诉诸制度设计而非自由的原子式个体所表现出来的去主体化倾向,极大地影响甚至形塑了后黑格尔时代西方伦理思想的发展谱系。他在其主体性哲学体系中提出的“事情自身的发展、作为静观的我们”以及“实体即主体”等观念所显现出的,恰恰是其“去主体化”的倾向。“名满天下,谤亦随之”,黑格尔逝世后,他的主体性哲学遭到了西方很多思想家全方位、多角度的批判与指责。认为其无所不包的主体性淹没了万事万物彼此之间异质性和外在性存在的事实。这种绝对同质并最终统属于主体的本体建构和描述完全关闭了人类精神的表象空间。这种状态一直伴随着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分化,并最终造成了学派纷呈的局面。但西方哲学家们在反对黑格尔主体性哲学的同时,却继承并发展了其非主体化的倾向。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如“非理性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尼采主义”、“语言分析学派”、列维纳斯“绝对外在性和异质性的‘他者’”等当代“反主客二分”的理论都可将黑格尔“实体即主体”的“去主体化”内涵作为追溯起始点。其次,黑格尔伦理思想对马克思的直接影响。黑格尔逝世(1831)的时候,马克思才13岁,但马克思却自称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并且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份子。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无论是研究主题、还是论证方法,都深受黑格尔的影响。如:马克思的辩证法直接来源于黑格尔庞大的唯心主义思辨体系;马克思有关劳动和革命的理论,可以从《精神现象学》的“主奴斗争辩证法”章找到根据。其包括“良心与伪善”理论在内的伦理观念,直接影响了马克思的伦理思想建构,黑格尔让良心理念在历史中得以展开并诉诸政制解决的思路,启发马克思将道德问题看成是历史变化着的一种现象、统治阶级通过制度设计来诠释和定位伦理标准和尺度的主张。正如迪特.亨利希所说:“马克思主义是与黑格尔和费希特的心灵哲学相分离的历史和社会哲学。”[1]75最后,黑格尔“良心与伪善”理论可以为我们合理解读儒家伦理有关问题提供启示性原则和视野。黑格尔认为,康德的作为“良心”的“善良意志”缺乏规定性,是无视人之感性事实存在的“形式主义”的伦理观念,不具有对生活世界的指导意义和现实价值,因此这一体系本身就是“伪善”的。从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伪善”的定义及分类来看,儒家所指斥的“乡愿”属于黑格尔所划分的“伪善”的第三类。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孟子将“乡愿”解释为“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愿也”。(《孟子.尽心下》)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具有强烈实践哲学的倾向:力图通过个人体悟和修行工夫将“圣人”或“君子”这一人格的至善理想在行为中现实地“做”出来。从这个层面讲,儒家学说与康德伦理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康德将道德理想的实现寄望于独立自由的个体,儒家则是以“家庭”为道德理想的本体基础,并以“三纲五常”作为其规定性维度。从这个方面来看,儒家与黑格尔在这个方面的诉求更为趋同。但是,黑格尔意识到道德问题的解决不能诉诸于独立个体的理性自律,而只能放在政治制度的框架内解决,儒家则是基于对人之自然本性的信任而建构一个外在的他律,于是,儒家最终如康德那样,有陷入“结构性伪善”的危险。
总之,正如黑格尔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7]12黑格尔“良心与伪善”的理论,也是对当时市民社会现实及理论背景进行反思的结果。
参考文献:
[1] (德)迪特·亨利希.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M].乐小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 邓晓芒,译.杨祖陶,校.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0.
[3]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四卷[M]. 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400.
[4] 舒远招.“良意、良情、良知之统一—康德良心概念解读”[J].湖南社会科学,2007(6):29.
[5]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M].贺麟,王玖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6] 邓晓芒.“康德和黑格尔的自由观比较”[J].社会科学战线,2005(3):24.
[7]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西南少数民族家训文献整理及现代性转换研究”(16BZX085)。
作者简介: 冉光芬,伦理学博士,上海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德国古典哲学、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 B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19)11-026-031
[责任编辑:黄 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