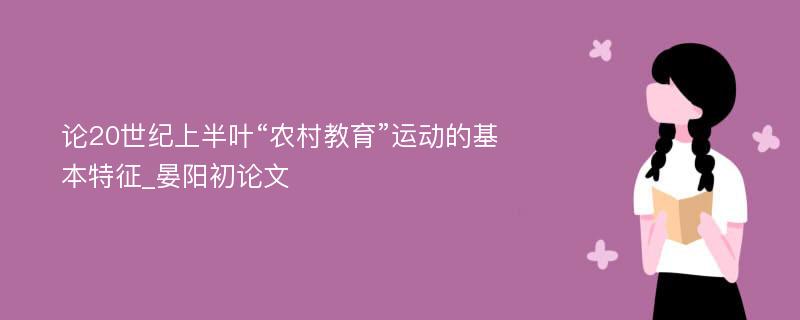
论20世纪上半叶“乡村教育”运动的基本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村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3)01-0117-07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风起潮涌般的“乡村教育”思潮运动,不仅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活跃一时的一种重要教育思潮,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重要社会改革运动。尽管它已经过去六七十年了,但“乡村教育”先驱们开始打破中国教育超然、闲适的局面,极具功利性地走出封建士大夫的象牙之塔,与时代、与政治紧密相连,可以说,“乡村教育”思潮运动,从诞生之日起,就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今天,我们站在新世纪、新千年的高度,带着沉重的历史感和时代责任感,从人类发展的伟大实践中,重新审视、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活动,令我们特别感动的是,无论是早期王拱璧的新村教育派,还是实验高潮时期的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和雷沛鸿的民众教育派,其创始人的经历和事迹,都展示着他们用青春的才华和辛劳的汗水谱写着至今仍熠熠生辉的乡村教育发展史。他们都是当时进步教育思想的传播者,科学技术的开拓者,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和移风易俗的推动者。他们都是用教育的手段和方式在塑造着中华民族的现代形象。尽管他们之间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但他们所具有的基本特点却是显而易见的。
一、深固的忧患意识
“乡村教育”先师们生活在内忧外患交相煎熬,人民生活极度悲苦的时代。这群以青年学者为主体,对中外教育研究有素的教育改革家,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但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面对华夏大地频遭列强瓜分、蚕食的厄运,忧国忧民忧时的意识从青少年到中老年历久弥深。这种忧患意识,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思想遗产的传承,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意识的觉醒,终于积淀为他们爱国思想的基础和原始动力。
诚然,忧患意识人人都有,但其性质却有所不同。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前途、命运出发而产生的忧患是公忧;从自我出发,对个人和小家庭的地位、生活的忧患是私忧。“乡村教育”家们的忧患意识是公忧而不是私忧。请看:王拱璧的大半生是在忧愤中度过的。他幼年时就对私塾生活、家庭生活和乡村环境心存忧思,发出“谁家天下”的感慨。[1](P289)自认“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P289)。袁世凯窃国后,“国耻民恨”使他无心在省城开封的高校任教,愤然去应考留日研究生。留学赴日途经沈阳时,看到“日逻驱人如驱羊,国弱方知人种贱”,“中国领土日本站,我来奉天乃创见”。[1](P249)中华民族的苦难激荡着他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在日本耳闻目睹的事实,使他“更难于安心治学”,大半时间用于校外的社会实践活动,争国权于域外。他还以留学生身份,多次潜回国内,奔走呼号,积极投身子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漫长的忧伤与痛苦的生活实践,使他超世脱俗,不计成败利钝,于1920年决心“宁到农村走绝路,不进都会求显通”[1](P312),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到农村去的人生道路。忧患意识使他成为我国乡村教育的最早探索者。
黄炎培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孜孜不倦地为“垂亡之国”寻觅“救急要药”。[2](P3)39岁时,曾作病中吟:“人当快乐时,须思天下人孰不求快乐”,“人当困苦时,须思天下人之困苦”,因而发出“身外愁长短,心头病浅深”的浩叹。[2](P65)为了探求解决中国的困苦和人民的生计问题,他矢志倡导实行职业教育。在他为之苦苦奋斗十几个春秋之后,国家民族的危亡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严峻,他十分痛惜地说:“到如今,内忧外患,重重叠叠,河山已破碎到不堪了。人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吾中华国族的命运,真所谓‘不绝如线’……一提到‘中华’两字,惟有痛心。”[2](P269)后来,他振臂高呼“集中大家的力量,抵抗敌人的压迫”,走国家民族生存的道路。正是由于他从青少年时代就萌生了忧患意识,终于铸就他襟怀宽阔、脚踏实地的可贵品质和献身精神。
陶行知早年在家乡教会学校接受西学教育时,外国人欺侮百姓之事常常牵动着他幼小的心灵,他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袁世凯窃国后,他认为民主共和在中国的这种遭遇,乃是“人民愚昧”和“领袖愚劣”造成的。因而他提出,在中国建设民主共和“最必要的手续”,舍教育则别无他途。[3](P43)1917年,他从美国留学归国后,看到帝国主义对中国欺凌宰割,军阀统治腐败,深切感受到人民所受的压迫和苦难,便立志挽回国家厄运。由于他长期忧国忧民忧时,终于成为一个“好恶真切分明”,“一直往前,奔赴真理的人”。[4](P357)
晏阳初和梁漱溟的忧患意识,除了具有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忧患内容之外,又注入了新的内容。晏阳初从小是在中西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因而他忧虑的是如何用“儒家的仁和基督教的爱”去“救国与救世”[5](P280)。他一方面弘扬“民为邦本”、“救中国”、“救自己”,改善中国劳苦大众的生活,另一方面也考虑以“基督征服世界”、“救人”、“救世”,改善世界劳苦大众的命运,因而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西化倾向的人物”。梁漱溟在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挑战和冲击下,不得不忧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他深刻地反思了中国的国民性,表达了先进知识分子对国民文化心态的深沉忧虑。他在悲痛愤懑中留心时局,积圾入世参政,期盼国家和民族的崛起,表达了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华民族悲壮的救亡意识。继而在黑暗迷惘中遁入佛门。然而,寂寥的佛门并不能使他的忧国忧民之心泯灭,最后他终于在深思挣扎中回归传统,重新膜拜于东方的古老文明。
雷沛鸿的忧患意识,使他成为伟大的民众教育旗手。雷沛鸿认为孟子讲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至理名言。[6](P35)随着20世纪30年代日寇侵略的日益加深,他指出:“必须注意民族生存的危机所在。”[6](P36)并告诫国人“我们这一代人物,生于危亡绝续之秋,必须人人下一大决心,立一大信念”:第一,随时随地备战;第二,大无畏地对敌作战。这既是中华民族自卫的主要方法,又是我们民族生存的基本条件。为了实现这种基本条件,他坚信民众教育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所在。这是因为,民众教育可以“创造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可以“唤起民族意识”,可以“恢复民族的自信力”,可以唤起民族的“自觉心”。[6](P39)由此可知,雷沛鸿一生致力于民族、民众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是他长期忧国忧民忧时的产物,是他为解救民族危亡而找到的出路。
以上可知,“乡村教育”家们的忧患意识是忧国家的前途,忧民族的命运,忧中国传统文化的中断,忧世界劳苦大众的苦难,他们是忧国忧民优天下。至于个人的经历坎坷、家境生活清贫、人们暂时的不理解等,他们都置之度外。这是一群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的思想境界和崇高品质,是正直知识分子的人格形象。
二、忠贞的爱国热忱
“乡村教育”领袖们,并没有把忧患意识停留在愤世嫉俗的宣泄和倾诉上,而是把这种忧愤化为爱国恤民之心、报国酬民之志和救国拯民之行。他们从“捍国”、“御侮”的立场出发,通过自己最熟悉的教育切入社会,投身到救国救民的伟大斗争当中。
王拱璧的一生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的一生。1907年,他在上海中国公学加入同盟会,“以身许国”。1910年,奉命回豫,发展革命组织,谋划武装暴动,因败露未成。辛亥革命后,深感民主政治徒有虚名,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怀着“实为伏虎而深入虎穴”的目的去日本留学。[1](P298)在日期间,他不畏强暴,多次参与组织留学生在东京的爱国抗暴斗争和游行示威,争国权于寰宇。特别是当他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在甲午战争、侵占台湾、八国联军劫掠北京、侵占青岛中抢劫大批中国文物,堂而皇之地在东京靖国神社展览时,顿感“冷汗浇背,热血充脑”,头晕目眩,“觉一矛、一戈、一铳、一弹、一戍衣、一旌旗,莫不染我先烈之碧血,附我先烈之忠魂”。[1](P31)于是,他先后五次入室,不顾管理人员的阻挠,将390余件赃物,一一密记下来,成为他后来所撰名著《东游挥汗录》的首篇,该著作还记载了1919年5月7日,3000名留日学生与日本警察在东京搏斗的场面,将搏斗中受伤者彭湃等27人、被捕者谭政等23人和判刑者杜中等7人的姓名、籍贯和情况一一首次披露于世,成为后人研究留日学生运动史、日本侵华史、中国青年运动史难得的珍贵资料。这部著作也反映了作者本人和留日学生置帝国主义屠刀和北洋军阀的牢狱于不顾,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
黄炎培坚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他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先驱。1917年,在上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接着,陆续创办中华职业学校、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南京女子职业传习所、镇江女子职业学校、四川都江实用职业学校、昆明中华业余中学、上海比乐中学等。后来又在上海开办了7所职业补习学校和一个职业指导所。他把自己工作的意义紧密地同国家利益、民族荣誉联系起来,真正做到与国家的兴亡盛衰休戚相关。诚如他在一首诗中所说:“我用一分精神都为国,我过一分光阴全为民。民得再生国再造,我愿卖力卖到老。”[2](P333)又说:“打开门户要入群众群,铲除崖岸要与平民平。烧得我心太阳一般热,照见我心明月一样明。‘身非我有’记得此言否?从此吾身献给民族献给国家有。”[2](P334)“一·二八”淞沪战斗打响后,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发动各界人士及社、校师生支援19路军,送衣送食送药。正是由于他对祖国深沉的爱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在苦苦奋斗了几十年后,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归宿了社会主义。
陶行知的爱国思想萌发较早。早在家乡教会学校崇一学堂读书时,他就抱着个人独立和国家独立的理想,孜孜学习。在金陵大学上学时,他紧紧抓住校刊《金陵光》这块阵地,积极宣传爱国民主思想,警勉同学要“捍国”、“御侮”,“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呼吁国人要振“国魂”,强“民气”,救“沦丧”。随着生活阅历的增长,他的爱国意识更加炽烈。他说:“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国,中国现在不得了,将来一定了不得。”[7](P41)又说:“国家是大家的。爱国是每个人的本分……凡是脚站中国土地,嘴吃中国五谷,身穿中国衣服的,无论男女老少,都应当爱中国。”[8](P54)所以,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就抱定教育救国理想,积极推行平民教育,企图通过普及教育“打通”壁垒森严的贫富贵贱等阶级关系,从而“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9](P22)正是这种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驱使他创立生活教育,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进步,终于成为一名党外布尔什维克和“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炽热的爱国情绪在晏阳初和梁漱溟身上也体现得真真切切。晏阳初是一位令人敬仰的爱国民主人士。早在幼年时代就“具有治国平天下的豪志”[5](P260)。在香港求学期间又具体感受到“国势衰微的种种悲哀”[5](P282),体会到“国之重要”和“苦难的中国,需人解救”[5](P291)。在美留学期间的所见所闻,使他认识到“华夏早已沦为二三等国家”[5](P290)。为了使中华民族生存在科技智能时代,使泱泱华夏与世界强国立于平等地位,“当从平人间智能上的不平等做起”[5](P290)。这实际上成了他后来从事平民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为此,他在以后数十年历尽坎坷,奔走天涯,一点一滴地积攒开拓平民教育事业的经费,连同他的全部心血和精力,都无私地奉献给他所挚爱的事业。晏阳初的所作所为,决不是一般的兴趣的爱好和沉迷,也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或心血来潮,这是一种真诚、美好的理想和对祖国、人民的一种虔诚和挚爱。梁漱溟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在中学读书时期就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极为关注。他亲眼目睹了西方列强“数十年间夷我于次殖民地”[4](P85),用不平等条约“束缚”我国民族企事业的发展,“几于制我死命”[4](P89)。虽然,先辈们数十年常变更“自救”的办法,但一直未能奏效。在这种对中国命运的忧愁与烦闷中,终于觉悟到“乡村建设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一个最后的方向”[4](P153)。于是,他下定决心倡导乡村建设实验活动,企图使乡村有新生命而后求中国国家的新生命,期盼以此来“辟造人类文明”和解救中国。
雷沛鸿也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在美国“工读”期间,加入了孙中山改组后的中华革命党,在纽约参与创办《民气周报》,继续宣传国民革命。在哈佛完成学业后,毅然告别身怀有孕的异国妻子,只身回到魂牵梦绕的祖国,“为穷而失教之劳苦大众教育事业而奋斗”[6](P6)。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无锡时,正在给学生上课的他,悲愤难耐地中断了讲课,全教室声泪俱下。“第二天一上课,他就在黑板上书写‘一寸山河一寸伤心地’九个大字,并令全体学生起立,自己一遍一遍地领读。他的脸因激动而涨得通红。同学们一遍一遍地跟着读,反复读了10多遍,‘诵得全堂泪眼红’。群情激愤,爱国烈火在胸中燃烧.悲愤的声音在无锡教育学院校园上空振荡”。[11](P50)面对日寇的野蛮侵略,他振臂高呼:开展“民族自救运动”,“务须念念不忘东北三省人民”,希冀全国上下“披发缨冠以纾国难”。他再度回桂主持教育行政时,明确提出“以爱国教育为灵魂,以生产教育为骨干”,“既要救穷,又要救亡”,充分体现了一位爱国教育家的崇高品质。他对日寇的残暴、骄横怒不可遏,严正指出:“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为什么他们要欺侮我们……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应该站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叫它永不反叛!”[12](P146)这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发自心底的呼声。
由上可知,乡村教育领袖们的灵魂深处无不跳动着一颗忠贞、赤诚的爱国之心。古往今来,真正成就大业的仁人志士,没有不把祖国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三、崇高的使命感和事业心
“乡村教育”先驱们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结必然积聚为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感、事业心。这是他们论著的精髓和贯穿人生轨迹的主轴或亮点。不管是从国外学成回国的“洋”知识分子,还是国内自己培养和自学成才的“土”知识分子,他们为学或做事的目的不是为了高官厚禄、光宗耀祖,而是找准自己的社会定位,匡时救世,报效祖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身上都有一种人格魅力,一种对自我价值的确信与坚持。
王拱璧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很强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他17岁中秀才后,就“自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在自己的房门上贴的对联是“豪杰无如岳忠武,秀才当学范希文”,横批为“天下为公”。[1](P3)后来在开封、上海求学期间,积极投身民主革命,同帝、官、封进行殊死搏斗,因而被乡人称为“疯子”,[1](P3)被北洋军阀当局称为“巨逆”。[1](P361)1920年从日本回国后,他把高官厚禄,安逸生活视如粪土,断然拒绝到北洋政府教育部报到,怀着超世脱俗的远大理想,把自己定位于名利、权力的谷底,豁出身家性命,从事改造旧农村,建设新农村的工作,掬一腔热血为桑梓服务,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在乡村教育的沃土中度过他生命的黄金季节。他不愧是我国乡村教育的先行者和最早探索者。
黄炎培说:“我们站在匹夫的地位,要负起兴天下的责任。”“一切从我个人做起,”把自己的聪明和力量“完完全全献给我们国家和民族生存需要的工作上”。[2](P298)几十年来,他不仅这样说,一生也这样做。他从职业教育切入社会,亲手创办、主持或参与创办了大量职业文化教育机构,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大批学有专长的职业技术人员,实践着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历史使命。抗日战争期间,他语重心长地对青年说,现在你们当学生,将来都要直接、间接地替国家服务,希望你们要自强、自尊,要凭自己的自信和勇气,来担负这“匹夫兴天下的责任”。[2](P298)他要求人们“尽国民天职”,“以坚强贞固的节操”,“从内心发出热烈的情绪,来担当救亡图存大任”。[2](P314)为了承担起历史的使命和责任,他曾两次拒绝担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职务,矢志委身职业教育。他说:“名,吾所不求;功,吾所不争,将吾整个生命,完全献给国家、民族生存工作上。”[2](P315)
陶行知为了集中精力推行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毅然辞去东南大学教授和系主任工作,脱去西服皮鞋,到农村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和山海工学团。虽历尽坎坷,却初衷不改,这与他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密不可分。他说,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展开全面的教育”,把教育展开到前方、边疆、敌后方、华侨所在地、全世界凡是有敌人斗争的地方去;[9](P259)我们应当尽自己的责任,即把各人的力量献给中华民族,毫不吝啬地贡献自己的汗、血或脑汁;[9](P256)我们生活在此时的伟大历史使命,就是“运用我们全副精神来挽回国家厄运,并创造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社会交与后代。这是我们对于千万年来祖宗先烈的责任,也是我们对于亿万年后子子孙孙的责任”。[9](P22)
晏阳初和梁漱溟的历史使命感和事业心也颇坚挺。晏阳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救国救世,都是义不容辞的。”[5](P280)“我一生奔走东西,无论在天南或地北,事业心和责任感,永远伴随左右,好似忠心耿耿的保镖。”[5](P280)因此,1919年他从法国回国后就立志“不做官,也不发财,把我的终身献给劳苦大众”[5](P280)。这成了他一生追求和奋斗的目标。他70岁以前,从未想过“老之将至”的问题,甚至90岁高龄时,他还说自己“不退不休”。[5](P280)这种“不知老之将至”的“永动机”精神,是一位爱国思想家和正直知识分子对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感的高度自觉的表现!1988年4月,在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举行的国际乡村改造研讨会上,晏阳初再一次谈到自己的使命:“现在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穷受苦,我们不揣冒昧,不分种族,不顾国界,以改造乡村,来负起达到天下一家的使命。”[5](P333)并进一步解释说:“乡村改造既是一种社会改造运动,就意味着要对自然的、社会的、历史的、现实的种种问题采取革命的措施,弃旧图新,走向光明。我们肩负的使命要求我们永远应当迎着困难上,向困难挑战,最终战而胜之。”[5](P331)由于这种“使命感和救世观”的驱使,晏阳初为中国和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饮誉海内外,度过了他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梁漱溟说,他在中学时代,国难已经开端,从那时起,他就立志为国家社会做一番事业,承担起匹夫应尽的责任和义务。20世纪30年代,严重的民族危亡摆在国人面前,他激昂慷慨地说:“民族自救的大任,除了我们更将靠谁?”[4](P44)“我们要有深心大愿,方可负荷此任。大家如果为俗见俗肠所扰,则没有力量担负此远大的工程。”[4](P135)在民族自救的过程中,他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不是发展工业和军备武器,而是补充文化,即“改造文化”、“创新文化”和“绵续文化”,换句话说,只要大家都认识孔子的道理——伦理情谊,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因此,梁漱溟自认一生的使命是“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以恢宏儒学为己任,致力于儒学的改造与创新。[12](P396)由于他多年对文化和儒学研究所做出的贡献,因而被称为“现代儒学的开路人”或“中国最后一个儒家”。
雷沛鸿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也颇感人。他长期留学英、美,多次游历世界,既学有所成,又娶有洋夫人,按今日“出洋热”者的观点,弄张绿卡,定居国外,可谓天经地义。但他为使命所驱使,怀着“为国民身心之发展而尽其绵力”[6](P6)的强烈愿望,毅然回到祖国,把自己的终身献给“穷而失教之劳苦大众”[6](P6)。回国后,雷沛鸿先后在暨南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江苏教育学院、中山大学任教授10余年,又5度主持广西省教育行政,五度出国考察教育,并出任广西大学校长、西江学院院长等职,不论从事教学或担任行政工作,他都能尽职尽责,兢兢业业,矢志不移,鞠躬尽瘁,表现出一个真正教育改革家的高尚情操和人生价值。他在兼任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院长时,上午在教育厅办公,下午到研究院上班,从不挂虚名。这种认真负责的作风和人格魅力,给同事和学生以深刻和永久的教育与影响。
由上可以看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崇高的时代责任心,是“乡村教育”先贤们积极参与改变现实的恒久驱动力。他们从自我做起,从自己最为熟悉的基层工作做起,脚踏实地,苦干实干,这种置名利、地位于九霄云外的奉献精神,比那些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权势之徒要高尚千百万倍!就是在当今社会,也值得大力提倡和赞颂!
四、执著的探索精神
“乡村教育”先贤们的人生都是执著探索的人生。他们探索着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道路,也探索着我们民族崛起、发展的道路。虽然,他们的主张并不能把中国引到新生之路,但他们在黑暗中以烛火萤光探照新的出路,终究比那些安于现状、逆来顺受、无所用心的人要高明千百倍。由于当时诸多主观和客观原因的制约,他们的实验和探索尽管没能取得理想的结果,但他们却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激起涟漪,掀起波涛,他们的人生价值得到展现。他们对民族、国家和人类进步的真诚关注,应该受到人们的理解和尊重。
王拱璧早年为了避开恶势力,而选择了远离城市的中原腹地西华县孝武营村(该村距西华县城80华里)进行“新村”实验。在20世纪初的穷乡僻壤去开创一番事业谈何容易!不仅人力、物力和财力极其匮乏,可以说,每进展一步都困难重重,而且恶势力到处都有,它决不允许身边有“世外桃源”存在。王拱璧凭着坚定的信念和执著的探索精神,从1920年10月开始,进行“新村”实验,到1926年冬,还是被恶势力扼杀了。暂时的浩劫并没有动摇他的初衷,他身在开封,仍遥领青年公学校长之职,一方面为公学募款和招聘教师,另一方面,利用关系,和地方恶势力进行不懈斗争。1928年冯玉祥主豫时,约他任省农林厅长,被他谢绝。1934年,他又在方城县后土屯村创办一所类似青年公学的嵩山公学。抗战爆发后,他先在川、康实地考察边疆少数民族状况,发表多篇论文,后又回到家乡青年村,继续以青年公学为阵地,开展抗日救国斗争。由上可知,王拱璧的青春是在奋斗和探索中度过的。
黄炎培先生在上海办职业教育,后来改为农业教育。作为一个私人教育团体,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苦苦奋斗了半个世纪,不仅为民族、国家培养了大批学有专长的职业教育人才,而且构建了独具特色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还总结积累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基本符合旧中国国情的职业教育方法和经验,终于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先驱和开拓者。这一切无不与他的不懈追求和全身心地投入息息相关。在旧中国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中,职业教育不仅报酬低微,工作繁重,教师匮乏,生活动荡。而且社会责难也不绝于耳,所有这些都不能动摇他的决心和信念。职教社刚成立时,被讥为“破靴党”、“饭桶教育家”,甚至有人把“职业学校”指责为“作孽学校”等。面对这些闲言碎语,他无怨无悔,“还是照样地朝前做去”[2](P261)。并且后来成了职教社、校的“定型风格”。不仅如此,他还坚持实地实验。并说:“不去实验,恰等于带兵的将官们不敢上火线。要是吾们的理想,连自己试验都还没有能成功,还能拿出去哄人么?”[2](P260)黄炎培还多次提到他改号的原因。他原号楚南,流亡日本时改号“韧之”。“韧字的意义,刃是刀,韦是牛皮”。用刀割牛皮,要有一股韧劲,表示他誓与清政府的反动统治斗争到底的决心。辛亥革命后,他又改号“任之”。其意,一是勇于承担责任,毫不推诿,二是对别人的议论、非难听之任之,不去管它,自己认准的路就要走到底。他认为职业教育是悠久的事业,必须不遗余力地提倡、研究、试验和推广。
陶行知也不例外。为了救亡图存,他一生迎着历史的风雨不断攀登和追求,其事迹催人奋进,令人敬仰。为了改革旧教育,把主要精力用于平民教育运动,他从1923年到1926年,南下北上,足迹踏遍大河上下,长城内外,广泛接触贫苦人民和各界人士,出入于街道、商店、工厂、机关、监狱、寺院、兵营、蒙古包之间,到处发起组织平民读书处及平民学校,甚至有两年春节都未能回家。1926年,他提出要办“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试验乡村幼儿园。1927年初,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探索中国教育的新路。后因他支持师生游行示威,遭当局通缉,逃亡日本。一年后,他又潜回上海,继续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出路。1932年他又创办山海工学团,开始普及教育的新试验。抗战期间,他拒绝任安徽教育厅长、四川教育厅长、武汉大学校长等职,奔走海外,宣传抗日救国,又创办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等。不难看出,他所走的道路何其崎岖,他的探索精神又何其可贵!
晏阳初和梁漱溟也是“一生耗在忧求之间”[5](P257)。晏阳初早年在法国从事华工识字教育。回国后看到国内“四分之三的人是文盲,人人受疾病的威胁和腐败政府的迫害”[5](P356),于是他决定继续推行识字教育运动。在探求如何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改变这种状况的过程中,他发现生活在广大农村的农民,不仅需要识字,更需要改进其整个生活。于是到定县开展农村划区实验,这一干就从1926年干到1937年,达11年之久。抗日战争期间,平民教育的实验又在华中、华西得到推广与发展。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又把定县实验的经验推向世界三大洲,在第三世界得到广泛传播和影响,因而他被誉为“国际平民教育之父”。在《90自述》中,他总结自己的一生与“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说:“60年来的工作,都是运动——识字运动、平民运动、乡村建设运动、乡村改造运动。”[5](P268)当然,大半个世纪的“运动”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诚如他自己所说:“过去在中国,我们曾受到军阀的威胁利诱,受到地主与高利贷者的围攻,受到贪官污吏的刁难与破坏,更不用说连年的战争造成了巨大的困难。”[5](P332)晏阳初还体会到:“中国的社会是:假若你落在后面,一般人都瞧不起你;你走在前头,他不了解你,误会你;如果你能搔着痛处痒处,就要打击你,摧残你,最好是同他们站在一条线上同流合污。所以我们在定县的创造工作在进行中也受到了不少的阻碍。”[5](P217)困难和阻碍并没有吓倒心怀“火种”的晏阳初,他说,要成功一件事业,一定要具有“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战乱不足忧”的精神。晏阳初正是用这种精神,把困难一一抛向九霄。他说:“知我多者认为,我的自制力强。知我浅者,说我是天生的好脾气。是乎?我自己知道,若不是忍耐,我没法活到今天。若不是忍耐,我早不愿为我的运动去募款求人,看人脸色。若不是忍耐,我早不愿住在穷乡僻壤,让虫子咬、蚊子叮。”[5](P261)所以,锲而不舍地探求与忍耐,终于铸成了晏阳初的一生大业!生在北京,祖祖辈辈一直居住在城市,和农村本没有什么瓜葛的梁漱溟,也会成为乡村建设的领袖,这是他一生不懈地探寻和孜孜追求的结果。他说,清末在中学读书时,“国家命运”多舛,“国难”已经肇端,从那时起他说:“立心吾国家社会做一番事业,希冀对国家社会有所建树。”[4](P212)民国后,国家由专制政体改为民主共和,本以为政治要求可以达到,国家已有希望,但事实竟“大谬不然”。[4](P212)民主有名无实,且“一天远似一天”,到后来“竟由失望而成绝望”。[4](P212)对于政治上的这种混乱状况,梁漱溟的见解与众不同。他不以为这是“弄权者”的破坏所致,认为是“西洋政治不合我国的国情”。[4](P212)所以,他说,欲在中国推行民主共和,“必须养成我国的新习惯”欲养成我国的新习惯,非实行“乡村自治”不可,即从乡村小范围自治做起,然后推广到全国大范围自治。”[4](P213)这是他长期对中国政治的烦闷、忧思和探寻的结果。后来,他又在政治烦闷和忧愁中认识到新风俗新习惯的养成,不是片面单做乡村自治所能成功,必须从各方面去统筹兼顾才行,于是再进行乡村建设的运动——开辟建立新组织制度,完成中国社会的改造,于是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主持下召开了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产生了一个“中国乡村建设学会”,分建派正式形成,梁漱溟成了乡村建设领袖。
雷沛鸿非常重视教育学术研究,特别强调教育实验。他说,在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我们的一切生活不能墨守成规;相反的,一切的一切概须用实验方法求出路”。教育问题也是如此。为了在广西顺利地推行国民基础教育,在他第3次出任广西教育厅长时,创建了“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亲任院长,院内特设实验推广委员会,并以家乡南宁市津头村为中心,划定四周20里之内的村、街作实验中心区,凡制定办学方针,拟定组织规程,编写教学指导书,培训师资等,都要经过研究实验,从理论上论证,从实践中检验,取得可靠成果后逐步推广。1940年,他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成立广西教育科学研究所,对国民教育,特别是国民中学教育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在那样的时代,身为一省最高教育长官,如此重视教育学术研究,认真进行教育实验,实在难能可贵,令人感动佩服。这是他抗战期间在教育实践中取得骄人成绩的重要原因之一。
“乡村教育”先贤们的这种不懈探求的精神,与他们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使命意识紧密相连。可以说,没有前三个特点,就不会有这第四个特点。这第四个特点是在前三个特点的驱动下升华和迸发出来的。一个无廉耻、无信仰、无知无识、无情感的行尸走肉是不会去探索的,一个妄自尊大和自暴自弃之徒,也不会在探索领域里下这样大功夫的。“乡村教育”领袖们的探索精神是正直的学者的人格特点和思想品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需要大大提倡这种奔赴真理而百折不挠的探索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