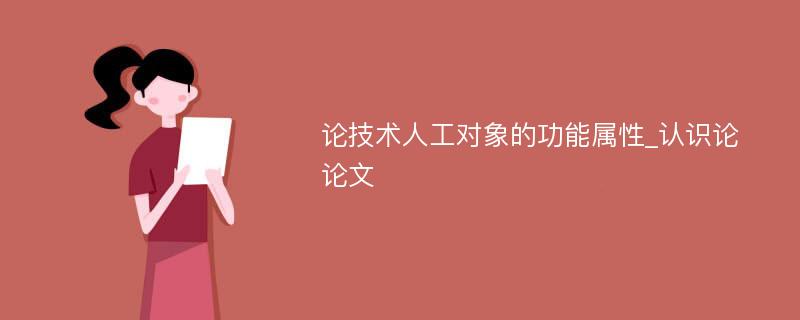
论技术人工物的功能归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功能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0-0763(2012)03-0001-05
一、技术哲学视域中的技术功能
技术人工物的功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乃至在整个现代工业流程中都处于核心位置,([1],p.5)工程师在设计、制作、维护技术人工物时都假设技术人工物及其组件具有功能,用户在使用技术人工物时也在心理上预设了技术人工物具有某种功能。那么技术人工物及其组件“具有功能”意味着什么?对这个问题,工程师和哲学家都怀有极大的兴趣。工程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主要是为了实用目的:在现代工程中,他们感兴趣于如何用软件工具格式化或可定量计算化地表述技术人工物的功能属性,以便支持工程师的日常工作;而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主要是由于功能这个概念与目的论的概念相连而引起了一系列概念上的、本体论的和认识论的问题。[2]
当工程师和哲学家对技术功能这个概念思考时,都面临着分析技术人工物的功能与技术人工物的物理结构以及人的意向之间的关系。然而,工程师和哲学家的分析思路有所不同。从工程师的视角来看,技术人工物的功能与技术人工物的物理结构紧密相关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正是技术人工物的物理结构实现了或执行了技术人工物的功能。工程师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设计、研发和制作能实现技术功能的技术人工物的物理结构。然而,技术功能看起来也与人使用技术人工物的目的相关,或者说与人的意向相关。例如,只是因为有人的使用目的,一个木棍与钢混合的物理结构才作为螺丝刀使用,或者说这时螺丝刀才作为一种手段,具有一种功能。在工程实践中,技术功能与人的目的密切联系在工业流程的早期阶段就已显现,例如在设计的前期,人类的需求和意愿就被转译为技术人工物的功能和规格要求。
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则起步较晚。随着技术哲学经验转向之后研究主题的转换,技术人工物的功能以及功能与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才被着重关注。目前,在技术人工物功能的哲学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认为“技术功能”是一个“心理依赖”([3],pp.213-233)(mind-dependent)或者说“意向依赖”[4](intention-dependent)的概念,技术人工物只有与人的意向相关联才具有功能。在这种心理依赖的观点看来,任何一个技术人工物功能的目的论的解释都可以追溯到人类带有意向的行为的目的,从而避免了技术人工物本身是有目的的客体而引起的问题。技术人工物作为“做某事”的载体,之所以具有这些“用途”,只是因为它们与人的目的相关。
在哲学理论中,这种技术功能心理依赖的观点通常被表述为功能归属理论(function ascription theory),它来自于约翰·塞尔对于功能归属的论述。塞尔认为,无论是自然物还是执行一种归于它的功能而特别创造出来的技术人工物,人类具有一种明显的赋予这些对象某些功能的能力。“人工物的功能不是物理学的任何现象所固有的,而是由有意识的观察者从外部赋予的”,([5],p.14)“功能的归属就是我们意向性地归于这些对象的用途”。([5],p.20)然而,正如汉森指出的,塞尔功能归属的概念本身是模糊的,功能归属可以是“描述意义上的功能归属(descriptive function ascription)”,也可以是“执行意义上的功能归属(performative function ascription)”。[6]克罗斯也认为不应混淆描述的功能归属和执行的功能归属,只有执行的功能归属才符合技术功能的心理依赖性。[2]同时,汉森虽然提出了描述的功能归属和执行的功能归属,但是并没有详细解释两者之间的区别,以及如何具体运用描述的功能归属和执行的功能归属理论解释技术人工物的功能。本文旨在就这些问题深入探讨,澄清技术哲学视域中的技术人工物的功能归属以及描述的功能归属和执行的功能归属之间的区别。
二、基于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技术功能分析
为了澄清技术功能归属的内涵,有必要首先区分认识论和本体论上的技术功能。
1.主观性和客观性概念
在讨论认识论和本体论上的技术功能之前,还要首先区分主观性和客观性的概念。塞尔提出区分主、客观概念主要有两条途径,一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另一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5],pp.7-9)从认识论意义上来说,主观和客观是对“判断”的基本论断。“当我们说某一判断是主观的时,通常是指这个判断的真假不能被‘客观地’解决,因为判断的真假不单纯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且要依赖于做判断的人和听到判断的人的某种态度、情感和观点。”([5],p.8)塞尔举了两个例子,一是陈述句“伦布朗是一位比鲁宾斯更优秀的艺术家”,二是陈述句“伦布朗在1932年居住在阿姆斯特丹”,前者是一个主观性的判断,后者则是一个客观性的判断。而从本体论意义上来说,主观和客观则是实体的属性,描述了实体的存在方式。塞尔举例说在本体论意义上“痛苦是主观的,而山是客观的”,因为痛苦的存在依赖于主体的感受,而山的存在则不依赖于任何感知者及其心理状态。
2.技术功能的主观性与客观性
在对认识论和本体论的主、客观概念区分的基础上,我们再来分析技术人工物的功能可以发现,当我们在本体论意义上提及技术人工物的功能时是把功能看做一种实体,是要分析其在本体论上是主观还是客观的实体;而在认识论意义上提及技术功能时是将功能(归属)看做是一种判断,是要分析其在认识论上是主观或是客观的判断,这是我们在分析技术人工物的功能前必须明确的一个前提。
沿着这个前提我们来具体分析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技术功能。当我们描述一个技术人工物的功能时,该技术人工物的功能是与观察者和使用者相关的(“观察者和使用者”包括制造者、设计者、所有者、购买者、出卖者以及以其意向指向这个人工物的任何其他人)。“它之所以是一把螺丝刀只是由于人们将它作为一把螺丝刀来使用”。([5],p.10)螺丝刀的功能依赖观察者而存在的特征并没有给实在世界增加任何新的物质客体,所以螺丝刀的功能的存在具有本体论上的主观性。因此,当我们对比生物功能的客观性而说技术人工物的功能具有主观性时是指本体论意义上的主观性。相反,就认识论意义上来说,对螺丝刀功能的判断具有认识论上的客观性,“这是一把螺丝刀”这个判断不会因判断人的某种态度、情感和观点而发生改变。
3.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技术功能分析的诉求
澄清技术功能本体论上的主观性和认识论上的客观性之后,我们来分析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技术人工物“具有功能”的含义。当我们说一个技术人工物或技术系统“具有某一功能”时是指这个技术人工物可以被用来“做某事”,而解释某一技术人工物“具有”“做某事”的属性的内涵可以是认识论上的也可以是本体论上的。具体来说,认识论上是要关注技术主体A判断技术人工物X“具有”“做某事”的属性这个判断,也就是要分析“主体A有理由相信(或者甚至知道)技术人工物X有做某事的功能属性”意味着什么,其目的是在对技术人工物的某些属性的正当信念中,明确主体A有技术人工物X具有做某事的功能属性的正当信念。这个目的只有在这些关于功能属性的正当信念不被看做是人工物本身的信念时才有意义。而本体论的目的是要将人工物“具有做某事”的属性看做是更根本的本体论属性。([7],pp.69-87)
技术功能认识论一般有以下形式:“主体A如果有理由相信技术人工物X具有属性P1,…Pn,那么主体A就有理由认为技术人工物X有做某事的功能属性。”[2]例如,一个由玻璃和金属丝复合组成的技术人工物X,主体A根据X及其组件的物理和化学属性有理由相信X具有能通电、发光等属性,那么主体A就有理由认为技术人工物X可以作为照明的电灯使用。
三、技术功能归属的形式与分类
1.技术功能归属的形式
在技术功能的文献中,上文提及的技术功能认识论的形式很少出现,而一般是以功能归属理论(function ascription theory)的形式出现的。具体来说,功能归属理论就是当主体把某一功能属性归属于一个技术人工物时,要详细论证该主体具有此归属的正当信念的必要的和充分的认识论条件。功能归属理论否认技术人工物自身在本体论上有其内在的功能属性,认为技术人工物的功能有心理依赖性或本体论上的主观性,技术人工物的功能是意向主体归属于或指派给技术人工物的。功能归属理论的形式如下:“主体A如果有正当的信念C1,C2,…,Cn,那么主体A就有理由将能做某事的功能属性归属于技术人工物X。”[2]
麦克劳克林还提出了本体论意义上的功能归属。他认为技术人工物的功能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被技术主体给予、归属于技术人工物的。技术主体通过自己的信念和愿望将技术人工物的功能赋予这个技术人工物,如果没有技术主体,就没有主体的目的,也就因此不存在技术人工物的功能或其他人工物的范畴。“螺丝刀、拖拉机和剪刀都是在文化的意义上被认定为是有功能的种类而不是自然种类的”,([8],p.44)根据麦克劳克林的理论,至今存在的技术人工物及其功能都是关涉人类主体的精神状态的。如果假设这些精神状态是世界基本的本体论构成,那么麦克劳克林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技术人工物的功能归属形式如下:如果在技术主体A的精神状态中,F功能被给予(归属于)技术人工物X,那么技术人工物X就有与技术主体A的精神状态相关联的F功能属性。
2.技术功能归属的分类
在上面论述的技术人工物功能归属理论及其形式中,正确的解释“归属”的概念是至关重要的。技术功能归属分为描述的功能归属(descriptive function ascription)和执行的功能归属(performative function ascription)。汉森指出,目前,功能归属在描述的功能归属和执行的功能归属这两种含义的区分上是模糊的,他明确了这两者的区别,认为当主体持有或表达一个客体有某一功能的信念(或类似的命题态度)时,该主体就做了一个描述的功能归属。汉森举例说,当我告诉我的朋友我的小提琴上某一特殊装置是一个小提琴肩托时,我就做了一个描述的功能归属。而执行的功能归属,是主体将某一客体以前不具有的功能指派或尝试指派给该客体的言语或行为。例如,我开始将某一个特殊的垫子作为小提琴肩托时就完成了一个执行的功能归属。又如我的小提琴琴弓在制作时就被琴弓制作者指派为有琴弓的功能,如果某人将琴弓偷去支撑开着的窗户,那么他就给了这个琴弓以窗撑的功能。
在目前的技术功能理论中,描述的功能归属和执行的功能归属这种区分很少被注意到,功能归属仅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然而根据上文讨论的两者之间的区别,描述的功能归属和执行的功能归属应该被明确地区分。当主体做一个描述的功能归属时,其本质是做一个认识论上正确或错误(有正当依据或没有正当依据)的判断;而做一个执行的功能归属时,应该用成功或失败来评价技术功能归属主体的行为。当然,除了强调描述的功能归属和执行的功能归属之间的区别之外,也应注意到二者之间的联系:当主体A首先成功地做了一个关于技术人工物X的执行的功能归属行为后,另一主体B基于此有了技术人工物X能执行该对应功能的信念或知识,这时主体B就可以做出一个正确的描述的功能归属的判断。
3.技术功能归属存在的问题
根据上文对描述的功能归属和执行的功能归属的区别,我们可以发现,当我们说目前的技术功能认识论一般以功能归属的形式出现时,这里的功能归属是指描述的功能归属的形式,而不是指执行的功能归属。为了更清晰地区分描述的功能归属和执行的功能归属,克罗斯提出将执行的功能归属称为功能指派。因此,我们可以称目前的技术功能认识论是以描述的功能归属的形式出现的,而并不是以功能指派的形式出现的。
当我们具体分析技术功能认识论的功能归属的形式时,就会发现这种形式存在一定的问题。功能归属是在描述的意义上解释技术人工物的功能的,也就是说当主体A有正当根据地相信技术人工物X有做某事F的属性时,主体A就能将F功能归属于技术人工物X,反之亦然。所以,可以说主体A相信技术人工物X有F功能等同于主体A有正当根据地将能做F事的属性归属于技术人工物X。因此,主体A可以不依赖于他自己或其他人将F功能指派给技术人工物X的行为而有正当根据地认为技术人工物X有F功能属性。这样,当主体A在做技术人工物的功能归属描述时,并不涉及主体A或其他人指派给技术人工物X某F功能的这个意向行为的目的,也因此,描述的功能归属并不符合技术功能理论的“心理依赖”性。
另外,描述的功能归属还可能引起技术人工物的功能属性存在性质上的关联性。例如某些情况下,主体A的正当信念C1,C2,…,Cn不仅是关于技术人工物X本身的,还要关涉其他因素。在弗玛斯和霍克斯提出的ICE功能理论中,主体A将功能归属于技术人工物X时,就要与技术人工物X的使用计划P和对技术人工物X行为的解释E相关联。[9]因此,对这个技术人工物X来说,其功能属性是一种关联属性。这样,功能归属的形式就改变为:主体A如果有正当的信念C1,C2,…,Cn,那么主体A就有理由将与R相关联的F功能归属于技术人工物X。这里的关联项R除了弗玛斯和霍克斯ICE理论中的使用计划P和主体解释E之外还包括其他类型的因素,比如社会组织、社会实践以及技术人工物X作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的复杂技术系统。
四、功能指派及其对技术功能心理依赖性的合理解释
1.功能指派成立的必要条件
执行的功能归属,或者说功能指派与描述的功能归属相比,就避免了上面提及的问题,仅仅是一个执行的有意向的行为就具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意义。仅是功能指派这种执行的包含意向的行为就可以在创建新的技术人工物时发挥作用,这也正符合了塞尔和托马森等[10]坚持的“心理依赖”的功能理论。例如,根据塞尔的观点,一个物质客体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螺丝刀仅仅是因为人类将这个客体作为螺丝刀来使用(或使用它为了能当做螺丝刀的目的,或将其看做是螺丝刀),或者说,仅是因为人类将作为螺丝刀的功能指派给这个物质客体。因此,在塞尔的理论中,功能指派具有本体论上的意义,因为功能指派可以将一个物质客体转变为螺丝刀。
当然,塞尔的理论还不够精确,例如克罗斯提出的一个功能指派的例子,当他试图将电话用作订书器时,他尝试指派给他的电话一个订书器的功能。但是,这是一个失败的功能指派,这种功能指派并不在认识论或本体论上支持电话具有订书器的功能。因此可以看出,“成功”是功能指派具有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的必要条件。但是要注意下面这种情况是一种例外。例如,当我打开我的电视机观看电视节目时,由于电视机的开关按钮坏掉而导致电视机不能工作的情况。在我打开电视机的行为中,暗示了我指派给电视机播放电视节目的功能,只是由于电视机功能失常,播放电视节目的功能才不能实现,但是这个客体仍然是一台电视机,这完全不同于我将订书器的功能指派给电话这种失败的功能指派。
除了功能指派在实用中的成功性,一些认识论上的考虑也对功能指派有重要作用。比如功能指派主体的信念——指派主体知道或有理由相信被指派功能的客体具有某一特别的、能实现所指派功能的物理性质,或者,他知道或有理由相信如果客体被以一种恰当的方式使用,这个客体将会成功地实现被指派的功能。[11]
2.功能指派对技术功能的解释
借助功能指派,心理依赖性技术功能理论中的人类意向可以以如下的方式被解释:根据心理依赖性理论,无论是认识论的还是本体论的,物质客体只是由于与人的意向或意向活动相关联才具有功能属性。这些人的意向或意向活动的形式之一就是功能指派。塞尔所提及的功能归属和麦克劳克林指涉的功能归属皆是执行意义上的功能指派。根据这种技术功能的心理依赖性理论,物质客体仅是由于与人的功能指派相关联才具有功能属性。
一般情况下,功能指派者和功能归属者是分开的,例如在考古学家探究某种古代的技术人工物的功能时,功能归属的主体与功能指派的主体是不同的。考古学家的行为是一种认识行为,他感兴趣于获得关于技术人工物功能的可靠知识,他对技术人工物功能的推断是一种描述的功能归属的判断。而技术人工物古代的制作者和使用者对于技术人工物可能并没有认识上的兴趣,而只是怀有一种实用的兴趣,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对技术人工物做出了功能指派的行为,而正是因为这种指派才使得技术人工物具有功能。
而更复杂的情况是,功能指派与描述的功能归属者是合一的。这种情况发生在当某人成功地创造出某一类技术人工物中的第一个单品(螺丝刀),并且声称他所制作的客体确是他所声称的技术人工物(螺丝刀)时。这个新的技术人工物的创造包括了一个功能指派和一个功能归属。根据托马森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中,这个创造主体具有一种认识论上的优先地位,([12],pp.52-73)因此,主体声称这个新的技术人工物是一把螺丝刀这个判断不可能是错误的。托马森的理论允许技术人工物的制造者具有这种认识论上的优先地位,这就使得这个创造者具有直接的功能指派的知识。另外,对这种情况还有另一种相反的解释。如某些功能本体论理论的必要条件中只承认社会集体(具有文化意义)的功能指派,不承认个体的功能指派,也就是说这种理论不承认某一发明者在本体论意义上能制造出一类新的技术人工物中的一个单品,这种功能本体论在认识论上的反映即是:这一发明者不能仅在他自己的功能指派的基础上做出一个有正当理由的功能归属。因此,根据这种理论,上面这个例子中不存在成功的功能指派和正确的功能归属。
[收稿日期]2011年3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