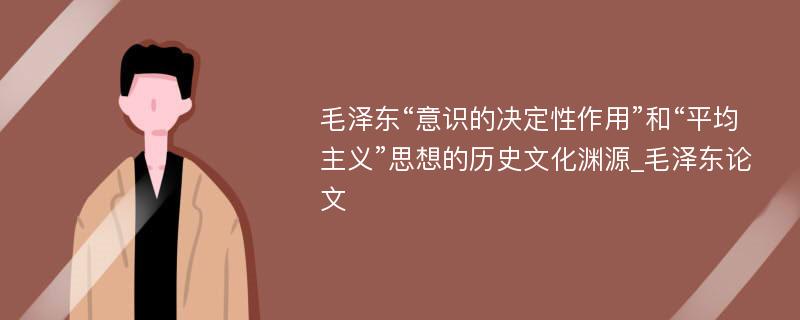
毛泽东“意识的决定作用”和“平均主义”思想的历史文化溯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均主义论文,历史文化论文,意识论文,作用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在毛泽东的著述和实践中,“意识的决定作用”和“平均主义”思想十分突出。“意识的决定作用”的思想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本源”思想和“心力”说的继承,后来发展为“主观意志和能动作用”。他坚信“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推崇“人定胜天”,提出“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都可以寻到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子。“平均主义”思想则源于古代的“大同”思想。多少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华精英无不崇尚财产公有、人的平等、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大同”盛世。这一思想对青年毛泽东影响至深。尽管他曾经严厉地批评过“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的绝对平均主义,但他始终没有彻底地抛弃平均主义,以致使“大锅饭”、“铁饭碗”式的经营和分配方式在中国畅行无阻。可以说,毛泽东对平均主义既有改造,也有迁就;既有批判,也有认同,中国革命就是在这样的价值选择中彳亍而行。探讨这两种思想的文化源流,无疑可以为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事业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
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思想家、革命家的毛泽东,在他一生的理论著述和革命实践中,给人们留下的教诲和经验是多方面的,难以尽述的。其中,毛泽东“意识的决定作用”和“平均主义”思想给人们留下的印象颇深。无论是在摧毁旧世界、建立新中国夺取政权的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乃至“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从未忽视过“意识的决定作用”和“平均主义”,而且时时处处强化、坚持这两种信念。笔者认为,在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时期,对此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研究,探求其历史渊源,肯定其历史作用,总结其历史教训,具有新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限于篇幅,本文只浅析其历史文化渊源。
一、毛泽东“意识的决定作用”思想源于对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并为中国当时斗争所需要
存在和意识是哲学中的两大范畴。存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对存在有反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而毛泽东更看重意识的反作用方面,并强调思想、道德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这不能看作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在存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上的背离,准确地说,正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标志。当然,这种发展是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为之开拓了视野,而且更有与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历史继承关系。
从历史继承方面看:本源是“五四”前期青年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最根本的范畴。可以说,阐发他当时任何一个方面的主张,都或多或少要涉及到他对本源的执著追求,以及他立足本源对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的观察和评价。
所谓本源,事实上就是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心目中的宇宙生存和发展的终极精神实体。如老庄的“道”和“太极”,柏拉图的“理念”,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等。在中国古代哲人中,明确把“太极”和“道”表述为本源的,是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毛泽东青年时最崇敬的伦理学及修身课的老师杨昌济,服膺于朱熹之论,他用大原或大原则来表述朱所说的大本,认为宇宙之所以为一个整体,是因为有一种贯通其间的大原则,“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悉自此大原则生”。人们应该深思默会,通晓和掌握它,这就叫“贯通大原”。
青年毛泽东上承于朱熹,下受于杨昌济,津津乐道于大本源。他说自己“将全副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所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去占日力。”后来,毛泽东精读康德学派哲学家泡尔生所著《伦理学原理》时,当读至“国民益进化,则能采其过去之历史,以构成理想。而实则全世界文明历史之生活,乃皆观念之所管辖也”时,则特意在眉批上加以肯定:“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这大概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启蒙阶段。
随着青年毛泽东对救国图强之策的孜孜求索,大本源这一云山雾罩的、看不见摸不着的、纯思辨的东西,毕竟解决不了现实革命的问题,他又把注意力放在对“心力”说的研究上。所谓“心力”,用青年毛泽东的语言表述就是,主体的精神、信念产生的力量。他始用这个概念,是受谭嗣同的影响。谭嗣同在《仁学》中写道:“人力或做不到,心力当无有做不到”,“夫心力最大者,无不可为”,“若能了得心力之本源,当下即可做出万万年后之神奇。”谭嗣同呼唤这种极端的主体精神力量,目的是用它来改造民心,冲决罗网,拯救民族的劫运。在这一目标上,青年毛泽东与之不谋而合。他说:“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青年毛泽东还曾以《心之力》为题写了篇文章,对“心力”问题做了较多的阐述,杨昌济极为赞赏,给打了满分。这是青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又一取向。
当然,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经过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反复探求和实践的毛泽东选择的最后哲学信仰是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后的革命实践和理论著述中,他抛弃了这一神秘的主观心力说,代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学说。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毛泽东那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从来没有忽视过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也就是说,抽象的“心力”在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那里,已升华为具体的革命意志了。
意志力,是任何一个革命家都不可缺少的东西。毛泽东始终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要改造主观世界,就是充分注意到了强调革命者的主观意志,提高革命者的思想素质,对于革命实践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这反映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中,主观能动性自然成为他经常谈论的话题。他坚信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转化规律,推崇“人定胜天”的传统观念,提出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在他长辞人世前不久,还写下激情豪迈的诗句,宣称“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用来警示后人。
毛泽东强调“在一定条件下,意识的决定作用”不无道理,并已被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今天,我们以回顾总结的目光来看,当时的“一定条件”,并能使意识发挥“决定作用”的因素有二:
其一,当时的主要目标是夺取政权的斗争,而不是经济管理和发展生产力,在这种政权的斗争中,人的主观意识本来就起着重要作用。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必须有统一的纪律和意志、高尚的道德和集体主义精神,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其二,近代以来的社会结构,特别是阶级关系、民族命运特征合乎逻辑地把一大批走投无路的农民“逼上梁山”,也唤起一大批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探索中国社会的改造道路,而这些同样需要强烈的主观意志发挥作用。
这就说明,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特有的斗争形式和环境,不仅造就了毛泽东特有的领袖性格,而且开拓了他的哲学视野,在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意识的决定作用”这样的新命题,而且它在指导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至于建国以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毛泽东仍然强调这一观点,尤其是大跃进时竟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应如何评价,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二、毛泽东的“平均主义”思想源于对“大同”说的执著憧憬,并受当时具体斗争环境的困扰
平均主义思想,作为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文化心态和价值观念,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源远流长,根基深厚。作为驾轻就熟地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大量吸收、改造、运用和发挥的毛泽东,对平均主义的危害不能视而不见。既然如此,毛泽东又为什么对平均主义倾向给予肯定和保护呢?这就说明还有影响、阻碍他超越传统的东西存在。这种东西是什么?从社会理想的层面上讲,中国文化传统中最深刻也是最根本的,莫过于“大同”之说了。
最著名的对“大同”的描绘,当数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礼运》。作者根据远古传说,确认人类历史上有个财产公有、人人平等、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和睦时代。其他如《吕氏春秋》、《管子》、《列子》都曾谈到太古之时“未有君臣上下之别”的美景。这些说法对力图维护等级制度的封建统治者固然是不利的,但由于讲的是“太古”之事,又是经传所见,诸子所言,竟也无人出来批驳诋毁,倒是给一代代知识分子以深刻的影响。几乎无人不知“大同”之说,怀古玄想之人屡见不鲜。一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从怀疑、憎恨、批判封建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出发,总会形成自己的社会理想。同一篇“大同”之说,可以是怀古思昔的依据,也可以是构想未来的凭借。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无不受“大同”之说的影响,也始终未能逾越这一闪耀古朴之光的境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是这方面的一篇代表作。从那个不为人世所知,“黄发垂髫”一并“怡然自乐”的平等山村中,我们可以看出远古“大同”传说是怎样经过知识分子的头脑而转化成对理想社会的憧憬的。怀古和理想的思维光束聚集在同一视屏之上,重合为一个永恒美好境界,召唤着一代代的民族精英。
作为熟读文史经典又深受新村主义、工读主义影响的青年毛泽东,本来就是怀着一个伟大的理想、一个建造空前未有的新社会、新人格和新生活的冲动投身革命、投身实践的。当他在《礼记·礼运》中读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这些描述时,怎能不为之动容振奋,一拍即合呢?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伦理关系、经济关系、社会秩序、道德境界啊!
尽管毛泽东早在1917年至1918年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曾对大同圣域表示否定和怀疑,但并不妨碍他在革命战争年代自觉不自觉地用它来鼓舞革命者的意志,提高农民队伍的人格境界,激发人们对未来的期望,最终转化成为愚公移山那样的实践力量。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便直接肯定了大同理想的合理因素,肯定了大同境界与共产主义理想的吻合之处,提出“努力工作,创造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的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他还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大同的路。什么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道路呢?他回答说:“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大同”理想的根基,是平均主义。它自然会给革命的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对此并不是没有察觉。1929年末,他在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中,针对当时红军(主要来自农民)中反对分轻重伤发给伤兵费用,认为官长骑马是不平等制度,要求物品的分配绝对平均,甚至出现了一副担架两个伤员时,宁愿大家都抬不成也不愿先把一个人抬了去的现象。对此,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绝对平均主义”的概念,第一次认真地向这一传统思想开了火,并分析了它的来源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其实质是“小农资产者的一种幻想”。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了青年知识分子中的一些“绝对平均主义”思想。1948年春,针对土地改革中出现的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和乱打乱杀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1949年7 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又提出一个深刻的任务:“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应该说,毛泽东对平均主义的批判始终没有放弃,但这种批判很不彻底,其表现有二:
其一,毛泽东对平均主义的批判改造,大多是就事论事,为了直接解决它在某些工作中或某一阶段上所造成的危害,随着问题的缓解,批判和改造也随之放松,从来没有就平均主义问题像群众路线那样做出系统的阐述和理论上的总结。
其二,毛泽东使用“绝对平均主义”这一概念,在相当程度上给批判平均主义设定了范围,似乎“平均主义”没有错,只是不能“绝对”罢了。其实二者并没有根本区别。
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大同”说的执著憧憬,充分地利用了平均主义对发动人民革命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决定了他对平均主义既有改造、又有迁就,既有批判、又有认同的最终态度。可以说,这个问题困扰了毛泽东的一生,使他领导的中国革命,就在这样的价值选择的困境中彳亍而行。
综上所述,毛泽东“意识的决定作用”思想也好,“平均主义”思想也好,都和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有关,并又用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它有历史贡献,也有历史局限,为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在正确处理道德建设、经济建设和分配等问题上都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这正是我们今天研究其历史文化渊源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