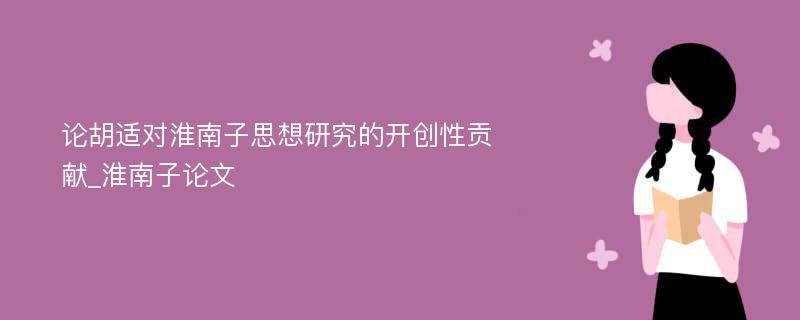
论胡适对《淮南子》思想研究的开创性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淮南子论文,胡适论文,开创性论文,贡献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1-0143-006
胡适曾于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30年写成《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每章写成时曾由上海中国公学油印,以后胡适曾抽出部分稿子公开发表。此书的第五章《淮南王书》(《淮南子》)即于1931年上海新月书店印行单行本,这是胡适对《淮南子》作思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胡适的《中国中古思想小史》,是他于1931-1932年在北京大学教书时编写的讲义,曾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行,此书的第四讲《道家》,也以《淮南子》为个案,作了充分论证。以上几种著述,是本文论述胡适对《淮南子》思想研究的主要文本依据。胡适作为《淮南子》思想研究的首创者,其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是对《淮南子》思想属性的辨识,二是对《淮南子》“无为与有为”思想的论析,三是对《淮南子》政治思想的发掘,四是对《淮南子》“出世”思想的探研。胡适的贡献不仅在对《淮南子》思想研究的全面深入的开创性上,而且为中古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诸多方法论的学术路径,这对后世治学具有极大的启示与借鉴。
胡适一生做学问讲了一辈子的“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他一生所写“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的文章,据说总数约在百万言以上。他早年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就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哲学史”①,他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于1919年2月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蔡元培在为该书写的《序》中称其科学的“证明的方法”以及“截断横流”的“扼要的手段”。[1]他在这里就用了科学的方法,他一生所用的科学的方法,即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或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2]他的思想与方法大抵是从西方进化论、赫胥黎的存疑主义以及杜威的实验主义那里汲取的,再加上他固有的中国传统的考据学的功底,这样就使得他在从事《淮南子》思想研究上,更能在“假设与求证”方面作出开创性贡献。
胡适是具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他在《淮南王书》第一章“淮南王和他的著书”中,就通过大量文献以证明,《淮南子》虽有宾客的帮助,但书中很有淮南王刘安的手笔,认为“淮南王是很能作文辞的”。“淮南王的提倡神仙方术颇有假此事号召革命之意。革命虽不成,然淮南王好神仙的名誉却流传很久远。他曾拊循百姓,颇得民心。”[3]120胡适将刘安的“造反”视为革命,又称赞他“拊循百姓,颇得民心”,可见他对刘安的思想文辞是颇为欣赏的。
胡适有个特点,他研究任何一部书都想找出书里的“思想系统”,他研究《淮南子》的思想更要找出它的“思想系统”,《淮南子》的思想属性是什么?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书?是道家的?是杂家的?是儒家的?关于《淮南子》的思想性质,有诸多说法:最早的班固《汉书·艺文志》将《淮南子》视为杂家,认为其“漫羡而无所归心”,没有一以贯之的统一的思想。王夫之也将其思想归之于“杂”;高诱则认为《淮南子》是道家之书;到了近现代学者,有从杂家说的,有从道家说的,有“外道内儒”说的(如李泽厚),等等。②胡适的高明处就在于:他在《淮南王书》开篇第一章就说:“淮南之书是一个大混合折衷的思想集团。这就是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说的‘道家’。”[3]121接着在第二章的一开头就说:“道家是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王书》又集道家的大成。道家兼收并蓄,但其中心思想终是那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道’。”[3]123胡适在这里首先“假设”《淮南子》是一部“大混合折衷的思想”,而道家的思想则是“兼收并蓄”,“大混合折衷的”。何以见得?“拿证据来”!胡适从先秦思想史料中考察出道家实际上综合了儒、墨诸家的思想。他说在先秦的思想史料中,从来没有道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的名称,以韩非的《显学篇》为例,韩非就说过:“世之显学,儒墨也。……孔墨之后,儒分八家,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韩非在战国最晚期还只承认当世的“显学”不过儒墨两大学派。[3]193而儒与道是什么关系呢?他以自己的《说儒》长文对儒的论述为例,特别提出了儒、道相融,“孔子和老子本是一家”之说。他研究“儒”的来历,其结论是:“儒殷民族的礼教的教士,他们(在殷亡之后)在很困难的状态之下,继续保持殷人的宗教典礼,继续穿戴着殷人的衣冠。他们是殷人的教士,在六七百年中渐渐变成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教师。他们的职业还是治丧,相礼,教学。……这才是那个广义的‘儒’。”“儒”字的本义是柔儒,《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而《老子》的教义也特别注重“弱之胜强,柔之胜刚”。从尚柔相通处出发,他找到了儒、道本不是相抵牾的,而是相融通的,“老子和孔子本是一家,原无可疑”。这样,“道家”思想“兼收并蓄”,“大混合折衷的”特点也就显而易见了。
如果说胡适将《淮南子》的性质归之于以“道”为主体的“大混合折衷的”思想系统,是他研究《淮南子》思想的一大发明,那么他对《淮南子》“无为与有为”思想的论析,又是他对《淮南子》思想研究的独特贡献。道家哲学规定“道”的特性是无形而无不在,无为而无不为,胡适认为:他们就是用这个原理来建设他们的无为主义的人生观和政治观,《淮南子》的无为主义即把自然演变的宇宙论应用到人生和政治上了。他以《原道训》为例,《原道训》说:“万物固以自然,圣人又何事焉?”他讲这上半句是宇宙观,下半句把宇宙自然用到人生和政治上去了。天地万物的形成,都只是自然的演化,没有安排,也没有主宰。人生和政治也可听自然的变化,《原道训》:“是故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未,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淡然无治而无不治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这里强调的“不为物先”,他们也承认万物“无时而不移”,但你不要去勉强变换它,只须跟着时变走就行了。在胡适看来,《淮南子》“不以物先”、“不易自然”,甚至还“不以人易天”,[3]134把自然演变的宇宙论用于人生和政治,形成这种无为政治,这样的“不以人易天”竟是要回到最原始的状态,这便是极端的自然主义了。这种极端的自然主义当然有其消极的一面。但是,胡适又进一步诠释到:他们也知道这种极端的自然主义是行不通的,因而就有了《修务训》中专说有为的必要:
如曰,“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象”。吾以为不然。尝试问之矣。若夫神农尧舜禹汤,可谓圣人乎?……以五圣观之,则莫得无为明矣。……(以下历叙五圣的功业)……此五圣者,天下之盛主,劳形尽虑,为民兴利除害而不懈。……不耻身之贱而愧道之不行,不忧命之短而忧百姓之穷。……圣人忧民如此其明也,而称之无为,岂不悖哉?③
胡适讲这便是“很明白的有为主义了”。但他们又不肯放弃无为论,这就形成了无为与有为之间的调和论调。
胡适不仅考释出了《淮南子》的在无为与有为之间的调和论调,而且还深入论述了它为何会出现这种调和之论。他以荀子批评庄慎的完全崇拜自然的变化,只有顺应自然的思想,将《淮南子》放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以考察这种无为与有为调和论之因。荀子批评庄子:“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由天谓之,道尽因矣。由法谓之,道尽数矣。”荀子是极力主张人治而“不求知天”的,人是可以征服自然的,是可以促进自然变迁的。荀卿门下出了韩非、李斯,也充分容纳时代变迁的观念,同时又极力主张用人功变更法制以应付时变。《淮南子》因袭《吕氏春秋》,两书都显出荀卿、韩非的影响,由此胡适得出结论:《淮南子》“尽管高谈无为,而都不能不顾到这种人为主义与变法哲学。但从无为跳到积极有为的变法,这是很不可能的事,故不能不有一种调和的说法,故说不为物先,又不为物后;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逮。变是要变的,但不可不先看看时机是否成熟。”[3]139
胡适从进化论出发,他考察出《淮南子》的《原道训》虽然有适应环境的思想,但“不易自然”,“不以人易天”则是极端的自然主义。而在《修务训》《泛论训》中,那种自动的适应环境所表现出来的积极的人生观就比较明显了。《修务训》认为:各种生物都有“见而就,避害而去”的天性,“各有其自然之势,无禀受于外,故力竭功沮”。自然之势是本能,禀受于外是外境影响某种生物而起的变化,即是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不能如此适应,便力竭功沮。生物用其本能,随着外境而引起自身机能上或生活状态上的变化,便是“以所知求合于其所利”。胡适将《修务训》里的自动的适应环境的见解,称之为“健全的,可以应用到人类进化的历史上,可以得一种很有现代性的进化论”。同时,他还对《泛论训》的有关自动的适应环境的话,加以称道。比如:“古者民泽处复穴,冬日则不胜霜雪雾露,夏日则不胜暑热蚊虻。圣人乃作为之筑土构木,以为室屋,上栋下宇,以蔽风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故民迫其难则求其便,困其患则造其备,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胡适称这种自动的适应环境,“便成了一种积极有为的变法论,所以说‘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这便不是《原道训》所说‘不易自然’‘因物之所以为’所能包括的了。《原道训》是从庄周、慎到一系的思想出来的,故说的是一个‘因’字。《修务》、《泛论》诸篇却受了荀卿、韩非的影响很大,故发挥‘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3]144
胡适对《淮南子》思想研究的第三大贡献,是将该著的政治思想作了深入开掘。政治思想是《淮南子》本身固有的,胡适的开掘是他的学术思想的独特发明。谈论《淮南子》的政治思想,你也可能用“无为”来概括之,但“无为”有哪些精义呢?胡适认为:“此书的政治思想有三个要义:一是虚君的法治,一是充分的用众智众力,一是变法而不知故常。”[3]148胡适发现《淮南子》政治思想的三大要义,他以《主术训》为个案,详细论证了虚君的政治的意义。从《主术训》中可以看出:虚君的政治,君主不但不轻于为暴,并且要不轻于施恩惠。“是故明主之治,国有诛者而主无怨(原作怒)焉,朝有赏者而君无与焉。诛者不怨君,罪之所当也。赏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依照客观的法制行事,诛赏予夺皆依客观的标准,皆不从君心出,“莫从已出”,这才能出现“诛者不怨君,而赏者不德上”。胡适也称道《淮南子》变法而不知故常的政治思想,《泛论训》、《修务训》、《齐俗训》中都有主张变法的议论,④强调“与时推移,应物变化”,而这个变化要靠人的努力,同时变法应反对崇古的迷信。
胡适发掘《淮南子》政治思想的三大要义,最注重的是“充分的用众智众力”,他说“众智众力”的政治,“颇含有民治的意味”,于是以《主术训》为个案,对《淮南子》的民治主义精神作了精辟论述。胡适论《淮南子》“民治主义”有四大特色,即发见其“民治主义”四大基本要义:一是将《淮南子》与《吕氏春秋》作比较,《吕氏春秋》不主张民主政治,而到了《淮南子》时期,封建社会已完全崩溃了,故此书对群众的知识能力,比较有进一步认识,所以书中屡屡指出“积力之所举无不胜也,而众智之所为无不成也”,胡适说“这便是民治主义的基本理论”。胡适发现民治主义的第二个基本要义即是“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贤主用人“无大小修短,各得其所宜,规矩方圆各有所施。”民治主义的第三个基本要义,即是尊重人民的舆论,《主术训》说:“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智虑,以天下之力争。是故号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闻。……聪明光万里不弊,法令察而不苛,耳目达而不暗。善否之情日陈于前而无所逆。是故贤者尽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民治主义第四个基本要义是承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对等的,只有相互的报施,而没有绝对服从的义务。[3]154胡适发掘《淮南子》无为主义政治,民治主义思想之要义,并在30年代出版此书,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1932年3月29日,蒋介石和胡适、陈布雷、陈立夫、顾孟馀等人晚餐,胡适送了一本《淮南王书》,此书不一定适合蒋介石的胃口,蒋介石喜读韩非子、墨子以及儒家经典,《四书》中的《大学》、《中庸》等。胡适于1935年7月26日致罗隆基的信中,谈了他送蒋介石《淮南子》书的意图:说据他观察,蒋管的事太多,“微嫌近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送蒋《淮南王书》“意在请他稍稍留意《淮南》书中的无为主义的精义”,“我的意思是希望他明白为政之大体,明定权限,而不‘侵官’,不越权。如此而已”[4]。对30年代的蒋介石的独裁专制,胡适想用《淮南子》中的无为主义的政治,民治主义的要义去“劝君”,这种温和的改良主义的做法,实际上于蒋介石是无济于事的。但从学术研究与现实联系方面看,胡适的研究还不是完全钻进“故纸堆”里,而是以古鉴今、为今所用的。
胡适《淮南子》思想研究的第四大贡献是他对《淮南子》“出世”思想的精深探研。胡适认为:《淮南子》受神仙出世之说和阴阳禨祥之说的影响很大。淮南王最提倡道术,其《内书》叫做《鸿烈》,而《中篇》叫做《鸿宝》,《鸿宝》之书多说神仙黄白变化的方术,而《鸿烈》之书虽包罗天文、地形以及齐俗治国之道,但主旨所在实是神仙出世的理论。他以《原道训》、《精神训》等篇作为材料,以考察其神仙出世的思想。《原道训》说:“大丈夫恬然无思,淡然载虑;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御,乘云陵霄,与造化者俱。”得道者“心而不朗,久而不渝;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以康为乐,不以慊为悲,不以贵为安,不以贱为危。形神气志各居其宜,以随天地之所为”。《精神训》说:“所谓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无,实而若虚;处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而不知其外。明白太素,无为复璞,体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芒然仿佯于尘垢之外,而消摇于无事之业。”如此等等,胡适说这些都是出世的人生观的理想境界。[3]163“入火不焦,入水不濡”,“出入无间,役使鬼神”,这是承认真人可以有超自然的神力,并且能役使鬼神,这就是神仙的理想境界。对《原道训》、《精神训》所说的“恬然无思,淡然无虑”,“不学而知,不为而成”,“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忘其五藏,损其形骸”,“存而若亡,生而若死”等,则是一种暮气的哲学,胡适称这种哲学为“精神哲学”。“精神哲学”主旨有二:在天地万物之中,则贱物而贵身;在一身之中,则贱形而贵神。凡恶动主静之学,厌世无生之论,都归于这两点。胡适还进一步将这种“精神哲学”与《吕氏春秋》作比较,认为:《淮南子》所说的“贱物而贵身”的理想,已不是百年前《吕氏春秋》中的贵生重已了。《吕氏春秋》的“贵生”“尊生”“全生”,只是要人“六欲各得其宜”,“虽贵富,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故不欲不能全得其宜,便是“亏生”;六欲莫得其宜,而反得其所甚恶,便是“迫生”,迫生便不如死。胡适说这还是近人情的人生观。《淮南子》的“贵身”却是教人排除“嗜欲好憎”,教人“无所喜而无所怒,无所乐而无所苦”,“能至于无乐者,则无不乐”。这样看来,他们所谓的“贵身”实则“贱身”,因为他们所贵的不是身体的全体,只是他们所认为精神的部分;精神以外的部分是不重要的。[3]166胡适这里强调了《淮南子》重视“精神”的力量,是难能可贵的。
以上论述了胡适对《淮南子》思想研究的开创性贡献,其实胡适的贡献不单在于对《淮南子》本体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对《淮南子》思想的研究,给后世治学提供了诸多值得借鉴的思想和方法。前文已提及胡适一生最“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他自述自己的思想主要受赫胥利和杜威的影响。前者的“怀疑主义”以及“拿证据来”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进行全面的审视与批判,后者的五步法:(一)疑难的境地;(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三)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一一想出来,看那一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5]使他提出著名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对《淮南子》以道家为主体的“大混合折衷”的思想作了多方面的思想“求证”,“求证”的内容即是本文所概括的他对《淮南子》思想研究的四大贡献。“求证”的方法既有历史的进化的眼光,将《淮南子》放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的长河中,考察它的独特的思想蕴涵和价值取向;又有比较分析的方法,尤其与《吕氏春秋》作比较,以显示其既受《吕氏春秋》影响又在其影响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尤其是具有“历史考据癖”的胡适,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包括对《淮南子》“道”的内涵、无为主义等思想所作的求证考据,均留有“汉学”遗风。蔡元培在为《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作序时就指出他“禀有治‘汉学’的遗传性”。[6]可见,胡适在作《中国哲学史》研究(包括对《淮南子》的研究)时,就能够将他从杜威那里学来的思维方法与清代考据学作了较好的“嫁接”,而且这种中西思想方法的“嫁接”,越朝后来越加成熟,成为他终身治学的理论武器。
注释:
①《中国古代哲学史》,是胡适在《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讲义稿)的基础上写成的,完稿于1918年9月,1919年2月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至1930年共印行了15次,同年收入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时,经胡适提议,书名改为《中国古代哲学史》。
②冯友兰认为《淮南子》“杂取各家,无中心思想”(《中国哲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侯外庐视《淮南子》为“杂家之言”的书(《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范文澜认为它不是一家之言,但不否认其道家的性质。李泽厚是从儒家说的。(可参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秦汉思想简议》,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③以上为胡适所引,见胡适:《淮南王书》,《胡适全集》第6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
④胡适论《淮南子》的政治思想关于虚君的法治和变法而不知故常的思想,可参见《胡适全集》第6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页、1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