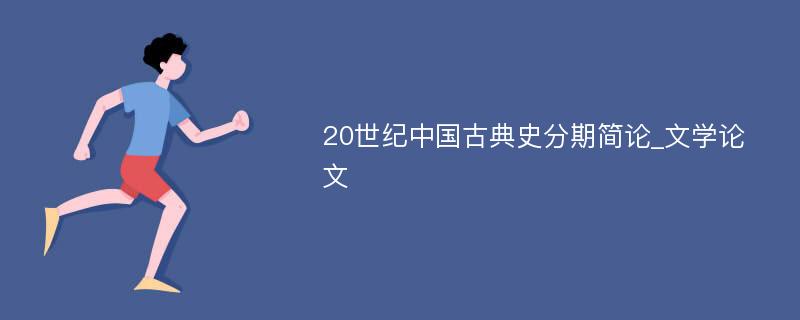
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史分期疏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二十世纪论文,中国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本文疏议的对象是20世纪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史著作文本,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史与中国近代文学史。史家治史为了集中和研究之方便,始断代为“古代”、“近代”和“现代”,它标属着中国文学的三个阶段,也是三个范畴。“古代”是一个悠久而漫长的历史阶段,从中国文学的发生至封建制社会的结束,庶几占去了中国文学史十分之九的篇页,故中国古代文学史习惯上也名之为“中国文学史”。近代文学是“古代”与“现代”之间过渡阶段的文学,与现代文学相比,仍属旧式文学,因而习惯上又统称古代文学和近代文学为“古典文学”。文学上的三种时态及其表现形态,构成了中国文学史宏观上的三期分。并逐渐形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三个分支学科。由于治史者的识见不同,使得中国文学史著作文本式样驳杂,近一个世纪以来付梓刊布者以百千种计,尤其30年代盛极一时。编作文学史大抵都有个体例问题,所谓体例,即“事之大体及内容细则也”,也即是事先规定的格局及文辞的体裁。这体例中就包含有“分期”一项。“分期”的得失影响着文学史著的根本面貌,也是文学史著达到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因而对其进行考察并确立科学的分期标准,是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课题。
二、中国古代的史书,大抵是记载政治、经济、战争乃至学术的活动及变迁的。于文学艺术,有“艺文志”的类项,是杂述,包含在所谓“正史”者中,只能称得上是“文学史”的胚胎。中国文学史的编作,据史料称,第一本乃属翟理斯(A·Giles)的英文本《中国文学史》,是1901年问世的;中国人自著《中国文学史》始于1904年出版的林传甲的文本。也即是说,“文学史”真正成为“历史”的一个“专支”,是本世纪初叶之事。20年代之后,治文学史者泱泱辈出,竞相撰述。为检视这一时期文学史著的状况,举例如次:1.刘师培著《中古文学史》,1920年初版,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印行。全书分“概论”、“文学辨体”、“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魏晋文学之变迁”、“宋齐梁陈文学概论”五章讲述,侧重于汉魏和魏晋的介绍。2.徐嘉瑞著《中古文学概论》,1924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全书分“绪论”、“平民文学”、“舞曲”、“贵族文学”、“唐代平民化之文学”五编,凡十八章。叙述以平民文学为主。虽以“中古文学”名之,实际上所谓平民文学,多指曲舞而言,近似于音乐文学史。3.朱炳熙著《唐代文学概论》,1929年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印行。全书分唐代文学发达的原因、特点、派别、对后世的影响、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以及唐文、诗、词、小说等九章,后附录唐代艺术。4.陈子展著《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年中华书局印行。全书九章,自近代文学从何时说起,至十年来的文学革命运动。中经诗界革命、宋诗运动、词曲价值、小说界革命、桐城派古文,以及从时务文学到政论文学、翻译文学各个阶段。此书是编作近代文学史之始,1930年作者续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由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增加了敦煌俗文学和民间文艺的内容。5.张宗祥著《清代文学》,1930年商务印书馆印行。内容简略,约3万余字,自清初至宣统,按朝概述,后为诗词,附戏曲。6.陈钟凡著《汉魏六朝文学》,1931年商务版。全书分两汉、建安、魏晋及南、北朝五章叙述,首为绪论。约5万余字。7.沈达材著《建安文学概论》,1932年北平朴社出版。全书分建安文学与东汉诗人、与时代背景、与乐府、趋势及其影响、中心人物、三曹、七子等十章叙述,首为引言。8.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1933年世界书局出版。全书分上下二编,上编为古文学,分文、诗、词、曲四类;下编为新文学,分新民体、逻辑文和白话文三类,均以作家为主。此书长于史实,体例芜杂,首开“现代中国文学史”之名。9.柯敦伯著《宋文学史》,1934年商务版。全书分宋代散文、四六文、诗词、戏曲、小说、诸家小传等八章述之。是一种文体辑合的著作。10.苏雪林著《辽金元文学》,1934年商务版。全书分辽之文学、金之作家、元曲之种类、北曲、南曲作家与作品、元人小说等七章概述,约2万余字。11.宋佩韦著《明文学史》,1934年商务版。全书自明初散文作家起,下为永乐以后的台阁体及其以外的诗人,弘治、正德间的文学,嘉靖、万历间的文学,明末文学和明之八股文,凡六章。由上述可见,这时期的文学史著一般说来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个人撰述,百家争鸣;二是体例不完备,大多是“述而不作”,写史而无“史”,仅作阶段性文学的面面观,或各种文体的辑合介绍;三是范围芜杂,对纳入文学史的精神产品未能作清醒的类别判断,以致枝蔓横生;四是多以作家为主,以人带史;五是议论多于记叙,史笔不足,鉴赏有余;六是规模小,系统性弱,两三万字至七八万字即成篇;七是虽有1933年王哲甫编著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出现,然尚未能构成清晰而明确的中国文学史整体性的“古代”、“近代”、“现代”三期分。迨至40年代,编作文学史相对沉寂,即使也出版了一批文学史著,如陈子展《唐宋文学史》(1947年作家书屋印行)、钱基博《中国元代文学史》(1943年新中国书局印行)等,无论在体例与笔法上均保留着二三十年代的痕迹。
三、首先比较严密的使用分期体制的是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郑氏在30年代有两部文学史著问世,一部是《中国俗文学史》(1938年商务版,1954年作家出版社重印),主述民间文学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另一部就是《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年商务版,1957年作家出版社再版发行。因其插图174帧,多为珍藉,故名。 郑氏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和藏书家,他的史著与同类相比堪称“白眉”,不仅第一次建立了中国文学史系统性的体系,而且识见不同凡响。郑氏认为,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文学史,应足以指示读者去认识“中国文学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和整个真实的面目”,而“这二三十年间所刊布的不下数十部的中国文学史,几乎没有几部不是肢体残废,或患着贫血症的”(《自序》)。这便是他著文学史的出发点。郑氏认为,作家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因而作家不是孤立的存在,文学史的任务“便不仅仅成为一般大作家的传记的集合体,也不仅仅是对于许多‘文艺作品’的评判的集合体”,而是“将这个人类最崇高的创造物文学在某一个环境、时代、人种之下的一切变异与进展表示出来”。郑氏强调的不是单一的作家和作品,而是在“环境、时代、人种”三种条件下的文学的“一切变异与进展”,因而他反对将文学史处理成“对于作家的与作品的鉴赏的或批判的‘文学批评’之联合”和“以‘时代’的天然次序‘整齐划一’”(《绪论》)。郑氏的这种文学史观明显地受19世纪法国文艺理论家泰纳的文学发展决定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因素的影响。泰纳认为,文学创造“全由这三个原始力量所产生和控制。”这是一种艺术社会学的批评理论,郑氏把它拿来作为编作文学史的立论依据。
郑振铎根据他的如是文学史观把中国文学史划分为古代、中世、近代三个大时期。郑氏认为,古代期的文学有两个特点:其一,纯然为未受有外来的影响的本土的文学;其二,纯然为诗和散文的时代。西晋以前大约两千年左右的文学历史属此范围。中世期的文学特点表现在这个时期是中国文学和印度文学“结婚”的时代,除诗歌和散文之外,又产生出许多新文体,像变文、诸宫调等等,在思想和题材方面均受到印度佛教文学的熏染,兼之民间文学的影响,使这一时期呈现出少有的辉煌。晋的南渡至明正德年间大约1200余年的文学历史属此范围。近代期则是活的文学与死的文学杂陈的时代,既有本土的伟大的创作,在最后的半个世纪又受到欧洲文化浮面的影响,但不曾产生过什么重要的反应。它是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过渡期,预示着几千年来的旧式文学即将闭幕和收场。明世宗嘉靖元年至五四运动前大约380 余年的文学历史属此范围。
郑振铎以本土文学——“结婚”文学——过渡文学的转轨描述中国古典文学整个的发展过程,并以此包容中国历史上更迭的朝代文学的兴衰。郑氏以文学运动、文体、文学流派的兴衰起落为主线,又把三个时期划分11个段落。古代期作四段分:1.从殷商到春秋时代,这是一个原始的时代;2.战国时代,这是散文最发展的时代;3.从秦的统一到东汉末叶,这是一个辞赋的时代;4.从汉建安到西晋之末,这是一个五言诗的时代。中世期作三段分:1.从晋的南渡到唐开元以前,这仍是一个诗和散文的时代,但已深印上佛教的影响;2.从唐开元、天宝到北宋末叶,变文、词、传奇文崭露头角;3.从南宋初到明正德末,散曲、词话(短篇小说)、讲史(长篇历史小说)、诸宫调乃至戏剧这一重要文体出现。近代期作四段分:1.从嘉靖元年到万历二十年(公元1522年—1592年),这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和戏曲的时代; 2.从万历廿一年到清雍正之末(1593年—1735年),这是小说和戏曲繁荣发展的时代;3.从乾隆元年到道光廿一年(1736年—1842年),戏曲气势渐衰,流派纷呈,这是一个转折的时代;4.从道光廿二年到民国七年(1843年—1918年),翻译文学的进入,新诗的试验,“新闻文学”的崛起,武侠与黑幕小说的流行,文学正孕育着一场大的变动。
郑振铎采用的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分期体制。宏观侧重于文风文气的流脉,民族文化的气韵,政治社会的变迁;微观则侧重于“一个文学运动,一种文体,或一个文学流派的兴衰起落”。这就创制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明晰、流畅的格调和以文学为主旋律的时空视界。
四、50年代伊始,为了建设文学史学科新教材,高校文科开始组织力量,至50年代中期,一批集体编著的文学史相继出版。诸如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1959年中华书局版),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小组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1960年吉林人民出版社版)等,都是比较引人注目的版本。这些文本的共同倾向及特点是视革命性为历史科学唯一的检验标准,从此时起服从于直接的政治需要已露端倪。只强调作家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和世界观,忽视作品的实际情况与客观效果;只讲或多讲作品的思想内容,不谈或少谈作品的艺术成就;认为革命性就是现实阶级斗争中的阶级性和政治倾向性,也就是为当前政治斗争的某一具体政治目的、某项具体政策服务。出于这样的理解,文学史的分期与阶级斗争史的分期也就合二而一了。这种分期的标准与方法对后来产生了长久不衰的影响。这时期,专家治史已退居后位,只有零星的旧著“修订本”再版印行,陆侃如、冯沅君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简编》(1957年作家出版社版)和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版)是比较通行的两种。陆冯著文本虽然简略,但是比较早地把近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史中独立的一部分来编写的史著,把近代文学列为古典文学史的六大段之一。在分期问题上这种新的处理方法,对后来文学史的编写有所启示。刘著文本从殷商社会与巫术文学写起,至清末止。以社会变革起落与作家作品、文体兴衰两线交织贯串之,不分期。全书共31章,往往以章构成一个文学现象的发展段落,如第二章周诗的发展趋势及其艺术特征,第六章汉赋的发展及其流变,第九章魏晋时代的文学思潮,第十章从曹植到陶渊明,等。
五、60年代以后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文本,基本上是50年代集体编著文学史编作方法的继续,更加明显的是引进“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批评标准入史,又逐渐地绝对化为“政治唯一”的标准,这就使得中国文学史弥漫着一层主观色彩和政治色彩,文学本身的特征和客观性相对减弱了。这时期的“文学史”主要任务是以今人的政治标准给古代作家和作品以较为恰当的评价,其次是以阶级斗争观点介绍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文研所本”)和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游国恩等主编本”),是颇具权威性的被推重的两种版本。
“文研所本”,1962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 从上古写到鸦片战争(1840年)止。三卷本。本书以社会形态为标准把中国古代文学划分为两个时期:封建社会以前文学(即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文学)和封建社会文学。“封建社会以前文学”仅以三章概述,仿佛绪论。从面貌上看这部史著不啻一部“封建社会文学史”。它基本上以朝代为起止界限划分为八个阶段:战国时代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代文学、宋代文学、元代文学、明代文学和清代文学。每个朝代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侧重介绍政治斗争、作家作品和文体变异之态,如“战国时代文学”介绍《左传》、《战国策》、《论语》、《孟子》、屈原和宋玉。“秦汉文学”介绍贾谊、枚乘、司马相如、司马迁及《史记》、刘向、扬雄、班固、张衡、蔡邕、赵壹、汉乐府民歌与《孔雀东南飞》以及五言诗。“魏晋南北朝文学”介绍三曹、王粲、刘桢、蔡琰、嵇康、阮籍、陆机、左思、刘琨、郭璞、陶渊明、谢灵运、颜延之、鲍照、谢朓、沈约、江淹、何逊、庾信,佛经翻译、南北朝乐府民歌、《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志怪小说、轶事小说,以及刘勰与《文心雕龙》、钟嵘与《诗品》、萧统与《文选》。从章节细目上看,均是作家分类排比,像“镜框”似的给人以平面的、凝滞的印象,中国文学的整个走势及气韵被这一个个“镜框”阻隔以至于淹没。
“游国恩等主编本”是1963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的,1992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发行。四卷本。这本史著从上古写到“五四”前夜(1918年)止。在分期上承继了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的体例,作九段分:上古至秦统一的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代文学、元代文学、明代文学、清初至清中叶的文学、近代文学——晚清至“五四”的文学。本书与“文研所本”相比较,除将“封建社会以前文学”和“战国时代文学”合并为“上古至秦统一的文学”,增加“近代文学”一段之外,其余基本上是一致的,甚至章节细目也如出一笔。如“上古至秦统一的文学”介绍文学艺术的起源,古代神话,《诗经》(此为“文研所本”之“封建社会以前文学”的内容)、《左传》、《国语》、《战国策》、《论语》、《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屈原与宋玉。“秦汉文学”介绍贾谊、枚乘、司马相如、司马迁及《史记》、班固、王充、张衡、汉乐府民歌与《孔雀东南飞》以及五言诗。“魏晋南北朝文学”介绍三曹、建安七子与蔡琰、阮籍、嵇康、傅玄、张华、陆机、潘岳、张协、左思、刘琨、郭璞、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南北朝乐府民歌、南北朝骈文和散文,志怪小说、轶事小说,曹丕及《典论论文》、陆机及《文赋》、刘勰及《文心雕龙》、钟嵘及《诗品》、萧统及《文选》。编写者在书前“说明”云:“除末编按社会形态划分外,其余则基本以主要封建王朝作为分期的标志。”因而它的主干部分依然是封建制社会“朝代文学”的联缀,但它注意到了各种文学形式的发展、相互影响以及它们的源流演变,同时也注意到了文学思潮的流变,这恰是“文研所本”薄弱之处。本书之所以如此分期,乃在于编写者认为,“在我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发展中,封建王朝的更替,往往是长期阶级斗争的自然段落,它或多或少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带来了若干新的特点,它也对文学的发展起制约作用,影响着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说明”)。这种认识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封建王朝的更替”的确“往往是长期阶级斗争的自然段落”,但它的“制约”和“影响”只能是外部环境与条件,这是一个方面;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往往又超越这种“制约”和“影响”,正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样,经济基础“决定”的是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而一旦旧的经济基础发生变革,曾与之相适应的部分上层建筑(如文学艺术等)不会立即随之消解,相反却会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延续,从而形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是另一个方面。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与阐术历史时,是“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对文学历史的分析阐述同分析阐述历史一样,也应把文学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
六、由上面检视可以看出,90年代以前中国古代文学史或称古典文学史的分期,大体有三种类型,反映出三种文学史著的“眼光”和编作方法。第一种类型,承认文学历史与社会历史有不同的发展轨迹,文学的演变史是文学本身的逻辑发展过程,它既非封闭的自生物,也不可能与社会历史完全相融而失去相对独立性,文学在时空中的发展规律既受社会变动的影响,又保持本身的相对独立性,因而文学的发展阶段不可能与朝代更替“整齐划一”。这是一种文学家的“眼光”,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属之。第二种类型,视阶级斗争规律支配文学发展规律。文学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因而阶级斗争史也即文学发展史。朝代的更替是阶级斗争规律的集中表现,于是朝代的更迭史就成为文学的发展史。因而文学的发展阶段可以和朝代的更替“整齐划一”。这是一种政治家的“眼光”,“文研所本”《中国文学史》属之。第三种类型,把文学的演变史看作是文学服务于社会历史的过程,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使用和发展的,文学的特征便是被使用的表现。承认文学既不是封闭的,也不是相对独立的,而是由“作用”的发展反映现实的发展和文学题材、内容、形式、语言乃至风格特征的变化。这是一种工具论的“眼光”,“游国恩等主编本”《中国文学史》属之。
应当指出的是,“文学的历史”与“历史的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主述文学变迁的历史,“文学”是主题,“历史”则是它的载体。也即是说,特定的历史阶段孕育了特定的文学现象并赋予它生命和灵气;脱离历史载体单一强调文学自身,将无以解释文学现象。但是“载体”并非“主题”。盖因文学是用语言手段构成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并表达作家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文学具有时代的、民族的特征,反映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民族的社会意识和生活风习,在这方面,文学和历史阶段是相契合的;但在另一方面,它又是作家思想感情的一种表现,是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而发展的。这就是“载体”与“主题”的逻辑辩证关系。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便是采用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来为中国文学史分期的。他以“时代”观察文学的生命力度和反映力度;以“环境”观察文学的适应性和起落消长;以“民族”观察文学的文化传统和本质特征。然后,拿这种“尺子”衡量文学的阶段性的特点及其进展,遂形成文学的分期。“历史的文学”乃主述历史上的文学现状,历史是主题,文学则是它的副题。也即是说,特定的历史阶段文学现象尽管是不同的,但文学仅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阶段已经过去,此阶段的文学也相应地结束。文学自身的连续性是附随于历史的阶段性的,它构成的是历史阶段的一个个静止的“平面”。“文研所本”和“游国恩等主编本”即是采用这种“平面”思维方式来为中国文学史分期的。
七、其实,60年代初,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已被提出研究。彼时有人从文学的流脉走势把夏到“五四”前夕的文学划分为四段,其标志是文学形式和内容的变革。持论者认为,文学起于民间,和音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最初的表现形式是源于民间的祭祀与舞蹈,然后才发展到庙堂里去。《诗经》是中国文学正式记载的开端,确立了被称为“文学”的文体,因此,《诗经》堪称为中国文学的第一次变革。第二次变革是汉乐府。它起自民间,而以“相和歌”为基础,句式为3∶3∶5或3∶3∶7,可以说是《诗经》以后的新国风。汉代的乐府发展到“古诗十九首”,已和音乐脱节,变成文人笔下的东西,由此下接建安。辞赋衰微,五言诗滋生繁长。待到南朝偏安,齐梁以后,“子夜吴声歌曲”和“襄阳西曲”兴起,给予了五言诗一种新生命。“子夜歌”每章四句,每句五字,合若干章成为一篇。这种歌曲的字法组织和汉乐府汉魏两晋的五言诗,都有不同。“子夜吴声歌曲”是情歌,可以入乐,给予凝滞的五言诗以新的生机。这种新路子发展下去,形成初唐四杰的五言诗,并逐步由五言排律(12句,10句)定制五言律诗(8句), 完成了诗的形式和格律。“襄阳西曲”每首多半七言二句,演变到初唐,形成七言古诗。东汉末,辞赋和散文是两种不同的文体,至建安时代发生新的变化,把《诗经》的四言句法,运用到散文里边,又把辞赋的四六句法运用到散文里,于是逐步形成骈文。第三次变革是唐代,这便是西域音乐由北朝时的传入到开元天宝的大盛,由龟兹乐的刺激而产生了唐代的大曲,再由大曲演变成为诸宫调,这就是后来元明杂剧传奇的音乐成分。同时,词中的小令也产生在唐代,并慢慢地演变成宋代的“慢词”。因此可以说,词曲的发源是在唐代。由于佛教与道教的影响,六朝时出现志怪小说,到了唐代,演变成传奇文。志怪小说多言神鬼,传奇文学多言人事。另外,展示唐代文学新面貌的是“变文”的诞生,又称“俗讲”,它原是佛教传入中国后,讲佛经的故事而编成的诗文合体的通俗文学。因为僧寺俗讲多半在故事前面绘上图像,边说边唱,从而成为绣象全图小说的来源。第四次变革是民间小说的兴起。民间小说和戏曲,构成宋、元、明、清四代文学的主流。这时期文学的趋势有两方面:一是说故事,从“大宋宣和遗事”起,演变成以后的章回小说,这是一个系统;一是演故事,从唐代的“参军戏”起,演变成以后的杂剧传奇,这是又一个系统。
但是,上述的这种看法未被引入文学史研究,反而被“文研所本”和“游国恩等主编本”等所覆盖,仅以理论的形式传递了信息。
90年代以后,“致力于文学史研究新模式的建立”的呼声日渐高涨,“探讨如何更新文学史研究的路径”,以及“对于文学史复杂的巨系统运动的认识”。其要点有二:一是意在达到使动和受动的统一,文学史应是既具有自身的动势又受到多种因素复杂影响的运动,而以往的研究方法(即使是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都仅是一种受动论;二是欲在浑沦的勃动中,从多元因素的整合中,把握无序的文学史运动通过其中介和动力结构而凝定的曲折过程,从而使文学研究从小圈子中走出来。
八、在此理论探讨的氛围中,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1996年3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初版印行。 编著者在《导论》中首先指出,“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任务,是清理并描述中国文学演变的过程,探讨其发展规律”。继而对“文学是以语言为工具的,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的定义进行了论辩。编著者认为,“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与深度并不是决定一篇作品高下的主要尺度”,文学定义中的“形象”如是指感性形象,系与‘抽象’相对而言,这样的‘形象’自为文学所必具,但那只是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标准”,也不能作为判定文学作品高下之分的依据。编著者认为,“文学作品是一种以情动人的东西,它通过打动读者的感情,而使读者获得某种精神上的愉悦”。继之,编著者引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一句话:“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作为这部文学史理论的支撑点,于是就形成了这部史著的理论框架与描述的方位:“文学发展过程实在是与人性发展的过程同步的。”基于如是的认识,编著者从没有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到个人的权利、自由、欲望、尊严等慢慢地得到尊重,描述了一条“其速度有时较快,有时较慢,有时甚或出现曲折、倒退,而其最终结果仍是向前进展”的线索;中国文学内容与形式的演进便与这人性的发展紧密地关联着。编著者立论说:“一部文学史所应该显示的,乃是文学的简明而具体的历程:它是在怎样地朝人性指引的方向前进,有过怎样的曲折,在各个发展阶段之间通过怎样的扬弃而衔接起来并使文学越来越走向丰富和深入,在艺术上怎样创新和更迭,怎样从其他民族的文艺乃至文化的其他领域吸取养料,在不同地区的文学之间有何异同并怎样互相影响,等等。”
这部文学史立论新颖、眼光独特,但在体例上与旧本文学史差别不大。全本分八编:第一编先秦文学,第二编秦汉文学,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第四编隋唐五代文学,第五编宋代文学,第六编元代文学,第七编明代文学,第八编清代文学。这八段分仍是“镜框”式的,基本上还是朝代文学的辑合。再看其章节细目,第一编设四章:第一章《诗经》,第二章历史散文,第三章诸子散文,第四章屈原与楚辞。第二编,设五章:第一章西汉前期至中期的诗赋与散文,第二章司马迁和《史记》,第三章汉代乐府民歌,第四章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的诗赋与散文,第五章东汉中期至后期的诗赋与散文。第三编,设五章:第一章魏晋诗文,第二章南朝诗文与民歌,第三章北朝诗文与民歌,第四章魏晋南北朝小说,第五章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第四编,设七章:第一章隋与初唐诗歌,第二章盛唐诗歌与李白,第三章杜甫与中唐诗歌,第四章古文运动,第五章唐代的小说与讲唱文学,第六章晚唐诗文,第七章唐五代词。第五编,设七章:第一章北宋初期文学,第二章北宋中期的文学变革与苏轼,第三章北宋后期文学,第四章南宋初期文学,第五章南宋中期文学,第六章南宋后期文学,第七章辽金文学的发展。第六编,设七章:第一章关汉卿与元代前期杂剧,第二章元后期杂剧,第三章元代散曲,第四章元代诗文,第五章元代南戏,第六章宋元的中短篇小说,第七章《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第七编,设八章:第一章明代前期文学,第二章明代中期诗文,第三章明中期戏剧与《西游记》等小说,第四章明代后期诗文,第五章《金瓶梅词话》与明后期长篇小说,第六章明代后期短篇小说,第七章汤显祖与明后期戏剧,第八章明代散曲与民歌。第八编,设八章:第一章清代前期的诗词文,第二章清代前期小说,第三章清代前期至中期的戏剧,第四章清代中期的诗词文,第五章《儒林外史》、《红楼梦》及其他,第六章弹词、鼓词与民歌,第七章清代后期的诗词文,第八章清代后期小说。
每编前均有“概说”。共51章。这种体例与60年代版本文学史几无二致。虽有新的文学现象、文学史料、作家与作品引入,范围也扩大了一些,但依然是似曾相识。本书初版之际,上海《文学报》曾以《人性的发展与文学的历史》为题专版介绍。“编者按”中说,这本文学史“广泛吸收了国内外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并以作者独特的眼光,重新描述了中国文学史的流程”。应该肯定,编著者对有些文学现象及作品的分析确有独到之处,立论新颖,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超越了旧版本文学史;但仅以人性的发展推断文学的演进,且又把它放在朝代的“镜框”中加以描述,这就减弱了文学自身的走势,并游离出社会历史发展这个“载体”,强调“文学”而失去“历史”,使“重新描述了中国文学史的流程”这句话悬在了空中。
这本文学史没有使用“古代”与“近代”的概念,以“清代后期文学”替代了以往版本中的“近代文学”,完成了“古典文学史”的统一。但这一部分是相当薄弱的,仅以两章的篇幅简述了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这一过程中的重要历史阶段,因为编著者仅把它“作为古代文学最后一个阶段的诗文创作”来对待的,所以也就只能是蜻蜓点水式的一掠而过,留下几处光亮的斑点。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推倒了旧版本文学史的理论支点,辐射出一定的力度与广度,但尚未完成科学化的文学史体系,它仍是一部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的过渡之作。
九、有人称中国近代史从广义上说就是一部西学东渐史,因此中国近代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演变中皆有“西学东渐”的痕迹。也即是说,中国近代文学的演变与发展均渗有异质文化的促激素。可以说,中国近代文学是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叶中西文化碰撞和交融的“全息摄影”。中国近代文学是介于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变革与动荡异常复杂的文学现象。一极是异质文化促激本土文化的“变革”,一极是不同类型、不同角度地吸收所产生的不同的创造。这两极构成了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它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投影、文化质变的一大标志。近代文化思潮的流派纷争又极其复杂,形成近代文学的多维主题。因而理清处于新旧嬗替之际的80年间的近代文学,实不是轻松之事。因此,研治中国近代文学史就成为整体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50至60年代出版的几部中国文学史对近代部分的分期,大体可分为两段分、三段分、四段分三种。陆侃如、冯沅君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简编》把近代文学史部分作两段分,以戊戌变法为界,上段是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前后的文学;下段是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前后的文学。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编著的《中国文学史》把近代文学史部分作三段分:1840年—1894年,是第一段,为资产阶级文学的启蒙时期;1894年—1905年,是第二段,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学时期;1905年—1919年,是第三段,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时期。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集体编著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1960年中华书局版)则作四段分:1.1840年—1894年,2.1894年—1905年,3.1905年—1911年,4.1911年—1919年。“游国恩等主编本”《中国文学史》没有给近代文学史部分划分明显的发展阶段,而以六章叙述之:第一章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文学,第二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时期的诗文,第三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时期的小说,第四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学,第五章近代戏曲,第六章近代民间文学。由章目上看也是作三段分的。
由上述诸种版本可以看出,近代文学史唯革命运动高潮作为分期的标准,而且定型为资产阶级文学的形态。这里有两个问题是需要讨论的:第一,近代史分期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近代文学史的分期是否也是这条轨迹线。如若是,80年间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中文艺思潮、文学流派的兴衰以及作家创作的相对完整性对分期也就毫无影响了。事实是,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均相当激烈的时代,近代文学与近代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其他部门一样,也处于剧烈的变革时期。“文艺革命”的口号几乎贯串于整个近代时期。一方面倡维新,呼变法,促改良,兴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高潮迭起;另一方面“诗界革命”、“文化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风行弥漫。仅从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内容上来认识文学的价值是不够的,因为忽视文学发展的独特规律,就会把文学作品与一般的政治思想宣传物等同起来。第二,中国近代历史是复杂多变的,既有农民革命运动,也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民主革命运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异常激烈而且错综复杂,新旧思潮回环交错,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展示出不同阶段的特征,诸如鸦片战争的文学、太平天国时代的文学、中法战争的文学、甲午中日战争的文学、戊戌维新时期的文学、庚子事变的文学、辛亥革命文学等,用单一的资产阶级文学形态来覆盖近代文学史并以之作为分期的唯一标准似乎是绝对化了。
十、编作中国文学史已历经了近一个世纪。其轨迹线大体可分作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本世纪初叶至40年代末,堪可称为草创期,百家争鸣,各陈己见,为编写文学史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及教训。由于这时期学术思想驳杂,科学的文学史观尚未形成,因而这时期的文学史著在体例上均未能形成规范。第二阶段是由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这是一个统一与发展时期,文学史的规范基本形成,出版了一批文学史著作版本,但这一时期由于受极“左”思潮和极端“厚今薄古”、“古为今用”思潮的影响,在文学史的研究中反映出思维单一化和简单化的倾向,甚至有某种虚无主义的态度,这样就导致了原本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变得干瘪或偏枯,兼之实用主义成为圭臬,文学史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就相对减弱了。第三阶段是80年代以来,通过反思、探索和引进新的科学思想,使得原已形成的文学史若干规范(如体制、结构、分期、语言等)发生动摇,科学的文学史观正在形成。这是一个思辨与追求的时期。
文学史的分期仍是使研究者困惑的问题之一。焦点是分期的标准尚未能得到明确的认识。我以为应同时注意这样几点:
第一,历史分期的决定因素,是经济基础也即生产关系的改变,以及随着这种改变而出现的新的生产关系的确立。分期的主要作用在于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指出历史各阶段间的本质的差别。文学史的宏观分期亦然,其主要作用同历史分期一样,在于阐明文学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指出文学历史各阶段间的本质的差别;微观段分的作用则主要显示同一时期各阶段文学表现形态的差异和文学思潮的流变过程。
第二,文学的演进变化是受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的。同时,文学属文化范畴,是一种观念意识形态,除了经济的影响,政治的影响也是同时存在的,因而在考察文学的发展过程和分期时,经济的和政治的影响是两个重要的因素。
第三,应确认文学的演进变化有自身的客观规律。经济的、政治的影响只能是重要的因素,而不可能以客体取代主体,或主体附随客体。文学的发展是以一定的时间间隔为周期的周而复始的连续运动过程,而这一过程在某一瞬间的横断面就是文学在该瞬间的存在形态。这一横断面反映了特定时间(时期或阶段)文学所进行的变换。因其运动过程是连续性的,存在着自身的批判与继承的关系,因而有时表现出对“影响”的超越性。分期所显示的具体意义即是文学在连续运动过程中在某一瞬间的横断面,即特定时期文学所进行的内容与形式的变换。
第四,生产方式的演进产生了社会制度的演变。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的演进是一种历史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存在着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且演进过程中先后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之间并不存在截然清晰的界限。文学的存在与发展受生产方式的影响与制约,而这种影响与制约同样存在着“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并不存在“截然清晰的界限”。文学史的分期实际上是在考察文学周期的发展过程时的“映象”,即文学表现形态。文学运动与社会运动一样,文学的动态连续组合就是文学史。
十一、20世纪以来,人们多用单一的线性理论来解释文学现象和描述文学史。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各门学科中的非线性问题,正在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对社会现象可借助非线性理论从无序中找到有序,从现象中揭示出规律。非线性经济学即是用非线性理论来解释经济现象的。文学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开放的和许多文学过程是不可逆的这两个基本特征决定了文学系统非线性性质的客观存在。文学系统的非线性性质决定了文学系统除了线性性质所具有的平衡、发散等运动形式外,还会产生失稳、浑沌等复杂的运动模式。如果承认文学系统的非线性性质客观存在,就会极大地增强我们描述复杂文学现象的能力。因此,走出20世纪的局囿,建设科学的中国文学史刻不容缓。21世纪新版中国文学史已在地平线上露出希望之光。
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论文; 艺术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读书论文; 历史论文; 散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