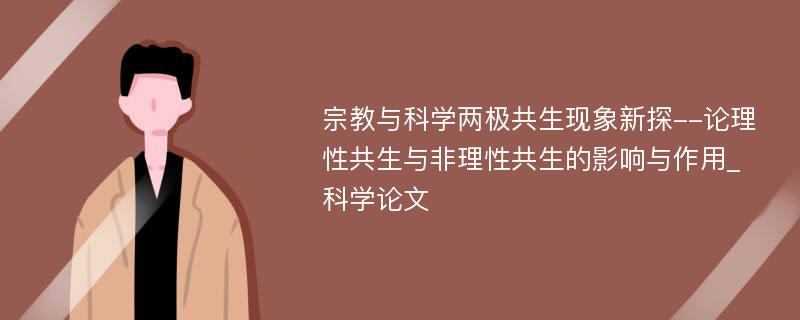
宗教和科学的两极共生现象之新探析——刍议理性和非理性共生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探析论文,两极论文,过程中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理性和非理性间的关系而言,与科学和宗教间的关系一样,本身是极其复杂的,还有着许多研究不透的东西,但无可非议,前者在后者这一对矛盾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笔者并没有将宗教和非理性及科学和理性简单地等同起来,仅是就其本质上的一些问题作了研究。为便于读者清楚地了解文章的脉络结构,本文拟从发生和发展学的角度加以系统阐述。
一、人类早期理性和非理性的浑沌统一是科学和宗教得以共生的深刻的历史根源
人类的理性与非理性是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整合结构。和人类的进化过程一样,它们之间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社会化过程。远古时代,人类的理性和非理性与现在的并不完全相同,那时它们仅仅是作为人与动物的连接点而存在,是从动物心理到人的心理的桥梁。人类精神和个体精神的最初发生,既不是纯粹理性的也不是纯粹非理性的,而是理性和非理性的浑沌统一。在这种理性和非理性的浑沌统一中,主体不能自觉地把自我和对象区分开来,只有主客两忘、主客交融的浑沌意识。此时,科学知识和宗教巫术是交相混杂的,很难严格地加以区分,这就为以后宗教和科学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培植了一块厚实的土壤。(注:参阅吴宁:《非理性发生的社会基础及其在社会历史活动中的作用》,《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6年第4期。)
在原始人那里,人类的理性和非理性是互相掺和、浸润在一起以萌芽的形式存在着的,他们打制的石器虽然十分简陋粗糙,但已经是事物的尺度和人自己内在尺度的实际统一,是人类理性(知识和技能)与非理性(欲望、意志、情感和幻想)的对象化。制造和使用工具是受一定的欲望和意愿支使的,这种欲望、意愿带有追求理想的性质,间接、曲折地反映了原始人肉体生命的需要。正是在一些原始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人们运用浑沌的思维和粗浅的技能制造和使用工具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满足了自己的需要。因而,工具是物化的知识力量,是人类理性的表现。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体现了人类理性的技巧。但是,在实践能力和理性能力依然十分低下的情况下,“人类差不多完全受着陌生的、对立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4页。)。原始人并不能全部实现其欲望、需要、意志和理想,在未知的不可抗拒的异己的自然力面前,他们常常流露出失望和焦虑的情绪,对之充满了恐惧、神秘的感情,并幻想通过运用一些方法和手段控制这些异己的自然力,由此而产生了最初的宗教情感和巫术活动,其中巫术活动表现得尤为突出。弗雷泽认为,“巫术和科学在认识世界的概念上,两者是相近的。二者都认定事件的演替是完全有规律的和肯定的。并且由于这些演变是由不变的规律所决定的,所以它们是可以准确地预见到和推算出来的。”“对那些深知事物的起因,并能接触到这部庞大复杂的宇宙机器运转奥秘的发条的人来说,巫术与科学这二者似乎都为他开辟了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前景。于是,巫术同科学一样都在人们的头脑中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强有力地刺激着对于知识的追求。”(注:弗雷泽:《金枝》,第76页。)在弗雷泽看来,巫术象科学一样具有知识的品格,决不是巫师和人们的胡思乱想,他甚至认为巫术能够推动知识的进步。
一些人类学家认为,上古时期的巫术从“交感”巫术开始。原始的巫术观念认为,同类事物可以感应相生。正是在这种想法支配下,人们不惜耗费大量体能去模仿一些自然过程,以企望现实的自然界按照人的意愿发生变化。譬如原始人发现蛙鸣则雨这一现象,于是天旱时,原始人就扮作青蛙鸣叫,希望求得雨水。对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而言,原始人类的这一举动纯是愚昧迷信,然而,就在这种巫术观念中也含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即自然界的运动是有规则的,人可以通过适当的形式去控制和利用自然,这显然已孕育了科学的胚胎。在上古的一些宗教活动中,如占星术、炼金术、用香料和药料保存尸体等等,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科学知识,为以后天文学、化学、药物学、解剖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讲,宗教就是最原始的科学。
从认识论的根源上看,宗教和科学的产生,都起源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观察和认识。宗教最初的出发点,也是想回答人们对自然界一些迷惑不解的问题。而且,科学和宗教对宇宙、生命和人类的起源是上帝创造的还是物质运动的产物?物质世界的运动是按其自身的规律发展,还是受神的支配?人的精神是与肉体共存,还是可以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既是宗教要回答的问题,也是科学要研究的对象。一旦逻辑的、理性的思维无法解释时,他们就求助于非逻辑的、非理性的直观思维。应该说原始人的这种活动并不是自觉的,几乎是出自本能。我们通过考察和研究可以发现,在古代,最早从事科学活动的人,主要是祭司和僧侣,因为只有他们受过教育,有条件可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他们同时又是科学知识的收集者、保存者和传播者。在古巴比伦,每一所庙宇都有图书馆,收藏了很多天文学和占星术的文献。但他们从事科学研究是为宗教服务的。科学活动也常常与宗教活动相混杂。因而从认识论的角度上看,科学与宗教的产生有着共同的基础,二者共同的出发点决定了它们缔结血与肉的姻亲关系,但二者的浑沌不分并不是简单的,其间又有着复杂的结构关系和相互作用,如科学的人文主义。
二、宗教和科学的矛盾斗争是理性和非理性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实践活动中的突出表现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在劳动过程中逐渐能区分自我和对象,确立了自我意识,这种原始的、最初的浑沌意识开始分化,分化出具有不同特性和功能的理性和非理性。理性和非理性是两种不同的把握外部世界的形式,它们都是在人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发展的,同时又能动地参与了人的社会实践。它们不仅反映外部世界,而且创造外部世界,它们的作用只有通过人的社会实践才表现出来。需要、欲望、意志、群体无意识、动机、直觉、灵感等非理性因素都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只不过它们尚未达到对客观世界的逻辑概括这样的高度),它们形成于人的社会实践,又伴随着人的社会实践,并通过人的社会实践发挥作用。(注:参阅吴宁:《非理性发生的社会基础及其在社会历史活动中的作用》,《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6年第4期。)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组成了人类主体能力的两翼,两者相互契合、相互渗透。(注:参阅胡敏中:《理性的彼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在人类历史上,宗教是先于科学而存在的(当然,科学形成后宗教并未消失),在宗教产生的时候,科学尚未出现,甚至也没有单独的知识存在,因而我们不能将宗教和科学简单地相并列。直至中世纪自然科学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科学作为教会恭顺的婢女的状况并未能得到根本的扭转。譬如基督教宣扬“地球是上帝特为人安排的宇宙中心”,于是亚里士多德创立后由托勒密完善了的“地心说”就被用来为上帝创世说作论证;基督教宣扬“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就有人以古罗马医学家盖伦的灵气论来证明其正确性。这个时期真正的科学和科学思想被贬为异端邪说,教会对自然科学家的镇压是极其残酷的。据统计,“仅在西班牙,就有一万多人被烧死,有二十多万人被处徒刑,中世纪欧洲各国被判刑、烧死的约有五百多人,其中有不少是自然科学家和宣扬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人。”(注:《自然辩证法讲义》初稿,第11页,人民教育出版社。)中世纪后基督教在欧洲极大地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因而恩格斯说,“中世纪的欧洲什么也未被留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7页。)人类理性的力量在非理性面前显得如此的脆弱和微不足道,宗教神学在这个时期内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
但是,非理性并不能也不会完全压制和调控理性,因为“科学没有宗教就象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象瞎子”(注:《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82页。)。这就是说,没有宗教,科学的发展就失去了它的根本动力;反之,没有科学,宗教就会因其愚昧、无知而失去它的前进方向和目标。中世纪之后的文艺复兴运动标志着宗教和科学间的矛盾尖锐化和公开化。“随着中等资产阶级的兴起,科学大大地复兴了,天文学、机械学、物理学、解剖学和生物学的研究又重新进行起来。”“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它的工业生产,需要探索自然物体的地理特性和自然力的活动方式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9页。)在人类科学理性强大的攻势面前,在人类渴求真知、渴求发展、渴求挣脱桎梏的强烈欲望的驱使下,在宗教神学越来越无法解释众多的新近出现的自然现象和规律的情况下,宗教非理性不得不对科学采取某些“让步”措施,它们被迫承认某些科学原理,开始改善同科学家的关系,并号召教徒和神职人员钻研科学,利用科学成果为宗教事业服务。人类在社会历史活动中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发展,不断地从非理性走向理性,从理性走向更加理性。(注:参阅吴宁:《非理性发生的社会基础及其在社会历史活动中的作用》,《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6年第4期。)
历史发展到19世纪,科学才对神学取得了基本胜利。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后,改变了封建的生产关系,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17、18世纪的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逐渐被联系的、发展的辩证思维所代替,人类的理性活动由低级转入高级,由个体转向群体。同时,宗教神学并不甘落后,它们也积极地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并利用科学成果进行论证,努力在科学理性的怀囊中寻找自己新的支撑点和突破口。
理性的发展促进了非理性的发展,非理性的发展又激励着理性走向更高的层次。可以说,人类在外部人化自然的同时也导致了内在自然的人化,人无论是在理性方面还是在非理性方面都是在不断提升的。(注:参阅夏甄陶主编:《认识发生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523页。)
三、人类认识领域的已知和未知使宗教和科学的长期共存成为必然
人类的认识是在思维的至上性和不至上性的矛盾运动中实现的。人的认识就其无限发展的本性来说,是无限的、至上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是不至上的、有限的。认识的两重性相互交织渗透,盘绕上升。我们知道,“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整理感性材料。”(注:丹皮尔:《科学史》,第10页。)“科学既是人类理性最高贵的花朵,又是物质福利最可靠的源泉。”(注:贝尔纳:《科学与社会》,第128页。)而“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4页。)(以上着重号皆为作者所加)美国著名的神学家保罗·蒂里希认为,“宗教就是被一种终极关怀把握住的状态,这种关怀和其它关怀对比起来,所有其它关怀都只能算是次要的,而这种关怀本身就包含着对人生意义这个问题的解答。”(注:宾克莱:《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96-297、297页。)科学能通过对人类心灵的作用,创造物质(包括理论)克服人们在自己面前和在自然界面前的不安全感。但是,关于人类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判断,作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信仰,是科学所无法回答的。因为科学只能断言“是什么”,而不能断言“应当是什么”,在“应当是什么”中包含的人类所追求的一切终极目标和价值判断,作为人类生活和发展所必需的信仰,是科学所无法回答的,它超出了科学范围之外而属于宗教的领域。也就是说,科学所追求的是真,它直接产生知识,间接产生行动的手段;而宗教所追求的是善,它可以使人们从自私欲望的镣铐中解放出来,全神贯注在那些因其超越个人的价值而为他所坚持的思想、感情和志向。因而,在人类认识活动的领域中,一旦理性无法达到,必定会转向非理性,求助于非理性。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在科技如此发达的当今社会,为什么依然有那么多的科学家相信宗教并热衷于宗教。恰如爱因斯坦所说,“我没有找到一个比‘宗教的’更好的词汇来表达(我们)对实在的理性本质的信赖;实在的这种理性本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的理性可以接近的。”(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25-526页。)这里所谓的“实在的理性本质”,就是爱因斯坦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对宇宙本质和规律的终极理解。在他看来,虽然外在的客观物质世界作为人们感性知觉的对象,只给人们展示着现象间不清楚的相互关系,而人们的行动在表面上看来是自由的,也就是不服从任何客观规律的,但是科学家们还是感到需要把自然界的各种事件解释为必然的,完全服从因果规律的。尽管相信自然现象必然遵守因果性规律,归根到底仅仅是以极为有限的科学成就为基础的,但是,这种需要却是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获得的理性经验的产物,是人类理智长期适应的结果。诺贝尔奖获得者,当代著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1987年在回答宗教和科学的关系时讲了一段发人深思的话:“一个科学家从事研究工作的时候,当他发现到,有许多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美丽的自然结构,我想,应该描述的方法是,他会有一个触及灵魂的震动,因为,当他认识到,自然的结构有这么多不可思议的奥妙,这个时候的感觉,我想是和最真诚的宗教信仰很接近的。所以你问,相信不相信在不可知的宇宙中有造物主在创造一切吗?这个话,我想我很难正面回答是或者不是,……我想,这也是一个永远不能最终回答的问题。”(注:《杨振宁教授畅谈当代人思考的若干问题》,《中国企业家》1988年第7期。)当然,造成这种现象的,除了社会阶级根源和认识根源之外,还有家庭、社会、传统观念、民族习惯、伦理道德和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原因。
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可能,就会存在着理性思维所无法把握的、科学方法无法探测到的已知和未知的领域,而既然宇宙的奥秘不能穷尽,人类也就无法从宗教情感和非理性中摆脱出来,宗教和科学也将会永远“两极共生”下去,问题的关键仅仅是:怎样寻求一种更为积极和有效的共生途径或共生状态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