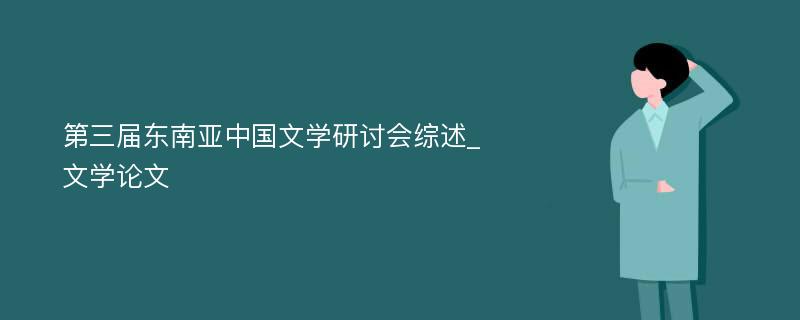
第三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南亚论文,第三届论文,研讨会论文,文学论文,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三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于1997年12月6日至8日在厦门大学召开。这次会议是由厦门市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会、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联合举办的。出席研讨会的代表近百人,其中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汶莱的文艺组织领导、作家、研究者30多位。提交论文60多篇。与前两届相比,本届会议在规模、研究范围和深度上都拓展到一个新的层面,一批青年研究者群体已初步形成。从研究队伍看,研究的重心逐步集中到与东南亚各国之间在地域和历史渊源方面关系密切的侨乡厦门岛上。本次会议中心议题除了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总体探讨外,重点讨论东南亚现有五位资深的代表作家作品。
关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综合研究
一、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价值和地位:会议代表们指出,东南亚华文文学属于现当代世界文学的东南亚文学的一个分支,是东南亚各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新文学的一个支流。作为异国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以华文为载体的文学,既与中华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母体保持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又根植于异域现实生活中,具鲜明的地方色彩。“五四”新文学运动后七、八十年东南亚各国作家受到“五四”新文学的熏陶,创作了不少有当地色彩、风格、语言、格调的作品,涌现了为数可观的作家群和受人推崇的文学活动领导人物,被所在国社会容纳接受,多数均能成为其国家文学的一环。近二十年来,随着华人经济崛起,华夏文化中兴,东南亚华文文学越过发展停滞期,在作家队伍、出版发行、文学社团、文学研究等方面都出现了共同发展、互动互补的新局面,有利于华文文学地位提高的情势正在形成之中。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文学均进入百花争艳的新的发展时期,享有一个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受尊重、更加开放和自由的人文环境,成就显著,特点突出。华文作家到东南亚落地生根后,与当地居民同甘共苦,和睦相处,以当地为荣,建立对当地民族文化的认同和精神归属。他们以自己的文学创作积极参与社会人生,发挥“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在反抗殖民统治、侵略压迫、实现民族独立、民主、和平、消除狭隘的民族主义偏见、培养国民热爱本土的爱国意识情操、开阔国民的精神视野、建立健康文明的社会风尚等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东南亚华文文学不仅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确立了在其所在国文化构成中的独特地位,成为影响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渐次走向世界,在世界华文总体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并因为它与中国文学有着语言同源的血缘关系而架设起文化交流的桥梁,推动了中华文化在海外的衍播。同时东南亚华文文学越来越传播到中国来,也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繁荣,共同为世界文学的进步作出贡献。有的代表指出,曾有一种说法:东南亚的华文文学无论在质与量上都无法与中港台甚至欧美地区的华文文学相提并论,此说是有偏差的。切勿忽略一个重要事实:港台欧美有成就的华文作家几乎都是从中国直接或间接移民过去的第一代作家,反观东南亚的华文作家大部分是土生土长的“第二代”华裔。我们不该对这些基本上已经“本土化”了的第二代(甚至是第三、四代)的华文作家太过苛求,拿东南亚第二代(或第三、四代)华文作家的创作水平与海外其他地区“第一代”华文作家的创作水平相比是
不公平的。还有的代表认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文化价值大于文学价值,历史价值大于文学价值。
二、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总体特征: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核心、主轴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自始至终贯穿其间的一根红线。一方面表现为对祖籍国——中国的怀念固恋情结、对华族母体文化的深深依傍;一方面表现为热爱所居留的东盟各国。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强烈寻根意识实质正是基于爱国情怀。当母国以东方巨人的历史新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华人作家对母体的守望和期待之情便转化为热烈的追怀和赞颂,文化寻根便从潜在的精神追求转化为涌动在文学中的一股强大不息的脉流。这种寻找从自身开始向外辐射便是怀乡,是摄魂夺魄的故国家园之恋。
现实主义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主流。东南亚华文文学贯穿着反帝、反殖、反封建的基本精神,受新兴阶层的先进思想所领导,以人民大众为主要的服务对象,把情感重心放在广大人民身上,放在广大侨胞(华人、华裔、华侨)身上,对他们表达出一种情同手足的挚爱深情。与居住国人民的生活频率休戚相关,走大众文学、乡土文学的道路。强调文学的现实性与时代性、作家的历史使命感、积极参与支持社会的时代变革运动,反映社会变迁,传达人民大众心声,充满了关怀现实的忧患意识。在文风上,淳朴、自然、写实、理性、动真感情、抒真人性,表现方法出于真诚。海外作家接触西方文化机会多,固然思想感情比较自由、活跃,少框框,少顾忌,他们也提出过“文学多元化”的口号,强调主题新意和表现手法的创新、美学思想和创作手法多元化。70年代出现了一批作者,兴起“现代派文学”,但就总体大趋势而言,仍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即令一些艺术手段或表现形式上虽然是现代派的作品,写得晦涩朦胧,可它的精神相当接近于现实主义。
重视与倾心于立足本土与向外延展构成了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双重特性。紧扣着脚下的现实生活,植根于华人社会,以华人生活为主要题材,富有浓郁的华人生活气息,反映所在国家的社会人生和特有面貌,向本土化演进是东南亚华文作家的共同追求。例如新加坡作家周颖南提出为广大侨胞而写作、侨胞是写作的对象,“我们写作的材料是从侨胞中来,我们写好的作品也是要回到侨胞中去”。马来西亚作家吴岸认为马华文学应立足于马来西亚的现实,具备独特的民族性、地方性与社会性,坚持走一条乡土文学道路。立足本土的标示,涵盖了作为所在国的一种民族文学的国家观念、写作途路、创作源泉、题材选择、感情寄寓、形式经营、读者对象等一系列问题的取向要旨。这既有利于华文文学的扎根与繁荣,也有利于消除各种阻碍华文文学进取的盲点。重视亚细安文艺的合作,突破原有区域性局限,扩大与台港澳地区的联系,加强与中国大陆的来往交流,发展与世界各地华文作家的情谊,这些都显示出东南亚华文文学向外延展的特点。
三、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产生与发展都深受“五四”新文学的巨大影响,如马华文学接受中国文学影响有三个方面:(1)接受中国健康文学思潮的传播;(2)学习中国个别作家的风格;(3)吸收中国的文艺人才成为本地作家。华侨的播迁实质是一种文化的播迁,他们的存在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在异域他邦不同文化的映照下,他们从反观自己中强烈意识到自己所代表的文化身份和价值。他们自身的文学素养与民族责任感方面都以中国文化为认同对象,文学创作与思潮就都直接带去了中国的影响,这给东南亚文学与中华人文精神之间的联系创造了条件。虽然中国新文学的影响已逐渐融入到其所在国的文化整体形态之中,但文学血脉里仍然渗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精神。华文作家对祖籍国的传统人文精神情有独钟,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东方文化、演绎东方价值观、优秀的伦理道德,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儒、释、道思想心有所归。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学传统,强调文学对社稷、时代所承载的使命、“兴、观、群、怨”的文学价值观哺育了一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关注现实、感时忧国的忧患意识,铸造了炎黄子孙刚直不阿的文化性格、中国心、民族魂。这一文学精神和文化性格也潜移默化成为海外知识分子的一面精神旗帜,并在华文文学中得以体现。即使一些年轻的作家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多,似乎也难完全摆脱其影响。有识之士指出,华文作家只有根植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才有可能写出成功的作品,当是不易之论。东南亚华文文学与大陆台港澳文学一样共同孕育于中华文化母体,彼此间联结着坚韧的民族纽带。它在多元种族与多元文化融汇的时空背景中互相渗透与融合,既有时代风雷的积聚和南洋本土色彩,又有中华民族传统关注人的生存价值、探索人类命运的人文精神的积淀,可谓中华文化的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学与世界上其他地域文化相融合渗透的结晶。
四、东南亚华文文学的走向:在东南亚华文文学面前危机与生机并存。其前程尽管仍存在着险象与暗礁,但趋势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华语华文地位日益提高,儒学复兴,华文文学的读者群、生存和发展空间必将扩大。华人的丰富经历和传奇色彩、与当地民族同心协力争取独立与开发建设业绩,为作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华人逐渐融合于多元民族的大家庭中,为多元文化增添光彩的呼声日高,以“信息时代”为主要特征的新世纪必将给华文文学提供走向辉煌的机会。有的代表提出,“适者生存”、华文文学应主动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关注人的现代化、人的整体综合素质的提高,培养健全的民族精神,相应调整自己的内容和形式、艺术技巧,在对自己的突破超越中朝多元并存、多样化方向发展。也可因时因地采取灵活变通的权宜措施,如近年新华文坛兴起的“微型小说热”适合城市生活节奏、成为城市人的精神食粮。有的学者认为东南亚华文文学正在努力于开拓与创新,蕴藏着一股坚毅的驱前力与开拓力,如新华作家方修对马华新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史书的撰写就是富有开拓性的工作;泰华作家司马攻开首进行微型小说新手法的试验,实现了新的跨越,好评如潮。还有的学者提出东南亚华人文学的流向应体现孔子说的“和而不同”。“和”即共同性;“不同”即个性、独特性。因“同根”而具有共同性,又因“水土异也”而带各自特点。在各国整体文化生态自由、多元的共同点下,均怀对全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的最终目标,这就是“和”;根据地域差别,容纳不同声音、写作方法、风格、色彩,这是“不同”。换言之,即以求同存异的精神共赴时艰。在不同的文化碰撞中对民族文化本位的坚守和对它文化的吸收,也是在文化历史演进中“现代”对“传统”的激活,两者并行不悖。研究马华文学的学者认为,马华文学的未来发展将在本土化和现代化的对峙消长中展开。本土化进程并未完结,因此再本土化将成为马华文学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向;现代化进程也没有完成,再现代化将成为马华文学未来发展的一种路向。当这两种路向从平行、对峙、互动走向交叉融汇时,一种真正博大的马华文学就诞生了。有的学者认为,还应打破地域或疆域的限制,建立起以华人世界为范畴的“整体互补”的战略观念。具体说,不分国家和地区互相发表出版作品,开展评论研究、访问交流、支持和促进,以达共同提高繁荣的目的。不忽视与整个大的文学格局之间的关联性与
互补性,在寻找借鉴中求得自身的丰富与发展。新华作家周颖南提出必须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共同目标,走到“中国取经”和“抱娃娃”(指好的成果与经验)、“回娘家”两条路。东南亚华文文学建设脱不开泛世界性的中华文学建设课题,两者是相互影响、双向共通的。合作与交流不等于兼并或同化,彼此仍须固守和发扬自己的民族风格及传统特色,才能真正构筑东南亚华文文学之共通特征。让中华文学走进世界文学去,也叫世界文学来了解、靠拢中华文学。
关于五位资深的代表作家作品的探讨
一、林健民:从事华文文学编著65年,被誉为“菲华文学拓荒牛”、“前驱者”。30年代最早把中国文化带到菲律宾,促进启轫期的菲华新文学运动发展。作品贯穿主题是爱与善的交响曲,用创作实践给人民施爱行善,涵泳中西和菲国的繁复文化,以博识、适时、新颖著称。人格追求上“世故”与“脱俗”和谐地存于一身。二千五百行的叙事诗《不流血的革命》揭示了震惊世界的1986年菲律宾二月革命中专制独裁政权的下场,谱写一曲正义战胜强暴的赞歌,结构与《荷马史诗》相似,被誉为反映整个时代的史诗性“巨大史著”。散文成就高,在菲国华文文学中占重要地位,在全球华文文学中也颇有名气。散文透出对亲人朋友的挚爱、关爱故土、族人之情和博爱,对社会人民的关切。感情充沛、真诚、朴素、开朗、率直。观察细致入微,善作比较。文笔简洁老到,疏朗有致。他的《中国古诗英译》创造了独树一帜的“整齐美”的译法,有白居易风格。
二、方修:成就卓然的新加坡文学史论家,50年代中期开始迄今,40年如一日,除著书立说外,专事新马华文文学史料的发掘、整理、研究,撰写文学史,编纂文学大系,评论作家作品。他以丰富翔实的史料、科学严谨的史论、精辟独到的史识在当地文坛率先撰写一部系统完整、具有区位特色和理论深度的马华新文学史专著。他以现实主义为基点、线性、阶梯式的进化文学发展观去审视马华文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其现实主义文艺观包含文艺与生活、形象和典型、创作方法、题材、艺术形式、文学遗产等丰富内容。其社会杂感、文艺杂感颇具鲁迅风,被称为“新加坡的鲁迅”、“一面旗帜,一个标识”、“马华文学史的一部活字典”。
三、黄东平:笔耕40年,三百万字的小说、诗、剧本、散文、杂文、寓言、童话广泛而深刻地反映这一个世纪以来南洋华侨社会的生活民情、风俗习惯、社会风貌、印尼华人的奋斗史的现状,是华侨、华人可歌可泣事迹的历史记录,也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侧面写照。享誉中国、东南亚,被称为“印华文坛一面光辉的旗帜”。他塑造了崭新的人物形象,艺术形象典型化,描写人物手法多样化,注重刻画丰富的内心世界,善用平易朴素的语言、舒缓的语调,作品富有浓厚的南洋民族色彩和乡土生活气息。小说成就更突出。中短篇小说集《远离故国的人们》多侧面、多角度描绘60年代后印尼华人社会各层面的世态人情及其变迁、各阶层的人物心态。洋洋百万言的现实主义优秀之作《侨歌》三部曲反映华侨反抗荷兰殖民统治、争取民主独立、抗日救亡的社会生活、华侨的出洋史、创业史与斗争史、华侨社会内部同甘共苦缔造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条件,洋溢着浓郁的中华情结。人物众多,富有个性,采取复式结构,展现极富地域特色的自然风景、人文传统风俗、生活方式。具有小说与史实的价值,被称为“艺术化的印尼社会全景的百科书”。
四、云里风:马来西亚著名教育家、文学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45载笔墨生涯,涉猎了小说、散文、文学评论各领域,尤以短篇小说引人瞩目。受鲁迅启发,歌颂韧性战斗精神,抨击虚伪狡诈、腐朽黑暗。小说总体看是伦理教化小说,题旨是社会教化、伦理启蒙。作品最大特色是通过平实的叙述揭示出常态掩盖下的马华社会人生实际问题、与职业婚姻家庭相联系的生存问题、下层众生的辛酸血泪。目光聚集于社会底层女性、社会教育问题的林林总总,塑造一群觉醒抗争、向往追求、自尊自强、自爱自信、富有个性的新女性形象。他的小说贯穿道德感,灌注健康意识、是非观念、悲天悯人精神,渗透华族固有的传统美德、文化素质、精神与思想。构筑一个基本意向:期待与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即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和谐,各民族、人际关系、家庭婚恋关系的和谐,起了警世醒脑的教育作用。文思路广,联想力强,具有理论家的观察力和美学欣赏眼光。表现手法沉实朴素、主题往往最后显示,读到篇末才感受到主旨的份量。文笔稳健、老到,时带幽默,在表里互动中形成朴实凝重的风格,为马华文坛带来一股淳正的清风。语言轻松活泼利落,继承“五四”新文学白话文传统,融汇了闽南话、广东话、马来话、英语等语汇,地区性特色鲜明。
五、司马攻:泰国著名第三代华人作家,散文、短篇小说、文学评论均成绩斐然,尤擅长散文、微型小说。海外赤子思乡情愫是贯穿散文的重要内容,爱祖籍国是主旋律,感情真挚炽热,情文并茂,情理俱到。散文中的叙述甚见功力,每多以物言情、托物言志、寓情于境、情景交融手法。小说内涵丰富深刻,富含中泰文化传统韵味,体式精悍多样,结构委曲而留有“空白”。尝试小小说的多种手法:剪影式、概括式、拼叠式、推理的、寓言的、透视的、单线的、多重指向的。90年代初创作相当数量的微型小说,“以正衬反”、“以乐写哀”对比法、诗化、散文化手法、思念与误会法并用。篇幅小容量大,做到“尺水兴波”,有冲击力、爆发力,成为本地创作微型小说的先声。文论禀承传统文论,比喻出韵致,象征见意境。作品中异国生活情调、浓郁的乡土感情和中国历史文化氛围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形式健劲清新、幽宛灵动的艺术风格。语言有语义容量丰富的“画龙点睛”之笔、整饬而清简的短句式、诗化、散文化的古韵,传神又醒神的比喻,“轻盈飘逸,又内蕴深厚”。幽默而有生趣,圆熟而老辣,善于铺陈,却不显沉冗,洗练畅达,精当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