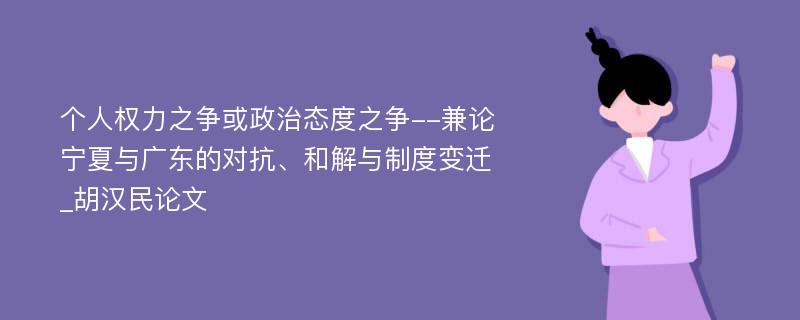
个人权力之争还是政治态度之争——也谈宁粤对峙、和解与制度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争论文,也谈论文,权力论文,态度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1年的宁粤对峙是国民政府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因约法之争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介石囚禁立法院长胡汉民,反蒋势力迅速集结,一批国民党元老派如古应芬、萧佛成等中央执监委南下,与粤方军事实力派陈济棠等迅速结成同盟,在广州成立非常会议,声势颇大,全面挑战国民党中央权威。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为宁粤和解提供了可能,各方奔走呼号,呼吁停止冲突,共赴国难。几经周折,最终以和平方式实现了双方初步和解,中央政制亦发生了很大改变,影响了其后国民政府的政治秩序与抗日准备。
对于因约法之争导致的宁粤对峙与和解的过程,目前学术界作出了不少考察或诠释,研究水准已达到了相当高度,金以林先生更是该事件研究的集大成者。①金先生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民国档案》等名刊上发表了一组文章,使用了大量有关该历史事件的珍贵海内外档案资料、要人往来函电、口述材料、相关人物的日记或回忆录等,试图复原宁粤对峙事件的来龙去脉,探讨国民党内蒋、汪、胡各派系的政治表现及权力之争,精细勾勒出了宁粤对峙的历史过程。
在金先生的几篇大作中,有几个观点颇为引人注目。第一,金先生强调,“宁粤之争是蒋、汪、胡之间的个人权力之争,而非领袖的不同政治态度”。(见《汪精卫与国民党的派系纠葛》一文)。譬如,论述汪精卫在宁粤和解中的态度时,金先生判断,汪精卫已和蒋介石达成妥协,合作前景日趋明朗,自然不愿支持胡汉民,粤方的孙科对宁粤合作态度也相当积极。故而,其结局是蒋、汪合流排挤了胡汉民,孙科也因与粤方分裂得以出任了行政院院长。换言之,这种斗争只是由谁掌控国民政府中枢的问题。
第二,金先生认为,九一八事变迫使粤方被迫接受政治解决宁粤对峙,上海和谈的最大成果,就是以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形式结束党内政争。但“由于粤方内部的分化导致在和谈中对蒋做出了过多让步,从而使粤方改革制度的目标完全落空”。(见《汪、胡联手到蒋、汪合作——以1931年宁粤上海和谈为中心》一文)。金先生认为,对于蒋、汪、胡之间不管哪一种组合,主导权始终掌握在蒋介石手中,另一方只是陪衬而已。伴随着国民党内各派势力的相互妥协,此后党内再难形成各派联合一致的反蒋基础,国民党基本形成了以蒋介石为主导、各派联合统治的局面。如果笔者理解无异议的话,金先生的结论是,在宁粤和解中,粤方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最后的制度改革完全违背了粤方的初衷。
笔者并不否定宁粤对峙与和解中,蒋、汪、胡及其各派系的相互妥协与权力重组,但以为,对该事件的理解,除复原其过程之外,恐怕还需考量几个问题。第一,宁粤对峙尽管因蒋介石囚禁胡汉民而引起,如无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宁粤双方会和解吗?第二,如果粤方在和解中被迫让步,则是否有其让步的底线?如和解结果在其底线之内,粤方制度改革愿望完全落空的判断能否立足?如果是宁方作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能否判断宁方为谋求统一,有整合政治资源、推进制度化的诚意?第三,如果粤方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解后是否在制度上得到了体现或保证?第四,宁粤和解对政治制度的变迁产生了何种影响?预示着何种政治制度才是能避免地方挑战国民政府中央权威的最佳选择?
笔者以为,把宁粤对峙与和解单纯理解为蒋、汪、胡等个人权力之争与派系政治稍显片面,它亦体现了不同的政治态度之争,同时与制度变迁存在着必然的关联。盖政治权威人物均有对国家命运与政党利益之考量,其意愿在制度上一定有其体现,并会主动或被动推动制度变迁。基于此,本文拟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首先分析九一八事变前宁粤对峙的动因以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次分析宁粤和解过程中双方的政治诉求与关注的焦点。第三,分析宁粤和解与制度变迁的因果关系。结论部分反思政治冲突对国民政府中央政制的影响。
一、宁粤对峙的动因与焦点
一般而言,宁粤对峙之起因大都解释为约法之争,并因约法之争而解释为胡汉民与蒋介石的个人权力之争,事实上并非尽然。从对峙的形式而言,是地方实力派对中央权威的挑战,而其源流则需要追溯到训政初期的政治模式。按照胡汉民的政治设想,是采用党权至上的训政模式。在政治实践中,其所主管的立法院具有对行政院的权力制衡,而非单纯的五权分立或权力平均。
这种制度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如果训政初期的国民党能建立一个强势的中央集权政府,完全统一全国,则断不会出现地方实力派对中央政权的挑战。事实上,国民政府能有效控制的省份非常有限,中央权威未能确立,党内派系冲突持续不断。政治主体最难处置的问题是,地方军事实力过分强大,一方面耗费无数军费,亦不利于国家真正统一与政治现代化的推进。因此,国民政府希望通过军事领袖共同商议立法程序(编遣会议),以和平方式清除阻碍国家统一的要素,使军权由私人手中转移到政府,使军队成为真正的国军,完成国家实质的统一,进而巩固国民政府的力量。②如蒋介石所言:“如果政府不能整理,则决心束身引退,以谢天下而已。”③蒋希望借助编遣机会以整顿政治,加速国家统一。“谁知以后的反复内战,却由这个编遣计划而种下恶因”。④蒋因整编军队,引起了各实力派的反对,并遭受舆论界之责难。有舆论认为,蒋“乃不幸其人不学无术,以偏私之道治军事,且行贪婪之政,遂致国家再乱”。⑤
通过军事行为虽然可以迅速提高军事胜利者的权威,但也让其他领导者害怕军权的膨胀而瓦解党权至上的政治关系。因而,必然出现持续的党权与军权、党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冲突。蒋介石利用武力威慑或分化瓦解取得了对各地方实力派的胜利,意味着在权力膨胀的过程中,可以利用个人权威推进中央集权制度的进程。介入政治领域的蒋介石希望在政治上尽量发挥其作为,蒋亦加强了对政治的学习与研究,以全面改革中央政制。如蒋所言,“政治自愧无学,对于现下适宜制度与国民会议皆有研究,余甚觉党中范围太狭,书生私见太深,所以国不能平也”。⑥面对国民党内的分歧,蒋认为,“应牺牲一切成见,赴其全力,以达成统一之一点,其他只要不越出本党主义之外与不兴兵破坏统一,则一切要求皆可允纳也”。⑦换言之,蒋在整顿或推进政治改革中,并非完全依赖军事行为,而是蕴含着诸多政治妥协的成分。1930年9月22日,资历极深但甘居蒋之下的行政院长谭延闿病殁。1930年11月18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通过了由蒋介石提出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制度改革案,加强中央政治会议,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中心,加强行政效率。⑧议案宗旨在于由委员制发展为集权制,提高行政效率,保证中央集权,保证中央政治会议对国民政府的指导与监督。会议决定推选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因而,蒋介石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时中常会不设主席,采用委员制的方式防止个人专权)、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主席、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行政院长五高职于一身。
通过树立中央权威而建立协调的政治关系本为政治必然之事。作为通过军事行动地位急剧上升的蒋介石而言,踌躇满志,然其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集权政治诉求必然会遭到了一些实力派的强烈反对。胡汉民充当了反蒋的精神领袖。如蒋所言,“彼借委员制之名,而把持一切,逼人强从……凡有重要之案,皆搁置不理,使人不能推行,一面则诽谤政府之无能,政治之迟滞”,“彼不欲有约法,思以立法院任意毁法变法,以图其私利,而置党国安危于不顾”。⑨胡汉民曾助蒋战胜过西山会议派、改组派,并成为国民政府训政制度的“教父”。然而,胡的书生意气与对别人的过分苛求使他易于失去支持者⑩,且胡并无自身军事实力为其支撑。但胡长期阐释三民主义建立的理论威信及身为立法院长的政治身份,又会驱使他走上极易受伤的政治舞台。胡对立法居于行政之上的西方政治理念,必然使他为民国政治的现代化与法制化作出反蒋集权的意向与实践。胡在与蒋的交锋中,试图净化党治基础,选择维护党权以获得党内外尊重的方式。简言之,蒋试图建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集权政治体制,而胡却试图通过政治方式或法律方式强化党权,以遏制个人集权。
胡汉民反对由国民会议制定约法演化的约法之争,成为宁粤对峙的导火线。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囚禁了胡汉民,引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风暴。针对囚胡之事,粤方认为此乃蒋的个人集权,是军事独裁的复活。汪精卫明确表示,自四中全会以后,“对蒋已失望”。(11)朝野内外皆认为,最要紧的是恢复法治,遏制军权的坐大。“兵权所在,万恶包围,军必成阀,环境所造”。(12)这一事件,使潜在反蒋实力派迅速有了聚集的机会与斗争的目标。
面对反蒋势力的冲击,蒋介石依然于5月5日至17日的国民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草案》,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各院院长及部会长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国民政府任免,国民政府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此一草案的通过,实际上是蒋为突破《训政纲领》对国民政府权力的限制,使政府治权的最高地位取得法律上承认,大大提高了国民政府主席的权力。
胡汉民落难后,国民党内文职官员如胡汉民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军事将领如陈济棠、李宗仁等两广地方实力派联合组成反蒋阵营。(13)5月25日,林森、唐绍仪、古应芬、孙科、许崇智、陈济棠、陈友仁、李宗仁、陈策、李文范等在广州联名发表通电,催蒋介石于24小时内辞职。5月28日,成立广州临时政府,历数蒋介石罪状,谴责蒋介石“假行政之名,行个人独裁之实”,对政见不同者“咸施以诈术与暴力,必尽去之而后已”。要求蒋介石于48小时内引退,“勿以一身为党国梗”(14),并欲讨伐南京。一场政治风暴有可能重新演化为粤方挑战中央权威的战争。
从宁粤对峙的起因不难发现其焦点所在:第一,作为国民党后进的蒋介石,此时未能全面掌控党权与解释党义,只能依靠军权为后盾,利用国民政府主席与行政院院长之职位,试图制定《约法》以规范政治运行方式,扩大政府的自主权,谋求政治统一。换言之,蒋制定《约法》至少体现了这样一种政治态度,即依靠集权方式,维护党内统一,加强政府权力,使政治权力能够合理运行。(15)但蒋的个人权威及其所主导的政府权威均未形成,集权意愿必然遭到党内外各派的反对。无奈之下,蒋采用了非常规方式,软禁集权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胡汉民,以实现其政治意图。第二,粤方形成了以胡汉民为中心的反蒋阵营,有党内元老派古应芬、萧佛成等人以及军事实力派陈济棠、桂系的支持。广东是国民党的发源地,是国民革命的摇篮,关系虽盘根错节,但有党内粤籍元老派坐镇,在民众中影响自是不小。胡汉民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且胡在国民党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对总理遗教的理论阐述与确立训政制度、建立国民政府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威望颇高,具有较大的号召力。宁粤对峙的处置成为衡量中央权威的指针,也是集权制政治模式能否得以推行的重要考验。
二、和解过程中的政治诉求
表面看来,宁粤对峙似成死结,训政初期建构的政治秩序有可能被颠覆,政治系统有可能解体。国民党中央政府在面对地方政府的挑战中,是否会如中原大战般的激烈战事解决争端还是另有转圜。九一八事变的发生,给各方提供了一个相互妥协的机会。
当蒋听闻九一八事变消息时,“心神哀痛,如丧考妣”,“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16)9月21日,蒋甫返南京,即召集中央要员商讨应对方略。关于对粤态度,蒋指出:(1)令粤方觉悟,速来南京,加入政府。(2)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只要粤方能负统一之责来南京改组政府。(3)胡汪蒋合作亦可。(17)9月22日下午,蒋邀请吴敬恒、戴传贤等,“详述余之怀抱与感想,要胡汪合作,余交出政权之意”。(18)此后,“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得到了蒋的高调渲染。9月28日,邵力子在中央纪念周上发表谈话,谓“一星期来,中央诸同志,天天开会,决定应付此事。先从团结入手,已致电粤方,望团结起来,共赴国难”。邵力子还表示,“我相信如有屈辱签约之事,中央同志必将全体自杀。”(19)宁方在国难当头希望与粤方合作的态度是相当鲜明的。
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宁粤双方军事敌对状态迅速收敛。侵湘之粤桂军已先自动退却,宁方的何应钦亦中止入湘。蒋令陈铭枢携亲笔函赴粤议和之询。25日,张继、蔡元培、陈铭枢由沪赴港,与粤方首领会商和平办法,粤方参军处及参谋团结束,停止办公。陈济棠于27日下午召集各将领会议,讨论撤兵后之治安问题、防务分配办法及应付日兵等问题。10月1日,粤方裁撤运输总站。(20)10月2日,蒋电陈铭枢并转蔡、张,继续强调和解的三原则:“(1)如粤中能负全责,则在中央同人,尽可退让一切,请粤同志整个的迁来首都,改组政府,中正个人下野,更无问题。只要粤中能确实负责,前来接代,则中正即可通电下野。(2)如粤中不能负责,则归中央负责主持,而广东政府自当取消。(3)如要各方合作,则中正更为欢迎,但必须来沪面商,方是开诚相见、同舟共济之道。”(21)
在宁方表达政治和解时,粤方对于蒋氏之统领党政军三大权,颇不赞同,希望蒋氏放弃党政专事治军以展其所长。其次,请胡汉民出任政治,共挽危局。(22)蒋原拟10月14日晨访胡,谈粤事。胡以国难日急,非力谋团结不可,乃决定亲访蒋协商。13日下午胡与陈铭枢、吴铁城商谈后,三人即往陵园谒蒋,相谈甚洽。(23)蒋表示“过去之是非曲直,皆归一人任之,并自承错误”,胡汉民“亦感动”。(24)10月14日,胡汉民得到了释放,蒋决定由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吴铁城、陈铭枢等陪同胡汉民到上海,候晤汪、孙等人,并欢迎他们入京,开和平会议。
汪精卫对宁粤和解亦积极响应,抵沪后发表了粤方主张,“对内以建立民主政治,推倒个人独裁为目的,对外以贯彻打倒帝国主义之侵略,求中国绝对平等为职志。”(25)换言之,粤方反对宁方的政治武器是以民主政治为口号,反对蒋介石个人集权或领袖集权,希望以党权支配军事权力。
此时,蒋对宁粤和解表现出了相当的诚意。10月22日,蒋飞抵上海,下午至孙科寓所会晤汪、胡,请他俩主持召开“和平统一会议”,并相邀入京,共赴国难,蒋、汪、胡相继握手。蒋表示效果极佳,和平基础已定,已采粤方主张,用会议形式,会议党务政治诸问题,决由胡召集开会,自24日起举行。蒋并表示:“诸同志皆党中前辈,本人为后进,想来服从前辈。此次诸同志议定办法,凡胡汪两先生同意之事,我无不同意照行,我若不行,尽可严责。”(26)汪精卫代表粤方表示:(1)国民政府主席如德国的总统那样,实际上不负责任,行政院应负责任;(2)废除总司令职;(3)一二三届中央委员共同负责党务。蒋、胡决定在上海召开和平统一会议。
对于在上海召开和平统一会议,无论是宁粤双方抑或地方党政大员,多寄予厚望。于右任认为,“为一致对外,不仅要京粤合作,应更进一步谋全国整个团结,且西南之川滇黔军政纠纷,西北之五马问题等,一切隐患,均应通盘筹划,作一劳永逸之计。”李济深乐观认为,“国难当头,国内和平统一自能实现。”邹鲁希望此次会议“应谋永久和平,不可暂时的或分赃式的和平,今后再无诚意团结,致国家破碎,实丧心病狂之徒。”伍朝枢认为,“对和会意见,仅八个字,即和平统一,共赴国难。至军政权限划分,余等向主张军权受党与政府之支配。”(27)
当然,粤方在宁粤和解中并非铁板一块,即使反蒋的精神领袖胡汉民亦宣称在上海和平会议中持“超然的中间立场”,对被宁方推为和会代表,坚辞不就,事实上已经昭示着粤方的分裂,而这种政治现状为宁方通过分化与拉拢逐步瓦解粤方提供了契机。不过,在政治态度的外部表达上,胡、汪的政治观感并无二致。胡氏认为政情的病情在于制度上有缺憾。胡对外界言,对蒋本人频加称许,而谓制度及环境不佳,故制度的修改是非常重要的。10月24日,汪精卫发表谈话:“为使政治从军事支配中解放出来,为二十年来待解决之问题,中国必须做到此着。始能成为现代国家。现役军人如果要从事政治,必须先把军职辞却,继不致挟持军力以威胁政治。”(28)
宁方坚持法统与制度不宜发生很大变动,但不反对容纳粤方或由粤方在法统基础上组织政府。10月27日至11月7日,宁粤代表在上海举行“和平统一会议”,会谈共进行了七次。(29)开会当日,汪精卫对记者谈话,重申粤方主张,谓政治上惟望做到军政分开,政治脱军权支配,论事不论人。胡汉民虽未与会,但自述为最爱惜蒋者,盛称蒋在党国之大功,本人爱人以德。胡谓其最大决心,维持国民党,不使成为元二年进步党,渐至渐灭。在上海会议中,宁方代表认为,(1)政治中枢不宜更动,政制亦未宜轻改,主席权限一原则无成见。军方总司令部尽可取消,使陆参各部之常设机关负责。(2)党统不能有问题。粤方却坚持由统一会议组织统一政府,国府采德法总统制,行政院如责任内阁制,国府主席由年高德劭者任之,军人不得当选等七条。(30)最后决议宁粤双方各在广州和南京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大,并提出改革中央政制。这样,分裂、对峙的双方就找到了团结统一的途径。(31)
粤方内部的分裂,是宁粤之间政治妥协能够达成的重要因素。如蒋所记,“粤方全为胡汉民一人所阻碍,而汪孙则愿来合作。以不愿胡破脸,故不敢明白表示,当使之有转回余地。”(32)胡汉民在12月5日举行的粤四全大会闭幕会上称:“此次大会高揭‘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第二个口号为‘推翻独裁,实行民主政治’。今人以为统一,必集权,但集权结果,遂形成独裁。”在四全大会的宣言中并提到“武力受政治之支配”,军权必须决之于党,而由政府负责执行,军权隶于行政院。(33)坚决表示要求蒋下野,进行政治改革。
在外部压力之下,国民政府政治不稳,谋求各方团结,共赴国难成为共同的心声。在倒蒋的风潮中,12月15日,蒋介石向全国通电,宣布第二次下野。蒋在“辞国民政府主席职呈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中称:“胡汉民同志等微日通电,且有必须中正下野解除兵权,始赴京出席等语,是必欲中正解职于先,和平统一方得实现……现在国事至此,若非从速实现团结,完成统一,实无以策对外之胜利,慰国民之期望,权衡轻重,不容稍缓须臾,再四思维,惟有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另行选任贤能接替,以维团结,而挽危亡……,解职后,仍当本国民之天赋,尽党员之责任。”(34)不过蒋在下野前当天,主持了行政院国务会议,决议改组苏、浙、赣、皖四省省政府。分别由其心腹顾祝同、鲁涤平、熊式辉、邵力子分任主席,并由贺耀组任甘宁青宣慰使(35),自己飞回了浙江老家。
至此,宁粤双方在蒋下野后,得以汇集于宁,全面解决政制问题。粤方在沪代表,除汪精卫因病留沪外,孙科等皆于17日入京。惟胡汉民仍称病留粤,中央执行委员会定21日召集第四届中执会第一次会议,一切党政改革及国府主席诸重要问题皆将取决该会。宁粤要人皆主张开放政治,进行宪政。(36)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知宁粤在和解中的政治诉求:
第一,粤方以民主政治为口号,要求蒋下野,实现粤方组织政府的愿望,实现高调倡议的党治政府,希望利用党权遏制军权;从制度上保证蒋不再重返个人集权,但不排除发挥蒋在军事上的能力为国家所用。这种主张的直接实现就是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废疏或漠视由蒋主导的《约法》。即使粤方汪、胡分裂,且演化为粤沪之争,但对民主政治的态度及要求蒋下野,赞成以党权制约军权、重组政府的要求是一致的。
第二,宁方希望在坚持党统法统的基础上组织共同政府,共赴国难。蒋虽表示可自愿下野,内心深处并不愿就此放弃权力。蒋个人下野在宁方内部亦未取得一致意见,蒋与宁方元老们戴季陶、李石曾、吴稚晖及其他将领熊式辉、何应钦等人进行过磋商,彼此意见亦不一。(37)这也是蒋在面对粤方逼迫下退步的重要因素。
第三,宁粤双方具有共同的政治诉求,均表示共赴国难,承认国家统一,分歧是在以何种方式实现统一,以何种方式保证党权高于一切的问题。此次政潮并未演化为内战的原因即为日本的入侵。这种利益共同点也是宁粤实现和解的政治背景与基础。
三、宁粤政治态度的制度实现
由上所述可知,九一八事变为宁粤和解提供了机会,加速了国民政府实质性的统一进程。由于粤方党内元老派居多,且在蒋、汪、胡三巨头中有两位,故向往采取以党统政,以党权制约军权的政制。在政治妥协的风气中,即便握有军权的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亦很难不受权力制约。因粤方的坚持与反蒋势力的庞大,蒋介石不得不下野。表面看来,宁粤对峙体现了蒋、汪、胡之间的个人权力之争。实质上,胡、汪在宁粤对峙中之所以能有所为,是因其民主政治态度的表达以及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党治理念。蒋在对峙中,虽遭受较大压力,但因其表达政权统一以对外的政治态度亦同样能得到不少的支持率,且蒋本身拥有合法的政府最高地位。
在此政治妥协的背景之下,12月25日,宁粤双方在四届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央政制改革案》,决定恢复五院分立,各自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但不负实际政治责任,行政院院长负实际行政责任。12月26日,通过了《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实行责任内阁制。12月28日,中政会决定了孙科为行政院院长。这种政制削弱了国民政府主席的权力,权力中心转移至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蒋、汪、胡同时为中政会常委。蒋对孙科任行政院长也寄予了希望,“闻今日孙科新政府就职,但愿期臻巩固,得慰悬念也。”(38)蒋尽管在政治上遭遇挫折,仍然表达了希望国民党领袖们之间的合作态度,“余仍愿随汪、胡之后负责”,“惟此次政治责任全在于胡,故必须其说一句话也。”(39)此后,在人事关系中,汪逐步倒向宁方,形成了汪、蒋联合的政治局面,胡汉民在“敦促北来”的呼声中,未能与汪、蒋合作,成为了最大的在野派。很快,蒋、汪利用孙科政局危机达成了权力分配,汪出任行政院院长,蒋出任重新恢复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剿共”与国防。
此次政潮之后,国内政局逐趋稳定,蒋与汪进行了较好的合作。蒋尽管产生过急流勇退的想法,但又认为汪难以担当全责。(40)故在汪、蒋合作初期,蒋逐步充当着政府稳定的主心骨。1932年5月7日,蒋与汪谈话,汪犹疑政局之不安,蒋“切嘱应稳定。”(41)5月23日,监察院长于右任弹劾汪精卫时,蒋亦为其开脱,“颇费调解心力”。(42)王子壮认为,“蒋利用汪在南京可为其支撑门面,对日折冲,蒋则身居后方,努力充实。”(43)蒋在很大程度上维护着汪精卫的地位,尽管蒋、汪尚存在斗争,亦不能否定他们的合作。宁粤初步和解后,在责任内阁制与军政分立的制度框架下,国民政府为从事经济建设与抗战准备迎来最好的几年黄金时期。
可以发现,宁粤和解在制度变迁上至少带来了三个结果:
第一,个人集权政治暂时受挫。国民政府中央实行责任内阁制,它是在宁粤双方政治态度上折冲的体现。在军事上,尽管蒋此后负责“剿匪”与“国防”,但其1932年3月出任恢复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显然不能与宁粤冲突前的陆海空军总司令相提并论。盖军事委员会采用委员制,制度本身是为遏制个人权力的扩张。
第二,宁粤和解整合了国民党的政治力量,政治局面趋于稳定。此后,中央政府基本上能够维持稳定,逐渐产生了凝聚力,政治上以制宪、谋求全国统一,共赴国难为重心。即使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多次犯“政治病”时,中央政局亦未发生较大更动。蒋亦一直将政府制度化作为了政治发展的方向,如蒋力主走宪政之路,并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倡言“天下哪有无宪法可以成立之国?”(44)在此后外部危机不断深重之际,蒋认为,“今日图存之道,对内只有开放政权,以政权奉还于国民全体,俾得共同负责,完成国民革命与实现三民主义之大业也。”(45)蒋的此种想法与胡、汪在宁粤对峙中的政治态度具有趋于一致之表达。
第三,采用和平方式解决党内冲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尊重。尽管宁粤和解并不彻底,1932年元旦,统一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广州方面宣布取消“非常会议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同时在广州分别建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一般合称为“西南两机关”。西南政权与中央政府进行着继续的对抗(46),但激烈程度已大不如前。尽管在1936年胡汉民去世后几乎再次酿成武力冲突,最终亦得和平解决。意味着在外患日益严重之下,和平解决派系政治的妥协方式已经得到了政客们的认可。
通过宁粤和解,双方政治态度在制度上得到了一定实现,和平解决内争得到了一定尊重,民主政治、党治得到了一定认可。此乃当局者与各政治派别基于国内外政治环境较为合理的政治选择。然而,接踵而至的问题随之产生。譬如,和解是在九一八后共赴国难的政治环境中获得的机会,势必需要加强国防建设与采取军事行为。国民政府虽采取了政、军分立,恢复本已撤销的军事委员会,尽管该会隶属于国民政府。然而,因国府主席的虚置,国府无权亦无力控制军事委员会的权力扩张。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为平行机构,尽管代表政府,亦无法控制军权。军事权所能受到的约束只能来自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然中执会基本不开会,中常会主管党务工作,而中政会三常委除汪外,均不在京,且汪称病或外出游历治病时日颇多,中政会即便开会亦为例行公事。党权如何加强,党治如何得到体现,如何实现以党治军,如何改革中政会的组织,是宁粤和解后在制度上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同时也预示着宁粤和解后制度上一直存在着刷新的需求。
结论
九一八事变为宁粤对峙带来了和解契机,宁粤对峙与和解有蒋、汪、胡之间的个人权力之争,也反映了宁粤之间的政治态度与体现政治态度的制度之争。以粤籍元老派与两广地方实力派支持的粤方,试图以民主政治为口号,反对个人独裁,回归以党权控制军权的制衡模式。粤方作为地方实力派,既挑战了中央权威,又推动了国民政府中央政治制度的改革。在冲突与和解中,代表中央政府的宁方作出了必要的让步,通过政治妥协,避免了中原大战的再现。
在宁粤和解过程中,第一,粤方接受和解并非被迫,相反,粤方初步实现了政治冲突的意愿,即利用冲突迫蒋释胡,且迫蒋下野,改革中央政制,防止个人专权。第二,蒋介石并未取得对峙的胜利,相反,蒋不得不暂时放弃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愿望与行为,重新思考政治制度的构建模式。第三,国民政府实施责任内阁制,集权于党,国府主席职权虚置,军权与党权、行政权迳相分离,元老派与后进派的权力分配亦已完成,减少了此后因中枢人事变动所致的政潮发生,政制本身趋于合理,国家政治局面趋于稳定。一个稳定的中央政府是现代性政府的基本要求,是有效应对国难的基本前提,有利于加强抗日准备,有利于加紧从事国内生产建设,从而迎来了训政初期最好的几年经济建设与国防准备时期。
基于此,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反思宁粤对峙与和解,尽管它是非对等的和解,但却能体会到这一事件对政治制度与行政制度变迁产生的重要影响。这一重大事件如金先生所言,是蒋、汪、胡的个人权力之争及其表现的派系政治,此一判断本身并无问题,但除此之外,亦可理解为各种利益集团为实现其政治态度的内部冲突与折冲,且最终以妥协方式避免了危机,并导致相关制度规范的出台,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重视以制度规范权力的现代政治理念。通过和解,蒋的第一次党政军集权模式暂时受挫,蒋在冲突中作出了主动或被动的让步,从而维护着国民党的继续治理与危机应对。因党内冲突的长期存在,从另一角度言之,1935年底汪精卫遇刺后,蒋兼任行政院院长,虽完成了个人集权,亦未走向独裁政治,与此亦有着相当的关联。因为通过和解方式建立的制度始终存在着反集权的力量如民主宪政的政治诉求,它在一定的舆论空间与制度空间内,有其生根发芽的土壤与成长的机会。
注释:
①金以林先生近年来以宁粤冲突为研究对象或研究中心的文章主要有;(1)《汪、胡联手到蒋、汪合作——以1931年宁粤上海和谈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全文分析了蒋介石通过政治手段,最大限度的稳定了自己的权力结构,也探讨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的重新分化与组合;(2)《地域观念与派系冲突——以二三十年代国民党粤籍领袖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考察了蒋介石与粤籍领袖之间的矛盾;(3)《宁粤对峙前后阎锡山的反蒋倒张活动》(《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进一步回答了宁粤对峙期间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的相互妥协和权力重组;(4)《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与再起》(《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考察的是胡汪合作反蒋,再到蒋汪联手排胡,经历了一番新的分化和重组;(5)《陈铭枢与蒋介石关系初探——以宁粤对峙初期为中心的考察》(《民国档案》2007年第1期),展现了粤籍人物中支持蒋介石的陈铭枢的活动与派系之间的关系;(6)《汪精卫与国民党的派系纠葛——以宁粤对峙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展现了国民党的权力斗争,而非领袖之间的不同政治态度。其他学者亦有宁粤冲突的研究成果,如陈红民:《关于约法之争的两个问题》(《安徽史学》2006年第2期);杨天石:《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等。此外,上述研究均以冲突的历史性考察为中心,而疏于探讨这种和解与政治制度变迁的关系。
②刘维开:《编遣会议的实施与影响》,(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01-292页。
③《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9年11月19日),原件收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④《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台北)跃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180页。
⑤《领袖人才与国家命运》,《国闻周报》第7卷第25期,1930年6月30日。
⑥《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0年9月3日。
⑦《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0年10月1日。
⑧《刷新中央政治改善制度整饬纲纪确立最短期内施政中心以提高行政效率案》(1930年11月1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二②/3。
⑨《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2月13日、2月25日。
⑩陈公博认为,“胡先生素来好骂人,他的词锋尖酸刻薄,经他批评,身受者都有些象挖心之痛。”陈公博著:《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11)《汪精卫之时局谈话》,《国闻周报》第7卷第15期,1930年4月21日。
(12)《以党役军论》,《国闻周报》第7卷第15期,1930年4月21日。
(13)首先是国民党元老派中央监委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于4月30日提出弹劾,继而第八路总指挥陈济棠、第四舰队司令陈策等于5月3日自广州通电诋毁中央,广东省主席陈铭枢先行离粤辞职,随之铁道部部长孙科、司法院院长王宠惠离京去沪,请辞不返,孙科携陈友仁、许祟智于5月24日离沪抵香港,晤唐绍仪、汪精卫、张发奎即同赴广州。期间,广西之李宗仁、白崇禧等曾于5月11日通电反中央。因之,拥护中央之党政要人及军事要人亦分别通电驳斥,成为极盛一时之电报战。见沈云龙:《民国史实与人物论丛》,(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299页。
(14)李勇、张仲田编;《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192页。
(15)杨天石先生指出,就蒋介石来说,他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显示出他企图迈上民主和法治的道路。或者说,他企图以民主和法治来装点门面。但是,当他遭到牵制,面临反对意见时,他又用粗暴的办法践踏了“现代民主的原则”,国民党由一党专政发展为个人独裁,陷入规模更大,时间更长的分裂。关于胡汉民与蒋介石就约法本身的意见中,胡汉民认为:“立法者只该忠于党,忠于国,忠于由法律案所产生的政治设施。”他企图以立法来限制行政,补救行政的过失。对此,蒋介石指责其为阻碍革命,破坏建国大纲之精神,“致胡函”称:“今先生对于政制之应单纯简捷者,必使之复杂纷纠,以致一切政治皆东牵西制,不能运用自如,必欲以五院院长牵制行政,且皆欲以立法院主张是从,而以立法院为国民政府之重心。”(杨天石:《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也有人认为,胡汉民主张净化党治,训政期间国民党应继续一党的统治,而不使他人参加。因此他反对蒋介石对于新约法中扩大政府基础的主张才有约法之争的。(参见成台生著《胡汉民的政治思想》,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9月再版,第123-124页。)
(16)《蒋中正总统档案之事略稿本》(12),1931年9月—12月,(台北)“国史馆”印行,第80-81页。
(17)《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9月21日。
(18)《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9月22日。
(19)《邵力子报告》,《国闻周报》第8卷第39期,1931年10月5日。
(20)《京粤和平决心》,《国闻周报》第8卷第39期,1931年10月5日。
(21)《蒋中正总统档案之事略稿本》(12),1931年9月—12月,(台北)“国史馆”印行,第127页。
(22)《京粤合议颇乐观》,《国闻周报》第8卷第40期,1931年10月12日。
(23)《蒋胡晤谈时局急转》,《国闻周报》第8卷第41期,1931年10月19日。
(24)《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0月14日。
(25)《汪等发表谈话》,《国闻周报》第8卷第42期,1931年10月26日。
(26)《蒋氏飞沪晤汪》,《国闻周报》第8卷第42期。1931年10月26日。
(27)《各方和平意见》,《国闻周报》第8卷第42期,1931年10月26日。
(28)《上海统一会议》,《国闻周报》第8卷第44期,1931年11月2日。
(29)有关上海会议的具体进程可参见金以林:《汪、胡联手到蒋、汪合作——以1931年宁粤上海和谈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
(30)《上海统一会议》,《国闻周报》第8卷第44期,1931年11月2日。
(31)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上),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9页。
(32)《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0月30日。
(33)《胡汉民演词》,《国闻周报》第8卷第50期,1931年12月21日。
(34)蒋介石:《自反录》(第二集),出版地不祥,第349-350页。
(35)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83页。
(36)《蒋介石辞国府主席》,《国闻周报》第8卷第50期。1931年12月21日。
(37)《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2月12日。
(38)《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2年1月1日。
(39)《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2年1月12日。
(40)1932年4月1日,蒋介石考虑曰:“沪案解决以后,隐退高蹈,放弃军政大权,付托于汪,勿使国内纠纷”,“如恋栈军权,事事亲办,大权独揽,疑忌异己,则收效不易。”《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2年4月1日。
(41)《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2年5月7日。
(42)《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2年5月23日。
(4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王子壮日记》第二册,1935年8月2日记,2001年,第402-403页。
(44)《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2年12月20日。
(45)《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3年3月22日。
(46)陈红民先生对宁粤和解后以胡汉民和陈济棠为中心的西南政权(粤方为主体)作了详细的探讨,分析了典型的中央与地方的冲突模式。(见陈红民:《胡汉民·西南政权与广东实力派(1932-1936)》,《浙江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标签:胡汉民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汪精卫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国民党主席论文; 历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蒋介石论文; 共赴国难论文;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论文; 国民党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