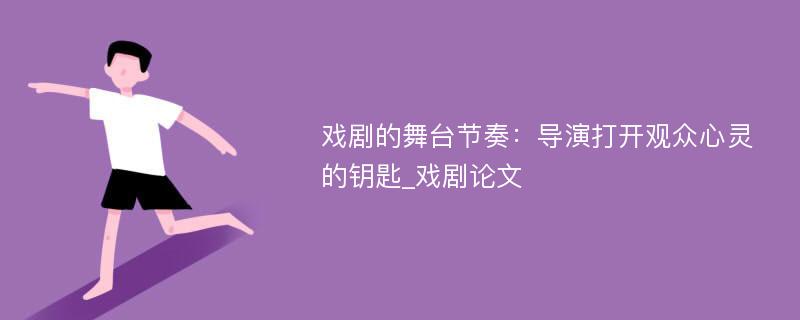
戏曲舞台节奏——导演打开观众心灵的钥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曲论文,钥匙论文,节奏论文,导演论文,观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节奏”作为音乐俗语,原本的意思是“音响运动的轻重缓急形成节奏,其中节拍的强弱或长短交替出现而合乎一定的规律。”艺术节奏的范围则更广泛,它是艺术作品的重要表现力之一,它的基本特征是建立在人的生理和心理基础上的能在艺术中表现、传达人的心理感情。但“节奏”与“和谐”又是相关联的。在古典美学范围中,“和”指的是性质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同”指的是性质相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史伯在《国语·郑语》中说过“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又说“声一无听”,就是说,单一的“声”的简单的重复,即“同”,就不能产生美,只有不同的“声”的统一,即“和”,才能产生美,所以“和谐”就是矛盾的统一。戏剧家张庚先生曾以书法的例子来说明“艺术节奏”的本质,他说一幅字的“节奏”,体现在笔墨浓淡、字体大小、布局参差等变化中。如果不注意变化,或者变化得没有章法,就使人觉得平庸,没有生气,但是如果变化没有统一的构思其作品就会显得散乱,这两种都会失去审美价值。所以,艺术作品的“节奏”,必须是辩证的统一,既要讲变化,又要讲统一,达到变化中的统一即“和谐”的美感。艺术表现的强弱、高低、主次、轻重、明暗、刚柔、起伏、动静、快慢等等都是对比的统一,都是构成艺术审美节奏的因素。
节奏是戏剧舞台打开观众欣赏心理的钥匙,观众从节奏变化中,接受戏剧情节发展的起伏和人物情绪上的抑扬。准确的舞台节奏,是导演艺术生命力的重要保证。西方戏剧虽然舞台表演的节奏基本上是等同于生活节奏(三一律),但也不是不注意舞台节奏的艺术化。比如原苏联戏剧导演梅耶荷德认为一出戏的“一气呵成”并不总是能做到的,有的时候也无须做到。所以,他的舞台技巧表现在他善于用“间隙动力”来组织戏剧行动,即高度紧张的瞬间和顿歇相结合,他认为“在高潮之间的空隙中,戏剧的原汁可以稍加淡化”。梅耶荷德说的“间隙”指的就是紧张中有松驰、浓烈气氛中有淡化。也就是说,他并不任凭舞台节奏按生活节奏原形刻模子,而是很重视把生活节奏处理为有审美价值的舞台节奏感。比起西方戏剧来,我们戏曲舞台节奏的概念,更不等同于生活节奏,由于戏曲表演的歌舞化和锣鼓音乐伴奏的制约,戏曲的舞台节奏的夸张和变形是与生俱来的。
戏曲的舞台节奏既包含速度因素,又不等同于速度。比如,有些“过场”戏,演员上、下场跑得很快,锣鼓也很紧,但观念却感到很“慢”,有些重复台词或舞蹈、开打堆砌,也使观众感到很“慢”;而另一种情况却相反:人物一瞬间的思想活动,用大段的唱腔或舞蹈来表现,观众却并不感觉“慢”,这是因为它细腻地剖析了人物的内心矛盾,使观众产生审美兴味。所以,戏曲的舞台节奏的实质是戏曲观众的一种特殊的审美感受,即“审美节奏”。而且,在戏曲舞台上,所有的内心节奏,都要把它变成艺术形象,可以看得见,可以听得着。戏曲观众习惯于矛盾的大起大落和对比鲜明而强烈的节奏感,如果停留在某一种定势的节奏上,观众会感到审美疲劳。我国清代戏剧家梁廷并在其《曲·卷二》中说,戏的“布局排场”要“浓淡疏密相间而出”,即戏要注意节奏的对比,才能达到耐人寻味的审美效果。为达到浓淡咸宜、跌宕有致、刚柔相济、喜愠分情这样理想的节奏感,戏曲导演必须事先对情节的张与驰,气氛的冷与暖,情感的刚与柔,表演形式的“文”与“武”,开打(或舞蹈)的各段样式和篇幅变化等节奏,有个总体的构思。
戏曲是综合艺术,它的舞台节奏感是剧本、音乐、舞美、表演等多种艺术奏的有机综合,换句话说,是声、光、色、形、表演、空间等变化的有机综合。为达到预想节奏总体构思的艺术效果,导演要从“构思”出发,对各艺术部门分别提出创作要求。如同交响乐的指挥,对乐队的各个分部提出要求,使其纳入“总谱”的轨道。这是贯穿整个二度创作过程的一外个重要的环节。
一、剧本节奏
关于剧本节奏,有人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作曲家笔下的乐曲节奏(速度)用符号标明;而剧作家则把剧本的节奏隐伏在描写之中。剧本的节奏是舞台节奏的基础。为了使未来的舞台节奏感流畅,导演要根据总体节奏构思,反转来对剧本进行必要的调整,使剧本节奏为舞台演出节奏奠定良好的基础。剧本节奏决定于戏剧冲突、风格、情节、台词等因素。
1.戏剧冲突
戏剧冲突是决定剧本节奏最主要的因素。当代观众青睐于情感冲突的戏——包括外部的人物关系的冲突和内心的情感冲突。
有“戏”则长,无“戏”则短。对于纯属于交待性的没有戏剧冲突的情节要浓缩或调整,而应该有“戏”的地方,则应丰富唱词或念白。比如,我主演的京剧《李慧娘》(原苏州市京剧团演出)中,家人去骗裴生进府的情节,就让家人坐船手持请帖一过了之;而当裴生不愿连累李慧娘,不肯随李慧娘逃走的情节,旧本中并没有唱词,为表现的李慧娘的内心矛盾,我们增加了一段描绘李慧娘痛苦的思想斗争的唱词。由于这段唱推进了戏剧冲突,非但没使观众感到“慢”,反而得到节奏紧凑的审美效果。
历来的戏曲家都有“凤头、猪肚、豹尾”作为把握剧本总体节奏的规律。也就是说,戏的开端,进“戏”要快。要开门见山地进入戏剧冲突。法国美学家狄德罗也说:“正是第一个情节决定了整个作品的色彩”,这种直捷了当、单刀直入的节奏,能很快地吸引观众投入到剧情中来。戏的结尾要利索,不要拖拉,而要嘎然而止,给观众留下余味,否则变成画蛇添足。
传统戏也这样一种的特况,就是整出戏没有什么戏剧冲突和人物内心矛盾,比如京剧《天女散花》、《卖水》等传统折子戏,这是由于它的载歌载舞,色彩绚丽,在一些观众心中积淀了一种特殊的欣赏习惯,所以被保留至今。但这种没有戏剧冲突的戏,其篇幅经过浓缩,一般不长,否则观众也会坐不住。
2.剧本风格
风格是作者在描写故事环境和表现人物命运、性格等的一种感情上、情绪上的基本态度,也是作者的思想感情在艺术风格上的表现,是一出戏的基调,它含有节奏因素,如悲剧、喜剧、闹剧、正剧等等都能形成不同的色调。但一出戏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种情绪,一种节奏,如悲剧一悲到底,喜剧则一笑到底,那就十分单调,所以,必须赋以色彩的变化。喜剧里要挖取“悲”的内涵,比如滑稽戏《一二三,开步走》的处理,常常使人含着泪笑;在悲剧或正剧里,也可以出现某种喜剧因素。所以,一出戏的总体风格和其中某部分的色彩变化,必须掌握得恰如其分,以达到总体节奏的统一。
3.情节设置
(1)戏曲情节要有相对的完整性, 这是由于我国戏曲观众喜欢看有头有尾的戏的欣赏习惯所决定的。所以,历来的戏曲家都强调“与其长而不终,无宁短而有尾”,也就是说,一出戏宁愿短得有头有尾,也不要长得没有结局,要使观众了解剧中故事的来龙去脉,便于欣赏。
(2)情节要跌宕多姿。 由于戏曲观众一般喜欢戏剧矛盾大起大落,对比强烈的戏,所以戏剧情节的悲与喜,矛盾冲突的张与驰、低潮与高潮等,都是构成戏曲情节奏的要素,也是使观众保持欣赏兴味的要津。
(3)情节内容要注意“可舞性”。比如行路、 激情性的身段舞蹈等,都要有适当的穿插,以使“文”“武”表演得到有机搭配,为舞台演出的视、听皆宜的审美效果提供良好的基础。
(4)台词简炼。用最少的笔触表现最大有真实, 准确地表现深刻的真实,巨大有感染力和表现力。这是世界上最高的艺术的共同点。由于戏曲表现形式的歌舞化,在舞台上,角色之间的一句对白或一个细小的动作,占用的舞台时间,一般都比真实生活中用的时间要长;有时剧本上几个字的唱词经过音乐人员的唱腔设计,到了舞台上演员会唱很长的时间;一个“开打”两个字的舞台提示,导演要根据剧情,为演员(角色)设计几分钟的斗打(舞蹈)动作。所有这些都属于剧本节奏的范畴。所以,剧本作者在写戏时,就要考虑舞台表演,要给演员的唱、念、做、打(舞)腾出时间,台词——念白、唱词、舞台提示要等尽量提炼、浓缩精湛,恰到好处。明代的戏曲理论家王骥德在他的《曲律》一书中时就指出:戏曲剧本的“句法”和“宾白”(念白)“不宜重滞”、“不宜堆垛”,要求“减一句不得,增一句不得”。对于戏曲创作创作中这些好的传统经验,作为戏曲导演,我们决不能随意抛弃,而是要经过消化,应用到我们当今的戏曲剧本创作中,使我们戏曲的舞台节奏,与当代戏曲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的心理节奏合拍,得到良好的剧场效果。
二、气氛节奏感
氛围是覆盖、渗透、弥漫在舞台的一种潜在的节奏因素。它能体现人物内在的真实,能直接感受观众。“冷”和“热”是属于戏曲舞台最基本的气氛节奏。
凡戏剧矛盾冲突比较激烈,其气氛节奏基调属于“热”,即戏剧冲突处于紧张激烈的状态,如矛盾双方的唇枪舌剑、尔乍我虞,以及刀光剑影等开打场面;或者打闹戏谑、缠绵纠葛、生离死别,以及人物内心因突发因素而引起的大喜、大悲、大惊、大怒等强烈的感情渲泄等等;凡戏剧矛盾冲突比较弱,其基调则属于“冷”,即戏剧矛盾处于相对静止状态或没有戏剧矛盾的抒情状态。如人物之间的审时度势、笑谈鸿儒、吟风弄月、浅斟低吟,或者人物内心的幽思、遥念、寄情、自叹、自省等细腻情感的抒发等等。
一般来说,舞台气氛的营造与戏剧冲突相一致。戏剧冲突激烈的,舞台气氛相应的“热”,戏剧冲突减弱的,舞台气氛则相应的“冷”。但是也不尽然,有时气氛的“冷”、“热”,并不与戏剧冲突同步。比如,京剧《空城计》,尽管矛盾冲突十分激烈,人物内心感情非常激动,但外部表现却需要温文尔雅、冷静沉着,舞台气氛并不表现为浓烈,这是出于戏剧情节与塑造人物性格的需要。
根据生活常理和观众的审美心理,无论情节的基调是属于“热”还是“冷”,舞台上的气氛,不宜一个劲地“冷”或一个劲的“热”,导演要通过各种舞台手段以及对演员表演的指导,使舞台气氛“热中有冷”或“冷中有热”。这样,既可以使塑造的人物形象更为细腻、丰满,又可变化气氛的色彩,调节舞台气氛的节奏,满足观众审美兴味。
1.“冷中有热”
我国明代文学家、戏曲家冯梦龙在分析《酒家佣》这出戏所蕴藏的内在戏剧冲突时,对第25折“郭亮寻孤”作了“此处甚冷,而实能动人”的眉批,即提出要在这“甚冷”处找出郭亮这个人物的“实能动人”之处,并把它表现出来。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在他的《闲情偶寄》中,也谈到要注意“外貌似冷,而中藏极热”的地方,把戏的“冷中之热”发掘并表演出来,以调节舞台气氛。比如,传统京剧《描容上路》这折戏,剧情很简单:张广才送赵五娘进京去找蔡伯喈。这两个角色之间没有对立的戏剧冲突,也没有大起大落的曲折情节,应该说属于“冷”戏。但在京剧麟派的表演天地里,它却成了一折烩炙人口的热门戏。原因就是周信芳先生挖掘到这折戏里的“热”点,这个“热”点,就是张广才性格中的“古道热肠”,以及对赵五娘公婆一家深厚的友邻感情。通过眼神、语气、身段、节奏的处理,时时闪发出张广才对赵五娘热切的关怀之情,比如,当张广才一见赵五娘描绘的公婆画象时,一拎神,头、颈、肩、背等部位都调动起来,人物的激情,似一炉红火,熏暖了舞台气氛。周信芳先生的表演或动或静,把一切舞台动作,都“着神”于张广才与赵五娘一家命运休戚与共的情感点上,临别对赵五娘的再三叮嘱,语气一次比一次郑重,节奏一次比一次加快,真切地表现了张广才对赵五娘进京前途莫测的担心,人们似乎在凄凉的西风落叶的长安古道上,感受到张广才肝胆照人的火热心肠。冷隽的舞台意境,在张广才艺术形象的魅力中,顿时透映出一派融融的暖情,做到了“冷”戏“热”唱。从“冷”中排出了情来,格外感人。
所以,对于貌似“冷”的剧本,导演要正确把握戏所蕴藏的、内在的戏剧冲突,排出其“热”点,即使没有斗打杀代、锣鼓雷鸣的热闹场面,也可以使“观众叫绝之声,反能震天动地”。反之,如果满台刀飞剑舞,貌似热闹,但观众席中,只想“掩耳避喧”,那再“热”也是失败了。
2.“热中有冷”
历代的戏曲家阐述的“闹中取静”、“动中求稳”等都是“热中有冷”的意思。指的是人物情绪与舞蹈身段的力度、幅度、速度都要避免自始至终地处于“热”的舞台气氛之中,不止是使观众感到审美疲劳,而且会使人物简单化。以梆子戏《打神告庙》为例:这出戏的情节是敫桂英因接到王魁的休书,到海神庙向海神控诉王魁负心,因得不到解脱,悲愤“打神”,而后自尽。这折戏,无论人物的内心冲突或外部表现(水袖功)基调属于“热”戏。但是,如果只看到外部情节造成人物内心情急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人物自身性格的一面,那么戏就会“热”成一道汤。敫桂英作为受封建社会压迫和蹂躏的底层妓女,她的“打神”是一个弱者的反抗,她的思想脉络不可能直线上升,而是有层次、有起伏的。所以必须找到敫桂英在戏中的“伏”点,即“热”中之“冷”点,才能准确表现敫桂英所处的典型环境和她的典型性格。敫桂英受到无情的打击,急到要找一个能倾诉自己痛苦的地方,在她心中唯一能为她主持公道的地方就是当初王魁与她盟誓爱情的海神庙。敫桂英上场时的心情是焦急的,但因一路奔走劳累,步履身段急促中带滞缓,眼神是失神的。这段戏,人物的内心世界与外部表现比较一致,舞台气氛基本上是“热”的;到了海神像前,敫桂英历数她当年搭救王魁、王魁发誓与她相爱白头、及至眼前将她遗弃的前因后果,这里有敫桂英的回忆和反思。她的思想情绪相对来说是理念的、平稳的。这段戏,人物内心的节奏和外部节奏,比前一段戏有所缓节,舞台气氛是“凉淡”的;敫桂英的控诉,得不到海神的“回答”,她所寄予希望的偶像破灭了,控制不住内心的愤慨,便向海神发泄。这是这折戏的高潮,这时的敫桂英神志是不清醒的,所以,“打神”这段舞蹈,幅度是大的,动作是激烈的,眼神是迷蒙的,舞台气氛是“炽热”的;敫桂英从昏迷中醒来,这时敫桂英是真正清醒了。她看到的不止是一个泥塑木雕的海神,而是一个麻木不仁的黑暗世界,她在这样的世道,只能任人蹂躏,是没有出路的,于是她的心彻底冷了下来,选择了自我解脱的道路……因此,从人物内心世界到外部表现,这时的舞台气氛是最“冷”的。
沿着以上的思想感情脉络,我们看到,敫桂英的内心思想活动是呈波浪形的,也就是说,这折戏应该营造有“热”,有“冷”,“热冷相间”的舞台气氛。而且,剧中的“炽热”点,是一个高潮,而它的最“冷”点——人物的终点,也并非低潮,而是在更深沉意义上的“高潮”,更需要演员着力从人物内心深处刻划。
戏曲界有一说法,戏有“人保戏”和“戏保人”之别。一般说,需要“人”来“保”的“戏”是“冷”戏。因为“冷”戏难演,容易演瘟,要靠舞台手段成为“冷中有热”,戏的矛盾比较尖锐、鲜明,所以,比较容易抓住观众,《打神告庙》就属于此例。但是,正是由于“热”戏比较讨巧,往往疏忽人物的内心感情节奏层次,看不到“热中有冷”的点,而使舞台气氛始终处于强烈炽热状态,观众只是觉得很热闹,但人物形象却并不感人。所以,从美学层次上说,“冷”戏排得“冷中有热”固然不易,但“热”戏排得“热中有冷”更是需要艺术修养。戏曲导演应该从这个高度来驾驭舞台气氛的“冷”与“热”的辩证关系。
三、“文”、“武”戏节奏
戏曲表演从形式上看,有“文”戏、武戏之分。“文戏”一般指以唱、念、做为主的戏;“武戏”指以武打或以身段技巧为主的戏。有的整本戏中既有文戏,又有武戏,就分别称之为某一场戏是文场戏或武场戏,这是约定俗成的区分,有时界线并不那么清晰。
戏曲表演体现我国的美学思想和民族特色。一般说来,文戏侧重于声乐,以阴柔美为主,武戏侧重形体身段舞蹈,以阳刚美为主。从接收美学来说,观念一般喜欢欣赏舞台上“揉刚于柔”或“揉柔于刚”即刚柔并济的表演。那种一味捂着肚子唱,或一味炽热的翻打戏,由于表演色彩缺少变化,往往会使观众感到单调,削弱美感。所以,“文戏武唱”和“武戏文唱”是构成比较理想的舞台节奏的表演。
1.“武戏文唱”
“武戏文唱”中的“文”这个概念,从美学上说,属于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所说的:“情文”,也就是说,武戏作为审美对象,也应是表达人物思想感情的表演形式,也要求出“情”。因为武戏打得再热闹,枪花耍得再漂亮,如果不把人物内心的思想活动“交待”出来,戏的主题、人物性格也就敛迹。因此,在武戏中需要构思一定的“文”的动作语言,有机地渗入“文”戏,帮助传达人物思想感情。比如,京剧《杀四门》中,刘金定每杀一门都耍一次枪花或刀花,有的演员武功技巧不错,可就是看不出这一次次的枪花或刀花为什么而耍?是杀不出去的焦急?还是杀退了对手高兴?就应设置武打的间隙,用“文”戏——表情、身段等,把人物情感变化交待清楚。再如,昆剧《伐子都》中,导演为表现了都谋害考叔时的内心世界,设计了一个“文”戏的表演:子都在向考叔射冷箭时,两次欲放不止,虽然是两个细小的文戏动作,却鲜明地渲染了子都心虚胆怯的心理矛盾,使人物卑劣阴险的性格得到充分的揭示,观众在欣赏武技的同时,犹有回味。如果导演能补充适当的台词,则更可以激起观众的审美判断。
但要注意的是“武戏文唱”决不等于武戏“瘟”唱。在技艺上不能“偷工减料”,成为没有功夫的花架子。因为戏曲观众对武戏有一种特殊的审美要求。希望从武戏中得到英勇、豪迈、威武、雄壮、矫健等阳刚之美的享受,如果武戏没有过硬的技巧和精彩绝招,把武戏演成稀松的一碗温吞水,武戏不“武”,成了武戏“瘟”唱,这是对“武戏文唱”的误解。
2.“文戏武唱”
“文戏武唱”的目的与“武戏文唱”一样,都是要求演员在舞台上刻划人物形象时,得到更加深刻的表现,同时调剂观众的审美感受。
“文戏武唱”中的“武”,指的是演员在文戏表演中,采用武技基本功表现人物的行为动作。在传统戏里,文戏中运用武技刻划人物的例子很多。如《追韩信》中老生萧何的圆场、吊毛;《断桥》中小生许仙的屁股座子、吊毛;《贵妃醉酒》中花衫杨玉环的卧鱼、下腰;《十五贯》中丑角娄阿鼠的倒翻、窜椅子等等。近几年来,在一些整理改编的传统戏或新创作的古装戏和现代戏中,“文戏武唱”的运用也屡见不鲜,比如,徽剧《临江会》(安徽省徽剧团演出)中,周瑜听说刘备已翻身而下,哈哈大笑三声;再如蒲剧《黄鹤楼》(运城地区蒲剧团演出)中,刘备被赵云保驾安然脱离了黄鹤楼,周瑜气得一个“吊毛”滚下“楼”去。周瑜是一个能够用兵的帅才,但气量狭小,不能容人,终成不了大业而被气死,这二出文戏中的武戏动作,非常形象地表现了被世人称为“大都督小周郎”的性格特征,为塑造人物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因为文戏中揉进武戏的身段、技巧,动作幅度大,表现力强,借助它,人物的情感能得到更加强化的渲染,增加人物形象的可观性和可感性,增添人物性格的鲜明度;在表演上,武技和绝招的这些技艺性表演,具有独特的美感力量,一旦与文戏融合,就会闪烁出一种夺目的光彩,激发观众的想象力,引起审美联想,得到酣畅的美感享受。所以,“文戏武唱”,既是继承我国戏曲表演的优良传统,也是今天发展戏曲表演艺术,争取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的需要。但是“文戏武唱”也不可滥用,必须符合角色的性格、身份和规定情境,要有助于人物形象的刻划,并与整个戏的风格和谐统一,还要看演员的基本功基础,否则,用得不贴切,成为卖弄技艺,非但失去可观性,还会损害或歪曲人物形象。
四、表演的节奏感
节奏是具体的,它表现的是事物自身的客观规律。
戏曲人物的内心节奏,需要用外形的节奏把它表现出来,应当让观众看得清楚,感情的东西不仅象话剧只让观众感觉到,还要用鲜明的动作表现出来。戏曲表演以“神似”为审美追求,以歌舞为表演手段,都是生活节奏的夸张和变形。观众通过对歌(唱、念)和舞(做、打)的审美,来感受人物的思想感情。所以,演员舞台表演的节奏感,直接干系着观众的欣赏情绪。有的演员不理解服从全剧总体节奏的重要性,只考虑发挥自己的唱、念、做、打的独立欣赏价值,常常疏忽其篇幅和节奏在总体节奏中应占的比例,因此影响了舞台节奏的总体把握,使全剧枝蔓横生,观众看了,不得要领,而感到乏味。因此影响总体节奏感和人物性格的塑造。所以,必须要从全局出发作细腻的安排。
1.“唱”的节奏感
首先要把握各段唱在整出戏中的位置,考虑各段唱腔应占的篇幅,然后进入唱腔设计。
戏曲唱腔有调式和板式之分,调式根据人物的情感色彩而取向,如京剧中的西皮宜于表现昂扬、喜悦等情感;二黄则宜于表现悲怆、深沉等情感。板式根据剧情进展,有快、中、慢之分;还有,行腔也有一个长度问题,这些都有关戏剧的节奏感。所以,整出戏中各场的唱段和同场的唱段,其调式、板式和行腔的旋律,都要根据总体节奏和唱词内容进行有机的搭配,要有色彩变化。否则会影响抒情,并使观众感到节奏不流畅。
对每段唱腔都要细致地进行艺术处理,尤其是大段的唱,要根据词意的感情作细致的变化,以达到传情。以我导演的《梦蝶劈棺》(河北省梆子剧团演出)末一场28句的大段唱腔为例:田氏上场时的唱词是:“王孙呼求声不断,倒叫我……心乱如麻、进退两难”,我处理为:第一句作为“倒板”在幕内唱,第二句在上场后唱“回龙”板,在最后“难”字上给一个长拖腔。这二句的节奏比较急切,是为了表现人物难于决断的矛盾心情。接下来是表现她回忆与庄周共同生活时的四句唱,其中唱“也曾同栖一屋檐”这句时,我在旋律上用“中速”,“檐”字腔往下落,不拖腔,因为她与庆周还是有感情的,不能太快,要为下一句“劈棺取脑心不安”的沉重心情铺垫。但唱“如今公子性命悬一线,不救王孙心不甘”这二句时,节奏马上加快,“甘”字的腔昂扬起来,因为这是她眼前心急如火的事;待唱到“但听邻里道长短,纲常礼法词正严”时,则用“紧打慢唱”的节奏,这是她考虑到“劈棺”后舆论的压力,是紧张中的间断思索,所以,接下去是连续三句的唱:“怎么办……”然后通过四甸节奏比较低沉缓慢的唱“无奈只把庄周喊,你在棺中可见怜……你曾说男婚女爱本自然……”,唱最后二句“只要公子命保全,千秋骂名我承担。”时,因为这是田氏经过矛盾、思考等思想斗争以后,下决心要劈棺了,所以节奏急促、由原来的原板转流水板和瑶板并用了一个长的拖腔,在高昂的旋律中结束。这样,通过快慢相间、时紧时松的板式节奏变化和唱腔旋律处理,使田氏的内心矛盾得到强化,同地时也为编排身段打好基础。
需要再说一下的是:唱腔的节奏处理,还包括每句拖腔的长度的安排,首先要开导演员,使他们懂得个中的美学要义。我在导戏过程中,曾遇到一位嗓子很好的演员,她希望在一句慢板中拖两次长腔,这是她不懂得这句唱词是叙事性的,并非情感很浓的内容,不需要这样夸张渲染,拖两次长腔会把戏唱松。所以,说服演员能服从总体节奏,也是导演工作中常会遇到而必做的一项工作。
2.“念”的节奏感
戏曲的念白是诗化的散文,在戏曲综合的总体节奏中,念白的节奏,是与歌(音乐唱腔)舞(动作身段)的相谐调的“韵律”化的节奏。我国古典戏曲理论认为:“说白固须字字清楚,不可含混,然而要分出阴阳、轻重、急徐,按其文之缓急,查当时之情形,应念急则急,应缓则缓,方为上乘。”(清·黄幡绰《梨园原》)这就是说,戏曲念白的节奏不能“一顺边”,一个劲慢了不提神,一个劲快了则不扰神,要根据不同人物、不同的思想感情,掌握高低、抑扬、缓急、顿挫等变化幅度,才能节奏鲜明,重点突出,铿锵动听而又传情。比如,在《四进士》这出戏中,宋士杰首次与顾读交锋时,有一段长达三十句的念白,周信芳先生在念诵时的节奏处理可称典范:开始的叙述,念得比较平淡、舒展;继而一边编话一边说,则语气稍稍拖长一点;后来对自己已经编熟的话就念得很流利;到最后他自己发挥出来的话,更是念得振振有词,越说越快,几乎是一口气喷出来的;当这大段念白收煞时,特别加重语气,拖长音,顿挫十分有力。中间还把它切成了四十多小节,凡是要强调的地方,都先作一个停顿,比如在“曾记得那年去往河南上蔡县办差”一句中,他在“曾记得”、“那年”、“去往”、“河南”之后,各作小顿,表现这个打官司的老行家能够杜撰对词,边想边说的老谋探算。周信芳先生从体验人物出发,鲜明准确地表现了规定情境下人物的心理节奏,使这段念白维妙维肖,精彩绝伦。
念白的节奏性,还体现在与锣鼓的配合上。在京剧麒派的《乌龙院》中,周信芳先生扮演的宋江和阎惜姣吵架出门后的大段独白,连用了二十三记大锣,而且,都是“冷锤”,随着语义词情的变化,有时用硬锣,有时用软锣,节奏感得到夸张,十分有力的烘托了宋江的起伏的感情(陶雄《评周信芳的艺术道路》)。
3.“做”的节奏
“做”包括身段、技艺和神情。通过“做”的节奏变化,突现动作的典型意义,塑造人物性格。比如《坐楼杀惜》中:宋江要看阎惜姣正在缝的鞋,阎惜姣慢吞吞地把鞋递过去,宋江正要接手,阎惜姣突然干脆地把鞋往地下一扔;宋江向阎惜姣要招文袋,阎惜姣懒洋洋地把招文袋拿出来,宋江刚要接袋,她也是突然往地下一扔。这两个扔的动作,前一个是阎惜姣不情愿把鞋给宋江看;第二个是她已胸有成竹,故意捉弄宋江。都是运用节奏的对比变化,使这两个丢鞋的动作显得十分典型,勾勒阎了惜姣的刁钻和阴险的心理。
身段、技艺的篇幅也会影响节奏感,所以,要按总体节奏来安排:
(1)身段的疏与密:伴随唱、念的身段或舞蹈的身段, 都要安排得有宽有窄:何处需要密,何处需要疏,何处多动,何处少动,这种有意识的相间处理,就能做到疏密有致,避免节奏感平淡。
在抒情的唱段中,不宜采用过分强烈的舞蹈身段,但也不等于身段空白,应该多运用眼神、身段造型、神情来传神,使动作“疏中有密”。
(2)技艺的篇幅:剧中所有角色的每一段身段技艺的篇幅, 都要根据规定情境和总体节奏来设计。一是要注意篇幅的长度要适宜,如果太短了,观众不够过瘾,但是太长了,会使戏拖塌。比如,角色得胜后“耍枪花”的情绪性虚拟程式,过长过短都会破坏整体节奏。对于想多卖弄技艺的演员,导演一定要做说服工作,因为技艺的无限发挥,占时间过长,会使戏的进展有中断感。有一次我为某剧团排《李慧娘》,扮演明镜判官的演员,希望把传统“跳判”的程式全部用上,我没同意,并说服他服从全剧的总体节奏需要;二是舞蹈本身要注意节奏变化,技巧不能准砌,以至使观众感到眼花撩乱,冲淡所要表现的内容和角色性格特征,把内容和感情全淹没,要“密中有疏”。
神情的起伏也属于“做”功,是塑造人物性格的有力的手段。戏曲表演中,人物的“神”,是由面部表情传达出来的。戏曲的神情表演是生活的夸张、变形,成为有音韵律感的、有美感的面部表情程式。如川剧的欢、笑、喜、乐、愁、想、思、悲、哀、忧、哭、气、怒等,都有程式,京剧也有如旦行的哭“喂呀”、花脸的怒“哇呀呀!”、表现笑的“哈哈、哈哈、啊哈哈……”等表演程式。戏曲表演要体验与表现相结合,演员必须设身处地地体验角色的感情,使表演“情动于衷而形于外”,才能避免程式化而创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演员如果缺乏内心体验,或者由于体验的不够准确和细腻,使人物自始至终只有一副面孔,缺乏神情变化,影响人物性格的塑造。比如,有一出京剧《窦娥冤》,窦娥绑赴法场这段戏,窦娥从头至尾哭得涕泪满面,台下观众却并不因她的“卖力”而感动,因为人物始终只有一种表情,使人看得很厌烦,反而认为演员的表演非常虚假。
(1)强烈的外部戏剧冲突,神情起伏要夸张。 仍以周信芳先生主演的《青风亭》为例:剧情是张继保中了状元,路经“青风亭”,他的养父张元秀闻讯赶来认子。周信芳先生的表演是:张元秀和老伴满怀希望、喜悦的表情上场,先把舞台气氛推到一定的高度:当张继保狠心不认养父养母,只扔下两百小钱打发二位老人,张的老伴愤而致死,张元秀悲愤填膺气得说不出话来……周信芳先生表现人物此时无言的控诉,其表情是:在“乱锤”的锣鼓点子中,眼含泪花抽泣着;身体和髯口大幅度地颤抖,一手握钱,一手指天、指地、指屈死的老伴、指禽兽不如的养子……这场戏中人物的神态表情,前后形成鲜明的对比,表达了人物在这个人世间无处渲泄的满腔痛苦和悲愤,艺术效果强烈而生动,虽然没有一句台词,却胜过千言万语,具有雷霆万钧之势,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观众无不为之动容。
(2)微妙的戏剧冲突,神情要有细腻的变化。 要从捕捉人物内心世界着手,通过神情变化构成情感节奏。比如,在京剧《坐楼杀惜》中,阎惜姣与张文远正在乌龙院私会,宋江来到乌龙院。同样是“笑”这个表情,扮演阎惜姣演员赵晓岚运用不同的“笑”的神情,准确而细腻地刻划她阴暗的心理活动:阎惜姣见宋江上下打量自己,心里有慌,脸部发僵光动嘴角,极不自然地笑了笑,这叫皮笑肉不笑的“僵笑”;宋江看了她正在做的鞋,一语双关地说:“颜色不对呀!”阎惜姣马上抢过了鞋,似笑非笑地在喉咙里短促地“哼”了一声,这叫“冷笑”;阎惜姣继而一想,自己究竟还在吃他,穿他,而且张文远还躲在内室,心里毕竟很虚,想哄走宋江,又自我解嘲地在脸上堆起一付笑容,假作轻松敷衍宋江,这叫“假笑”;当宋江向阎惜姣要招文袋,阎惜姣撇着咀,眼睛斜视着宋江的笑叫“讥笑”;阎惜姣逼宋江写完休书,急不可待地扑向桌子抢休书,不料休书被宋江抽走,她扑了个空,有些窘迫地用造作的献媚神气,眼睛特别有神地瞟着宋江的笑叫“媚笑”;阎惜姣欲致宋江于死地,不还梁山的信,宋江气急,当胸一把抓住她,阎惜姣睁圆眼睛斜盯住宋江,抄撇着嘴,咬紧牙关,用鼻音哼出的笑叫“狠笑”。通过这用一连串“变脸变色”的笑构成了这出戏一连串的情感节奏,使观众层次分明地感受到人物微妙的心理活动,推进了剧情的进展。
(3)亮相是现实生活本身的节奏的夸张, 它不意味着生活的中止,而是一种静中有动的无言的动作。有时表现一种刚刚经过的内心纷扰,有时表现一个正要来临的情绪的爆发,有时是一种紧张的期待,有时是人的意志、精神状态的外化。
4.“打”的节奏
“开打”是戏剧中矛盾着的双方矛盾激化到刀枪相见的表现。有的戏其情节以“开打”为主,如昆剧传统戏《挑滑车》、京剧《三岔口》、《伐子都》等。有的“开打”则只是整出戏中的一个情节。“开打”具有阳刚美,使人产生亢奋感,运用得得当,能帮助把戏推向高潮。但“开打”要根据剧情,在篇幅、形式、神态、速度、奏等方面把握住“度”,并要打出感情来。
“开打”的篇幅。“开打”的演技以功架、舞蹈、斛长、把子等武技为主,动作强烈,气氛炽热。所以,篇幅不能无限延长,不可使观众长时间维持在同一种亢奋的感觉中,会影响剧场气氛的调节。
“开打”的形式。“开打”挡子的编织,如“群挡”、“单对”等形式要交叉运用,避免重复,可穿插滑稽开打,调节气氛;把子、跟斗等要讲究技艺性,但要简而精,难度要由简向繁步步升高;“挡子”要在传统程式的基础上创新,太陈旧会影响审美。
“开打”的神态、速度的变化。比如《八大槌》中,陆文龙分别与四个槌将的四次“开打”,就要根据人物性格,表现他非凡的武功和孩子气,要越打越称手,越打越有劲,越打越得意,这样在神情和速度上就会有层次,打出不同的神态,打出节奏感。
“开打”要打出感情。“打把子”的刚、柔、快、慢均是情感节奏的外化。尤其是连唱带打的戏,尽管技巧有难度,更不能疏忽内心体验,要打出人物情感的层次变化。我主演的传统京剧《白蛇传·盗仙草》(原苏州市京剧团演出)这场戏,是学习关肃霜老师的路子。情节与一般演出的路子没有大的区别。但是,关老师的路子中,白素贞“求”仙童时,有一段连唱带打的表演。我根据这段唱的感情层次,对这段载歌载舞的表演节奏分以下层次:鹿童不允白素贞的请求,用剑向她刺去,白素贞被迫拔剑架住,继续求鹿童,唱:“为什么苦为难,仙翁应有慈悲念,替人间解为难”,唱腔较急促,并用剑轻轻抵开仙童的剑;仙童不顾白素贞拜求,继续以剑向她进逼,白素贞步步退挡,并继续哀求,接唱:“可怜我丈夫生命断,我云山万里求宝丹,只要求得回生草……”这段唱腔比较柔慢,抒发悲伤的感情;接着,白素贞眼神思索后,怀着犹豫和心虚,急急闪过仙童,偷摘灵芝仙草,却被截住;白素贞感到无望,慢慢回身下山;当猛想起许仙命在旦夕,又急返回再跪求鹿童;仙童毫不心动,又以剑相逼,白素贞决心以武力夺取灵芝仙草,连打带唱:“休得要跃武扬威呈凶蛮,宝剑一举寒光闪,为夫君拚性命,不盗仙草誓不回还!”这几句唱腔伴随着开打,一腔一调,一招一式,节奏明快、干脆、有力度,表现白素贞宁死也要夺取仙草的决心。
5.行当的节奏
不同性格的人有不同的外部和内心运动的节奏规律。戏曲的行当程式,蕴含了某一类人的性格特征和动作节奏的规律。行当程式是戏曲演员塑造人物的物质手段,它的外部形式的典型性很强,行当之间的表演色彩的区别十分鲜明,包括音色、声腔、身段等。一出戏的行当色彩区别,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审美节奏。所以,一出戏里的行当不宜太单调,排练前分配角色时,导演要注意行当的色彩差别,如果行当不单调,舞台表演色彩也就会显得丰富多采。比如,我导演的《闯法场》(石家庄评剧院演出)中的知府和知县官,原先都是老生行当,两个角色表演手段相仿,因此给突出人物性格造成困难,两个人物形象都难以鲜明。改编剧本时,作者陈牧为了区别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差异,把县官的行当改为丑行,把他的台词赋以丑行幽默诙的语气。排练时,要求演员挖掘戏剧冲突和人物性格中的喜剧因素,运用丑行夸张甚至变形的程式来塑造人物。这样,他与其它人物的行当表演形成较大的差异,使整个舞台表演色彩显得比较多姿和活跃,各个人物形象也相对地更加突出、鲜明。
五、伴奏、舞美、灯光节奏感
构成戏曲舞台节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舞台物质因素的处理。包括伴奏、灯光、布景等变化的综合。通过其动静、强弱、明暗等处理,起到烘托气氛节奏和外化人物心理变化的作用。
1.伴奏
音乐音响效果,可以显示人物心情和显示内部节奏。也就是给予观众以听觉的直接影响或暗示,用来影响促进舞台节奏(气氛)的有力手段。二度创作首先要根据剧本的主题、体裁、人物性格等,设定整出戏的音乐气氛的基调,但是,无论是“大江东去”的气势,还是“小桥流水”的情调,都要避免从头至尾维持在一种氛围中,否则会使观众感到单调。近30多年来,西洋乐介入戏曲文场,导演要根据戏的体裁和规定情境等来判断是否需要运用,否则艺术效果会适得其反。
戏曲音乐中,锣鼓是一个重要的特色,它能突现和强调人物的心理节奏和感情的变化,所谓“一打节奏,二打感情”。武戏或舞蹈场面的伴奏,要避免自始至终音响强烈的锣鼓点,否则会“闹”得观众坐视不安。比如京剧《四杰村》,大约15分钟的“开打”,传统的锣鼓点子用的几乎全是“急急风”的点子,“闹”的时间很长,使观众听得吃不消。所以,“开打”场面,器乐伴奏要多样化,可用锣鼓点,用音乐,或音乐中混进锣鼓或穿插“静场”即无伴奏等多种样化处理,使观众得到甜美的享受。
明代汤显祖对表演艺术要求:“微妙之极,乃至有闻而无声,目击而道存。”指的是在无台词无伴奏的“静场”中,通过演员的形体动作表现人物内心活动,充满了“无声的语言”,使观众清楚地看到角色的精神世界,以及角色的思想意念、内心活动。举一个运用“静”与“闹”的反差来强调气氛的例子:传统戏京剧《乌龙院》中,宋江急急上场,进门上楼寻找招文袋的前一段戏,运用强烈的“乱锤”的锣鼓点;而后一大段回忆思索的戏,则全部用身段动作表现宋江的回忆,这段戏无台词、无伴奏,完全是静场处理,强烈的反差,所以,使这前后两段戏都得到了强调,并增强了紧张的气氛:
2.灯光
戏曲舞台的灯光,一般来说,以照明为主,新编的戏中,也努力探索舞台灯光的应用,通过色彩、切光、明暗、聚收、特写、光圈等变化,表现情调的变化和构成气氛节奏的对比,来达到造型、寓意的目的。
我主演的《李慧娘》(苏州市京剧团演出)中“见判”一场戏,全场黑暗,只有照射李慧娘的一束追光随之流动;当好心的判官赠她阴阳宝扇,助她去人间救裴生,李慧娘的白色云肩、长裙变成绿色的瞬间,灯光顿时大亮,舞台由漆黑顿时变得满台生辉,烘托了李慧娘从阴间能返回人世救裴的喜悦心情,这种强烈的明暗对比,把舞台气氛推向高潮;再如,我主演的京剧《百花公主》(原苏州市京剧团演出)的“赠剑”,当百花公主坠入海俊的情网时,顶光变为红色,呈暖色调;“哭陵”这场戏,百花亲手杀了奸细海俊,蓝色侧逆顶光衬托百花公主心中的仇恨,构成悲剧的韵味,色彩的对比形成人物前后遭遇的鲜明对比;再如,京剧现代戏《红灯记》(中国京剧院演出)中,铁梅坐在桌前,对着号子灯沉思,开唱“听罢奶奶说红灯”前,随着铁梅捻亮号子灯,舞台灯光由暗变亮,寓意铁梅听了奶奶说家史,心里豁然亮堂,真正的成长了,灯光在这里隐喻了剧情的内涵,体现了革命自有后来人的主题。
3.布景
布景的纱幕、平台、吊挂、天幕、布景质料,以及“二道幕”的开闭或升降的快速、缓慢、或先慢后快、顿息开闭等变化,都能构成不同的节奏气氛。
布景也可以通过色调的变化,渲染气氛节奏变化。比如上海沪剧团演出的《明月照我心》,描写一个教师领养几个孩子的一片爱心。占领天幕四分之三的大月亮每幕根据情节改变色彩,达到很好的示意人物心绪,构成气氛转换的节奏感。
尽管导演按预想的“构思”分头要求各艺术部门进行创作,但是,各艺术部门在具体创作时,难免与导演的“构思”相碰撞,而且,部门与部门之间也会有矛盾,导演就要做谐调工作,同时,也要对自己的“构思”不断进行修正,以求逐步完善。只有在完成排练时,导演的“构思”才算真正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