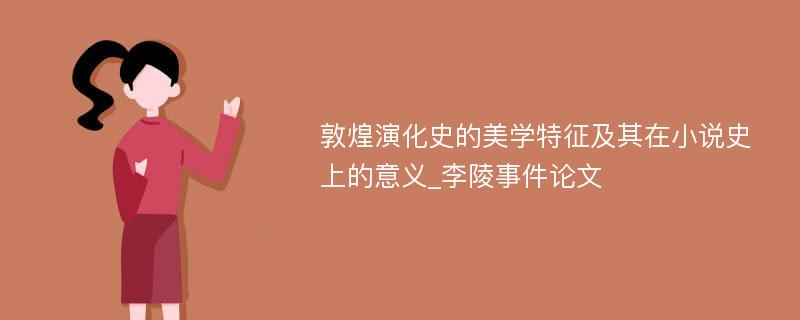
敦煌演史类变文的美学特征及其小说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美学论文,特征论文,意义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中国古代通俗历史小说起源问题,有起源于汉代、起源于魏晋等多种说法。但由于迄今发现的资料有限,这些说法多带臆测性,故而也就不见得准确可靠。而现存的敦煌变文,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实证。因为变文当中存在不少讲唱历史题材的作品,如《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文》、《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前汉刘家太子传》、《韩擒虎话本》、《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等等,它们在题材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皆与后世的讲史平话、历史演义有着一定的关联。所以,本文不打算将通俗历史小说的源头溯得过远,姑且将这些演史类变文视为我国通俗历史小说的滥觞,并由此入手来探讨它们在思想旨趣和艺术形式上的美学特征及其对后世历史小说的影响。
一
变文最初是僧徒俗讲(即面向俗众演说佛经)的文本,其得名,乃因其文讲述佛诸菩萨神变及经中所载变异之事。后来,一些非僧徒的民间艺人因见俗讲甚受民众欢迎,且有经济效益可图,遂亦取鉴俗讲的形式,选取一些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来加以敷衍,以求招徕听众,敛财糊口。如晚唐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就记载说:“妖姬未著石榴裙,自道家连锦水濆。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说尽绮罗当自恨,昭君传意向文君。”由诗中内容可知,这是一位色艺俱佳的女艺人正在搬演《王昭君变文》,说唱配合,不惟形象可感,且声情动人。而王建的《观蛮妓》亦有类似记载:“欲说昭君敛翠蛾,清声委曲怨于歌。谁家年少春风里,抛与金钱唱好多。”
这大约可以说明,当时俗讲已经由寺院斋会逐渐走向民间闾巷,讲唱内容也由佛经故事延及历史传说。也许正因如此,今存的演史类变文,才显得宗教意识甚淡,世俗气息颇浓,民间的道德色彩、观念情绪灼然可见。
例如,《伍子胥变文》讲的是伍子胥逃难、复仇的故事。该故事就表现了民间浓厚的反暴君情绪和有仇必复、有恩必报的价值观念。故事中的楚平王荒淫好色,谋娶子媳,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听信谗言,残害犯颜直谏的忠臣伍奢及其子伍尚,悬赏缉拿在逃的伍子胥。这种暴虐无道的行径,激起了民众的普遍义愤,他们非常同情伍子胥的不幸遭遇,所以在伍子胥逃难的过程中,浣纱女、渔父等平民百姓不贪楚王重赏,不避官府诛戮,先后仗义相助,慷慨赴死,激励子胥为父兄报仇。后来,子胥辅助吴王富国强兵,吴国百姓皆争先恐后愿为子胥报仇雪恨。子胥在民众的广泛支持下终于率兵破楚,捉住了昭王。面对昭王,他先是愤怒谴责其父平王谋娶子媳、宠信佞臣、杀害忠良的罪行,然后便破坟开棺,取得平王骸骨,以剑斩之,“其骨随剑血流,壮似屠羊”,又“取火烧之,当风扬作微尘”,并将昭王剜心斩首,以祭父兄。这种极其残忍的屠杀、报复行为,当然不可能出自以宽容、慈忍为本的僧徒之口,也不大可能为秉持忠君观念的封建正统文人所作。实际上,伍子胥以一个臣子的身分向君主复仇,并且痛鞭平王之尸的举动,向来就为正统史家和儒士们所诟病,他们自然不会再恣意虚构出比鞭尸更为过分的斫骨扬尘、剜心斩首的情节。这只能是民间艺人的创造,反映的是平民百姓痛恨暴君、快意恩仇的心理。伍子胥在报了仇之后,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报恩之举。他先是念及渔父救己之恩,停止讨伐郑国,并册立渔父之子为楚帝,后来又在浣纱女抱石自沉之处,投下百金,进行祭祀。这种看似荒诞之举,正是“有恩不报,岂成人也?有恩若报,风流儒雅”之民间心理的形象写照。所以,该变文应该是民间艺人演史的产物,反映的是民间的观念情绪。
与之相类,《李陵变文》也当出自民间演史。该变文演述的是爱国英雄李陵被君王误解、抛弃、迫害的悲剧。李陵本为汉代名将,与匈奴作战,孤军无援,箭尽粮绝,投降匈奴,实出迫不得已。但是,汉武帝却毫不留情地将其一家全部斩杀,这未免有点冤屈。所以,自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其鸣不平以来,同情李陵者代不乏人。而变文作者则更将真诚的怜悯和理解植入人物内心,以蘸满情感色彩的笔调,在赞美李陵英勇善战的同时,揭示了他强烈的忠君爱国之心。文中写道:“李陵弓矢俱无,勒辔便走,捶胸望汉国,号咷大哭。赤目明心,誓指山河,不辜汉家明主。”可见,身处绝境的李陵,对“汉家明主”是多么忠心!后来,他接受手下将领劝求,投降匈奴,更是为了“先降后出,斩虏朝天”。这样写,就不仅涤除了李陵降敌的耻辱,而且还赋予此举以悲壮、可敬的忠君报国色彩。同时,变文对于汉武帝残忍寡恩、屠戮李陵一家,不加掩饰地作了谴责,说李陵老母妻儿被害时,“日月无光,树枝摧折”,上天都为之变色,并且还让李陵悲愤地唱出“今日黄天应得知,汉家天子辜陵得”的诗句。这在封建统治阶层看来,无疑是大不敬的,但它却是变文讲唱者顺应民众的情感和认识,对历史人事所作的重新叙说和评价。
在《汉将王陵变》中,我们也可看到作者站在民间立场上,对残忍无道之君项羽的抨击,对虚伪狡诈、犹疑怯懦的刘邦的揶揄,对谋略多端、奇袭制胜的王陵及深明大义、不惜自我牺牲的王陵之母的推崇和赞誉。而《前汉刘家太子传》写汉太子逃亡民间,得一耕夫相救,耕夫将他埋于地下,口含七粒粳米,嘴衔竹管出气,得以避难的情节,当亦出自民间的历史传说。至于《韩擒虎话本》,极力夸饰一个十三岁的少年英雄为隋灭陈、慑服突厥的智勇武略及其建立的不世之功,更带有鲜明的民间色彩。此外,《王昭君变文》、《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等所抒写的心向汉唐、抵御外侮的民族思想情感,也可以说是真切地表露了处于异族侵凌之下的边地民众归心大唐的强烈心愿。
现存的敦煌演史类变文,基本上可以视为替世俗民众写心的文本。它们的世俗气息和民间属性,决定了其创作者和讲唱者最为可能是在民间。尽管后来可能有僧徒参与讲演,也有一些文人来加工、润色,但是它们所展示的仍然是世俗民众的精神世界,体现的主要是世俗民众的审美趣味。
二
敦煌演史类变文虽然以历史人事作为其重要的题材来源,但由于其叙事旨趣主要在于迎合世俗民众的文化心理和审美口味,所以其讲唱者就不可能谨依史书上粗疏、提要式的记载,而是尽可能地在史事的框架内进行大胆的夸张和虚构,加进新奇、怪诞的故事情节,掺入鲜活可喜的野语村谈,甚至不惜改动历史,以求耸动听闻,获取市场效应。这样,历史人物、事件便在不同程度上被神异化、传奇化和戏剧化了。
先就主要人物而言,变文的艺术旨归就是要塑造为世俗民众所崇尚、追慕的英雄,展示其不同凡响的性格、命运。为了达致这一目的,讲唱者难免要夸大其辞,张皇神异。如《汉将王陵变》说王陵去劫楚营,只带了三百人,突入项羽六十万大军之中,纵横驰骋,致使项羽手下“二十万人总着刀箭,五万人当夜身死”,而王陵却不折一兵一卒。《伍子胥变文》说子胥冲杀楚军,“剑锋交横,抽刀剑吼,枪沾汗血,箭下獐狂。尘土张天,铁马嘶灭,一死一进,唯努唯前。各办杀心,终无退意。西军大败,遍野横尸,干戈不得施张,人人重重相压。子胥十战九胜,战士不失一兵”。《韩擒虎话本》为了突出韩擒虎的智勇超凡,把他说成十三岁的少年,善用奇计,惯摆奇阵,箭术出奇的高明,一个人就完成了灭陈、定边的历史重任。凡此,皆披露了民间艺人天真好夸的特性。此外,他们还爱将英雄人物神化。如韩擒虎,由于建立了不朽功勋,临终时,地府里的五道大神就赶来请他去作“阴司之主”,他在辞别隋文帝时还说:“若有大难,但知启告,微臣必领阴军相助。”然后,“摸马举鞍,便升云雾”而去。有时,就连英雄使用的武器,都带有神异色彩。如伍子胥将佩剑掷于江中,“剑乃三涌三没,水上翩翩。江神遥闻剑吼,战踔涌沸腾波,鱼鳖忙怕攒泥,鱼龙奔波透出。江神以手捧之,惧怕乃相分付”。这样的描述虽然荒诞,但在彼时俗众的心目中,真正的英雄就应该是与神相通的,故民间讲史鲜有不渲染英雄之神术异能的。
不过,英雄们虽然本领非凡、神异,但是他们也同样具有普通人的思想情感,诸如忠君、爱国、孝亲、重义等,只是他们的情感比起一般人要深厚、博大一些,往往带有慷慨、凄怆的悲剧色彩。变文的讲唱者通过对英雄人物内心情感及其艰险处境的着意渲染,使当时的听者不知不觉地走进了英雄人物的精神世界,与人物的悲剧命运连在了一起。如《伍子胥变文》说子胥得浣纱女救助之后,继续前行,一路上“风尘惨面,蓬尘映天,精神暴乱,忽至深川。水泉无底,岸阔无边。登山入谷,绕涧寻源,龙蛇塞路,虎狼满道,遂即张弦。饿乃芦中吃草,渴饮岩下流泉”。后来,救他的渔父又覆船而死,他禁不住悲歌而哭:“大江水兮淼无边,云与水兮相连接;痛兮痛兮难可忍,苦兮苦兮冤复冤。自古人情有离别,生死富贵总关天,先生恨胥何勿事?遂向江中而覆船。波浪舟兮浮没沉,唱冤枉兮痛切深,一寸愁肠似刀割,途中不禁泪沾襟。望吴邦兮不可到,思帝乡兮怀恨深……”像这样的景物描写、心理刻画,无疑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力量,使听者切实地感受到了英雄人物身上深厚的人情味,而不至于把他们完全当成可敬而不可近的神明般的超人。其他如《王昭君变文》、《李陵变文》等,都具有令人共鸣的艺术效果。
与塑造英雄人物相适应,变文的作者和讲唱者对于故事情节的编排和建构也极为重视,总是有意识地将历史事件故事化、传奇化。例如,按《史记》记载,王陵的事迹是这样的,他在“高祖起沛,入至咸阳”时,曾“自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及汉将之还攻项籍,陵乃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为老妾语陵,谨事汉王。汉王,长者也,无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剑而死。项王怒,烹陵母。陵卒从汉王定天下”。这件事本身并无多少故事性,但变文却以此为基础,一方面进行虚构、增衍,一方面又加强了事件之间的因果关联:先说楚汉两军对峙,汉军屡战屡输,王陵与灌婴因奏请刘邦偷斫楚营,致使楚军损失惨重。项羽大怒,就用钟离末之计,捉拿陵母,命其作书招陵。适逢汉使卢绾到楚营来下战书,得知此事,回禀王陵。王陵急与卢绾同到楚营救母,陵母闻之,怕其子枉送性命,遂口承修书招儿,因借项羽宝剑,自刎而死。经过这样的改造,历史本事就变成了一段曲折惊险的故事,有力地烘托出王陵智勇非凡及其母大义凛然的英雄性格。又如《捉季布传文》,乃本诸《汉书·季布传》而演绎,但史书文字平直,故事性弱,而变文所写,则不惟故事性强,而且情节跌宕起伏,极富有戏剧性。写季布为刘邦通缉,到处藏身,一时险象环生,几乎陷入绝境,但后来听说来捉他的是大侠朱解,又感到绝处逢生。等他得到刘邦赦宥,赶来觐见时,不料刘邦忽忆前愆,突令武士擒捉,欲置之鼎镬,季布大声抗议刘邦谩语诓杀自己,刘邦这才回嗔作喜,终释其罪,拜其为太守。可见,本来是一段死历史,一经变文的转化,就变成了一出活戏剧。
除此之外,变文讲唱者还喜欢在史事的框架内加进一些新奇、怪诞的情节片段,以增强故事的神秘感。如《李陵变文》写李陵欲与匈奴决战,“方令击鼓,一时打其鼓不响。李陵自叹:‘天丧我等!’嗟之未了,从第三车上有三条黑气向上冲天。李陵处分左右搜括,得二个女子,年登二八,亦在马前,处分左右斩之,各为两段。其鼓不打,自鸣吼唤……胡还大走,汉亦争奔,斩决匈奴三千余骑”。这种女在军中、战鼓不响的描写,自然乖谬可笑,但却是民俗禁忌的一种形象反映,为故事增添了一层神奇色彩,颇能满足世俗民众嗜奇好异的审美口味。《伍子胥变文》写子安、子永想捉其舅父子胥去领赏,子胥用法术掩护自身,子永占卦得知子胥头上有水,腰间有竹,木屐倒着,认为他已身亡,便不再追赶。这个情节则表现了民间的术数信仰,自然也能让民间俗众喜闻乐道。其他如上文所举的刘家太子藏于土中躲过劫难、韩擒虎死后成神的情节,也都具有使故事内容神奇化,以吸引听众的艺术功能。
在语言运用上,变文讲唱者不仅将简奥、朴质的史书语言通俗化、口语化,而且还在其中掺入一些鲜活的野语村谈,以佐趣味。如伍子胥在逃难途中来到其姐家中就餐,其姐不敢明言,“遂取葫芦盛饭,并将苦苣为荠”。子胥心领神会,解而言曰:“葫芦盛饭者,内苦外甘也;苦苣为荠者,以苦和苦也。义合遣我速去,不可久停。”这种以哑谜的形式暗传心意的做法,就使故事话语颇富生活情趣。后来,伍子胥又逃到妻子门口,叩门求食,又不敢相认,否认自己是伍子胥。夫妻二人于是采用了四十多种药物名称谐音取意,互相问答。这也是一种民间通俗的文字游戏,读来妙趣横生,想必彼时现场讲说,听众定会兴致盎然,击掌称叹。
三
将敦煌演史类变文与后世讲史、演义略加比较,便不难看出它们在题材内容和思想意趣方面确实存在着传承关系。如《汉将王陵变》所虚构的王陵斫营之事,就曾被明代熊大木的《全汉志传》所承取,后者只对变文作了很小的改动。当然,两者之间还有一个中间环节——《前汉书平话正集》,只可惜该平话已佚,但其主体部分已被《全汉志传》撷取,也就是说,变文先是影响了平话,再由平话影响了演义。《捉季布传文》与《前汉书平话正集》、《西汉演义》之间,《伍子胥变文》与《吴越春秋平话》(已佚)以及《春秋列国志传》中的伍子胥传奇,当然也有一脉相传的关系。不过,更重要的是,变文与平话之思想意趣的息息相关。如《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李陵变文》等,表现了民间强烈的反暴君倾向和浓厚的复仇主义情绪;而平话《武王伐纣书》、《前汉书平话续集》等,也喜欢讲复仇、讲报应,矛头也主要指向荒淫无道、贪残寡恩的暴君商纣王和刘邦等。变文喜爱夸示英雄人物如伍子胥、王陵、韩擒虎等人的智勇武略,甚至使其趋于神化;平话比之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平话中的王翦、张飞等即多谋善战、神勇无敌,姜子牙、孙膑、诸葛亮等则智术莫测、神通广大,两者皆表现了民间俗众追慕、崇拜英雄人物的文化心理情结。
至于在战争描写的方法和套路上,变文更具有首创、开启之功。如《韩擒虎话本》写韩擒虎与陈将任蛮奴比斗阵法,先是猛破对方的“左掩右夷阵”,再以“五虎靠山阵”斗败了对方的“引龙出水阵”。与蕃使比试箭术,蕃使箭中鹿垛,韩则射中蕃使箭栝,穿过鹿垛十余步远。后来,他与匈奴王子同射,又一箭双雕,使单于大为慑服。像《汉将王陵变》写王陵夤夜偷营劫寨、《李陵变文》写单于火攻李陵之类情节,在讲史平话和历史演义中比比皆是。
此外,变文在情节建构上讲究传奇性和戏剧性,只截取英雄人物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片段,抓住其主要性格及命运播迁,来打动听者、衍展故事的做法,也直接影响了宋元平话乃至后来的英雄传奇小说。宋元平话主要就是围绕着勇将王翦、张飞、薛仁贵或军师姜子牙、孙膑、诸葛亮等,来组织、生发故事情节的,他们的英雄性格和传奇经历构成了平话叙述的核心,其他人只不过是陪衬而已。而《韩擒虎话本》的主要故事情节,还直接被英雄传奇小说《说唐全传》所袭取。
在叙述体式上,变文采用散韵相间的方式进行讲唱。散文用以讲述故事情节及其发展,韵文则用以写景状物,揭示人物内心情感,描绘战争场面,同时也推进故事情节。宋元平话、历史演义也是散韵相间,在散文叙述中穿插诗词、韵语,这无疑带有变文的影响在内。当然,两者在韵文的比例及表现功能上,存在着不同之处:典型的带有唱词的变文,其韵文所占的分量很重,故事进展也非常依赖韵文;而平话中的诗词韵语只用于念白,且数量少,主要用以品评人物、情节,很少加入叙事,其故事进展也全赖于散文部分,极少看到在情节进展上绝不可少的韵文段落。就此而言,变文与《大唐秦王词话》这样的历史小说,似乎更为接近。不过,变文中也并非没有只说不唱、用以品评人物、情节的韵语。如《李陵变文》讲到李陵斩讫军中两个女子,就引了北朝庾信的两句诗“军中二女忆,塞外夫人城”,以证前述内容之不诬。《前汉刘家太子传》讲完故事后,则引用了故语“南阳白水张,见王不下床”来作补充。《韩擒虎话本》讲到箫磨呵不懂用兵之道,也引故语评价说“军愣即将妖,主愣即国倾”。这与平话、演义小说中韵语的运用,并无二致。可见,在韵语运用上,变文对平话、演义也是有所启发的。
变文在讲唱历史故事时,为便于听众更好地理解讲唱的内容,往往配以生动、直观的画图。《汉将王陵变》中就有“从此一铺,便是变初”的话。《王昭君变文》故事卷子中也有“上卷立铺毕,此入下卷”的提示语。《韩擒虎话本》结尾则明言:“画本既终,并无抄略。”可见,变文确是图文并茂的。而其图画主要出现于讲与唱的交替之处,也即故事情节比较吃紧的地方,讲唱者常用“……处”或“……处,若为陈说”等套语,提醒听众观看画面,同时开始用韵文将画面上的情景唱给观众听,让观众充分感受到故事所传达的情绪、氛围,加深对故事关键内容的理解和印象。这种图文结合的方式,对后来平话、演义小说中的插图有着直接的启示作用。如现存的《全相平话五种》及明代的一些演义小说,正文的每页上方皆有图像,图像左右两边还有小标题,用以揭示该页所写的主要内容,这样读者即便识字有限,也能依据图、题,大致领略小说的故事情节。当然,变文配图是为了辅助讲唱,而平话、演义小说配图则是为了辅助阅读,它们分别服务于口头文字和案头文学,但是它们在通俗、悦众这一点上却是完全相同的。因此,我们不妨把后者看成是变文配图的演变形态。
由上面论析,可以看出,敦煌演史类变文不仅具有独特的审美艺术风貌,形象地反映了唐五代民间俗众的历史意识、道德情感、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而且在小说史上,对后世的讲史平话、历史演义小说,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尽管它们所讲唱的历史故事还很简单,情节结构单纯,篇幅比较短小,讲述技巧也显得稚拙、粗糙,但它们毕竟在题材内容、思想意趣和艺术形式上,直接开启了平话、演义,为平话、演义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艺术经验。所以,我们说敦煌演史类变文乃是中国通俗历史小说的雏形,标志着中国通俗历史小说的正式起源,在中国通俗小说史上具有不容低估的历史意义。
标签:李陵事件论文; 韩擒虎话本论文; 历史论文; 伍子胥论文; 三国论文; 李陵论文; 韩擒虎论文; 汉朝论文; 西汉论文; 史记论文; 隋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