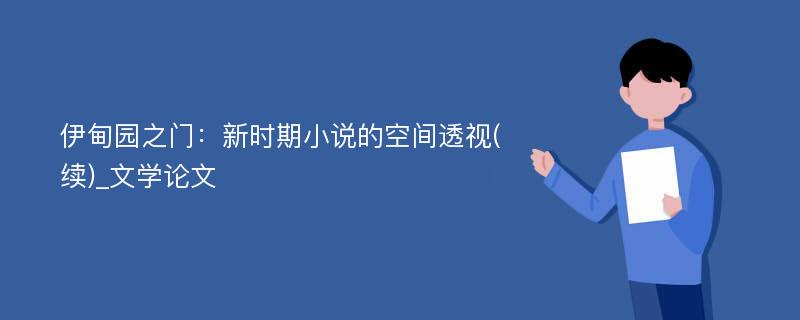
伊甸园之门——新时期小说的空间透视(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甸园论文,之门论文,新时期论文,透视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下篇 小说精神:盲者与赎罪情怀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文学精神的每一举措都深深地刻在人们沉重的记忆之中。对灾难的回忆已成了我们精神的一种幻象,我们这代人似乎已经注定要饱受梦魇的残酷折磨。在暴力与恶行、空虚与无聊同时繁殖的年代里,人们更多地处于一种迷津之暗中。这是一种面对家园的冥想与渴望,是一种信仰失落后痛楚的追寻。面对生存无意义之痛苦,现代人与当代人一同开始了寻求寻魂的艰难历程。在这漫长的隧道中穿行,文学精神孕育成熟,人们面对诸多的暗丧失了价值的视力而成为盲者。
世纪末的钟声立时敲响了。颓废与绝望共同诉说人类生存的暗夜,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我们看见,这是由人建造的迷宫,冰冷的机器世界,这个世界舒适和表面上的各得其所越来越剥夺了我们的权力和尊严”。①“不安定的人类本质赋予我们时代以其风貌:到处都有反抗,到处都有虚无主义的绝望,大批不满现状的人感到困惑,那些放弃有限的目的,不受和谐引诱的人沿着错误道路不断探索。民众‘从来就没有上帝’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失去上帝的同时,人类失去了价值感——人类相互残杀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感到自身的价值”。②这是人类生存的虚无暗夜,当此之际,悲哀、哭号、疼痛与死亡都不再是明朗的了。这是一种对生存的目的意义和终极价值的怀疑心态,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法摆脱的梦魇。
1.怀疑的时代
在世界之夜降临之际,沉睡千年的中国大地迎来了自身的觉醒与思索。伴随着十年浩劫那沉寂的钟声渐渐远去,人们一度麻木的灵魂缓缓复苏了。这是一次人的意义上的根本还原,它不仅对历史留下的伤痕进行着安详的抚摸。而且也开始了对历史性变乱与灾难的追讨与拷问。在这历史以来最大变故中,人们终于由狂热变得理智,他们绝望地发现,原来一切是这样的迷惘与痛苦,而制造这一切的又是人类自己。现实冷酷无情地打破了他们善良的愿望,在他们发出的悲悯与浩叹中,文学奏出了响亮而曲折的音符。
《伤痕》和《班主任》的出现,新时期文学有了“第一束报春花”,在它背后,是阵痛般的回忆的惊悸与战栗。人们饥渴的目光欣喜地拥抱这批“春的使者”,虽然它们并不完善,但毕竟带来了喜讯。在它们身上,人们看到了时代的悲凉与阴影。伴随着伤痕的抚摸与反思,人们的眼光转向了朦胧,在这怀疑一切的年代里,人们的心头的创伤是难以愈合的。他们有权发问,用一种怀疑与不信任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在历史那斑驳的面孔中,人们精神依傍的再度沦丧导致了艺术精神的理想的陷落,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迷惘,是重新寻找信仰而不得的迷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境中,茹志鹃、从维熙、张弦、李国文、陈国凯、路遥、张贤亮、张一弓、冯骥才、王蒙、王安忆、谌容、刘心武……一大批作家如雨后春笋般走进了文学的殿堂。他们或者重诉伤痕,或者反思历史,但根本上,这些小说都没有从实际解决人心头的悲凉。在他们的作品中,由于对历史缺乏一种宏大的把握而沦于琐碎,虽有一些短中篇佳制,却缺少长篇佳构,由于他们对历史拷问的表面化,而且纯粹的过去时态化,使他们的作品缺少比较现实存在的意向。也就是说,没有很好把历史作为现实生存的一个维度加以体现。显然,正是由于“伤痕”“反思”文学只把读者视野局限于过去的那段时光之下,导致读者一把眼光挪开,一切便显得缈茫,难以理喻。
这无疑是反思不彻底所造成的。在那繁多的短中篇小说中,“人”往往是历史的牺牲品,是被放大后的人。他没有自己特殊的地方,普遍的是一种命运的锁链式安排着主人公的悲剧一生,由此而产生的概念化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主人公的光辉。此时,小说家关注的似乎是那段历史,而不是人。他们对历史的症结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对历史的残酷作出了拷问与追寻,却没想到是人写的历史。没有对人的根本性的探寻就没有深刻的作品,在他们心满意足对历史作出了判词之后,他们转移了视线,开始了对历史的潜在逃亡。
怀疑的心态继续存在着。在这批“伤痕”的言说者与历史教训的反思者转移视线之后,现实以沉闷而清晰的景象呈现在读者面前。在现实面前,作家那愤懑与沉痛的血泪之情渐渐在光怪陆离的现实中消隐了。他们乐意做的是,面对现实言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历史渗透中的现实的刻画。此时此刻,改革的潮流已经汹涌而来,展现变革时代的新人新事成了作家注目的焦点。
任何转折都不是断裂性的完成。就是在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许多作品已经尝试着描绘出热情投身于新生活建设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形象,颇为引人注目。如贾平凹的《满月儿》、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小说,就给当时文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乔光朴的典型塑造得到了广大读者的交相称颂,作品以其震撼人心的思想和艺术力量脱颖而出。这是一次成功的脱胎换骨,它展示了作家的勇气以及对政治对文学干预影响的淡化。在这些小说中,人们看到了新生活所呈现的时代风貌,这是全新的,也是激荡人心的,因而是朝气蓬勃的。正是在这刻不容缓的时代紧迫感面前,读者再次被欺骗了。它把人们推到了时代的前方位置,成了舞台的成员,在一阵演作之后,人们又将重新回忆起那个并不让人愉快的过去。十年浩劫就仿佛一场梦魇,时刻袭击着被现实所鼓舞的当代人。正由于此,“改革小说”很快地网罗了一大批与先进人物相抗争的势力,从而使作品呈现出一种新的怀疑姿态,一种沉郁的力量和一种豪壮雄浑的悲剧风格。如蒋子龙的《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拜年》,王蒙的《说客盈门》等无不都展示着作家那敏感的担忧。应当承认作家是没有忘却历史的,他们更加愿意的是,在现实中去发现历史遗留下的问题。在作家们那隐晦曲折的艺术化的笔端下,文学渐渐发育成熟,作品也渐渐出现了亮色。如在徐怀中的笔下,战争被深化,作者虽然是从紧张的、残酷的战争中摭取了主人公的一些充满生活情趣的“轶事”写就的,但无不透露着浓郁的新时代部队生活的气息,感人于深。特别是刘毛妹(《西线轶事》)这样一个具有丰富内心世界和复杂性格的英雄形象,作者既写了十年浩劫在他心灵上所留下的深重创伤,又写了十年浩劫后全新的图景对他那包裹在冷漠躯壳里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发。刘毛妹是特殊的,是属于那个特定时代的,但同时他又是普遍的。同样,在《乡场上》这短篇中的冯么爸也是一个极突出的人物典型,作品通过冯么爸的转变于斑驳中写出了历史转折时期我国农村生活急遽的、复杂而又深刻的变化。在这样的变化中,写得最彻底的当首推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小说。高晓声为文坛带来的是陈奂生这不朽的典型,通过陈奂生,农村的巨大变革被浓缩成一面镜子。应当说,此时的读者对这样的小说是有热情的,在这艺术的朴实之中,人们看到这个特定时代所赋予主人公的以及每位读者的思索。人们不仅思索时代车轮飞旋的奥秘,也在瞬息万变的现实面前充实起来。从小说艺术看来,这样一个时代是封闭的,时代束缚了人们的头脑,人们不可能超越这瞬息万变的事实,而凌驾于生活之上。因而作品多以短中篇出现,即使是像《将军吟》(莫应丰)、《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芙蓉镇》(古华)、《冬天里的春天》(李国文)等等这样优秀的长篇小说,也缺乏一种超越生活的能力。虽然它们都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再现了十年浩劫的真实面貌,但在严格的意义上它们都没有达到长篇作为史诗这一美誉。无疑,史诗是心灵的,没有一种心灵的强撼震动,作品就往往流于一般历史的简单记录。面对历史,我们需要的是在历史的刻画中渗透出一种心灵的隐痛,让读者去体会、品评,从而使作品建构在心灵的普遍共鸣中。在这认同的持久影响下,作品才是恒久的史诗。
2.文化的困境与最初的逃亡
怀疑时代没有过去,人们只是缓缓地从记忆的沉重的飞行里挣脱出来。多变是这个时代文学与大众心理的特征。在多变的思维里,人们渐渐地发觉现实的残酷与不可追逐性。伴随着新生活的重新展示,人们对文化这曾经一片空白的地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一次城市对乡村的重返,也是人们心理在现代社会急剧变化面前的一次选择。这次选择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改革带来的纷繁复杂的变化的逃避,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则是一种怀旧般的迷恋。在此契机上产生的“寻根文学”正是这种心境的典型反映,它同时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文化的本体回归,作为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人们来说,每一种文化都是一次美丽的记忆,人们有权力要求文学作品作出反应。由于十年浩劫的深刻铭记,“寻根文学”对文化的寻根索隐都没有纯粹意义的承诺,它在不同程度上折射出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悲剧。虽然韩少功、贾平凹、阿城、李杭育、郑万隆等人存在的意义是确实的,而他们也确实对民族传统文化、民族之根做出了一番别有风味的梳理,然而,这种梳理却由于在相当大程度上只满足于一种文化的探寻。因而就带着浓厚的非平民意向,在他们那艰深晦涩的文本间,广大的读者被撇在一边。这无疑是一次严重的文学背叛,在文学史上罕见的对读者群的叛逃。通过这次逃亡,作家们开始构筑自己的“文化圈”,它往往体现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精神。如阿城的《棋王》中所体现的一种超然物外的人生姿态,那是一种自我信念的执著,一种“棋”所引发出来的精神境界(有批评家说是道家精神)。在贾平凹那边,则体现为对商州那块土地一种梦幻般的迷恋所产生的特殊情结,呈现出来的较多是一种禅意的自足。同样,在李杭育、张承志等人身上,文化的巨大魔影笼罩着他们,使他们的作品在一定含义上成了文化的代名(如张承志的《北方的河》),或者成了风俗民情的详细记录(如王安忆、贾平凹、李杭育、郑万隆等)。
文化是多层次的。文化在文学中得到的较多是一种精神的体现。在民族、社会、民俗、人类、历史、地理的广阔领域内,作家运用各自的“文化”概念去理解现实与历史交叉时产生的矛盾、隔膜、误会以至谬误都是难以避免的。正由于此,作为寻根的文学在“文化”面前显得举步维艰,尴尬随之而来。正如李杭育所说:“‘寻根’也寻得很不整齐,层次参差,鱼目混珠。并且也得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们谁也不见得寻出了多么高深的名堂来,水平是很有限的。确实有人只往大森林里去寻,所以被人说成是‘寻到了猴子尾巴上’。也确实有大量的表面文章,浮光掠影,弄点古色古香来装点门面。”③无疑,这话是中肯的,作家绝没有自我菲薄之意。在“寻根文学”的文化困境中,我们可以看到庞大的文化对于作家的双重逼迫,作家们面对文化这巨兽永远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驯服与惊惧好奇的姿态。在这样的脸孔背后,作家们面临的窘境便可想而知,因为只要作家想继续窥视这头巨兽,他就必须做好孤身奋战的准备,而且显然有着生命的真正意义上的冒险。文化产生的文学并不能从根本上根治时代的病态,这已是一个显然的事实。人们缺乏的并非文化精神,而是十年浩劫所造成的心灵的空白。在这空白的心灵深处,涌动的是存在精神的贫困以及信仰失落后的巨大虚无与绝望的滋生。因此,当文学认识到人们缺乏的并非文化精神以及传统文化的贫乏时,文学的眼光是迷离的。
迷离代表了一种情境,在这背后,小说开始了逃亡的路途。在刘索拉,徐星等人为发端的探索小说身上,人们看到了一种全新的言诉。视点正在转移,人们已经不满足于那种平淡乏味的故事,他们需要一种心灵的强烈共鸣。宣泄一种情绪的欲望在探索小说那狂热的放肆的言辞中得以实现,这是一次躁动的心灵狂舞。面对探索小说那放肆的语言变革以及那放荡不羁的情绪话语,文学似乎在一夜之间摆脱了人道主义的束缚而得以脱胎换骨。然而,事实并非这样,早在寻根文学那里,作家们就以粗俗为高雅,把那“充满粗鲁,鄙陋、俚俗、木拙、野性的语言的小说接连掼出来”,“想借此来摆脱掉规范叙述的因袭陈套”。④因此也曾一度给文坛带来一种斑驳、绚烂、生动而充满活力的原始的野性的质朴气息。当然,探索小说的野性似乎是更加躁动的,它展示的是一种非理性的城市文化。在《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以及刘毅然的《摇滚青年》等一系列都市小说中,青年的精神世界开始向缪斯舞台的前台位置进发,人们必须重新思索那灾难性的十年带给青年人什么样的后果。显然,历史发展并不愿意以十年为周期,随着潘多拉盒子的开启,某些后遗症在生活的现实当中显出轮廓。在这怀疑一切的青年身上,西方的非理性哲学、文学思潮得到了沟通,中国文学从此走向了与世界文学相互填补的渠道。在对理性展开的激烈反叛当中,原先在伤痕文学以及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中所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被放逐了。在尼采与柏格森以及叔本华的论述中,生命冲动、生命之流成了“实在”之物。非理性的成就恰恰在于它应和了青年一代对良心的淡漠以及对世界的不信任。这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跋涉,也是一次反文化、反崇高的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正由于此,探索小说的主人公往往被一个放大的“我”所取代,而这个“我”在作品中又往往有使不尽的活力,需要发泄点什么却又总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在这里,读者几乎可以明显摸到人们心中的那份骚动不宁。仿佛一个东西在滋长,在抗争,它要冲破某些传统秩序的规范。正如有位批评家所说的:“那是一个繁荣而不平静的时期,显文化层次,改革开放正在不断推进,人们用‘新旧交替、新旧交错、新旧交锋’描述的文化转型,激烈却又充满希望。亚文化层次,这种‘交替、交错、交锋’以另外的形态进行着,它可以描述为生命活力冲动与冲撞的曲线。”⑤正是在这种生命活力的冲动与冲撞之中,探索小说成就了其青春魅力,因而吸引了一大批青年读者。然而,这只是一次简单的编局,就在人们把活力投放到粗鲁的言语和粗放有力的迪斯科舞厅以及那一曲曲“西北风”的吼叫时,人们的疲惫急速赶来,心灵的空白地带愈加扩大。人们意识到,探索文学只是一次精神贫困的呓语与失语,在这样一次不成熟的精神狂舞背后,作家首先退出了舞台,这是羞涩的撤退,但却是明智的。
没有依靠成了时代青年的特征。在喧哗与骚动的背后,我们看到时代青年那脆弱的心灵深处涌动着一种绝望的呐喊,这是信仰失落的表层爆发,探索小说无疑正好应和了这强大的声部。然而,在情绪发泄之中,由于情绪本身不存在持久性而令读者很快感到腻味。如流行歌曲一般,探索小说亦很快销声匿迹。这正是一种消遣式的文化,它对读者心灵的淡漠同样是显而易见的。它非但没有良心为心灵负担一种责任,就连最基本的艺术目的也淡忘了。
3.残酷:叩响绝望的门铃
这个时代的作家是没有多少人道主义负担的,在非理性、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话语的援引过程中,人道主义话语被渐渐放逐到荒原地带。莫言、张辛欣等作家那张扬的生命意识背后,人们开始接受了残酷冷漠的叙述。这发端者无疑首推残雪和莫言。残雪的一曲《苍老的浮云》把人们推向了一个对人与世界意义的全新解读。当人们一直在美的维度上追寻意义时,残雪却冷冷地指给人们一个“丑”。如果说在人道主义那里世界是充满意义的话,那么残雪对这种乐观精神及乐观人生图景则划上了巨大的问号。人的孤独、苦闷、焦虑、畏惧、虚无,世界的荒诞、无意义这一切逐渐笼罩了小说全体,让读者没有喘息的机会。在此基础上,存在主义的论述的话语被中国的批评家所启用。作为面对两次世界大战而产生的绝望言论的存在主义来说,中国是幸运的。但一个骨定的事实是,危机的推迟只有令人们感到加倍的痛苦,文革后的中国人开始理解了西方人的精神,虽说不是完全的但至少也是大部分的。在十年浩劫中,人的极端的异化加深了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精神的整体认同,加上一种信仰的迷失,人们也普遍感觉到一种空虚一种危机正潜入人的心灵深处。正由此,中国人接受了尼采、叔本华、萨特、海德格尔等人的绝望描述。在残雪、莫言以及先锋小说家共同编织的残酷世界里,我们看到人性的变异与信仰失落后的迷惘,恶行与暴力共同编织了最为引人注目的黑暗权势,这是真正绝望的开始,它预示着心灵对绝望的承受已经开始,人们没有办法逃避。在这没有家园渴望与依托的年代里,人们开始重新从一个层面上对那个暗无天日的年代进行反省。在此,许多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寻求到恶行与暴力身上,因为在它们身上有残酷(那个年代的特殊字眼),也有黑暗与人异化后的麻木(那个年代的人类特征)。这时,先锋小说家一齐登台亮相,他们各自诉说对着恶行与暴力的残酷的理解。如余华的《现实一种》、《1986年》等小说就达到了一种骇世惊俗的程度,这位靠蚕食人的血肉得以存活的小说家无疑是极为残酷的,他不仅揭下现实那血淋淋的事实,而且揭下了在十年浩劫后的人们那温情脉脉的面纱。这是一次濒临绝望的近乎麻木的却又强大的抗议。在他身上,我们才知道,原来残雪的残酷,莫言的丑陋与粗鄙都不算什么。本来,世界之夜已经带给人们荒诞与虚无,但中国人对荒诞的理解并不深刻,虽说也有不少作品(如高行健的《车站》等)反映了荒诞这一主题,但显然是,中国人不愿意走这条西方人早已叫得雷响的道路,况且,已经过时多年。于是聪明的小说家为我们展示了惊心动魄的残酷,这是一次全新的认识,也是一次创举。当然,残酷永远不是内在的,作家重返心灵的暗角成了应时的一种必然趋势。
重返心灵的诉说是青年小说家的专利。在先锋小说家等更年轻的一代人身上,他们由于现实话语的缺乏而走入心灵的暗门。这是一次逃亡般的记忆,幼时留下的阴影在梦幻中显得分外模糊。也正是这种梦幻与潜意识深层的挖掘使得青年小说家感到分外的自足。他们满足于自己心灵中的声音,也满足于聆听一种童年记忆的声响。故事往往是虚假的,重要的是一种感觉,在这各式各样的感觉背后,逃亡与归乡得到了作家神话般的认同。从作家的描述里,这逃亡与归乡同时诉说一种迷津之暗,那就是,逃亡是不可避免的,而归乡之途则是漫长的,至于家园,那纯粹是一种梦幻般的遥远的记忆。于是,为着归乡而走上的逃亡就成了一次永久的放逐,成了一次漫无目的的流浪。
正是处在这种特殊的地位上,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对家园展开了激烈的讨伐。面对精神家园的丧失,作家们无不以一种凄凉的声音传诉着走出家园的悲惨记忆。在洪峰的《奔丧》中,我们亲眼目睹了“我”对家园的冷漠残酷的畸变。“我”成了家园的世界的“局外人”,这是一次流浪者的最为悲苦的却又带点自得的言说。如果说洪峰的记忆是真实的话,那么苏童、余华、北村的记忆则显然更具有真实的力量。特别是北村的《逃亡者说》与《归乡者说》,北村对逃亡与归乡作了一次意义上的实验,迷津之暗令人发指。在作家的眼中,逃亡与归乡代表了一种心境的过程,逃亡寓示着对世界家园的背叛,因为即使在这个真正的可见的家园里,心灵仍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满足。正是由于心灵需要一种安慰与憩息之地,作家们开始了“逃亡”,在余华身上,他开始了十八岁的出门远行;在苏童身上,则开始了《1934年的逃亡》的话语记忆。逃亡是为了寻找心灵的憩园,因而在逃亡的同时,作家与诗人是归乡的。归乡的渴望是真切而悲凉的。因为诗人作家身上,家园(心灵的)缥缈不定,它仿佛海市蜃楼那样可遇不可求。重返家园(世界的)已经同样成了一种没有承诺的记忆(因为逃亡是一次激烈的背叛),因而这样归乡的努力是徒然的。在青年诗人海子等人身上,这一切都曾那么真切地发生过,正是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精神家园的记忆是何等的贫乏。作家诗人寻求着心目中的家园而不得的悲情可想而知。
朝家园进发的征途中,历世历代以来挤满了辛勤的出征者,他们满含希望出发,却又往往绝望而归。在这十年浩劫留下的破败家园里,人们欲图重建一个理想的家园无疑是艰困的。在十年来作家诗人徒劳的往返过程中,我们看到家园正被越来越多的替代品取代,这是一次悲伤的记录,它比没有找到家园的人们更加虚伪。因为在替代品背面,家园越来越模糊,越变越遥远,完完全全地从心灵里撤退也来。虚假的家园并非夸大其辞,在这世纪末日渐沉沦的气息中,虚假代表了一种最无耻的逃避。这是一种孱弱者对现实的妥协,在它背后则一个无能者身影的放大。直面生存,无疑是需要勇气的,而追寻终极,无疑更值得钦佩。倘若一个人的终极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生存的意义是值得怀疑的。正由于此,面对那一切沉缅于世俗世界而没有追寻终极(至少必需有这个指向)的作品,我们没有理由不指摘它意义的缺失。特别是在这个意义失落的年代里,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艺术家没有理由不负担起神圣的使命。不管意义是否过时,艺术家都必须言诉意义的重要,毕竟,精神永远是作为核心存在的。
4、伊甸园之门
重返精神的探求之中,这已成了文学的日益偏爱的方向。面对家园的越来越近,一切越加陌生与艰难,陌生在记忆的深处,艰难在最后路途的完成,好像一位背叛故乡的浪子,在这归乡的路途中起伏的思绪,文学作出了最为难堪的妥协。踏上了故乡的走向家园的出路,一切因年代的久远而变得模糊亲切。怀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这最后的路途显得漫长而犹疑不定。文学开始在遥望家园中徘徊。
徘徊在通往家园的路上,这是现实与记忆的光怪陆离的交融。时而,文学是深沉的,充满生存之思;时而,文学是绝望的,因为那些记忆阻塞了通向家园的希望;时而,文学又是充满阳光的,因为家园已经在望。各种各样的情感得到了充分的交流,这是一次最后的较量,面对家园是进还是退的较量。提起张承志、史铁生的名字以及更年轻的北村的名字是令人激动的,因为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三个不同家园的最终获得。史铁生是自己追寻着靠近家园的,凭着他那有限的知识有限的智慧对人生之神开始的追寻中,史铁生抓住了人生终极问题的解答钥匙——宗教,从而展开了大规模的冥想运动。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他对佛教与基督教的思考及摇摆都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靠人的知识探求人生的意义是艰难的。所幸的是,史铁生最终抓住了自己智慧闪出的火花,即抓牢了由理智思索而出的属于自己的宗教。在这点上,史铁生同世界上许许多多宗教哲学家、思想艺术家(宗教的)没有什么区别。应当说这是值得钦佩的一次思想历程,它完成了心灵的即使不是永远的但也是暂时的满足。在我看来,这是浪子走过的最后路途以及举手叩门姿态的最后完成,至于那声叩门的令人惊悸的声响却没有发出来,更不用说家园里的亲人出来迎接,因而悲剧也是必然的。
相对于史铁生来说,张承志显得幸运得多。虽然他曾多方寻找家园与终极,但更多的是家园不可得的悲伤的吟咏。在这多情的草原歌手身上,历史的考查更多地给了他深沉的思索,也给了他更多的古朴、浑厚、抒情的特征。正是这样的特质,命运安排他来到了西北大荒漠,这是一次神对人的拣选与挽救,因为在作家的记录里,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一种心灵深处的激动。在这激动背后,是他回民信仰的最终获得的狂喜与感谢。在这浪子回归的路途中,无疑可以看到这样一幅景象;浪子奔跑着来到家园面前。那门却在没有叩响时刻开了,真正的亲人奔跑出来拥抱了这久违多年的浪子。这无疑是作家的幸运,因为对于浪子来说,这一幕是人生最为辉煌的也是最难以忘怀的无价遭遇。重返精神的家园是人生最为幸福的经历与价值的终极完成,正由于此,张承志曾动情地诉说:“我站在人生的分水岭上。也许,此刻我面临的是最后一次抉择。肉躯和灵魂都被撕扯得疼痛。灵魂和潮水涌来。”(《心灵史·序》)这便是张承志寻到了回民的信仰以及这种信仰如影随形的殉道精神的一种诉说。在这诉说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作家人生价值的最终获得。正由于此,写作对于作家来说已不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作家甚至不知道能否把这积习日深的癖好戒掉。显然,宗教在此代表了一种满足,它已不仅仅是苦难的安慰,还是生存力量的源泉。
这显然是一个信仰的时代,在那信仰迷失的年代里,人们已经饱受了创伤与苦痛,人们没有理由不寻找那心中的太阳,重返家园的渴望是迫切的,在年轻一代身上,青年作家道出了这最为隐晦的声音。声音在共鸣中越奏越大,谁也不能轻轻地绕过它的拷问。正是基于这样的思索,北村,这南方精神的苦痛之子勇敢地挺身而上。他在哲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徘徊多年,在他的一系列小说创作中,北村始终坚持着终极精神的追寻,这在先锋小说家中是独特的,也正是由于如此,他被一些批评家确认为是最极端的先锋小说出征者。在文学中,北村已经习惯于寂寞但又不甘于寂寞,他的实验是小心翼翼的,比起他的许多同行来说,关键不在于写的多少,而在于写的是什么。特别是对于终极探寻执著而认真的北村来说,思考毕竟是严肃的,它生产不出“玩的文学”。正是这种绝对意义上的探寻很快把北村逼上了死路,在那绝望的精神背后,人渐渐走向尽头。就在这样的时刻,创造主的手伸了下来,按在作家的背上,这是一次人生意义的完全拯救,是一次人类没法推测的奇妙的救赎。和张承志一样,北村对这次奇妙的神圣的降临发出内心的赞美。这在北村以往的作品中是个奇迹,因为北村以往小说的主人公无一例外的结局就是死亡、而在得到救赎后的北村看来,人物出现了光明,这也就是刘浪(《施洗的河》中主人公)最终没有走向死亡却得到救赎的最完美解释。北村对这次得救的经历无疑是极为深刻地铭记在心的,因为这之于他是一次生命的重新获得。在北村的几篇散文作品中,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他对这次圣灵的垂顾的由衷赞美之情。
然而,北村显然有别于史铁生与张承志的家园的诉说,在北村那里,家园是神的预定,它的名字叫伊甸。重返伊甸园带给了北村平安与喜悦,也给他带去了超凡的智慧,在他那急剧的转变中,小说一样地成了并非最重要的事情。在作家看来,生存是首要的,写不写小说已经非作家所能决定的,因为对于顺服神旨意的信徒来说,一切在神的安排之下。也正是由于绝对的顺从,作家获得了一种截然超越的地位,以这样的眼光,作家创作出一批令读者耳目一新的作品。这是一种全新的视角,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革命,在这样的革命背后,我们看见了文学伊甸园之门正朝广大读者开启。
1994年4月于福州
注释:
①见《卡夫卡对我说》第55页,时代文艺出版社92年版。
②雅斯贝尔斯《存在与超越》第207页,上海三联书店89年版。
③李杭育《“文化”的尴尬》,《我的文学观》第242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87年版。
④蒋原伦:《粗鄙——当代小说创作中的一种文化现象》,《读书》1986年10期。
⑤程文超《意义的诱惑——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当代转型》第65页,时代文艺出版社9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