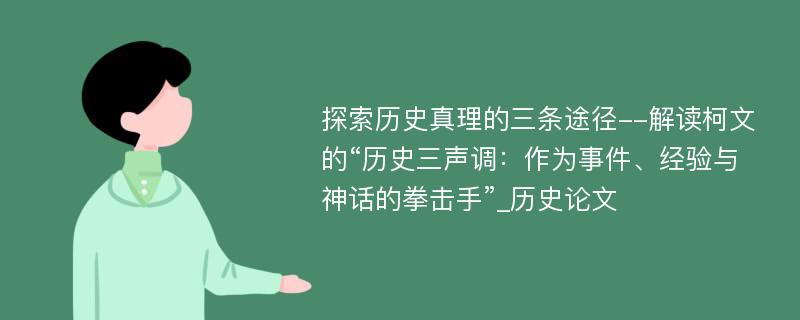
探寻历史真相的三种途径——读柯文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和团论文,历史论文,三种论文,真相论文,途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07)10—0159—04
柯文(Paul A.Cohen)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著名的中国学家,先后著有《中国与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China and Christianity: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1963年出版,以下简称《中国与基督教》)、《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íng China,1974年出版,以下简称《在传统和现代性之间》)、《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1984年出版,以下简称《在中国发现历史》)、《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History in Three Keys:The Boxers as Event,Experience and Myth,1997年出版,以下简称《历史三调》)。
柯文主要的学术研究集中关注19世纪、20世纪的中国历史,而在这段时间中国与西方之间接触频繁,双方实现了交流和互动,虽然这种情形的出现最初并非出自中国自愿。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史家解释鸦片战争(1839—1842)到义和团起义(1899—1900)这段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西方冲击’与‘中国回应’这两个概念。”[1] 柯文在50年代进入哈佛读书,受费正清和史华慈的影响颇大。而费正清正是美国研究中国的“冲击——反应”模式的代表人物。柯文的第一本著作《中国与基督教》就受到了费正清的影响。他研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影响,而非研究传教团自身的历史。柯文的第二部著作《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写于1964到1973年间,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他感到了从前美国学者研究中国19、20世纪历史的那些模式的缺陷。他后来说:“在力图理解王韬的过程中,我遇到的问题是:我在撰写此书的十年中,开始写作时所持有的关于‘中国’与‘西方’、‘近代’与‘传统’的假设受到了强烈冲击。我曾经意识到其中的矛盾,而且在书中许多地方的着重提到‘传统一近代’这种两极分法本身有待商榷。”[2] 正是由于柯文意识到了美国战后有关19、20世纪中国历史论述的总思想框架或模式(paradigms)存在不足才促使他写出了第三本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该书分析了二次大战后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三种思想框架:冲击—回应框架、近代化框架与帝国主义框架,指出三种框架的各自不足。冲击—回应框架把中国描绘成消极的,把西方描绘成积极的;近代化框架则把中国描绘成停滞不前的“传统”社会,有待西方赋予它生机;帝国主义框架则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各种变化的动因,同时它也是阻碍中国前进的祸根。这三种模式都是以西方为中心来研究中国19、20世纪的历史。针对这些,柯文提出在研究这段中国历史时把起点放在中国而不是西方,具体地说就是:“(1)从中国而不是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3] 但是,柯文也强调他的“中国中心观”并不是要无视外界因素,把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来探讨,而是“力图摆脱从外国输入的衡量历史重要性的准绳,并从这一角度来理解这段历史中发生的事变。”[4] 正是在先前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柯文写出了《历史三调》。该书延续了他的“中国中心观”中所提出的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用历史学以外诸学科(如宗教学、心理学等)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义和团运动,并且试图进入当时的情境来体验时人感受。不过,该书又是对“中国中心观”的超越。柯文在书中不只是局限于从中国或是义和团本身的角度来看义和团,而是从世界文化的范围来探讨义和团运动,从人性的角度来进行考察。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三调》超越了中国中心,或可称之为人性中心。
众所周知,在中国关于义和团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到现在已经很多了。建国后到文革一段时间,关于义和团的研究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过重,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对义和团的研究也渐渐恢复历史研究的本来面目,但是“应该承认,义和团研究近年来多少受到学术界冷淡”。[5] 在美国,1987年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出版,并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那么柯文为什么还要来写作一本关于义和团运动的书呢?原来柯文写作《历史三调》的主要目的在于“考察与历史撰述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义和团只是这项工作的陪衬”,但他也希望该书“能够引起那些关注义和团运动本身及中国人在20世纪纪念该运动的方式的中国专家的兴趣。”[6]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该书归为关于历史书写的理论著作,至于对义和团历史的探究只不过是作者为了解说的方便而选取的一个例证。
“不是历史学家的人有时以为历史就是过去的事实。可是历史学家应该知道并非如此。当然事实俱在,但它们数量无穷,照例沉默不语,即使一旦开口又往往互相矛盾,甚至无法理解。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追溯过去,倾听这些事实所发出的分歧杂乱、断断续续的声音,从中选出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探索其真意。”[7] 所以柯文认为,“历史学家重塑历史的工作与另外两条‘认知’历史的路径——经历和神话——是格格不入的。对普通人而言,这两条路径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8] 因此,柯文在《历史三调》中对义和团运动这段历史的书写分作三部分,即事件、经历和神话。作为事件的义和团是由历史学家来书写关于义和团的故事,以此来实现对过去的解读;作为经历的义和团是由义和团运动的直接参与者来讲述过往的那段经历;作为神话的义和团则考察义和团运动怎样在20世纪的中国不断被神话化的过程。事件、经历、神话是人们根据不同原则来认识和塑造历史的三种不同途径,表现出不同的音调。这也就是书名定为《历史三调》的原因。在这里柯文所用的“历史”一词有双重含义,从技术层面上讲,“用以特指历史学家重塑过去的正式过程”,但从更广泛的角度讲,“涵盖了认知历史的各种途径,包括经历和神话在内。”[9] 下面分别来看一下探寻历史真相的这三种途径。
一、事件
在这一部分里,柯文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来书写义和团运动。既然他只把义和团运动来作为他解说自己历史书写理论的例证,因此他在绪言中首先探讨了历史学家的重塑工作所面临诸多问题。他提出疑问“历史学家的工作是真实和完整地重现过去发生之事呢,还是舍弃一些确实存在的史实并增添一些未曾发生的事情后形成新的历史呢?”[10] 不是历史学家的人很可能认为答案是前者,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准确的恢复过去的本来面目,非如此便不称其为历史。但是柯文还认为,无论历史学家怎样的努力,他们最终书写出来的史书肯定有别于真实的历史。因为历史著作在叙述的过程中把过去高度简化和浓缩了,这样过去本来的混乱和复杂经过历史学家的解释变得条理化和明晰化了。历史学家和直接经历者对过去的整理和理解虽然不是完全不同,但是两者的动机却大为不同。直接经历者会在以后的岁月中不断复述和改造过去发生之事,以此来保持个人经历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历史学家在理解和解释历史时“必须有意识地遵奉(在实践中从未完全实现过)社会公认的关于准确性和真实性的强制标准。”[11] 他们不能感情用事。历史学家在已经知道结果的情况下从事研究工作的,这使他们能够自由的跨越时空,赋予事件以不同的意义。但是这也可能造成他们认知上的错误。因为“历史的研究突出了时间的顺序和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12] 历史学家因此可能错误地推定既成事实的必然性,发生于后的事必然是其前的结果。但是事实有时并非如此,历史事件的发展有许多偶然性,因此虽然已经知道事情的结果,历史学家在重塑历史时也要避免草率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事情的结果是前定的,不可改变的。”[13] 同时也要避免赋予发生于后的历史事件以过高的意义。历史学家在塑造历史的过程中也受不确定性的困扰,“这影响到历史学家重塑历史的全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包括在关于历史事件的结论中重点强调哪些问题或哪些方面。”[14] 对此的更清晰表述,笔者以为当是他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所说的:“所有的历史研究都不可避免引进大量主观成分。选择什么事实,赋予这些事实以什么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和我们进行研究的前提假设是什么,而这些问题与假设则又反映了在某一特定时期我们心中最关切的事物是什么。随着时代的演变,人们关切的事物不同,反映这些关切的问题和前提假设也随之发生变化。”“制约任何史学研究领域之变化的各种因素中,最根本的是史家生活于其中的政治、思想与文化环境;其他一切都是次要。”[15] 柯文也反对关于历史的概括性结论,首先是“转折点”或“分水岭”一类,认为其中有太多神话的成分,体现了做结论人太强的感情偏好。
历史学家在重塑历史的过程中也无法保证占有的证据的数量和质量。因为遗留下来多少证据,什么样的证据具有极大的偶然性。而历史学家的工作只能在证据的基础上开展,也就是说“任何历史学家都可能在其著作中过多地使用容易留存下来的那类证据。”[16]
虽然历史学家重塑历史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难,但这不等于说历史学家的工作没有意义。柯文认为虽然历史学家无法提供原原本本的历史,但是他们提供了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这就是意义之所在。
作为历史学家,柯文对作为事件的义和团的叙述相对于经历和神话两部分来说所用笔墨是最少的。可见他的重点也不在此,他并非要向人们展示义和团运动的整个历史过程。因此他只是简略地叙述了义和团运动的起源、高速发展阶段、经历的国际化。其中所用资料亦多是来自他人的研究性著作(如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或是大陆方面出版的有关义和团的文献,并无特别之处。作为三调的这一调估计作者本人也不企望它能奏出精彩华章来。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分析义和团高速发展的原因时提出1898年冬季以来殃及华北地区的干旱是促成的原因之一,并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他指出饥荒和饥荒造成的恐慌情绪使人们易于相信某些人对现实问题的宗教解释:“不下雨是由于神发了怒,神发怒是由于基督教和其他洋物成泛滥之势”。[17]
二、经历
这一部分在全书中所占比重最大,是作者重点着墨之处,也是三调中最精彩的部分。柯文在这部分里力图从事件的经历者的角度来再现他们经历之事:干旱、降身附体、法术、谣言和死亡等,书写历史参与者的经历。这与我们从前习见的历史书写方式大为不同。过去的经历者和历史学家感受过去的方式也不同。在这一部分前面的《绪论》中柯文先进行了理论的探讨,分析了个人经历的特点,指出它与历史事件的不同,历史学家在面对个人经历时具有的优势和可能造成的错误。他认为历史学家无法完全恢复人们所经历的过去,因为在任何历史环境中只有一部分人的经历被记录并流传下来,而且我们也无法直接经历当时的每件事,但是我们个人的主观经验可以使我们评说和省察历史经历,部分的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也就是他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倡导的移情(empathy)方法的运用。人们的历史经历以感觉为基础,人们对经历的记忆和历史学家的价值标准不同。在难以忘怀的经历中有一些并不值得记住,“真实的过去中包含许许多多的不同经历,其中一部分是重要的、关键的、值得记住的、明确的,另有一部分(常常重复发生)是辅助性的,处于从属地位的。过去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的盲目性,”[18] 这样造成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往往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准备应付不可能发生的意外变故。而历史学家在叙述历史时普遍重视发生过的事情,而不重视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对自身经历的理解不仅受到他们所处的文化空间的制约,而且也受到他们所处的社会空间、地理空间的制约。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与历史学家和神话制造者在动机意识上也不同:“历史学家的目的是了解和解释历史,神话制造者则从历史中吸取能量,为现实的政治或宣传目的服务,为深层次的心理基础造势。与这两种人的想法不同,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的意识包含着人的所有情感和目的”,“促使人们采取行动并在形成人们生活经历的过程中常常起重要作用的动机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19] 但是不仅神话的制造者而且历史学家也可能曲解这种动机,历史学家试图从自己认为合理的阐释体系来解释。历史事件不同于个人经历,它是个人经历的综合,超越个人经历之上。
柯文喜欢从心理和感情方面来研究历史,他研究义和团中最大的部分,谈义和团成员“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感情,他们的恐惧,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追求的梦想。”[20] 对“当时参与这件事的非中国人的思想、感觉和行为也很感兴趣,并且不时指出中国和外国双方共同之处,虽然这部分的分析所占的篇幅较少。”[21] 也就是尽可能进入他所描述的人们的情感世界中,力图描绘义和团拳民、中国教民、既不信教也不练拳的绝大多数普通中国百姓、中国的官绅、外国传教士、外国和中国的军人和官员等所经历的那个经验世界的特性。面对干旱,处在华北各处的传教士都表现出了担忧,他们害怕被中国人杀死。因为中国人指责干旱是传教士们造成的。义和团的许多揭帖把洋教的渗透、上天的震怒和干旱三件事联系在一起。柯文认为,面对灾难,超自然的力量是人们对此进行解释的一个普遍的文化因素。人们经常把自然灾害看做是超自然力量对人类错误行为的惩罚。他列举了《旧约全书》中上帝对他的选民偏离正路的将遭惩罚的警告:1973年,尼日利亚的穆斯林和英国16世纪90年代的基督徒认为当时的旱灾或大饥荒是安拉或上帝对人类的惩罚;1980年象牙海岸的本加人因为该地区的旱灾惩罚一对行为不检点的夫妇;19世纪的博茨瓦纳人们把干旱归因为基督教的入侵。他在这里用了跨文化比较的方法,指出这种现象并非义和团独有,实际在世界范围内是普遍存在的。柯文从民间宗教的角度来分析义和团的降神附体现象。他认为这一现象和中国的民间文化密切相关,无论在中国古代还是20地纪的中国,都有与此相类似的现象。他也从心理和生理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而不是一味的纠缠于这类现象是否是真的。在他看来,个人或群体面临危机时,人们往往愿意求助于宗教手段。他也把义和团的宗教行为和台湾、新加坡等地的童乩等现象进行比较,来进一步解说此类现象所具有的普遍性。他指出从生理角度上说,饥饿确实可以造成精神不正常。对于义和团的法术,他是从心理上分析法术给义和团成员提供了情感上的安全感。至于义和团把法术失灵的原因多数归结为客观因素,如污秽或不洁之物冲犯了法术,特别是妇女的污秽败法,他也举出更多的例证说明这种解释在其他文化中也存在。关于谣言,柯文更是旁征博引来进行分析评说,指出谣言的诸多特点、作用、发生的原因等等,义和团只是他所列举的众多例证中的一个。他指出谣言有时表达了人们的愿望,有时表现了人们对现实处境的担心和焦虑。面对痛苦和绝望,谣言也能起到缓解痛苦的作用。义和团时期流传的诸如肢解人体、买卖器官、水中投毒这些谣言不仅在此前的中国社会就有,在世界范围内在特定的时期也有此类谣言。柯文从个人经历的层面来探讨死亡:目击者看到的各种死亡情状、加害者(即参战者)面对死亡威胁的种种反映、受害者所遭遇到的死亡忧虑。他从人性的角度来描写死亡,既写出了面对战争人性魔化的过程,也提到了在非常状态下人性表现出的善良和富有同情心性的一面,还有人们面对死亡的脆弱、恐惧以及当死亡频繁发生之时人们把死亡视为平常之事。
总之,柯文在这部分的研究中,“着重以人为中心多于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取向。”[22] 他注重研究人的感情、心理,思想,从人性的角度来考察义和团成员的思想情感以及此次事件的其他参与者的各种行为表现。他在书中分析不局限于义和团本身,很大程度上涉及世界范围内的相关现象,如降身附体在不同文化里的表现和相似之处,非常时期造成谣言流行的共同特点,关于投毒谣言在罗马、在1832年巴黎霍乱流行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尚武好战的国家中、抗日战争中的上海的流行。这些都强调人性的共同性,某些文化现象所有具有的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而非差异性,从这个角度说,“不如用人类中心取向”。[23]
三、神话
这一部分主要研究义和团在20世纪中国怎样不断被神话化的过程,它更像是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学术思想梳理。和前两部分一样柯文首先在这一部分前面的《绪论》阐述了他关于过去被神话化的见解。他指出了神话制造者和历史学家不同。历史学家的主要目标是在尽量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准确和真实地再现过去;神话制造者却要使过去为政治、意识形态、自我修饰和情感等方面的现实需要服务。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复杂性、细微性和模糊性,而神话制造者往往以片面的观点看待历史,从历史中找出个别的一些特点、特性或模式,把它们当作历史的本质。但在实际操作上,神话和历史在叙述过去时的区别却微乎其微。历史学家探寻历史真相的活动会受到目前他们头脑中固有观念的影响,他们也可能成为无意识的神话制造者,而神话制造者在制造神话时不会把自己的作品视为神话,他们也要注意作品的可信度。对过去神话化有各种形式:普通百姓头脑中的历史形象的神话化、对自己生平经历的修改、文艺作品中对历史的神话化。
柯文研究了义和团在20世纪中国人观念中的神话化过程:义和团运动时期当时人们所留下的文字中对义和团的贬斥,将其称为“匪”、“乱”、“邪教”;改良派人物指责义和团的迷信、盲目排外;世纪之交的革命派谴责义和团,邹容认为义和团是野蛮革命;新文化运动时期倡导科学、理性、民主的知识分子批评义和团的迷信、非理性,把它当作中国文化的象征;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时期把义和团当作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者;在“文命”中,义和团作为攻击刘少奇的武器,义和团中的红灯照又被与妇女解放联系起来;在与苏联修正主义的宣传战中,义和团又成了揭露苏联的政治工具。柯文就此对历史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精辟见解:“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撰写脱离政治的历史,而在于撰写反映正确政治观的历史。”“然而,一个人只有在具有正确政治观的情况下,才能写出反映正确政治观的历史。”[24]
总之,《历史三调》柯文所要书写的并不只是义和团的历史或中国的历史,他只是以义和团为例向人们解说探寻历史真相的三条不同途径,即历史的三调:事件、经历、神话,“想发现一种历史学家们跨越他们历史论题界限的方式”。[25] 对他而言,义和团运动并非独一无二,而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一个放大了的个案,可以作为他解说自己关于历史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可以实现“从一粒沙中看世界”。他向我们展示了历史学家、事件的亲历者、神话的制造者三者眼中不同的义和团运动。他在对义和团的描述中尽可能地进入所描述者的情感世界,从人性的角度来考察在特定情形下人的心理、思想、情感。他舍弃以往研究中将义和团置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等框架内的做法。同样是研究义和团的起源,他不是简单肯定或否定义和团是否来源于白莲教,而是指出鉴于义和团各团受到外来控制比较松散,华北各地义和团受白莲教的观念的影响程度极有可能是不同的,对此的回答不能过于刻板。对于民众参加义和团的原因,他也从多方面进行考察(如干旱使人们无事可做,义和团发展起来后人们容易形成赶风潮的心理等等)而不是简单的归为爱国,虽然爱国使义和团运动看起来更富有英雄气概。他对义和团事件的考察也不局限于运动本身,而是把它放在世界范围内,把它和非洲、美洲、欧洲以及亚洲和中国的其他地方相类似的事件和现象进行比较,赋予它更普遍的意义。这体现了柯文反对夸大中西方之间文化差异的立场,他认为这种立场往往还是西方中心论。他认为“如果我们要对中国的过去有一个更全面、更细致、眼光更广阔的认识,我们在探讨文化差异的同时,必须注意人类社会有许多共通的方面。这是其中一个有效的办法,让我们突破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学家以不同理由、不同方式为中国和中国历史设定界限的做法。”[26]《历史三调》实现了柯文的这一想法。
柯文认为,历史学家书写的历史与实际经历的历史和神话三者之间没有谁优于谁的问题,三者之间虽然有矛盾,“但在其各自的范围内,都有相当大的合理性。”[27] 柯文指出“历史事实(这是历史学家梦寐以求的)必定比人们想要相信的历史实情更有价值,这种观点本身也许只是一个神话。需要谨记的是,许多不同种类的价值(如道德价值、知识价值、情感价值和审美价值等)和某种关于历史事实的定论对某些人而言很重要,但对其他人而言也许就不那么重要了。”[28] 此话听来有些让人感到残酷,历史学家孜孜以求历史的真相,以为真实是历史的最高价值。但是尚且不说我们是否一定能够得到真实的历史,就是真实本身的价值在社会实际生活中也未必如历史学家期望的那样高。任何社会中都存在各个阶层,不同阶层面对同一事件重视的东西不同。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各类价值的需求也不尽相同。假的东西未必没有意义,甚或造成比真实更大的影响。对于20世纪的中国,神话化的义和团也许比真实存在的义和团运动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尽管许多时候这种作用是政治上的,义和团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武器。不过尽管如此,柯文还是坚持认为历史学家需要以敏锐的感觉,尽可能多的诚实求真精神,坚持不懈地在历史与现实这两个不同的领域间来回游走。相对于理论,柯文的历史具有“更多反思性”。[29]
[收稿日期]2007—04—11
标签:历史论文; 义和团论文; 历史三调论文; 神话论文; 在中国发现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清朝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八国联军论文; 历史学论文; 古希腊论文; 历史故事论文; 白莲教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史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