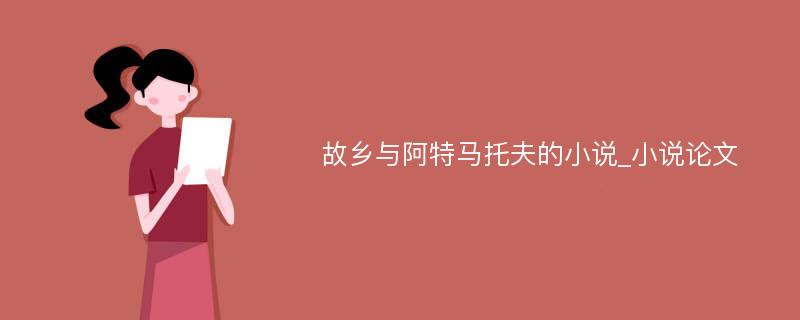
故乡和艾特玛托夫的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故乡论文,托夫论文,小说论文,艾特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苏联作家钦吉斯·艾特玛托夫1928年生于风景秀丽的山区小国吉尔吉斯。他的家乡舍克尔村座落在南部塔拉斯谷地。辽阔的山脉、纯朴的民风和长辈们的循循教诲,一直深刻地留在艾特玛托夫的记忆中,使这位几十年后崛起于苏联文坛的少数民族作家,在少年时代便获得了不少宝贵的思想启迪。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人的命运从一开始,便蕴育在他和他父辈出生、成长的土地上。重要的是,他能如蜜蜂采蜜浇灌自己一样,从这片土地中汲取心灵的慰藉。”〔1〕
吉尔吉斯族是个相对古老的民族,它在公元前五世纪便开始了自己的繁衍。发源在叶尼赛河上游的一支吉尔吉斯人早先为数重多,他们皮肤鲜亮,头发淡黄,是欧洲人的模样。只是后来,其它新族不断崛起,吉尔吉斯人被迫四处迁徙,继而集中在中亚楚河谷地这片各族势力的交汇处,与蒙古、汉、突厥、欧洲一些民族等不断混和交融,他们才逐步演变为黄皮肤、黑头发的亚洲人种。
在中亚各族中,吉尔吉斯人与哈萨克族的关系最为亲密。有一种说法认为,哈族是从吉尔吉斯人的一支中分离、演化出来的。他们之间允许自由通婚,亲缘关系很广泛,所以艾特玛托夫的作品中常常出现哈萨克大草原的景象,也是很自然的。
吉尔吉斯人一直过着游牧生活,从前是信奉多神教的。在中亚一带稳定生活后,逐渐接受了在这里影响较大的伊斯兰教。但吉尔吉斯人仍保留着许多自己特有的传统,而显示着这个民族的古老性。
吉尔吉斯人非常注意教育孩子不忘祖先,尊敬长辈是他们的神圣法则。要维护祖先的声名,继承他们的事业,将自己的名字毫不逊色地在未来一同排列在族谱上——这些古训使艾特玛托夫很早便意识到:人对自己、对祖先、对未来都肩负着重大的责任,这也正是艾氏文学创作中贯彻始终的一个主弦律。
钦吉斯的祖母,一位传统典型的吉尔吉斯妇女给幼小的艾特玛托夫奠定了坚实的民族文学基础。作家自己回忆到:“对我来说,她就是一座神话和民歌的巨大宝库!她有讲不完的真假难分、无奇不有的趣闻轶事……看来,正是祖母坚定不移地向我灌输对母语的热爱……才使我从童年就掌握和理解了母语,这能使心灵装满由人民的经验而诞生的诗篇,能使人的民族自豪感永不衰竭,并从先辈语言的丰富多彩的含义和节奏中得到美的享受。”〔2〕
蕴育培养了艾特玛托夫的故乡一直是他创作的根基。因为有对民族的深厚感情,也因为这里的山山水水总唤起他无穷的灵感,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总能嗅到作家所热爱的泥土的醇香,辨出作家所热爱的民族的风韵。
1958年问世的短篇小说《查密莉雅》是艾特玛托夫文学创作道路上第一个良好的开端。小说以简朴直白的笔触描写了发生在吉尔吉斯乡村的一段美丽、感人的爱情故事。
吉尔吉斯是一个山区小国,19万平方公里中,75%的面积均为山地。这里人口也不多,470万居民中,吉尔吉斯族大概有50%略强一些, 其次的是俄罗斯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等等。虽然也尊奉真主安拉,吉尔吉斯人与其它穆斯林比较起来,更为自由自在一些。他们过游牧生活的时间较长,女人们和男人们一样。常常要骑在马背上辗转迁徙,四处奔波。这就使得吉族的妇女显得吃苦耐劳、聪明、能干,她们和男人一起并肩作战,而不象一般穆斯林妇女那样,整日遮头盖脚,轻易也不迈出家门。
艾特玛托夫细心体味到了吉族妇女这些鲜明的特征,进而更深一步地向我们揭示出她们丰富的情感和美好的内心世界。查密莉雅是一个浸满泥土芬芳的热情姑娘,她周身散发着健康的活力,她快乐的笑声总四处洋溢,她勤劳又质朴,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队里,她干的活儿都受到夸奖。虽然她已经嫁给了上前线的萨特克,村里的小伙子们仍都喜欢她,想追求她。
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个只裹了一件旧军服的退伍兵丹尼亚尔。他的腿在前线受了伤,走起路来有点儿瘸,他沉默寡言,甚至还土里土气的。所以,当查密莉雅被分配和他一起运送公粮时,无忧无虑的她常常喜欢捉弄一下面前这个老气横秋的跛子。可渐渐地,查密莉雅被丹尼亚尔回荡在大草原上的歌声震憾了,那不是一般的歌声,那是心底最深的倾诉,是对生命的孜孜渴求和对生活的无限钟爱。小说在此极为真实地叙述了查密莉雅内心的变化。不错,她的确有丈夫,有一个美满的家,但她所做的一切只是人们希望她做的,她自己活泼涌动的热情却一直被禁锢着,她渴望从丈夫那里得到爱和关怀,而丈夫每次写信回家,只是遵循传统,在信的末尾问候妻子一句,再没有其它的。从丹尼亚尔身上,查密莉雅感受到了心与心的对话和交流,感受到了那融化一切的真情:艾特玛托夫一直认为,音乐是来自于宇宙的旋律,有着无法抗拒的魅力。查密莉雅即是在丹尼亚尔的歌声中找到了自己感情的真正归宿。
作家在谈到对查密莉雅出走的肯定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人道主义是人的一种自然、不可分离的本性,是人的伴侣,它就象人需要劳动那样,是极其自然和平凡的。”〔3 〕小说《查密莉雅》的成功首先在于作者敏锐地抓住了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对人性深层次的探讨。丹尼亚尔对生活的丰富理解常常得不到回应,只好默默无语;查密莉雅身受着束缚,心却在抗争;谢依特爱哥哥,又同情理解着查密莉雅……在这些矛盾不断冲撞的过程中,作者以真挚的笔调颂扬了人道主义,使自然的人性最终获得胜利。艾特玛托夫正是把握了读者对人类这种真情实感的认同性,同时又赋予作品浓厚、独特的吉尔吉斯民族风情,使小说既新鲜又不陌生,既民族化又沟通着各类读者的心。
法国评论家皮耶尔·列思丢尔认为艾特马托夫在《查密莉雅》中继承了高尔基的传统,将人类的生存置于生活的琐事和悲观离合之上。比利对评论家布兰科夫·斯卡尔说:“这位吉尔吉斯作家所要肯定的价值,是浸透着深厚人道主义的价值。他在与我们共享自己民族的丰厚文化时,又将它和全人类的价值观相连系。他为整个人类文化的宝库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法国著名作家路易·阿拉贡则称这篇小说为“描写爱情的空前杰作”。
艾特玛托夫对悲剧有着一份特殊的钟爱,这也许缘于少年时代经历了父亲无辜被害和战争给家乡带来的苦难。前不久,在与日本作家池田大作进行对话时,他专门阐述了这个问题。艾特玛托夫认为悲剧性是人内心世界的一个标志。当人在自己的活动中与真理、正义的相反面相遇时,人性便在悲剧性的各种历程中展现开来。悲剧并不是因为简单的没有出路而造成的。生活中和艺术中对没有出路的理解也不是丝毫不差的。比如,朱丽叶的死在莎士比亚的笔下,已不单单是因为没有出路了,这个死具有巨大的反击力量——这是来自心灵的力量,是不屈服、不妥协,是一种坚定性的表现。这是爱,又是恨,是付出生命代价而对人性的肯定。艾特玛托夫还认为悲剧是艺术的最高形式,而现代文学会在这一标志下不断发展。因为悲剧能引起同情,这也正是它的力量所在。这种对悲剧的理解和思考,使艾特玛托夫笔下出现了一系列悲剧人物。
1969年问世的中篇小说《永别了,古利萨雷!》即为我们展示了一种人性的悲剧。小说以描写60年代吉尔吉斯集体农庄的生活为背景,塑造出羊倌塔纳巴依这个平凡、普通的劳动者形象。他年轻时充满热情,愿意做别人都不想干的苦差使,去山沟沟里放马、牧羊,曾经是个榜样人物。后来,由于集体农庄管理混乱,导致大批羊羔死亡,而塔纳巴依却成了替罪羊,成了其他人争权夺利的牺牲品。最后,他的党籍也被开除了。
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命运如此坎坷,使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塔纳巴依悲剧的根源在哪里呢?细细体味,不难发现,他的悲剧是人性的悲剧。他只懂得勤苦劳作,而不善于对自我、对社会进行合理、及时的思考,一直停留在被动接受过程中,无法驾驭自己的命运。从另一方面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塔纳巴依的悲剧并不属于他自己,这是那个时代、那种生活的悲剧,而又因为艾特玛托夫从那种典型生活中挖掘出人性上的深刻哲理,使塔纳巴依的形象具有了代表性。
艾特玛托夫在1970年发表的小说《白轮船》也是一部清新优美的悲剧情节作品。小说以流传着许多美丽传统的伊塞克湖为背景,沿着莫蒙爷爷给自己的孙子叙说吉尔吉斯人的祖先长角母鹿的神话故事这一线索,展现了现代生活中的人忽视祖先宝贵的遗产而过渡挥霍,使自然遭到破坏,使人内心的美好愿望纷纷破灭的现实。
伊塞克湖区位于吉尔吉斯的东北部。那里群山环绕,包围着神秘美丽的伊塞克湖。湖水清澈碧蓝,四周的山上终年积雪。冬天湖水并不结冰,一汪轻盈的海蓝被周围银白的世界映衬着,格外迷人。吉尔吉斯人总是以他们拥有这样一个冰雪晶莹的湖泊而自豪。关于它,还有一个动人的传说。
相传很久以前,在这片山区住着一位美丽的姑娘,附近的居民都传颂她的勤劳和美德,说谁要是能娶到她,谁便会终生幸福。当地的大巴依听说了这件事,便几次带着重礼去求婚,但均遭拒绝,姑娘不愿嫁进富人家做妾。大巴依无计可施,便在一个月黑的晚上掳走姑娘,把她锁在自己的小楼上。姑娘对着窗户流了许多眼泪,那些眼泪慢慢聚成一片水洼。最终,姑娘为了不屈从大巴依纵身跳下小楼,那盛着眼泪的水洼于是化成一个巨大的湖泊,湖水是咸的,人们说那是姑娘的眼泪,湖面永远是那么纯蓝透明,人们说那是姑娘的眼睛。
艾特玛托夫在小说《白轮船》中,通过莫蒙爷爷的口为我们讲述的长角母鹿的故事同样也充满了耐人寻味的哲理。传说吉尔吉斯人在一次遭到外族入侵的血战中几乎全军覆没。长角母鹿在危难的时刻救走了族人中仅剩下的一男一女,她精心地一直抚养两个小生灵,用自己的乳汁将他们喂大,使得吉尔吉斯族得以延续。在吉尔吉斯人看来,母鹿就象他们的祖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可就是这位自己对母鹿念念情深的老人,却无法不屈从女婿阿洛斯古尔的强迫,开枪打死了一只酷似传说中的白色母鹿。小男孩寄托的美好理想和希望都破灭了,他投入大湖,游向能载他驶向幸福的白轮船。
古老的吉尔吉斯神话传说在《白轮船》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单独构筑了“过去”这一层面,使小说的结构框架坚实地建筑在过去、现实、未来这个三角面上,达到了一种较好的艺术上的审美效果。
中国读者大都非常喜爱《白轮船》,因为伊塞克湖的美丽传说,因为小男孩的纯洁不屈,也因为莫蒙爷爷的沉痛创伤和阿洛斯古尔的冰冷无情。对这些人物的细致刻画和精心描绘,使整篇小说在不长的篇幅内道出了许多深刻的哲理。
1980年与读者见面的长篇小说《一日长于一百年》可称为艾特玛托夫的一部力作,它使艾氏的创作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这部作品以具有浓郁中亚民族气息的萨雷——奥捷卡大草原为背景,不仅以一个偏远冷清的铁路会让站为中心涵盖了40—60年代发生的社会、历史事件,描绘出一个具有深刻时代气息、时代性格的铁路工人叶吉盖的高尚形象,还将作家逐渐成熟起来的宇宙思维观念,以“外星来讯”的形式穿插其中,使小说的结构得到了丰富的内部扩张,使故事情节增加了悬念和吸引力。
小说的基本框架是一个送葬的过程。铁路工人叶吉盖的多年挚友卡赞加普去世了。叶吉盖在给他送葬这一天的时间里,回忆了他们相识、相知,一同在这个风雪小站默默工作的故事。
叶吉盖是作者倾心塑造的一个代表着时代精神的人物。正如生活在中亚一带的国家一样,你会感到,那里并不繁华,处处都紧贴着大自然,简单而朴素。但生活在那里的人却紧跟着时代的步履,他们的精神生活,透过辽阔的草原,散发出诱人的魅力。叶吉盖是个普通劳动者,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只是默默无闻地工作。他的生活范围并不广阔,偏僻的小站将他与热闹繁华的城市现代生活隔离开来,他甚至不是很清楚有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正发生在他的周围,在谈到这一人物的魅力所在时,作家自己说:“给文字肌体赋予生命的心脏——是人物的性格。一本书的当代内容,首先取决于主人公身上的时代感展现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他作为自己时代的人达到什么程度。”〔4〕的确, 在叶吉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向上、不屈、自尊、爱憎分明的时代风貌。布兰内的叶吉盖是一个“支撑大地的人”。他懂得,人不能只为自己活,那样会难以找到自我。每个人都应明白,他是谁,和他血脉相连的都有什么,他永远都应该为自己的过去和未来着想。
《一日长于一百年》不仅胜在对人物的刻画、对现实的反映上,作者还利用传说和神话的穿插,使叶吉盖和民族记忆、人民的命运紧紧相连,使他成为人的生命最高价值的体现者。同时,神话、传说还使小说的艺术构思、结构框架显得完美而巧妙。也许正是由于少年时代艾特玛托夫窥见了传统文化和民间传说的奇光异彩,神话和寓言才被作家越来越深地挖掘出来,而成为他创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0世纪艺术作品的神化性同时出现于詹姆斯·乔伊斯的现代派作品《似水流年》(1922)和托马斯·曼的现实主义作品《魔山》(1924)中。而在此之前,人们运用神话时,都未想到,它可能会成为某种形式的社会意识。从前,神化性艺术一直被当做是一种模仿形式,它使作品有双重意义。实际上,它可广泛运用于各个艺术层面上,以达到各种目的。如突出人物性格、帮助情节的发展等。它也不是一种静止不动的、受时间限制的典型形象。在新一代作家的不断实践中,假定性艺术思维已成为一种流动的艺术结构。在思索过程中的神化模式与新的现实在艺术上相结合,产生出一种新型的艺术建构,它们与神化本身是分立的,但由于有神化的存在,其内涵便得到了丰富,其层次也变得多重化。
在小说《一日长于一百年》中,艾特玛托夫正是利用阿纳贝特墓关于杜年拜鸟的传说和关于宇宙“林海人”的大胆设想,为自己的作品在艺术结构上创造了多维空间,在思想内容上拓展了哲理意义。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假定性使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上升为公众意识,它已成为一种进行艺术概括的方法。它着重致力于揭示我们时代的精神领域,揭示人和传统、人和未来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使刻画人物性格、展示人物内心的素质潜能和精神风貌增加了立体效果、多个层面。艾特玛托夫创作过程中的这一大特点,值得我们作更进一步的探讨。
长篇小说《断头台》于1986年出版。这也是艾氏创作中的一部重要作品。对于这部作品,一直众说纷纭,在国内外都存在着完全相反、差别极大的各种评论。有些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结构散漫,东拼西凑,不是大家之作。而另一部分评论家则认为小说是艾特玛托夫的又一个创新。它看似结构零散,实际上每个篇章均无形地相联系,设计得十分巧妙。笔者认为,从长篇小说《断头台》开始,艾氏的创作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作家在逐渐改变他纯朴、自然的文风和娓娓的故事叙说,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理性的思考,投入对人性、道德等问题的哲学探讨。他强烈地意识到,在科技、物质文明日益发展、丰富的现代社会,人的精神文明却经受着严峻的考验。越来越多的人抵御不住对权、对利的渴求,开始挥霍祖先的宝贵遗产,破坏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使道德沦丧,爱心泯灭,令人忧虑。小说《断头台》即描写了人和自然的强烈冲突,表达着作者深刻的忧患意识。
写作手法的变化并没有使艾特玛托夫离开他热爱的家乡,特别是对一对狼夫妻的生活辗转的描述,使作品显露出浓郁的民族风格。
小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描写青年编辑阿夫季为写一篇针贬社会时弊的报道,深入到在中亚一带进行毒品买卖的贬毒团伙中进行查访。他一心向善,试图以自己的说教感化那些毒贩子洗心革面。但他的劝导被嗤之以鼻。阿夫季惨遭毒打,奄奄一息地被抛下火车。
第二部分描写阿夫季醒来后,被胡里胡涂地带到莫云库梅大草原,成为大规模围捕羚羊的一员。他不忍心对那些世世代代以草原为家的生命开枪,被同行的人绑在树上,最终凄然死去。
第三部分写得更为流畅、自然。它塑造了一个兢兢业业、朴实、善良的牧人鲍斯顿的形象。如果说小说的第一、二部分稍显诲涩的话,第三部分则保留了从前作品的风貌。牧人鲍斯顿与唯一的儿子相守着生活。一次放牧的时候,他发现村人巴扎尔拜掏了狼窝,拿狼崽子去换酒喝,他上前劝说,却不起作用。丢了狼崽子的母狼阿克巴拉闯进鲍斯顿家的院子,刁起孩子往外走。鲍斯顿向母狼开了枪。母狼倒下了,不幸的是自己的儿子也中枪而亡。故事的结局十分令人悲痛,使我们意识到,人在破坏与自然的关系时,自己却付出着更沉重的代价。
艾特玛托夫从他的成名作《查密莉雅》开始,在文坛上一直是以文风朴实、语言自然见长,以揭示本质性内涵和捕捉矛盾交点而受人瞩目的。当然,随着作家年龄的不断增长,他的生活经历的改变,使他对周围事物和人、自然本身的思考不断深入。很自然,作家的艺术思维方式也在不断地复杂化。这种过程很明显地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它所揭示的方方面面更为交错,而并不很直观了。这一方面,使得一些熟悉他作品、并十分喜欢他清新明朗的写作手法的读者、批评家对《断头台》产生了一些疑惑,觉得它似乎是作者艺术思维穷尽的产品。由于无法继续解释人、生命本身的一些问题,只好求助于神、上帝,求助于狼。那些大段的关于耶稣殉难的描写更有模仿之嫌,手法并比不上布尔加科夫。而另一方面,也有许多评论家能正确看待艾特玛托夫在创作上的不断探索和求新,认为《断头台》是一部和谐精美的交响诗篇。
从最新问世的长篇小说《卡桑德拉印记》(1995年》可以看出,艾特玛托夫自《断头台》开始在创作手法和艺术思维上的转变得到了继续。作家在故事发生、发展的安排上除更注重矛盾的尖锐化、情节的突发和快速转变性外,小说的哲理性思考的痕迹更为突出。篇首大段理念性狠抓虽使小说读起来不是那么简单,但之后的情节发展一气呵成,读来非常引人入胜。
小说是以来自遥远的太空站,一封致罗马教皇的公开信开篇的。俄罗斯学者安德烈·克雷里左夫自称宇宙僧人费拉菲依,他经过自己多年在太空站的科学研究,发现了一个人类繁育的重大秘密——妇女在怀孕时,身上会出现许多明显的变化,而有些妇女的额上会出现一粒黑色的斑点。弗拉菲依发现,这其实并不简单只是一个斑点,它预示着她将降生的孩子会给世界带来不幸和灾难,是战争、饥荒、凶恶的象征。弗拉菲依把它称之为“卡桑德拉印记”。
卡桑德拉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人物。她是特洛伊斯王普里阿姆的女儿。传说阿波罗为了给卡桑德拉献殷勤,赋予她神力,能预知未来。但卡桑德拉并未因此接受阿波罗的求爱。阿波罗为了惩罚她,又下了另一个咒言,使人们不相信卡桑德拉的预言,虽然这些预言都是千真万确的。宇宙僧人弗拉菲依告诫人们,额头上出现了这种印记的妇女及其家人要认真考虑,并不仅为自己的孩子,还要为整个世界的和谐与安宁认真考虑。
这则消息一经电视的披露,立即引起全世界的恐慌和关注,因为这涉及到每个人、每个家庭,和大家息息相关。美国正在进行总统大选,后选人之一奥利威尔·奥尔多克在发表竞选演说时被许多人问及对这则新闻的看法。他向好友人类学家罗伯特·波尔特询问,罗伯特深知,这是对人类的一次巨大考验。他以一个学者的公正态度告诉奥利威尔应该正视“卡桑德拉印记”的发现,并向选民们仔细解释。但奥利威尔认同“卡桑德拉印记”的话刚一出口,便遭到选民们的极大抵触。人们根本不愿面对这个现实,认为这是对人们正常生活的一种愚弄。奥利威尔以政客的狡滑立刻改变了立场,并出卖了多年的朋友罗伯特。为了赢得选票,他公开表示,认同“卡桑德拉印记”并非他的愿望,而是受到罗伯特的蛊惑。于是激动的人们包围了罗伯特的家,不愿听任何的解释,开始围攻和殴打。罗伯特自己都未意识到他将很快死在群众的围剿下。而宇宙僧人弗拉菲依早就预见到,人们现在还无法接受这个预言,还没有清醒的头脑和超前的意识冷静地思考未来。他也不愿返回地球,而将自己抛入宇宙中自由坠落。他是带着对未来的希望葬身宇宙的,因为他坚信在未来,人们一定会有勇气面对这个现象。不能忽视的是安冬尼·雨戈尔这个形象。他本是总统候选人奥利威尔年轻、忠实的助手。但渐渐地他发现,他所跟随的人并不是他理想中治理国家的雄才,只不过是一个投机政客。真正的英雄是敢于面对严峻挑战的罗伯特。虽然于事无补,但还是为深陷困境的罗伯特做了许多努力。在罗伯特和弗拉菲依相继死后,安冬尼成了作者希望的延续,是我们的安慰。
小说的结构依然是建筑在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个层面上。随着每一部小说的问世,我们可以看出艾特玛托夫不断地在将这几个层面之间的联系复杂化、交错化。过去,是卡桑德拉的神话,她在神话中得不到相信,在现在也得不到认同,在未来呢?卡桑德拉预言贯穿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现在的世界是代表过去的宇宙僧人费拉菲依——他与“卡桑德拉印记”密切相连,代表现实矛盾的奥利威尔和罗伯特——他们对“卡桑德拉印记”的选择反映了现实世界人们认识中的尖锐矛盾,还有代表未来的安冬尼——他将是证实“卡桑德拉印记”的希望;未来的世界都留给了安冬尼。这些点在三个层面上构成纵横交错的线条,使小说表现出现代社会中人们纷繁错乱的心态,给读者以时空交汇的现代感。的确,现代社会再不是从前那种单纯、简单的人和事了,在奇异缤纷的现代生活中,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矛盾叠合、交织在一起,而人们也需要以更大的勇气和更睿智的头脑去面对。《卡桑德拉印记》在同读者见面后,引起较大争议的是作者的写作手法。作家在小说中运用了叙述、报道、纪实、荒诞等多种手法,使小说读起来有多种文体的感觉。一些批评家认为,这是一种“大杂烩”,而不是小说。对这个问题,作家自己谈道:“小说中同时运用了多种手法。有幻想、有现实、有报道、有电影片段、有散文、有话剧。总之,一切都有。……到现在为止,我一直有着内心的斗争,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在所有写作手法、所有艺术形式中的出现,使我并不开心——它很具挑衅性。但现在,我很多地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后代考虑……我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是一种对人的新角度的观察。这是勇于面对一些可怕的、不愉快的东西,从而揭露出我们从前想掩盖或修饰的一切。旧文学中对正面形象或负面形象的忠实塑造,在我心中破灭了,而破灭它的力量正是后现代主义。但我还是不想说,后现代主义是未来的世界文学。它当中有许多东西仍使我警觉。无论怎样,它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必然会产生的。”基于这种想法,作家认为,小说中出现多种手法的描述是必然的,而在未来,一切终将是归一的。其中各类宗教劝善的宗旨都一样,它必将会大同。而写作手法也一样,都是为了交待事件,表达思想,在未来,也许它们会很自然地同时出现在一部作品中。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承认,艾特玛托夫是一位具有超前意识的作家。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将背景置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美国。在吉尔吉斯,许多读者就此向作家提出了问题:他们已习惯了那些飘着清风的空阔的原野和那些带着大山气息的朴实、善良的主人公,对这个遥远星球上的费拉菲依不免有些生疏之感。艾特玛托夫自己也讲,他的下一部作品仍将是以中亚生活为背景的。故事大概会发生在他的家乡——塔拉斯河谷。看来,作家自己也意识到,家乡、故土确实是他无论身在何处也丢弃不掉的创作之魂。而从家乡的生活中,提炼出人类思想的精华和哲学的启示,使艾氏作品走出了家乡的重重山峦,走进了世界各国的万户千家。
注释:
〔1〕《ПΛач над пропастъiо》,цзд. “рауан”,1996,с.9.
〔2〕〔3〕〔4〕《对文学和艺术的思考》, 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4,27,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