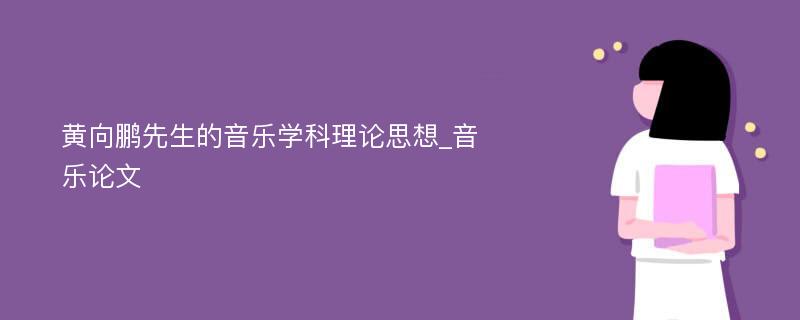
黄翔鹏先生的音乐学科理论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论文,理论论文,思想论文,音乐论文,黄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黄翔鹏先生是当代中国音乐学界公认的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在音乐史学、音乐民族学、音乐考古学、乐律学等学科为中国音乐理论的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今天,我们纪念他,研究他的学术理论及其思想,这对于促进中国的音乐学研究,建立中国音乐理论体系并将这一宏伟的系统工程全面推向21世纪,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先生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笔者才疏学浅,不仅不可对其进行全面而深刻的论述,而且就本论题所示的“音乐学科理论(注:在我国当前的音乐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两个具有不同内涵的研究对象,笔者曾将之称为“音乐理论与音乐学科理论”。前者,是指各种具体的音乐研究之理论;后者,则指对音乐理论研究的再抽象,是说明、阐释和研究、探讨音乐理论研究的理论。参拙作《音乐理论与音乐学科理论》,载《黄钟》1996年第2期。)”思想,也只能在笔者所接触的有关文献范围之内,谈谈学习体会而已。
一
在先生留给我们的诸多论著中,既有《曾侯乙钟、磬铭文乐学体系初探》、《中国传统音调的数理逻辑关系问题》、《均钟考》、《两宋胡夷里巷遗音初探》、《中国传统音乐的高文化特点及其两例古谱》等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并直接作用于中国音乐理论建设的重要文献;也有诸如《中国人的思路、风格和气派》、《音乐考古学在民族音乐型态学研究中的作用》、《传统乐种召唤着研究工作》、《对“中国乐律学史”学科建设问题的一个初步构想》、《音乐学在新学潮流中的颠簸》等发人深省,并对中国音乐学研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文章。依笔者愚见,在上述两类论著中,前者属“音乐理论”之研究,后者则属“音乐学科理论”之研究。一般在人们的印象中,先生的“音乐理论”研究较之“音乐学科理论”研究更为引人注目。可能原因之一在于:先生在“音乐理论”这一领域的研究上著述较多,而在“音乐学科理论”的研究方面,专门的论述相对较少。特别是后者——先生的许多有关中国音乐研究的主张还常常散见于在标题上不大显赫的诸如“序言”、“纪念”、“回忆”等文章中。不仅如此,先生还在一些文章中对音乐理论界目前存在的只注重“方法”(音乐学科理论中的一个领域)研究,而不注重对“音乐本体”进行研究的倾向提出过批评。因此,似乎容易让人形成一种错觉:先生主要是一个研究“音乐理论”的学者,而较少考虑“音乐学科理论”的建设问题。或者说,先生只重视具体的研究,而不重视“方法”研究,甚至是反对研究“方法”的。对此,笔者想谈谈自己的看法,并对先生的“音乐学科理论”思想及其在中国音乐研究中的作用和意义作些初步的探讨。
二
首先,先生是非常重视音乐学科理论研究的。特别是当中国音乐学界对国外有关音乐学科理论成果了解甚少的时候,先生主张打开国门,借鉴国外的有关学科理论。如80年代初,他曾“向出版部门有关负责人呼吁:应化大力气把国外有关民族音乐学的文献和资料系统翻译出版,以使我国对国际上这门学科的进展情况以及他们的研究方法和具体研究成果有一个明白的了解,作为我们发展这一学科的参考和借鉴。(注:董维松、沈洽编:《民族音乐学译文集》前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第1版,第10页。)”至90年代初,先生还提出要“重视基础研究”的主张。认为在考虑学科建设的时候,要有务实的精神。如对音乐民族学来说,他极力推荐并建议要尽快翻译西方“比较音乐学”时期的奠基作品——黑尔姆霍茨(Helmholtz)的《论音的感觉》(注:黄翔鹏:《重视基础研究 培养后备人才——在一个学术规划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载黄翔鹏《中国人的音乐和音乐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55页。)。因为这对于中国的音乐民族学学科理论建设来说,是一篇重要的参考文献。对于80年代以来,音乐民族学(ethnomusicology)的引进和提倡,先生是抱以极大的热情:“内地之于裕固族音乐、基诺族音乐、白族音乐的研究,如此种种,渐已有所展开,学界的调查研究之风,出现了可喜现象。(注:黄翔鹏:《王耀华〈三弦艺术论〉序言》,载黄翔鹏《中国人的音乐和音乐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51页。)”并评价此学“从其单纯着手于比较研究,进而发展为重视民族学研究与文化历史阶段的研究,实在是一个拓展视野和从深搜抉的过程。(注:黄翔鹏:《王耀华〈三弦艺术论〉序言》,载黄翔鹏《中国人的音乐和音乐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51页。)”不仅如此,先生还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国音乐民族学研究的“高文化”领域:要注意中国与东亚各国、与西亚各民族、与古印度系音乐文化的历史联系和比较研究(注:黄翔鹏:《王耀华〈三弦艺术论〉序言》,载黄翔鹏《中国人的音乐和音乐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52-53页。)。
其次,先生还身体力行,撰写过为数不少的专论音乐学科理论的文章。如著名的《乐问——中国传统音乐历代疑案百题》(注:参《音乐研究》1997年第3期,第5页。),可看作是先生关于中国古代音乐史的一部研究提纲。该文集先生40余年的研究心得,“以一百个小标题的形式,在考察了既往音乐史著述之后,提出了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史上的一系列重大阙疑环节,为真正反映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内在科学规律,重新写作中国音乐史提出了新的起点和任务。(注:参《音乐研究》1997年第3期,第5页,整理者按语。)”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百问’,不是‘百解’,是提问题,不是回答问题。(注:参《音乐研究》1997年第3期,第5页。)”音乐学科理论的研究,就是对既有音乐理论研究的再抽象。先生所提出的一百个问题,正是对原中国音乐史研究中存在问题的总结。之所以不是“百解”,一是因为先生对历史的问题极为慎重,结论下“匆忙了没有好处(注:参《音乐研究》1997年第3期,第6页。)”;二是先生将这些自己的研究之所得和盘托出,目的也是供大家继续研究。特别是其中的第1问至第40问,既有古代文献、文物方面的参考资料,还有今人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论文之篇目和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等等。这是一篇关于中国音乐史学学科理论的重要文献。此外,除了前文所提及的若干文献以外,尚有《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曾侯乙钟磬铭辞乐律学研究十年进程》、《“二十世纪国乐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的祝词》、《“悟性”与人类对音调的辨识能力》等等。
第三,在先生的所有论著中,有关“方法”的文章虽然较少,但不能据此而认为先生是不重视研究音乐学科理论的。对此,笔者以为原因有如下几点:1.对我们每个音乐学者而言,音乐理论的研究和音乐学科理论的研究是不可能平分秋色的,其侧重点与每个人的志趣、该学科的研究现状以及他周围的学术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有关。因此,“方法”文章的多少,不是衡量一个音乐学家学术水平、学术贡献的标志(完全不顾及“方法”或完全不顾及具体研究的情况则另当别论)。2.与我国目前音乐学的研究现状有关。在目前的中国音乐研究中,音乐理论的积累还相对薄弱,音乐学科理论的建设自然相对滞后。当然,这涉及到一个“音乐学科理论从何而来”的问题。不过,在笔者目前所见到的先生的论著中,对此问题虽未作明确回答,但从先生有关音乐学科理论建设的主张中可以看出(容下文详述):我们目前还应作大量的、具体的音乐理论的研究。
第四,先生并不是反对研究“方法”,而是反对那种侈谈“方法”而不脚踏实地地进行具体研究的作风。先生认为,要“善于用新方法来开垦自己脚下这块现实的基地,而不是用意于炫耀新方法的本身,也不是离开这块基地、另起炉灶来架构空中楼阁。(注:黄翔鹏:《〈民族音乐论集〉读后感》,王耀华《民族音乐论集》代序,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1页。)”在学术研究上要有“一种勇于吸收,善于消化而不以骛奇为目的的态度,”“一种不以空论为标榜而埋头苦干、虚实并务的作用。(注:黄翔鹏:《〈民族音乐论集〉读后感》,王耀华《民族音乐论集》代序,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2页。)”对于新的方法,先生说过:“如果有人限制你,不许进行‘民族学’或称‘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只许困在‘型态’范围中进行比较研究,我就举起双手赞成你起来造反了。现在确是侈谈方法论者,嫌弃‘比较’,想抛掉这个‘落后’方法。(注:黄翔鹏:《音乐学在新学潮流中的颠簸》,载黄翔鹏《中国人的音乐和音乐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43页。)”问题很明显,先生倡导的是脚踏实地、不尚空谈的学风。如果只是侈谈方法,而不运用这方法去研究,就如同只谈磨刀而不去动手砍柴一样。由此可见,先生反对的只是学术界的一种浮躁作风,而不是“方法”本身,更不是某一学科理论的引进和有关音乐学科理论的研究。
三
目前看来,先生关于中国音乐学科理论建设的主张,主要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方法”的新旧问题——“方法”是否有先进与落后之别?
对此问题,先生明确提出:“方法自然是有新、旧,而且可以论新、旧的。问题在于:我们怎样鉴别它的新、旧?何以论之?”“方法虽有新、旧,却不该以庸俗进化论的眼光把新、旧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注:黄翔鹏:《音乐学在新学潮流中的颠簸》,载黄翔鹏《中国人的音乐和音乐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42-143页。)”笔者的体会是:方法的确是有新旧之分,对我们东方人而言,分析的方法就较之综合的方法要新;定量的方法就较之定性的方法要新;逻辑的方法就较之直觉的方法要新。但是,如果我们不论研究对象是什么,不论研究目的是什么,笼而统之地认为新方法就一定比旧方法好,比旧方法先进,那就失之偏颇了。
比如,定量的方法在80年代以来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一再被提倡,并认为是一种新方法(实际上,该方法的运用并不普遍,也是应该提倡的)。这对于过去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较少注意量的倾向,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特别是对音乐的诸要素进行量化,为我们认识某种音乐形态的特征,进而求其代表性和典型性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是,如果我们不深入进行实地考察,不考虑某些曲调的重复率、运用率及其在特定文化背景中的地位和影响,一句话,忽视对其进行“质”的研究,那么,这统计的数据又能说明什么呢?再如在西方音乐研究中,分析的方法的确是运用得较多而又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特别是在对音乐形态的研究上,它那从微观处着眼的角度,往往是揭示音乐本身深层奥秘的重要途径。然而,它仅仅是诸多方法中的一种。其局限还在于:我们如果仅仅将音乐作品“大卸八块”,而不管其分析后的诸多音乐要素之有机联系,不顾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与作者的创作意图,淡化作品在流传过程中与外部世界的种种复杂关系,只能使我们的研究走向误区(注:杨燕迪:《二十世纪西方音乐分析理论述评》(六),载《音乐艺术》1996年第2期,第50页。)。
2.音乐学科理论的民族特点问题——“方法”从何来?
这是一个较令人困惑的问题。近年来,笔者逐渐感到,在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和研究中直接搬用西方的音乐民族学学科理论,总有些隔靴搔痒的感觉。对此,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过“如何看待音乐学科理论中的中西关系(注:参拙作《音乐理论与音乐学科理论》,载《黄钟》1996年第2期,第14页。)”这一问题。日前,读到不久前出版的先生的论文集《中国人的音乐和音乐学》,方知先生早在《重视基础研究 培养后备人才》一文中就说过:“用‘音乐民族学’来研究中国音乐,并不能把人家那一套搬过来就套得上去,还要再讲中国音乐的人类文化学研究(注:黄翔鹏:《重视基础研究 培养后备人才——在一个学术规划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载黄翔鹏《中国人的音乐和音乐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56页。)。”该文原载中国艺术研究院《科研动态》1991年第2期,是先生在一个学术规划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
笔者以为,先生所云之“中国音乐的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研究,就是强调研究中国音乐必须是“中国式”的。因为研究对象是中国音乐,从中总结出的“方法”也应具有中国的特点。这并不是一种封闭和保守的态度,而是说在学习、借鉴西方的音乐民族学学科理论的同时,要注意和中国的研究“实际”相结合。先生认为在展开对中国音乐的人类文化学研究时,必须重视基础工作,诸如“今文、古文《尚书》、《尚书大传辑佚书》、《山海经》等材料中有关音乐史料的基础建设工作”、“民族文化历史调查”以及“与中国社科院的历史所、考古所、民族所进行双边、多边的合作”(注:黄翔鹏:《重视基础研究 培养后备人才——在一个学术规划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载黄翔鹏《中国人的音乐和音乐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56页。)等。这些问题,正是基于中国音乐和中国的历史文化特点才提出的。我们从先生那大量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无论是他“鉴于最新的考古发现,用来分辨传统音乐的‘型态学’历史信息”,还是他“到近年来并且因之发展到‘曲调考证’工作”(注:黄翔鹏:《音乐学在新学潮流中的颠簸》,载黄翔鹏《中国人的音乐和音乐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45页。),这其中之“方法”,是不可能在国外的音乐学科理论中找到现成答案的。先生虽没有在他的文论中直接回答“方法”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但从他的有关学术主张中可以说明,“方法”只能从研究的实践中来。因此,中国的音乐民族学研究,除了要借鉴埃利斯、孔斯特、梅理亚姆、胡德等从他们的研究中总结的“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从大量的中国人的研究中总结出具有中国特点的“方法”来。
3.目前中国音乐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如何看待对音乐本体的研究?
如音乐民族学。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音乐民族学(ethnomusicol-ogy)的引进,这对促进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和中国的音乐民族学学科建设,是不无积极意义的。西方音乐民族学的研究特点是:“不仅研究音乐本身,而且也研究这种音乐周围的文化脉络。(注:曼特尔·胡德(Mant-ie Hood)关于音乐民族学到定义。转引自山口修:《民族音乐与民族音乐学》,载董维松、沈洽编《民族音乐学译文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第1版,第287页。)”这在80年代“方法论”的热潮中,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因此,在当时有一种说法,认为“打破了原来仅仅偏重于对音乐自身特点进行研究的局限,更多地注意到了与形成这些音乐密切有关的文化背景方面的问题(注:董维松、沈洽编:《民族音乐学译文集》前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第1版,第6页。)”,是西方民族音乐学与以往比较音乐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受其影响,至90年代初,人们在总结近年来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时,也认为“将传统音乐放在整个音乐文化发展长河中加以考察,致力于总体研究(注:冯光钰:《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方法的变化趋势》,载《中国音乐》1992年第2期,第69页。)”,是研究方法的变化趋势之一。诚然,从对音乐本身的研究进而扩展至对民族历史及文化的研究,“实在是一个拓展视野和从深搜抉的过程”。但若不顾中国的具体情况,也最容易因此而步入轻视对音乐本体进行研究的误区(注:黄晓和:《要关注音乐本体的研究》,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第91页。),甚至还会衍生出研究文化比研究音乐更高级的错误观念。
先生曾指出:“对于各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说来,前者(指比较音乐学对音乐本体的研究,笔者注)研究了‘其然’的问题,而后者(指音乐民族学对文化的研究,笔者注)却进一步研究了‘其所以然’的问题(注:黄翔鹏:《音乐学在新学潮流中的颠簸》,载黄翔鹏《中国人的音乐和音乐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44页。)”。然而,就目前中国的研究现状而言,尚有许多“其然”的问题未解决,因此“不应侈谈文化历史问题而离开了音乐自身。(注:黄翔鹏:《王耀华〈三弦艺术论〉序言》,载黄翔鹏《中国人的音乐和音乐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52页。)”如果认定对文化背景的研究就是高级的、先进的,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就是低级的、落后的,那就是“有意无意地要把生物学中的进化论直接搬到文化问题、社会问题上来(注:黄翔鹏:《音乐学在新学潮流中的颠簸》,载黄翔鹏《中国人的音乐和音乐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42页。)”。因为“讲学术成就必然要有个积累过程,不到那个阶段就开不了花,结不了果”,必须“老老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单凭聪明是跳不过去的。(注:黄翔鹏:《音乐学在新学潮流中的颠簸》,载黄翔鹏《中国人的音乐和音乐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43页。)”
笔者的理解是:对中国的音乐民族学研究而言,一是要注意阶段性的问题。因为目前的中国传统音乐尚处在求“其然”的阶段,大量的收集、整理工作诸如各种“集成”、“志书”正在进行。“其然”的问题没有弄清楚,而侈谈“其所以然”,这种研究岂不是空中楼阁?二是要注意文化研究与音乐本体的联系。对文化的研究固然是对音乐本体研究的延伸,但所谈之“其所以然”若与“其然”无关,这种研究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先生的有关论述,应引起我们许多中青年学者的深思。在学术问题上是不能好高骛远的,必须脚踏实地,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
此外,先生在音乐史学和音乐考古学等领域,也提出要重视对音乐本体研究的问题。如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中说:“乾嘉学派遗留下来的文献考证工作在方法上虽然未可厚非,但在我们的时代,文献学本身却应得到新的发展。”不能让我们的音乐史“停留在书面上,停留在音乐文学史的阶段,仍然要仰仗调查实践。乐器实物的调查,音乐实践的调查,可以得到最丰富最生动的材料。(注: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11页。)”再如在《逝者如斯夫——古曲钩沉和曲调考证问题》中说:“如果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只限于实物而反倒不能研究艺术品的本身,我就要劝它改用乐器考古学之类的名称;或者由我自去研究历史上音乐艺术品的本身,宁愿不当那个什么‘音乐考古学家’。(注:黄翔鹏:《中国人的音乐和音乐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9页。)”如此等等,都是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研究现状而提出的重要学术主张。
四
黄翔鹏先生的音乐学科理论思想,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杨荫浏先生的学术传统,更与我们炎黄民族深远的历史文化脉络紧密相连。正如先生在《中国人的思路、风格和气派》一文中所言,“善作多元综合的全局观和整体观”、“长于思辨而立足于实践”(注:黄翔鹏:《中国人的音乐和音乐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页。)是其特点。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学术主张,一方面是他身体力行为中国音乐理论的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重要动因,另一方面也必将对中国的音乐学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它理应成为中国音乐理论大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即将跨入21世纪,中国音乐在经历了几千年的积累和这近一百年的思考之后,应作何种文化选择,已是几代中国音乐学人的孜孜追求。其中,如何继承、发扬黄翔鹏先生的学术传统,研究这重要的理论财富,是我们中国音乐学界面临的一个新课题。限于篇幅和笔者的能力,本文所及,仅仅是其中之一部分。不妥之处,望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