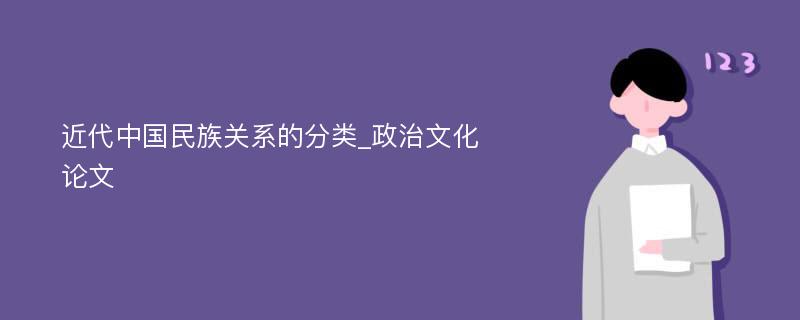
现代中国民族关系的类型划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民族论文,类型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解与分析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讨论和制定这个国家有关民族关系的制度与政策,这是每个多民族国家的政府与学者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除了极个别种族主义政权,现在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与主流社会都承认民族平等、个人自由、基本人权等是“普世价值”。这些源自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普世价值”包含了两个层面,即群体的层面(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平等)和个体的层面(个体之间的平等、宗教自由、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在近代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的过程中,首先在西欧出现了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国家”的新的政体形式,并逐渐推广到世界各地。
在各国推动“民族国家”的创建过程中,实际上不可能完全按照“一族一国”的理想模式来操作,所以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最后仍然包括了许多族群的成员,成为程度不同的多民族国家。在近两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这些多民族国家中有关“民族问题”的讨论出现了两个导向。
第一个导向是中央政府和主流社会要求加强全体国民的国家政治认同。在近两个世纪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激烈竞争中,世界各国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这一潮流中来,无论是对外扩张的强势国家,还是仅求自保的弱势国家,对本国各族国民进行政治整合成为加强政治凝聚力和国家“软实力”的必然措施,这是以“民族国家”(nationstate)和“民族”(nation)为单元的“民族主义运动”①。在进行政治整合时,要求国内各族民众把国家利益放到本族利益之上,加强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并使之成为自己心目中的核心认同,使他们在意识理念上从各种传统组织(家族、种姓、部落、部族)的成员转变为“国民”(“公民”),这已经成为各国民族政策的一个核心内容。
第二个导向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基本完成之后,民众中的民主主义运动有所加强。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是这一新思潮的代表。越来越多的民众反对种族歧视和文化歧视,提倡“文化多元主义”,要求对本国少数群体(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成员)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给予充分的尊重,以使本国的弱势族群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上逐步赶上主流群体,为了达到这一“平等”的终极目的,他们提出政府与社会应当制定政策给予这些弱势族群的成员一定的优惠待遇。
检视当前各国的种族—族群政策,大致都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1)以国家为单元的政治整合;(2)以族群为单元的文化多元;(3)政府和主流社会对弱势群体的优惠与扶助。②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各个群体的情况可能会千差万别,所以政府在制定本国的民族政策时,有可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对各族有所区别的政策或做法。
一、多民族国家的政府需要制定不同政策来对待不同族群
从“民族平等”的原则出发,政府对待所有的群体及其成员应当是完全一视同仁、毫无差别的,即“待遇的平等、机会的平等”。但是由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种种原因,各国内部各民族、族群之间在文化传统上(如语言、宗教、习俗、对待商品经济的态度)存在差异,在与中央政府的历史联系方面(是否在历史上建立过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是否长期在政治上从属于主流群体)各有特点,在社会经济水平和能力方面(主要体现在教育和职业结构方面)存在不均衡的现象,这使得各族成员在获得社会经济资源和个体发展条件的机会方面存在差距(即“事实上的不平等”),各个群体在这些方面存在的差异,应当是不争的现实。
那么,各国的中央政府是否需要设计与实施一些不同政策对不同群体实行区别对待,以便对那些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和弱势地位的群体给予特殊的扶助呢?我们知道,有些国家对历史上曾经遭受过不平等待遇的弱势群体(如美国的黑人)③ 在教育与就业方面给予一定优惠,以缩小族群之间在社会分层方面的差距;有些国家对一些历史上与主流群体有较大距离的群体给予特殊的优惠并给予某些自治权力,以巩固国家的统一(如加拿大的魁北克)。那么,各国政府在构建与巩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是否需要根据各群体与主流群体在认同程度方面的差距,对不同的群体采用不同的政策呢?
许多国家对不同群体采用了不同的政策,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各国政府在这方面的表现各异,有的只做不说(如对少数群体的歧视),有的只说不做(如对少数群体的优待),有的多说少做或少说多做。在优惠政策的幅度和实施时间的长短方面,各国政府会按照本国国情来设计制定相关政策,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对之进行调整。
在民族平等和实施优惠政策的对象方面,需要考虑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主体(多数)族群与其他非主体(少数)族群之间是否平等,是否对非主体(少数族群)实施优惠政策,而这自然就意味着对主体(多数)族群成员的不优惠,也就是实际上对主体(多数)族群成员的歧视;第二个层面是政府在对待各非主体(少数)族群时,对不同的少数族群是否采取完全一样、整齐划一的优惠政策与执行标准。例如美国政府对“有色人种”在就业和入学方面有一种一般性的优惠考虑,但是对黑人的优惠考虑的程度明显高于亚裔人(华人或日裔)。这里体现的正是“实事求是”的客观精神,哪个群体更需要扶植,对其的扶植力度也就更大一些。
这些特殊制度安排或优惠政策,从原则上讲背离了“人人平等”的普世价值,但其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与这一普世价值并不冲突。因为从各族群间存在的现实差距看,人人平等并没有落实在现实生活中,从长远发展效果看,这些制度安排与政策恰恰有利于达到“人人平等”这个终极目标。
如要制定对各族群成员实施区别对待的政策,而且希望这些政策被主流社会和广大国民所接受,需要使民众觉得这些政策符合普世价值、符合本国国情,既合情又合理。为了达到这一点,必须对国内各群体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与发展态势进行分析,通过“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在此基础上把各族群进行某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分类,有针对性地为不同类别的群体分别设计不同的政策,这样设计出来的具体政策才能符合国情与族情。在一个民族关系历史曲折、群体纷杂的多民族国家,对历史与现实中各民族的状况、对民族关系的发展态势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与分析,是制定政策的重要前提。
二、中国各民族之间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别
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政府以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和其他民族问题上的基本理论为依据,结合了各地区不同群体的实际情况,开展了民族历史与社会大调查,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全国性的“民族识别”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直至今日政府开展的各项民族工作的基础。在“民族识别”工作的过程中,对于一些“民族”的认定,在专家学者、地方干部、少数群体代表人物之间也曾出现了不同的观点,最后由中央政府正式确认了56个“民族”(nationality)④。我国目前在民族问题上的各种制度建设、政策设计都是以这个框架为基础和前提的。
在被识别出来的56个“民族”中,各族无论是在原来的社会制度、传统经济活动、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许多方面,在人口规模、聚居程度和迁移历史方面,还是在族际交往历史、各族与中央政权的关系方面都存在极大的差异。我们必须坚持“所有民族一律平等”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在政治与法律平等的基本问题解决之后,当我们考虑如何促进各少数族群的社会经济发展、如何巩固国家的政治统一、加强各族知识分子与广大民众对于中华民族大家庭和祖国的政治与文化认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其他比较深入和具体的层面。因为政治和法律地位方面的平等并不意味着在各族之间不存在重要差别,也不意味着中央政府必须对所有群体采取完全一样的政策。检验任何政策的实施效果,就是看在长期的具体实践中,这些政策是否推动民族关系走向一个我们设定的政治目标。
既然我们从历史文献和实际观察中发现了我国各族群在许多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一些重要的相关因素和分析指标尝试着把中国现有的56个“民族”归纳为具有不同特点的几种类型,然后通过类型之间的比较、对同样政策在不同类型“民族”中实践效果的比较来对有关政策进行反思与总结,这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
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从人口迁移和通婚混血的角度讨论了世界各国种族—族群关系的类型划分⑤,现在让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内,看看能否把国内的族群与族群关系归纳为几个不同的类型。我们在分析世界各国情况时,只能从最粗略的历史发展大线条来讨论,必然会忽略各国间存在的许多差异,而当我们面对中国的这些具体群体来思考类型划分时,实际上面临着更大的难度,因为我们将不得不从一些具体的指标体系入手,而这些具体的指标揭示的往往不仅有宏观上的共性和规律,更表现出各族间复杂的多样性和差别。
三、近代学者们在民族史中对我国民族的分类
从阅读文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老一代学者也曾经尝试将中国的民族进行分类。林惠祥先生在他的《中国民族史》(1939,商务印书馆)曾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当时各相关文献对中国民族之分类(见表1),笔者把林先生自己的分类内容也列入这一表中进行比较。
表1中罗列的各文献的民族分类方法,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偏重历史上的族源与族称;另一类则偏重于民国时期族群分界与语言使用状况。因此,林惠祥先生参照了以上文献的分类后把中国历史记载中出现的各种族称归纳为“历史上之民族”,将其划分为16个“系”,又把“现代之民族”划分为8“族”(见表1),林在其著作中再用实线和虚线把“历史上之民族”与“现代之民族”连接起来,以表示两者间的血缘演变关系(林惠祥,1931:9)。如“回族”(实际上包含新疆各穆斯林民族)族源主要来自历史上的“突厥系”,但又包括了其他如“华夏系”、“匈奴系”、“氐羌系”和“白种”的来源。而“汉族”族源主要来自“华夏系”、“东夷系”、“荆吴系”和“百越系”这4大系,但也从其他12个族系吸取了成员并有混血现象。应当说,林惠祥先生在这一分析框架中既注意努力分清历史族称与现实民族之间的差别,又强调了两者之间密不可分、由此及彼的历史延续关系,生动地勾画出几千年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各族间复杂多样的混血进程。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从生物基础,或所谓‘血统’上讲,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发生混合、交杂的作用,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以说是‘纯种’。”(费孝通,1989:11)
需要指出的是,林惠祥先生在分类中所依据的主要是血缘族系,而不是各族之间的共性与特性之比较。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1934,上海文化学社)、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1934,上海世界书局)、江应梁主编的《中国民族史》(1990,民族出版社)等对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民族大致也是依照血统族源来加以分组并分别叙述的。这些学者对中国历史上民族的分类,注重的是族源和族称的演变,对族群血脉的演变进行学术研究,并不代表中央政府在政策制定中对各群体的区别与分类,也不是对政府在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讨论。对后一个方面的研究,在这些民族史的研究文献中是不多见和不系统的。
表1:林惠祥介绍的近代学者对中国民族之分类
作者及文献 类别(包括的群体)
缪凤林《中国通史》 (1)北方国族(如:荤粥、东胡、肃慎),(2)东方国族(如:屿夷、莱夷、
(四裔国族表) 淮夷),(3)南方国族(如:瓯、闽、蛮荆),(4)西方国族(如:西戎)
那柯通世《支那通史》
(1)支那种(汉人、华人),(2)韩种(朝鲜人),(3)东胡种,(4)鞑靼
种,(5)图伯特种,(6)江南诸蛮
梁启超(1924)《中国
(1)中华族,(2)蒙古族,(3)突厥族,(4)东胡族,(5)氐羌族,(6)
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蛮越族
白眉初《民国地志》 (1)汉族,(2)满洲族,(3)蒙古族,(4)回族,(5)藏族,(6)苗族
章钦《中华通史》
(1)汉族,(2)满族,(3)蒙族,(4)回族,(5)藏族,(6)苗族
张其昀(1935)《中国
(1)华夏族,(2)东胡族,(3)突厥族,(4)蒙古族,(5)西藏族,(6)苗
民族志及中国地理》 蛮族
宋文炳《中国民族史》
(1)诸夏族,(2)通古斯族,(3)蒙古族,(4)回族,(5)藏族,(6)苗族
赖希如《中华民族论》
(1)中华族,(2)匈奴族,(3)东胡族,(4)突厥族,(5)蒙古族,(6)西
藏族,(7)南蛮
王桐龄(1934) (1)汉族,(2)满族,(3)蒙族,(4)满蒙混血族,(5)回族,(6)藏族,
《中国民族史》 (7)苗族,(8)东夷(族属不明)
常乃悳《中国史鸟瞰》
(1)诸夏系,(2)东夷系,(3)巴蜀系,(4)东胡系,(5)闽粤系,(6)北
狄系,(7)氐羌系,(8)西藏系,(9)苗蛮系
吕思勉(1934) (1)汉族,(2)匈奴族,(3)鲜卑族,(4)丁令族,(5)貉族,(6)肃慎族,
《中国民族史》 (7)苗族,(8)粤族(马来族),(9)濮族,(10)羌族,(11)藏族,(12)
白种
李济(1928)
(1)黄帝子孙,(2)匈奴群,(3)羌群,(4)鲜卑群,(5)契丹群,(6)女
“The Formation of the 真群,(7)蒙古群,(8)西藏缅甸语群,(9)掸语群,(10)蒙克麦语群,
Chinese People”* (11)戎,(12)突厥,(13)尼革利陀(矮黑人)
A.H.Kean,
(1)蒙古利亚种之蒙古鞑靼多缀语族(包括蒙古、通古斯、突厥),
Compendium of (2)蒙古利亚种之图伯特中间语族,(3)蒙古利亚种之中国孤立语
Geology and Travels族,(4)人种及语系不明之高地民族,(5)雅利安语族(如大食人等)
(Asia,Vol.1)
林惠祥(1939) 历史上之民族:(1)华夏系,(2)东夷系,(3)荆吴系,(4)百越系,(5)
《中国民族史》 东胡系,(6)肃慎系,(7)匈奴系,(8)突厥系,(9)蒙古系,(10)氐羌
系,(11)藏系,(12)苗瑶系,(13)罗缅系,(14)僰掸系,(15)白种,
(16)黑种
现代之民族:(1)汉族,(2)满洲族,(3)回族,(4)蒙古族,(5)藏族,
(6)苗瑶族,(7)罗缅族,(8)僰掸族
资料来源:林惠祥,1939:2-6,9(有些文献未注明出版时间)。
*李济先生论文2005年新译本中各族名的译法为:(1)黄帝的后代,(2)匈奴族,(3)羌族,(4)鲜卑族,(5)契丹族,(6)女真族,(7)蒙古族,(8)讲藏缅语族语言的民族,(9)讲掸语的民族,(10)讲孟-高棉语族语言的民族,(11)B时代的戎人,(12)E时代的突厥人,(13)无从追溯其起源年代的尼格里陀人(李济,2005:295)。
值得注意的是,翁独健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200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第四编在论述明清两朝时,分别叙述了各地区(各族)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王朝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所采取的不同具体政策。虽然他没有对不同群体进行分类,但是这一观察视角,对于理解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的民族关系极为重要。
我们考虑到需要对国内各族群进行分类,目的是为制定符合国情的民族政策寻找依据,而民族政策的核心内容是前面讲到的三个部分:(1)以国家为单元的政治整合;(2)以族群为单元的文化多元;(3)政府和主流社会对弱势群体的优惠与扶助。前辈学者们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进行的“民族分类”研究,乍看起来似乎与这三方面内容没有直接关系,但仔细审视,其实仍有许多关联。这些分类的研究主要偏重于血统族源,这与文化多元的历史追溯有密切联系,在分析各族与中央政权历史关系时,这既联系到国家进行政治整合的历史条件,也与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历史上采用的优惠政策的传统相关。但是这些摘引历史记载而做的讨论,对这几个方面所提供的信息比较零散,也没有与现代民族主义理论直接挂钩。
四、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对不同民族采用区别对待的政策
回顾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两千多年来中原皇朝对待边疆各族的政策,不难发现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对待不同的群体所采取的是各不相同的政策,而且随着该族形势和态度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政策。之所以采取这样多类及灵活的政策,其原因就是这些群体的基本情况各不相同,它们各自的人口规模、与中原汉人血缘关系的远近程度、文化习俗上接受汉文化的程度、各自的宗教信仰与传统习俗、各自的经济活动模式和发展水平都不相同,而且各群体与中央皇朝的关系在历史上也是不一样的,有的曾经非常紧密,有的则一度比较疏远,而且这些方面也随着不同年代的政治经济形势在不断变化。所以,“不审势则宽严皆误”,中央政府在理论上不应该、在事实上也没有制定出同一个政策来对待所有这些群体,因为这样一种僵化的“一刀切”政策忽视了各族间的重要差异,没有动态和辩证地看问题,是不恰当和不合理的,用来处理民族关系时会导致重大误差。所以,把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区分为不同的“群”,在制度和政策上以不同的“类”来处理,因地制宜,因势利导,这是中国历朝历代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重要传统。
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朝代在对待周边民族的制度与制定政策的传统中,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不划“界”⑥,即使各群体有特定的族称、有大致的聚居地域,但各族个体成员身份的“族属”仍是相对模糊的。也正因为这种个人身份的模糊性,从而使跨越本族传统聚居地的人口迁移和族际通婚经常发生,在各族交叉混合居住地区则尤为普遍。“分类”的目的是根据各族情况的差别来实事求是地制定以群体为对象的不同政策,“不划界”的目的则是促进各族成员在民间层面的相互交往与融合。
在《二十四史》或其他历史文献中,似乎没有出现一个具体词汇把所有少数民族都涵盖在内,而是在论及每个具体群体时使用其独立的族称(如契丹、鲜卑,而不是某某族)。这很可能是因为各群体相互之间差别很大,共性有限,无法用同一个词来涵盖所有群体。所谓“北狄西戎东夷南蛮”,那只是春秋时代的一个泛泛的称呼,表示当时的中原华夏诸国之外(甚至之间)存在着尚未完全接受中原文化的各种不同的群体。
在有些文献中出现了两个词用来称呼边疆民族,就是“生番”和“熟番”。“生番”就是指那些尚未接受教化、茹毛饮血、发展水平较低的群体;“熟番”指的是基本上接受了中原文化的群体。清朝在称呼穆斯林时,把穆斯林群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叫“汉回”,指的是讲汉语的回回;另一部分叫“缠回”,指的是西北的维吾尔、哈萨克等突厥语系的群体,也是表示两者有所不同,应予区别。
这些相互对应的词汇和称呼,像“生番”与“熟番”、“汉回”与“缠回”,也可看作某种“分类”,表示了当时统治者根据各族群的实际情况,一一分析,对他们给予不同的称呼,区别对待,一个地区设计一个制度,一类群体制定一个政策,而不是简单地制定一个单一的政策,用来对待所有的族群。中国历史上曾出现了许多有才能、有智慧、雄才大略的皇帝、政治家和学者,他们在处理边疆少数民族问题时非常小心谨慎,许多政策也是相当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没有类似当代政治意识形态(“所有民族一视同仁”)这样的思维定式,对待边疆或境内各少数民族群体的态度和政策基本上是实事求是、区别对待,并没有用同一个政策来思考、理解和对待不同的群体。而且正是因为这样区别对待,这些政策才能够被各族首领与民众所接受,既维持了中原政权的统治,也可因地制宜地促进族际交流与融合,推动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比较稳妥、恰到好处地处理好各地的民族关系。
五、西方学术界对民族、族群类型的研究
人类学研究在以种族、民族、族群为对象进行分类时,主要着眼点和依据是血统和族源,所看重的主要是人种的体质差异、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包括历史记忆、宗教、习俗等),有时也注意考古发现对族源的考证,这也是人类学四大分支(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社会学研究所关注的是社会整体结构和社会中各个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通常受到两大因素的影响,其中之一是两个群体之间的认同差距。人类学研究看重的体质、语言、宗教差距等,毫无疑问是研究群体成员之间的认同程度和心理距离的重要领域,在这个方面人类学做了许多深层次的探讨。在实证研究中,社会学家们也试图通过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来把群体之间的认同程度和心理距离进行定量的测量与分析(马戎,2004:493)。另外一个因素则是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各群体的相对地位,换言之,就是从经济利益、权力分配的阶级分析的角度来看待群体关系,也就是族群社会学中的“族群分层”研究。
人类学家们容易强调文化与认同因素而忽视社会结构与分层因素,这与人类学家偏重微观社区调查和文化分析的学术传统有关。与之相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则相对忽视文化与认同因素,而比较重视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因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尽管各民族之间存在族源、语言与文化的差异,但是“全世界的无产者却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敌人,面临着同样的斗争;所有的无产者生来就没有民族的偏见……只有无产者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恩格斯,[1845]1957:666)。所以“阶级”在认同和社会斗争中的重要性和作用是远在“民族”之上的。关于各民族的传统语言与文化,列宁(1913:552)指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最喜欢谈‘民族文化’,并且强调把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分开,从而把各个民族的工人分开,用‘民族的口号’来愚弄他们。……写在我们旗帜上的不是‘民族文化’,而是国际主义(国际)文化”。毛泽东在1963年提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⑦,他强调了阶级斗争在种族—民族关系中的实质性核心作用。
对这两方面的因素,社会学家必须兼顾,但在社会学家内部也有不同的个人偏好,其中有些偏重社会理论和M.韦伯传统的社会学者较多地关心文化与宗教因素,他们根据语系、宗教传统来对各民族进行分类,如划分为基督教民族群、伊斯兰教民族群;而受到马克思经济分析传统影响的社会学者则更注重对社会中的族群分层与流动的研究,他们根据各群体在政治权力分配结构和社会财富占有方面的相对地位对各族群进行分类,如划分为强势族群、主导族群(如美国社会的白人新教徒WASP)、弱势族群、边缘化族群等。
由于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移民社会,社会流动已形成一定的机制和规模,各族群成员在社会结构、分层体系中的地位是相互交叉和变化的,所以西方社会学家们较少使用概念固定和边界清晰的族群分类模式,这样做既充分考虑到现实社会的动态流动,也有利于避免少数族群民众对这种“分类歧视”的反弹。西方学者对于民族主义和族群关系的研究和类型分析可作为我们思考中国民族问题的借鉴。
六、对当代中国各民族进行类型归纳的因素
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对管辖下的不同群体,采用的政策是分地区、分类别给予区别对待。这体现了各群体事实上存在的各种差异,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我们面对当今中国56个民族,进行分类归纳,以探讨制度设计与政策实施的效果也十分必要的,这既可以促进学术上的族群研究,也可为政府检验政策实施效果与原定目标的距离提供依据。
我们可以尝试先从以下5组因素入手来进行分析:(1)人口变量,包括人口规模和人口聚居程度;(2)族际通婚情况,我们发现这个因素导致北美和拉丁美洲的民族关系出现重大差异;(3)文化变量,包括语言差异和宗教差异;(4)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交往历史和紧密程度),包括历史上是否成立过独立的政权;(5)境外的同族是否建立独立国家。在许多有关民族关系的文献中都曾提及这些因素,而且我们多年来在民族地区的调查也反映出这些因素在理解中国民族问题方面确实比较重要(马戎,2004:474-492)。
表2:中国各族人口规模(2000年人口普查)
分组 人口规模
族别
第一组11亿 汉族(1)
第二组超过1000万
壮族、满族(2)
第三组500-1000万 回族、苗族、维吾尔族、彝族、土家族、蒙古族、藏族(7)
侗族、瑶族、布依族、朝鲜族、白族、哈尼族、哈萨克族、黎
第四组100-500万
族、傣族(9)
第五组50-100万畲族、傈僳族、仡佬族、东乡族(4)
拉祜族、水族、佤族、纳西族、羌族、土族、仫佬族、锡伯
第六组10-50万 族、柯尔克孜族、达斡尔族、景颇族、毛南族、撒拉族(13)
布朗族、塔吉克族、阿昌族、普米族、鄂温克族、怒族、京
第七组1-10万 族、基诺族、德昂族、保安族、俄罗斯族、裕固族、乌孜别
克族(13)
门巴族、鄂伦春族、独龙族、塔塔尔族、赫哲族、高山族、
第八组少于1万 珞巴族(7)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2002:18-45。
在表2中,我们根据各族人口的规模把中华民族下属的56个族群粗略地分成八组。汉族占全国人口的91.6%,在人口规模上与其他任何族群相比的差距都是十分悬殊的,⑧ 事实上汉族可以被视为一个通过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民族融合进程所形成的综合群体,不应被简单地视作一个“族群”(马戎,2004:128)。人口超过500万的还有其他9个族群,处于100万和500万之间的有9个族群,处于10万到100万的有17个族群,人口少于10万的有20个族群。
一些人口很少的族群虽然具有某些与其他群体相区别的特点,如语言特征和关于族源的历史记忆,但是如果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他们大多属于其他大群体的旁支,在交往过程中发生某种演变而与主干群体产生差异,而且由于人口太少,他们无法形成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和文化体系,这一特点在“藏彝走廊”的小群体中表现得很明显。与此同时,当我们考察那些人口少于1万的这些族群的发展态势和他们与他族的关系时,显然也无法把他们与那些人口超过500万的群体混为一谈。
第二个因素是各族群在族际通婚方面的基本态势存在差异。
根据男性、女性的通婚比例(特别是与汉族通婚比例),我们把表3中的各族分为6大组,表中各组共列出36个族群。另外南方的阿昌族、德昂族、普米族、怒族、崩龙族、独龙族、京族、门巴族、珞巴族、基诺族、高山族;东北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西北的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裕固族以及俄罗斯族共19个族群的样本量少于10人,因缺乏统计意义,故不列入表内。以上55个少数族群加上汉族,共为56个族群。下面我们对这些族群进行分组讨论。
(1)男性和女性中至少有一方与汉族通婚比例在30%以上,另一方也不低于18%(8族)。其中人口规模大的重要群体是满族与蒙古族。满族经清朝267年和民国38年,共有305年的时间与汉族长期混居融合,在55个少数民族中是与汉族融合程度最高的一个群体。蒙古族聚居地位于华北,与多个汉族省份接壤,自清末实施“放垦”政策以来,内蒙古南部逐渐变为农业区,当地蒙古族长期与汉族混居,与汉族的融合程度在我国人口规模大的少数族群中仅次于满族。另外6个族群的人口规模都较小:畲族(71万)、羌族(30万)、锡伯族(20万)、仫佬族(20万)、达斡尔族(13万)、景颇族(13万),属于与汉族和其他族群混居模式,出现较高的族际通婚比例并不令人惊奇。其中锡伯族和仫佬族的族内婚比例分别低于30%和40%,显示出族际融合的大趋势。
表3:各族已婚男性的婚姻构成(2000年)
族群 已婚 通婚类型(%) 总样本数
性别
与本族 与汉族 与他族总计
锡伯族
男性28.955.615.6100.0 45
女性27.751.121.3100.0 47
畲族 男性47.749.0 3.2100.0 155
女性48.450.3 1.3100.0 153
满族 男性53.345.0 1.7100.02879
女性54.143.6 2.3100.02836
蒙古族
男性62.333.2 4.6100.01362
女性53.743.7 2.6100.01580
仫佬族
男性38.625.036.4100.0 44
女性39.539.520.9100.0 43
达斡尔族 男性58.634.5 6.9100.0 29
女性54.829.016.1100.0 31
景颇族
男性73.123.1 3.8100.0 26
女性67.932.1 0.0100.0 28
羌族 男性75.918.5 5.6100.0 54
女性65.131.7 3.2100.0 63
白族 男性74.519.1 6.4100.0 439
女性75.920.0 4.2100.0 431
土家族
男性74.418.0 7.6100.01820
女性73.420.2 6.3100.01844
土族 男性74.515.7 9.8100.0 51
女性66.722.810.5100.0 57
彝族 男性81.914.9 3.3100.01659
女性77.220.1 2.7100.01758
瑶族 男性74.017.6 8.4100.0 550
女性72.019.6 8.3100.0 565
布依族
男性81.713.2 5.1100.0 627
女性78.417.8 3.8100.0 653
纳西族
男性80.313.6 6.1100.0 66
女性73.616.7 9.7100.0 72
侗族 男性71.715.412.9100.0 669
女性75.414.8 9.9100.0 637
苗族 男性79.611.5 8.9100.01905
女性72.415.611.9100.02094
壮族 男性87.510.0 2.5100.03343
女性81.815.7 2.4100.03575
布朗族
男性68.415.815.8100.0 19
女性76.511.811.8100.0 17
仡佬族
男性61.114.024.8100.0 157
女性65.313.621.1100.0 147
水族 男性72.411.416.2100.0 105
女性72.414.313.3100.0 105
回族 男性86.911.6 1.4100.02424
女性86.712.0 1.3100.02431
傣族 男性87.7 9.2 3.1100.0 260
女性79.217.0 3.8100.0 288
拉祜族
男性84.3 8.3 7.4100.0 108
女性72.218.3 9.5100.0 126
黎族 男性89.2 8.2 2.6100.0 231
女性80.218.3 1.6100.0 257
佤族 男性91.2 7.7 1.1100.0 91
女性83.011.0 6.0100.0 100
朝鲜族
男性92.5 6.8 0.7100.0 439
女性87.711.0 1.3100.0 463
哈尼族
男性88.9 5.2 5.9100.0 324
女性83.712.5 3.8100.0 344
傈僳族
男性86.4 5.0 8.6100.0 140
女性87.1 8.6 4.3100.0 139
藏族 男性93.9 4.3 1.8100.0 866
女性90.2 7.7 2.1100.0 901
毛难族
男性64.7 5.929.4100.0 17
女性73.3 6.720.0100.0 15
撒拉族
男性68.4 0.031.6100.0 19
女性81.3 6.312.5100.0 16
哈萨克族 男性97.2 0.0 2.8100.0 252
女性98.0 1.2 0.8100.0 250
维吾尔族 男性99.2 0.5 0.3100.01864
女性98.9 0.7 0.4100.01870
东乡族
男性92.8 0.0 7.2100.0 111
女性83.7 0.815.4100.0 123
柯尔克孜族
男性97.1 0.0 2.9100.0 34
女性94.3 0.0 5.7100.0 35
资料来源:本表数据由北京大学2004级硕士生李睿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计算。
(2)男性和女性中至少有一方与汉族通婚比例在20%以上,另一方也接近15%(4族)。这4族除了人口较少的土族(24万)居住在青海外,其余3族都有上百万人口(土家族800万、彝族780万、白族180万),主要居住在南方多族群地区,以农业为主,汉族是当地人口的主体,所以有较高的族际通婚比例,具有族际融合的基础。
(3)男性和女性与汉族通婚比例都在11%与20%之间(10族)。除回族外,其余9族大多居住在南方各省区(云南、广西、贵州),人口规模在9万(布朗族)到1,600万(壮族)之间。这些民族都以农业为主,汉族是当地人口的主体,所以有较高的族际通婚比例,具有族际融合的基础。
回族人口近1,000万,散居全国,在族际通婚方面各地回族的情况差距很大,沿海省份,如江苏省回汉通婚约占回族已婚人数的50%以上,而西北回族的回汉通婚率则很低。以上特点再加上回族在宗教信仰上的传统,回族在中国各少数民族中应单划为一类,而第(2)组和第(3)组的其余南方各族可以合并为一大类。
(4)男性与汉族通婚比例在10%以下,但女方与汉族通婚比例在10%到20%之间(6族)。这一组除朝鲜族外,其余5族都居住在南方各省,以农业为主,汉族是当地人口的主体,有较高的族际通婚比例,由于女性与汉族通婚的比例高于男性,这是本组在族际通婚中的特点,显示出族际融合的发展趋势。
(5)男性和女性与汉族通婚比例都在4%与9%之间(3族)。傈僳族(63万)和毛南族(10万)分别居住在云南和广西,毛南族男女性与其他少数族群的通婚比例占总婚姻数的20~29%,处于族际融合进程之中。藏族居住在青藏高原,当地的汉族人口规模很小,如西藏自治区汉族人口仅占常住人口的3.6%,所以汉藏通婚少,有其客观原因,故本组中的藏族情况应单列一类。
(6)男性与汉族的通婚比例都低于0.5%,女性低于1.2%。属于这一组的是西北的5个穆斯林民族,由于宗教信仰和相关生活习俗,穆斯林族群一般保持族内婚,在族际通婚方面这一组的特点是十分明显的。
表4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了14个族群的通婚情况,这张表是从2000年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库中筛选出有0—9岁子女的夫妇作为样本计算的,样本规模不大,而且许多族群由于样本量太少没有被吸收进这一分析中,只选出了样本量在100或接近100人的14个族群。由于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分析族际通婚家庭中子女申报“民族成分”的选择性,所以与表3相比,表4反映的是年轻夫妇(假设以25岁为结婚年龄,婚后一年开始生育,那么表中的样本反映的是26-36岁组)的族际通婚情况,这有助于我们分析1990-2000年期间这些族群在族际通婚方面的发展趋势与特点。
表4: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计算有0-9岁子女的14族通婚情况
族群 0-9岁 父母通婚%族群0-9岁 父母通婚 %
抽样人口 类型抽样人口 类型
族内通婚
47.5 族内通婚 69.3
满族 1242
与汉族通婚 51.0
侗族 384 与汉族通婚17.4
与他少通婚 1.5 与他少通婚13.3
族内通婚
47.2 族内通婚 73.7
蒙古族 826
与汉族通婚 49.0
苗族 1294 与汉族通婚15.6
与他少通婚 3.8 与他少通婚10.7
族内通婚
72.4 族内通婚 86.0
白族
257
与汉族通婚 23.3
壮族 1688 与汉族通婚11.8
与他少通婚 4.3 与他少通婚 2.2
族内通婚
65.3 族内通婚 88.3
瑶族
334
与汉族通婚 23.1
回族 1444 与汉族通婚10.5
与他少通婚 11.7 与他少通婚 1.2
族内通婚
74.2 族内通婚 87.8
彝族 1426
与汉族通婚 22.7
朝鲜族 98 与汉族通婚10.2
与他少通婚 3.1 与他少通婚 2.0
族内通婚
73.1 族内通婚 90.9
布依族510与汉族通婚 22.2
藏族 778 与汉族通婚 8.2
与他少通婚 4.7 与他少通婚 0.9
族内通婚
70.0 族内通婚 99.4
土家族960与汉族通婚 21.8
维吾尔族 1421 与汉族通婚 0.1
与他少通婚 8.2 与他少通婚 0.5
资料来源:李睿,2007:13。
第一,蒙古族和满族的族内婚比例低于50%,而与汉族通婚比例超过族内婚的比例,这一比例高于表3中的比例,这说明近年来这两个群体对于族际通婚的态度更加开放。满族已经通用汉语,也没有很强的宗教传统,这都有利于满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与通婚。农业区的蒙古族也大多通用汉语,与汉族混杂居住,这为族际通婚创造了客观条件,所以,满族和蒙古族与汉族的关系和相互融合程度在55个少数民族中是最高的,而且有加快的趋势。
(2)除了蒙古族和满族外,表4中还有7个族群的族内婚比例低于80%,其中彝族、布依族、瑶族、白族和土家族这5个族群与汉族通婚的比例占总婚姻数的20%以上(表3中的比例均低于20%),另外2个族群(苗族、侗族)与汉族通婚比例分别为15.6%和17.4%(表3中分别为13.5%和15.1%,为男女平均值),同样说明这些族群与汉族的通婚比例有增加的趋势。
(3)族内婚比例最高的是维吾尔族(99.4%),其次是藏族(90.9%)。维吾尔族人口主要聚居在南疆,加之有很强的宗教因素,这两个因素限制了维吾尔族与其他非穆斯林族群的通婚。由于年轻夫妇中的族内婚比例高达99.4%,高于表3中男女平均数的99.05%,这也许说明了近年来维吾尔族在族际交流和族际通婚方面有进一步封闭的趋势。
藏族人口高度聚居在青藏高原,那里的汉族移民数量很少,客观上限制了族际通婚。表3中藏族男女族内婚的平均比例为92.05%,表4中为90.9%,这说明族际通婚在藏族的年轻人中有所增加。
七、对中国各民族进行的初步类型归纳
参考了以上的数据分析,从人口规模、聚居程度、独立语言、宗教因素、族际通婚、与中央政府关系、是否本族在境外建立独立国家这七个方面来看,也参考了历史上中央政权对待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框架,我们把中华民族下属的各族群初步归纳为八大类,并以具有代表性的某一族为首。
(1)藏族:人口规模较大,高度聚居,有独立语言文字,藏传佛教与其他宗教相比特点突出,族际通婚比例很低,西藏在历史上曾一度相对独立,这几个特点使藏族成为独立的一类。但是居住在青海、川西、甘南、滇西北的藏族在语言、政治传统上与西藏有所区别,清朝的管理办法也不相同,这一点应予注意。
裕固族人口较少(1.4万),信仰藏传佛教,聚居地邻近青海藏区。门巴族(9,000人)、珞巴族(3,000人)居住在西藏东南边境上,信仰藏传佛教,与藏族联系密切。土族(24万)居住在青海藏族、回族、汉族杂居区,大多信仰藏传佛教,与藏族关系密切。以上4族似也可归为本类。(本类共5族)
(2)回族:人口规模较大,在全国呈散居,但在部分地区聚居,通用汉语文,普遍信仰伊斯兰教,具有一定的族际通婚率,因而可成为独立的一类。宁夏自治区和临夏自治州的回族相对聚居,与散居在其他各省的回族也应有所区别。另外,甘青地区的3个穆斯林族群(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在历史上与回族联系密切,虽有语言但无文字,通用汉语文,也可大致归为这一类。(本类共4族)
(3)满族:人口规模较大,已经通用汉语文,散居在全国各地,与汉族有很高的通婚比例,可以归为单独一类。赫哲族和锡伯族在清朝时期与满族关系密切,语言都属于满语支,除新疆部分锡伯族人口外,两族都通用汉语文,可归入满族一类。(本类共3族)
(4)蒙古族:人口规模较大,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南部农业区蒙古族人口与汉族长期杂居,有很高的通婚率。由于历史原因,蒙古族在境外建立有独立的民族国家,与其他族群相比,这是蒙古族的一个特点。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与蒙古族族源相近,可归为这一类中。(本类共4族)
(5)朝鲜族:人口有一定规模,是上世纪从境外迁入的群体,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人口相对聚居,与汉族长期杂居,有一定的通婚率(10%左右),境外有独立的民族国家(事实上是两个国家)。(1族)
(6)维吾尔族:人口规模较大,人口聚居,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普遍信仰伊斯兰教,基本上属于族内婚,是独立的一类。(1族)
(7)新疆的其他4个穆斯林族群(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可归为一类,共同特点是族源相似、人口聚居、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有自己语言文字,族际通婚率低,境外建有独立国家。新疆其他两个群体(塔塔尔族、俄罗斯族)人口很少(0.5万和1.6万),混居在以上各族聚居地中,也可归为这一类。(本类共6族)
(8)南方各族群(除了以上7大类的24族之外的31族):这些族群人口规模不一,本族相对聚居的同时又与汉族和其他族群相互混居,有一定的族际通婚率,且有增加的趋势,大多有自己的语言,没有文字,或虽有文字,但没有普遍使用,主要从事农业,有自己的信仰(小乘佛教或民间宗教),但宗教排外心理不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态势大致相似,因此,这些族群可统归为一大类。但这31个民族之间仍然存在差别,如畲族与汉族通婚率已达50%,而傈僳族和毛南族与汉族通婚率尚不到10%,本类内部各族的差别还是明显的,把他们归为一类,主要是考虑到他们基本的社会环境相似,今后的发展态势比较相近。
我们以表5中的14个族群为对象,按照7个因素(前面讨论的5组因素的进一步分解)对它们各自的特点进行描述,从而尝试着做进一步的归纳分析。从表5反映出的14个族群的情况看,由于7个因素等相互组合的情况千差万别,使中国各少数族群的族际关系呈现出多种模式,通过一些具体因素或指标的分析可以进行归类或分组,但是在整体上进行简单准确的归类仍是有很大难度的。以人口规模这个因素为例,我们会发现即使是人口在1万人以下的20个民族,他们之间的差别也非常显著。例如俄罗斯族、高山族与鄂伦春族之间就缺乏可比性。所以我们在前面讨论的8大类,也只能是非常粗略大致的概括,但是经过对这些因素组合的分析,通过对相关特征的讨论,这8大类仍然可以作为我们分析族际关系基本态势、讨论政策设计与实施效果的一个参考系。
表5:14个族群的几个基本特点
壮族 满族 回族 苗族维吾尔族
彝族土家族
人口规模 1600+ 1000+ 1000
900 900 800 800+
聚居程度 + - - +++
++
独立语言文字 + - - +
+++
+-
宗教因素 - - ++ -++
--
族际通婚 +++++ +-
++
++
历史与中央关系- - - -+--
境外国家 - - - ----
蒙古族藏族
布依族朝鲜族侗族 瑶族 白族
人口规模580+
540+
250+ 190+ 300 260+ 180+
聚居程度 + +++ ++++
独立语言文字 +++
++++ +++
+--
宗教因素 - ++- ----
族际通婚 +++- + ++++
历史与中央关系- ++- ----
境外国家 + - - ++---
注:“+”、“++”、“+++”依次表示程度高,“-”表示程度低。
八、结束语
作为一个多族群的统一大国,中国已有两千多年延续不断的历史,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唯一的。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历代的皇帝、思想家、政治家、封疆大吏们对于如何看待、思考及处理中央皇朝所面对的边疆少数族群问题,殚思极虑,苦心筹划,不断反思前朝亡国的教训,审时度势,精心设计各项制度与措施,他们十分清楚,如果在族群问题上处理得稍有不慎,就可能危及本朝的安危。从公元前《史记》中描述边疆民族的《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再到《汉书》的《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之后历代史书对边疆少数族群都给予充分重视。从唐朝李世民的《取关中策》必须分析突厥的态度、后周王朴的《平边策》要分析契丹的国势,到成吉思汗在临终遗言中制定了如何利用宋金矛盾击破金国的策略、清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里苦心辩说“华夷之辨”的核心是文化,以满人已接受儒家传统为理由来争取汉人对满人的认同,这些都充分说明族际关系的妥善处理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盛唐的衰败、宋朝的灭亡、明朝的倾覆都与边疆族群入侵有着直接的关系,更不用说东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多族混战所导致的社会凋零和人口锐减,而那些强盛一时并彪炳青史的朝代,如汉、唐、元和清朝的鼎盛时期,也都是与当时政府对少数族群政策取得重大成功联系在一起的。真是成也在于斯,败也在于斯!
历朝历代中央政府在对待边疆的不同部族和群体时,大多制定了各自不同的制度(封王封侯、设土司、置郡县等),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在这些思考和设计中包含了大量对历史经验的吸收、对实地调查资料的系统分析、对政策执行效果的反思与调整,这些工作都是在对各个不同部族、群体进行分类研究、分类对待的指导下开展与推进的。今天中国正处在一个和平崛起的关键历史时刻,我们无疑应当关心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实力的扩展,也应当关心国外势力的“封堵”和边境上的风波,但是此刻我们应当予以同样重视的是国内族际关系的调整与改善。
我国少数族群总人口已经超过一亿,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占我国陆地面积的64%,从几千年中外朝代兴亡的历史教训看,国内的族群问题绝对是不可掉以轻心的。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的55个少数族群进行系统分析,区分类型,有的放矢地制定政策,努力改善族际关系,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族群融合,逐步建立全体公民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的核心认同,这将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重新崛起的重要基石。
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之一是进行类型分析,但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要不折不扣地坚持实地调查和实事求是,这是社会科学研究者所需具备的最基本的科学精神。类型归纳的探索有助于我们梳理思路,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分析中进一步系统地认识我国各族群演变历史的差异和各类特征方面存在的差异,但是真正符合客观实际的类型归纳是要经得起实践与历史的考验的,而且同一类型中的各个民族也仍然可能具有自己的某些特点。在制定具体政策时,这些特点也不应忽视。
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具体政策时,对不同族群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法。如西藏地方政府对汉族职工、藏族国家职工、藏族民众在计划生育方面的要求是不同的;新疆地方政府在高考中对民族学校的少数民族学生(“民考民”)、汉语授课学校的少数民族学生(“民考汉”)、汉族学生(“汉考汉”)制定了不同的录取分数线。但我国在民族理论和全国性宏观民族政策上并没有提出分类对待的问题⑨,在与前苏联和西方国家的民族政策进行比较时,强调中国的特殊国情,但对本国各族具体“族情”差异重视不够。2000年国家民委提出,对“人口较少民族”(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特殊扶持政策⑩,是以人口规模为标准提出的分类对待的积极步骤。
本文围绕着对影响民族关系因素的讨论以及对中国民族关系类型的讨论,仍然十分肤浅和不够系统,仅仅是一些最粗浅的探索,希望今后能够有更多的学者关心并参与有关中国民族关系特征要素和类型分析的讨论,并进而推动对我国民族理论和有关制度政策的反思。
注释:
① 这里的“民族”指的是欧洲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现代“民族(nation)”意识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运动中的概念,而汉语中的“民族”用于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与欧洲的“nation”概念相近的“中华民族”;第二个层面是56个“民族”,这个概念与美国的“族群”(ethnic groups)比较相近。本文中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所指的是第二个层面。
② 当然,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都还存在着种族主义思潮和极端宗教主义集团,这些人继续主张种族歧视或对其他宗教信徒的“圣战”,但是这种主张和做法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里已经不占主流,也得不到世界各国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③ 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时期,族群之间由于历史上对黑人的奴役造成的“事实上”竞争能力的差距成为一个主要话题。1965年美国总统约翰逊(Lyndon B.Johnson)曾这样形象地说:“你不能把一个被铁链锁了多年的人释放以后,把他带到一个比赛的起跑线上,对他说‘你可以自由地与其他人进行竞赛了’”,而必须考虑需要对黑人进行某些扶植(Threnstrom & Thernstrom,2002:3)。
④ 从现代政治学和中英文术语对译的角度考虑,笔者曾建议把我国的56个“民族”改称为“族群”(ethnic group),同时保留“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的提法,以避免在两个层面(国家与群体)上使用同一称谓(“民族”)所可能引发的逻辑混乱和误导(马戎,2001:149)。考虑到目前读者仍普遍习惯于“56个民族”、“少数民族”的提法,本文沿用了这些传统提法。
⑤ 这篇文章题目为“世界各国民族关系类型特征浅析”,即将刊登在《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期。
⑥ 有的朝代是对民族既分类也划界的,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建立的朝代,如元朝把各族臣民划分为四等(四大类),每人都有相对明确的身份;清朝的“旗人”与汉人也是有明确的身份与待遇差异的。另据《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介绍,明朝对少数民族如蒙古族“采取了民族压迫和同化的政策,在《大明律》中规定‘不许本类自相嫁娶’,并令他们改取汉姓,改变服装,力图取消其民族特点。由于长期杂居、同化的结果,内地的蒙古族多数融合到汉族和其他民族之中。”(翁独健,2001:606)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每人的“民族身份”自然是不需要去正式划定的。如果正式划定,肯定将阻碍官方的“同化”政策。
⑦ 这是毛泽东在1963年“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中提出的。
⑧ 在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汉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94.1%。
⑨ 由国家民委主持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人民出版社,1981年)只是按4个大行政区划(东北内蒙、西北、西南、中南东南)来逐一介绍各少数民族,《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的“当代民族”部分也沿用了以上行政区划的分组方法。
⑩ 这一研究项目由费孝通先生提议、由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联合其他研究机构共同实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