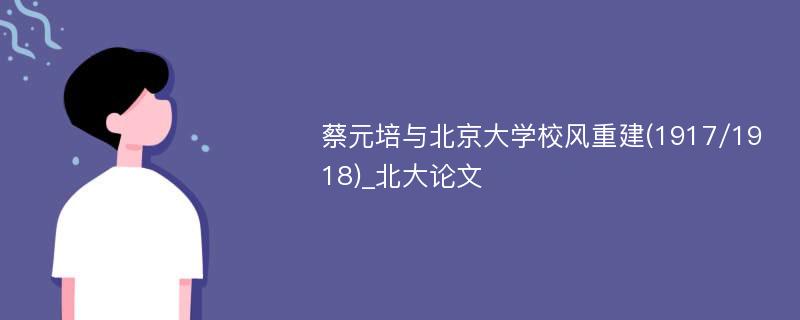
蔡元培与北大校风的重塑(1917-1918),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校风论文,北大论文,蔡元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1)04-0101-10
近代中国的大学,虽然因不同的历史背景、学科设置、学术环境,有着迥乎不同的品格和特性,但一所大学的“校风”是否优良一直是判断大学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准。而所谓“校风”,主要指校内的学术风气和文化氛围,是一种“态度”或说“风范”,难以用量化的数字衡量。
1925年第1期的《学生杂志》“社评”栏目曾对“学风”与“校风”做过细致的区分,认为“学风”是指“一地方或一国家的学术界——包括教育界,学术团体及学问家——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校风”则是指“一所学校内大多数人在各方面生活上表现出来的一种态度和趋向”。两者虽有范围大小的区别,但常能相互影响。文末还特别举例蔡元培掌校之后北大种种革新现象,正是一校的校风足以影响全社会学风的明证,将其看做“转移中国学风的枢纽”。[1]
一直以来,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都被视做近代大学的典范。学界一般将北大校风由“官僚养成所”到新文化运动先锋的转变,归结为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大学理念之下诸项改革的结果,多集中于对聘任新派教师、创设评议会及教授会、废门改系等方面的讨论。对蔡元培如何重塑校风的问题也大多放置于上述专门主题之下,少有将其作为独立问题进行讨论的。
在大学运行的实际过程中,与重塑校风相关联的往往是那些牵涉到更多具体且略带琐碎的操作性问题。如果从北大在近代教育史上的实际境遇来看,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革更多是以点滴改造的方式进行,重在追求大学理念设计与实际办学效用的统一。本文着眼于以往研究较少注意到的大学实际运行层面,通过1917-1918年间《北京大学日刊》上所呈现出的蔡元培出任校长后北大校风的变化,讨论蔡元培如何有意识地引导北大逐渐洗涤科举时代所遗留的官僚之气,向着研究高深学问的现代大学转变。
一、蔡元培掌校前的北大校风
早在民国初建之时,作为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就曾发布《大学令》,要求“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2]虽然蔡元培之前的几任校长对于北大的发展看似未有过人之处,但他们对大学所应负起学问上的责任已经有较为一致的认识。①民国后首任校长严复就曾表示,大学的宗旨是“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3]严复发此议论正值北大内外交困之时,教育部有传言要关闭北大,学校内部则是联合罢课,反抗教师,冲突不断,此时以崇尚高尚学术规劝学生显然是微弱的。②严复被迫辞职,由马良(相伯)接任。暂时代理校长的马良在就职演说中就已言明:“诸君皆系大学生,然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诸君在此校肄业,须尊重道德,专心学业,庶不辜负大学生三字云。”[4]此后一周,梁启超也被邀请到北大演讲,他继续马相伯的思路,认为大学目的是“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于世界文明”,“大学校不仅为一国高等教育之总机关,实一国学问生命之所在,而可视为一学问之国家也。且学问为文明之母,幸福之源。一国之大学,即为一国文明幸福之根源,其地位之尊严责任之重大,抑岂我人言语所能尽欤”。[5]梁启超将北大与国家文明、学问生命联系在一起,亦是希望大学生能将学问本身作为一种高尚的追求,负起应有之责任。
在传统读书人的观念里,读书与入仕并不割裂。京师大学堂早就有毕业即奖励出身的规章。尽管民国已然建立,但政权更迭并没有直接导致风气的转变。所以,当顾颉刚1913年考入北大预科时,北大仍是一派官僚气象:[6]
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有的教师死守本分,不容许有新思想;当然也有好的,如教音韵学、文学批评(《文心雕龙》)的黄侃先生,教法律史的程树德先生(他著有《九朝律考》),但不多见。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学生一年要花五千银元;当然,这样的豪富子弟数量不多,大约不过两三人。至于一年花千把银元的人就多了,少说也有好几十。像我这样一年从家里只能拿二三百银元来上学的,就是穷学生了,在学校里简直没有地位。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指京师大学堂)。这种坏现象是从清末保留下来的。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何谓“结十兄弟”?就是十分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由十人分摊。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蔡元培先生来长校之前,北大搞得乌烟瘴气,哪里像个什么“最高学府”?
尽管比顾颉刚晚两年考上北大预科的陶希圣说:“那时北大预科的学长是徐崇清先生。他办理预科一切从严,学风很好。预科三年,分文科和实科……预科设在译学馆,有一个独立的局面;而预科的学生甚至对本科的学生看不起”,但他也承认学生之中仍有不少贵族子弟,政治社会风气仍是“满清末年留下来的”。[7]
如果说顾、陶二人都是事隔多年的回忆,多少有些夸大,那么,北大学生陈其鹿对自己三年的大学生活的失望,则更直接、更真切。他说:[8]
初意大学为人文荟萃之区,研究高深学问之地,孰知不然。其所谓一学校之优秀分子者无他,终日孜孜於残缺不全之讲义,习应试之资料,而忘学问之精英。一旦而有文官考试,或县知事考试,则时机斯至,挟策以往,趋之如鹜。落第者嗒然若丧,中试者喜形於色,此一类也。又或以内国学生,终不若出洋之为尤美也,乃竭力运动,以冀西游,归而干录,宜若易然,此又一类也……我非谓学生之中举属无心肝者。其中诚不乏一二俊彦,刻苦修学,矻矻穷年者。然统全体而观之,则不堪问矣。必人念硕果之可珍,学殖之宜养而后可,必不醉生梦死和光同尘而后可。
这样的学风当时并不只存于北大一校,而是弥漫于整个教育界。杜亚泉观察到,尽管科举已废,但观念犹存,“其视学校也,不以为一切事业必经之路,而以为希求仕宦进身之阶梯”,所以,“入校肄业,多为士籍及有希望仕进资格之人,此外每存观望”。[9]时任江苏教育司长的黄炎培描述了当时的学风,“光复以来,教育事业,凡百废弛。而独一日千里,足令人瞿然惊者,厥惟政法专门教育。尝静验之,戚党友朋驰书为子弟觅学校,何校?则法政学校也;旧尝授业之生徒,求为介绍入学校,入何校?则法政学校也;报章募集生徒之广告,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行政机关呈请立宪之公文,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10]众人对法政学校的吹捧,无疑是看中了它是做官的捷径,非为求学而来。当年冯友兰在报考文科时就曾被“好心”提醒,可先考法科。[11]1915年他进入北大哲学门学习,更是有切身感受,“当时北大的大部分学生和他们的家长,都还认为上北京大学就是要得到一个‘进士出身’,为将来做官的正途。当时的北大学生都想着,来上学是为了混一个资格为将来做官做准备。北大无形中是一个官僚养成所。当时法科是一个热门,因为人们认为上法科到做官是顺理成章的,文科是一个最冷的冷门,因为人们都不清楚文科究竟是干什么的。”[12]
曾任校长的胡仁源在《北京大学计划书》中说:“大学设立之目的,除造就硕学通才以备世用而外,尤在养成专门学者”,但是,“我国创立大学垂十余年,前后教员无虑百数,而其能以专门学业表见于天下者,殆无人焉,不可谓非国家之耻矣”;他分析个中原因,认为是“社会心理大都趋重于官吏之一途,为教员者多仅以此为进身之阶梯,故鲜能久于其任”;所以他主张“延聘教员,务宜慎选相当人才,任用以后,不可轻易更换。国家对于教员尤宜格外优遇,以养成社会尊尚学术之风”。[13]但理念与施行之间的鸿沟并不容易弥合。蔡元培之前几任校长扭转学风的努力,都没能使北大学风有实质性的改变。
蔡元培曾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的教习,讲授国文及西洋史,对大学堂之风有切身体会。他后来回忆道:[14]
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接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
蔡元培同样把北大的“腐败”原因归结为不能洗尽官僚的习气,“错认大学为科举进阶之变象”。③他认为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是,学校本从科举之制蜕变而来,“故形式虽仿欧洲,而精神则尚不脱离科举时代之习惯。父兄之送其子弟于学校也,初不问在校有何所得,惟望其能毕业;毕业以后,又可进较高之学校,以至于毕业,如科举时代之由生员而举人,而进士而已……于是学校遂为养成资格之机关。”所以,革新北大需要从根本上拔除掉“科举时代所遗传之虚荣心”。[15]由此,倡导高深学问,重塑北大的校风便成为蔡元培改革北大重要内容之一。
二、北大校风的重塑——以《北京大学日刊》为中心的讨论
周作人后来曾评价蔡元培在教育文化上的施为“多以思想主张为本”,因此“他一生的价值亦着重在思想,至少当较施为更重”。[16]其实,若从“五四”前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实践来看,这样的论断恐怕失之于笼统:此段时间,蔡元培对于大学的体认,重在实际行动而非文字建构,积极引导了北大内部学术风气的转变,同时也重新塑造了北大在社会上的形象与地位,其思想意义的彰显是与他在北大的具体改革实践相关联的。
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不久,给老友吴稚晖去信,谈及了改革北大的初步构想。他把北大存在的问题归结为两点:一是学制、课程等“学课”的“凌杂”,另一是学校“风纪”的“败坏”;应对之法则是延聘“纯粹之学问家”和“学生之模范人物”。[17]他一入北大即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18]此后,他亦不时强调大学研究学理取向。蔡元培在北大的诸项革新中,无论是制度上的建构,如教授治校、建立评议会制度,还是对于延聘教师时所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之原则,抑或是组织各种社团、研究会,无疑都是基于“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的理念。蔡元培认为“学”与“术”虽然“关系至为密切”,但因为“习之者兴趣不同”,要区别对待。“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目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法、商、医、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经验,促其术之进步。与治学者之极深研究,不相侔也……学为基本,术为支干,不可不求其相应。”[19]蔡元培希望通过强调学问和研究本身,扭转北大学风。
蒋梦麟将蔡元培出掌北大比喻为“在静水中投下革命之石”,“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会从中荡漾开来,而且愈漾愈远,愈漾愈大”。[20]以校长的身份,蔡元培曾多次在开学典礼、学校庆典等公开场合强调学术风气的重要,不过问题往往是,校长如何说是一事,教员学生于此种舆论环境下如何想、如何做则是另一事。只有当向学之风成了北大师生都普遍关注,参与讨论的这个话题之时,蔡元培在北大投下的石子才真正荡起了涟漪。创刊于1917年11月的《北京大学日刊》(以下简称《日刊》),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北大校方、教职员和学生之间交流的平台,借助这个平台北大朝向研究高深学问之所转变的信号逐渐传达出来。④
蔡元培重塑学风的提议一经提出,即引发了不少北大教师的回应。文科学长陈独秀在1918年北大开学典礼上也提出,大学学生应以研究学理为目的。为此,他提出三条具体办法:一是要“注重外国语”,因为“最新学理,均非中国书所有”,所以要求学生必须精通外国语;二是“废讲义”,因为“讲义本不足以尽学理,而学者恃有讲义,或且惰于听讲也”;三是“能节不急之费以购参考书”。[21]他还以文科学长的名义在《日刊》上通知文科各门任课教员,“将所授科目至不可少之参考书(汉文或洋文)约需若干部,开单赐下,以备采要购置”;同时,还在文科各门“设阅览室,以为学生读书之所”。[22]此外,理科教授俞同奎也专门在《日刊》上发表公开信,回应理科学长夏元瑮提出的“若何引起研究所趣味之问题”。他认为在理科仪器药品不足的情况下,可从筹备实验室开始,“有实验而后研究之问题可解决,研究之问题有解决之希望,则研究方有兴味”。[23]北大立校之基础的文理两科,可谓皆呈现出一种全新气象。
1918年初,蔡元培在“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上提出“大学改制之议”,不久也在北大评议会的讨论之下得以通过实行,北大开始了一系列的学制改革,将文理两科扩张、预备法科的独立、归并商科于法科、停办工科、缩短预科学时,等等。[24]可以说,此时的学制改革是以制度化的形式确定了蔡元培改革北大为“高深学问研究之所”的初衷。⑤同年10月,教育部召开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讨论专门以上学校的教育问题。北大特意将“大学应如何注重学理研究,使学生确能潜心研究”以及如何“奖励大学毕业生入大学院研究之办法”列入提案,提交大会讨论。[25]11月19日、20日,《日刊》不惜篇幅连载了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校长许肇南的议案《人才教育之方针与办法》,看中的正是此项意见书与北大所提出的大学改革议案可“互相发明”。[26]1919年2月,教育部则依照北大提交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中讨论的原案发布训令,要求各校“遵照办理”[27]。整顿学风之议获得了制度形式的肯定。
作为北大校方出面办理的刊物,《北京大学日刊》主要设有命令、法规、校长布告、各科通告、公牍、纪事等专栏,同时也刊登师生对于改进教学及管理工作的建议,并发表学术论文、演讲实录,等等。初期只有两版,后扩展为四版,又增加“杂录”、“通信”等栏而扩展至八版。自1917年11月创刊,至1932年9月10日因改做周刊而终刊,共出版2885期,其间由于政治环境及学校风潮曾有短暂停刊。以初期改版变动最大,如1918年2月,《日刊》发行不久即进行改组,扩大了机构规模,下设编辑、经理二部。由蔡元培请徐宝璜教授为主任,总理一切。[28]编辑部主要负责编辑各类稿件、审定各种规则、决定办刊方针;而经理部则负责招登广告、发送稿件、发卖日刊等工作。[29]后因“销数日广”,已有“与中西各大日报交换”的考虑,为此《日刊》还特别向中华邮政总局申领执照,认定为新闻纸类,准许公开发行。[30]至此,经过改组的《日刊》不再只是北大的普通校内刊物,而是担负起向校外主动发布北大动态的责任。10月初,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召开的之时,《日刊》就曾特意在头版刊发启事,给来京参会的各位专门以上学校的校长免费发放《日刊》三天,以便交流。[31]主要面向大众的《晨报副镌》也曾为《日刊》做过介绍。其中有“足供全国教育界及志愿升学者之参考”一句,颇能显示出北大对自己处于学界领导地位的自信。[32]由北大参与筹办的《新教育》杂志,也在第1卷第2号上刊出《日刊》详细广告,称“本日刊乃北京大学之出版物,纪[记]载校内近事极详而校内教员学生之著作亦日有登载。诚为研究学问或欲知本校情形不可不看之报”。⑥
作为沟通校方、教职员与学生之间的“桥梁”,《日刊》主要承担的是传递信息的沟通和交流作用。这种交流是以多方互动的形式展开:一方面与学校及各系所有关的各种消息和规章除去临时发生或系紧急事件外,均由《日刊》发布;[33]另一方面,教职员、学生也可以借此对校内各项事务表达意见,公开讨论。北大校方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和媒介,师生间的关系日渐融洽。法科学长王建祖就曾在北大二十周年纪念会的演说中表示过:“半年来教员与学生及学生与学生相互之关系因有日刊及其他各种集会之机关日渐融洽,深为可喜。”[34]蔡元培也观察到,《日刊》创办之后,“全校同人始有联络感情,交换意见之机关”,而且也可借此将北大现状告知于全国教育界,可谓一举多得。[35]对于学生来说,《日刊》起到了加强学校与学生联系的作用,让“学生对于学校就一点不觉得隔膜,而向来喜欢对学生摆架子的职员也摆不成他的架子了”。⑦
作为北大内部公共信息传达的渠道,与改良北大校风有关的问题,经常出现在《日刊》的版面上,构建出一个平等的舆论空间。比如,当时还是本科二年级学生的顾颉刚,观察到图书馆存在呆滞停顿的现象,就撰文《上北京大学图书馆书》,并在《日刊》上连载了十来天。顾颉刚对图书馆建议主要涉及图书定购类别、编目及归类方法、借阅规则、阅览环境等21条。其中,他特别提到希望图书馆能够及时公布新购图书目录、捐赠图书目录、出版图书目录、代售图书目录以及分类阅书统计、分日阅书统计等项,务使读者能够了解图书馆的最新情况。⑧此后不久,法科经济学门的学生周君南也以《本校图书馆改良刍议》为题致函日刊,讨论了图书馆的开放时间、阅览规则、硬件设施等问题。他从应对学生施以“自动主义”教育入手,认为改良图书馆正是解决蔡校长提出的防止学生沾染赌博恶习的方法。之所以学生会有赌博恶习,是因为“校课过宽,无事可为而为此者,实占大半”。如果一面减少课堂讲授时间,令学生自习,各班主课每月作一文,详列参考之书,记作平时成绩;另一面尽力改良图书馆,诱发学生研究精神,已有专注赌博的念头“自可潜消感化自然,固非徒具形式之责罚可比”。由此,图书馆的改良,实际上便是“不仅关乎智育已也”。⑨
对于这些建议,北大图书馆早已开始积极寻求改良方法,并经由《日刊》将图书馆的变化传递给北大师生。⑩自《日刊》第6号开始,图书馆便已不定期列出馆藏西文书目、新到国文书目等介绍。就在顾颉刚文全部刊载完成两日后,图书馆又在《日刊》刊出馆藏关于中国英文书籍目录,并附有各册图书简要介绍。[36]图书馆后又在春假开始前发布通告,要求教职员和学生归还所借图书,以便利用假期对中西文书籍改编书目。[37]行动也可说相当快速。不久,图书馆便延长了开放时间,每日自上午八时至十二时,下午一时至五时半,晚七时至九时止,星期日仍照常开馆。(11)此外,从1918年5月3日开始,图书馆开始在《日刊》刊出上月借出及阅览情况月报,分别对教职员、文理工法四科学生、校内外各机关人员借阅情况做出了详细统计。同时,《修正图书馆借阅规则》也在《日刊》予以公布,严格规定了图书借阅制度。比如重新规定教职员及学生借书册数,并表示“无论教职员学生借书逾期不徼,就立即停止其借书权。过期一日便惩罚一星期不得借书”。[38]此后,北大图书馆亦不时在《日刊》上刊出各类馆藏目录、新到杂志书籍介绍,及时将各种相关信息广而告之。
与此同时,蔡元培发起成立的进德会,则是将风气的转换付诸道德修养的提升。1918年1月19日,蔡元培在《日刊》上刊出了《北京大学进德会旨趣书》,将他早年与吴稚晖、李石曾和汪精卫等人一起创建的进德会引入到北大。其实,蔡元培早有此类计划,只是“一年来鞅掌于大体之改革,未遑及此”。1918年初,蔡元培接任校长的第二年,北大各项改组已经开始施行,组织进德会便是“应时势之要求,而不能不从事矣”。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进德会旨趣书》中详细阐述了组织该会之缘起及意义,并规定了会员等第分别为: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又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他希望进德会能起到“如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的“清流”作用,与“敝俗奋斗”。入会之效用,要达到既“可以绳己”,也“可以谢人”,以期实现“苟人人能守会约,则谤因既灭,不弭谤而自弭。其或未灭,则造因至范围愈狭”之目的。[39]
自蔡元培发起组织进德会开始,《日刊》几乎每天都会刊发入会名单,至5月底教职员已入会者168人,学生已入会者301人。(12)而这一年,北大在册登记的正式教员有193人,学生1695人(13),参与人数可谓相当可观。更有学生致函《日刊》表示赞成,认为进德会规定中尤以“戒嫖”一项最为切中北大时弊,建议“作一剀切详明之告诫,连登日刊上一二星期,稍作鼓钟之警”。(14)文本科国文门的学生陶明浚在《日刊》上发表《进德五箴》一文,分别从戒游冶、戒博塞、戒饮食、戒做官吏、戒做议员五个方面讨论了他对进德会的理解。[40]周作人译自日本油谷治郎七所著的《废娼问题之中心人物》,特意表明“进德会译著”,在《日刊》上连载一周。5月28日,北大进德会召开了成立大会。蔡元培致词说:“申明进德之名,非谓能守会规即为有德。德者,积极进行之事;而本会条件,皆消极之事,非即以是为德,乃谓入德者当有此戒律,即孟子人有不为而后可以有为之义。”[41]可以说,自蔡元培发起进德会起,高悬的德性与学问双重立意,使得北大校园内外师生重新找到了久违的道德归属与学术热情。《日刊》上刊出的持续增长的入会数字和各种进德会的通知布告、不断寄往北大要求入会的各式信笺,都昭示出积极进取的态势。不过,其中也有例外。据北大档案记载,行事狂放的北大教授黄侃就曾在回复进德会入会邀请时表示,他对于进德会的宗旨“本极赞成”,但是“入会与否系个人自由。此时信向不出本心,则时守之不力,万不敢自欺复欺”,最终退回了进德会入会的志愿书。[42]
如果说黄侃拒绝入会只是特例,那么进德会在具体运行中受到的质疑则是不少人共同的困惑了。进德会成立不久,北大学生朱一鹗在进德会大会上针对“外间毁誉”有感而发,着意说明了入会会员要抱有“责任心”与“自信心”,号召大家“勿为内欲所克制,勿为外力所牵动”。[43]10月17日,《日刊》又刊发了北大学生梁绍文写给蔡元培的信,说明了自己“狠怀疑的事”:他曾听到过不少与进德会旨趣相悖的负面传闻,所以“好几回,想写信来与先生商量一个好方法,来止止他人的谤,又因谤的事情太多,所以到今日,始能把这封信作出来”,如此境况让他觉得“进德会的条文,不过一种欺人之具罢了”。[44]若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有质疑的声音存在反而可以看做受到关注的另一种表现。进德会的创办是欲借助于外力对每个人的道德进行监督,约束力自然相对薄弱。但蔡元培选择从道德入手,显然并不是希冀获得短时的效用,更多是着眼于施行后的影响。当时就有人赞誉进德会是“现代道德及政治上自觉之一机运,且由北京大学校长所发起,其意义自更深长”,看到的正是其超越现实的表率作用。[45]
力图做到沟通各方的《北京大学日刊》记录了北大师生的改变,也呈现出了一派北大新的校风。无论是以提升个人修养为目的的进德会,还是种种改良图书馆的努力,其初衷无疑是与蔡元培所倡导的北大应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所的设想相一致的。不同于以往官僚养成所以升迁进阶为目的,北大师生借此共同参与到创建全新北大的过程中去,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对北大所负担的学术和道德重任的新认同。
三、北大校风之变化
1919年1月,《教育杂志》刊出主编朱元善《改造学风》一文。作者认为,学术“纯为精神上之产物,萌于人心而系乎风习”。而所谓“学风”,最开始“恒由一二人心意之所向倡之于前”,然后逐渐“誊为口说,布为声气,群众共趋,锲而不舍,遂独自成为一种好尚”;所以要想改造学风,可以从学校与社会两方面努力。其中学校方面,首先就是要求校长教师联结一心,以忠实恳挚之精神研究各种学术或组织学会,事事躬行实践,以身作则;其次则是鼓励学生组织学会,“时时以学为生命,而不以学为借径”。如果各个学校皆能如此,“则学校之学风自得而良善矣”。[46]朱元善所言将“学风”解为学术风气,改造学风关键在于营造众人虚心向学之风气,此点也与蔡元培所设想的改善北大校风相一致,也可视为时人对此的普遍观念。
从一定程度上看,蔡元培苦心营造扭转校风的努力也确实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亲历此一变化的罗家伦,曾描述过“五四”前夕充满学术自由风气的北大:[47]
我们不但在宿舍里早晚都进行激烈的争论,也聚在其他两个地方进行这种辩论:一个是中文系教员休息室——你可以经常在那里找到钱玄同,另一处是图书馆员办公室(即李大钊办公室)。在这两个地方,教师和学生之间没有任何等级之分,无论谁都可以加入讨论。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见解,同时也将面临批驳。这两个地方每天下午三点以后都站满了人……这两个地方有一种真正学术自由的气氛。每一个加入讨论的人都带着一种亢奋的情绪,以致常常忘了时间的存在。有时,有人会离开一个地方而去另一个地方参加讨论,并且边走边讨论……文学革命记忆对旧社会和旧思想的抨击即从这两个地方发生。
1918年,在秋季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对北大一年的情况做了总结:“本校一年以来,设研究所,增参考书,均为提起研究学问兴趣起见。又如设进德会,书法,画法,乐理研究会,开校役夜班,助成学生银行、消费公社等,均为养成学生人格起见……一年以来,于英语外,兼提倡法、德、俄、意等国语,及世界语;于旧文学外,兼提倡本国近世文学,及世界新文学;于数、理、化等学外,兼征集全国生物标本,并与法京‘巴斯德生物学院’协商设立分院。近并鉴于文科学生轻忽自然科学、理科学生轻忽文学、哲学之弊,为沟通文、理两科之计画。望诸生亦心知其意,毋涉专已守残之习也。”[48]尽管蔡元培仍不忘提醒北大师生们“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但还是无法掩盖他在语气之中表露出的自得之意。
1917年夏天到北京大学参加入学考试的蒋复璁,偶遇校长蔡元培,给他留下了难忘的记忆。若干年后,他仍满怀深情地回忆到:(我)“在马神庙新造好的大门里边空院内等考卷,见台阶上坐着一个戴金丝眼镜、穿黑马褂的先生,靠在铺绿呢的桌上,用红殊笔点名,态度非常安详,真是慈而有威。据旁人告诉我说,这就是我从小学即晓得的蔡先生。我精神上顿时感到一种莫名的喜慰,同时也生了一种莫名的骄傲。我想这才是大学生的光荣,有这样一位校长来陶熔,那不是幸福吗?”[49]
严格来说,“幸福”只是一个带有个人体验性意味的描述性词语,但是,如果幸福感和归属感是北大校园弥漫的普遍情绪,它所带来的不仅是一股无形的校园风气,更是一种自信与气度。北大新闻研究会会员李光宇,曾帮助北京中小学校联合运动会编辑新闻,结果得到“全会人一致之称”。他特意写信给校长蔡元培,表示“所刊新闻亦能引起全场人之注意,认为会场中不可少之一发布消息机关”,并进而特意指出其背后的意义,即“于此足见吾北京大学学生对于社会服务制精神及任事之能力”。[50]
1926年9月才进入北大预科的千家驹更是在入学之前即对北大满怀深情。他回忆说:“我对本校发生感情,是在三四年前。那时候新潮流也渐渐地灌输到交通比较不便的金华来了,我才知道有所谓‘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并且有《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都是北大的先生及同学们。我相信学生是智识阶级,智识阶级是应该站到民众之前去引导他们走;而不是站在中间或跟在后面的。而那时候配得上引导民众的,只有北京大学。我便非常羡慕本校,以为进大校[学]必须进本校才对!”[51]
北大越来越显现出的活力以及要前所未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让身在其中的教职员深受感染。1920年9月,北大新任教授陈衡哲在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语气中也透露中能加入北大的自豪。她说:“这个大学自从蔡先生做了校长,他的进步,真所谓‘一日千里了’。所以我对于北大全体的希望,简直可以说是一种信仰心,是一种没有疑惑的希望心。……我愿尽我的力,用极诚恳的精神,和诸位一同去求学问的真理。……我愿诸位知道:我到这里来,对于诸位是富有领路的责任的。我应当尽我的力,去帮助诸位发展各人的天才的。我应当引起诸位对于学问的兴趣的。我对于大学,是希望能不负蔡先生的苦心,助他制造一种新空气!一种师生中没有障碍的新空气!”[52]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的变化也开始得到学界更多的关注,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无可替代的力量,也逐渐成为向往新文化青年们追捧的对象。1919年3月的《东方杂志》转载了《时事新报》记者公时对北大的报道。报道中称,蔡元培乃“学界泰斗,哲理名家,就职后励行改革,大加扩充,本其历年之蕴蓄,乐育国内之英才,使数年来无声无臭生机殆尽之北京大学,挺然特出,褒然独立,延名师,严去取,整顿校规,祛其弊习……学风丕振,声誉日隆。各省士子莫不闻风兴起,担簦负笈,相属于道,二十二行省,皆有来学者。”[53]1920年3月,《北京大学日刊》曾转发上海《新申报》的报道。该文的“主脑”是讨论“废除道尹制,多设大学校”问题。文章从北大已有的成绩谈起,认为北大的教师和学生自“五四”之后已“渐渐有了大觉悟”,“晓得他们的职志,在制造文化”。于是,北大“一洗从前顽旧不堪的习惯”,做出了“文化运动”这个“惊天动地的事业”。作者还在文中感慨道:“要是中国像北京大学那样的学校,设满各省,这文化运动的势力,足以改良社会而有余”;“要是没有北京大学那样的学校,那么文化运动就失了主持者,就不能够发生文化运动”,进而得出结论说“北京大学是最应当希望他扩充的,各省也最应当多设像北京大学那样的大学校”。[54]
吕思勉曾言:“孑民先生主持北大,所以能为中国的学术界,开一新纪元,就由其休休有容的性质,能使各方面的学者,同流并进,而给与来学者以极大的自由,使与各种高深的学术,都有接触,以引起其好尚之心。讲学看似空虚无用,其实风气的转变,必以此为原因。风气是推动时代的巨轮。风气一转变,就无论什么事情,都转变了。”[55]
总体而言,作为改革北大的倡导者和参与者,校长蔡元培所需要面对的是如何扭转北大学风这一复杂的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除了需要做好观念层面的理论应对之外,更多的是要面对大学实际运行中的诸多细节。1917年-1918年北大实际发展过程中的点滴变化,为观察蔡元培与北大之间丰富而又生动的关系提供了另一种视角。蔡元培掌校后的两年时间里,北大校风为之一变,逐渐褪去了官僚养成所的风气,初步完成了朝向现代意义的大学的转变,也为迎接此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作好了准备。
蔡元培早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时就要求学生做好三件事:第一,抱定求学宗旨;第二,砥砺自身德行,束身自爱;第三,敬爱师友,以诚相待。[18]此后,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革,与这些最初的设想大致吻合。可以说,他对校风与学风重新塑造,源于对近代大学的深刻体认,其中既包含了对大学发展方向高瞻远瞩的理论引导,也含有深谋远虑的制度规范设计。针对普遍而典型的学风问题,他身体力行,以身垂范,充分发挥了舆论的作用,由此将北大带入到了新的发展阶段。
注释:
①蔡元培就任之前北大的改革状况,可参见萧超然:《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49页。
②参见萧超然:《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第37-40页;魏定熙著:《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
③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蔡元培全集》第八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10页;蔡元培:《对大公报记者谈话》,《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36页。
④已有研究者对《北京大学日刊》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进行过研究,参见陆远,刘超:《校园改革与新文化运动——〈北京大学日刊〉为中心》,《船山学刊》,2009年第1期。
⑤蔡元培早在《大学令》中即表示过,“大学为研究学术之蕴奥”,须设大学院,以供各科毕业生或有同等学力者入院研究。他出掌北大之后也积极筹建研究所。1917年底,北大评议会通过决议,设立文、理、法三科研究所。1918年初,各科研究所均已设立。研究办法分研究科、特别研究及教员共同研究三项。但后来蔡元培认为,各系分设的办法太过散漫,“所以有几系竟一点没有成绩”,遂改组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外国文学四门。1922年成立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便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蔡元培的相关论述见《大学令》,《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213页;《北京大学第二十三年开学日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188页;《北京大学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484页。关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创建及发展,可参看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⑥见《新教育》第一卷第二期起刊登的广告插页。
⑦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页。余毅(顾颉刚):《悼蔡元培先生》,蔡建国编:《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5页。
⑧顾颉刚:《上北京大学图书馆书》,《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4日-9日,13日-16日。引文见1918年3月13日。
⑨周君南:《本校图书馆改良刍议》,《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23日-28日,3月30日,4月9日。引文见1918年4月9日。
⑩关于北大图书馆发展的整体情况,可参见《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1)《图书馆布告一》,《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4月12日。此前图书馆的开馆时间为上午八时至下午五时,见《图书馆书目编订室日记录》,《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1月22日。
(12)入会名单连续在《北京大学日刊》连续发表多日,计有1月22日38人、23日84人、24日18人、25日50人、27日48人、31日30人、2月3日66人、6日6人、9日10人、27日48人等,《进德会最终成立之日的名单可参见进德会通知及名册》,《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下册,第2568-2571页。这里的统计也包括了外校报名者数人,见《进德会近闻》,《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4月22日。校外进德会会员名单,可见《校外进德会会员签名簿》,北京大学档案馆藏,BD1918002-3。
(13)《全国专门以上学校一览表》,《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下册,第3263页。关于1918年度教职员及学生统计的数据,目前有两个数据可供参考:一为《国立北京大学统计表》,原刊于《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月29日,统计的是从1916年8月至1917年7月的人数,其时教员人数为148人,职员人数为44人,在校学生人数为1503人,毕业生393人,辍业生111人;另一则是《全国专门以上学校一览表》,原刊于《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24日。与统计进德会人数的时间相比虽有差距,但教职员大致未有过多变化,学生人数因有新生人校则有近200人的增加,暂取后者。
(14)《陈君仲与来书》,《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月22日。此信可与上文顾颉刚回忆相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