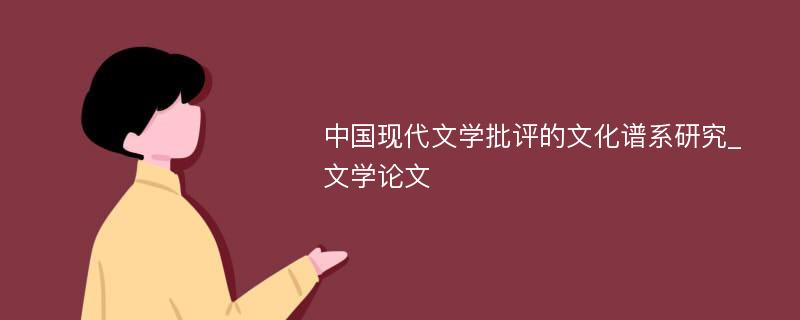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动的文化谱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谱系论文,文学批评论文,中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08)10—0094—07
“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激烈、最起伏动荡的岁月。”①鲁迅称20世纪为大时代,在这个大时代中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的血雨腥风中走过它凄惶的岁月,并沉入崩溃的黑洞。时代来不及喘息,便又匆匆上路,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动荡的岁月不断地磨砺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也使文学和文学批评在不经意中肩负了本来不该由它来承担的重负。“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化,以及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历程,伴随着社会的现代化梦想,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了。”②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形成的历史语境,实际上,在这一历史语境中,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经历了艰难而痛苦、漫长的抉择过程,从物质层面现代化的诉求,到政治制度现代化的反思,再到文化现代化的抉择。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维新运动,再到全面反传统,这其中西方始终是一个先进的参照系和评判支点。西学东渐一浪高过一浪,中国文化中不断插入西方异质性基因,西方的思维方式、话语模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本民族文化现代化的法宝。因此按“知识考古”的方式对中国现代文学及批评进行一番文化谱系的考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思和作用,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及批评发生与形成的内在轨迹。
首先,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自身的生存境遇。
伴随着中国国门被西方洋枪洋炮的轰毁,中国文化也面临着尴尬的局面,可以用“文化困境”四个字来形容。西洋知识的涌入,已越出中国文化可以阐释的疆界,如何应对,此时中国旧有的知识系统已无法解释周围变化了和变化着的世界。“不仅因为西洋的东西汹涌而至,而且还因为中国人一切都没有调整好,就被汹涌而来的新知识新经验淹没,于是茫然,仿佛宋襄公,还没有列队鸣鼓,西洋人就来了,赶快搜寻自己固有的文化底囊,匆忙翻检圣贤的书本,可是没像《甘露寺》里诸葛亮留下来应付变动的锦囊可以使用,于是,他们陷入了有史以来少有的文化困境。”③这种外部世界的巨变从而导致的思想文化上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古老的天文地理知识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天圆地方”等天文知识在地球仪、望远镜面前显得破绽百出。“七政仪,其构造的知识背景是西洋关于天像的判断,而地球仪的形制,其知识依据当然不是中国的‘天圆地方’,望远镜观察到的天象星辰,足以瓦解古代中国关于星象的解释,而显微镜所看到的细菌世界,则可能给中国人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天地,使得古代中国知识世界无法诠释它的原委。应该说,这些仪器的知识背景,显然已经与传统中国人的知识有相当大的歧异,也已经蕴涵了足以对整个中国知识系统提出颠覆性质疑的资源。”④“自古以来一直为官方重视的天象之学,也越出了为政治谋求合法性和为农事安排历日的畛域,渐渐接近近代的天文学,十九世纪下半叶,人们逐渐知道了宇宙生成理论,也知道地球与月球的分离‘因旋转之势而分’的学说,而且知道太阳系的行星和围绕太阳运转的周期,甚至还知道了万有引力、行星轨道椭圆、各行星绕日一周天数、火星有冰顶、木卫四星,以及天王海王星、日蚀、月蚀等等。”⑤中国传统习惯中的“天下”、“九州”等地理观也伴随着魏源《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瀛环志略》等书的相继问世开始瓦解,新的名词、新的知识如决堤的洪水一般涌入中国传统文化中,使中国文化开始打破自身封闭状态,开始与西方接轨。“各种新词语,也相继在汉语中出现并被接纳下来,像什么‘亚细亚’、‘欧罗巴’、‘地中海’,……是一种全新知识系统。”⑥地理空间的变化背后是知识空间的扩大,随着地理知识尤其是欧美地理知识的增加,中国人的眼界也逐渐开阔起来。
二、经史子集等中国旧有的知识分类体系已无法满足日益输入的新知。西洋新知的涌入,对中国传统的知识系统进行了潜在的消解,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不得不重新进行根本性的调整以求应对。“在西洋新知的冲击下,十九世纪中国的传统学科系统已经不能容纳新的知识,这就仿佛一个被区分成了四个大格子若干个小格子的箱子一样,过去甲乙丙丁、经史子集的,已经没法把纷至沓来的新知妥善地安放,它的格子已经阻碍了新知在传递中的增长。当新知增长到旧衣服再也不能包裹住它的身躯时,衣服就被撕破了。……当经、史、子、集的分类法在新知的冲击下转化为文史哲政经法以及数理化等等西洋学科的分类法时,传统的知识系统已经恍然崩溃。”⑦“当传统的,赖以支持自己的理解和解释的系统崩溃,这种恐慌是很难抵抗的,重建知识系统便是普遍的需求。”⑧
三、中国传统的人文知识在洋枪洋炮的威胁下显得苍白无力,实用技术炙手可热。屡战屡败、赔款割地等丧权辱国的现实危机使中国开始反思自己甚至怀疑自己的传统知识及教育内容。相比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中国传统人文道德教育显得既无能又无用:“中国之所谓格致,所以诚正治平也,外国之所谓格致,所以变化制造也,中国之格致,功近于虚,虚则伪,外国之格致,功证诸实,实则皆真。”⑨崔国因《出使美日秘日记》卷八也说,“外国于格致之学,较之中国士子之用心举业者,略相同焉。然举业之学,但托空言,而格致之学,实有实用,宜其日致富强乎。”⑩两相比较,关于知识的价值判断出现了逆转,“中国旧学渐渐被当做‘无用’知识,而西方新知则被当做‘有用’知识,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宋育仁给陈炽《庸书》作序时,就曾经提到,当时流行观念之一,是‘天下之说曰:今日之病在尚文之弊’,这里所谓‘尚文’,其实就是传统中国把儒家经典作为全部知识,旧时天下人都把精力和智慧耗费在这种本来应当是人文知识的知识世界,而忽略了其他的所有知识与技术,因而导致了实用技术的衰落,他觉得这导致了中国的‘贫’与‘弱’。”(11)十九世纪末,废科举,兴西式学堂,办实业在中国蔚然成风。
四、一元文明观的破灭与以我为中心价值体系的变化。世界变大了,中国人的自尊心却缩小了。世界由过去的九州一隅扩大到了整个地球,而中国则从过去的“天下”缩小到了东亚一隅。“世界的扩大和中国的缩小,使中国知识阶层开始思考和接受一个至关重要的新观念,也就是多元文明区域的存在,那些过去被想象成荒蛮异邦、蕞尔夷狄的‘万国’,不再是天朝大国理蕃院属下职贡天朝的四裔,也不再是上国不屑的小小弹丸的弃岛,而是与‘中国’同样的国度,因此它们的文明、物产、语言都渐渐被认识,这种认识逐渐地改变着中国知识界的无端傲慢。”(12)在屡战屡败、割地赔款的现实面前,中国人不得不痛苦地放弃唯我独尊一元文明观,不得不承认西方船坚炮利,不得不承认西洋历史与中国历史同样悠久、西洋文明并不亚于中国文明。同时,伴随着一元价值观念的轰毁,中国人关于文明的价值评判标准也发生位移,以伦理道德为中心文明优劣观转变到以强弱为中心的文明优劣观。“‘富强’在‘理性’的名义掩护下,以‘实用’和‘有效’的方式,被当做‘文明’的标准,这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实际上源自西方的思考方式,一个一元的普遍的价值尺度,它使得急于保存自身文化存在的中国人在西方强势的全球背景中,在坚船利炮的威胁下,放弃文明评价上的独自立场,也放弃文化与价值上的传统观念。”(13)中国传统观念中至高无上的“王道”渐渐让位给了“霸道”,富国强兵成为最重要的事情,在失败面前中国人不得不低下夜郎自大的头颅,被迫承认西方的价值观念。“正是因为当时人已经开始把中国置于全球背景中,而全球万国之间又以强弱论英雄,而强弱又以富与强划分,是非则以成王败寇来定,所以‘富强’就等于‘文明’,这种关于‘文明’的思路引起一系列观念转变。他们开始反省历史,从最直接的原因开始调整自己文明的视角,‘富’和‘强’成了最重要的价值标准。”(14)
五、随着西方文明观念的输入以及价值与道德评判标准的变异,儒家的合法性地位受到质疑,以教化载道的旧的文学也遭到空前的反对。
在传统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儒家经典被奉为圭臬,人们总是把伦理的合理性、道德的自觉性、国家政治与家族伦理的同一性、社会秩序的有序和谐当作文明价值的中心,而且总以为中国文明优于西洋,称自己为“天朝”,称中国之外诸国为“四夷”,并以此得到心理上的自慰和满足。可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后,人们渐渐发现西洋人也有相当成熟和合理的伦理道德系统,也有其维持社会秩序的合理建构,而且比我们的更人道、更人性化、更合理。相反,我们那种通过政权建立起来的合法性的儒家思想倒显得戕害性灵、摧残人性。反对孔孟之道,反对载道文学,提倡言志文学,清算儒家思想的历史罪责,揭露儒家思想通过政权取得合法性和政权通过儒家思想取得合理性的合谋目的,肃清孔孟之道流毒的影响,成为思想界、文学界共同愿望。
其次,中国文学面对文化困境利用西方理论资源进行自我救赎。
文学的外部形势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的思想、新的语境、新的价值道德标准,旧的文学形式已难以适应,寻找新的文学形式以表达新的社会思想如箭在弦上,正如周作人所言的那样:“因为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变动,所以须用白话——假如思想还和以前相同,则可仍用古文写作,文章的形式是没有改革的必要的。现在呢,由于西洋思想的输入,人们对于政治,经济,道德等的观念,和对于人生,社会的见解,都和从前不同了。应用这新的观点去观察一切,遂对一切总是又都有了新的意见要说要写。然而旧的皮囊盛不下新的东西,新思想必须用新的文体以传达出来,因而便非用白话不可。”(15)
中国文学的旧皮囊已盛不下日益变化的新东西,再加上赶超欧美,尽快与世界接轨和救亡图存的内心紧张与焦虑,促使中国学者必须整合中西文化资源,进行文学改革。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赶超欧美日的政治诉求,遂形成一股文学改革的合力。
而在全球环境范围内,在中西对比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中国人感到了未曾有过的生存焦虑与紧张。“那个时代的心情下,一切都在变,一切都求新。”(16)文学的外部世界已发生了天崩地裂,桐城派古文、八股文等旧的文学形式不能胜任新的社会要求,必须“别求新声于异邦”进行改革,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在梁启超、黄宗宪等人的倡导下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对这种变化,周作人深有体会,他说:“自甲午战后不但中国的政治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即在文学方面,也正在时时动摇,处处变化,正好像是上个时代的结尾,下一个时代的开端。新的时代所以还不能即时产生者,则如《三国演义》上所说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所谓‘东风’在这里却正改作‘西风’,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和文学各方面的思想。到民国初年,那些东西都已渐渐输入得很多,于是文学革命的主张便正式的提出来了。”(17)文学外部世界的变化人人都感受到了,但是旧文学影响的惯性还在,人们还在按习惯沿用着旧的文学形式。谁来发春雷般振聋发聩的呼喊,谁来提出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这时候,进化论无疑成为文学改革者首选的思想理论武器。因为随着严复《天演论》的出版发行,进化论在近代中国产生了普遍、深远的影响,很快为多数人所接受和信仰,成为近现代中国的主要意识形态。蔡元培说:“自此书(指严复的译著《天演论》—笔者注)出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人的口头禅。”(18)有的学者形容进化论在当时的影响说:“现在的进化论,已经有了左右思想的能力,无论什么哲学、伦理、教育以及社会之组织,宗教之精神,政治之设施没有一种不受它的’影响。”(19)这时,利用深入人心的进化论来论证中国文学由旧文学向新文学的变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无疑最具感召力。王国维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20)他从文学史的角度指出文学进化的必然性。梁启超对进化论推崇备至,他说:“自达尔文《种源说》出世以来,全球思想界忽开一新天地,不徒有形科学为之一变而已,乃至史学、政治学、生计学、人群学、宗教学、伦理道德学一切无不受其影响,斯宾塞起,更合万有于一炉而冶之,取至至赜之现象,用一贯之理,而组织为一有系统之大学科。伟哉!近四十年来之天下,一进化论之天下也。”(21)“进化者,向一目的而上进之谓也。日迈月征,进进不已,必达于其极点。凡天地古今之事物,未有能逃进化之公例者也。”(22)他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观念来看待文学事件,他在《释革》一文中说,“淘汰复有二种:曰‘天然淘汰’曰‘人事淘汰’。天然淘汰者,以始终不适之故,为外风潮所旋击,自撕自毙而莫能救者也。人事淘汰者,深察我之有不适焉者,从而易之使底于适,而因以自存者也。人事淘汰,即革之义也。”(23)他依据进化论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人事淘汰”,抨击桐城派古文和八股文,提倡“新文体”,使之适应于新的形势需要。既然“天地万物”都不能“逃进化之公例”,文学当然也不能例外:“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几及,余生平最恶闻此言。窃谓自今以往,其进步之远轶前代,固不待蓍龟,即并世人物亦何遽让于古所云哉?”(24)他认为,文学是进化的,而“文学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25)他在1897年续写《变法通议》的《论幼学》一章时,反对用“古语”,强调使用“今语”著述,提出用“说部书”作为蒙学读物之一的主张:“古人文字与语言合,今人文字与语言离,其利病既缕言之矣。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而《水浒》《三国》《红楼》之类,读者反多于六经。……但使专用今之俗语有音有字者以著一书,则解者必多,而读者当亦愈夥。”(26)为适应新的变化形势,使文学走向平民走入生活,他要求改革旧的文体,提倡一种与桐城古文、八股文截然不同的通俗易懂“报章体”的新文体,“从内容来说,它包容了着眼于世界范围的新事物、新思想,并大量运用新的名词概念;从结构来说,它讲究逻辑的严密清晰,不故作摇曳跌宕之姿;从文字来说,它力求通俗流畅,为说理透彻而不避繁复;从风格来说,它感情发露,具有强大的冲击力。”(27)从文学进化与救亡图存期待与实践出发,梁启超大力提倡小说,认为小说入人心最深,接受者最广,是适者生存的典型范例,首先将文学提升到救亡图存的层面,他将东西洋的发达与文学尤其是小说联系起来,借以说明中国小说界革命的必要性,“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28)所以他振臂高呼:“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29)“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30)小说,曾经被称为小道,不入流的文学门类,此时被提高到了救亡图存的高度,甚至被当作文学的正宗。陶曾佑形容小说,“其感人也易,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神,其及人也广。是以列强进化多赖稗官,大陆竞争,亦由说部”,(31)“西哲有恒言曰:小说者,实学术进步之导火线,社会文明之发光线也,个人卫生之新空气也,国家发达之大基础也。”(32)“欲革新支那一切腐败之现象,盍开小说界之幕乎?欲扩张政法,必先扩张小说;欲提倡教育,必先提倡小说;欲振兴实业,必先振兴小说;欲组织军事,必先组织小说;欲改良风俗,必先改良小说。”(33)白话小说,因为改良者的提倡,在近代日渐流行起来,报刊出版事业也日渐发展,这些为新文学的到来做好了舆论与实践上的准备。
接其余绪,陈独秀、胡适利用进化论学说揭起文学革命大旗。1915年9月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明确指出:“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34)“世界进化,骎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35)他又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进一步指出,“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36)“进化公例,适者生存:凡不能应四周情况之需求而自处于适宜之境者,当然不免于灭亡。”(37)他还从进化角度出发,强调变化的重要性,“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存亡之数,可以逆睹。”(38)他认为西欧、北美的近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以会如此突飞猛进,就因为进化论提供了强大的源泉和动力。“自英之达尔文,持生物进化之说,谓人类非由神造,其后递相推演,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格言,昭垂于人类,人类争吁智灵,以人胜天,以学理构成原则,自造其祸福,自导其知行,神圣不易之宗风,任命听天之惰性,吐弃无遗,而欧罗巴之物力人功,于焉大进。”(39)进化论不仅是陈独秀改造社会的武器,也是他倡导新文学,进行文学批评重要理论根据。他在《文学革命论》中大声疾呼:“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进化。”(40)他痛斥唐宋以来的古文为“代圣人立言”,“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讫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空泛之门面话而已。”(41)他认为“此等文学,作者既非创造才,胸中又无物,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42)所以他高举文学革命大旗,要“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要“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立诚的写实文学”,要“推倒迂晦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43)进化论是胡适观察研究中国文学现象和文学史,借以批判旧文学,提倡新文学重要的理论武器。胡适说:“我曾用进化的方法去思想,而这种有进化性的思想习惯,就做了我此后在思想史及文学的成功之匙”,“我在中国对于文学革命的辩论,全是根据无可否定的历史进化的事实,且一向都非我的对方所能答复得来的。”(44)胡适正是运用进化论这一西方资源为理论支点,以历史进化观为根据,提出了文学革命的相关主张。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八事”,他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是文学进化的公理。“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也”,因此他反对“模仿古人”,提倡新文学。随后他用中国文学史实加以证实,“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45)他认为各时代各有其特长,从历史进化的眼光去看,决不能说古人的文学胜于今人,因而摹仿古人逆天时,违反进化的轨迹,是无法取得理想效果的。据此他说:“既明文学进化之理,然后可言吾所谓‘不摹仿古人’之说。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46)他放言时下白话文学(即新文学)是文学进化的必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47)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他以欧洲各国国语历史为依据,如意大利从拉丁“死文”到国语的过渡靠的就是但丁等人文学的力量,提出著名的文学革命口号“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认为文学与国语的合一是完成了活文学,是活文学对死文字死文学的取代,是文学进化的方向和必然结果。在《文学进化观与戏剧改良》,他更加具体地阐释了他的文学进化观。他分四层意思论述他的文学进化思想:“第一层总论文学的进化: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人的生活随时代变迁,故文学也随时代变迁,故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48)“第二层意义是:每一类文学不是三年两载就可以发达完备的,须是从极低微的起源,慢慢的,渐渐的,进化到完全发达的地位。”(49)这一文学进化观念的论述与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观点完全一致,达尔文认为,生物的进化是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渐进过程。“文学进化的第三层意义是:一种文学的进化,每经过一个时代,往往带着前一个时代留下的许多无用的纪念品:这种纪念品在最先的幼稚时代本来是很有用的,后来渐渐的用不着他们了,但是因为人类守旧的惰性,故仍旧保存这些过去时代的纪念品。”(50)胡适认为“中国人的守旧性最大,保存的‘遗形物’最多”(51)。在胡适看来,这些遗形物“很可阻碍戏剧的进化,不把它扫除干净则中国戏剧永无完全革新的希望。“文学进化观念的第四层意义是:一种文学有时进化到一个地位,便停住不进步了;直到他与别种文学相接触,有了比较,无形之中受了影响,或是有意吸收别人的长处,方才再继续进步。”(52)胡适的例证是:英国戏剧受欧洲大陆新剧的影响,从而产生萧伯纳、高尔华胥;中国古代音乐则受到了西域音乐的影响。胡适的这一论述点明了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从哲学上讲,系统内部资源不足时,必须吸纳外部资源以赢得发展,一个封闭的系统意味着穷途末路。事实上,胡适、陈独秀等人开启的五四文学革命,正是得力于外部资源特别是西方文化资源的输入,诸如科学、民主、进化论、现实主义等等。
因此,单从进化文学史观,便可以清晰地看出新文学的产生正是借助西方文化资源,“别求新声于异邦”的结果,正如陈独秀坦言的那样:“要拥护那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53)正是西方思想文化资源的输入,异质因素不断插入中国传统文化内部,使它发生遗传变异,以适应新的变化形势与要求。
第三,中国新文学与批评对自身传统资源的反动、改造、利用情况。
一种文化的变化离不开它的内因,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新文学的产生一方面伴随着对旧文学的反动与批判,一方面是对旧有的文学资源的开发利用。对于这一点朱晓进有相当深刻的见解,他说:“中国的文化转换,是发生在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胜利这一背景上被动展示的,当中国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变革中国文化的必要性时,他已不得不在理智上承认西方文化的优越,并试图去接受这种完全相异于中国文化体系的另一种文化。但是,这里本身就必然存在着两个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人们不得不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另一方面,由于批判者自身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养育出来的,在其实质上并不能真正完全抛弃传统文化,尤其是在精神深处对之怀着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依恋;一方面,当时面临的任务是尽快实行文化的转换,为防止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销蚀作用,必须在整体上反传统,另一方面,从文化价值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又确有优秀的值得肯定的东西。这是宏观文化调节的历史任务与微观的具体文化门类的实际价值之间的矛盾,而在文化剧变期必然会出现以牺牲后者的某些方面来保证前者顺利完成的现象。”(54)葛兆光总结中西文化对撞中,中国知识界的应对策略时说:“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面对着天崩地裂式的大变局,在这种巨变的时代,进入新语境的古代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不得不重组自己的知识系统。而在这种力图谋求适应新世界的知识重构中,拥有相当深厚历史与传统资源的中国士人,通常采取的是重新诠释古典以回应新变的途径,而在这种重新诠释古典的过程中,首当其冲的当然是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因为,在古代中国相当时间里,儒家的经典是读书人最熟悉的文本,儒家的经学是读书人最熟练的关于所有知识、思想和信仰的诠释方式。”(55)
在中西文化的对撞、融合过程中,中国文化始终是问题的中心,无论是批判也好,消解也好,吸收也好,改造也好,它终究是中国文化自身的问题,始终要围绕着“中国文化”这个中心展开,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格局中变革的实践过程。也就是说,新文学的诞生是在对旧文学批判的基础上完成的。
胡适提出改良文学“八事”针对的就是当时文坛言不由衷的拟古风气,(56)他斥责那些拟古之作为“逼真赝鼎”,只该放在博物院,不能算作文学。“更观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规姚曾上师韩欧;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以为六朝以下无文学可言,此皆百步与五十步之别而已,而皆为文学下乘。即令神似古人,亦不过为博物院中添几许‘逼真赝鼎’而已,文学去乎哉!”(57)他认为那些陈词滥调的诗文,面目最为可憎:“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滥调,‘蹉跎’,‘身世’,‘寥落’,‘飘零’,‘虫沙’,‘寒窗’,‘斜阳’,……之类,累累不绝,最可憎厌。其流弊所至,遂令国中生许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实非之诗文。”(58)
陈独秀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也是针对雕琢腐朽旧文学立言的。他认为当时“归、方、刘、姚之文,或希荣慕誉,或无病而呻,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每有长篇大作,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道说些什么。此等文学,作者既非创造才,胸中又无物,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59)他分析当时文坛的流弊是阿谀、虚伪与铺张、雕琢,“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敝。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所谓骈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也。所谓江西派者,山谷之偶像也。求夫目无古人,赤裸裸的抒情写世,所谓代表时代之文豪者,不独全国无其人,而且举世无此想。”(60)
周作人从形式到内容上对古文持否定态度,“就形式说,古文多是贵族的文学,白话多是平民的文学。但这也不尽如此。古文的著作,大抵偏于部分的,修饰的,享乐的,或游戏的,所以确有贵族文学的性质”,“这内容上的缺点,也正是如此。”(61)他还进一步从人道主义和人性化的立场,论证了中国文学大部分是扼杀人性的非人的文学,就这一点而言必须改革,使之回到人的文学轨道上来。他说:“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著作的态度,是以人的生活为是呢?非人的生活为是呢?这一点上,材料方法,别无关系。即如提倡女人殉葬——即殉节——的文章,表面上岂不说是‘维持风教’,但强迫人自杀,正是非人的道德,所以也是非人的文学,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62)他还较详细地列出那些非人文学的例类供大家参照,“现在我们单从纯文学上举例如:(一)色情狂的淫书类(二)迷信的鬼神书类(《封神传》《西游记》等)(三)神仙书类(《绿野仙踪》等)(四)妖怪书类(《聊斋志异》《子不语》等)(五)奴隶书类(甲种主题是皇帝状元宰相乙种主题是神圣的父与夫)(六)强盗书类(《水浒》《七侠五义》《施公案》等)(七)才子佳人书类(《三笑姻缘》等)(八)下等高谐谑书类(《笑林广记》等)(九)黑幕类(十)以上各种思想和全结晶的旧戏。(63)
鲁迅则更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学瞒与骗的性质:“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64)“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65)他不无愤激地追问:“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66)因此他大声疾呼:“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67)
一方面是对旧文学的批判,一方面是对旧的文学批评资源的利用和改造。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学健将在利用进化论理论提倡新文学,批评文学复古思潮流弊的同时,毫无例外地把目光瞄准了中国古代小说和戏剧,把它们当作了新文学的典范与发展方向。王国维说:“往者读元杂剧而善之,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68)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里对古典白话小说推崇备至:“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三人而已)一项。此无他故,以此种小说皆不事摹仿古人,(三人皆得力于儒林外史,水浒,石头记。然非摹仿之作也。)而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其他学这个,学那个之诗古文家,皆无文学之价值也。”(69)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里也盛赞古典小说戏剧,他说:“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70)对于建设什么样的新文学,新文学创建者一方面向外从西方文学汲取营养,一方面向内挖掘自己已有的传统资源。胡适立论文学改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须言之有物”,这是对孔子“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反向立论,强调“物”比“文”更重要。胡适的“物”是什么呢?一曰情感,二曰思想(胡适的思想应该指真实的生活感受即他所说的见地、识力、理想)。谈情感,胡适引用毛诗《大序》中关于诗的定义说明描述:“‘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谓情感也。”(71)关于思想,胡适援引庄子之文、陶潜杜甫之诗、辛弃疾之词、施耐庵的小说为例来加以说明。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中国古代文论中谈情感思想的文章早已有之,像“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胜之害”“质者何?情与思二者而已”这些观点,刘勰等人早就论述过。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中,胡适说“(文学随时代变迁的)这种思想固然是达尔文以来进化论的影响,但中国文人也曾有很坦白的主张文学随时代变迁的。最早倡此说的是明朝晚期公安三兄弟,清朝乾隆时代的诗人袁枚、赵翼也都有这种见解……”(72)这表明,胡适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找到了与他的文学进化观的共鸣。
陈独秀所谓的文学革命三大主义,要打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无非是接胡适“八事”的话茬而已,通俗明了平易也好,抒情新鲜写实也罢,一言以蔽之:真的文学要写出真的情感与思想。
周作人对文学曾下过这样的定义:“文学是用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独特的思想和感情传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感到愉快的一种东西。”(73)他还从历史学的角度,梳理了中国文学变迁的历史,认为中国文学在历史上主要有两种潮流——言志派与载道派,到了近代,由于外界形势的变化,载道派衰落,走向新的文学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向。“以感情和形式并重的,则是这时期以后的新文学。就中,八股文和桐城派的古文很相近,早有人说过,桐城派是以散文作八股的。骈文和新文学,同以感情为出发点,所以二者也很相近,其不同处是骈文太趋重于形式方面。后来反对桐城派和八股文,可走的路径,从这表上也可以看出来,不走向骈文的路便走向新文学的路。而骈文在清代的势力,如前面所说,本极微弱,于是便只有走向新文学这方面了。”(74)为什么会走向新文学呢?他认为“新文学的基本观念是‘言志’”(75),“因为要言志,所以用白话——我们写文章是想将我们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的。能够将思想和感情多写出一分,文章的艺术分子加增一分,写出得俞愈多便愈好。”(76)为什么言志就是新文学必选之途呢?他分析认为言志派的文学是即兴的文学,古代著名的篇章都是即兴的,如《诗经》、《庄子》等,而载道派的文学是“赋得的文学”,是死的文学,是按格式规矩填写而已,无思想无真情实感,譬如高空走索子,走路可以任意而行,走索子只能按照先生教的方法去走,由不得自己。对新文学与白话文学运动,周作人从诗大序立言,从公安派性灵说找证据,认为胡适等人的文学改良主张实质上就是明代公安派“独抒性灵”的主张。“其后钱玄同刘半农参加进去,‘文学运动’‘白话文学’等等口号才明显地提了出来。接着又有了胡适之的‘八不主义’,也即是复活了明末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只不过又加多了西洋的科学哲学各方面的思想,遂使两次运动多少有些不同了,而在根本方向上,则仍无多大差异处。”(77)对于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一直持自己的看法,那就是新文学是明代公安文学的余绪,他找出了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胡适主张“话怎么说,就怎么写”,性灵派主张“信腕信口”;新文学反对拟古提倡今文,周作人举出性灵派见解“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关于文学情感与思想的重要性,周作人用性灵派的意见作了阐释:“言语无意见则虚浮,虚浮则雷同矣。故大喜者必绝倒,大哀者必号痛,大怒者必吼叫动地,发上指冠。惟戏场中人,心中本无可喜而欲强笑,亦无可哀而欲强哭,其热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78)“其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若使胸中的有所见,苞塞于中,将墨不暇研,笔不暇挥,兔起鹘落,犹恐或逸,况有闲暇引用古人词句耶?”(79)
破坏与建构是同时的。中国新文学从发生之日起,文学批评就担当起了急先锋,一方面从近现代西洋文学的发达与中国文学的没落作比照,意在从外来的资源中汲取新鲜的营养,突出新文学的时代性与全球性战略,一方面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资源寻找变迁的轨迹,意在说明新文学的到来是历史演变发展的必然;一方面对古代文学进行批判与颠覆;一方面利用古代文学资源进行阐释与建构现代化的中国文学。中西文化对撞,内因外因结合,中国新文学在文学批评中踏上了它的现代化之途。
注释:
①许纪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②周海波:《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6)(55)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98,447,469,447,476,476,465,466,466,453,464,463,453,477页。
(15)(17)(73)(74)(75)(76)(77)(78)(79)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112,99,10,60,87,105,100,49,50页。
(18)蔡元培:《蔡元培哲学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4页。
(19)陈兼善:《进化论发达略史》,《民铎》,1921年第5期。
(20)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21)(23)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梁启超全集》第4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6,759页。
(22)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绪论》,《梁启超全集》第3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71页。
(24)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引自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第1集,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681页。
(25)梁启超:《小说丛话》,引自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第2集,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308页。
(26)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梁启超全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27)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95页。
(28)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郭绍虞、王文生编《历代文论》第4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29)(30)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选集》上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316页。
(31)(32)(33)陶曾佑:《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郭绍虞、王文生编《历代文论》第四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21,222页。
(34)陈独秀:《敬告青年》,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5页。
(35)(36)(37)(38)(39)任建树、张统模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136,178,231,137页。
(40)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72页。
(41)(42)(43)(59)(60)(70)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胡明编:《陈独秀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50,43,50,50,50页。
(44)(48)(49)(50)(51)(52)(72)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221,117,119,120,126页。
(45)(46)(47)(53)(56)(57)(57)(58)(69)(71)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姜义华编:《胡适学术论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1,21,28,82,20,20,21,23,22,22页。
(54)朱晓进:《文化视角与鲁迅研究》,黄修己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61)周作人:《平民文学》,张明高,范桥编《周作人散文》第2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30页。
(62)(63)周作人:《人的文学》,张明高,范桥编《周作人散文》第2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125页。
(64)(65)(67)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254,255页。
(66)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
(69)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标签: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读书论文; 胡适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达尔文论文; 西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