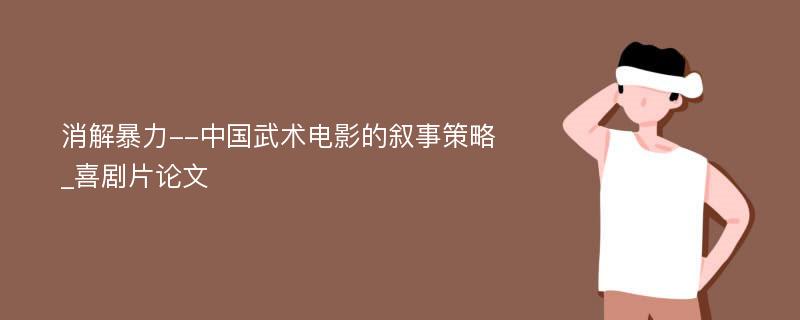
消解暴力——中国武侠电影的叙事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暴力论文,策略论文,武侠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暴力、爱情、喜剧是当代电影艺术基本的叙事类型,也是电影艺术家始终青睐的三大 主题。在电影的商业市场上它们构成了主流电影业的三大支柱。时至今日,暴力、性、 笑已经进入到各种样式、各种风格、各种题材的影片之中,它们几乎成为任何一部叙事 性的电影都不能缺少的“观赏性卖点”。特别是那些以暴力动作为叙事重心的类型影片 ,由于其特定的表现内容更决定了暴力“出场”的必然性。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电影 中的暴力越来越成为一种具有“消费性质”的视觉文化样式。进而使观众在无形中认可 了影像暴力的合理性。其实,无论从道德的意义还是从美学的意义上讲,在电影中一味 地渲染暴力都是不可能的(一场腥风血雨的枪战,与一场美仑美奂的歌舞表演是不能同 日而语的)。但是,在相似的叙事背景和规定情节下,如何处理暴力的内容,如何选择 暴力的表现方式,就显得十分重要。为此,电影对暴力的表现方式——是强化了暴力的 恐怖和惊悚、还是消解了暴力的血腥和残酷,便成为我们判断一部影片艺术品位的重要 尺度,也是衡量影片精神境界的重要标准。在这方面,中国武侠电影数十年的创作历史 ,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可以借鉴的成功范例。
正视暴力
首先,由于电影艺术“拟真性”的语言形式和梦幻化的观赏机制,它会对电影观众提 供一种假想的心理满足。无论是心理暗藏的性爱的欲望还是在潜意识中蛰伏的暴力情结 ,人们通过电影这种特殊的娱乐机器都能够得到某种程度的宣泄。电影中经过叙事逻辑 “校正”后的暴力,正为观众的心理需求提供了一个正常的“出口”,使他们受到压抑 的“心理冲动”通过电影中“故事化”的表述得到某种缓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 不加区别地一味否定电影中的暴力,笼统地把所有涉及到暴力的内容都称之为“娱乐的 毒药”,进而把今天的武侠、动作影片与二三十年代的武侠神怪片相提并论,把革命战 争历史影片中的暴力与好莱坞电影中的暴力等量齐观,就等于从总体上否定了不同电影 类型与表现题材间的区别,进而否定了中国武侠动作电影中崇侠尚义的文化精神和抑恶 扬善的文化主题,特别是否定了那些以抵御外敌、捍卫民族尊严为题的历史影片的意义 。最终等于混淆了整个电影艺术的评价尺度。
其次,我们不能把电影中的所有动作——技击表演、武术竞技、武舞、剑舞、擂台比 武、比武招亲统统称为“影像暴力”,并用一种尺度来评判它。因为在以上这些动作场 面中,并不具备通过暴力来杀伤对方的“叙事动机”,进而也不具备真正的暴力性质。 有些民俗化的武打动作场面,虽然有时也具有某种对抗性,但是它们的真正意图通常是 为影片增加表演性的视觉奇观,以此来增强影片的娱乐性和观赏性,其中许多的场面如 “舞剑”、“舞狮”、“擂台比武”、“比武招亲”都已经成为中国武侠动作片中常演 常新的经典段落,如果我们把这些以武术技击为原型的动作场面与好莱坞电影中的那种 血腥的凶杀场面一概而论,都将它们称之为影像暴力的话,那么就从根本上抹煞了电影 艺术中暴力与非暴力的区别,进而否定了我们讨论暴力问题的意义。
再次,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本文,武侠电影里的生死拼杀就从未终结过:一场接一场 的厮杀,一次接一次的争战。有时刺客甚至想要结束拼命杀的生涯,也是要通过杀人来 完成(如《刺客新传》,1993年)——这也许正是刺客一生最悲惨的命运所在,他几乎无 法摆脱暴力的阴影!这就是说,由于特定的表现题材武侠电影不可避免地要诉诸于暴力 ,它甚至是这类题材的作品解决矛盾冲突的唯一方式。这是以武打为动作重心的电影和 电视剧必须恪守的一种叙事常规——这是武侠影视艺术与生俱来的“文化原罪”。然而 ,中国武侠电影有时正是通过这一幕幕血泪横流的惨剧,在刀剑丛中唱出过一曲曲壮烈 的悲歌。所以,我们必须要区分在电影具体的叙事过程中哪些暴力动作是以正义的、道 德的名义实施的,哪些暴力动作是以非正义的、非道德的名义实施。从外部动作上看, 同样是击打对方,同样是杀人取命,由于他们各自的动机不同,目的不同,所以实施暴 力的意义也就不同。
另外,武侠电影向人们昭示着一个以暴制暴的世界:人们面对暴力的威胁和挑战,尽 管一忍再忍、但最终都会以暴力抗争邪恶、最终铲除邪恶。以血还血,以命抵命,通常 是江湖豪侠信奉的人生哲学。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看,几乎每一部武侠电影都是不能接 受的,因为它背离了人道主义非暴力的道德准则。尽管如此,就电影的叙事层面而言, 我们还是要分清的是哪些暴力动作是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和影片叙事逻辑的暴力表演, 而哪些是违背人物性格逻辑和影片叙事逻辑的对暴力的渲染。那种完全脱离了人物性格 的走向,游离于影片整个叙事情节之外的暴力,通常是一种纯商业化的暴力表述方式。 它除了给观众一种感官刺激之外没有任何正面的意义。相反,一种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 和影片叙事逻辑的暴力表演,则对于电影的思想内容可能会具有正面的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讨论影像暴力虽然是一个理论问题,但是它绝不是一个“从抽象到抽 象”的纯思辨的问题。它不仅要放到具体的社会历史层面上来考察,同时还必须还原到 电影的叙事过程及影像的表现形态上,才能够真正澄清问题的实质,进而真正把握影像 暴力的是非曲直。
暴力的神圣化
中国武侠影片中最常见的神圣旗帜是“替天行道”与“为民除害”。天意,在中国是 超越任何法度的最高道德范畴,“是世界的最高主宰”。在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中,天与 人历来是相通、相合的,正所谓天人合一。所以“替天行道”本身就是为人(民)除害。 武侠电影正是利用这种世俗冲突的非世俗化表述,赢得了广大中国观众对影片的“信服 ”,同时弥合了大众心理在现实生活中对正义、对秩序的笃诚。
从根本上讲,在电影中任何以杀戮为目的的暴力行为都是残忍的,惟有经过历史与道 德的双重修辞之后,才会给人造成一种合理合情的感觉,甚至造成一种对恶势力“不杀 不足以平民愤”的心理感受。只有为民除害,替国杀敌的侠义英雄才更容易赢得观众的 普遍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实施正义暴力,对于个人来讲,塑造的是一个道德与民族意义 上的“双重英雄”,对于群体和集团来讲,当暴力成为一种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捍卫 民族尊严的历史责任的时候,在正义与伦理的旗帜下的力量,就不仅是强大之师、威武 之师,而且还是正义之师、神圣之师。中国武侠电影有许多是以“反抗侵略,驱逐鞑虏 ”为叙事主题的。特别是以晚清为历史背景的武侠电影,像《黄飞鸿之王者之风》(199 3)、《方世玉》(1993)始终都贯穿着这样的历史主题。在这样的叙事语境中,正义一方 所实施的暴力就具有“神圣”的意义。
在具体的叙事进程中,中国武侠电影在处理人物命运的结局时,往往将其与某种“天 意”联系起来。强调冥冥之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伦理法则。在《黄河大侠》(1987) 中马义在“妙法寺”与罪孽深重的段王决一死战,正是在“天意”(闪电)的指引(照耀) 下展开与恶势力的生死交锋。段王最后并没有被利剑血刃,而是葬身于黄河的万顷狂涛 之中,显示出历史巨流对这个逆贼的无情埋葬!《新龙门客栈》(1992)中朝廷昏庸,宦 官当道。大太监曹少钦主持东厂,上挟天子,下令百官,官场上腥风血雨。影片在结束 这个罪恶集团的历史命运时,作恶多端的东厂鹰犬贾廷同样并没有死在豪侠义士的刀剑 之下,而是在与金镶玉的拼杀之中,被转动的石磨碾得肝胆俱碎!又被金镶玉用磨出的 一瓢血水浇得“狗血淋头”!使这个茹毛饮血的恶魔最终只能落得一个“自作自受”的 下场。《晚清风云——邪教白莲》(1993)里的占承天尽管有一身过人的武艺,但他也难 逃“天意”对他的最终裁决:在一阵惊心动魄的搏击之后,从高处跌落下来的占承天被 劈开的青竹刺透心窝,使这个历史的叛逆得到了“罪有应得”的结局。不论是石磨、还 是青竹都不是杀人的凶器,但这些物体最终成为置人于死地的因素,进而体现出武侠电 影所强调的叙事结局中隐含的神圣“天意”。包括《少林寺》(1983)里王仁则的归宿也 是他行凶作恶的必然结果:觉远在将他击倒在地后,接过牧羊女扔过来的复仇之剑,一 剑刺破了王仁则的胸膛,罪恶的血迹直冲而上,像是用它在祭祀被他杀害的生灵。由此 可见,对鲜血的展现并不都意味着是对暴力的渲染,武侠电影创作者们这种不约而同的 情节设计,其实都是想在精彩的武术演义背后,通过暴力的神圣化转述一种“善恶有报 ”的世俗伦理。豪侠义士也时常是以这种“替天行道”的名义来除暴安良,行侠仗义。
武侠影片中的暴力美学同时也是道德的美学。不论冲突的背景具有怎样的合理性,正 面人物在特定的情景中,通常都是后发制人。特别是在一场事关生死的较量之前,更会 一忍再忍,不到迫不得己决不会出手伤人。与此相反,那些恶势力的代表人物总是首先 寻衅动武,滥杀无辜,而且常常在“斩草除根”的旨意下把暴力的魔爪伸向妇儒……包 括以武侠电影为原形的动作影片,在处理暴力情节时,也特别注重设定暴力的“伦理依 据”。吴宇森导演的影片《英雄本色2》中有两个到餐馆里寻衅的恶棍。他们凌辱女性 ,肆意捣乱,甚至把饭菜倒在客人的脸上。这显然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一 种人性尊严的挑衅者。但即便在这种个人的财产遭到破坏、人格受到污辱的情况下,主 人公阿KEN也没有直接反抗,而是先把倒在地上的饭拣起来,重新放在盘子里,一边吃 一边对两个恶棍说:“饭对你们没有什么,但是饭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不允许你们污辱 我们的亲人!”这时,恶棍开始拔枪,威胁到阿KEN的生命,阿KEN才夺过手枪打伤了随 时可能向他开枪的恶棍。这种既是自卫又是反抗的暴力行为,由于出自对亲情和人格尊 严的捍卫、对社会正常秩序的维护,使其自身具有很强的正义色彩。包括影片的高潮段 落阿KEN、阿杰、四叔一起冲进犯罪集团印制伪钞的地下工厂,捣毁了犯罪集团的老巢 ,尽管主观动机是为了替死去的亲人报仇,但客观的叙事效果是这种“出师有名”的暴 力所维护的也是一种正常的社会伦理秩序。吴宇森的动作影片所表述的暴力美学,在相 当的程度上所渲染的是这样一种伦理美学。
暴力的伦理化
在中国武侠电影史上,黄飞鸿系列影片当初在香港电影市场上之所以大受观众的欢迎 ,除了它摆脱了过去港派武侠片舞台化的、意念化的武打设计,力求展现真实的武功外 ,重要的原因就是黄飞鸿所扮演的基本上是一个正剧角色。他打抱不平,抑恶扬善,一 贯奉行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精神。讲究礼(谦恭有礼)、义(行侠仗义)、忍(克己忍 让)、恕(劝坏人改过从善)、和(力主和平解决问题)。尤其是特别强调武德,强调练武 是为了健身,切忌恃技凌人,反对滥用暴力。在影片的叙事过程中非不得已不出手伤人 。对恶人也尽可能不杀伤,而是力劝他改过从善。对于个人得失甚至受辱都可以不计较 ,可是为了除暴安良,抑恶扬善就必须挺身而出。应当说,黄飞鸿电影这种因循传统精 神、维护现行文化秩序、讲究伦理道德的文化策略,特别符合当初香港社会祈求稳定、 保持平安的民风。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忠与孝分别体现了对人作为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的绝对要求:“ 在家为孝,入国为忠”,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它们共同强调的是对上(父)、对主(君) 的绝对服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里“父”与“主”、与“君”一样,都是一种至高 无上的道德偶像。这就是说,忠与孝,不仅是对人物行为的外在规定,而且已经变作了 人物内在的一种精神品格。所以,在武侠电影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它逐渐形成了以 尽忠为核心的“报主”主题和以尽孝为核心的“复仇”主题。同时创造出中国电影史上 一个又一个忠孝并举、义勇双全的神话英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是其最基本 的主导思想。忠孝传家的道德训戒是深入人心的。谁要是破坏了这个伦理秩序,轻则犯 罪,重则杀身。《礼·曲礼》有言:“父之仇,弗与共戴天”,所谓“此不共戴天者, 谓孝子之心不许共仇人戴天,必杀之乃止”。由于侠客浪迹江湖的本性使他们必然会远 离官场,进而远离君王,所以忠君为核心的报主的主题在武侠电影中时常会被以尽孝为 核心的复仇主题所取代:特别是作为一种伦理编码,武侠电影中“替父报仇”的叙事母 题,经常成为其诱导观众向银幕认同的重要手段。张彻古装武侠电影的代表作《独臂刀 》(1967)中有一个本己断臂、隐退江湖的侠客方刚,他后来之所以重入江湖,不是为了 名、更不是为了利——而是为了孝。他是在得知义父齐如风败于长臂神魔之后,为报答 义父的养育之恩,也为了完成亲生父亲生前留下的遗愿,才愤然出山报仇雪耻的。这种 “双重继替”的叙事格局,足见在武侠片里父对子、师对徒的亲情关系是何等的重要。 方刚的右臂虽然后来为师妹齐佩所断,但他并没有怀恨在心。却刻苦练成独臂刀,救出 为恶势力所囚的齐佩,严惩了恶势力,报达了师恩。尽管方刚在影片的叙事过程中出演 了许多暴力搏击的场面,但由于他始终是在“替父报仇”、“替民除害”的道德旗帜下 使用暴力,他的行为便具有充分的伦理依据。中国武侠电影中这种“孝义双全”的人格 典型,也是世界电影人物画廊中极具个性色彩的艺术形象。该片之所以能够成为当时港 台最卖座的影片,之所以能够再领武侠片的创作风潮,其中对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信守 与高扬,必是原因之一。
在许多情况下,电影中实施暴力的准则与现实社会中正义的暴力准则是一致的。或是 说,它们所需要的历史和道德依据是一致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 犯人。”这不仅是现实世界正义的战争法则,而且也经常是电影艺术惯用的叙事法则。 电影为了突出暴力实施者的正义性,在表现善恶双方的搏斗、拼杀之前,电影作者特别 注意首先表现非正义者的挑衅与侵害行为,从而为正义者使用暴力进行反抗确立充分的 道德依据。在个体英雄的表现方面,成龙的影片特别注重对暴力的“书写”。成龙所扮 演的角色在叙事过程中总是先处于被欺压的、被压抑的、受到不公对待的位置——无论 他是作为乡野的平民,城市里的厨师,还是作为警察,他首先都是被非正义的势力伤害 的对象,此时他的反抗在使用暴力上便具有了“天然”的合理性。即便是把对方打得魂 飞魄散,观众也不会感觉到反抗本身有问题。应当说,所有成功的动作型影片,在处理 暴力情节时,都是十分注重暴力表现的“伦理性”。
一般来说,仅仅从社会历史(正义/反动)的意义上来肯定暴力的合理性,只能诉之于观 众的理性,要真正地赢得观众对影片的认同,还必须建立一种符合于观众普遍的观赏心 理和是/非、善/恶标准的叙事逻辑。使观众从感情上融汇到整部影片的叙事情境之中, 使他们即便是以个人身份来判定影片的意义,也不至于得出与影片创作者的初衷相左的 结论。而这种效果的达成,就要求影片对暴力动作的表现,必须符合“大众伦理”的叙 述方式。而这种“大众伦理”的叙述方式通常又是建立在家庭伦理的原型之上。我们知 道,家,在中国传统文化语汇中有着双重的意义:它既是指家庭、家族、家园,同时还 指的是国家社稷,所以,一个为亲人、为家庭而战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为国家 而战的人。这样,武侠电影中的暴力英雄不仅是除暴安良、匡扶正义的勇士,同样也是 民族文化传统和家族亲情伦理的捍卫者。影片《方世玉》(1993)中,方世玉与恶势力的 最终决斗,是在营救方世玉父亲的刑场上展开的,一个为民族、为国家、英勇无畏的方 世玉,同时又是一个为父亲、为家庭舍身忘死的方世玉。这种双重的人物性格是武侠电 影中英雄人物的一种独特风范。由于伦理本文已经成为先(决定)于叙事本文而存在的“ 绝对律令”,所以,当二者在银幕上相互重合的时候,伦理本文必将成为推动影片叙事 的内在动力:方世玉为营救落入虎口的父亲,凭借着一身高强的武功,勇劫法场。在经 过殊死搏斗之后,血泪沾衣的方世玉怎么也拉不起那刃即将要落在父亲头上的巨型铡刀 !一个孝子舍生忘死的救父壮举,眼看要化作一场让人心肺俱碎的悲剧。然而就在这时 候,导致影片叙事逆转的另一种力量出现了:一位老母亲为方世玉这种旷世的孝子之心 所感动,毅然冲上法场,与方世玉一起奋力拉起悬在方父头上的屠刀,紧随其后的是两 个幼小的孩子、是长者、是数不清的百姓……影片《方世玉》的这种伦理编码,其中心 词语就是一个“孝”字。它是推进影片叙事情节的发展、强化观众对影片主人公心理认 同的主要动力。
暴力的喜剧化
中国传统的武侠电影,大都是以正剧或悲剧为主要样式,凸现的是豪侠义士壮烈的人 生经历。即便有些喜剧的成分,也仅仅是起一种点缀、调味儿的作用。像李小龙在影片 《猛龙过江》(1973)中一改他在《精武门》(1972)和《唐山大兄》(1971)中的悲剧英雄 形象,以带有喜剧化的武打风格为武侠电影增添了新的娱乐性内容。他在打斗时的特殊 动作,如凌厉的叫声、睥睨的眼神,已成为李小龙武术风格不可缺少的标记,特别是他 创造的“凌空三弹腿”更成为李小龙特有的武林绝技。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改变中国武 侠电影的传统样式。到20世纪70年代,当武侠电影随着整个电影商业化的进程不断发展 的时候,武侠电影的创作者便开始把极有商业价值的喜剧性元素引入到刀光剑影的武侠 世界中,这次喜剧与侠义的汇聚,不再仅仅是从细节上、武打上改变中国武侠电影单一 的艺术风格,而是从结构上、整体上重新创造了中国武侠电影的经典样式。
武侠电影的喜剧化是消解暴力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中国武侠电影中,袁和平所创立的 以喜剧性动作为主的谐趣武打片,是武侠电影与喜剧电影结合的成功典范。他将高度的 动作性、惊险性和喜剧性、娱乐性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武侠电影中特有的一种影片类 型——谐趣武侠片。武侠电影喜剧化转变,是其创作风格从英雄化趋向平民化的重要标 志。也是在电影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武侠电影自身的一种生存策略。特别是在 言情、枪战、喜剧等诸种类型电影各领风骚的香港电影界,传统的以武术技击为主的武 侠电影,已很难保住它昔日的票房霸主地位。所以,兼容不同的类型影片的创作手段, 即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以《蛇形刁手》(1976),《醉拳》(1976)为代表的一系列 谐趣武侠电影是动作电影与喜剧电影相结合的成功典范。它将喜剧性元素引入到刀光剑 影的武侠世界中。从此,中国武侠电影完成了从传统的古装刀剑片到现代功夫片的转变 ,喜剧与动作的汇聚,不仅是从细节上、武打方式上改变中国传统武侠电影单一的艺术 风格,而是从样式上重新创造了中国武侠电影的经典形态,使武侠电影这个充满着动作 、暴力的世界,融进了谐趣喜剧的因素。《醉拳》的导演袁和平在回忆他当年拍《醉拳 》时说:“在此之前,我参与拍摄了许多部武侠影片。我总是感觉到武侠电影里有太多 的血腥、太多的暴力!那么,我就想有没有一种既好看又没有那么多暴力的东西呢?后来 我把动作和喜剧两种类型结合在一起,用喜剧来代替那些血腥的东西,喜剧加动作,又 漂亮又好看又好笑。结果呢,很成功!”应当说,武打场面的喜剧化处理方式,使许多 武侠电影摆脱了那种传统的正剧面目,而换上了一种时而轻松愉悦、时而又惊险紧张的 兼容主义的美学风格。也许,这也正是中国武侠电影走进现代时尚的最重要的“症候” 。即它不再是被一元化的美学体系所笼罩,而真正地呈现出多元化的美学品格。
影片《醉拳》对暴力的喜剧化处理无疑是中国武侠电影中的经典。黄飞鸿的师傅苏叫 花子在影片中创造了一种武林绝技“醉八仙”。它是一组由八仙的名字所构成的系列技 击方法。黄飞鸿在师傅的教授下开始苦练这种绝技。但是,此时的黄飞鸿已不再是20世 纪五六十年代香港影坛上那个传统的侠义英雄,而是一个以现代社会生活为背景的“平 民英雄”,是一个消解了崇高色彩的世俗形象。在这种历史语境下的黄飞鸿即使面对的 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搏杀,也不再是那种一脸正义的形象。在影片的结尾部分,黄飞鸿在 师父的指导下借助酒力越打越勇。但对手阎铁心识破了黄飞鸿的“醉八仙”的套路,用 “鬼魅无影手”重创了黄飞鸿。就在决定胜负的关键之时,黄飞鸿急中生智,自创“何 仙姑”套路:嬉笑怒骂,功到自然。以“美人照镜子”、“骚寡妇送情郎”、“扭屁股 老娘坐马桶”一系列喜剧化的武打动作弄得阎铁心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甚至不 得不质问黄飞鸿这是何种拳法?黄飞鸿说道“各施各法,各马各扎,各庙各菩萨,同一 师傅,不同的玩法”。最终严惩了冷血杀手阎铁心,为民除了一害。成龙脱颖而出后, 成为中国武侠电影史上顶尖儿的谐趣武星。
由于武侠电影是一种动作性极强的类型影片,所以在武侠电影中的喜剧表演时常是和 武打情节联系在一起的。影片《新少林五祖》(1994)甚至将一场婚礼场面变成一种动作 场面。一会儿拳打脚踢,一会儿嬉笑怒骂,新娘新郎分别从婚礼上的主角变成了这场动 作喜剧的主角。按理说,过分夸张的喜剧性表演虽然容易取悦于观众,但由于刻意营造 的喜剧情景时常会远离生活的原貌,进而也非常容易使影片和观众产生间离。而谐趣武 侠片中的动作性场面却正好及时地阻塞了这种间离效果的发生,它能够以紧张的武打场 面“弥合”因夸张的喜剧情景所造成的观众与影片之间的裂痕——就如同《新少林五祖 》中,在洞房里的戏已全然是一场喜剧表演:当准备携宝逃跑的新娘刚一出门,一刀劈 过,将她手中的一个宝瓶劈成碎瓦!新娘随即大叫一声“赔钱”!便与官兵厮打起来。在 这样短暂的叙事情节中,喜剧与动作这两种情绪线索能够如此有机地交错在一起,不能 不说是谐趣武侠电影创作的一种“成功技艺”。武侠电影中的喜剧情景不仅出现在武侠 电影的“武戏”中,而且也出现在武侠电影的“文戏”之中。包括像《少林寺》(1982) 这样以匡扶正义、除暴安良为主旨的武侠影片,也将喜剧的因素注入到影片的叙事情境 之中。棍僧在菜田里捕捉青蛙,在竹林中烧烤狗肉的“嬉闹之戏”都使这部充满复仇、 搏杀的影片又增添了一份嬉笑的乐趣。随着武侠电影中喜剧因素的不断增加,练功习武 的场面也掺入了不少噱头和笑料。武侠电影中武术的练习就时常是被神奇化的,也是被 喜剧化的。《英雄本色》(1993)中林冲和鲁智深对武术痴迷已到了如醉如痴的境界,两 人见面就打,甚至连说话也要用动作来作注释,直打得昏天黑地,墙壁崩塌……《少林 英雄》(1993)中方世玉的母亲教儿子练功,也是一种极具喜剧性武艺表演。方世玉的母 亲挥舞着竹竿,将躲在水缸的儿子打出来,又用梯子当竹竿挑着他在放满药水的大缸里 “涮来涮去”,直炼得方世玉连连求饶才罢休。这种方式的“千锤百炼”在传统武侠电 影中是很难看到的。影片《新龙门客栈》(1992)中的金镶玉是武侠电影中的一个少有的 喜剧化了的女性形象。她取代了1967年原版《龙门客栈》客栈老板的正剧角色。由于她 的出现,《新龙门客栈》里异常惊险紧张的气氛,常常会被嬉闹、喜剧的情趣所冲淡, 从而彻底改变了武侠电影的传统样式。这位风骚入骨的老板娘,在善恶两方剑拔弩张之 际,却拿着茶杯在一旁悠然“戏水”。她张口一个老娘闭口一个老娘,遇到谁就和谁“ 较量”:她一会儿和侠客周怀安调情,一会儿与侠女邱莫言斗法;一会儿和东厂的官兵 周旋,在杀机重重的龙门客栈中,这种喜剧情景的设置几乎已经达到“走钢丝”的境地 。而随着影片的剧情发展,金镶玉的喜剧表演又逐渐转向了正剧的风格,从而巧妙地“ 缝合”了喜剧与动作的“接口”。
夸张化了的戏剧情景和脸谱化的人物性格,是武侠电影中最为明显的喜剧特征,特别 是那些本身不会任何武术的角色,当他们处于一种惊心动魄的战场之时便会产生出奇的 戏剧性效果。在《少林豪侠传》(1993)中的阿苏就是这样一个被夸张了的喜剧性角色。 他与黄飞鸿一起进入藏着鸦片与炸药的仓库里,清兵的大刀在他的头顶上呼呼作响,枪 弹在他的身边四处飞溅,而正是这个既不会武功,人还没有枪高的阿苏,利用种种偶然 的时机,创造了赫赫战功!《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1993)中田启云将军与顾长风在营 帐外对打,本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但顾长风点了对方的笑穴,一方面向帐外的官兵 掩饰了这场冲突,使顾长风免受围攻,另一方面又使这场血战顿生诙谐、嬉戏的情趣。 当代武侠电影中的喜剧不再是仅仅靠演员的表演来营造谐趣的效果,而是在此基础上运 用各种的电影特技和影像效果,共同营造喜剧化的情节,力求使喜剧与武侠这两个不同 的类型影片得到完美结合。《东方不败》里的华山派的弟子们将“乌鸦嘴”的胭脂换成 辣椒面,使她在化妆时洋相大出,令观众忍俊不禁。《倩女幽魂》宁采臣为了寻求公道 ,半夜到县衙门报官求救,结果衙门的官员张口就是“升堂费”,并以此为由先打宁采 臣30大板,以这种喜剧的形式讽刺时事。《新火烧红莲寺》里的方世玉一边拼死救美女 ,嘴里还一边嘟嚷着“女人可真麻烦”……这一切喜剧化的情景,为以暴力动作为主要 商业卖点的武侠电影带来了新的市场活力。
暴力的舞蹈化
舞蹈化是消解武侠电影中暴力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我们知道,中国武侠动作片中的动 作原型、它的构成基础是中国武术,但是当代武术作为一种体育项目,它并不直接等同 于暴力本身。因为武侠电影中的武术技击动作经常在叙事过程中会演变成一种具有表演 性的“武术之舞”,这时它的击打性的“实用功能”实际上已经让位于舞蹈化的“表演 功能”。此时的观众与其说是在观看一场武打,倒不如说是在观看一场武舞表演。尤其 是许多这种表演都是安排在非对抗性的情节轴线上,对打的双方有时是一场误会,有时 是一种竞技,有时甚至是一种逗趣儿。
毋庸讳言,武侠影片中武术的舞台同时也是暴力的舞台。只不过与其它影片中的暴力 影像相比,中国武侠影片中的暴力是高度风格化、程式化的。即便同样是以暴力的方式 完成叙事,武侠电影也都别有一种神韵融贯其中,而不像好莱坞影片那样人被打得血肉 横飞,浑身颤抖,几乎全然都是机械暴力的渲染。武侠影片这种风格化的暴力呈现方式 ,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武侠电影与讲究章法、注重门派的中国武术有一种天然的血缘关 系;另一方面是因为武侠电影与中国传统戏剧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中国许多武侠影片 的空间形态都是“脱胎”于京剧舞台。为此,中国武侠影片更注重在有限的空间内制造 出奇异精彩的视觉效果。单一的武术表演并不能满足电影观众所特有的观赏需求,所以 ,武侠电影中的武术技击,从来都不是以单纯地展示武术技艺为最终目的,它必须将武 术技击与剧情、与人物、与主题“镶嵌”在一起,进而在银幕上演变为一场时而激烈、 时而飘逸的武术之舞:长拳的疾速舒展、南拳的刚劲猛烈、太极的柔韧轻灵……所有这 些风格各异的武舞表演,共同构成了中国武侠电影多姿多彩的整体面貌。
由于武术与舞蹈在武侠电影中的有机结合,我们在影片中观看武打动作的同时,也就 仿佛是在欣赏一场优美的武舞表演。武术与舞蹈的混然一体,时常会产生一种如诗如画 的境界:影片《白发魔女》中卓一航在漫天的朝霞下练习剑术,缤纷的飞花在其周围悄 然飘落,而练剑的地方依然是一片洁净空场,作者在此着意追求的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美 学境界。《少林寺》里觉远在春、夏、秋、冬的景色中挥舞红樱枪时而凌空跃起,时而 扑地飞旋的表演,更是武侠电影中武舞的佳品。武侠电影中武术的舞台是无所不在的: 客栈,街巷,荒野,山崖,丛林,大漠……尤其是在近年来的武侠电影创作中,制作者 的商业意图之明显是日甚一日。武术的舞台便逐渐地向着名山古刹、风景胜地扩展:作 为一种极有观赏价值的文化本文,九寨沟、少林寺、五台山、清西陵、桂林山水、三峡 风光,都已成为中国武侠电影中不可或缺的叙事本文。
武侠影片中的舞台道具也在不断翻新:从昔日的扇子、筷子、铜钱、酒坛、板凳,样 样都有神奇的魔力,到今天的银针、丝线、绸带、剪刀,件件都是致人于死地的利器。 飞檐走壁、腾云驾雾在武侠影片中本来就是常事,近年来,武侠影片的制作者借助于不 断完善的电影特技,更是把武术之舞拍得出神入画、触目惊心。在当代武侠电影中,武 术技击的表演成分已不仅来自于演员本身的武术技能,更多的是来自于影片特技所造成 的奇特的视觉效果,许多已完全不再是拳脚对拳脚、刀剑对刀剑式的“搏击”,其主要 的“搏击”场景是数字技术神奇莫测的力量所造成的非凡效果,武(舞)者的风采多少已 被武器的威力所覆盖。
就动作的表现而言,任何一部武侠电影,其实都是在借用武侠文学所提供的情节线索 ,来展现中国武术的神奇力量。从动作设计上讲,武侠电影实际上是为中国武术搭建的 一座展示其独特魅力的艺术舞台。在中国传统的武侠电影中,由于严格地遵循着“太阳 时”式的、线性的剧作传统,讲究启、承、转、合的戏剧化模式,注重的是在保持完整 的线性叙事的基础上,把不同的武打样式、不同的武术流派穿插在故事情节之中,利用 武打动作来展示剧中人物的性格特征和道德归属,并使观众能够欣赏到武侠电影独特的 动作神韵。《卧虎藏龙》(2001)在武打设计方面不仅具有利落紧凑的节奏,而且呈现出 舞蹈般的美感,其中在轻功部分更是打破了以往传统武侠片的表现方式,达到如武侠小 说中所描写的“飞檐走壁”、“凌波微步”、“旱地拔葱”的境界。在戛纳放映时令外 国媒体记者瞠目咋舌。《卧虎藏龙》被《加拿大环球邮报》称为“画面精彩,是芭蕾舞 般的武打艺术片”。(注:见《新民晚报》2001年2月15日。)《英雄》(2002)为了尽量 消解影片的暴力特征,在剧情设计上编导首先淡化了对打双方的“敌对性质”,尽量把 影片中所涉及的暴力拼杀转化成一种以展示中国武术神韵、推进剧情发展为主的“武舞 表演”,这与其他武侠电影中那种以暴力取胜、以杀生夺命为目的的武打动作有根本的 不同。
秦国七大高手在棋艺馆里与长空展开的搏击是一种典型的表演性武打。对打的阵势分 别采取了1比1、1比2、1比4的对打形式。形式严整的武舞队阵和通过高速摄影呈现的击 打动作,充分消解了暴力原本的残酷性。接下来是长空与无名之间在棋艺馆院内的“双 雄对决”。表面上看来双方面临着你死我活的境遇,而实际上却是长空与无名之间早已 预谋好的一场“武舞表演”,它根本就是演给秦国七大高手(也是演给观众)看的一场“ 武戏”。加上迷蒙细雨的“装点”和伴着古琴时而悠然时而密集的弹奏,棋艺馆内这场 看来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实际上是一场借助于棋艺馆的“舞台”展开的“武术之舞” 。
胡杨林里的武打,尽管如月步步紧逼,飞雪仍然是频频退让,这种剧情设计又为武舞 “留出”了大量的表演性的空间舞台。在如月反复地进攻,飞雪不断地躲闪的过程中, 直卷起漫天的胡杨树叶如缤纷落英、回旋飞舞,直到使观众完全沉溺到由色彩和刀光所 构成的武侠境界。这种疾风卷落叶的场景在袁和平导演的《太极张三丰》中我们曾经领 略过,那是被太极拳的神奇功力所鼓荡的巨大旋流所卷起的漫天落叶!而在《英雄》中 因为有飞雪与如月这两个红色的精灵在林中穿梭,它的恐怖暴力的色彩已经几乎降至了 最低点。
长空与无名之间在棋艺馆院内的武戏后来在秦王的叙述中又“重演”了一次,并被“ 说”成是一种在主观意念中进行的比武。它依然保持了非对抗的性质。无名的利剑穿过 雨帘直取长空(剑挑雨帘)的镜头,动作设计之优美上已经臻于中国武侠电影中的经典样 式。在九寨沟无名与残剑的对打,同样被“说成”是在意念中展开的、为了祭奠飞雪所 举行的一种武打仪式。张艺谋刻意把它描绘成一种空灵、飘逸的“水上武舞”。残剑与 无名之间并没有仇怨,也没有争夺霸主的动机,更没有相互杀戮的意图,他们在波光如 镜的湖面上腾跃,在如诗如画的山林间飞翔,与其说是两位武林高手之间的一场武术竞 技,倒不如说是建构在主观意念之上的一种超然于世的“武舞巡展”。它比胡金铨在《 侠女》和李安、袁和平(动作导演)在《卧虎藏龙》中所展示的“凌波微步”更空灵、更 超然。只是剑划水面的创意既没有王家卫在《东邪西毒》(1994)中那种剑气冲天的气势 ,也没有《新碧血剑》中那种用热血点化剑锋的神韵。飞雪与残剑的大漠之战原本是一 场“意气之战”,可是后来却转变成为一场杀戮。可悲的是飞雪成为在影片中真正开了 杀戒的侠士。她在得知无名刺杀秦国失手之后,又知道残剑在大漠上书写的“天下”二 字动摇了无名刺秦的决心,便一怒之下与残剑在狂沙中“刀剑相见”。残剑为了证明对 飞雪的笃情,迎着飞雪的利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如果说,影片的前半部分残剑与飞雪 是为殉义而生的,那么到影片的后半部分,他们则变成为殉情而死。最后悲愤交加中的 飞雪用刺进残剑的飞雪剑又刺进了自己的胸膛。这种在《龙门客栈》里义士为了殉义而 采取的自尽方式,在《英雄》中变成了一种殉情的方式。
综上所述,《英雄》里没有一场真正的以杀戮为目的、以生死较量为旨意的武打。影 片中所有的武打场面几乎都是非对抗性的武舞表演。他们不是假定的,就是意念化的, 不是想象的,就是虚拟的。在中国武侠电影的历史序列中,这样一部本身就带有暴力( 刺秦)色彩的影片,仅出现了三处滴血的镜头:残剑在无名的故事中被飞雪刺中后淌出 的血,飞雪与如月对阵时剁在树上的剑锋上滴下的血与秦王被残剑划破脖子流出的血。 与那种血光四溅、尸横遍野的武侠电影相比,《英雄》这种“消解暴力”的叙事策略, 表现出它的作者对武侠电影经典叙事方式的把握和对国际电影市场心理趋向的洞悉。影 片就是这样把一场接一场的武舞“镶嵌”到影片的叙事情节之中,观众既看到了一场舞 蹈化的武术打斗,又没有被暴力的、血腥的场面所惊吓。除此之外,无名在藏书阁显示 “十步一杀”的威力、飞雪与无名在书馆外抵挡秦军的箭阵的武戏,都是没有对手出现 的纯表演性武舞场面。所有这些对暴力场面的非暴力化处理——即在电影的表层结构对 暴力的“隐性书写”和“诗化表现”,使整部影片在视觉上呈现出一种“低度暴力”的 特点。使《英雄》在影像上确实有效地消解了中国武侠电影历来难以消解的暴力和血腥 的视觉场景。
中国武侠影片始终都贯串着武术技击。在这里,通过精心设计的武打动作,通过刻意 选择的技击兵器,通过严格划分的镜头景别,影片的价值取向(是/非、善/恶、美/丑) 渐渐澄明,人物的命运被一一判定。几乎每部武侠影片的结局,都导向一场以武术对打 形式出现的暴力冲突。它既是影片影像特技的呈现高潮、影片剧情的叙事高潮,同时也 是一场建立在叙事体内的对抗性的武术表演——武术之舞的展示高潮。这种已经延续了 数十年的“经典本文”,映现着中国武侠电影最诱人的动作奇观。它构成了武侠影片主 要的观赏来源(兴趣中心)。从叙事的层面上讲,它是所有武侠影片的主导动作轴线;从 电影市场的层面上讲,它又是武侠影片常居不变的“商业卖点”。世界上任何一种样式 和类型的影片,都没有像中国武侠电影这样能够将舞蹈化的武术技击与剧情、人物如此 完美地同时呈现在银幕上,所谓“武舞同台”,突出强调的正是武侠电影的这种独特美 学特征。所以说,中国武侠电影是一种以武侠文学为原型,融舞蹈化的中国武术技击( 表演)与戏剧化的叙事情节为一体的类型影片。
以暴力的形式消解暴力
动作型电影的核心是用动作解决争端,用暴力决定胜负。动作电影这种电影的独特品 种决定了它永远无法回避暴力的手段,无法删除暴力的抗争,决定了它“动作叙事”的 性质。为此,如何处理动作、武舞以及种种暴力性的动作便成为武侠动作电影艺术创作 中的重要问题。从根本上讲,中国武侠电影的叙事策略,并不在于渲染暴力,而是在以 一种独特的方式来消解暴力的残酷性。这样才能够真正赢得观众的喜爱。
尽管侠客除暴安良的义举是在充满血腥的进程中进行的,但作为一种在叙事层面进行 的对暴力的“校正”,武侠电影中在江湖中搏杀的侠客,时常也会向往着一种没有杀戮 、没有血泪的世界。他们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后,时常会离开这个血泪横流的江湖。 他们有时甚至宁愿以自己的性命来中止江湖上的仇杀。影片《少林达摩》(1990)中杀人 无数的刀客面对着江湖上循环往复的杀戮,怨怨相报的因果,最后竟然选择了自杀来完 成自己的忏悔。真正的武林志士是把抑恶扬善作为自己毕生的天职,对功名、对财富即 便是得到了也会将它抛入九霄。《天剑绝刀之独孤九剑》(1993)的结尾,夏侯太子和后 唐公主(在胜利之后,最终向往的是一种归隐山林的田园生活。他们一个扔掉了象征着 权力和暴力的宝剑,一个扔掉了象征着财富的玉箫,双双退出江湖。虽然这是一种虚幻 的理想,但这种理想的流露表达的正是人们渴望世间永世安宁、不再征战的宿愿。《新 龙门客栈》(1992)的“闭幕式”同样也充满了对无休止的暴力的唾弃!一场血腥的屠杀 终于结束了,大漠上一片寂静,金镶玉用烈酒烧毁了自己苦心经营的客栈,也烧毁了那 个充满血腥气味的处所,她远离了大漠,也远了那个杀人取命的生涯。她向往的是一处 没有欺诈的精神寓所,一个没有杀戮的情感的归宿。
吴宇森执导的动作片的英雄总是流血、流泪的英雄。他的影片就是有再凶险的境遇, 再残酷的场面也不会失去人性的温情。这些情景使因过于激烈的动作和枪战给观众造成 的心理紧张能够得到间隙的缓解。吴宇森小时家境贫寒,自幼饱尝了人间的冷暖,目睹 了暴力的无处不在,使他在内心世界产生了“拥有暴力来反抗暴力”的心态。中国武侠 电影这个暴力的王国使他儿时的梦想找到了归宿。“以暴力的方式反对暴力”便成为他 一系列影片始终不移的叙事主题。他反对暴力的方式不是去否定暴力的作用,而是在展 示暴力的同时,揭示暴力给人类世界造成的无法挽回的代价。在他导演的许多部影片中 ,以慢动作(高速摄影)拍摄的人物如舞蹈般腾空而起的射击动作和天女散花般的无数炸 点、弹着点,使整个银幕上呈现的是一幅枪林弹雨中的英雄图景。最后的决战都被安排 在金碧辉煌的教堂里:在这样一个带着终极意义的空间里,所有的是非善恶,所有的贫 富强弱,面对的都将是生与死的最终抉择。在一阵铺天盖地的弹雨之后,教堂里的圣像 纷纷倒下,象征着和平安宁的白鸽如惊鸿般骤然而起,璀璨夺目的壁画变得满目仓痍! 暴力对世界上所有这些神圣的、祥和的、美丽的东西的毁灭和破坏,使它即使取得了胜 利也总带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悲凉!这就是吴宇森在影像世界中的“暴力论”。暴力那种 与生俱来的残忍在这种情境中呈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又表现出吴宇森对生命的弥足珍视 。
在世界电影史上,处理暴力情景方面有许多经典影片都为我们留下了可以借鉴的范例 。希区柯克的名作《精神病患者》里的浴室谋杀是世界电影史上经典的恐怖段落。但是 这场为人们反复“移植”和“重演”的暴力情节,却始终看不到那“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式的血腥场面。我们看到的是:摇晃不止的灯光,是阴森的人影,是急速的流水,是 拽下来的浴帘和恐惧的惊叫。作为一起谋杀案,它没有一个真正血腥暴力的镜头。但是 它所造成的心理的恐惧比视觉的恐惧更强烈,也更真实。影片《邦尼和克莱德》中两个 被追逐的罪犯走投无路的时刻,警察用冲锋枪对躲在树丛中的他们进行密集的射击。树 枝在冲锋枪疯狂的扫射中不停地颤抖、树叶在纷纷凋落,喻示着两个生命的完结。影片 《辛德勒名单》表现的是二战期间纳粹法西斯对犹太人进行种族屠杀的血腥历史。这种 题材本身就决定了它根本无法回避法西斯对犹太人野蛮屠杀的描述。然而,怎样在银幕 上再现600万犹太人的惨死,确实是一个关系到这部影片成败的重要问题。如果采用纯 粹纪录的方式来处理这个杀戮过程,那么其血腥和恐怖的场面将令人不寒而栗!导演斯 皮尔伯格在表现纳粹法西斯凶残的屠杀罪行时,采取的则是一种“写意”的方式:观众 并没有看到集体屠杀的血腥场面,看到的是堆积如山的衣物、首饰、镜框和金牙,看到 的是夜空中如飞雪般飘散的骨灰,听到的是钢琴鸣奏和冲锋枪的狂啸……在表现德军对 一座城市的疯狂屠杀时,镜头的前景是几个漫不经心的纳粹军官,他们的背景是整座被 杀戮、被涂炭的城市,城里每座楼的窗户里都映照出冲锋枪扫射时喷出的火光,可想而 知,此时此刻,每个家庭、每户人家、每个生命都在经受这场野蛮的杀戮!生的希望对 每个楼里的人来说都已经微乎其微。这种表现方式既从视觉感受上回避了观众直接目睹 大屠杀的残酷场面,又展现出纳粹法西斯血洗全城的过程。同时使辛德勒后来的营救行 动更显得艰巨而伟大。
人对痛苦、对灾难的这种普遍的退避心理是电影艺术创作中应当特别注重的。否则, 尽管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尽管是革命、正义的、胜利的战争,也容易给观众的心灵带来 不必要的阴影。笔者在访问俄罗斯时,圣彼得堡电影和电视大学校长亚历山大·别洛乌 索夫陪同我们参观封锁纪念碑的时候,他说他们现在已经不再忍心走进修建在半地下的 封锁纪念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要忘却这些惨痛的历史,而是因为里面有许多令他们不 堪回首的东西。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残酷了!所以,他们在铭 记历史的同时又在对历史的灾难保持着一种心理的距离,不愿用那些真实但却残忍的情 景来触动他们心灵的创痛。《血战台儿庄》从题材上讲是一部表现抗日战争革命历史的 影片,特定的历史真实决定了它的残酷性。除了对战争中激烈、凶残场面的表现之外, 由人的尸体所堆成的“血肉长城”使这部影片的暴力性达到了极为强烈的程度。为此, 它在香港曾被列入“儿童不宜”的影片。并不是说它的内容有悖伦理或与真实的历史不 符,而是当时的电影审查机构认为那堆积如山的尸骨会给儿童心理造成某种恐怖的、血 腥的印记,在他们还不能完全用历史和道义的观点来审视这些历史事件的时候会对他们 产生不良的心理影响。
在世界社会史上,有许多因对电影暴力进行模拟、仿效而走向犯罪的人。毫无疑问, 在暴力的阴影笼罩下的银幕世界,给人类社会造成了诸多的灾祸。在电影艺术无法彻底 去除暴力内容的情况下,怎样消除电影暴力的负面影响,消解暴力的残酷性给观众心灵 带来的恐怖和厌恶,建立一种既符合电影观众的观赏心理又适应电影艺术自身规律的表 述方式,是电影艺术创作中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电影理论所面对的紧迫的、复杂的学 术课题,特别是在中国电影走向市场化的年代里,面对着激烈的市场竞争,怎样满足观 众特有的审美心理需求,怎样建立中国主流电影的叙事体系和价值体系,都是十分重要 的历史问题。
标签:喜剧片论文; 电影论文; 暴力电影论文; 暴力美学论文; 武侠片论文; 新龙门客栈论文; 黄飞鸿论文; 方世玉论文; 醉拳论文; 影视论文; 武打片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