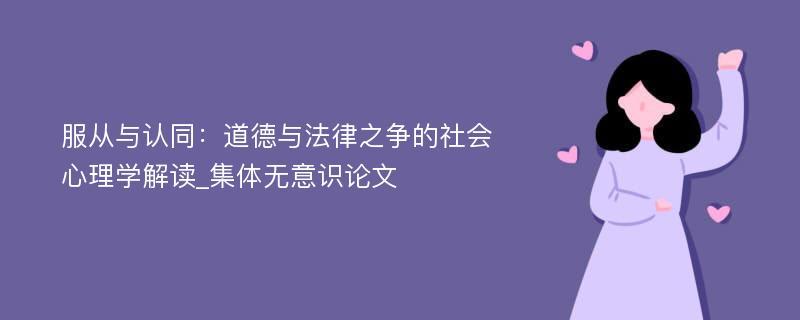
顺从与认同:“德法之辩”的社会心理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心理论文,顺从论文,德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及其研究视角
“德法之辩”一直是法学与伦理学史上的经典命题之一。究其实质,它是人类在借助于法律与道德构建良好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争辩,即将道德与法律作为可供选择的手段与工具之际,在形而下层面所出现的如何配置和建构合理的行为规范体系,以及在形而上层面的治国方略与社会管理模式的争辩。争辩的产生、进行与拓展虽受制于诸多因素,但因文化传统而形成的社会心理所产生的反作用力,往往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种。因为对于个体而言,总是先天地置身于其祖先所创造出的文化价值体系与结构之中,由此而形成了具有同质性的“行为情结”①,凝聚成了具有影响整体行为选择倾向的社会心理,从而在“德法之辩”命题上,表现出是崇尚法律,还是迷恋于道德之治的不同选择。
社会心理,它是一种潜藏于人们内心深处、对社会成员行为习惯与思维方式带有共性支配力量的强大心理因素,往往通过以“行为情结”为内容的集体无意识形式表现出来。因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试图再现、无限趋近于自身的祖先之行为惯性与思维习惯,表现出行为上的顺从与认同,并由此影响我们在选择道德与法律作为国家与社会管理手段上的意愿,更为重要的是这往往是我们遵守法律、认可道德对自身行为具有的约束力一种心理动因。正是基于此,心理学研究认为,在确保遵从规则方面,其他因素如信任、公正、信实性和归属感等远较强制力为重要②。所以,以社会心理的视角来诠释“德法之辩”命题,需要客观地还原它所蕴含的内在规定性及其价值,探究支撑这一命题的社会心理要素的形成及其影响,以此来呈现法治社会合法性的心理结构,这不仅摒弃了价值优劣的主观臆断,而且可以忠实地呈现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的社会心理特征,以期在社会公众心理层面上实现传统与当下的沟通和对接。
二、从顺应自然到凝聚共识:“德法之辩”的社会心理形成
在“德法之辩”命题之下,是重法抑德,还是德主刑辅,无疑是人类的主观设计与期望,它来源于我们的先祖在面对客观生存环境时所形成的集体认知与整体行动。当然,这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则是他们追求善生活、良秩序的生活经历。对此,虽东西方路径不同,方式各异,但均是通过自身的生活经验及其生存智慧来呈现“从集体意识到集体无意识”的社会心理形成进程。事实证明,“文明是‘一种遭遇的结果’,是‘交互作用的产物’,它是在人类与自然环境的‘挑战’和‘应战’中诞生的”③。因此,如何“迎战”来自于特定自然环境的“挑战”就成为了东西方文明诞生之初面对的第一道命题,同时,这也是一个民族社会心理特质形成的重要历史关口。
1.西方“良法之治”社会心理的形成——以古希腊为例
在古希腊,其先民们所面对的自然环境营造出了一种理性认识自然运行规律的社会氛围,由此,也形成了一种典型的社会日常生活方式与环境——陌生人之间的商业贸易。客观上,对人性利己甚至贪婪的假设与防范便成为了国家与社会管控理论的逻辑基点。因而,对人性贪婪的合理控制就成为了他们创设社会生活正常运行机制的出发点,而该机制得以产生并正常运转,人性恶的主观假设则是不可或缺的逻辑起点,所以它不能依靠在“熟人社会”中发挥效用的“以情动人”自律性的伦理道德,而是多种利益冲突与妥协下所形成的、凝聚了多数人意志的法律。
所以,为了构造一个正常的生存环境与秩序,在维护社会或城邦秩序的手段上,古希腊人更青睐于法律,而非道德;更依赖于理性,而非人情。因为他们相信“法律具有确定性和稳定性等理性特征,可以避免社会治理中非理性因素的混入,能够防止人的感情用事和偏私”④。究其原因,这一选择无疑是基于生存实践而形成的一种集体认知与整体行动。为此,孜孜以求的践行这一认知理念,如城邦的民主共和制度——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与执政官选举等。
可见,在如何应对客观生存环境的历史进程中,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所建构的治国方略与社会管理的模式则是良法之治,其后,历经中世纪宗教近千年的熏陶与洗礼,从而在“德法之辩”命题上所形成的社会心理内容则是法律乃不可逾越的上帝之旨意。由此确立了西方社会在“德法之辩”命题上的基调与方向。
2.东方“德主刑辅”社会心理的形成——以中国为例
相对于古希腊人对法律之治的矢志不渝,古老的中国却钟情于伦理,迷恋于道德。这缘于孕育中华文明的自然条件与古希腊文明完全不同。在生存的自然环境上,适宜农耕的自然环境特征明显:相对隔绝的地理特征、辽阔多样的生存空间、温湿为主的气候条件。因此,生存环境基本决定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家庭式的小农经济。所以,只要一家老小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辛勤劳动,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基本可以保证一家老小的生存。这就在获取生活资料上形成了以一户一家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生存机制。此种生存方式由此塑造的个体角色并不是国家公民,而是家庭成员;人与人之间关系是宗法式的网络,社会结构则是家国同构的模式;构造的社会关系网也不是一个陌生人的场域,而是熟人的伦理世界。因而,在选择维护社会和国家秩序的手段与方式上,与古希腊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不遵循“家”的逻辑,那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会被斥之为“无父无君之禽兽”。由此,社会关系的内容与结构只可能在血缘关系中的得到诠释,在人性善的主观假设上得以确立,也只有在人伦情理中获得真正的内涵,而绝不会在人性之恶逻辑中得到解读。
那么,在此之下,阶级消纳于伦理,国家隐没于社会。道德固然不能消除社会矛盾,但得以凝聚成稳定的社会结构便完全取决于道德的力量⑤。为此,人伦之情理则成为了包含法律在内的所有行为规则理应彰显的精神实质,道德之恶等同于法律之罪则是自然的逻辑推演。所以,情、理、法融于一体治国方略与社会管理模式则是水到渠成的选择。所以,不难理解,中华文明为何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家天下的道德文明史,而不是犹如西方那般崇尚法律的理性主义文化传统。
至此,在生存逻辑的维度之下,“德法之辩”这一命题在东西方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内在规定性,一个是需要借助于法律来稳定主要由陌生人交往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与秩序,而另一个则是始终需要温情脉脉地道德来安抚处于小农经济模式中的家国同构的社会温情,所以,因为东西方在治国理政与社会管理模式上便形成了不同内容和价值取向的社会心理。“对于每一民族来说,它所处的地理环境都直接或间接地给予这个民族的文化以巨大的影响。由于地理环境的相对不变,它对于一个社会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恒定的……它并不直接地参与到人类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之中去,而只是给人类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真正舞台’和‘表演的场地’。”⑥但由此而搭建的“舞台与场地”却决定了即将上演的戏目的类型——尚德抑或重法,也决定了置身于舞台之上所有角色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惯性——从主观认同到客观行动。
三、从主观认同到客观行动:“德法之辩”的社会心理影响
囿于生存环境,主观上的整体性努力——集体意识(即集体认知)一旦形成,并经长期的生存实践便沉淀为一种同质性的社会心理——集体无意识,而“沉淀本身包含着内化(心理)和外化(历史)两个方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不过是外化了的心理,心理不过是内化了的历史”。⑦因此,一个民族早期的实践性生活经验与方式往往以一种巨大的历史惯性力量从心理层面上影响着她的子孙后代,并影响着他们“定纷止争”的行为规则以及社会与国家治理的模式。
1.在“德法之辩”形而上层面的影响——以国家立法创制信访与调解制度为例
内化是指社会意识向个体意识的转变,就是把别人的或者是社会的观念、行为、评价等事物融合进自己的心理或者行为中去。⑧所以,在诸多个人以及社会矛盾解决的思维逻辑上,我们习惯于在道德话语的逻辑延长线上进行,都试图将这些问题转换成道德问题。哪怕是同质性的社会心理——集体无意识的影响力所赖于栖身的社会客观环境因社会发展或转型而不复存在了,但它却仍以一种道德意义世界的景象停留在社会成员的意识结构之中。所以,我们始终对“包青天式人物”的出现充满期待,也始终对通过“上访及其调解”⑨的渠道来解决问题方式在心理上存在依赖,且并非只是一种局部的或单个个体的,而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心理诉求。
那么,如何满足并通过合理的渠道疏解这一社会心理诉求,则是每一个国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一般而言,国家的立法行为并非是在创造发明某种法律制度,恰恰相反则是在表达和疏导具有同质性社会心理的行为。所以,“立法者应该……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⑩。为此,我们设立了专门的国家机构——国家信访局,制定了专门的法规——《信访条例》,无不是为了回应和承载这一社会心理诉求。那么,究其实质,无疑不是用现代的法律来规范自古既有的“拦圣驾,告御状”的社会现象,只不过是载体形式发生了变化,而实质上内容并没有改变。除国家制定《信访条例》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颁布实施同样是国家通过立法的渠道来将长期留存与普通民众心中的厌讼、贱讼的心理进行了合理疏导和表达的又一举措。在“以和为贵”的社会心理支配下生活了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对通过调解方式进行定纷止争的模式一直关爱有加,因此,为调解制度的存在和完善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心理平台。
2012年10月9日,我国首次发布的《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所统计的数据表明,截至2011年底,中国有人民调解组织81.1万个,调解员433.6万名。调解纠纷893.5万件,调解成功率96.9%;全国法院调解民事案件266.5万件,调解撤诉案件174.6万件。可见,人民调解制度作为中国司法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挥的作用及其社会认同度更是不容置疑。所以,无论是信访,还是调解,如果我们就此进行溯源性追问,它们无疑是中国传统社会“情理法”价值观念的一个缩影与再现,因而,当下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来表达和疏解此种社会心理诉求,不仅让社会公众实现了内心认同上与传统的对接,而且增加了文化上的归属感。因此,信访与调解制度便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从而在当下的定纷止争模式之中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
可见,以集体无意识形式潜藏在社会成员内心之中的心理诉求,与其说它是一个民族生存经验的沉淀以及生活方式的坚守,还不如说它是一个民族子孙后代协调利益冲突,化解社会矛盾的话语规则。所以,在“德法之辩”形而上价值维度之下,仁政模式下的德主刑辅之于东方所具有的独特的心理期待与认同。因为以集体无意识方式所表现的社会心理内容,它在一个民族心灵上打下的烙印,往往以一种隐形的同质结构性的强制力默默而又深刻地影响着当下甚至是未来的经济、文化以及政治制度的架构,并由此将隐形力量转化为客观的制度构造。因此,在这一隐形的、惯性力量的作用之下,东西方历史上便构造出内容迥异的社会及其国家治理模式——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进而,各自在“德法之辩”形而上的价值维度上的差异性也同样以此为出发点,进行治国方略与社会管理模式的理论建构和论证。所以,在西方,从霍布斯、洛克到孟德斯鸠、汉密尔顿与麦迪逊等一大批思想家都以人性恶的社会共识来作为政治与法律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而东方的中国,处于文化核心地位的儒家,将人性之善逻辑之下的“内圣必外王”作为了政治制度的内在规律。最为重要的是,此种理论的假设与构造通过文化传承所形成的话语在社会中的反复激荡,不经意间激活并试图强化着沉淀在社会民众内心深处的此种行为情结与心理诉求,而此种话语所产生的社会环境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由此而将以集体无意识形式存在的社会心理所具有的隐形之力转换成显性的社会集体行动,这简直就是一个理所应当之必然性的结果:所以,为何我们仍然对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模式“德治”念念不忘,而西方却始终坚守法律的理性之治——一切皆归于法。因为“德治对于我们,不仅意味着曾经的治式(传统德治)与传统(德治传统),且意味着当下的治式选择(以德治国方略),传统德治、德治传统与德治的当下治式间确乎存在某种生命意义上的关联,而它们对于中国法治进境的意义也是独特的。……对于国人说来在某种意义上带点儿‘情结’的味道”。(11)
由此,在“德法之辩”形而上的维度之中,西方从尚法到良法之治,始终保持着对权力的高度警惕。因为他们坚信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12)而在东方,修齐治平的道德修养路径所成就的“内圣则外王”之道则成为了获取政治权力及其稳定运行的不二法门。
2.在“德法之辩”形而下层面的影响——以亲亲相隐和宽严相济制度为例
在“德法之辩”形而上的层面,因受社会心理的影响往往是呈现的是现代文明观念与文化传统价值之间的对接、冲突与整合,而在“德法之辩”形而下的维度之中,则是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来表征这一对接、冲突与整合的具体内容。
(1)现代“亲亲相隐”法律制度与传统文化的对接
众所周知,亲亲相为隐,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一个典型制度与原则。它之所以在传统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因为它演绎的是这样一个基本的情感逻辑:法律如始终关注人性中合理的成分,那么,它的生命力将亘古不衰。而大义灭亲,虽是我们长期以来所倡导的司法观念与政策,但经过实践的检验,我们发现它虽可以将违法犯罪行为逼上绝路,但却违背了人之常情,它剥离了家人之间与生俱来的自然情感联系。所以,大多数人并不认同。2010年10月14日,《南方周末》在《量刑的抉择:“大义灭亲”还是“亲亲相隐”》一文中刊载了一组对“大义灭亲”民意调查数据:认同的为31.80%;反对的为29.39%;矛盾的38.81%。可见,在该问题上,持反对意见与持矛盾的心态的,占到了受访者近70%的比例。那么,从国家立法层面上而言,是继续坚持大义灭亲,还是与传统的亲亲相隐价值观念来对接,来关注和表达社会的心理期待与认同呢?2012年,在《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便回应了这一社会心理诉求。该法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可见,在某些情况下近亲属可以拒绝作证,为此,通过修改法律摒弃了“大义灭亲”的观念,与中国“亲亲相隐”的传统法律制度相契合,实现了与文化传统观念的对接。如此,将既往焦虑的、矛盾的大义灭亲社会心理完全予以释放与合理化,从而极大地提升了法律制度的社会实效,扫除了法律实施的社会心理障碍。
(2)现代“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
在《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中,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司法机关惩罚犯罪,必须实行区别对待……宽严相济……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该《意见》第22条规定:“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因劳动纠纷、管理失当等原因引发、犯罪动机不属恶劣的犯罪,因被害方过错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性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但是,这条规定在“李昌奎案”的处理过程中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在该案中,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基于被告人所犯故意杀人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即强奸后用锄头敲打致死18岁的王家飞,并摔死王家飞年仅3岁的弟弟王家红),因此依法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昌奎死刑(立即执行),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却认为在该案中,不仅被告人有自首情节,并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3万元,且属于邻里纠纷引发,符合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一审量刑失重,故二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可民众并不买账,一片喊杀,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当时,甚至连李昌奎的大哥都以为,这种事,一定是活不了。不难发现,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与民众心理诉求之间出现了冲突。云南省高院欲借此案来改造冤冤相报的传统观念,突出国家对杀人偿命的文化记忆引导和整合,而民众却是杀人偿命、同态复仇的心理诉求,表达的是群体与生俱来的文化情感。所以,哪怕是依法作出的判决,如果与社会心理诉求相背离,不可避免地会遭遇某种集体的不理解,甚至是整体的抵制,因此,云南省高院撤销了二审判决,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结局收场。
可见,通过上述简要的分析,可以明确的是在“对接”与“冲突”之间,但凡顺应社会心理(如杀人偿命)与契合自身“行为情结(如合情合理)”的法律制度则必然会获得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同,反之,必将遭到社会公众的抵制。
所以,不难得知,已凝聚成集体无意识形式的行为情结与社会心理,对于我们的行为惯性所具有的整体性强制力并不只是简单地表现为一种隐藏在内心深处悄无声息的心理抵抗,而是将一个个原子式的个体凝聚并塑造成为一个具有同质型心理结构的类本质存在式的整体,并通过这一类本质形成相互之间的关系结构、内容以及处理问题思维上所形成的集体认知,从而在行为上表现出一致性,所以,我们也就习惯于将合情合理置于合法之前类考量各种制度规范与行为,这几乎成为了我们心理上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四、回归自身:“德法之辩”的价值导向与路径选择
一个国家的治国方略与社会管理模式,贵在有根,贵在合于现实。这就需要关切并合理的表达和疏导社会整体性的心理诉求。因为这一诉求,它以独特的视角透视着一个国家与民族治国方略与社会治理模式合法性的心理认同程度,呈现出一个国家法律制度体系运行功效的真实性与实效性。
中国法治社会的建设并不是一种社会自我演化、内生型的路径与模式,相反,它是一种“自上而下”政府推动式的、依靠近二十年的大规模的法律移植运动而渐趋所形成的共识,因此,以一种隐性力量存在的社会心理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通过“自下而上”的通道自然而然地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得到合理地表达,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被遮蔽了,所以,关注民意,回归社会,将社情民意合理地植入法治社会的价值体系之中,合理地疏导和表达社会心理的整体性诉求,以此彰显法治社会建设的主体规定性,这是“德法之辩”命题的现实价值之所在。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地做到让每个公民从内心深处真切地认同国家的治国方略与社会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或者借助于外在力量强加于每个人的行为之中,这也就决定了“德法之辩”命题的价值导向与路径选择——必须回归自身,最大程度的关注自身的文化传统,合理表达具有同质性的社会心理诉求。
注释:
①心理学研究认为,不是人支配着情结,而是情结支配着人。它表征的是个人无意识重要的特性,即一组一组的心理内容可以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簇心理丛,从而构成“情结”,它犹如一块磁石,将相同或类似的经验吸附在一起。“情结”来源于集体无意识,而集体无意识与种族的往昔生存经历相联结。参阅[美]C.S.霍尔:《荣格心理学入门》,冯川译,陈维政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5月,第35页。
②[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页。
③[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末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74页。
④卢建军:《法治理想与“法律神话”的悖论——兼论西方法治思想发展中对理性与非理性的不同态度》,《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⑤蒋传光:《中国古代社会控制模式的历史考察——一个法社会学的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⑥[德]黑格尔:《历史哲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第123-124页。
⑦冯川:《荣格“集体无意识”批判》,《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
⑧转引自王兆辉:《道德内化中的各状态分析——以道德知、情、意认同与否为视角》,吉首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⑨张梅姿、贺志明:《无讼的价值取向与调解制度的法律传统》,《湖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⑩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83页。
(11)孙莉:《德治及其传统之于中国法治进境》,《中国法学》2009年第1期,第69页。
(12)[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