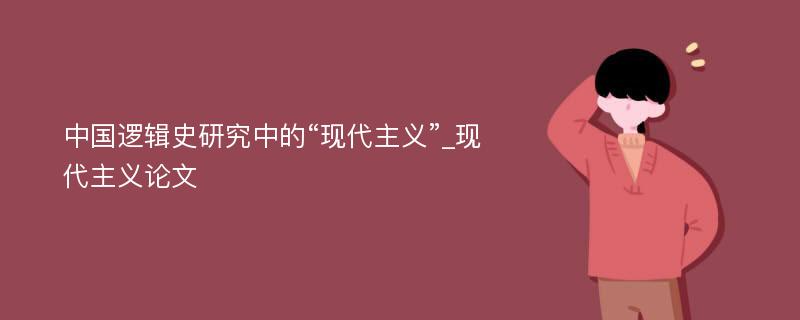
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现代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主义论文,中国论文,逻辑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古典诠释中的“现代主义”倾向,已经有过一些分析和批评。这个批评,原则上我同意。的确,“诠释受所属的思想体系的限制”,戴上现代的眼镜看古书,难免看走了样。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是如何减少甚至摆脱这个“现代眼镜”的影响,矫正那个“现代主义”带来的扭曲。当然,这是个大问题,也是老生常谈了。为了稍微具体一点,我准备举个古典研究的例子,就是“中国逻辑史”的研究,看看其中“以今释古”的情况。先说明,这方面我不是专家,下面要讲的也是泛泛而谈,够不上多么具体,但无论如何,我希望能够从一个侧面说明一下“现代主义”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克服“现代主义”的一些困难所在。
我的问题说明白一点就是,虽然诠释要落脚在那个思想体系上,但对这个“思想体系”的理解,有时也是诠释的结果,或受这个结果的影响。所以,抽象地说这里有个循环,似乎诠释要从诠释的结果开始。既要摆脱这个循环,又不能落脚在现代,那么,这个诠释的落脚点在哪里?某本古书,或某个说法,如果大家的理解基本一致,那么可以从这个一致的地方出发往前走。但是,如果难以找到这个基本的一致之处,那么该怎么办?对于先秦逻辑史的研究来说,这个困难似乎尤其严重。根本的原因是,跟其他的古典研究对比,这里有那么多年的空白,隔着两千年看那当时就聚讼纷纭的东西,材料不充分且不说,难解是肯定的。惠子“其书五车”,都丢了;《墨经》近一百来年才整理得勉强可读,虽然读起来还是像天书;至于《公孙龙子》的“诡辞妄言”,几乎可以充当见仁见智的最佳例子。如今的逻辑史研究,对这些典籍,可谓歧见纷呈,莫衷一是。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从现代的眼光回望古人,不以现代的理论揣测古意,那么这个研究似乎就难以找到下手的地方。
我们或许可以用两种基本态度对这个逻辑史的研究做一下划分,然后看看两大分支里都怎样或能够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既然说的是逻辑史,那么就自然假设了我们的古人是有逻辑的(这里的逻辑是逻辑学或逻辑理论的意思),所以,这里不须考虑中国无逻辑的态度。剩下的两种态度,一是我们有自己独特的逻辑,跟西方逻辑不一样;再一个就是逻辑是普遍的,不分中西,虽然中西传统对这个理论或其中的原则的表达方式可能不同。
先看第一种态度,它不是主流,但似乎总是有人坚持。取定这种态度,那么那种“现代主义”的路子,看来就必须排斥。你看,我们的古人有独特的逻辑,原则上不同于西方逻辑,因此当然不能用后者来硬套。这里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两方面的问题。打个比方,我们要捕捉的对象是水里的游鱼,不是天上的飞鸟,就对象方面而言,我们首先不能把鱼硬当成鸟。然后,就方法上讲,要捕鱼当然就要用网之类的东西,而弹子那类打鸟的器具,在这里不适用。反过来看现代主义,它既“指鱼为鸟”,又企图“一石二鱼”,因此必然无的放矢,套用公孙龙的话,这好比“飞者入池而棺椁异处”,是“天下之悖言乱辞也”。
这样一种态度,说实话,我不认为能坚持住这个反现代主义的立场。上面的论证,有一个假设:我们要研究的是一种独特的逻辑——那是鱼,不是鸟。我现在从这个假设问起:你如何知道那是一种独特的逻辑?你当然不能在看清那个研究对象之前就先天地知道,那是鱼,不是鸟(而且是一种我们以前没见过的鱼)。所以,你的回答大概是:这是我研究的结果——我捞出它了,看到它是鱼(起码不是鸟)。那么,我再问:你是如何捞出它的?你回答:用渔网。(可能你还要说,我也试过用弹子之类的工具,但得不到任何东西;用网一捞,它就出来了,这起码证明它不是你说的那个西方飞鸟吧?)最后,问题归结在你的这个网上,好吧,我们且来看看你这张网,看看它是怎么结的。
这个网,或者你的研究方法,我们即使不了解它的其他方面,也至少知道它应该是一种独特的工具,跟别人捕鸟的工具不一样。那么,它是怎么造的?难道里面没有“西方逻辑”的构件、原理等等?难以想象一种研究或阅读方法,摆脱了我们熟知的基本逻辑原理的限制,像同一律、矛盾律等等。不遵守同一律,把“白马非马”读成“白马非牛”,或者,不遵守矛盾律,把“白马非马”等同于“白马马也”,这样随便混淆牛马,颠倒是非,就真成了公孙龙所说的“天下之悖言乱辞”。同一律、矛盾律等逻辑原理,历史渊源上是“西方的”,但道理上是普遍的。即使换了它们的西方名字,那些原则本身就在那里,你只要思考,只要判断,就没法走一条跟它们不同的路子。比如,在你说“中国有不同于西方的逻辑”的时候,就已经假设了它们(你说的“不同”是什么意思?这意思不能是“相同”吧)。要试着不用它们来思想,那我们一步也走不动,因为即使要想象这样的“试”,我们在这个想象中也要符合它们,否则就成了胡思乱想。同样道理,其他的“西方逻辑”原理也不可避免,它们是思想之为思想的必要构件,你的研究方法若是违反它们,那你什么也得不到;你若是不按它们结网,那么就无网可言。
既然你的方法不得不包括别人的方法的逻辑,一点也不少,那么,要解释你为什么得到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似乎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不但用了别人的逻辑,还往里加了一些东西。因为,如果你跟别人用了一样的逻辑,那么你如何能够看出另一种逻辑?这就好像你戴的眼镜看一切都是蓝的,但你偏偏透过这个眼镜看到了红的东西。逻辑这东西有个特点,它是形式的,无所不包,是思想的最底层的东西,我们没法跳到它外面来看它。你用一种语言可以理解、研究另一种语言,但你能做到这点,是因为两种语言有一样的逻辑。你用一种观点去理解另一种观点,也是基于共同的逻辑。但是,无法想象你可以用一种逻辑去理解另一种逻辑,因为那个最基本的共同的东西没有了。或者这样说,就“理解”的意义来说,它是在逻辑中进行的,我理解A,首先是把A放到我的逻辑中来,但A若是另一种逻辑,我就放不进来,因而无法理解。所以说,你如果看到中国有另一种逻辑,那你的看的方法,就已经包含那另一种“逻辑”了。如前所说,你往那方法里加了东西。你加的东西,或许是“整体”、“有机”、“辩证”等等原则或“视角”,也可能是别的东西,总之是不同于“西方”形式逻辑的东西。但是,这样一来,你之所以能够得到“中国有不同于西方的逻辑”的结论,只是因为你用了那些“不同的”视角来看我们古人的书。所以,这个结果的“不同”,根源在你的方法上,在你的先入之见上,而不必在古书中。这种先入之见,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叫做“现代主义”,但它跟现代主义一样,都是拿自己的东西套古人的东西。特别是,大家所谈的现代主义的缺点,它似乎都具有。比如,用类似的先入之见,也可以把西方逻辑看成另一种“逻辑”——用黑格尔牌的网子一捞,西方典籍中捞出来的,就主要是黑格尔式的逻辑。至于主流的形式逻辑,顶多也只是一种“初等逻辑”。
结论似乎是,这第一种态度,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排斥现代主义,但骨子里还是某种现代主义或有着现代主义主要缺点的什么主义。因此在这里,减少或摆脱现代主义的负面影响的问题,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容易解决。当然可以设想,方法上的先入之见越少,现代主义的影响就越小。可是,一旦取消了这些先入之见,在我看来,这种态度也就从根本上取消了。
我们再看第二种态度,这是多数人的态度。它主张,逻辑是普遍的,只有一个,不分中西,无论今古。那个现代主义问题在这里,也似乎有个轻易的解决:既然逻辑只有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那个古代的,天然地就是我们现代的(虽然现代的理论比古代的更精致、更完备),那么,所谓现代主义的问题,用现代来硬套古代的问题,在这里就消失了,因为二者本来吻合,不须削足,就能适履。
但是,问题好像并没有消失得这样快。古书里毕竟有那么些东西,看起来不合“现代逻辑”的尺寸,如《公孙龙子》的“白马非马”,《墨经》的“杀盗非杀人”。对付它们。于是又有了两种方式:一是把它们(至少它们中难解的那些)当作“插科打诨”的“游戏之作”,不予考虑;再就是承认它们有严肃的理论价值,需要适当的解释。前者否定了那些表述的特别的理论意义,因此可以称为“否定说”,后者则可相应地称为“肯定说”。
否定说,夸张一点讲,好像导致这么一种结局:逻辑“一统江湖”,古代理论只是现代的一部分而已,因此,古书的那些说法,顺我者,收编到我的门下,逆我者,革出门墙。在这个结局下,可以说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基本上无事可做。你看,这里只剩下个“收编”的任务,而能收编到你门下的东西,又少得可怜。有些人把古人的那些论证符号化,纳入到今天的系统中来,以为这就是逻辑史研究。这个研究,好像只是在验证我们的古人也能符合逻辑地思维。可是这个结论,还用得着你花功夫研究吗?你这个研究的基本假设里有一条:逻辑是普遍的,因此是人都能符合逻辑地思维。这直接推出你那个结论。
否定说还导致一个相关的结论,就是我们古人的那点逻辑理论,除了有点历史的、收藏的价值之外,于逻辑研究、于人类“认识自己”的事业,几无贡献,乏善可陈。如果事实如此,我们也只好认了,虽然承认这一点是痛苦的。一位学贯中西的老先生,历史学家,我非常敬重他。有一次他说起,年轻的时候,他一直读中国古书。初次看到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时,他感到非常震惊——希腊人竟然有那么严格、精致的演绎系统,相比之下,我们的类比、比附什么的,简直是荧光之如日月。他说,若是我们只有这点简陋的逻辑,就不要讲我们的什么文明了,中华民族不存在算了,不存在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的话很激动,但对逻辑史家这是个大问题:我们古人留下的逻辑理论,是不是只有简单的类比、比附等不成套路的法子,或者再加上点貌似排中律、矛盾律等简单原理的表述?
大概多数人不认为如此,或不想如此认为,可要说出我们到底有什么值得夸耀的逻辑理论,就要对那些看起来不合逻辑或至少是扑朔迷离的文本有个独到的、合乎情理的解释。由于文本的晦涩,这种肯定说一开始就碰到了严重的现代主义问题。我们似乎不得不拿一些现代的或西方的理论来解这些谜。还是举“白马非马”的例子。冯友兰以“马”和“白马”为共相之名,认为“白马非马”说的是二共相不同一[Fung 1948,pp.87-91]。陈汉生(Chad Hansen)则主张,这里的“马”指众马组成的“曲全集”(mereological set),或由一些形状相似的、不连续的物体组成的“马之整体”,而“白”指一些不连续的颜色片断组成的整体[Hansen 1983]。葛瑞汉(A.C.Graham)也认为应该从部分和整体的理论来理解公孙龙[Graham 1986,pp.197-211]。这些“现代主义”解释,招来了相应的批评。比如,弗雷泽(Chris Fraser)指出,共相说太西方化了,先秦的文献中根本未见共相的影子[Fraser 2005]。拿这个标准来衡量,葛瑞汉、陈汉生等不但太西方,而且太现代。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评论道:“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当时的古人思考过列斯捏夫斯基(Stanislaw Lesniewski)的曲全论(mereology),或把苹果与黄昏的天空当作时空中不连续的同一对象。”[Harbsmeier 1998,p,312]
这些肯定说,不管是否符合公孙龙的原意,从逻辑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它们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以某种现有的形而上学假说为基础来解释公孙龙的名实理论,顶多把公孙龙“对号”到某种语言哲学里去,而没有说明《公孙龙子》以及相关的《墨经》在逻辑或论证方式上有什么贡献,因此也未回答上面提到的那位老先生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的古人用所谓的类比或举例得出结论时,这个论证到底有没有高于单纯类比或举例的力量?如果有,这个说服力的根据在哪里?当然,古书中的类比比比皆是,不能一概而论,但一些典型的或理想的“类比”范例,如公孙龙以“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来支持自己的“异白马于所谓马”,就不是一般而言的松散的类比。这个推论,可以叫做“同形类推”或“典型例证”,是具有同一个模式的一个实例到另一个实例的过渡。这具有演绎推理的力量。① 雷丁(Jean-Paul Reding)把中国古代的典型推论方法总结为这样一个过程(他仍然叫做“类比推论”),它始于一种“展示”(exposition),终于一种“应用”(application),其中的那个“展示”一般为一个故事或寓言,而那个“应用”则是把“展示”中的一些词项代换为另外一些词项而得到,这种代换必须保证前面的“展示”中的逻辑结构原封不动地转移到后面的“应用”那里。因此,这种“类比推论”,虽然是从实例到实例,但其实是演绎的一种方法。[Reding 2004]
当然,一种论辩方法或说服人的特别方式,还谈不上是逻辑本身,前者依赖于后者。雷丁所谓从“展示”到“应用”的过渡,首先还是要弄清那些实例中的逻辑结构,否则如何过渡?所以,虽然探讨古人特殊的论辩方式是有价值的努力,但既然是逻辑史研究,落脚点还是应该在那些论辩后面的“逻辑结构”上。我们既然主张逻辑只有一个,就不能指望这里的“逻辑结构”长的不是现代的样子,不能甩掉了现代而专找一种古代的“逻辑”。因此,中国逻辑史的研究,除开对传统的论辩方式的探讨,它对于逻辑本身,大概只能是依照现代的逻辑框架,做一些挑拣、连缀、阐发的工作,主要是揭示古人对于逻辑的特别应用,澄清他们对于一些一般逻辑原则的表述,分析他们思想背后的逻辑结构。比如,有些文章探讨《墨经》中变元的使用问题,含有类名的句式的逻辑结构问题,一些特别的推理形式问题(如侔式),以及其他文献中一些具体说法的逻辑依据(如邓析的“两可之说”),等等。这些工作,不知能不能回答那位老先生的问题,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算是在探讨中国人对逻辑理论本身的历史贡献。比起那些基于现代形而上学的解释,这些研究大概较少受现代主义的诟病,因为,如前所说,我们这里一开始就认准逻辑不分古今,不存在削足适履的问题。如果你认为,这种“不分古今”的假设已经是削足适履,那么我还是那个回答:你不可能脱开“现代的”逻辑,来想象一种古代的“逻辑”。理由前面已经说了。
但话也不能说满,即使在这些研究中,似乎现代主义的影子还是不能彻底扫除,因为,毕竟这些研究是拿现代的、甚至非常晚近的一些具体的逻辑理论(如弗协调逻辑、“任意对象”逻辑等)来解古代的谜。我不知道这里可不可以拿“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来“搪塞”,但好像可以说:这已经是我们能做到的最不现代主义的努力了。
最后总结一下。减少或摆脱现代主义影响的问题,就逻辑史研究来看是复杂的。我们区分了两种态度,以及这些态度之下的几种研究方式。结果,第一种态度看起来反现代,但其实最现代;第二种态度好像不受这个“现代主义”的困扰,但其中的研究,有的深陷于现代的形而上学,有的虽然不那么现代,可似乎不能说完全摆脱了“现代主义”——结论到底如何下,取决于我们如何严格定义这个“现代主义”。但无论如何,逻辑史的研究要依赖“现代的”逻辑——这个程度的“现代”,是不能少的。
注释:
① 顺便说一下,按照这种“同形类推”的模式,上面提到的对“白马非马”的几种形而上学解释,都不合公孙龙的论证方式。公孙龙以“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同于自己的“异白马于所谓马”,表明他的“白马”与“马”是在楚王故事里的“楚人”与“人”的意义上使用的。既然故事里提到“楚人得之”、“人得之”,那么,这里的“楚人”和“人”都有得到楚王所丢失的那张弓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二者显然不是类、共相、曲全集、部分一整体等等,因为这些东西都缺乏“得之”的能力。由此看来,公孙龙的“白马”与“马”也不是类、共相、曲全集、部分一整体等等。另外一个佐证是,《白马论》里有“求马”论证(“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这里所求的,当然也不会是类、共相、马之整体等。所以,公孙龙的“白马”与“马”另有所指(见拙文《白马论一解》,载于《科学文化评论》,2006年,第3卷,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