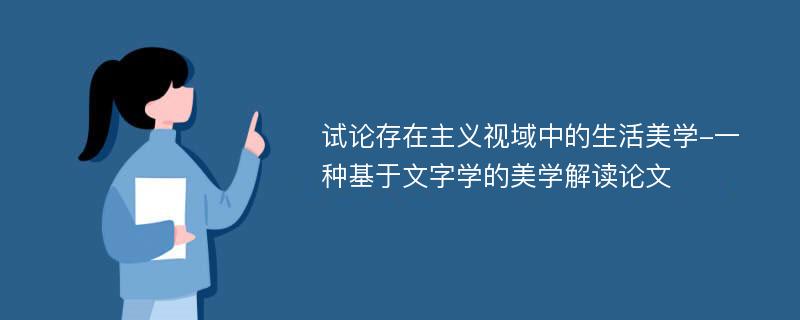
试论存在主义视域中的生活美学
——一种基于文字学的美学解读
袁方明
(四川大学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5)
摘 要: 文章从文字学的角度深入挖掘“在”“存”两字体现出的生活美学思想。充满生机的生命状态,对生命的仁爱精神,对生命的无限珍惜和长久追求,这三者都是一种美,都是生活本身的一种显现。同时结合存在主义,简要分析海德格尔美学思想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美学”的扬弃。
关键词: 存在论视域;生活美学;生命;仁爱;贵生乐活
在中外美学思想史上,美学观点层出不穷,前苏联哲学家、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生活与美学》一书提出的“生活美学”就是其中的一种。李泽厚先生认为“生活美学”“吻合重生命重人生的华夏美学传统……,构成现代新美学的起点。”[1]这种美学观是重视生命、重视人生和现实社会生活的人本主义思潮在美学领域中的反映,曾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风行一时。关于“生活美学”的界定,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本文主要采用薛富兴的说法,即“所谓‘生活美学’,是指美学应当以大众现实审美现象为自己的理论出发点,以造福大众的现实生活为最后目的。”[2]近期,笔者在“中国知网”输入“生活美学”,检索出783条相关论文条目;输入“存在主义美学”,检索出1384条相关论文条目,近期亦有相关论文发表,可见“生活美学”和“存在主义美学”仍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①
文字是人类的伟大发明,是文化文明的载体。汉代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把文字提高到了治国安邦的高度,认为“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3]317汉字是一种象形表意文字,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表意文字。与其他文字不同,汉字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如汉字学、甲骨文学、金文学、书法学等。“汉字是中华文化的基石——它既是中华文化流传和发展的载体,自身的结构中又保存着很多中华文化的信息。”[4]先民在造字之时就表现出了对世界的认识。文字的字源型和结构型分析无疑是解读文化文明的一种方式。属于哲学学科范畴的美学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文字的诞生和演变过程体现出人们对包括美在内的世界的独特体认。本文结合存在主义,从文字学的角度分析“在”“存”两字体现出的生活美学思想,并与车氏的“生活美学”进行简要比较,同时简要分析海德格尔美学思想对车氏“生活美学”的扬弃,以期尝试为美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解读视域。
一、“在”——充满生机的生命状态
作为象形表意文字,汉字“在”的原始意义体现了中国古人对生命生活的认识和礼赞。许慎《说文解字》对“在”字的解释是:“在,存也,从土,才声。”[3]289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在”字进一步解释为:“存,恤问也。《释诂》:徂、在,存也。在,存,察也。按《虞夏书》,‘在’训察,谓‘在’与‘伺’音同,即存问之义也。‘在’之义,古训为存问。”[5]687从字源看,“在”的本义指存在,是对世界事物在世规定性的界定,引申为存问,恤问,体恤。从构字法看,“在”是形声字,“土”表形,“才”表音,“在”的字义由“土”所规定。对于“土”,《说文解字》释为:“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丨’,)物出形也。凡土之属皆从土。”[3]287《说文解字注》释为:“吐、土,叠韵。《释名》曰:‘土,吐也,吐万物也。’......‘地之上’,谓平土面者也。”[5]682综合许慎和段玉裁对“在”“土”的解释,可见“地之吐生物者”即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生命。新生命体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生机活力。内在的携带着生命基因和富有生命活力的种子顽强地冲破土地的重重阻挠,体现出一种顽强不屈的生命活力。
综合型实验 此类实验需学生在掌握相关专业基础实验操作能力的基础上,使用多种实验技术来完成最终实验[9]。正是因为需要用到多种实验技术,综合型实验对于仪器的开放性及实验室的开放性要求更高。与基础验证型实验相比,综合型实验更能锻炼学生的协调能力,在专业实验课中应当占有一定比例。
美感是在人与事物的关联中产生的,是在作为客观的外在事物(被审美者)与具有主观性的人(审美者)的内在情感的相互关联交际(即审美活动)中产生出来的。美感产生于人的心灵情感之中,产生于意象意境之中。②“一切美的光是来自心灵的源泉:没有心灵的映射,是无所谓美的。”[6]包括人和自然在内的天地万物是富有生机活力的。“大自然(包括人类)是一个生命世界,天地万物都包含有活泼泼的生命、生意,这种生命、生意是最值得观赏的,人们在这种观赏中,体验到人与万物一体的境界,从而得到极大的精神愉悦。”[7]“在”字体现出的这种充满生机活力的生命状态是美的体现,原初生命冲破重重阻挠而体现出来的顽强不屈精神也是美的体现。人类面对“最值得观赏的”“活泼泼的生命、生意”,“体验到人与万物一体的境界”,由此“得到极大的精神愉悦”,进入到审美的状态,产生美的享受。“构成自然界的美的是使我们想起人来(或者预示人格)的东西,自然界的美的事物,只有作为人的一种暗示才有美的意义。”[8]244美在这里之所以体现在“暗示”之中,是因为人和万物生命具有源始本真意义上的生命相似性(或者说生命同构),即充满生机和顽强不屈,这是一种“人与万物一体的境界”。无论是人类还是动植物,都是由最初的小生命逐渐成长成熟。“生命与存在是人生天地之间的最‘好’(即最美)的事物,也是人生最喜‘好’的(即能够从中感到最大美感享受的)事物”。[9]在动植物和人类身上共同体现出的这种生机和活力,表明这个世界处于积极的生命状态之中,处于美的世界之中,也让人感受到审美的愉悦。这种存在样式构成了美的世界中的一环。车氏在此基础上将这种审美活动引申至日常生活,提出了“生活美学”。
在手表式血压计的基础上提供一种通过手机摄像头以及闪光灯测量心率的方式。该模块使用基于小波变换的带通滤波器及快速傅里叶变换(FFT)技术,通过手机自带摄像头以及闪光灯实现,在食指指腹轻贴摄像头时,通过捕捉毛细血管的搏动,对血液流变以及毛细血管蠕动的影像分析,获得其心率值(如图5所示)。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存在者的存在本身不‘是’一种存在者”[10]8,“存在总是某种存在者的存在。存在者全体可以按照其种种不同的存在畿域分解为界定为一些特定的事质领域。这些事质领域,诸如历史、自然、空间、生命、此在、语言之类,又可以相应地专题化为某些科学探索的对象”[10]11。众所周知,海德格尔提出了著名的“存在论区别”(Der Ontologische Unterschied),在这里他明显区别了“存在者”和“存在”(存在本身)。他认为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史就是遗忘“存在”本身而只注重研究“存在者”——各种具象或抽象事物的历史。在存在论视域中,在人和其他生物身上体现出来的生命力是作为存在者的存在本身,而不是存在者,换言之,具体的一粒种子是存在者,种子所具有的先天的内在的生命力是存在本身。这种生命力是种子本身亦即生命本身所先天具有的,是由作为一粒种子的存在本身所给出的,且不强加于任何外在的力量。
按照存在主义的观点,车氏“生活美学”中的“生活”只是日常的每个人生活于其中的形下的生活世界,而不是“生活”这种存在本身,换言之,他所理解的生活是各种“存在者”,而不是生活的“存在本身”。以现在的眼光来反思,车氏的“生活美学”是在存在主义问世之前在美学视角里对“生活”的最高的历史的理解,是其生活时代对“生活”的应然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德格尔的巨著《存在与时间》的问世在美学上意味着对车氏的《生活与美学》的扬弃和终结,为我们探讨美提供了新的视域和空间。
二、“存”——对生命的仁爱精神
第五,巡演类演艺。巡演类演艺指的是在整个景区内进行巡游演出,这种演艺节目大多都出现在大型游乐场等需要和游客实时互动的旅游场合,这类演艺能调节游客在景区的心情,能营造更加强烈的氛围。
儒家强调“仁”和“不忍人之心”。[12]237“仁,亲也。从人,从二。臣铉等曰:‘仁者兼爱,故从二。’”[3]159“仁”是会意字,由“人”和“二”两个意符构成,表示两个人,引申为对众人的仁爱兼爱。这种“仁爱”精神是儒家仁者之心的体现。黄玉顺先生认为:“在儒家看来,生活本身首先显现为仁爱情感本身。”[13]27他同时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一切的一切的本源。生活本身既是形而上学的本源,更是形而下学的本源。”[14]生活本身是形上形下的大本大源,也是儒家仁爱仁政学说的源头活水,具体显现为各种人、生命及其活动,换言之,“仁”是生活的本体,“仁爱情感本身”即“仁”,亦即对众生的仁爱。对众生的仁爱表征的不仅是一种情感伦理学的态度,也是对人类和众生的一种关切关爱,亦是一种美学的态度,即视众生为美丽,视生活为美好。“就本原意义而言,美的活动就是‘本真生活’的一种原发状态。”[15]在此,“本真生活”亦即“生活本身”,审美活动也由“本真生活”生发出来。质言之,“仁”即“美”,“仁”亦是美的一种体现,“仁爱”是对世间芸芸众生的仁切关爱,仁爱活动是一种无功利性、超越性的审美活动,人在仁爱的审美活动中感受到一种审美的愉悦。③
“存,恤问也。从子,才声。”[3]311“恤,忧也,收也。从心,血声。”[3]219“子,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人以为偁,象形。凡子之属皆从子。李阳冰曰:‘子在襁褓中足併也。’”[3]311“存”是形声字,“子”表意,“才”表声,“子”是象形字,是对新生儿形体的描摹,“存”字意为“恤问”,即对新生命的呵护,扩言之,“存”字是对人类乃至所有生物体的体恤和关心,也可以说是对人生—生命的关切和喜爱。在儒家的视域中,这是一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1]的悲天悯人的仁者情怀,也是一种天地大爱。
儒家的“仁”具有先验性和本源性,是先天所具有的人性的本源状态,如孟子所言:
对于道家来说,整个道教史可以说是对长生长寿的不懈追求史,无论外丹还是内丹,无论性修还是命修,无论即身成仙还是尸解成仙,其实质都是追求长生久视,成就完美的人生人格。道教经典《太平经》认为,“三万六千天地之间,寿最为善”[17]222,“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17]80;唐朝道教上清派第十二代宗师司马承祯也认为“夫人之所贵者生,生之所贵者道”[18]。这些都是典型的贵生乐活思想,以追求长生不死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摒除这种思想的宗教色彩,我们认为同样可以从一般人生认识上认同这种对长生的追求。
这是海德格尔的死亡观和时间观。死亡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避免”性,是人的“终结”,是人的终极归宿。在时间方面,“过去”和“未来”实质上是一回事,都是一种“现在”。人的一生由无数的“现在”所组成。“一切都已经在最好的安排之中,人所能做的,仅只剩下一条:抓住现成的。”[19]72就此而言,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抓住组成生命整体的无数的“眼下”“当下”,即“现在”,作为存在者去努力“生存”。基于“死亡不可避免地到来”和死亡的不确定性,海德格尔对“当下”的看重是包括对“现在”“时间”的珍惜在内的。就其实质而言,欲求生命的长生长寿就是渴盼拥有更多的“当下”,这其实也就是道教贵生乐活思想:一方面是尽力延长生命的长度,另一方面是努力提高生命的质量,增加生命的厚度。通过对“在”“存”二字的分析所得出的“对生命的无限珍惜和长久追求”(贵生乐活)的结论,与海德格尔的观点有相似之处。
对于人而言,“仁爱”体现在人的先验本性之中。对人的领会也就是对具体这个人、那个人的规定性——人皆有之的“仁之四端”的领会。可以说“仁爱”本身就是一种存在,也是具体的存在者——人处于存在论境遇中的一种本质规定性。“存在的至高性并不是因为,一种特殊性或者一种特别的属性使得存在不同于所有的存在者。相反,存在中的差异源于它对于任何存在者差异的无所差异(in-difference),此即,源于它的绝对普遍性。”[16]人作为一种存在者,不同个体具有“存在中的差异”,但就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而言,人之“四端”即“任何存在者差异的无所差异”,也就是人的先天本性,亦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按照存在主义的观点,存在与存在者、美与美的事物或美的呈现,两者存在着对应关系:存在对应美本身,存在者对应美的事物(即美的呈现)。
通过“存”字的分析,可以看出儒家对生命的仁爱精神和“仁-美”主张,亦可看出儒家仁学思想对“生活美学”的影响。海德格尔对存在与存在者、美与美的事物(或呈现)的判分属于存在主义式的“存在论分析”,超出了“生活美学”的实践美学⑤范畴,属于后实践美学的范畴。
三、“在”“存”——对生命的无限珍惜和长久追求
由以上分析,可见“在”字体现了充满生机的生命状态,“存”字体现了对生命富于仁爱的精神。在生机、生命力勃发的世界中,生命是可贵的,人生和生活是美好的。对车氏和儒家来说,对生命的仁爱和关怀体现了人的价值取向。“对于人,最亲切最可爱的莫过于人和人的生活。”[8]243既然生命和人生如此美好,所以人们对肉体的长存长生寄予了深切的期盼和美好的向往,期望长生久视。这一方面是为了肉体的长生,是有限生命个体对无限时空的渴盼和超越;另一方面是为了能更好地对生命万物予以更多的关爱,毕竟,肉体的长生是施予关爱的前提和基础。这也是儒家和道家所共同关注关心的。
对于儒家来说,孔子面对着滔滔江水,感叹道:“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12]113生命、时间的流逝就像江河水一样,不分昼夜地向前奔涌而去,永不停息,一去不复返。面对滚滚的江水,不禁会发出人生如白驹过隙和人生如梦的感慨,进而期盼生命长久,珍惜现世生活。此外,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12]90这里,除了可以从仁学的角度进行解释外,笔者认为还有从语言背后透露出的对长生的渴望。“寿”而“仁”,“寿”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施“仁”;“仁”而“寿”,“仁”可以让人更加长寿,“仁”“寿”统一于人生实践中,统一于仁爱的美学实践中。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12]237-238
注释:
“死作为此在的终结乃是此在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确知的、而作为其本身则不确定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死,作为此在的终结存在,存在在这一存在者向其终结的存在之中。”[10]297
秀容月明成亲那天,天蓝蓝的,门前的桃花开得正艳。娶亲的队伍吹吹打打,从东大街到西大街,又从西大街回到东大街。
在儒家看来,人之“四端”是人人生而有之的,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体现,也是人性的彰显,也可以说是人这种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依据。就此而言,对于儒家来说,存在本身就是生活本身。④[13]27生活本身赋予了人这种存在者的境域和意义,其境域表现在生活于其中的具体时空,其意义表现人之为人的先天之性——“仁”性,对人的关怀,对生命的仁爱精神。这与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者”相似。正如海氏所言,“存在总是某种存在者的存在。”[10]11“存在”不等于且先于“存在者”。“从存在者层次上来看,其(笔者按:指此在)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这个存在者在它的存在中与这个存在本身发生交涉。”[10]14“对存在的领会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的规定。”[10]14
本文从文字学的角度对“在”“存”二字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在”字体现出充满生机的生命状态,“存”字体现出对生命富于仁爱精神,二者共同体现出对生命的无限珍惜和对生命长久的不懈追求。同时结合存在主义,认为在存在论的视域中,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美学思想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美学”有相似处和差异处,前者是对后者的扬弃:就“存在”(美)和“存在者”(美的呈现或美的事物)的区别而言,是“弃”;就“对生命的无限珍惜和长久追求”而言,是“扬”,两者都高扬对生命的珍惜和礼赞。通过对“存”“在”二字的文字学分析解读,或可在与存在主义的对照中重新认识车氏的“生活美学”。这对更透彻地认识现世人生和追求人生的诗意栖居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再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进行分析。海德格尔认为时间是存在的境域,“源始地从现象上看,时间性是在此在的本真整体存在那里、在先行着的决心那里被经验到的。如果时间性是在这里源始地昭示出来,那么可以推测先行的决心的时间性是时间性本身的一种特具一格的样式。时间性可以在种种不同的可能性中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到[其]时[机]。”[10]346-347“到时”意味着出场和现身,也是一种当下的存在生活状态。作为“亲在”(发问存在问题的人这样的存在者)也终究是有限的生命体,受到具体时空的限制,而死亡之大限是其归宿,是其不可逃脱的终极宿命。
死亡不可避免地到来,迫使我们对时间的本性进行新的思考。死亡的脚步踏碎了任何可依赖现成东西的梦幻,向人展现出一片虚无的场景。“未来”是不可“期待”的,走向未来就是走向死亡(vorlaufen zum Tode);现成的“现在”也是不存在的虚构,一切都是转瞬即逝的“眼下”(Augenblick);而“过去”,则是我们早已就在其中,生于斯、乐于斯的所在。它不是什么“已然定型的东西”,而是孕育万有的胚胎和土壤,因此,对它来说,不可能有什么“遗忘”,而只有“回复”(Wiederholung)。从这个意义上说,走向未来就又是走向过去,未来的死亡之光使我们免却遗忘,唤醒“回忆”,照亮已渐隐入黑暗的过去。[19]73
①关于生活美学,以薛富兴于2003年在《文艺研究》发表的论文《生活美学——一种立足于大众文化立场的现实主义思考》、仪平策于2003年在《文史哲》发表的论文《生活美学——21世纪的新美学形态》和刘悦笛先生于2005年在《哲学研究》发表的论文《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日常生活化——试论“生活美学”何以可能》为代表,这些论文引发了研究“生活美学”的热潮。关于“存在主义美学”,2007年伏爱华在其博士论文《萨特存在主义美学思想研究》进行了系统性的专题研究,董学文、陈诚于2009年在《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论文《“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
②关于艺术境界及意象意境,朱光潜、宗白华和叶朗分别进行了论述。比如宗白华先生在《艺境》中认为:“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艺术境界主于美。”(见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51页)叶朗先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美在意象”之说(见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4-58页)。自从柏拉图提出“美是难的”著名论断之后,关于“美是什么”(美本身),古今中外不同学者众说纷纭且至今没有达成共识,但关于“什么东西是美的”,进而关于“美在哪里”亦即具体的美(或美感的生成路径),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美在意象”观。笔者对“美在意象”之说深以为然。美感不是自体凭空产生的,美感是通过“心灵的映射”,产生于作为审美者的人与被审美者的事物的关联交际(即审美活动)之中,存在于主客(物我)交融后的情景相融的“意象”“意境”之中。
目前,大部门电力企业都依据国家电网的相关规定,设置了企业风险管理机构,并根据不同的部门划分了不同的职权范围。但从已有的执行情况来看,相关风险管理部门并未将全面风险管理作为常态工作纳入日常,相关工作人员甚至对如何有效进行风险规避也一知半解,如此环境下电力企业的风险管理机构形同虚设。同时,从现有的工作情况来看,风险管理机构的管理重点在于公司的大规模投资项目以及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项目等,往来款项的管理并未在重点管理范围之内,造成往来款项管理的疏漏。
③一般而言,审美活动具有无功利性(超功利性)、直觉性、创造性、超越性和愉悦性。“审美愉悦是由于超越自我、回到万物一体的人生家园而在心灵深处产生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是人在物我交融的境域中和整个宇宙的共鸣、颤动。”(见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将我院于2016年1月至2017年2月接诊的66例老年痴呆出院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对照组,每组33例。观察组男19例,女14例;年龄68~83岁,平均年龄(75.46±3.23)岁;病程1~11年,;对照组男18例,女15例;年龄70~81岁,平均年龄(75.21±3.43)岁;病程2~9年。比较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以及病程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④黄玉顺先生在《复归生活重建儒学——儒学与现象学比较研究纲领》一文中认为:“在儒家思想中,区别于‘生存’的那个所谓‘存在本身’,不过是子虚乌有、没有意义的东西。”(见《复归生活重建儒学——儒学与现象学比较研究纲领》,《人文杂志》,2005年第6期,第30页)笔者尊重并总体认同黄先生提出的“生活儒学”观,但不认同上述观点。儒家虽然也说“天道”,但总体看重的是形下的生活。任何自成体系的思想理论都是源于现实生活和形下世界并总是奠基于一种形上观念之上。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视域里,“存在者”与“存在”(存在本身)俨然不同,如果以传统形而上学即理念世界与物质世界二元判分观念作为类比,可以说“存在者”奠基于“存在”之上,“存在者”是“存在”的显现。虽然按照黄先生的说法,形下生活是大本大源,但生活本身不是凭空虚构。在笔者看来,生活之所以呈现出如此样态,必然有其内在的基础,如天体之所以如此运行,必然有显现为如此运行的背后的规律(如开普勒定律,即“行星运动定律”。当然,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视域里,严格来说,“规律”本身也是一种“存在者”。此处言说“规律”,是不得已而用之)。而这“基础”并非是“子虚乌有、没有意义的东西”。限于篇幅,兹不展开论述。
⑤关于“实践存在论”美学本体观,可参阅董学文、陈诚的论文《“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上海大学学报》,2009年5月。
因此可以看出,本区铀矿化产于主要受控于与断裂构造,区域性三级断裂与其次级断裂或破碎带发育部位,即为矿床的有利构造部位。
参考文献:
[1]李泽厚.美学三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384.
[2]薛富兴.生活美学:一种立足于大众文化立场的现实主义思考[J].文艺研究,2003(3):25.
[3]许慎,徐铉.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4]王宁.汉字与中华文化十讲[M].上海:三联书店,2018:90.
[5]许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6]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151.
[7]叶朗.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98.
[8]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9]潘显一.大美不言:道教美学思想范畴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26.
[10]马丁·海德格尔,陈嘉映,王庆节等.存在与时间[M].上海:三联书店,2006.
[11]张载,章锡琛.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62.
[1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黄玉顺.复归生活 重建儒学:儒学与现象学比较研究纲领[J].人文杂志,2005(6).
[14]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185.
[15]刘悦笛.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日常生活化:试论“生活美学”何以可能[J].哲学研究,2005(1):111.
[16]马克·弗罗芒·默里斯,冯尚,李峻.海德格尔诗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219.
[17]王明.太平经合校[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8]司马承祯.坐忘论[M]//道藏:第22册[Z].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892.
[19]王庆节.解释学、海德格尔与儒道今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Aesthetics of Life from an Existentialism Perspective——Aesthetic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Philology
YUAN Fɑnɡminɡ
(Institute of Taoism and Religious Culture,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Sichuan 610065,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based on philology,explores in depth the aesthetic ideology of life embodied in"Zai(在)"and"Cun(存)".Vital life,kindheartedness to life and infinitely cherishing and everlastingly pursuing life are a kind of beauty and representations of life in itself.Besides,from the viewpoint of existentialism,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how Heidegger sublates Chernyshevsky's aesthetics of life in his aesthetic ideology.
Keywords: Existentialist Angle;Aesthetics of Life;Life;Kindheartedness;Cherish Life and Live Happily
中图分类号: I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66(2019)06-0124-06
DOI: 10.16069/j.cnki.51-1610/g4.2019.06.018
收稿日期: 2018-11-07
作者简介: 袁方明(1980—),男,四川内江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宗教学专业2016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道教影视和易学。
[责任编辑、校对: 王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