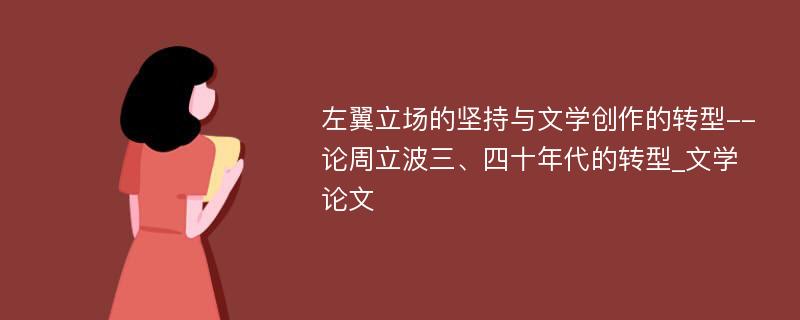
左翼立场的坚守与文学创作的转换——论周立波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文学创作论文,立场论文,世纪论文,周立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014(2013)06-0095-06
追溯周立波的成长史,不难发现:从亭子间到左联,至延安和解放区,最后到新中国,他的转换都是自觉的。在亭子间,左联之雄风似乎风去人走,他却加入左联并成为革命者;在延安,当许多作家遭遇批评时,即使他写出了《麻雀》等与延安气氛不一的小说,他也没有像丁玲一样受到类似的严厉的批评;在鲁艺,讲授外国文学,同样没有人因他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文学而对他产生异议。本处于安静之中,他却以《后悔与前瞻》、《思想、生活和形式》等文章来自我剖析与批评,自我确立为改造对象,并引起人们关注。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为了和大众保持一致,他毫不犹豫地以记者身份随王震部队南征北战,并在东北为剿匪和土地革命鼓与呼,进而写下带给他极大声誉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由此可见,他身上已经固有的左翼文学理想和已经付诸于行动并确立的革命姿态,都足以证明他的文学立场与时代立场的一致性。总体来说,他的转换在集体的转换中完成,在集体的排队中,在加入合唱与交融中实现独立。总之,他的每一次转换都可以视为一次历史性事件,其中的根由就是他从一名亭子间作家转换成左翼作家不仅代表他自身这一个体,转换中有随行的大众,只是他的转向总是独树一帜。
一 从自由主义文人转换成革命的鼓动者
(一)亭子间的艰辛成为其转换的契机
1928年为躲避家乡的恶势力,新婚未足一个月的周立波随远房叔叔周扬来到上海,住进了闸北区北四川路恩德里的一个亭子间,从此开始了另外一种生活,这种生活是他一生的跨越。西方文艺素养在此期间养成,加入左联也在此期间,创作也在此起步。最为重要的是,在亭子间里,一个作家成了革命者,一个自由文学者变成了革命作家,恒固的革命意识影响了他的后半生。同时,周扬也成为其后来命运重要的影响因素。而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焰在中国大地燃烧时,周立波的创作也受到极大影响,以后的作品《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小说的革命姿态如影相随。即便有着后面的变化,与其他亭子间作家一样,周立波对亭子间刻骨铭心。
关于亭子间,周立波在《亭子间里》后记中这样说:“上海的弄堂房子采取的是一律的格局,幢幢房子都一样,从前门进去,越过小天井,是一间厅堂,厅堂的两边或一边是厢房;从后门进去,就直接到了灶披间;厅堂和厢房的楼上是前楼和后楼,或总称统楼;灶披间的楼上就是亭子间;如果有三楼,三楼的格式一如二楼。亭子间开间很小,租金不高,是革命者、小职工和穷文人惯于居住的地方。”[1]多年后,周立波还那么具体地描述亭子间,可见亭子间在他心中留下印象之深。
在描述中,我们可见,亭子间作家的生活相当清苦,基本属于上海社会底层或准底层。而在今天上海残存的“保护”建筑和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到亭子间作家和房主人条件的巨大反差。一间仅仅能放置一张单人床和一张书桌,面积仅六七平方米左右,而且既不透风又不见阳光的屋子,近乎蜗居。许多人常常因为贫穷和住宿条件恶劣染上肺病而亡。姚克明对此也进行过考察,他记述道:“亭子间,可以说是石库门房子里最差的房间。它位于灶披间之上、晒台之下的空间,高度2米左右,面积六七平方米,朝向北面,大多用作堆放杂物,或者居住佣人。”[2]在如此条件下,从1928年春天到1937年秋天,除开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关的2年半以及回家的3个月,伴随着一帮穷兄弟,如叶紫、戴平万、何家槐、林淡秋、梅益等,周立波在亭子间里写作、生活近7年。同样待过亭子间的还有胡也频、丁玲、欧阳山、草明、张天翼、蒋牧良、朱凡、杨伯凯、韩起、沙汀、艾芜、任白戈、何家槐、吴奚如、叶紫、陈企霞、彭家煌、黑婴、白兮(钟望阳)、徐懋庸、舒群、罗烽、白朗、关露、王实味等,其中大部分后来去了延安或其他解放区,成为周立波后来的同行者。
亭子间是周立波他们在上海谋求生存的据点,除此之外,他们没有任何求居的地方。他们与公务员、职工、教师、卖艺者、小生意人、戏子、弹性女郎、半开门的、跑单帮的、搞地下工作的,乃至各种洋场上的失风败阵的狼狈男女,以及那些做了坏事而在此回避的人们,不得不混在一起。当然,生活在亭子间,不只穷困,也不只身份的卑微,还在于讹诈、抢劫、传染病等笼罩着那里的人们。在这里生存,需要毅力与勇气,因为明天谁也无法预料。在此,所谓知识分子的面子和地位都得抛掷一边。
当然,穷困可能滋生很多东西。正是因为穷困,亭子间作家们面对着生存的困境与地位的卑微,面对社会的动荡不安与国家的危难,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反叛和抗争意识。他们见证了上海乃至中国1927-1937年间变化。“九·一八”事变、“一·二九”运动、鲁迅逝世、“七·七卢沟桥事变”等等无不震动他们的神经。在骚动不安中,他们加入了左联,而周立波却在加入左联中走了一条不平坦的路。
由于穷困,周立波用一张中学假毕业证考入了上海劳动大学,但好景不长,由于参加飞行集会,他被学校开除。1932年,因参加印刷工人举行的大罢工,贴传单时被抓进了监牢,在苏州监狱一待两年半。其实,在他进监狱前,左联已经成立,他也曾在周扬的指导下加入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没有直接加入中国左联,但对他的影响很大。对此,周扬在答胡光凡问时说:“一九三○年夏,通过赵铭彝介绍,他和我一起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我们跟赵铭彝是在亭子间认识的。”[3]
在亭子间里,周立波在求生无门的情况下,开始自学外语和写作,并于1929年发表了第一篇散文《买菜》,1929年发表第一篇翻译《北极光》,在生活的艰难中开始文学之路。在此期间,周立波不仅广泛涉猎了西方许多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并对其中所喜爱的作品、文学评论进行翻译、介绍,还结合自己所积累的文学经验和些许文学理论,对日本、波兰、西班牙等国外的文学现状、文学思潮进行评析和综述,这很有益于他西方理论修养的培养。
可以说,周立波的大部分翻译、文艺理论批评来自亭子间时期。在低微寂寥的生活中,周立波学会了忍耐,也得到了充分的积累。和他一样,丁玲、胡风、叶紫、彭家煌、萧军、萧红、欧阳山、徐懋庸等在此完成了积累,并在此成名。这一大批人也就称为“亭子间作家”,并成为延安以及解放区的艺术工作者的三大来源之一。
所以,毛泽东多次把延安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分为“亭子间的人”和“山顶上的人”。1938年4月10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上说“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可见,赵树理们是山顶上的人,周立波、周扬、萧军、欧阳山、草明等一大批作家都来自于上海的亭子间,自然是“亭子间的人”。这一方面扩大了“亭子间作家”的影响,另一方面说明这些作家不是根红苗正之辈,也就和国统区的许多作家一道成为后来的改造对象,自然就影响了亭子间作家的人生之路。而后一种思维对周立波的影响,延续到“文革”得以“爆发”,使其不能幸免于被红卫兵推上走资派的“斗争席”。
正是亭子间生活的艰辛,稳固了周立波挣扎的信念,也成为他义无反顾参与革命的由头。清冷的生活、冷清的文字阅读也同样让他心在偏移。在亭子间初期,他还是一个为生活奔波的激进青年,谈不上革命。但这种生活就是他革命的源头,在观望中,他的心在倾斜。激进姿态在初期愈演愈烈,最后变成进入左联的必然条件。
(二)加入左联,在调整身份与争取角色中转型
值得说明的是,周立波出狱后再次来到上海,仍然居住在亭子间。实际上,后来加入左联并没有使他的经济生活得到改变,“亭子间文人”的头衔依然箍在他的头上。同样的,与他同为左联成员的许多盟友,也依然居住在亭子间。但是,他们的政治生活自此起步,由孤立或三五成群变成了集体的一员,群体意思被强化,并以此扩大了视界。左联的成立,给亭子间作家带来的新契机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并不是说,当时,如果不加入左联就没有出路。沈从文、梁实秋、周作人等都与左联无缘,也因左联的过度激进而不屑于加入左联,却同样在创作上影响巨大,甚至超越左翼作家。周立波从小就在益阳、长沙等政治激进的环境下生活,即使来上海的时间比他人晚,却正好赶上了革命文学兴盛的年代,同时,亭子间几年的蛰伏,只有革命才是他的出路。他必然以一种更直接的姿态加入左联,乃至革命。
虽然左联自动解散,但周立波却对其赋予了极大的热情。自1934年加入左联后,周立波参加了诸多左联活动。他为呼应左联做了大量工作:一加入左联,马上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党团成员。在左联中,周立波曾经作为左联成员,又是共产党员,这就决定了他的革命文学者的身份。参与编辑过左联刊物《时事新报·每周文学》;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翻译过前苏联的作品,在报刊上发表大量阐述文艺理论问题和评介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如艾芜等,其革命理论家的素质也在养成。撰写了《关于“国防文学”》、《我们也来谈谈“国防文学”和“国难文学”》、《“国防文学”和民族性》、《希望于文学者们——反对谩骂要求团结》、《非常时期的文学研究纲领》、《怎样使国防戏剧运动深入民间》、《我们应当描写什么》、《中国新文学的一个发展》、《为“国防文学”的民族性问题答周楞伽先生》等一系列论文,积极宣传“国防文学”,这又让他成为了革命文学的鼓动家。这些工作激发了他的热情,也诱发出了一些不足。在左联活动中,他与周扬走得更近,特别在“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论争中,他在配合周扬与鲁迅“争正统”中产生不和谐。因此,后来他这样检查自己:“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对鲁迅尊重不够”,“应当作为历史教训来吸取”。[4]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和当时本已经十分向“左”的鲁迅都发生争端,周立波的激进态度已经与亭子间早期完全不同了。
周立波通过加入左联和参与左联活动,而成为社会公众的一员,这是他转换的重要收获。1963年他在《〈亭子间〉后记》里回忆左联:“左联是我热爱的一个文学团体。鲁迅是它的骑手;胡也频、柔石、殷夫等等五位作家的鲜血染红了它的首页;它有郭沫若、茅盾、周扬、夏衍等等同志这样一些杰出的、活跃的作家和领导者;它冲破了国民党无数次文化‘围剿’,虽然遭受了敌人几次重大的破坏,它还是继续地战斗。左联的特点之一是战斗性强韧。自始至终,它和我们的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总是针锋相对地不停不息地战斗。左联的工作是有缺点的。在这篇短短的后记里自然不能全面地评价这一团体,我只想就文学问题谈点个人的意见。记得左联的刊物曾经讨论文艺大众化,但是没有得出切实可行的结论;而关于文艺的方向,创作的源泉,作家深入群众的活动以及普及和提高等等一系列问题,他都没有提出来处理。这些根本性的问题,直到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问世以后才获得了真正的、正确的解决。”[4]这是周立波20多年后的评价,多年的思考后,他对左联的评判有了微妙变化,但对左联时代行为的不后悔,甚至以此为荣,流露在字里行间。
虽然左联的发起者中没有周立波,成立大会召开时他也没有赶上,但他对这一组织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这使得他一出监狱就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马上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左联的党团成员,实际上是谋得了负责人身份。同时他还是左联常务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委员,比他早4年加入的人都未担任这样显要的职务,个中原因当然是他的争取和周扬的扶掖。他获得席位时的心情无法考证,我们也不能妄加猜测。我们只能说,一个蛰居亭子间为生计奔波的人,一个只想在文学上谋求发展的青年,通过奋争,有了新的念想。他也要革命,也要像他的引路人一样,成为真正的革命者。文人要革命,走的必然是一条未知的路。周立波是文人,也就这样开始了他的革命作家之路。在中国现代历史的演进中,文人们经受的风雨,以及受到煎熬时的内心律动,甚至彷徨,要比其他类型人剧烈。特别是当他们企图成为职业革命家时,为自己辩护的要求就更强烈,文学之火必须熄灭。在未来的路上,周立波选择了一条具有自己个性的路,他自觉地不断调整自己,不去与人争胜,不去追求权力,默默地教书、写作、编文稿、当记者,做一些与文学有关的活动。但受过西方文学影响、具有知识分子身份的他,要抛开知识分子特有的个性、行为、思想,必然很难。在面对新的时代和新的要求时,许多知识分子的转变弄成玉石俱焚的结局。虽然他们革命了,但在职业革命家的眼里,仍然还是闯入者。因此,周立波怎么也不会想到,《暴风骤雨》会弄出响动,《山乡巨变》、《韶山的节日》会受到那么严厉的批判。从《暴风骤雨》以后,他的小说一直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而且在研究中,我们找不到他妥协于自己的创作理想的证据,这是不是与左联时代确立的理想有关?
二 完成知识分子的“蜕变”,走向工农兵
在延安后期,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面临着空前的危机。那就是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本来姿态,已经不能在延安这个军队、农民、工人占主导的地方生存,而且抗日战争一天天残酷,知识分子的担当之心必须化为实践才合时宜。在这样的环境下,延安开始整风,知识分子的心灵受到猛烈的清洗。知识分子面临脱胎换骨的重大选择。很多人选择了去农村,而周立波则自觉地选择了到部队生活。周立波的这种选择代表了他革命性的一面,也许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时候只有部队是最能证明个人的真诚。而延安的知识分子大批量迁移,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一个显要的事件。
(一)“忏悔”:远离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是现实主义创作中永不停息的母题,它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十分巨大,并且引起了中国文坛阵阵波澜。它在中国一直是文艺摆脱不了的话题,就像梦魇般压着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有担当的文学家。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人道主义创作一直残酷地拷问知识分子的心灵。人道主义创作,对左翼文学来说,时断时续。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王实味、丁玲、周立波的人道主义创作刚萌芽即被掐灭;到了50年代,宗璞、邓友梅等的创作也是昙花一现;80年代张贤亮、张洁、谌容的现实主义创作终于将人道主义延续。中国人道主义创作受到主流意识的干预,影响了它的深刻性,艺术上既不大气也不细腻。从50年代起,人道主义在中国,常常被冠以“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等修饰语。但是,从中国的社会现实来看,书写人生命运的作品很有存在的必要。而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它应该不断被创新,才有生命力。从其在中国的命运来看,其既没有得到推广,更没有得到创新。一种文学思潮,一种创作方法要生存则必须具有可能生存的土壤。和人道主义在中国文学里并行的话题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小资产阶级情调之说与人道主义一样,同样来自于法国。夏多布里昂等一批家境处于中产阶级与平民之间的知识分子,常常聚于小酒馆、茶室、咖啡屋或古典音乐吧,清谈艺术、人生,并且注重穿着打扮,谈吐温文尔雅,行走不疾不缓,这种生活方式被许多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带回国,在不同国家产生变种。在我国,20年代产生了民族资本家、买办资本家,也产生了一些文化人构成的小资产阶级。起初的小资产阶级,不关注社会民生,只注重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生活方式后来被称为“小资情调”,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后来也常常被指称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泽东在他的很多篇文章里都有阐释,特别是在《讲话》里,这种阐释也就决定了后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在面临命运的挑战时,一部分知识分子保持沉默,而另外一批知识分子则选择了“忏悔”,用以达到与主流的沟通与同步。而按照卢梭的逻辑,“忏悔”就是对人道主义的一种阐释,而在中国40年代至70年代的知识分子那里走了形。而我们研究的周立波,就是后一种知识分子。
从亭子间狭小的个体到投入左联集体,那是周立波的第一次转变。而40年代的“忏悔”,则是周立波的第二次转变。这次转变对周立波来说,意义丰富而深刻。我们不能说这只是一个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新星被遮蔽的过程,还必须证明周立波转向了现实主义典型化,并且确立其在中国“新小说”创造中重要位置的开端。无意之间,他成为了“十七年文学”规范化的典型作家之一。而回到我们的文题,周立波的“忏悔”是在发表了《麻雀》等6篇小说后开始的。
1941年6月6日至7日,周立波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以陕北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牛》,这是他的第一部写农村生活的小说,也是他一生中的第一篇小说。随后,他又分别发表了《麻雀》、《第一夜》、《夏天的晚上——铁门里的一个片断》、《阿金的病》、《纪念》这5篇短篇小说。这5篇小说和《牛》一起成为小说家周立波的开端。
周立波的后5篇小说结集出版时名为《铁门里》,小说写的是提篮桥监狱的囚犯们对自由生活的强烈向往和对爱与美的强烈的渴望。1996年,笔者在北京拜访林蓝时,她说何其芳到他们的窑洞里来,看了《麻雀》后,激动得手在抖泪在流。而严文井则说:“这个短篇比他以后受某些条条框框束缚写出来的某些作品,更为动人,更为有着永久的艺术魅力。”[5]从《麻雀》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作者的人道主义情怀,看到作家心中的不变的“自由”情怀。延安自由的生活,给了他灵感,但他马上陷入题材不宏大的苦闷中。
小说发表后,雪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评论,称:“《麻雀》的吸引人之处,不在他的人物(因为这里没有展开人物性格的描写),而是作者给予这故事上的浓厚的抒情气氛和微妙的表现手腕。作者确实是‘善于抒情’的。”[6]根据这篇文章发表的日期1941年12月5日来看,正是文艺座谈会和延安整风运动的前期。分析这些作品,的确可以找到“抒情意味”。同时,我们可以从雪苇的评论中领悟到,文章实际在强调周立波的这篇小说是追求一种“趣味”,一种温暖的“情调”,显然与大的政治气候不合。充满自觉意识的周立波似乎嗅到了什么。
而《讲话》发表前与毛泽东和文艺工作者的几次谈话,使周立波似乎想象到了自己的“不足”。就在这段时间,毛泽东两次邀请周立波、严文井、何其芳到杨家岭谈话,核心内容即作品要写工农大众,要抛开上海小资产阶级情调,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同时,批判丁玲,清算王实味的思想,一种知识分子的改造之风开始兴盛。丁玲、王实味的“小资”之火是被强力扑灭的。丁玲接受了来自周围的种种诘难,在百口难辩中,痛切地自我反省,然后去河北才得以安定,但是对她的审查才刚刚开始,解放后,丁玲的命运就是延安时代问题的延续;王实味则不同了,一个不关心争论的编辑无端被人带入漩涡,只能用生命解决“歇斯底里”的宣判。周立波在这个时候,表现出十分的“清醒”,坚信了自己的“不足”。于是写了两篇文章自陈不足,然后离开,当然在上海的“清白”与革命的坚决无疑成为身正的铁证。这是在延安能全身而退的重要原因。
而此时,一向矜持的何其芳的态度剧变,对自己大加挞伐,同样对周立波影响很大。何其芳在《解放日报》上撰文反省和检讨。何其芳在文章中批判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情调跟不上需要,阐释了知识分子不仅要改造自己,还要改造文艺以适应时代需要,然后指给自己一条路:下乡改造。何其芳在此自戴高帽,对延安知识分子的改造起到洞心的作用。何其芳的自我批判文章极大触动延安的知识分子,也使何其芳的一生变得更为复杂。后来人们讨论的两面的何其芳,就是以本篇文章为分界。
同为鲁艺教员的周立波,当然不敢沉浸在《麻雀》等小说发表的喜悦中。一个有着艺术修养和天分的小说家刚刚开始找到一种言说方式,但他马上就要更换了。作为回应,周立波自觉表现出反省姿态,先后在《解放日报》发文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过去,为什么走了这条旧的错误的路呢?我现在反省,这原因有三。第一,这拖着小资产阶级的尾巴,不愿意割掉,还爱惜知识分子的心情,不愿意抛除。譬如在乡下,我还想到要回来,间或外还要感到过寂寞。这正是十足的旧的知识分子们的坏脾气,参加生产和斗争的群众,不会感到寂寞的,恐怕连这个字眼也不大知道,为了群众的利益而斗争的战士,在边区,也不会感到寂寞的。只有犯有偏向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才会有这样的病态的感觉。有这感觉,就自然而然地和群众保持着距离,而且自然而然地退居于客人的位置,这是我错误的头一个原因。
其次是中了旧书子的毒。读了一些所谓古典的名著,不知不觉地成了地主阶级的文学的俘虏。在这些开明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精致书里,工农兵是很少出现的,有时出现,也多半是只是描写了消极的一面,而那些寄生虫,大都被美化了。贾宝玉、安娜·卡列尼娜,都是一出场,就光彩照人,特别是安娜,在鲁艺的文学系,有一个时期,连她的睫毛都被人熟悉,令人神往。自然,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人们,不仅不会上这些书本子的当,而且还会从那里面吸取他所需要的东西。例如,列宁就是极高地也是极正确地评价了托尔斯泰的作品的。但是对于一般的立场还不稳定的小资产阶级者,她是有毒的,它会使人潜移默化,向往于书里的人们,看不见群众,看不清现实里的真实的英雄。这是过去的错误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在心理学上,强调了语言的困难,以为只有北方人才适宜于北方,因为他们最懂得这里的语言。一个南方人来表现这里的生活,首先碰到的就是语言的困难,这是事实。但这困难可以克服的,只要能努力。夸大语言的困难,是躲懒的藉口。”[7]
在检讨中,周立波用“小资产阶级情调”、“地主阶级的文学俘虏”、“夸大语言的困难”等狠狠地批判自己。在文中,可以看到周立波对外国文学的阅读仍然带有保留,也是后来在《暴风骤雨》等重大题材中出现欧化等特征的原因。文中提到的方言学习,成为了他以后的不断追求。通过自我反省和批判,周立波又一次选择了离开。那是1944年,跟随部队南下然后又入关,以实际行动开始了改造之路,他的新小说创作开始起步。
(二)“歌唱”:深入现实生活
作家的使命应该是用良知来书写社会民生。“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在抗日相持向战略反攻阶段,作家书写社会人生被社会现实赋予了不同意义。在鲁艺的周立波,以及当编辑的周立波,都不能容忍自己的落后。鲁艺的严肃的政治气氛和单一的教学内容,让周立波感到待下去会成问题。而中央也没有把它视为一个长期生存的机构,伴随整风运动的完成,鲁艺被并入延安大学。而“忏悔”后的周立波真正地深入到工作中去了。他是带着反省“没有好好地反映我所热爱的陕甘宁边区”[8]离开的。在他的头脑中形成一种“我不能成为工农兵,那我就写好工农兵”的理念,那是显而易见的。
1944年,他主动申请报名,参加了以王震为主的八路军南下支队,11月开始南征,历时将近一年。11月10日从延安出发,周立波开始写战地日记,300多天未间断。张振海、丢眼镜等故事就是记录的南行中的事。行军中,作为书生的周立波,又是一名高度近视者,他的困难可想而知。在南行中,他不仅仅是行者,还是一位歌者。他编印油印小报《解放》,报道消息,宣传政策。三五九旅南征的事迹,周立波写成了报告文学集《南下记》和《万里征尘》。
1946年,周立波被调入冀热辽区《民生报》,任副社长。同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号召共产党员:“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周立波被分配到松江省珠河县(今黑龙江省尚志县)元宝镇,并分别担任过元宝区的区委副书记、书记,深入屯干部和农民中,进行深入的调查,并学习地方方言。半个月的土地改革,使他对农村有了全新的认识。后来被调动到松江省宣传部编辑《松江农民报》,并酝酿《暴风骤雨》的写作。经过反复调查,《暴风骤雨》上卷终于写成,新的小说诞生了,它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起成为延安整风后的“新小说”。
在创作小说时,他还不断参与社会活动,编辑《松江农民报》和《文学月刊》杂志,主持编写《农民文化课本》。《松江农民报》停刊后,周立波又编东北文协主编的《文学战线》,开辟了青年之页和工人创作等栏目,刊登了茅盾、丁玲、严文井、草明等人的作品,刊登了许多苏联及西方一些国家的文学作品。那些翻译的文学作品和评论,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创作,这与他的心理追求保持了一致。在抛开自我中,在农村广袤的土地上,周立波以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大声“歌唱”起来。
至此,我们这样概括:亭子间生活是周立波作为文学家的开端,在五六十年代,那么多亭子间作家只有他敢提起亭子间,并出书《亭子间里》。反右中,他有些过左,伤害过别人,但又可以看到他的纯粹,他企图保持完整的自我和信仰。这种性格不能不影响到他的创作。在性格层面上说,他是不完整的。因而,当政治遭遇革命时,必然会碰到动荡不安;当作家遭遇政治时,必然经受更多的挑战。周立波就是作家,而且通过动荡社会的淘洗,他成为了革命作家,从此他必然经受那么多的考验,在社会演进中“脱胎换骨”。这些是其坚守和转换中的必然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