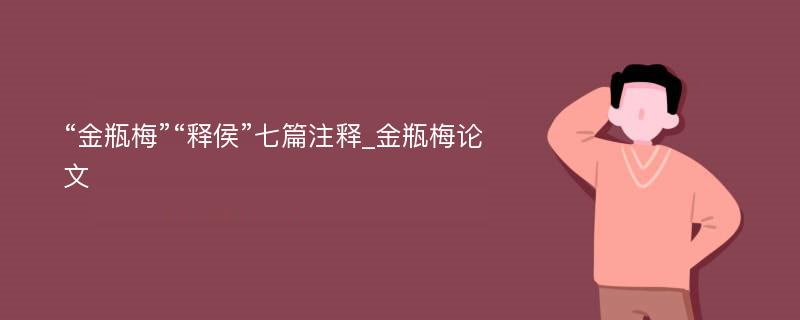
《金瓶梅》歇后语七则解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歇后语论文,金瓶梅论文,七则解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许多学者致力于《金瓶梅》语词研究,成果显著,已出版专著多种,许多歇后语的深文奥义都已得到确切诠释,给读者及研究人员以极大方便。但还有一些,似有待作进一步探求。今取七则,略陈愚蒙,以就教读者及同道诸君。
山核桃,差着一槅儿哩 七回:“如今他家,一家子只是姑娘大,虽是他娘舅张四,~。”《注释》(指魏子云《金瓶梅词话注释》,中州古籍重印本,1988)43页:“山核桃乃吴越所盛产。核桃仁中间有隔,一层层的……比喻两下里的亲情不够直接。舅与外甥,终究隔着一层了。”《鉴赏》(指《金瓶梅鉴赏辞典》,上海古籍,1990)509 页:“山核桃中间有一层层槅子……此俗语的意思是‘(舅舅与外甥),中间还隔着一层哩’。”《词典》(指白维国《金瓶梅词典》,中华书局,1991)731页:“山核桃果实里面有若干内果皮将种仁隔开。 比喻人关系疏远不是贴近的亲属或朋友。”《辞典》(指黄霖主编《金瓶梅大辞典》,巴蜀书社,1991)375页:“以山核桃有槅的形状, 比喻双方关系多着一层隔阂,关系也疏远一点。”《汇释》(指李申《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北京师院出版社,1992)64页:“山核桃内有许多隔子。‘差着一槅儿’即……隔着一层。……”
按,语本谓“差着一槅儿”,差者,少也。而诸家尽于“多”上求索(见笔者加着重号处),恐未得其要。今按,山东人所称“山核桃”,即常见老年人团于手掌中那种(此其大者,而多数果型较小)。此语不言“核桃”(胡桃),而言“山核桃”,不可忽也。盖此类歇后语的构成,句法上取紧缩式,其造语规律常是用一种特殊型某物,与同类的普通型某物相较,以构成歇后义。比如“水蝎子,不怎么着”,是用水蝎子(一种尾部有夹子的小昆虫),与普通蝎子相比,其蜇人不甚重也。他如“草鞋,没号”、“猪血李子,中看不中吃”等,皆属此类。本语亦然,是用山核桃与普通核桃相比,它差着一槅子。故此乃言其槅少,非谓其多也。为了验证,笔者曾找来几枚山核桃,细心敲开与核桃相较,不禁惊叹老俗话之言之不爽:核桃在两半个内果皮里,除却小槅不计,尚各有一片薄薄的半月形大槅,此槅轻轻用指一揿即可取下;而山核桃无此薄槅,仅在该处突起一短粗的棱,且与内果皮连为一体,不能取下。所谓“差着一槅儿”,盖指此也。证诸上下文意,原文是说张四(山核桃)与杨姑娘(核桃)相比,同孟玉楼的亲情差一槅(即差一层,因张四终属外戚)。而非“舅与外甥”“隔着一层”(显然这是由山核桃隔层多推演而来。其实姑侄之间亦何尝不隔一层)。语中“差”字,不宜解作“隔”。
江浙一带还有一种山核桃,外形似龙眼而坚硬,果仁酥脆如香榧子,当地人称作“小胡桃”者。《注释》所谓“吴越所盛产”,当即指此。魏子云先生于《金瓶梅》作者主南人说,这在《注释》也有所表露。此言“吴越所盛产”,或也出于这种考虑。其实小胡桃果仁间并无一层层槅子,若与核桃相比,那就更差大槅儿了。
此语于元明俗文学中,今所见有三处,除本例外,尚见武汉臣《老生儿》二折:“这个是你的,~。”及《醒世姻缘传》五十三回:“你们凭着甚么分得这地?就使这地不干我事,都是晁近仁自己的地,放着晁为仁亲叔伯兄弟,你们山核桃差着一格子哩!”两处用法均与《金瓶梅》相合。值得一提的是,《老生儿》、《醒世姻缘传》两部作品,都出自山东作者之手(武汉臣,济南人),殆非偶然。此似可为《金瓶梅》作者山东人说,增一小小佐证。
旋簸箕的,咂的好舌头 二十回:“嗔道五娘使你门首看着旋簸箕的,说你会咂的好舌头。”
《词典》736页:“旋簸箕,用线绳、皮条和柳条等编制簸箕。 制作时,工匠时常用口水咂润线绳或皮条,故歇‘咂的好舌头’。这里实指接吻。”
按,此语诸书多未收。《词典》释“咂舌头”为接吻,是。唯与“旋簸箕”之关涉,说解欠安。制簸箕主要用去皮柳条、柳木片(用于簸箕前端敞口部分)、竹篾和木条(用于最后滚边沿),以及线绳、牛筋(俗称“弦”)等物。柳条用线绳编好后,下一步即安前端板片,这块板片与柳条部衔接,绑扎得紧密平齐与否,直接关乎簸箕的使用效能,故这道工序工艺要求较高。此前端板片,俗谓之“簸箕舌头”。本语“咂的好舌头”,其表面义是说宋惠莲会旋簸箕,扎的簸箕舌头极受使唤,而实则是用“扎簸箕舌头”,谐音双关“咂人舌头”,以此调侃宋(与西门庆)的咂嘴勾当。
旋簸箕所用的柳条、木片等物,都是用水浸泡过的,而且制作作坊多在地窖中(取其湿润),既无须也不可能“用口水咂润线绳或皮条”(柳条湿润,线绳可不咂自润;反之,咂润也无济于事)。
尖头丑妇硼到毛司墙上,齐头故事 二十回:“(玉箫)因问:‘俺爹到他屋里,怎样个动静儿?’金莲接过来道:‘进他屋里去,~。’”《注释》135页:“……意指西门庆与李瓶儿已并头睡在一起了。 尖头男子丑陋妇人,被绷(硼)弹在厕所的墙上……厕所墙是臭的,以‘臭’字谐‘凑’,……是‘凑(臭)在一起的齐头(男女相关)故事’。”《词典》723 页:“尖头丑妇人碰到毛司墙上(其实碰什么墙都可以,说毛司只是表达了说话人的一种感情色彩),……齐头,指人并头睡在一起。”
按,自十年前魏子云先生将“齐头故事”释为“并头睡在一起”,此后诸家大抵取此说,兹不俱引。今按,“齐头故事”乃山东俗话,“齐头”,今鲁东也称“齐头子”,是“齐同”、“一样”的意思;“故事”,口语读“故事儿”,通常指“招子”、“点子”、“鬼主意”,也有时指某种动静,某种作为。文中写李瓶儿嫁过来后,西门庆竟一连三日不进她屋,她心里腌臜,乃“脚带吊颈,悬梁自缢”,俨然是个烈性女子。但当西门庆抽了她几鞭子后,她便立刻服软了。至于西门庆,本即恼着李瓶儿(嫁蒋竹山),今见她又上吊,更是火上浇油,故袖着马鞭子进她屋,看架势非闹出点事儿不可。但当瓶儿一说软话儿,他也就“欢喜无尽”,又是“搂在怀里”,又是让春梅放桌儿,取酒取菜……。闹了归齐,也是水蝎子,不怎么蜇!故当玉箫问西门庆进屋怎样个动静儿时(显然捏着一把汗),潘金莲乃悻悻地说:“进他屋里去,~。”意思是两人臭味相投,都是一路货,没什么新鲜出手的。证之此语上文,当金莲听春梅说了屋里情景,并让春梅放桌取酒后,乃道:“贼没廉耻的货,头里那等雷声大雨点小,打哩乱哩,及到其间,也不怎么的。我猜也没的想,管情取了酒来,教他递。”这段话,正是此语的绝好注脚。将“齐头故事”解作“并头睡在一起”,不过是出于联系下文的想象,无论从语义抑或当时实际情况,均不相合。
另,“尖头丑妇”是偏正结构,释为“尖头男子丑陋妇人”(并列),不妥。此外,《词典》认为“碰什么墙都可以”,不可以也。此类歇后语的构成,往往是先有一俗语,然后依据俗语去构思比喻语。此语是先有“齐头故事”,其后才想出离奇荒诞的“尖头丑妇碰毛司墙”。倘碰一般的墙,只能满足“齐头”,而“故事”则无着落;唯有碰“毛司墙”,方扣“齐头拱屎”,盖以“拱屎”谐“故事”也。故“毛司”不可看作闲笔。“丑妇”,谐“臭妇”,臭碰臭,瘸驴对破磨,恰是一路货。
云端里老鼠,天生的耗 二十回:“贼小肉儿不知怎的,听见干恁个勾当儿,~。”《注释》135页:“……所谓‘耗’乃消耗之意。 指老鼠天生的本性就是消耗人间粮米。……”《辞典》400 页:“此语是潘金莲责怪春梅、小玉无故消耗自己的力气去服侍别人。 ”《词典》738页:“耗,谐音‘号’,指某一类。这里说春梅是天生的那一‘号’(类)……”
按,此语索解关键确在“耗”字,表面是说“天生的耗子(老鼠)”,实则以“耗”谐“好”(hào)。“天生的好”是俗语,指天生好干某种事(山东方言称与生俱来的为“天生的”)。这里潘金莲明着是骂春梅喜欢给人狗颠屁股锤儿跑前跑后,生就一副贱骨头,而实际则是怀恨李瓶儿。春梅自然听得出,故“笑嘻嘻”地走了。《注释》、《辞典》解为“消耗”,显非是。《词典》释为“号”(类),亦不妥。作“类”解的“号”,用时一般要在其前加指示代词限定(如“这道号”、“那一号”),“天生的号(类)”,恐不合语言习惯。
夹道卖门神,看出来的好画儿 三十一回:“贼囚,你~!”《注释》213页:“……意为我听得出来你这话不是好话。”《鉴赏》559页:“似应作‘听出来的好画儿’。在昏暗的夹道中卖门神,买主只能听卖主的介绍,而看不清绘像好坏。……”《辞典》420 页:“夹道是比较昏暗的地方,看不出门神的好坏。”《词典》723 页:“……好话儿,反语,其实是歹话儿。”《汇释》216 页:“……‘出来的好话儿’是反语……”
按,语言“夹道”,主要意取“狭窄”,而非取其“昏暗”。“看出来的好画儿”,“画儿”谐“话儿”,自不待说,而索解关键在“看”字。诸家多将“看”字凿实,认作“观看”之“看”,以为“画儿”可看,“话儿”岂能看?故《鉴赏》解为“似应作‘听出来的好画(话)儿’”。盖由未审“看”之义也。此“看”是经过度量后作出的否定判断,意思是“绝不会”、“不可能”。如“他五音不全,看(能)唱出来的好歌”!意谓他不可能唱出好歌来。“看出来的好画儿”,是绝不会拿出好画儿来(因夹道狭窄,买画人多,画又不宜折叠,或舒或卷,携出时都易破损)。而解说义则是“(你个贼囚)绝不会说出来的好话儿”,也即狗嘴吐不出象牙之意。《注释》解作“我听得出来你这话不是好话”,其实书童的话原不隐晦,明显是打牙犯嘴占便宜(玉箫向书童要他身上系的香袋儿,书童说:亏了是这个,要是个汉子,你也爱),本不存在“听得出”“听不出”的问题(玉箫甚等样人,倘连这都听不出,岂非傻丫头)。另,《词典》、《汇释》分别以“好话儿”、“出来的好话儿”为反语,亦失察。原语中“好话儿”若改为歹话儿(看出来的歹话儿),则恰与语意相反了。
隔墙掠见腔儿,可不把我唬杀 四十二回:“哥儿那里~!”《注释》283页:“意为行走之间,突然由隔墙掠扔过来一付内脏等物, 真能把人唬死了。”《词典》721页:“腔儿,腔子, 割去头的人或动物的躯干。隔墙扔过一具血淋淋的腔子,可不就把人吓死了。又,‘腔儿’也可指腔调……”
按,“隔墙掠见腔儿”,于语法难通。《注释》将“见腔儿”释为“一付内脏等物”,不知义所从取。《词典》似乎意识到“见腔儿”不辞,故抛开“见”字,只就“腔儿”作释,解作“腔子”。姑不论“腔儿”与“腔子”是否一义,即使可通,如欲唬人,直接扔过具尸首岂不更爽神?要想取血淋淋效果,扔过个头来则更为可怕,何必舍轻就重?至若“‘腔儿’又可指腔调”,亦未必妥。单讲“腔儿”,确有腔调义(如“甩腔儿”、“撇京腔儿”),但与“掠见”搭配,恐不合语言习惯。今按,“见腔”当是“鬼脸”形之误。“见”与“鬼”,“腔”与“脸”,草书近似,手民眼错,容或有之。崇祯本此处正作“鬼脸”,宜从。鬼脸者,假面也。猛然间自墙外扔过一神头鬼脸,初不知为何物,自会唬人一跳;然一旦落地,知其为假面,便可化作一笑。文中写应伯爵骂韩玉钏、董娇儿两个唱的:“头里知道我在这里,我叫着怎的不先来见我?这等大胆,到明日一家不与你个功德,你也不怕!”其实伯爵不过是个帮闲,无非说句大话而已,两个唱的并不惧他,故董娇儿笑道:“哥儿那里~!”既是“笑”道,显不在意。“可不把我唬杀”,是反语,意为“隔墙扔过个假面(说句大话),是不会把我唬杀的”!意在讥诮伯爵。此语崇祯本作“隔墙掠个鬼脸……”,加“个”字,益言其不足构成威胁也。连下文韩玉钏嘲讽伯爵“好个丢丑的孩儿”(即好个现眼的孩儿),更表明“可不把我唬杀”为反语。
马回子拜节,来到的就是 十一回:“怪小淫妇儿,~!”《词典》726页:“回族人多信奉伊斯兰教,每日有固定时间做礼拜, 规定时辰一到,不论在做什么都要停下来向麦加方向朝拜。比喻命令来得急,克时立办(表示不满)。”
按,“来到的就是”是山东俗语,即“来到的(时候)就是(时候)”。此语是用来对那一到就要求人家立即给他办事的人,表示不满的,与今天津俗语“来到就是时候”,义同。《词典》释作表示对“克时立办”的不满,是。但这只是解释了“来到的就是”这一俗语的意义,至于与“马回子拜节”的干系,解说则欠安。《词典》以为“马回子拜节”本身就蕴含“克时立办”之义,用以比喻“来到的就是”,恐未必。今按,此语表面是说“马回子拜节(做礼拜),来到寺”,即信奉回教的回民做礼拜,到清真寺。然后以“寺”谐“是”(二字山东同音),再过渡到俗语“来到的就是”。此种歇后语仅仅是利用谐音双关,非义所从取,故不宜看作比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