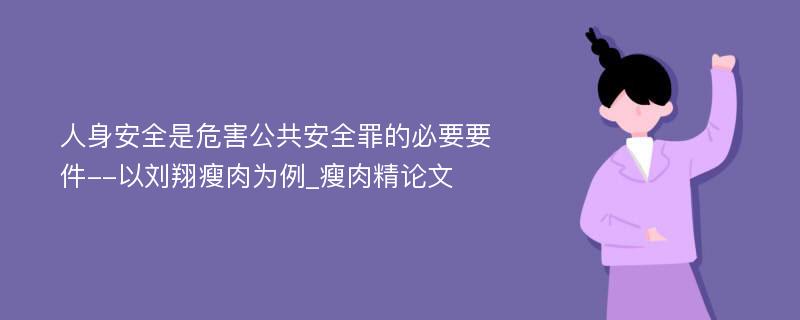
人身安全是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必备要素——以刘襄瘦肉精案切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要素论文,公共安全论文,人身安全论文,瘦肉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之提出:两个瘦肉精案例及其相关判决
案例一:2007年年初,刘襄等5人为牟取不法利益,生产、销售盐酸克仑特罗(俗称“瘦肉精”)2700余公斤,销售金额高达640余万元,并造成数额特别巨大之财产损失。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刘襄等人明知盐酸克仑特罗的危害,仍然从事购买原料和盐酸克仑特罗的生产、销售等活动。刘襄等5人生产、销售的盐酸克仑特罗被分布在8个不同省市的生猪养殖户,最终致使大量含有盐酸克仑特罗的猪肉流入市场,给广大消费者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①并使公私财产遭受特别重大损失。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罪名,判处主犯刘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本案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2011年8月10日维持一审判决。②
案例二:2009年11月至2011年2月期间,韩文斌等7人为牟取利益,在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件和批准文号的情况下,非法购买“瘦肉精”及含有“瘦肉精”成分的稀释粉销售给生猪经纪人和生猪养殖户,并传授饲喂方法,供生猪养殖户喂养生猪时往饲料内添加使用。2011年8月9日,河南省获嘉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韩文斌等7人明知“瘦肉精”是国家禁止用于喂养生猪的药品,明知人食用喂养“瘦肉精”的生猪对人体有害,但为牟取利益,非法经营销售“瘦肉精”及含有“瘦肉精”成分的稀释粉给生猪养殖户,并传授饲喂方法,供喂养生猪时往饲料内添加使用,其行为违反了我国对有关国计民生、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及公共利益的药品实行限制经营的规定,并造成重大影响,引起严重不良后果,韩文斌等7人的行为均构成非法经营罪,判处主犯韩文斌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2.8万元。③
显而易见的是,上述两个瘦肉精案件之案情非常相近,审判日期也几乎相同,但其裁判结果,尤其是被告人所判处之罪名却判若云泥。刘襄案系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而韩文斌案则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前者属于刑法分则第2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之范畴,其同类客体为公共安全;而后者则归属于刑法分则第3章,其同类客体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上述两个案件之共同特点在于,对于被告人使用瘦肉精所造成“消费者身体健康及生命安全之实质性危害”,公诉人均未能举证证明,而法院也并未对此予以特别认可。尽管在刘襄案中,公诉人指出:“刘襄等人作为研究化工产品的专业人员,清楚地知道瘦肉精具有相当的毒性,动物食用后会在动物组织中形成残留,特别是可以终生残留于肝、肾、肺等内脏中,人食用含有过量瘦肉精的肉制品后,会出现肌肉震颤、心慌、战栗、头痛、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甚至导致死亡”。但在本案中,公诉人却未能证明曾有任何一个被害人因刘襄等人之行为而产生上述症状,甚至刘襄案开庭时另一被告人肖兵更是语出惊人:“这些瘦肉精猪肉,我也经常吃!”因此,在刘襄案中,河南省两级法院认定刘襄等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核心证据,均在于数额特别巨大的财产损失。刘襄案中,公诉人指控称:“本案5名被告人大肆生产销售盐酸克仑特罗涉及8个省市,危害难以数计人的人体健康,并且造成了特别重大的财产损失,扑杀销毁生猪700多头,直接损失110多万元,即原双汇公司为处置该类肉及其制品损失3400多万元,焦作市辖区生猪养殖户收入损失达1.6亿多元”。④而在韩文斌案中,公诉人和法院对所谓的重大财产损失均避而不谈。因此,两案之间的微小差别仅在于,刘襄案中具有所谓的“特别重大的财产损失”。然而正基于此,对比上述两个案情极为相似的案件,才会不由得使人产生如下疑问:“如果被告人之行为在没有危及多数人的人身安全,而仅仅造成所谓的重大财产损失(或称之为,纯粹性财产损失)的情况下,是否也会必然侵犯公共安全之法益并因此而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而本文亦将凭籍法益侵害说、刑法实质解释论、罪刑均衡之相关刑法理论,对此相关问题进行解读。
二、纯粹性财产安全不属于公共安全罪之保护法益
(一)刑法之根本目的在于保护法益
法益是刑法理论的基石,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刑法规定各种具体犯罪的根本目的即在于保护特定的法益。台湾学者林山田曾称:“刑法之本质乃在于法益保护,故刑法实为一种法益保护法。刑法分则规定之每一个不法构成要件均为防止特定法益遭到特定行为模式之侵害所为之刑事立法设计。”[1](P.12)并且“一切犯罪之构成要件系针对一个或数个法益构架而成。因此,在所有之构成要件中,总可找出其与某种法益的关系。换言之,即刑法分则所规定之条款,均有特定法益为其保护客体。因此,法益可谓所有客观之构成要件要素与主观之构成要件要素所描述之中心概念。准此,法益也是适法者进行刑法解释之重要工具”。[2](P.6)而张明楷教授亦旗帜鲜明地指出:“法益是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3](P.167)
法益是刑法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最基本概念之一,对其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尤其是在刑法分则具体个罪中,构成要件的设置与确定中更是如此。“构成要件形成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是法益”,“法益是构成要件的中心概念(Zentralbegriff),根据该中心概念来决定所有客观的和主观的特征”[4](P.316)。在刑法学理论研究及司法实践中,法益之重要性还体现在,其具有此罪与彼罪之间的区分机能。换言之,“各形各色之犯罪行为,之所以能够井然有序地规定于刑法分则中,即是依据法益之分类,编排而成者”。[2](P.6)就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益而言,其不仅具有确定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之具体个罪客观构成要件实际内容之作用,还具有“通过刑法对具体罪名的规定以及各种规定之间的关系进行确定该罪的刑法法益,从而实现此罪与彼罪之间的区分功能”。[5]P139因此,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保护法益究竟为何,毋庸置疑也成为公共安全犯罪理论研究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核心议题。
(二)公共安全法益之学说争论
何为公共安全?刑法学界对此聚讼纷争,莫衷一是。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此也是惜墨如金,语焉不详,而仅是在刑法第115条中极其含蓄地以“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一笔带过。因此,研究者仅能在中国刑法教科书及相关论文中得以窥见若干“公共安全”之定义。本文在此仅简要撷取推介以下3种较有影响力之学说:
第一种观点指出,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6](P.510)由于该观点提出时间较早,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广有影响,因此仍然在中国刑法学界占据通说地位。
第二种观点主张,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公私财产的安全”。[7](P.537依照该观点,公共安全应当包括不特定多数人和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公私财产的安全。或者说,区分特定还是不特定并无实质必要性。由于这一观点系由张明楷教授提出,受其影响,如今赞成这一观点的学者越来越多,而该观点在我国也逐渐演变成一种有力的学说。
第三种观点认为,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产安全以及公共生产、工作和生活的安全”。[8]较之第二种观点,公共生产、工作和生活的安全也被增加为公共安全的范围之内,而这也和97刑法典及其相关修正案中危害公共安全罪修正演变之趋势是不谋而合的。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尽管上述3种观点之间还存在若干分歧。但其共同之处在于,一致未对所谓“财产安全”之范围进行限定,因此阅读者也不难品读出如下感觉,即“纯粹性财产安全”似乎也应该成为公共安全罪侵害之法益。但是,正如下文所述,这种“纯粹性财产说”是笔者所不能赞同的。
(三)公共安全罪之保护法益应仅限于人身安全
尽管我国刑法理论中主流观点均认为,公共安全应当包括财产安全,即便是“纯粹性财产”,也应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保护法益。但笔者认为,基于法益侵害说之立场,公共安全罪之保护法益应仅限于人身安全(或称之为“人身安全说”)。或详而言之,如果危害公共安全罪涉及财产安全,也应当是与多数人的人身安全有密切关联的财产安全(即侵犯该财产安全,必然会不可避免地危及相关人员人身安全。例如放火烧毁有人居住的房屋,或者破坏正在使用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等等),对于仅仅侵害到多数人的财产,但并不牵涉生命、身体安全之行为则不能认定为危害公共安全罪。其原因在于,刑法中的法益具有区别此罪与彼罪之功能,即不同法益能够明示不同个罪之间的根本界限,从而在整体上赋予具体个罪较为清晰的构成要件之轮廓。例如,故意杀人罪和盗窃罪之间的界限,不仅在于外在客观行为方面存在显著殊异,更在于两个行为所侵害之法益的囧然有别。正基于此,即便因盗窃行为使得受害人无法支付医疗费用而死亡,也不宜使犯罪人承担故意杀人罪(也包括过失致人死亡罪)之责任。又如,故意损坏交通工具罪属于公共安全犯罪,该罪是具体危险犯,拆卸一个车轮的行为一般人当然认为有危险,但是并不是所有拆卸车轮的行为都具备犯罪构成要件中所要求的具体危险。此时,还必须进一步判断:(1)该车辆在被拆掉一个车轮后仍能行驶(至于行驶距离远近,则在所不问);(2)这样的行驶会造成倾覆或者冲撞事故;(3)司机有可能在启动汽车前或开始正常运行时难以意识到车辆的这一缺陷;(4)该车辆正在使用期并实际投入了使用。缺乏上述任何一个条件,都不能认定为存在具体危险,也难以因此而危及多数人生命健康安全,故而只可能成立故意毁坏财物罪,而不能构成故意损坏交通工具罪。[9]
同理,也正是基于法益所具备之个罪区分功能,“纯粹性财产”,无论其数额多么巨大,也不应成为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保护对象。我国刑法分则第5章专门设有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破坏生产经营罪、盗窃罪、抢劫罪、诈骗罪、抢夺罪等财产犯罪,其保护法益均为财产权。倘若将诸如放火烧毁无人居住的房屋,使用炸药炸毁尚未交付使用的铁路桥梁,或者将车辆修理厂中检修的大型公交车推入太平洋中沉没等等仅仅危害到纯粹性财产安全之行为一概视为危害公共安全罪,则必将使得公共安全之法益所应具备的“构成要件区别功能”丧失殆尽。因此,本文原则上赞同“人身安全说”,即“公共安全在本质上是指多数人的安全。具体地说,会使社会的一般成员感觉到危险,客观上可能使更多的人(而非单纯的与人身安全无关的财产)遭受侵犯。因为唯其如此,方能体现出行为危害‘公共’安全这一属性,也才可以说是多数人的安全”。[10]基于“人身安全说”,不仅上述行为不会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而且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的,诸如向水族馆中养鱼池通电而击杀大量珍贵观赏性金鱼的,或者向皮革加工基地的养貂厂投放毒药使得数千只皮革用貂(而非食用貂)死亡的,或者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中放火烧毁大量林木的,尽管会造成巨额财产损失,但因为上述行为根本不可能危及到多数人的人身安全,故此也不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投放危险物质罪、或者放火罪等危害公共安全罪,而只能视其具体情节认定构成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或者破坏生产经营罪。
三、对公共安全法益应当作出合乎目的之实质解释
在刑法解释中,文义解释是一种重要的解释方法。“一切法律规范都必须以作为‘法律语句’的语句形式表达出来。可以说,语言之外不存在法。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表达、记载、解释和发展法”。[11](P.73)就此而言,解释之首要步骤便是就条文字面意思进行直接的理解,从字面探求追索法条用语的正确意义。“文义是法律解释的开始,也是法律解释的终点。法律解释始于文义,然众所周知,法律概念具多义性,有其核心领域及边际地带,其射程的远近,应依法律意旨而定,在边际灰色地带容有判断余地,但不能超过其可能的文义。否则即超越法律解释的范畴,而进入另一阶段的造法活动。尊重文义,为法律解释正当性的基础,旨在维持法律尊严及其适用之安定性”。[12](P.305)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构成要件是刑罚法规规定的行为类型,其具体内容是通过刑罚法规的解释决定的。因此,构成要件并不一定等同于刑罚法规的文言”。[13]在刑法中,“法条并非等于构成要件,构成要件是根据条文之解释始得以明确,”[14](P.93)或者详而言之,“条文文字本身往往根本看不出来是结果犯或行为犯……立法者无权任意区分结果犯与行为犯。因此,虽然立法对于杀人罪的文字规定是‘杀人’,文字上并没有表明必须以杀死人为要件,但是学说上却永远以杀人罪作为结果犯罪最典型的例子。质言之,所谓杀人罪是结果犯,是解释出来的”。[15](P.113)因此,刑法的法条文字所呈现的不一定属于构成要件,反之,甚至于法条文字未呈现者,也未尝就不会成为构成要件,就中事理曲折,仍需经由刑法实质解释予以说明。故此,适法者决然不可故步自封,不顾法条之实际目的,静止而机械地解释刑法,而应当在坚持法益保护之前提下,引入法律实质解释之观念。“实质解释论就是透过法官,以其作为社会成员的身份,在具体个案中进行法律分析,且依其价值判断作出利益衡量,求取法律适用与社会现实面的平衡以及追求个案的妥当性与合理性”。[16](P.27)而实质解释之重要性即在于,“毕竟立法是从各个在评价上具有重要相同特征的法律事件予以抽离其事实态样,再就得以抽离的共同因素加以规范化而形成法律规定,俾用于同类案件。而法律解释则正好反其道而行,系透过将已经类型化固定化的法律条文予以去规范化的动作,而将系争案例事实特征一一纳入法律条文,藉以观察是否可为系争条文所容纳。而此时亦需考虑到法律秩序的价值取向,俾用以指引法律解释之运作方向。”[16](P.28)
例如,刑法第144条规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指违反我国食品卫生管理法规,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行为。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却出现了使用福尔马林浸泡洗涤鱼虾、墨鱼等水产品,或者以保存、催熟、保鲜、增色为目的而将有毒有害食品添加剂涂抹于水果蔬菜表面的行为。无论是使用有毒有害物品浸泡、洗涤,还是将有毒有害食品添加剂涂抹于水果蔬菜表面的行为在社会危害程度上和传统形式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之行为可谓是旗鼓相当。⑤这些行为能否被认定为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呢?对此有学者指出,浸泡、洗涤、涂抹等是慢慢渗透进入,而掺入等于混同,“掺入”本身无法涵盖浸泡、涂抹、洗涤等类似慢慢渗透的行为。如甲醛泡鸭血、膨大剂药水泡猕猴桃则绝不可以理解为掺入。严格地说,如果把渗透、浸泡、洗涤、涂抹等解释为“掺入”本身,则有扩大解释之嫌。因此,或者需要两高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作出司法解释,增加与掺入行为相类似的浸泡、涂抹、熏染行为,使本罪的行为方式更加全面;或者由立法机关修改立法,将刑法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第一档刑期的罪状修改为,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以浸泡、泡发、洗涤方式渗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明知是上述食品而仍然予以销售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7]。但笔者认为,立法者之所以设置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其目的即在于为保护公众健康而处罚在食品中“加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之行为。因此,以任何方式在食品中“加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都属于掺入。而且,以列举式立法模式明确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之罪状,也并不适宜。因为除了掺入、以浸泡、泡发、洗涤方式之外,诸如用硫磺熏染黄花菜或者馒头的熏染行为,以敌敌畏滴灌大葱根部的滴灌行为,给动物喂食瘦肉精的喂食行为,用硫酸亚铁爆炒瓜子的爆炒行为以及拿针管在食用肉鸡上注射生长素的注射行为,都是典型的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之犯罪行为,其社会危害性也不亚于掺入、以浸泡、泡发、洗涤方式,并且还不排除在未来的某个时期中还会出现一些前所未见的新型加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之行为方式。因此,适法者大可不必强烈要求制定司法解释或者修改立法,而只需对“掺入”进行符合立法目的之实质性解释,对其理解为“加入”,从而提高“掺入”行为的实际容量,便可将形形色色的生产有毒、有害食品之犯罪行为一网打尽。
又如,刑法第140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达5万元以上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年《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刑法第140条规定的“在产品中掺杂、掺假”,是指在产品中掺入杂质或者异物,致使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者产品明示质量标准规定的质量要求,降低、失去应有使用性能的行为。但适法者千万不能认为,“在杂质或异物中掺入真品”,例如在染黑的白芝麻中掺入大量的真品黑芝麻,并在打包后以纯品黑芝麻销售的,就不属于“掺杂、掺假”。因为按照刑法实质解释说,“掺杂、掺假”的本质在于使得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者产品明示质量标准规定的质量要求。即便在500公斤染黑的白芝麻中掺入1000公斤的真品黑芝麻,也不是商品外包装上所称的纯品黑芝麻。故此,该种行为当然也是“掺杂、掺假”。
再如,在信息学中,从其字面意思来讲,情报是指“被传递的知识或事实,是运用一定的媒体(载体),越过空间和时间传递给特定用户,解决科研,生产中的具体问题所需要的关于某种情况的消息或报告”。因此,按照这一文义解释,“2013年初,在上海黄浦江中漂浮数千具死猪”的消息显然也是情报。但在刑法中,却不能对“情报”作出上述解释。否则,某人在获知《参考消息》即将排版刊发该消息,并秘密复制该版面之相关内容,并用电子邮件发给美联社的,有可能涉嫌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情报罪,而这显然是不可思议的。如我国刑法第111条规定,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这里的“情报”,如果仅作形式的字面解释,即“关于某种情况的消息或报告”,则只要为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一切“关于某种情况的消息或报告”的行为,均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的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情报罪。在这种形式上做到了将司法权限制在法条的文义范围内,实现了人权的形式保障,但显然不当地扩大了本罪的刑罚处罚范围,实质地损害了人权与自由[18]。故而,我国主流刑法教科书均从危害国家安全罪之保护法益出发,对本罪中的“情报”作了合乎法益保护目的之实质解释,认为此处之“情报”仅指“国家秘密以外的,一切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科技等不应让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知悉的资料、情况和消息”[19](P.374)。
还如,刑法第255条非法经营罪,是指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以及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该罪之保护法益是国家限制买卖物品和经营许可证的市场管理制度。在我国,药品销售需要经营许可,并且我国药品零售和批发行业判然有别,批发商不得零售药品,零售商亦不能批发药品。对此,《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17条规定:“未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核同意,药品经营企业不得改变经营方式。药品经营企业应当按照《药品经营许可证》许可的经营范围经营药品”。显而易见的是,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而从事药品销售的,只要达到一定金额,毋庸置疑会成立非法经营罪。但药品零售商在未经审核同意之情况下批发药品的行为,或者药品批发商在未经审核同意之情况下零售药品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则还不无争议。对此,应从药品管理部门严格区别药品零售与批发的初衷入手,结合非法经营罪之保护法益,方能窥见端倪。事实上,我国药品批发及零售之所以不能相互越界,完全是根据药品批发商和零售商不同的药品质量控制条件所决定的。药品批发数量较大,因此批发商对药品销售去向能够及时追踪,且其销售客户都具有质量保证体系,能够对药品质量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所以《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规定药品批发商的质量控制要点是购销渠道审核、储存养护、运输配送。药品零售购销量相对较小,零售商对药品销售去向难以实施追踪回访,且用药人往往不具备合理安全的用药常识。故此,《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规定药品零售商的质量控制要点是确保消费者安全用药。因此,就药品批发商而言,“需严格按规定从事销售活动。不能随意将药品销售给单位和个人,必须对客户和其采购人员的资质及真实性进行审核。审核合格后,按照客户经营范围销售药品,决不能超范围供货。药品配送需送至客户证照所载仓库地址(或地址),客户查验无误后签收,送货回执返回存档”。[20]而对于药品零售商,则“要了解药物的性质、特点、适应证、不良反应等,要选用疗效好、毒性低的药物,注意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帮助顾客选对药的同时还要告诉顾客所选药物的最佳服药时间。对于建立会员制的零售药店,建立健康档案,定期进行血糖、血脂、高密度脂蛋白、血压等简单易行的检测,及时发现潜在的健康风险,给予患者健康的生活指导和进一步检查等建议”。[21]而从上述“药品零售业和药品批发业不得随意变更经营方式”之具体缘由中不难得出如下结论:药品零售商不能批发药品,或者药品批发商不能零售药品之执业禁令,仅仅是《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对药品批发及零售有着不同质量控制要求而已。从药品购销流程来看,药品零售商和药品批发商都具有《药品经营许可证》,二者均是通过GSP认证的药品经营企业,其所经营的药品都处于药监部门的严格监管之下。因而,药品零售商在未取得药监部门允许的情况下,擅自批发药品的,以及药品批发商在未取得药监部门允许的情况下,擅自零售药品的,按照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17条之规定,虽然具有一定的行政违法性,但该行为却并不属于非法经营罪中的“未经许可经营”,因而也并未扰乱市场管理制度,当然也不构成非法经营罪。⑥
又如,虽然《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3条规定,“运输、携带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出县境的,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批准”。同时,刑法第341条也规定,非法运输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野生动物的,成立非法运输珍贵野生动物罪。但适法者切不可断然推论,只要未经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单位批准而擅自运输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就必然构成本罪。其实,非法运输珍贵野生动物罪之保护法益,是为了保障珍贵野生动物生命安全及正常生育繁殖。如果某动物园基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熊猫繁殖之需要,在大熊猫发情期间,在等不到林业局运输批文的情况下,为了不至于错过大熊猫发情期而将大熊猫运到外地去配种的,虽然是运输珍贵野生动物行为,但基于刑法实质解释之考虑,也不宜将其作为非法运输珍贵野生动物罪处理。同理,尽管《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2条规定,“禁止出售、收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需要出售、收购、利用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批准”。而刑法第341条亦规定,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野生动物的,成立非法收购珍贵野生动物罪。但适法者亦不能不假思索地认为,凡是未经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单位批准而擅自收购国家一级或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就一定会构成本罪。例如,2012年10月,华南理工大学博士生朱杰旅游时遇上野生动物贩子,为避免3只猫头鹰落入餐盘,他和同伴花了300元将其买下。⑦在放生了两只大猫头鹰之后,朱杰将剩下的小猫头鹰移交了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但该局工作人员却振振有词地指出,以任何理由收购野生动物的行为都属于违法行为,并声称朱杰的做法已经触犯法律。⑧事实上,在本案中,诚如朱杰所言,如果不是其当机立断买下这3只猫头鹰,而是打电话举报,坐等林业部门姗姗来迟,它们可能已经成为饕餮食客的盘中餐。故此,从保护国家二级野生动物猫头鹰生命之角度而言,在这3只猫头鹰即将被屠戮之情况下,果断将其买下是最为行之有效的应急办法。由是观之,较之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工作人员以官话行规来“有条不紊,按部就班解救即将被放血拔毛的猫头鹰”,朱杰之购买放生行为无疑更值得提倡。因此,其收购并放生猫头鹰之行为既不构成一般行政违法,更无所谓刑事可罚性可言。事实上,也正基于此,广州森林公安亦未对朱杰进行任何处理。
再比如,某一地方政府颁布条例明文规定禁止在作为一级饮用水源的水库中垂钓,如果该规定之立法原意是为了保护饮用水源之水质清洁的话(如该条例规定,为了饮用水源之洁净安全,不得在水库中放养鱼类,亦不得在库区中钓鱼),则对该条例作出合乎目的之实质解释就很有必要。从实质解释之立场来看,撒网捕鱼、高压电鱼,以及携带自制炸药炸鱼则当然属于禁止行列。同样的,类似于在该水库中清洗渔网、洗澡、洗脚或者洗马桶甚至清洗动物大肠中粪便之行为更应当不被允许。
还有,针对货币类犯罪之保护法益为“货币的真正性公共信用以及国家对货币的发行权(通货额权)”[22](P.251)。刑法第172条设置了非法持有假币罪,即“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数额较大的”。如果仅从其法条之字面含义来看,似乎行为人只要明知是伪造、变造的货币而非法持有,并且数额较大的,便毫无疑问构成本罪,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例如某甲系私营企业主,因经营不善急需现金偿还银行贷款,就将自己价值200余万元的宝马小轿车以80万元低价卖出,但在银行办理还款手续中,才发现其中竟有70万元面额为50元的货币均为同号高仿假币。由于假币数量过多且银行没收假币之程序异常繁琐,银行一时间难以处理,加之与某甲长期形成的较为融洽的合作关系,银行工作人员便在每张假币上盖上“假币”之印戳后,将70万元假币交与某甲,并叮嘱其务必尽快销毁。某甲在烧毁60万假币之后,基于愤懑以及警示,将剩余10万元假币用胶水贴在公司财务室墙面上,并以此而告诫自己及员工。经人举报后案发,公安机关遂以非法持有假币罪将某甲控制。在本案中,仅从表面上来看,某甲之行为似乎和非法持有假币罪之构成要件极为吻合,但实质不然。刑法之所以设置非法持有假币罪,其立法意旨在于通过早期化处罚,防范假币被扩散到流通领域中从而实质性侵害“货币的真正性公共信用以及国家对货币的发行权”之法益。但在本案中,由于10万元假币已经被盖上“假币”之印戳,加之已被涂满胶水贴在墙上,无论如何也不能重返流通领域而对货币保护法益造成实质性侵害,故而,将某甲之行为认定为非法持有假币罪,将与本罪之立法意图大异其趣。因此,对于“假币上墙”案件,也只能作无罪化处理。⑨
此外,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第1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使用轻微暴力或者威胁,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随身携带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钱财数量不大,且未造成被害人轻微伤以上或者不敢正常到校学习、生活等危害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发生了多名15岁未成年人使用轻微暴力,强行向某体育学院在校研究生索要随身携带生活用品未果,反被该研究生当场制服之现象。对此,适法者不能想当然认为,既然该解释并未对未成年人使用轻微暴力向已成年学生索取财物的如何处理予以明确规定,因此,该行为仍然应当认定为抢劫罪。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该解释制定之初衷,即为贯彻落实“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以及“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因此,该解释之保护对象系实施轻微暴力取财的未成年人,而被害人是否属于未成年人,则无关紧要。另一方面,毋庸置疑的是,就社会危害而言,未成年人使用轻微暴力向未成年学生索要财物的行为远远大于未成年人使用轻微暴力向已成年学生索要财物的行为。质言之,既然社会危害较大的行为不认为是犯罪,而社会危险较小的类似行为,则更不必作为犯罪处理,否则将造成处罚上的实质不公平,还会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背道而驰。因此,对于未成年人使用轻微暴力强行索要成年人数额较小财物的行为,也不宜认定为抢劫罪。
因此,借助法益保护原则并结合刑法实质解释说,大致可以作出如下结论:尽管刑法第115条中确实包含“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但基于法益保护原则及刑法实质解释说,就应当对该条中的“公私财产”作出如下限制解释,⑩即该处的公私财产应当仅限于“与人身安全密切攸关的公私财产”。事实上,如果适法者不是对文义解释过于迷信的话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司法解释还是刑法理论层面,在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认定中,对“公私财产”所作的此种限制解释可谓俯仰皆是。例如,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只有在“实行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内”才能构成交通肇事罪(其法益为道路交通公共安全),之所以作出这一限制性条件,是因为在空无人烟的道路上,即便出于过失而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辆毁损,无论如何也不会对多数人的人身安全造成侵犯。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坏生产单位正在使用的电动机是否构成破坏电力设备罪问题的批复》(1993)中指出:“破坏电力设备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该罪所侵犯的客体,是社会的公共安全。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不具有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性质,不能构成该罪”。该司法解释之意图显然是为了准确区分破坏电力设备罪与破坏生产经营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财产犯罪之界限。再如,我国司法实践和刑法理论均没有争议地认为,破坏交通工具罪的行为对象必须是正在使用或者飞行中的交通工具。其原因不外于,只有破坏了使用或者飞行中的交通工具(即已经载上或者即将载上乘客或服务人员的交通工具),才会危及多数人的人身安全。因而,从刑法实质解释之立场出发,应当将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公私财产”(例如,刑法第115条的放火罪、爆炸罪、决水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所出现的“公私财产”)限定为“与人身安全密切攸关的公私财产”。
四、“人身安全说”符合刑法中的罪刑均衡原则
保护法益是刑法分则个罪设置之根本目的。由于不同法益在满足社会成员生存、发展需要的程度和价值方面必然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刑法对于不同类型的法益保护强度也应当迥然相异。毋容置疑的是,这种必然性差异也是罪刑均衡原则最本质之体现。在刑法所保护的各种法益中,包括生命、健康在内的人身安全无疑应当处于最为崇高之地位,而财产法益固然重要,但较之人身安全法益,则只能是刑法退而求其次的低位顺序选择。或简而言之,在任何情况下,人身安全都远比财产安全更为重要,也更值得倍加珍惜。任何财产,无论其价值多么庞大,都不能和人身安全相提并论。(11)因此,如果坚持罪刑均衡原则,刑法就应当对公私财产与多数人的生命与健康的保护区别对待,而不能一视同仁。假如适法者拘文牵义,过于信奉文义解释,固执己见地将公共安全保护法益之通说奉若神明,将与人身安全毫无牵连的单纯财产安全罗列入公共安全范围之内,则必然直接和罪刑均衡原则背道而驰。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刑法分则第2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除了上文所提及的第115条的放火罪、爆炸罪、决水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外,还包括破坏涉及交通工具、交通设施、电力设备、易燃易爆设备,以及盗窃、抢夺、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等犯罪,其最高法定刑均为死刑。而与之相较,刑法分则第5章破坏财产罪中,单纯毁损公私财物的行为,无论是按照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还是认定为破坏生产经营罪,其最高刑仅为7年有期徒刑。仅以在空旷之野外,放火烧毁无人居住的价值数亿元的高档别墅,并且火势也不会扩散之案件为例,如果依照本文所提倡之“人身安全说”,则应被认定为故意毁坏财物罪,根据刑法第275条的规定,其最高法定刑为7年以下有期徒刑;然而,如果依照通说之观点,则必然会构成放火罪,而根据刑法第115条的规定,则可能会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12)显然,在仅仅损害财产的情况下,如果将该行为认定为放火罪,将使行为人面对极端严厉之处罚,而这显然有失公正。同时,“如果说只要行为侵害了价值重大的财产就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那么,一方面,盗窃银行、博物馆并取得重大价值财物的行为,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另一方面,会出现大量的不协调现象:刑法只处罚故意毁坏财物罪,而过失毁损价值重大的财产时,反而成立危害公共安全罪;倘若说只要行为侵害了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财产就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那么,面向不特定或者多数人实施的集资诈骗行为,流窜盗窃多人财物的行为,都成立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也难以令人接受”。[5](P.323)因此,基于罪刑均衡原则,也应当认为,公共安全法益并不能包容与人身安全无关的纯粹性财产安全,否则会造成危害公共安全罪与侵犯财产罪的冲突,而由于两者处罚力度大相径庭,还会造成处罚上的实质不公平。
五、余论:刘襄案件以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滥用之反思
在刘襄案件中,河南省两级法院对未造成人员伤亡的食品安全事件责任人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这在全国尚属首例。本案虽然已经随着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之终审判决而尘埃落定,但案件中争议问题,尤其是刘襄等多名被告犯罪行为之定性,却决然不能因为案件的终审而就此偃旗息鼓。正如本案中刘襄辩护人所称:“被告人既没有企图报复社会的动机,也没有危害不特定人的身体健康的故意。他生产盐酸克伦特罗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他故意的内容就是明知国家禁止生产药品,药物肯定不能随便生产,但为了牟利而擅自生产,实际上这种药到底对人体有多大危害,我们公众都不知道,刘襄也和我们一样。”而事实上,正是因为在刘襄案中,公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的行为对公众的人身安全已然造成实质侵害,无法认定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加重处罚情节,也不能因此而对被告人适用重刑。(13)因而才不得退而求其次,为追求严刑峻法的审判效果,只能以所谓的“重大财产损失”为依据,祭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大口袋,将刘襄等人囊入其中,并最终对刘襄适用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但依照本文所提出的“人身安全说”,则不难断定,刘襄等人固然有罪,但在本案中却断然不能仅依从所谓“数额特别巨大的纯粹性财产损失”,而将该案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实害犯,而使刘襄等人承受原不应有之刑罚。在此,本文并不否认瘦肉精之客观危害。在刘襄案审理中,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曾复函证实,瘦肉精能引起急性中毒和慢性中毒。急性中毒一般表现为四肢震颤、肌肉酸痛、头疼、头晕、多汗、胸闷、心悸等。长期慢性中毒可引发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疾病,致染色体畸变,导致胎儿致畸。但该份复函仅能证明,人食用含有瘦肉精的肉制品具有潜在致害风险,因此在没有造成实质性人员伤亡的情况下,仅能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危险犯”而已,并仅应在3至10年有期徒刑之范围内对刘襄确定宣告刑。(14)而河南省两级法院之所以作出如此错误之裁判,其原因无外乎案件的裁判者不是“循名责实”地根据法益保护原则对刑法第115条中的“公私财产”进行实质解释,而是“望文生义”地理解法条,从而对公共安全之保护法益作出误读和误断。进而言之,本案所谓的“全国首例”绝非是具有开风气之先的精品审判标杆,而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危险判例,而以“危害公共安全”之定罪路径向全国推广食品犯罪处罚模式,更无异于以讹传讹,隐患良多。(15)
同时,刘襄案之判决还流露出司法实践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滥用之反常倾向。我国各地的刑事判例中,“在禁猎区设置‘千斤砸’等大威力捕猎工具而误伤他人的、投放普通传染病病菌(并非艾滋病或者其他致命性病菌)的、在非机动车道上盗窃窨井盖的,都无一例外地被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另外,公交车上盗窃后为了下车而急踩刹车致人重伤的行为、碰瓷行为、菜农贩卖喷洒过敌敌畏的蔬菜致人死亡的行为、在非食用动物的饲料里添加激素类药物的行为,甚至生产、销售添加剂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也往往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罚”。[23](P.110)在这些案件中,只要裁判者认定存在着所谓的“置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生命和财产安全于不顾”,或者“足以危及到其他不特定的多数人的人身或财产安全”之情节,便均会以本罪处理。如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已经沦为刑法中最受司法机关青睐的三大口袋罪之一,(16)而本罪也日益面临着被泛化的现实危险。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但凡是社会上新出现的,在刑法中难以准确找到对应条文的但是又应当处理的行为,只要稍稍危及“多数人的人身或财产安全”,都可以被司法机关大笔一挥而作为本罪处理。事实上,鉴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极度之模糊性罪状和异常严厉之法定刑,(17)再联想到该罪在司法实践中的极度扩张,以及肆意张开大口袋时的蛮横与恐怖,不由得让人毛骨悚然。诚如有学者所言:“纯粹一般式的规范或包含模糊因素的规范对法律规范明确性的消极影响,则表现为法律规范没有具体或确定的内容,因而可能被适用于性质不同的行为。”[24](P.26)而正是因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相对模糊之罪状表述,加之重刑主义刑罚观之影响,司法机关有意无意地误将社会危害明显较为轻微的财产犯罪或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认定为本罪的情况一再发生,而刘襄案之判决,就是有力之明证。司法机关如果能够从中及时汲取经验教训,恪守刑法实质解释之方法,采取“人身安全说”之立场,对公共安全之法益范围作出合理而精准之界定,从而防止出现该罪被漫无边际地滥用危险,无疑是功莫大焉,善莫大焉。
注释:
①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公诉机关并无证据事实予以证明“已经对人身安全造成严重危害”,因而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等两级法院的判决书中对此问题或者是闪烁其词,或者是讳莫如深。
②本案之案情可参见,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告人刘襄等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案的一审刑事判决书”,文书号:(2011)焦刑二初字第9号,以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被告人刘襄等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案的二审刑事裁定书”,文书号:(2011)豫法刑一终字第137号。
③本案之案情可参见,河南省获嘉县人民法院“被告人韩文斌等人非法经营一案的一审刑事判决书”,文书号:(2011)获刑初字第121号。
④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中也认可了公诉人所提出的此证据事实。
⑤仅以福尔马林为例,其是一种慢性中毒药物。长期接触低剂量的福尔马林会引起慢性呼吸道疾病、女性月经紊乱、新生儿体质降低甚至鼻咽癌等病症。另外,高浓度的福尔马林对神经系统、免疫系统、肝脏等都有强烈的毒害作用。
⑥另外,从药品流通实践来看,某些基层医疗机构,由于地处偏僻,在采购某些非常规的零星药品时,或者在批发商临时供货不足时,为了让患者及时用药,就近从零售药店少量购进药品,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并且,《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规定药品零售商的质量控制要点是确保消费者合理安全用药。而毋庸置疑的是,医院等卫生医疗机构显然会比零售药店以及普通患者更能够合理安全用药。因此,对这种现象予以禁止甚至处罚,虽然有着法律上的依据,但却没有现实必要性。
⑦猫头鹰属于鸮形目鸟类,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根据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购买1只即可构成非法收购珍贵野生动物罪。
⑧对本案之详情可参见,“博士向动物贩子购猫头鹰放生,林业局称其违法”,http://news.sina.com.cn/s/2012-10-20/040925398471.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3-01-06。
⑨同样的道理,本文认为,基于刑法实质解释说,将枪膛中灌满滚烫的铅水而致使枪膛永久性堵塞,从而彻底丧失发射功能之枪支,已然不属于刑法枪支犯罪中的“枪支”。如果将其用于收藏而持有,亦不会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另外,将火药粉中添加面粉或者沙尘,由于火药、面粉及沙尘颗粒微小且体积相同,一旦混同将无法区分,并因此而会使得火药丧失爆炸能力的,亦不能将该火药视为刑法中的“爆炸物”;再如,对于放置在公园或者游乐场中的仅作观赏用途的退役军用飞机,因为该飞机已被永久报废而无法继续载人飞行,亦不能被视为刑法中的“交通工具”。
⑩限制解释是指将法条的字面含义作限制范围的解释,即解释的内容较之法条的字面含义范围为小,从而避免严格依照法条字面意义所有可能导致的某种不合理现象出现。一般认为,在刑法中,较为典型的限制解释存在于第29条。该条规定:“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从字义上看,不满18周岁的包括不满14周岁的人,但不满14周岁的人的危害行为不构成犯罪,因而教唆者不属于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构成间接正犯。因此,这里的“不满18周岁的人”应限制解释为“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唯其如此,才符合立法原意。
(11)这也可以解释,在紧急避险中消防队员可以不惜将整栋楼房拆除而拯救濒临死亡的火灾幸存者,而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因此,在财产法益和人身法益之权衡中,后者永远居于道义和法律之最高点,不容有任何质疑。
(12)例如,刘襄案中的财产损失为1.6亿,其最终判决即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3)依据刑法第144条及141条之规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只有在“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才能够适用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4)与刘襄案相对应的是,在“三鹿奶粉”案中,被告人张玉军虽然因制售含三聚氰胺“蛋白粉”而被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实害犯,并被判处死刑。但“三鹿奶粉”案导致众多婴幼儿因食用含三聚氰胺的婴幼儿奶粉引发泌尿系统疾患,多名婴幼儿死亡。因此,在重大人员伤亡结果已然发生的情况下,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玉军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实害犯,自然也是无可厚非的。
(15)令人欣慰的是,2011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瘦肉精”案、“毒奶粉”案、“染色馒头”案、王二团等玩忽职守案等4起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其中,只有刘襄案件被定性为危害公共安全之犯罪。而在2013年浙江温岭市涉46人特大产销病死猪肉案中,司法机关在缴获的大批病死猪肉肉制品中,检出了奇异变形杆菌、副溶血性弧菌等,并检出菌落总数严重超标,经危害性评估认定,人食用后可能导致严重的食物中毒或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仅从医学角度而言,这些病死猪肉及其肉制品对人体健康之危害并不亚于瘦肉精,但是在本案中,浙江温岭市人民法院2013年3月12日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兴兵等被告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猪肉和猪肉制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其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并判处主犯张兴兵有期徒刑6年6个月。较之刘襄案件,在张兴兵案件中,浙江温岭市人民法院应更为妥帖适当。
(16)另外两个是非法经营罪和寻衅滋事罪。
(17)在此,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本罪罪状缺乏对行为自然性质的描述,只有纯规范性、依赖价值判断的描述。因此,认定本罪从一开始就必须进行实质判断,不仅需要借助其他罪名判断本罪的实行行为,而且本罪的成立更需要依赖法益侵害、社会危害性等本属于犯罪概念领域的概念。对此可参见,高艳东:《谨慎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危险相当性》,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5期。正基于此,对于本罪之司法认定,更应当坚持刑法实质解释之立场,适用“人身安全说”,对某一具体行为有无对公共安全法益造成侵害进行实质性判断。
标签:瘦肉精论文; 公共安全论文; 财产安全论文;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刑法理论论文; 法律论文; 构成要件要素论文; 犯罪构成要件论文; 食品生产论文; 药品生产论文; 刑法基本原则论文; 野生动物保护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