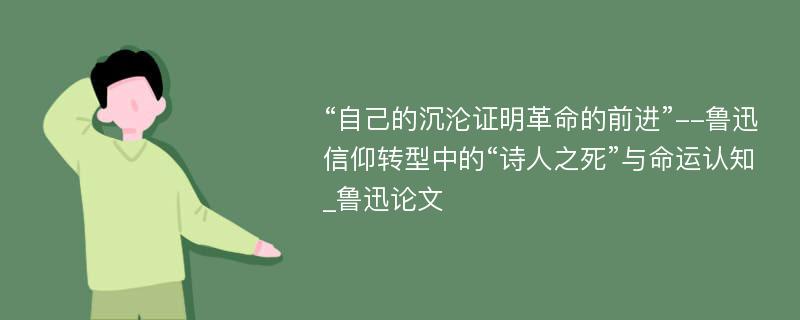
“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诗人之死”与鲁迅信仰转换中的命运认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己的论文,鲁迅论文,之死论文,认知论文,诗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确立一种信仰,就是把自己未来不可知的命运交付给一个可知而可信的对象,因而,信仰从本质上说就是主体关于自我命运的一种自觉认知。信仰的力度,往往也直接体现在信仰者对自我命运认知的深度。这种深度当然不是观念性的,而是血肉性的,越是浸润在血肉深层的命运体验,越能唤起、激发信仰的生命强力。鲁迅曾经用两个非常形象的词汇来形容自己信仰构成的这种血肉体验,一个是“轰毁”,由轰毁以至断裂,由断裂以至转型,由转型以至新生,“轰毁”一词本身具有的形态感概括了鲁迅信仰转变的过程特点;另一个是“煮”,在“革命文学”论战中,鲁迅读了一些包括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文艺论著,用这些理论的火“煮”自己的肉,在自我解剖与反省中由进化论进到阶级论。毫无疑问,“轰毁”也好,“煮”也好,这种文学性的描写语言,说的都是肉体生命的感觉,显示出的是鲁迅在信仰构成中对信仰本身的血肉性的重视。在鲁迅看来,信仰的建构不仅仅是精神的飞扬,也相关着信仰者的肉身的献祭以及自我生命的命运的托付。在历史上,有些信仰者其信仰强大到具有足够的力量引导肉身共同前行,但也有许多时候肉身的巨大惰性成为信仰者精神前行的巨大包袱。信仰实践中精神与肉身的合体性,这是鲁迅坚守的一个生命准则,所追求的一种生命境界。正是在这种坚守与追求中,后期鲁迅曾经对无产阶级文学发展史上的一种生命现象有点痴迷,这就是革命文学兴起后接二连三地出现的“诗人之死”现象。面对这一现象,鲁迅有过强烈的心灵撼动,有过深刻的理性分析,并且最终在这种强烈的心灵撼动与深刻的理性分析中,完成了一个革命前驱者自我命运的认知与担当。 本文所谓“诗人之死”,特指俄罗斯“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界出现的一种现象。有些诗人,在革命兴起时,热情洋溢地投向革命,讴歌革命,甚至成为革命的号手。但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国家与民族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些曾经为革命欢呼歌唱的诗人们反而对革命的成果深深失望,对自己在革命政权下的生活失去信心与希望,最后或者在“活不下去了”(梭波里)的叹息中,或者在“一点办法都没有”(马雅可夫斯基)的决绝中,用自杀的形式结束自己的肉体生命与诗歌生命。叶赛宁如此,梭波里如此,后来的马雅可夫斯基也是如此。勃洛克因病死在四十出头的壮年,他死时已经对自己的生活与曾经的诗歌生涯感到绝望,而那些一向攻击苏俄革命文学的西方媒体也在拿勃洛克的病说事,如《法国水星杂志》(Mercure de France)就刊登弥里士考夫斯基的看法,认为“坏血症”是“左党政治下的智识阶级中人的应有病”,似乎暗指勃洛克的致命的“坏血症”不仅是生理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生理上的“坏血症”剥夺了他的肉体生命,而精神上的“坏血症”则剥夺了他的诗歌生命。如果说,在革命兴起时,勃洛克是“从人文主义变迁的历程感受俄国文化变革和社会制度变革的必然性,可能性,呼唤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理解革命”,那么,革命后的勃洛克则是“从理想人文主义角度,质疑、悔恨甚至反对现实中的许多有悖于民族文化建设、破坏人文精神建构的革命行为”①。所以,勃洛克虽然不是死于自杀,但是他在逝世前一段时期的精神绝望,对革命现实中的一些行为的“质疑、悔恨甚至反对”,其实也已经意味着作为革命歌手的诗人已死。 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原因是什么,迄今仍然有争议。诗人死后,苏共中央与“拉普”为了避免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极力把这次事件淡化为个人生活中的“失恋”事件。但即使在当时,从“拉普”写给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的信中也可看到,苏联文艺界对诗人的自杀原因有不同的看法。这封信指出,“对诗人自杀的原因的解释被敌人利用了,因此出现种种谣言,说‘共产党员们藏匿了’马雅可夫斯基的真正的信件(即‘第二封’信),说什么诗人对一切都失望了,他被那忌贤妒能的苏维埃政权扼杀了。在青年人之间出现了这样的情绪:如果马雅可夫斯基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榜样,‘同工人阶级保持紧密联系’的诗人都自杀的话,那我们这些平庸的人该怎么办?一些怀恨在心的人则公开宣称:‘马雅可夫斯基一生都在撒谎,终于没词儿了,所以就自杀了’”②。这些意见不管是同情的还是攻击的,显然都是在精神与诗学的层面上来解读诗人的自杀,没有把这一事件简单地归之于诗人的“失恋”。马雅可夫斯基的死在中国文坛也曾引起震动,不论左翼还是非左翼刊物,都曾报道其自杀消息。《现代文学》杂志1930年第1卷第4期上还曾编辑出版一个纪念特辑,其中刊发了马雅可夫斯基的新作诗一首、戴望舒翻译的法国奥古斯坦·阿巴库(A.Habaru)作的《玛耶阔夫司基》、杜衡翻译的梅吉尔(A.B.Magil)作《玛耶阔夫司基》、毛翰哥翻译的杉本良吉作《玛耶阔夫司基的葬式》、赵景深翻译的拉莎洛夫作的《玛雅阔夫司基的自杀》等外国文坛的报道评论,还有谷非作《玛耶阔夫司基死了以后》、陆立之作《玛耶阔夫司基底诗》、杨昌溪作《玛耶阔夫司基论》等论文。很有意味的是,这个专辑中的译文和评论都没有迎合社会读者的兴趣去渲染马雅可夫斯基自杀的“失恋”事件,而是将关注点侧重在挖掘这一“诗人之死”事件背后的诗学意义与精神启示。如奥古斯坦·阿巴库说:“自从革命底斗争时代一终结,他的诗的兴感就死了,在以后的建设的过程中,他的诗便失去了气势了。当然,玛耶阔夫司基还写,还写得很多,可是他只给我们一些使他跌到节米扬·白德芮(Demian Bedny)、或保尔·台鲁莱德(Paul Delouled)一流的宣传诗了。”杨昌溪的论文则指出马雅可夫斯基死于诗歌实验的失败,他说:“他不愿作艺术的说教者,而他把他整个的艺术都呈现给革命驱使。他以自己的人格充满革命的场所,广场和街衢,在或种的限度上打破个性底限制而接近于集团,使集团成为革命的集团。他从旧时代的艺术而到狂放之士底未来派的时代,更由衰落的未来派而到烈夫派(左翼),在12年来他都在文坛上不绝地实验着他底艺术,这次的自杀就是他以身殉艺术的表征。虽然他不是纯粹的普罗列塔利亚诗人,然而在工人们所加于他底‘革命诗人玛雅阔夫司基’的称号是值得配上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赵景深翻译的拉莎洛夫的文章,这是一篇专门探讨诗人自杀原因的文章,作者不仅将叶赛宁、梭波里的自杀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相提并论,而且专门对所谓“失恋”论进行了驳斥。文章说:“爱的解释是不能使人信服的。只要想一想过于傲慢的玛雅阔夫司基,他的对于恋爱的态度是革命的,他自己也宣言他的放荡,便知道他要是为了一个难近的妇人而自杀,是犹之于一个常态的人为了吞一块不容易消化的食物而自杀是一样的不容易。即使他的‘不幸的恋爱’不完全是谣言,人家也知道这决不是自杀的唯一的原因,显然还有政治和群众的原因。”从这些翻译的和自作的文章中,不难看出国内文坛(当然包括左翼文坛在内)对于马雅可夫斯基之死的一般性认知。 鲁迅对上述苏俄诗人及其命运是熟悉的。1926年至1930年间,鲁迅曾细致地阅读过勃洛克的作品,并且为胡斅译的《十二个》写过序言;在理论上他曾阅读过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以及其他一些苏俄文学的评论文章,而且翻译过其中的一些著作与篇什,如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中的勃洛克专章等。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中对十月革命前后一段时间的俄罗斯文学有十分精彩的评论,尤其是对叶赛宁和勃洛克等俄罗斯诗人热情地投身革命但在革命胜利后又失望于革命的现象,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和深刻的剖析,关注的焦点则在于旧的诗人如何在新旧时代交替时不仅讴歌新时代而且融入新时代。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之时,鲁迅被新兴作家们打上旧时代作家的代表人物的徽号,对此,鲁迅并不否认,甚至以此自豪。鲁迅所讨厌的是那种“唯我独革”的嘴脸,是那种关起门来“革命”拒绝同路人跟着走的激进态度。鲁迅深知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新旧转换而新生未生、旧的未去的时代,自己的旧的信仰确实被血淋淋的现实所轰毁,自己愿意追随新的时代前行。但正如鲁迅当年在S会馆里同钱玄同对话时的心态,对于旧的,自己的信念是坚定的,但新的属于未来,未来的事物对于每一个前行者而言都是未知数。虽然自己不能以自己的确信折杀了未来,但对甘心情愿追随时代前行的自己的未来将是一个什么状况,这是鲁迅这种所谓“生性多疑”、喜欢刨根究底的人所必要弄明白的。所以,作为一个愿意追随时代前行的旧时代的代表者,鲁迅不能不深切地关注在时代大潮中那些自愿前行的旧时代代表者的命运,这也许就是在“革命文学”论战中,尽管当时由苏俄传入的理论资源多种多样③,但仅仅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等理论家和叶赛宁、勃洛克等俄罗斯曾经的“革命诗人”特别使鲁迅感到兴趣的原因。而且可以说,正是叶赛宁、梭波里、勃洛克以及后来的马雅可夫斯基的死亡这一非常态现象,深深地震撼了鲁迅的心灵,鲁迅曾说:“‘在一个最大的社会改变的时代,文学家不能做旁观者。’但拉狄克的话,是为了叶遂宁和梭波里的自杀而发的。他那一篇《无家可归的艺术家》译载在一种期刊上时,曾经使我发生过暂时的思索。”④这种表述虽然语气平静,但确实证实了叶赛宁、梭波里的自杀促使信仰转换中的鲁迅对“革命时代”、“革命文学”、革命文学家的历史宿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得出了自己与众不同但发人深省的结论。 革命时代是一种大时代,激动人心的时代。伟大的诗人往往有一颗永不安分、永远冒险的灵魂,厌恶平庸、刻板、没有惊涛骇浪的生活。那些旧时代的诗人们之所以投奔革命,向往的其实就是革命时代剧烈动荡与变化的大气魄、大精神。勃洛克曾经对“革命”做过这样的定义:“改造一切。力图使一切变得崭新起来:使我们那虚伪的、污秽的、苦闷的、不成体统的生活变成公正的、纯洁的、愉快而美丽的生活。”“这类想法自古以来就深藏在人类灵魂与人类心灵之中,当它们挣脱束缚自己的桎梏并以汹涌澎湃的洪流摧毁大坝,冲决无用的堤岸时,这就称之为革命。规模较小,程度适中或者层次更低级的现象——被称之为骚乱,造反和变革。但是,这被称之为革命。”⑤鲁迅也曾用力度的“大”和“小”来划分“革命”的时代。1927年4月8日,鲁迅应邀到广州黄埔军官学校讲演“革命时代的文学”。在谈到“革命”与“文学”的关系时,鲁迅很风趣地用猴子进化到人类的故事做比喻,说明“革命是并不稀奇的,凡是至今还未灭亡的民族,还都天天在努力革命,虽然往往不过是小革命”。至于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则明确地指出“在革命时代的文学和平时的文学不同,革命来了,文学就变换色彩。但大革命可以变换文学的色彩,小革命却不,因为不算什么革命,所以不能变换文学的色彩”。在鲁迅心目中,当时广州的“革命”其规模和力度还不是真正的“革命”,至多也只能是“小革命”,因为它并“不能变换文学的色彩”。鲁迅接着直截地批评广东的文学形势,指出“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不但如此,并且也没有叫苦,没有鸣不平;止看见工会参加游行,但这是政府允许的,不是因压迫而反抗的,也不过是奉旨革命。中国社会没有改变,所以没有怀旧的哀词,也没有崭新的进行曲”⑥。可见,鲁迅尽管身处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又在“革命”骨干力量的培养学校做演讲,但他并未忌讳言说自己对当时广州已经十分热闹了的所谓“革命”的观感与思考,这种关于革命规模、力度乃至性质的“大”与“小”的思辨,显然是从勃洛克那里得到了启示。 在这个讲演中,鲁迅表面上谈的是文学,其实表达的是他透过“革命文学”的诞生所得到的对“革命”的理解,这一点对观察鲁迅思想或者后期信仰的转换最有意义。鲁迅认为革命与文学有三种关系,三个阶段:“大革命”之前,没有“革命文学”,有的是“叫苦鸣不平的文学”;“大革命”之中也没有“革命文学”,因为“到了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没有声音了”,“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荡,大家由呼喊而转入行动,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大革命”以后才有“革命文学”。“等到大革命成功后,社会底状态缓和了,大家底生活余裕了,这时候又产生文学。”“这时候的文学有二,一种文学是赞扬革命,称颂革命,另有一种文学是吊旧社会的灭亡——挽歌——也是革命后会有的文学”⑦。鲁迅关于“革命文学”产生的条件与机缘的观点是否妥当,姑且不论,在此应该关注的是,在鲁迅的心目中,何谓“大革命”?在谈到“大革命”前的“叫苦鸣不平的文学”时,鲁迅指出这种文学有两种发展趋向,一种是叫苦无用就沉默下去,甚至渐渐更加衰颓下去,如埃及、阿拉伯、波斯和印度,一种是那些“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他们已经很愤怒,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复仇。苏俄革命将起时,即有些这类的文学”。后来在谈到第三个阶段即“大革命成功后”所产生的那两种文学时,鲁迅更是明确地将中国与苏俄相提并论,“不过中国没有这两种文学——对旧制度挽歌,对新制度讴歌;因为中国革命还没有成功,正是青黄不接,忙于革命的时候”,“中国社会没有改变,所以没有怀旧的哀词,也没有崭新的进行曲”。但是,“苏俄却已产生了这两种文学。他们的旧文学家逃亡外国,所作的文学,多是吊亡挽旧的哀词,新文学家则正在努力向前走,伟大的作品虽然还没有,但是新作品已不少,他们已经离开怒吼时期而过渡到讴歌的时期了”⑧。讲到大革命兴起前的“怒吼的文学”是以苏俄革命前的文学作为例子,谈到大革命成功后的“革命文学”仍然是以苏俄革命后的文学作为例子,可见,在鲁迅的心目中,所谓的“大革命”就是苏俄式的革命,反过来也就是说,只有苏俄式的“革命”才能配称得上是“大革命”。所以,勃洛克曾引用丘特切夫的诗句来欢呼“我们俄罗斯人正在经历一个无与伦比的伟大时代”⑨,而鲁迅在谈到勃洛克与苏俄革命的关系时,也特别突出的是苏俄革命的规模、力度与性质的“大”。他认为“勃洛克独在革命的俄国中,倾听‘咆哮狞猛,吐着长太息的破坏的音乐’。他听到黑夜白雪间的风,老女人的哀怨,教士和富翁和太太的彷徨,会议中的讲嫖钱,复仇的歌和枪声,卡基卡的血。然而他又听到癞皮狗似的旧世界,他向革命这边突进了”⑩。 但是,“大革命”呈现给诗人的不会只是丘特切夫诗歌中所欢呼的“宴会的盛大场面”,“大革命”的声音是“咆哮狞猛”的“破坏的音乐”,是“复仇的歌和枪声”。在这样的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时代,每一个与革命发生关系的人,都可能有新生与猝死两种命运。对此,鲁迅有着极其透彻的见地。1927年12月,他在给黎锦明的中篇小说《尘影》做的序言中开篇就说:“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许多为爱的献身者,已经由此得死。在其先,玩着意中而且意外的血的游戏,以愉快和满意,以及单是好看和热闹,赠给身在局内而旁观的人们,但同时也给若干人以重压。”“这重压除去的时候,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11)破坏的目的是为了建设,革命的理想当然是为了更好的“生”,但鲁迅在此谈“大革命”时代的生与死,显然意在突出和强调“死”的前景与结局,尤其是那些投身革命的“革命文学”家的“死”的前景与结局。这种思路的发生,一方面当然是因为鲁迅深知,革命文学家的攻击社会,必得攻击革命的对象,而革命的对象是具体的,是有力量的,因而革命诗人就得面临危险。鲁迅在《答有恒先生》的文章中曾说:“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试一攻击社会的一分子的陈源之类,看如何?而况四万万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12)另一方面,叶赛宁、梭波里的自杀事件以及后来的勃洛克的消沉态度深深地刺激着鲁迅,让鲁迅意识到了像他这类从旧的阶级中投向革命的“革命诗人”们无可回避的一种历史宿命,也就是鲁迅自己所说的,“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13)。 这种命运意识,在苏俄革命爆发时期的俄罗斯诗人中其实是相当普遍而典型的。俄罗斯思想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曾用大地漫游者来形容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特征,他认为:“在俄罗斯的灵魂中,存在着动荡与不驯,存在着一切暂时的、相对的、有条件的事物都难以消除的贪婪和不满。”(14)作为民族灵魂的俄罗斯诗人,这种漫游者气质当然更加突出。浪漫的俄罗斯诗人,天生地会对革命充满了幻想与激情,因为在“革命这一种打扫的行动中,有一种无限制的前进的趋势,鼓荡着人类要求解放的热情,诗人可于浪潮中听出令人欢畅的音乐,看出革命的心灵”。“革命是人类历史的道上的胜利日,也是悲剧日,是一篇史诗”(15),诗人的激荡不已的心灵恰恰能够在这种胜利日与悲剧日中得到宣泄,获得狂欢。但是,革命必然有破坏,不仅会破坏诗人憎恨的东西,也会破坏诗人心爱的东西,正如勃洛克在《知识分子与革命》中对那些知识分子的诘问:“你们曾经考虑过些什么?革命等于田园诗?在革命的道路上创造不会毁坏任何东西?人民是听话的乖孩子吗?”“‘黑骨头’和‘白骨头’、有文化教养的人和没有文化教养的人之间,知识分子和人民之间由来已久的纷争,这样‘没有流血地’和‘没有痛苦地’就可以解决吗?”(16)显然不是。正由于意识到了或者说亲眼见到了这种破坏,勃洛克“他向前,所以向革命突进了,然而反顾,于是受伤”(17)。而叶赛宁说:“他能领受一切,他可以将灵魂都交给红色的10月和5月,但只有一张亲爱的鸣琴不愿给与任何人的手里,因为他要这张鸣琴仅仅为他歌吟,细腻地歌吟。”(18)当革命要求他交出这把鸣琴,或者要砸烂他的鸣琴的时候,诗人的心伤就是可想而知的了。更进一步说,革命虽然是狂欢日,但“进化是和平的时日,是无风浪的散文。革命后要渐渐地走到进化的路上,要发展到自身的第二阶段。在此第二阶段,破坏的风浪要让位置于和平的建设,所谓理性和计划登了表面的舞台,而所谓革命的心灵不得不隐藏到自身的深处。到此时,我们的诗人,我们的罗曼蒂克,失去了兴趣,心灵上起了很难过的波纹”。所以,蒋光慈曾将勃洛克的痛苦归因于对感觉中的革命的“停顿”的失望与困惑。“布洛克现在所以发生痛苦的,是因为革命,照着他的感觉,似乎走到半路停下来了,不能满足自己的无限制的态度。”(19)这种解读确实是切中了问题的实质。对于诗人投身革命后的这种必然的两难处境,这种历史宿命,勃洛克有着深切的预感,他虽然没有像叶赛宁那样自杀,但他在投身革命时就已经宣示了自己的命运:“正是那个果戈理把俄罗斯想象成是飞驰的三套车。”“我们年复一年越来越清晰地听到的那个音量迅速增大的嘈杂声,就是三套车铃铛那神奇的叮叮当当声。在三套车周围是‘阵阵气流发出的呼啸声,而且这气流变成了风’,如果这辆三套车直向我们飞驰而来,那会怎样呢?我们奔向人民,即直接扑向疯狂的三套车的车轮下、直接奔向必然的死亡。”(20)敢不敢扑向车轮,这是时代对诗人的考验;能不能碾碎诗人的罗曼蒂克幻想,这是历史对革命的考验。鲁迅在勃洛克的诗歌中感知到了这个运命。 在一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里,诗人的自杀,尤其是“革命诗人”的自杀绝不是一个日常事件,而是一个信仰事件。诗人是信仰的描摹者,鼓吹者,讴歌者,人们往往不是在政治家的演说中,而是在诗人的吟唱中感受到信仰的美好,体验到信仰的力量。所以那些伟大的诗人在这份使命的鼓舞下,一旦发现自己坚信的理想与自己生存其中的现实相悖离时,宁愿自己碰死在自己的信仰上,也绝不会去修正信仰,或者背叛信仰,像一个常人那样苟活下去。比较而言,俄罗斯民族是一个以信仰而骄傲的民族,诗人丘切特夫就曾这样评价过他的俄罗斯:“俄罗斯并非理智可以悟解/普通的尺度无法对之衡量/它具有的是特殊的性格——/唯一适用于俄罗斯的是信仰。”(21)确实,俄罗斯的“诗人之死”绝非“理智”的结果,也超越于“普通的尺度”之外,领悟这种事件只有从信仰和信仰者的命运承担这一角度,才能深得其中三昧。 鲁迅显然是从信仰的意义上来看待叶赛宁、梭波里的“诗人之死”的。在这段时间里,鲁迅曾不断地提到“革命人”、“革命文学”、“革命文学家”这三个概念。对这三个概念的理解,过去一直比较粗略,仅认为鲁迅在此只是想说明“革命文学”的产生须先有“革命人”的产生,文学家要创作出“革命文学”,须先成其为一个“革命人”。这种解读当然没有问题,鲁迅所谓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的名言,确实是明确地指向这层意义。但是,如果更深层地来思考,不难发现鲁迅这三个概念的使用还有着更为精微的含义。“革命人”是“革命文学家”(在有的地方鲁迅也称之为“革命诗人”)的基础,二者的不同在于,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革命人”无须整天把革命信仰挂在嘴边,“革命人”当然必须是“理想主义者”,但“革命人”也往往表现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甚至在一些特殊的情境中为了革命的成功,可以修正或者掩盖自己的信仰。而“革命文学家”的革命工作就在于革命信仰的宣传与讴歌,信仰是他们生命的基石与内容。所以,鲁迅在谈到“革命文学家”的概念时,有时是十分敬重的,如他说叶赛宁和梭波里,“俄国十月革命时,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革命尽力。但事实的狂风,终于转得他们手足无措。显明的例是诗人叶遂宁的自杀,还有小说家梭波里,他最后的话是:‘活不下去了’。”“叶遂宁和梭波里终于不是革命文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俄国是实在在革命。”又如他说勃洛克,“然而他究竟不是新兴的革命诗人,于是虽然突进,却终于受伤,他在十二个之前,看见了戴着白玫瑰花圈的耶稣基督”,“但这正是俄国十月革命‘时代的最重要的作品’”。有时说起时则显然是一种嘲讽的口吻,如他对当时创、太两社中那些“革命文学”倡导者的评论,“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22)。“不远总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现在创造派的革命文学家和无产阶级作家虽然不得已而玩着‘艺术的武器’,而有着‘武器的艺术’的非革命武学家也玩起这玩意儿来,有几种笑眯眯的期刊便是这。他们自己也不大相信手里的‘武器的艺术’了罢”(23)。敬重是因为,叶赛宁、梭波里、勃洛克们虽然还不是“革命文学家”,他们没有真正地投身革命的实践中去作“革命人”,但他们忠诚于自己的信仰,并且在向着革命的潮流“突进”,尤其是他们要“突进”的是真正的大时代与大革命;而嘲讽的则是,在中国,真正的大时代、大革命还没有到来,“革命人”还没有尝试去做,自封的“革命文学家”们就急急忙忙地宣称“革命文学”已经到来了。而这种“革命文学”无论是“奉旨革命”,还是“赋得革命”,就像鲁迅曾经批评过的,要么“是刊物的封面上画一个工人,手捏铁铲或鹤嘴锹,文中有‘革命!革命!’‘打倒!打倒!’者”,要么就是“画一个少年军人拿旗骑在马上,里面‘严办!严办!’”(24)之类。 所以,在与那些自封的“革命文学家”们论战时,鲁迅曾向他们提出了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成仿吾教人克服小资产阶级根性,拉‘大众’来作‘给与’和‘维持’的材料,文章完了,却正留下一个不小的问题:倘若难于‘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呢?”(25)鲁迅之所以这样提问,是有他的理由的。第一个理由当然是未来的事本来未可预料,所谓“最后的胜利”谁能确切地保障?当时“大革命”尚未到来,前景就更加渺茫,何况革命中间还会有流血,有牺牲。第二个理由更加确切,叶赛宁、梭波里、勃洛克等投身革命的诗人已经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而真正的大革命、大时代也确实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那些希望一个晚上就能“奥伏赫变”成为无产阶级作家的文学家们是否能有勃洛克们这种气魄,这种真诚,明知道直接扑向疯狂的三套车的车轮下就是直接奔向必然的死亡,但他们还是奔向了人民?是否能够像叶赛宁和梭波里那样,“他们先后给自己唱了挽歌,他们有真实。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26)。带着这样的疑问,鲁迅在“革命文学”论战中,思路与其对手们颇有点不同,他不太关心革命文学的内容、性质、对象等理论性的问题,而是关心两个互相连带着的问题。一个问题是作家是否真诚。鲁迅十分赞赏勃洛克,就因为他对“大革命”有“真的神往的心”,“呼唤血与火的,咏叹酒与女人的,赏味幽林和秋月的,都要真的神往的心,否则一样是空洞。人多是生命之川之中的一滴,承着过去,向着未来,倘不是真的特出到异乎寻常的,便都不免并含着向前和反顾。诗《十二个》里就可以看见这样的心”(27)。他批评广东的所谓“革命文学”,想到的也是这“革命文学”是否是“心中流露的东西”。“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28)。另一个问题则是反对投机。鄙薄与反对投机,这是鲁迅一贯的性格与主张。在后期信仰的转型与建构中,鲁迅的这一性格和主张体现得更加显著。他在谈到文学家与革命的关系时曾告诫人们,“外国是革命军兴以前,就有被迫出国的卢梭,流放极边的珂罗连珂”(29)。他在谈到革命中的牺牲时也说:“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这并非指赤化,任何主义的革命都如此。但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倘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虽是投机,成败之数也不能预卜的。”(30)所以,鲁迅赞美革命家的牺牲:“革命成功的时候,革命家死掉了,却能每年给生存的大家以热闹,甚而至于欢欣鼓舞。唯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同时也指出:“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不过,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而赏玩、攀折,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31)这两个问题的中心点其实就是投身革命的动机如何,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还是看到了前景的诱惑? 当然,提出这样的问题,鲁迅并非是要与那些自封的“革命文学家”们刻意为难。正如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是为了“煮自己的肉”一样,鲁迅提出这样的问题,根底里还是为了检测自己的内心,还是要做出自己的回答。鲁迅在自我信仰转型时期,不断地提到叶赛宁、梭波里的死亡,提到勃洛克的“突进”与“受伤”,不断地告诫人们真正的革命有流血、有污秽,从这些现象上可以看到,鲁迅自己的回答是十分明确的。可以这样说,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鲁迅看到了“大时代”与“大革命”的即将到来,所以他说:“现在则已是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中国以外,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倘要将自己从没落救出,当然应该向他们去了。”(32)而苏俄十月革命前后一段时期苏俄文坛上的“诗人之死”现象,也使鲁迅深切地预感到自己这一类知识者的献祭的运命。鲁迅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选择了献祭,哪怕是要“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如果说绍兴会馆里,鲁迅听从朋友的力劝投入到新文化运动中去,是在绝望中的对绝望的反抗,那么,1927年前后一段时期的鲁迅在轰毁了自己原来的进化论信仰之后,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的战士,从一个个性主义者进到集体主义者,则显然是一种充满着献祭精神的主体的自我选择。克尔凯戈尔曾经通过亚伯拉罕的故事指出,建立在恐惧之上的信仰才是真正经受得起考验的信仰,那么,像鲁迅这样,建立在献祭精神基础上的信仰,无疑是一种最为纯粹的信仰。没有利益的牵引,也没有得失的考量,有的只是自我牺牲的对运命的承担,这些恰恰也是后期鲁迅信仰转型之后,为什么能在左翼文学阵营中始终保持清醒的批判精神,抱持个人的独立人格的一种重要的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后期鲁迅信仰转型与重构中的这种特性,虽然来之于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后“诗人之死”现象的直接启示,但它与鲁迅对社会进化过程中的“历史中间物”的使命的思考,对人类精神发展过程中的“过客”的历史宿命的思考不仅息息相关,而且也是一脉相承的。作为一个文学家,每在自我精神发生重大状况时,鲁迅都会构建起一个鲜明而独特的意象来象征性地宣示自己的生命体验,“历史中间物”、“过客”与“诗人之死”就是这样具有标志性质的三个递进的生命意象。关于“历史中间物”的思考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过客”的思考发生在1925年,也就是鲁迅的心灵处在“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最为寂寞而焦虑的时刻,而对苏俄文坛“诗人之死”现象的兴趣与关注也就在其后的一二年中发生,这时恰恰也是鲁迅的世界观发生极其剧烈的转变的时候。其中无论是“历史中间物”,还是暮色苍茫中的“过客”,都不是历史的“旁观者”(鲁迅就明确地指出叶赛宁和梭波里“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而是历史的参与者、弄潮者,但“历史中间物”只是自己“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年轻的一代到光明的地方去,幸福合理地度日”,他的运命中没有光明的享受,而是当生命的力量使尽时,就粉身碎骨地死在闸门的重压下。“过客”的命运也是如此,他的前面也许是坟也许是花园,他听从前面声音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朝前走去。其实,已往的经验已经告诉“过客”前面就是坟,但“过客”甚至憎恶这花园的温馨美丽,宁愿筋疲力尽地倒在荒郊野外的坟场。叶赛宁、梭波里、勃洛克等“诗人之死”的结局,可以说更是活生生地验证了鲁迅对“历史中间物”和“过客”命运的预感。确实,在现实生活中,鲁迅一贯主张“壕堑战”,反对青年们做无谓的牺牲,这是鲁迅与恶势力抗争的一种战术意识,是鲁迅在日常生活中的日常理性的表现。但这种战术意识和日常理性从来没有妨碍过鲁迅在心灵层面对大精神、大人格的追求,在形上层面对生命价值的崇高性的确认。从“历史中间物”到“过客”再到“诗人之死”,我们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鲁迅对于精神自省的强烈的自觉性,而且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鲁迅内心深处那像地表下熔岩一样涌动不已的生命激情。在这种意义上,或者说从“历史中间物”、“过客”、“诗人之死”这三个意象的精神内质的相似性与联系性中可以断言,鲁迅后期信仰的转换,与其说是一次飞跃,不如说是一种顺承,一种发展。对鲁迅而言,信仰的内容变了,但信仰的方式与信仰所赖以存在的生命激情则依然如故。 ①林精华:《勃洛克不可缺失的另一半形象》,见勃洛克《知识分子与革命》,林精华等译,第3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②芝恩:《关于“拉普”领导人就马雅可夫斯基之死给斯大林的信》,《苏联文学》1989年第1期。 ③可以参见艾晓明、李今等人关于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著。 ④(13)(26)鲁迅:《在钟楼上》,《鲁迅全集》第4卷,第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⑤勃洛克:《知识分子与革命》,林精华等译,第161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⑥⑦⑧(28)(31)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第437、438、440、4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⑨丘特切夫的诗句:“一个人在关键时刻造访这个世界/他是何等快乐幸福,/他被特别幸运的人们所召唤,/作为一位观临宴会的客人/他们目睹了宴会的盛大场面”。转引自勃洛克《知识分子与革命》,林精华等译,第160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⑩(17)(27)鲁迅:《〈十二个〉后记》,《鲁迅全集》第7卷,第3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1)鲁迅:《〈尘影〉题辞》,《鲁迅全集》第3卷,第5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2)鲁迅:《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3卷,第4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4)[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第13页,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 (15)(18)(19)蒋光慈:《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见贾植芳、陈思和主编《中外文学关系资料汇编》下册,第834、849、83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6)(20)勃洛克:《人民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革命》,林精华等译,第166、62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21)转引自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第3页,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 (22)鲁迅:《革命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第5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3)(25)(32)鲁迅:《醉眼中的朦胧》,《鲁迅全集》第4卷,第66、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4)鲁迅:《扣丝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第5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9)鲁迅:《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第3卷,第5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0)鲁迅:《铲共大观》,《鲁迅全集》第4卷,第1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标签:鲁迅论文; 叶赛宁论文; 马雅可夫斯基论文; 革命论文; 文学论文; 大革命时期论文; 勃洛克论文; 读书论文; 洛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