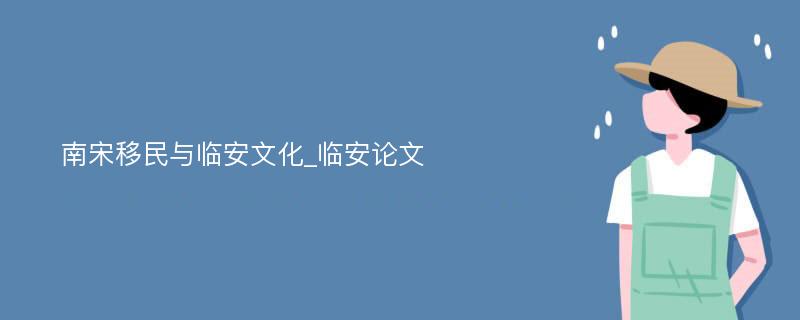
南宋移民与临安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临安论文,南宋论文,移民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的人口,出现过几次重大的变迁,初年因战争人口锐减,以后由于外来移民的迁入才逐渐恢复。迁入的外地移民,可分为两宋之际南迁的北方老移民、绍兴末年以来南迁的北方移民和女真、契丹、奚、渤海等东北移民,以及南宋中后期迁入的南方移民等三类。临安文化面貌的变迁,可以说是各地移民带来的不同文化融合的结果。以往关于临安外来移民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少,但主要集中在第一类移民,对第二类和第三类移民的迁入及影响的研究非常不够。① 因此,仍有必要对各类移民及其文化影响进行全面研究,借以揭示杭州历史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源性,并为说明中国历史上的移民活动如何影响各地域的文化提供一个实例。
一 两宋之际迁入的北方移民及其文化影响
杭州在五代是吴越国的首都,经过吴越国的大力经营,“钱塘富庶由是盛于东南”。② 北宋时,杭州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嘉祐四年(1059)欧阳修说杭州:“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③ 据此语,杭州城市居民达十余万家,是南方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达的重要城市。
北宋靖康元年(1126),金军占领开封,次年掳掠徽、钦二帝,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即位,是为高宗,建立南宋政权。北方人民为躲避战乱,纷纷向相对安全的南方迁移。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达成和约,这一移民潮才暂告结束。
杭州在建炎中曾为高宗驻跸地,升为临安府,绍兴二年高宗率文武百官迁入,八年正式以临安为行在所,定都于此。临安周围经济发达,风景秀丽,作为南宋首都更对北方移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成为北方移民的分布中心。南宋文献这样记载:“西北人以驻跸之地,辐辏骈集”;④ “大驾初驻跸临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辏”;⑤ “中朝人物,悉会于行在”;⑥ “西北士大夫多在钱塘”。⑦ 笔者在各种宋元文献和地方志中搜集靖康之乱以来迁入南方的移民名单,制成《靖康乱后南迁的北方移民实例》各表。表中,已知迁入地的北方移民共1006人,其中迁入临安的94人,占了总数的9%,远高于其他府州;此外,迁入地不详的移民311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如宗子与外戚),也有很大一部分住在临安。⑧
临安在两宋之际曾遭方腊起事和金兵南下等战争影响,人口大幅下降。宣和二年(1120)年底,方腊军占领城市,据说“纵火六天,官吏居民死者十二三”。⑨ 建炎四年(1130),金军血洗临安,自州门开始杀人,四面放火,一周后才撤离,⑩ 仅在清波门里竹园山一带金军即杀死万人。(11) 南宋定都以后,随着外出避乱的市民的回归和北方移民的迁入,临安的人口数量开始恢复。绍兴二十六年,起居舍人凌景夏说:“切见临安府自累经兵火以后,户口所存,裁十二三,而西北人以驻跸之地,辐辏骈集,数倍土著,今之富室大贾,往往而是。”(12) 这一段话,反映了临安的居民多来自北方。乾道五年(1169)以前临安府有户26万,(13) 如将当地土著人户估计为7.1万,(14) 外来移民及其后裔约18.9万户左右,即北方移民及其后裔约占人口的72.7%,此数与凌景夏言“西北人数倍土著”之比例大致相符。如认为这一比例可能过高,将北方移民及其后裔占比例估计在三分之二左右,也当有17万户左右。
南宋时期,类似临安那样北方移民及其后裔成为人口主体部分的重大人口变动,同样发生在临安附近的平江府(治今江苏苏州)、建康府(治今江苏南京),而在镇江府、绍兴府等府州,北方移民也占有一定的比重。(15) 在这种环境下,因移民大规模迁入临安而带来的北方文化,不至于被周围的南方文化很快冲淡,得以长期保留下来,甚至一度成为当地占主导地位的文化。
临安移民四分之三左右来自今天的河南省,其中绝大多数又来自开封,并往往是在南宋初年迁入的。(16) 因此,南宋临安文化受开封移民的影响最大,在语言、经济生活、社会风俗等方面都极像开封。此外,移民还来自今之山东、山西、河北、陕西,以及江苏与安徽两省的淮河以北地区,临安文化也受到这些地方的北方移民的影响。
北宋时期,临安居民主要讲当地的语言,吃南方的食物,服饰、节日习俗和艺术表演形式无不具有南方尤其是本地的特色,宗教信仰同样如此。南宋时期随着北方移民的大批迁入并成为当地人口的主体部分,这些方面都发生了重大改变。
1.语言
由于外来移民以开封人较多,临安普遍流行开封话。虽然一二百年以后开封话已逐渐融合到南方语言中,但其影响直到明代仍清晰可见。明人郎瑛说:杭州“城中语言,好于他郡。盖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如呼玉为玉(音御),呼一撒为一(音倚)撒,呼百零香为百(摆)零香,兹皆汴音也。惟江干人言语噪动,为杭人之旧音。”(17) 甚至现代杭州的方言中,还可以看到宋代开封话的痕迹。当代历史语言学家指出:南宋建都杭州达148年,“越中方言受了北方话(中州音)的影响,明显地反映在今日带有浓厚‘官话’色彩的杭州话里。杭州话属吴语,可是文白异读的字较少(如‘问味’声母只读V—,不读M—),儿尾词很发达,人称代词完全采用北方话的,都是北方话影响的结果。”(18)
2.食物
北宋时期南北方的食物分成南食和北食两个区别较大的系统:大致区别是南方人的粮食以稻米为主,北方人的粮食以粟麦为主;南食的荤菜以猪肉、鱼为主,北食的荤菜以羊肉为主。(19) 临安人的食物属于南食系统。
北方移民迁到南方以后,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食物习惯,对面食的追求导致江南小麦供不应求,绍兴初年每斛涨至12000文,(20) 即是证明。到孝宗时期(1163—1189),由于麦子的广泛种植,面食在江南一带才逐渐成为价格低廉的大众食品,临安一碗面30文,来自北方的老兵可以终日以面食为主食。(21)
北方人认为羊肉是第一等的美味食品,向有“西北品味,止以羊为贵”一说。(22) 南宋时临安人也以羊肉为第一等美味,临安俗语讽刺滥封官员的现象, 便提到“户度金仓,细酒肥羊”。(23) 南宋时临安所在的江南地区盛产牛乳和以牛乳、羊乳为原料制成的酥酪,绍兴府出产的品质尤其好,按照《嘉泰会稽志》的看法,酥酪原产于中原,西晋时南方并无出产,后逐渐南传,(24) 这些食物南宋时扩大生产,极可能是北方移民迁入后食用者剧增的结果。
冬天取冰藏于窖中,夏天取出冰融化后喝冰水消暑,这种北方人的生活习惯南宋初年传入临安。临安人冬季藏冰。(25) 到了盛夏,商人将藏冰出售以供消暑。杨万里赋诗记载这种现象:“帝城六月日卓午,市人如炊汗如雨。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26)
《梦粱录》总结临安人饮食习惯的变化:“向者汴京开南食面店,川饭分茶,以备江南往来士夫,谓其不便北食故耳。南渡以来,几二百余年,则水土既惯,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27) 这种局面的形成,既有北方移民逐渐适应南方食物的一面,也有南方人民逐渐适应北方食物的一面,而后者往往是北方移民将北方食物与吃法在南方广为传播的结果。如果将反映北宋开封的《东京梦华录》和反映南宋临安的《梦粱录》两书记载的当地食物加以比较,可以看出临安人的饮食喜好几乎与开封没有区别,不过是增加许多南方产品更显丰富。
3.服饰
《宋史》卷153《舆服志》说:“中兴,士大夫之服大抵因东都之旧,而其后稍变焉。一曰深衣,二曰紫衫,三曰凉衫,四曰帽衫,五曰襴衫。”可见南宋时朝臣的服饰,大多从北宋朝臣的服饰发展而来。此外,北宋时开封官员已开始穿凉衫,以褐绸制作,南宋时“渐及士大夫”,到后期“遍于天下”。不过,颜色不再是褐色,而是白色。(28) 除了官员的服装,百姓的服装和打扮同样深受北方移民的影响,例如,妇女的打扮方式,“如瘦金莲方、莹面丸、遍体香,皆自北传南者”。(29)
4.节日习俗
南宋以前,临安的节日风俗反映了南方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的特点,与北方有很大的不同。南宋初期移民带入北方的节日风俗,给临安的节日生活增添不少北方的色彩。
元旦,人们在街坊以食物、冠梳、领抹、缎匹、花朵、玩具等物沿门歌叫关扑。(30) 此习俗和《东京梦华录》卷6所载开封元旦的部分习俗相似。
立春日,有鞭春的习俗。前一日,以镇鼓锣吹妓乐引春牛到临安府前迎春馆内。次日,郡守率僚佐用彩杖鞭春牛。(31) 据《东京梦华录》卷6,此俗北宋开封已有。
元宵夜晚,街道上游人如织,“至夜阑则有持小灯照路拾遗者,谓之扫街,遗钿坠珥,往往得之,亦东都遗风也”。(32)
七月七日为七夕节。“市井儿童手执新荷叶,效摩睺罗之状。此东都流传,至今不改。”(33)
七月十五日中元节临安人有吃素食、接祖宗之举,“盖因南宋杭人多半由汴京南渡而来,祖宗坟茔在北,无从设祭,遂有是事,相沿成习,为他郡所无。”(34)
九月初九日重阳节,人家以五色米粉塑成狮子蛮王的形状,放在熟栗子和麝香、蜂蜜拌和的糕上,称为“狮蛮栗糕”。(35) 此俗完全同于开封。(36)
十二月八日为腊八日,寺院以一些瓜果作原料制成腊八粥供应僧人和施主。王洋赋诗说:“腊月八日梁宋俗,家家相传侑僧粥。”(37) 可见原为北方风俗,南渡后传入南方。
十二月二十四日为小节夜,三十日为大节夜,宫中和街市举行驱傩仪式。自此入月,街市贫丐者三五人为一队,装扮为神鬼、判官、钟馗、小妹等,敲锣击鼓,沿街乞钱,俗呼为打夜胡。这一习俗亦传自开封。(38)
5.艺术表演形式
北宋开封是全国艺术的中心,城市中汇聚了来自各地的艺术,宫廷里有许多专供皇室和群臣娱乐的艺术。南宋时期随着开封人口的迁入,相当多的原来临安没有的艺术形式传入城中。例如,唱赚、(39) 诸宫调、(40) 陶真、(41) 叫声、杂扮、(42) 影戏,(43) 这些艺术形式原来主要流传在北方,随着北方人口的迁入而传入临安。无论南宋还是明代的杭州地方文献,在追溯这些艺术形式的起源时,都溯源到北宋的开封,或干脆用“盖汴京遗俗”等词语。《宋史·乐志》说宫廷雅乐:“南渡之后,大抵皆用先朝之旧,未尝有所改作。”可见在乐人南迁的同时,宫廷雅乐也传入临安宫廷。琴(今名古琴,又称七弦琴)为宋代重要乐器,北宋中后期的琴谱以藏于秘阁的宫廷乐谱阁谱最为时人看重。南宋时阁谱传入临安,先是保存在宫廷和南迁的北方大族韩氏家中,后来得到流传,并改造成影响颇大的江西谱。(44)
6.宗教
宗教在古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进行群体迁移的移民只要可能往往要在新的定居地建立家乡原有的宗教建筑。建炎南渡以后,开封僧侣道士纷纷在临安建立寺庙。道观有四圣延祥观、宁寿观等,佛寺有太平兴国传法寺、开宝仁王寺、千佛阁安福院、演教院、崇宁万寿教寺、慧林寺、净胜寺、大德尼寺、永隆院等。(45) 其中的一些寺庙,如四圣延祥观、宁寿观、太平兴国传法寺、开宝仁王寺、慧林寺,都是以僧侣道士南迁前在开封所居庙宇的名字命名。还有一些祭祀地方神的庙宇,如太乙宫、显应观、祚德庙、昭节庙、皮场庙、宗圣曾子祠、萧酂侯祠、东平忠靖王庙,也随着信众的南迁而在临安建立起来。(46) 除上述开封人所建的庙宇,临安还有旌忠庙、忠勇庙、崇恩延福院等北方其他地方的移民所建的寺庙,(47) 以及一批目前无法确定兴建者的迁出地的北方人所建的寺庙。(48)
值得注意的,是信奉自北方迁来的菩萨仙人的人绝不止北方移民,还有不少的南方百姓。例如,临安的皮场庙是前来赶考的士人,不管是北方籍还是南方籍,求神保佑的处所,临安人有病也去此庙祷告。(49)
二 南宋绍兴末以来北方新移民的迁入与文化影响
绍兴十一年宋金双方签订和约,两国开始进入南北对峙时期,这一局面一直继续到金亡。在这一时期(1141—1234)中,宋金双方都发动过大规模的战争,但往往几年便告结束,双方仍维持秦岭—淮河这条军事分界线。在每一次南北战争发生的几年间,都要发生北方人口南迁。虽然这些移民潮持续时间只有几年,仍然保持一定的规模。例如,南宋隆兴元年(1163)发动北伐,五月,军队渡过淮河夺取金的灵璧、虹县两城,金将蒲察徒穆、大周仁等万余人投降,继而萧琦率部分兵马自宿州归宋;(50) 七月,寿春府军民士庶万余户归宋。(51) 一时间,“中原之民翕然来归,扶老携幼相属于道”。(52) 南宋于开禧二年(1206)再度北伐,“淮民稍徙,入于浙、于闽”。(53) 每次北方人口南迁时,都会有一定数量的上层移民和军人移民迁入临安。
值得注意,绍兴末以后迁入临安的北方新移民所携带的北方文化,与以前迁入的北方老移民携带的北方文化已有不少的差异,这是宋金时期另一股移民浪潮影响的结果。当时,在中国的南北方都出现人口大迁移的局面。一方面是北方的汉人为避乱而大举迁入南方,另一方面是金朝的统治民族女真族为便于统治中原,率契丹、渤海、奚等民族自东北大批迁入华北。东北民族的内迁过程,自金军攻入中原不久便已开始,到金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今北京)时达到新高潮,此后仍在进行着,估计约有300余万人迁入中原。(54) 随着移民的迁入,东北民族的文化,包括服饰、音乐、舞蹈、语言、社会风尚开始传入中原。
东北民族文化是金朝统治者的母文化,金朝前期统治者为了同化汉族不遗余力地在华北推行自己的文化。在入主中原的初期,甚至采用武力强迫的手段,逼迫汉人穿女真人的衣服,留女真人的发型。金朝曾多次下达禁止中原人民穿汉服、保留原来的发式的规定,违抗者要处死。例如,天会七年(1129)六月,“行下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之”。(55) 在这种背景下,自然会迅速实现服装和发式的统一。
金朝是华北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这种融合,既是女真、渤海、契丹、奚等内迁民族吸收北方汉族文化的过程,也是北方汉族吸收这些边疆民族文化的过程。北方汉族由于人数众多并有着相对先进的经济文化,在这一轮的民族融合中占据了相对优势的地位,使内迁的东北民族最终融入中原汉族。然而,内迁的东北民族在人数上仍占一定的比例并在政治舞台上占据有利的地位,其文化影响同样不可小觑。因此,新融合而成的中原汉族的文化不可能是原先的面貌,而是掺入边疆民族文化的色彩。如果说在这一过程中,内迁的边疆民族完成了汉化的话,中原汉族同时也受到内迁的边疆民族的胡化。
经历了太祖、太宗、熙宗、海陵王、世宗等五朝七八十年间的胡化,到世宗时期(1161—1189),东北民族文化的许多方面已在华北流行开来。当时出使金朝的南宋使节范成大、周辉、楼钥、韩元吉等人都注意到华北汉族的胡化现象,并将之记载于他们的日记和行程记中。
北方汉人的胡化,首先表现在服饰和发式上。范成大说:中原汉人胡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河)已北皆然,而京师(指北宋京城开封)尤甚”;“男子髡顶,月辄三四髡,不然亦间养余发,作椎髻于顶上,包以罗巾,名曰蹋鸱,可支数月或数年。村落间多不复巾,蓬辫如鬼,反以为便”;“惟妇人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绝少,多绾髻,贵人家即用珠珑璁冒之,谓之方髻”。(56) “大梁宫中设毡屋,大梁少年胡结束”,(57) 则是另一名南宋诗人刘克庄在开封所见到的现象。可见服装方面的胡化已相当普遍和严重。甚至艺人在表演音乐舞蹈时穿的服装也同样出现胡化。楼钥看到:“乐人大率学本朝,惟杖鼓色皆幞头红锦帕首,鹅黄衣,紫裳,装束甚异。”(58) 韩元吉看到:“舞女不记宣和妆,庐儿尽能女真语。”(59)
除穿胡服、留女真人的发型,中原汉人的胡化还表现在食物、音乐、舞蹈、语言、社会风俗等方面。
女真人的饮食,“以糜酿酒,以豆为酱,以半生米为饭,渍以生狗血及葱韭之属,和而食之,芼以芜荑”;在招待客人时往往以大盘盛肉,上“间插青葱三数茎”。(60) 到了金朝,女真人的一些食法,包括吃生葱、生韭菜的习惯也传到中原,南宋使节楼钥在河南、河北就受到大盘肉上放生葱的招待。(61) 周辉见金人吃饭时“先汤后茶”,遂将这种吃法称为“虏法”,以别于南宋境内的吃法。(62) 楼钥还看见,侍者接待客人时,兼用女真礼仪和中原礼仪,“或跪或喏,跪者胡礼,喏者犹是中原礼数”。(63)
在南宋使节的眼中,金朝统治下的中原的音乐、舞蹈,因渗入东北文化的色彩已大不同于宋朝。楼钥说金朝音乐:“乐声焦急,歌曲几如哀挽,应和者尤可怪笑。”(64) 范成大说金朝舞蹈:“虏舞悉变中华,惟真定有京师旧乐工,尚舞高平曲破。”(65) 甚至北方汉人的语言也发生变化。楼钥说金初的开封人“语音犹有微带燕音者,尤使人伤叹”,(66) 以及韩元吉所说的“庐儿尽能女真语”,表明北方语言已染上东北以及原辽国燕云地区的语言成分。
范成大在金朝境内看到“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67) 表明汉人在社会风俗方面也受到东北民族的影响。中原“放偷”习俗的形成是东北社会风尚影响汉人的一个典型体现。据说“金国治盗甚严,每捕获论罪外,皆七倍责偿。惟正月十六日则纵偷一日以为戏,妻女、宝货、车马为人所窃,皆不加刑。”这种习俗,金初传到北京一带,故洪皓说“今燕亦如此”。(68)
由于金朝的北方汉人,在服饰、发式、饮食、礼节、习俗、歌舞、语言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就使得他们在文化上已与以前的北方汉人有一定的区别。而文化上存在的这种差异,就使得两宋之际已经迁入南方的北方老移民及其后裔,对绍兴末年以后迁入南方的北方新移民,产生文化上的疏远感。更何况每年的南迁都夹杂着一定数量的女真人、契丹人和渤海人。南宋人对绍兴末年以后迁入的北方新移民和东北移民,因文化上的疏远感而导致不放心,因不放心于是便有人建议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因此,南宋孝宗以后的每一次北方人口南迁,都会引起大争论,焦点无非是两个,一个是是否接纳这些人(南宋称他们为归明人、归朝人、归正人),一个是如何防范附载于他们身上的源于东北民族的文化的扩散。(69) 由于首都临安是北方新移民和东北移民的重要迁入地,每一次争论几乎又都以临安为焦点。透过这些争论,可以看出绍兴末年以后迁入的北方新移民和东北移民对临安文化的影响。
文献所载的有关北方新移民和东北移民对临安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孝宗和光宗朝,有关争论也多集中在这两朝。
孝宗时期,因北方新移民和东北移民的迁入,胡化了的服饰、语言、歌舞、音乐开始进入临安。在临安的官员和百姓当中,出现“服饰乱常,声音乱雅”的现象,还有一些人热衷于“插棹篦,吹鹧鸪,拨胡琴,作胡舞”;这些行为,遭到不忘收复中原、以夏变夷的宋孝宗和大臣们的坚决反对,隆兴元年(1163)朝廷下令严厉禁止,并禁止新移民“不改胡服”和诸军“仿效蕃装”,要求“所习音乐”不得“杂以胡声”。(70)
这些禁令其实没有收到多少效果。仅仅过了五年时间,到乾道四年七月,又有臣僚就临安的胡化问题进言。臣僚们不仅提到临安十数年的胡化现象依然存在,“服饰乱常,习为胡装;声音乱雅,好为胡乐;如插棹篦,不问男女;如吹鹧鸪,如拨胡琴,如作胡舞,所在而然”,而且还提到临安人“静夜十百为群,吹鹧鸪,拨胡琴,使一人衣黑衣而舞,众人拍手和之,道路聚观,便同夷路”,简直成为街头群众集体娱乐的一种形式。他们还指出:这些胡化文化在临安流行“十数年来”,“所在而然”,“初则效学以供戏笑,久则习之为非。甚则上之人亦将乐之,与之俱化矣。”也就是说,这种胡化最初只是模仿以供取笑,但模仿久了便成了习惯,甚至上层人物也乐此不疲,一同胡化。臣僚们为之感叹道:“中原士民沦于左袵,延首企踵,欲自致于衣冠之化者三四十年而不可得,而东南礼义之民,乃反坠于胡虏之习而不自知,甚可痛也。”(71) 朝廷不得不再次下令禁止,“申禁异服异乐”。(72)
尽管大臣们痛心疾首,朝廷禁令屡下,都没有收到实际效果,临安的胡化现象仍越来越厉害。在淳熙年间(1174—1189)和绍熙二年(1191),袁说友、蒋继周和余古等人都就临安的胡化现象再三地向皇帝上奏。
袁说友的奏文着重分析临安官民在服饰方面的胡化现象。他指出:“都下年来一切衣冠服制习为虏俗,官民士庶浸相效习,恬不知耻。”具体表现在:“紫袍紫衫,必欲为红赤紫色,谓之顺圣紫。靴鞋常履,必欲前尖后高,用皂革,谓之不到头。巾制,则辫发低髻,为短统塌顶巾。棹篦,则虽武夫力士,皆插巾侧。如此等类,不一而足。”(73) 依据这份奏文,来自东北移民和北方的新移民的服饰穿着为临安官民士庶竞相追求,从头上的头巾,到身上的袍衫,再到脚上的靴鞋,无不如此。
蒋继周和余古的进言着重分析音乐舞蹈方面的胡化现象。据他们的报告,“渤海乐”等来自东北民族的音乐,已“盛行于世,都人多肆习之”,而且流传到皇宫之中。甚至贵为一国之尊的光宗皇帝,也是东北音乐舞蹈的喜好者,余古批评光宗皇帝“宴游无度,声乐不绝……甚至奏胡戎乐,习齐郎舞。”(74) 南宋后期临安有多个专门表演歌舞的团体“清乐社”,每个都不下百人,其中的“鞑靼舞”、“老番人”两个团体,(75) 顾名思义应该是分别表演蒙古草原的鞑靼族和东北的女真等民族的舞蹈的团体。
综上所述,孝宗、光宗两朝的皇帝、大臣,深受北方新移民和东北移民带来的胡化了的服饰、语言、音乐、舞蹈在临安流行的困扰。在他们看来,这些胡化文化的流行,容易混淆华夷界限,以夷变夏,必须禁止。然而,这种胡化文化却屡禁不止,日趋加剧,其中的原因值得思考。依据文献,可以猜测绍兴末年以来迁入临安的北方新移民和东北移民的人数,和他们在临安的文化影响是极不成比例的。就人数而言,尽管绍兴末以来的每次移民南迁都保持一定的规模,但移民总数无疑大大小于两宋之际南迁的北方人口的数量。至于在临安府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乾道五年临安府有户26万余(上揭),这些新移民只能占极小的比重。人数并不算很多的北方新移民和东北移民,在人口众多、文化高度发达的都城临安掀起大波澜,个中原因颇值得进一步探讨。
三 南方籍移民和南方文化
除了北方老移民、新移民和东北移民之外,自南方各地区迁入临安的移民数量也不少。甚至可以说,在两宋之际的北方人迁入浪潮消退之后,迁入临安的外地移民便主要来自南方。这种移民,属于单个的自发性迁移,且都发生在和平时期,文献中的有关记载较少又比较零散。尽管如此,仍留下他们的迁移痕迹。
临安商业发达,自各地前来经商的商人很多。南宋文献说:“杭城富室多是外郡寄寓之人……其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穹桅巨舶,安行于烟涛渺莽之中,四方百货,不趾而集,自此成家立业者众矣”;(76) 又说临安:“贩铜谋利,当严江上之云帆”;“持楮易钱,盍验市间之茗肆”;“闽商海贾,来万里之货珍”。(77) 据此推测临安的商人大多来自外地,其中一部分是南方各地的商人,而且不少人已定居临安。
宋代福建商人以善于经营海上商业而闻名全国,文献如果将福建商人和外国商人相提并论,往往称福建商人为“闽商”,外国商人为“海贾”;而如果只提“海贾”,则这一“海贾”大多只指经营海上商业的福建商人。以上文献所说的“海贾”、“闽商”大多是福建商人。天妃(又称妈祖)是福建海商和渔民的保护神,福建沿海之人一旦在外地定居,往往要在新住地建造天妃宫(或称妈祖庙),以祈求庇佑保护,因此天妃庙的兴建常可视为福建人定居的一个标志。临安艮山门外建有天妃庙(又称圣济顺妃庙),城南萧公桥及候潮门外的市舶司旁边还设有行祠,用来祀天妃,(78) 刘克庄也说临安人“祀妃尤谨”。(79) 凡此都说明自福建迁入临安的海商不在少数。
福建是南宋按人口平均耕地数量最少的地区,存在着较多的无地少地的人口,因此是移民的主要输出地之一。曾丰说福建:“居今之人,自农转而为士、为道、为释、为技艺者,在在有之,而唯闽为多。闽地偏,不足以衣食之也,于是散而之四方。故所在学有闽之士,所在浮屠、老子宫有闽之道释,所在阛阓有闽之技艺。”(80) 据此,迁入临安的福建移民除海商外,肯定还有道、释、工匠、文士。福建的演艺人员在临安建起“福建鲍老社”,参加者达三百余人,就是一个证明。(81)
在宋金以及宋蒙(元)对立时期,位于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江淮地区是南北战争的主要交战地带,每当战乱发生时当地人民不得不渡江避难,有的便在避难地方定居下来。此外,自南宋中期开始,两浙、江西、江东、福建等路的人口压力加大,大批无地少地的人口为了解决生计问题,向耕地开发未尽的地区和可以寻找到谋生途径的城市迁移。如果遭遇水旱灾害,这种迁移往往达到一定的程度。对于南渡避乱的江淮移民而言位于江南的临安是重要的迁入地之一,而对于寻找谋生途径的南方移民而言,作为都城的临安无疑也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82) 因此,迁入临安的南方籍移民,除了迁自福建,也迁自江淮地区以及两浙、江西、江东等路。
上述文献提到的寄寓临安的“江商”,应该是经长江用船运货到临安的江东、江西一带的商人。临安仰山有二王庙,出自江西袁州(治今湖北宜春);又有源于徽州婺源的灵顺庙(即五显神祠),在临安立有7个行祠;钱塘门外霍山有源于广德军(治今安徽广德)的广惠庙,它供奉张王,创建于南宋乾道年间;仁和县百万新仓西有源于常州的显佑庙;此外,临安还建有源于秀州(治今浙江嘉兴)敬奉霍光的显忠庙,源于婺州(治今浙江金华)敬奉胡则的显应庙,源于温州敬奉温琼的东嘉忠靖王庙,(83) 等等。龙登高以为,仰山二王庙应是随着江西至杭州的木材贸易传播而来的,(84) 而美国学者韩森(Valerie Hansen)对上述源于某地的地方神信仰扩展到其他区域现象的研究,更表明这种地方神信仰的扩展往往是移民(尤其商业性移民)的结果。(85) 依据这些思路,上述自外地进入临安的南方地方神庙宇在临安的建立及信众的扩大,一定程度上都是信仰这种地方神的外地移民迁入临安的结果。这些移民可能相当部分是商人,但也不排除有手工业者、农民、文人和演艺人员。(86)
南宋科举发达,每到三年一次的会试期间,各地汇集临安的士人“不下万余人”,(87) 加上随同的人员,人数还要多上数倍。按照另一位南宋末年人的观察,遇到混补之年,“诸路士人比之寻常十倍,有十万人纳卷”;“每士到京,须带一仆,十万人试,则有十万人之仆,计二十万人”。(88) 有的考生因未能高中在考后仍然滞留临安,这类人数量不少,给首都带来诸多压力,朝廷有时不得不要求临安府尹发布命令,请这些学子返回家乡。(89)
除了这种蔚为壮观的应试流动人口,还有一些文人因首都是文化中心,又有着较高的生活水平,有意前来寓居,或者解官后以临安为自己的定居地。宝庆二年致仕以后“筑室九里松,买舟西湖会意处”的乌程(今浙江湖州市)人俞灏,(90) 曾受业于朱熹后定居临安的袁州分宜(今属江西)人宋斌,(91) 就是他们的代表。一些流寓临安的外地文人还和当地文人一起组织西湖诗社。耐得翁说:“此社非其他社集之比,乃行都士夫及寓居诗人,旧多出名士”。此外,临安还有猜谜、写诗的团体“南北垕斋”、“西斋”,耐得翁说这些团体“皆依江右”。(92) “皆依江右”一语提示“南北垕斋”和“西斋”的成员可能大部分来自江西。
除此之外,如医生、术士与僧侣道士等也有自南方迁入临安的。洪迈《夷坚志》“徐防御”条提到医好某位太后眼疾的吉州吉水人徐远,就是一位在临安行医的外地医生。而活跃在临安的番禺(今广州)人戴某,则是一位擅长占星术的术士。(93) 《西湖游览志余》卷19说在临安城中的大街上,“天下术士多聚焉,皆获厚利”,可见像戴某这样的术士人数应该不少。临安的佛寺道观众多,相当部分的僧侣道士应来自南方各地。除了以上提到过的福建的僧侣,僧侣还来自南方的其他地方,一位名叫重喜的长老,就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94)
被吸引到临安的南方移民,还有各地前来卖笑的妓女。在《梦粱录》卷20《妓乐》列举的临安名妓中,苏州的钱三姐、七姐,婺州的张七姐,应该都是迁入临安的南方人。
由于文献阙载,有关南方下层移民向临安的迁移情况往往暗昧不明,更难以估计他们的迁移规模。据林正秋估计,从事工商行业的人口约占临安城区居民的三分之一。(95) 由于北方移民主要是王公贵戚、官员和军人及其家属,从事工商业和服务的人员较少,这一部门的人员估计主要是南方人。
李晓在研究宋代城市人口增加的途径这一问题时,注意到宋仁宗景祐二年正月戊申的一道诏令:“诏京东西、陕西、河北、河东、淮南六路转运使检察州县,毋得举户鬻产徙京师以避徭役,其分遣族人徙他处者,仍留旧籍等第,即贫下户听之。”(96) 他认为,这条资料透露出:第一,宋仁宗时乡村居民迁移到汴京居住已形成较严重的社会问题;第二,乡村人户不少是卖掉田产举家迁移的;第三,导致乡村人户向首都迁移的原因,除了徭役等重要的方面,肯定还有赋税、土地兼并、灾荒以及城市经济发展提供的谋生机会等方面的原因;第四,如果乡村人户依然按原定的户等承担徭役,政府不禁止其部分家庭成员迁移到城市,而对原先按规定承担徭役较少或没有徭役的“贫下户”即客户,政府原则是放任。(97)
宋代农村人户的离乡进城,已经不是少数或个别地区的现象,也不可能只发生在仁宗时期。南宋的情况固然不同于北宋,而临安也不同于开封,但在南宋商品经济比北宋更加发达、农民的各种自由比北宋更多的情况下,农民向城市和家乡以外地区迁移的可能性显然增大了。淳熙十二年四月,侍读萧燧论及广西农民的负担情况时,便说到当地人为避免身丁钱的负担,“或改作女户,或徙居异乡,或舍农而为工匠,或泛海而逐商贩,曾不得安其业”。(98) 在南宋的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两浙路农民仍然有身丁钱的负担,发生在广西的事情完全可能发生在两浙,而“徙居异乡”与“舍农而为工匠”都不排除迁入临安的可能性,只是文献对此类下层人民的零星迁移往往不予记载罢了,如能将零星的迁移累计起来,数量当不在少数。
四川居长江上游,距江南比较遥远,加之对外交通不便的原因,和平时期迁居临安的只有人数不多的士大夫或经商不归的商人。南宋后期,蒙古军队在四川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普遍采用疯狂杀掠的野蛮做法。为了逃避这场当地历史上少有的大劫难,人们特别是衣冠士族纷纷向长江中下游迁移。刘克庄说:“自蜀有狄难,士大夫避地东南者众,几置乡国于度外矣。”(99) 在这种情况下,临安成为四川难民的主要聚居地之一。
梓潼帝君是四川当地特有的地方神崇拜,据说这位主管科第和文官职位的神仙,在激烈竞争的科举考试中能够给虔诚的信众以暗中的帮助,因此有着广泛的信众。四川移民东迁以后,纷纷在自己的定居地兴建梓潼帝君庙(又称文昌宫)。(100) 临安也不例外。每逢梓潼帝君诞辰的二月初三日,“川蜀仕宦之人,就观建会”,举行宗教活动;而且,除了川蜀之人,“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选者悉祷之”。(101)
四 外来移民和临安的文化变迁
综上所述,在南宋的一个半世纪中,临安经历了极其复杂的外来移民迁入及其文化影响的过程。首先是两宋之际迁入的北方移民,适时地填补了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当地土著锐减形成的人口空缺,成为临安居民的主体部分,而人口的优势又使得他们所携带的北方文化压倒原先的南方文化,临安开始了北方文化为主的南北文化重新融合的过程。北方移民的南迁潮,在高宗绍兴末以后仍在持续着,北方新移民和东北移民的迁入,不仅加强了北方文化的影响,而且给临安文化增添了东北文化的特色。在以上两种北方移民向临安迁移的同时,另一种移民,即来自两浙、江东、江西、江淮、福建、四川等地区的南方移民,也在源源不断地向临安迁移。由于官方或士大夫书写的历史文献比较关注因战争引起的长距离的集团式的迁移,对那些零星的为求发展而进行的迁移往往疏于记载,因此有关外来移民迁入临安的资料主要集中在北方人口的迁入上,南方移民迁入的记载非常零散。然而,南方移民的影响决不可低估。就临安文化的长时段发展过程的考察而言,固然要注意北方移民迁入的影响,同样要注意南方移民迁入的影响。
临安毕竟是南方的一座城市,尽管城市及其邻近的地区不同程度地受到北方文化的影响,南方文化的汪洋大海迟早会将临安重新改造成一座以南方文化为主的城市。这一过程,其实在南宋初期的北方移民大规模南迁结束不久便已开始了。除临安和其他南方城市之间频繁的文化交流以外,源源不断迁入的南方移民带来的南方地域文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南方移民对临安迁入虽然很少采用集团迁入的形式,但长时间的连续不断的个人的迁移却可以汇成移民的洪流,从而加强南宋初期一度弱化的南方文化,势必要在语言、饮食、文学、艺术、服饰、节日习俗、社会风尚、宗教等各方面,冲淡北方成分,并且越到后来南方文化的色彩越加浓厚。估计到了明代,杭州文化已演变为南方文化为主但保留一定北方文化特色的地域文化。
临安文化的这种变迁在许多方面都有表现。以下试以宗教崇拜、节日习俗以及社会风尚等方面,略作论述。
1.宗教崇拜
北方移民迁入时,曾在临安建立一批源自北方的佛寺道观,仅上面提到的便有32所。然而,到了明代,这些寺庙的绝大多数都已不存在了。综合《万历杭州府志》、《西湖游览志》、《武林梵志》、《雍正浙江通志》,以及翟均廉《海塘录》(102) 诸书所载,到明朝中叶仍然存在的,只有开宝仁王寺、慧林寺、宁寿观、宗圣曾子祠、萧酂侯祠、白马庙(显应观)、东平忠靖王庙、昭节庙、三圣庙、慧应庙(皮场庙)、忠勇庙等十一所庙宇,还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
如上所述,南方籍移民迁入临安以后,也在城市中建立了源自移民迁出地的九所庙宇,这些庙宇是否也像北方移民建立的庙宇那样,明代也大多不存在了呢?综合上述五部古籍所载,除二王庙不可查外,其他的八所,即顺济圣妃庙(天妃庙)、灵顺庙、广惠庙、显佑庙、显应庙、梓潼帝君庙、显忠庙以及东嘉忠靖王庙,明代仍然存在。据此可见,在南宋临安源于外地的庙宇中,到了明代源于北方的庙宇已大多不存在了,而源于南方的庙宇绝大部分仍然保存下来。
2.节日习俗
《梦粱录》、《武林旧事》(103) 等南宋人的著作和明代《万历杭州府志》分别详载杭州在南宋或明代的节日习俗,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的部分论述也能看出明代的某些习俗。(104) 现据此制成下表。
宋明方志对临安岁时风俗的不同记载
节日南宋《梦粱录》、《武林旧事》明代《万历杭州府志》、《西湖游览志余》
元旦细民男女皆鲜衣,往来拜节。街坊以食物、动先夕汛扫堂室,盛陈花彩糕果于各神并祠堂
使、冠梳、领抹、缎匹、花朵、玩具等物沿门影堂前。先以糖豆米团祀灶,次迎岁神,次
歌叫关扑。不论贫富,游玩琳宫梵宇,竟日不炳烛炷香拜各神、祖先。讫,幼拜贺尊长,
绝。家家饮宴,笑语喧哗(《梦粱录》卷1《正
男子出拜宗党亲友(《万历杭州府志》卷19,
月》,第1页)
第13页)
立春前一日,以鼓乐引春牛到临安府。次日郡守率先一日,官府迎春于部内之东方,接芒神、
僚佐用彩杖鞭春牛,街市以花装栏,乘小春牛, 土牛。老幼集街路,谓之看春。其所历人家
及春幡春胜,相献于贵家宅舍,示丰稔之兆 各设香烛、焚楮币,以过芒神、春牛,并用
(《梦粱录》卷1《立春》,第2页)五谷抛掷之(《万历杭州府志》卷19,第13—
14页)
元宵歌舞,观灯。夜阑,有持小灯照路拾遗者,谓歌舞,观灯,饮宴(《万历杭州府志》卷19,
之扫街(《武林旧事》卷2《元夕》,第32页)
第14页)
正月十六无记载 有往养济院施舍者,盖与北方走百病之俗相
同(《万历杭州府志》卷19,第16页)
二月初一中和节。民间以青囊盛百谷瓜果种子互赠,禁中和节虽不举,民间犹以青囊盛五谷瓜果之
中宫女以百草斗戏(《梦粱录》卷1《二月》,第 种相遗,城中士女有出郭探青扫墓设奠者
6页)
(《西湖游览志余》卷20,第317页)
二月十五花朝节。出外赏花,寺院启涅盘会,观者纷集宋时有扑蝶之戏,今不举,而寺院启涅盘会,
(《梦粱录》卷1《二月望》,第8页) 拈香者麇至,犹其遗俗(《西湖游览志余》卷
20,第317页)
三月三日禊饮踏青,士庶烧香,诸道宫宇,俱设醮事 戴霁菜花,亦多出游西湖,水滨多为流觞之
(《梦粱录》卷2《三月》,第9页)戏(《万历杭州府志》卷19,第16页)
寒食、清明 清明节前两日谓之寒食,家家插柳条门上。第清明门檐遍插柳枝,各设奠享祖先。出郭扫
三日即清明节,俱出郊省坟,又有龙舟可观 墓,挂纸钱。食用青白圆子(《万历杭州府
(《梦粱录》卷2《清明节》,第11—12页) 志》卷19,第17页)
端午自初一至端午日,家家买桃、柳、葵、蒲叶、悬九色花纸于门,庭下以盆杂植葵、艾、菖
伏道,及茭、粽、时果,采百草或修制药品以蒲,至日焚纸移盆宴所。以角黍、牲酒祀神
避瘟疫,家家焚香一个月(《梦粱录》卷3《五
享先,家众聚饮雄黄酒 (《万历杭州府志》卷
月》,第22页) 19,第17页)
六月六日民众游湖避暑(《梦粱录》卷3《五月》,第24
夜间游湖。郡人浴猫狗于河(《西湖游览志
页)余》卷20,第319页)
立秋都人戴楸叶,饮秋水、赤小豆(《武林旧事》卷 戴楸叶,并以煎汤澡浴(《万历杭州府志》卷
3《乞巧》,第43页) 19,第18页)
七夕富贵人家令女郎拜月、乞巧。市井儿童手执新殷富人家设瓜果为乞巧会(《万历杭州府志》
荷叶,效摩睺罗之状(《梦粱录》卷4《七夕》, 卷19,第18页)
第25页)
中元道家各有斋醮等会,僧寺于此日作盂兰盆斋, 前后五日依释氏盂兰盆法,用素馔馄饨祀祖
而人家亦于此日祀祖。茹素者十八九(《武林旧 先。或召僧道施食,焚楮衣,点放荷灯,以
事》卷3《中元》,第44页)
资冥福(《万历杭州府志》卷19,第18页)
中秋玩月游人,婆娑于市。虽贫困人家,亦解衣市以月饼相馈,夕宴饮玩月(《万历杭州府志》
酒 (《梦粱录》卷4《中秋》,第26页)
卷19,第19页)
重阳赏菊。以五色米粉塑成狮子蛮王的形状,放在市中蒸栗糕,插五色旗于上,各市以祀祖先。
熟栗子和麝香、蜂蜜拌和的糕上(《梦粱录》卷 亦有登高饮者(《万历杭州府志》卷19,第19
5《九月》,第30页) 页)
十月朔日出郊祭祀(《梦粱录》卷6《十月》,第46页)
出郊拜墓,如寒食仪(《万历杭州府志》卷
19,第19页)
立冬无记载 采野菊煎汤澡浴(《万历杭州府志》卷19,第
19页)
冬至馈送节仪,举杯相庆,祭祖,加于常节(《梦粱 祀神享先,交贺诸事,略仿元旦(《万历杭州
录》卷6《十一月冬至》,第48页) 府志》卷19,第19页)
腊月八日,寺院制腊八粥。二十四日,祭灶神。自二十四日,祀灶神。丐者于数日前装貌灶公
此入月,贫丐者装扮为神鬼、判官、钟馗、灶灶母(《万历杭州府志》卷19,第20页)
君等形,沿街乞钱(《武林旧事》卷3《岁晚节
物》,《梦粱录》卷6《十二月》,第49—50页)
除夕比屋以五色纸钱酒果迎送六神,围炉团坐,饮祀城隍、百神和祖先。焚楮币,以送旧神。
酒、唱歌、博戏,终夜不寐(《武林旧事》卷3
架松柴门外焚之,宴饮,谓之分岁(《万历杭
《岁晚节物》,第47页) 州府志》卷19,第20页)
依据上表,可见杭州的节日和民俗活动日,明代与南宋比较,废除的只有二月初一的中和节、二月十五日的花朝节,增加的只有正月十六日和立冬。但如果将宋明两代都存在的节日和民俗活动日的活动内容进行对比,可以发现,除了十月朔日和冬至变化不大之外,绝大多数的节日和民俗活动日,包括元旦、立春、元宵、三月三日、清明、端午、六月六日、立秋、七夕、中元、中秋、重阳、腊月二十四、除夕,其活动内容都有相当大的改变,甚至已面目全非了。那些被废除的内容,如元旦的沿门歌叫关扑、元宵夜的“扫街”、七夕的儿童手执新荷叶效摩睺罗之状,原本都是北方移民迁入临安带入的北方民俗,而花朝节、中和节、端午节等并非自北方传来的节日习俗同样遭到革除或改易。那些宋代没有的活动内容,一部分可能是明代才形成的,例如除夕的祀城隍;一部分是在宋代基础上变化的结果,如丐者于腊月中扮成灶公灶母的形象以乞钱,便源自宋代的“打夜胡”。
岁时风俗的变化,是多种文化因子影响的结果,不能都归之移民的影响,否则便难以说明花朝节、中和节、端午节等并非北方传入的节日习俗,明代得到革除或改易的原因。但是,较大规模的移民的影响却不能不是主要原因之一。如果说,南宋临安的源自北方的节日习俗,是靖康之乱以后南迁的北方移民带入的话,到明代这些习俗已大多被革除或改易,只能说是后来迁入的南方籍移民数量渐多,他们的文化影响逐渐超越北方移民及其携带的北方文化的影响的结果。
3.社会风尚
《梦粱录》卷16《面食店》条说:“南渡以来几两百余年,则水土既惯,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临安之所以形成这种南北饮食混淆的局面,不仅是北方食物进入,也是南方各地食物进入临安的结果。临安有一种专门满足下层人民需求的饭店称衢州饭店,出售虾鱼、粉羹、鱼面之类,(105) 从名称来看这种饭店应是两浙的衢州人所开,从菜单来看应以南方传统食物为主,但“鱼面”之“面”在南宋初却主要是北方移民的食物,此时已被改造成北方移民后裔和南方人普遍接受的“鱼面”了。
临安食物的变化,连北方移民的后裔也不否认。在他们看来,临安的汴京食物和其他传自北方的食物,与开封的口味和样式已有所不同。周辉就持有这种看法,他说:“自过江来,或有思京馔者,命仿效制造,终不如意。今临安所货节物,皆用东都遗风,名色自若而日趋苟简,图易售故也。”(106)
今天的杭州乃至全国的绝大部分地方,无不以乌鸦为厌见之物,以听到乌鸦的叫声为不祥;又无不以喜鹊为喜见之物,以听到喜鹊的叫声为吉祥之兆。然而,宋代南、北方之人,却对乌鸦和喜鹊以及它们的叫声持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大致是“北人喜鸦声而恶鹊声,南人喜鹊声而恶鸦声”;(107) “南人喜鹊而恶乌,北人喜乌而恶鹊,好恶之不同有若是”。(108) 南宋时临安人对乌鸦和喜鹊叫声的态度,是否随着北方移民迁入而发生改变,又如何再次转变过来,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笔者有理由推测,北方移民初到临安仍持原先对乌、鹊的态度,而后来的南方移民以及来自周围地区的文化影响最终使南方人对乌、鹊的态度占了上风。
尽管文献中有关南方移民文化影响的记载极少,以上的论述已能够证明,南宋后期以来临安文化中的南方的色彩逐渐得到增强,北方文化的特色日益冲淡,到了明代杭州已成为南方文化占主体兼具有一定程度的北方文化特色的城市。今天我们看到的杭州,虽然仍保留着宋代迁入的北方移民的文化和语言的痕迹,毕竟已没有人将她看作北方的城市,原因即在于此。在这一变迁过程中,杭州位于南方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以及来自南方的外来移民的进入,无疑是导致变迁的最主要的两个因素。如果说两宋之际北方移民在南方土著居民锐减时的迁入,使临安城市文化从南方文化为主演变为北方文化为主的话,那么,南宋中后期的南方移民的源源不断的迁入,以及位于南方文化的汪洋大海中的客观环境,则使临安(杭州)又演变为南方文化为主、同时带有一定的古老的北方文化特色的城市。
注释:
① 最早探讨这一问题的,是张家驹的《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42年)一书。杭州市政协办公室主编的《南宋京城杭州》(杭州:政协杭州市委员会办公室内部发行,1985年),也收集了有关论文多篇。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4卷(辽宋金元时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章和第14章在讨论北方移民的分布与影响时,较多地提到临安。然而,上述诸书除《中国移民史》之外对第二类、第三类移民及其影响均未涉及,《中国移民史》虽略有涉及但远未深入,又因放在全国的移民运动中论述,未能特别说明对临安的影响,更未论及南宋中后期临安的文化变迁。
②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78《吴越二·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85、1087页。
③ 欧阳修:《欧阳修集·居士集》卷40《有美堂记》,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年,第172页。
④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3“绍兴二十六年七月丁巳”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858页。
⑤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8,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04页。
⑥ 陆游:《陆放翁全集·渭南文集》卷15《傅给事外制集序》,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上册,第86页。
⑦ 《宋史》卷437《儒林七·程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949页。
⑧ 参见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4卷《靖康乱后南迁的北方移民实例》所附各表。
⑨ 方勺:《泊宅篇》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9页。
⑩ 赵鼎:《忠正德文集》卷7《建炎笔录》,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128册,第738页。
(11) 方勺:《泊宅篇》卷6,第35页。
(12)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3“绍兴二十六年七月丁巳”条,第2858页。
(13) 周淙:《乾道临安志》卷2《户口》,丛书集书初编本,第25页。此书成书年代不明,按周淙于乾道三年初任知府,五年再任,姑作五年成书。
(14) 据《宋史》卷85《地理志》所载崇宁元年(1102)和大观四年(1110)的全国户数推算,全国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8‰。同书卷88《地理志》载崇宁元年杭州有户203574,依此平均人口增长率,宣和二年(1120)方腊军进入前杭州应有户21.8万,如估计乱时人口减少十分之一,则应余19.6万户。建炎四年金兵侵入前杭州应有户20.4万,如以十分之三比例折算,应余6.1万户。到乾道五年增长到7.1万户。
(15) 参见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4卷(辽宋金元时期),第276—289页。
(16) 参见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4卷(辽宋金元时期),第293—297页。
(17) 郎瑛:《七修类稿》卷26《杭音》,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94页。
(18) 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年,第57页。
(19) 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20) 庄绰:《鸡肋编》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6页。
(21) 《宋史全文》卷27上,作者不详,四库全书本,第331册,第467页。
(22) 周晖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9《猫食》,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01页。
(23)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6,第83页。
(24) 《嘉泰会稽志》卷17,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044页。
(25) 《鸡肋编》卷中载:“二浙旧少冰雪,绍兴壬子,车驾在钱塘,是冬大寒屡雪,冰厚数寸。北人遂窖藏之,烧地作荫,皆如京师之法。临安府委诸县皆藏,率请北人教其制度。”(第53页)
(26) 杨万里:《诚斋集》卷18《南海集·荔枝歌》,四库全书本,第1160册,第197页。
(27) 吴自牧:《梦粱录》卷16《面食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5—146页。
(28) (佚名):《爱日斋丛钞》卷5,四库全书本,第854册,第687页。
(29) 袁褧:《枫窗小牍》卷上,四库全书本,第1038册,第211页。
(30) 吴自牧:《梦粱录》卷1《正月》,第1页。
(31) 吴自牧:《梦粱录》卷1《立春》,第2页。
(32) 周密:《武林旧事》卷2《元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页。
(33) 吴自牧:《梦粱录》卷4《七夕》,第25页。
(34) 王企敖:《南宋杭州的时俗》,政协杭州市委办公室:《南宋京城杭州》,第290页。
(35) 吴自牧:《梦粱录》卷5《九月重九附》,第30页。
(36) 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8《重阳》,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16页。
(37) 王洋:《东牟集》卷2《腊八日书斋早起南邻方智善送粥方雪寒欣然尽之因成小诗》,四库全书本,第1132册,第3227页。
(38) 吴自牧:《梦粱录》卷6《十二月》、《除夜》,第49—50页;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卷10《十二月》、《除夕》,第249—252页。
(39) 吴自牧:《梦粱录》卷20《妓乐》载:“唱赚在京时,只有缠令、缠达。有引子、尾声为缠令。引子后只有两腔迎互循环,间有缠达。绍兴年间,有张五牛大夫,因听动鼓板中有《太平令》或赚鼓板,即今拍板大节抑扬处是也,遂撰为‘赚’。”(第193页)可见唱赚源于开封,在临安采用鼓板等伴奏,于是发展为“唱赚”。
(40) 吴自牧《梦粱录》卷20《妓乐》载:“说唱诸宫调,昨汴京有孔三传编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今杭城有女流熊保保及后辈女童皆效此,说唱亦精,于上鼓板无二也。”(第193页)可见诸宫调源于开封。
(41)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20载:“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四库全书本,第585册,第554页)显然陶真也与北方移民有关。
(42) 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载:“叫声,自京师起撰,因市井诸色卖物之声,采合宫调而成也。”“杂扮或名杂班,又名钮元子,又名技和,乃杂剧之散段。在京师时,村人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人,以资笑。今之打和鼓、捻梢子、散耍皆是也。”见《南宋古迹考(外四种)》,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83页。
(43) 吴自牧:《梦粱录》卷20《百戏伎艺》载:“更有弄影戏者,元汴京初以素纸雕镞,自后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用以彩色妆饰,不致损坏。杭城有贾四郎、王升、王闰卿等,熟于摆布,立讲无差。”(第194—195页)
(44)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44《琴述赠黄依然》,丛书集成初编本,第756页。
(45) 《咸淳临安志》卷13、76、81、82,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3486—3487、4040—4041、4046、4103—4104、4114—4115页。
(46) 《咸淳临安志》卷13,第3481、3488、3490页;卷72,第4004页;卷73,第4010页。雍正《浙江通志》卷217,四库全书本,第525册,第11、13、16页。
(47) 《咸淳临安志》卷72,第4002—4003页;卷76,第4048页。
(48) 据《咸淳临安志》卷76,第4047—4048页;卷81,第4103—4106页。已知北方人建但原建地不明的寺庙主要有:白莲慈云院、瑞云院、无碍院、大佛万寿院、瑞应院、国清寺、西北真如院、惠严院、传法五藏院、法明院、演法院。
(49) 《咸淳临安志》卷73,第4010页;卷93,第4210页。
(50)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17之28,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7051页。
(51)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16之2,第7029页。
(52) 《宋史》卷390《周淙传》,第11958页。
(53)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戊集《淮民浆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97页。
(54) 参见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4卷(辽宋金元时期)第5章第1节,第129—135页。
(55)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5《太宗文烈皇帝三》,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52页。
(56) 范成大:《范成大笔记六种·揽辔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3页。
(57)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8《大梁老人行》,四部丛刊本,第17页。
(58) 楼钥:《攻愧集》卷112《北行日录》,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594页。
(59) 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4《得韩无咎书寄使敌时宴东都驿中所作小阅》,第71页。
(60) 徐兢:《三朝北盟会编》卷3,政宣上帙3;卷20,政宣上帙2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7、144页。
(61) 楼钥:《攻愧集》卷112《北行日录》,第1594页。
(62) 周辉:《北辕录》,陆楫编:《古今说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说选壬集,第1页。
(63) 楼钥:《攻愧集》卷111《北行日录》,第1580页。
(64) 楼钥:《攻愧集》卷112《北行日录》,第1594页。
(65) 范成大:《范石湖集》卷12《真定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54页。
(66) 楼钥:《攻愧集》卷111《北行日录》,第1580页。
(67) 范成大:《范成大笔记六种·揽辔录》,第13页。
(68) 洪皓:《松漠纪闻》,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丛书集成新编本,1984年,第117本,第472页。
(69) 有关这方面的争论,黄宽重的《略论南宋时代的归正人》已从政治的层面,作了深入研究。(《食货月刊》(台北)复刊第7卷第3、4期,1977年)从本文引用的资料看来,文化上的疏远感应该也是引起争论的原因。
(70) 《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56,第6573页;兵15之12,第7022—7023页。
(71) 《咸淳临安志》卷47,第3775页。
(72) 《宋史》卷34《孝宗纪》,第643页。
(73) 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12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591页。
(74) 《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22,第6556页;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11,四库全书本,第331册,第467页。
(75) 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南宋古迹考(外四种)》,第100页。
(76) 吴自牧:《梦粱录》卷18《恤贫济老》,第175页。
(77) 祝穆撰,祝洙增订:《方舆胜览》卷1“临安府”,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4页。
(78) 吴自牧:《梦粱录》卷14《外郡行祠》,第131页。
(79)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1《风亭新建妃庙记》,第18页。
(80) 曾丰:《缘督集》卷17《送缪帐干解任诣铨改秩序》,四库全书本,第1156册,第193页。
(81) 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南宋古迹考(外四种)》,第100页。
(82) 参见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4卷(辽宋金元时期)第8章、第7章第1节。
(83) 《咸淳临安志》卷72,第4006页;卷73,第4008—4014页。
(84) 龙登高:《南宋移民与江南城镇市场》,《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2004年5月3日。
(85) 韩森著:《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包伟民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6—159页。
(86) 《西湖老人繁胜录》提到的“婺州角儿”就是来自婺州的演艺人员。
(87) 吴自牧:《梦粱录》卷2《诸州府得解士人赴省闱》,第10页。
(88) 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南宋古迹考(外四种)》,第106页。
(89) 南宋淳祐十一年七月,就发生过类似的事。参见《宋史全文》卷34,四库全书本,第331册,第751页。
(90) 《咸淳临安志》卷67,第3970页。
(91) 《宋史》卷413《赵与欢传》,第12406页。
(92) 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社会》,《南宋古迹考(外四种)》,第89页。
(93) 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戴生星术》,《癸辛杂识(外八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20页。
(94) 《咸淳临安志》卷93,第4208页。
(95) 参见林正秋:《南宋临安人口》,《南宋京城杭州》,第69页。
(9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042页。
(97) 李晓:《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第90页。
(98) 《宋史全文》卷27下,四库全书本,第331册,第480页。
(99)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66《何逢吉叙朝散大夫利路运判兼四川制参制》,第4页。
(100) 马廷鸾《碧梧玩芳集》卷17《梓潼帝君祠记》载:“自吾有敌难,岷峨凄怆,君之灵与江俱东。今东南丛祠,所在崇建,自行朝之。”(四库全书本)
(101) 吴自牧:《梦粱录》卷19《社会》,第181页;卷14《外郡行祠》,第131页。
(102) 翟均廉:《海塘录》卷12,四库全书本,第583册。
(103) 四水潜夫辑:《武林旧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104)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
(105) 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食店》,《南宋古迹考(外四种)》,第83页。
(106) 周辉:《清波别志》卷2,四库全书本,第1039册,第105页。
(107) 彭乘:《墨客挥犀》,四库全书本,第1037册,第680页。
(108) 薛季宣:《浪语集》卷2《信乌赋》,四库全书本,第1159册,第154页。
标签:临安论文; 宋朝论文; 移民论文; 中原文化论文; 南方与北方论文; 南宋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东北文化论文; 中国服饰论文; 东京梦华录论文; 开封论文; 东北历史论文; 绍兴论文; 中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