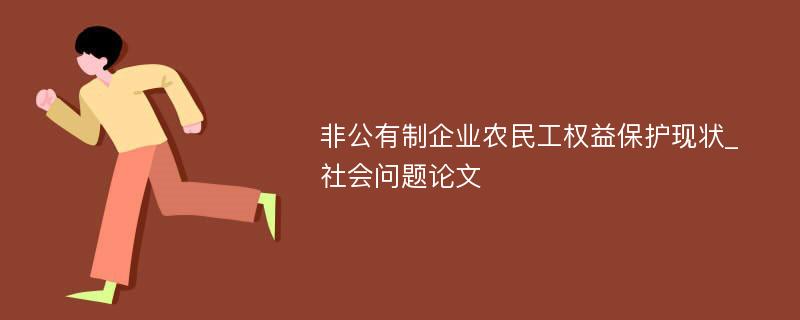
非公有制企业外来女工权益保障现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工论文,非公有制论文,权益保障论文,现状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背景和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后,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走进了社会的各行各业。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外来流动人口聚集的地方之一,据有关的资料介绍,广东省的外来工有1000多万,其中外来女工占60%以上(注:陈杭:《对非公有制女工权益保障的思考》,妇联系统调研成果交流会材料,2002年11月。)。她们主要集中在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蓬勃发展的旅游、餐饮等服务性行业,为广东外向型经济快速的增长作出积极贡献,成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外来女工大批的流入,亦带来了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权益保障问题就是其中最为直接且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九十年代以来外来女工的权益问题成为重要的社会舆论关注点和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从已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对外来女工权益保障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往往是与打工者整体的权益联系在一起的,从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两个层次:
1、对外来女工权益状况的描述性及简单解释性的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两种类型,一种是扫描式,一种是调查式。扫描式的多见于新闻报导或杂文,如熹灵的《今日“包身工”——部分“三资”企业工人地位透视》(注:熹灵:《今日“包身工”一部分“三资”企业工人地位透视》,《经济师》,1994年第5期,第22—23页。),赖诗卿的《前进中的阴影——“三资”企业劳资关系扫描》(注:赖诗卿:《前进中的阴影—“三资”企业劳资关系扫描》,《劳动保护》,1995年第6期,第6—8页。),三木的《中国不要“野麦岭”——对打工者的特别关注(一)》(注:三木:《中国不要“野麦岭”——对打工者的特别关注(一)》,《中国工运》,2001年第2期。),尤露的《深圳血汗工厂中的异乡人——外省女工的血和泪》(注:尤露:《深圳血汗工厂中的异乡人—外省女工的血和泪》http://www.xinmiao.hk.st/sim/
chinafuturel/chifu1012.htm)等等,这些文章多是针对当前非公有制企业的外来女工权益保障现状的简单描写。
调查式的多于学术报告类的文章,包括定性和定量的。广东省总工会《关于广东省外商投资企业职工权益保障状况的调查》(注:广东省总工会:《关于广东省外商投资企业职工权益保障状况的调查》,《珠江三角洲经济》1993年第4期。),刘敬怀,曾明子《权益与尊严不容侵犯——“三资”企业劳工保护忧思录(下)》(注:刘敬怀、曾明子:《权益与尊严不容侵犯——“三资”企业劳工保护忧思录(下)》,《了望》1994年第6期,第15—17页。),黄雪峰《被法律遗忘的角落——沿海“三资”企业虐待女工现象透视》(注:黄雪峰:《被法律遗忘的角落——沿海“三资”企业虐待女工现象透视》,《中国妇运》,1994年第7期,第37—38页。),王加林《归来兮,员工合法权益——“三资”企业员工权益受侵犯大透视》(注:王加林:《归来兮,员工合法权益—“三资”企业员工权益受侵犯大透视》,《中国行政管理》,1994年第5期,第26—28页。),扈海丽《苏南地区外来女性劳动力状况调查》(注:扈海丽:《苏南地区外来女性劳动力状况调查》,《妇女研究论丛》,1997年第4期,第16—20页、44页。),朱敏《非公有制企业女工调查报告》(注:朱敏:《非公有制企业女工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第105—111页。),佳旋《“三资”企业职工权益忧思录》(注:佳旋:《“三资”企业职工权益忧思录》,《企业管理》,1998年第5期,第22—23页。),福州市妇联《外来打工妹在福州生存状况的调查与分析》(注:福州市妇联:《外来打工妹在福州生存状况的调查与分析》,《中国妇运》,1999年第9期,第26—28页。),石彦芳等《对中小型私营企业女工问题的调查与思考》(注:石彦芳等:《对中小型私营企业女工问题的调查与思考》,《河北月刊》,2002年1月,第84—89页。),全国妇联办公厅、浙江省妇联联合调查组《浙江外来务工妇女情况调查》(注:全国妇联办公厅、浙江省妇联联合调查组:《浙江外来务工妇女情况调查》,《中国妇运》,2002年第2期。),陈爱和《“打工妹”的权益不容侵犯》(注:陈爱和:《“打工妹”的权益不容侵犯》,《劳动保护杂志》,2002年第3期,第22—23页。),甘萍等《非公有制女职工劳动保护调查与思考》(注:甘萍等:《非公有制女职工劳动保护调查与思考》,《中国妇运》,2002年第6期,第42—43页、48页。),谭深《泣血追踪——原深圳致丽玩具厂11.19大火受害打工妹调查纪实》(注:谭深:《泣血追踪——原深圳致丽玩具厂11.19大火受害打工妹调查纪实》,来源于“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网。),广东省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外来妹合法权益的维护与思考》(注:广东省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外来妹合法权益的维护与思考》,来源于“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网。)等等,这些文章比较详实地对侵犯外来女工权益的行为进行了揭露和抨击。
2、外来女工权益保障的理论解释性研究
这类研究以学术报告和政策分析居多,其分析的角度主要是经济学、人类学和社会学。
傅江景利用劳动力供应与需求的经济模型作出分析,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1)顾主对利润最大化刻意追求的本性,是降低劳工成本、侵害劳工权益的必要条件;(2)顾主拥有劳动力市场的绝对买方垄断权,是其压低劳工成本,损害劳工利益的充分条件;(3)由于缺少工会组织的保护和法律的不完善,为顾主恣意剥夺劳工权益提供了“宽松”的环境(注:傅江景:《外商投资企业与私营企业劳工权益受损的经济分析》,《当代财经》(南京),1994年11月。)。
谭少薇(注:谭少薇:《蛇口工业区的结构化——变革与再生产》,《中国社会科学辑刊》(香港),1994年夏。)认为外来女工权益地位形成原因是当地特殊的工业组织结构,要改善现有状况就必须对原有结构进行变革。周燕飞(注:周燕飞:《外来工权益保障的权力结构分析——深圳S区的个案研究》,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本科学位论文,1996年5月。)也从劳资双方和第三方——政府三方的互动关系来看外来工的权益保障,认为外来工权益保障程度取决于当地工业关系中企业、政府和外来工的权力结构。
包芳(注:包方、孙平:《私营企业女工权益保护论》,《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第84—88页。)等学者认为女工权益受损的原因,既有社会大环境方面的原因,也有企业主方面的,还有女工个人方面的原因。谭深认为流动的女工与流动的资本在珠江三角洲聚合,与当地社会一起,形成了资本、外来工及当地社会这三方的关系。在这三方关系中,外来女工相对于资本,她们只是廉价劳动力,她们的权益等社会利益由于工人与资本的对话能力太弱而往往不能实现;相对于当地社会,她们是外来人,在工人与外资企业发生冲突时,当地社会不能给外来人提供必要的支持。(注:谭深:《珠江三角洲外来女工与外资企业、当地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全球化与劳工问题学术研讨会”(1999·12·24-25清华大学)。)
二、调查的基本情况
(一)相关的定义
非公有制企业:本文研究的非公有制企业是除了公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乡村集体企业之外的企业,主要是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
外来女工:“外来工”是在人力资源问题上的一种地域概念。本文的外来女工是指在进入本地区就业的外地(含外省、外市、外县的)女劳动力,她们在本地区就业前无当地的户口,但现在不一定无当地的户口。有的学者也将外来女工称之为外来妹。
权益保障:权益是以国家的法律和法规为基础的,是国家的法律和法规所规定的权利。权益保障在这里主要是指保护劳动者的人身权利、经济利益和社会福利不受非法侵害。
(二)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方法主要有问卷调查法、定性的访谈法和文献法。在广东省妇联权益保障部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帮助下,我们在广州、深圳、中山、东莞、顺德、汕头进行了问卷调查,同时也对一些典型个案进行深入访谈。本次的问卷调查,由于直接进入企业发放问卷的困难,未能做到严格的随机抽样。问卷调查的结果对于总体的推论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我们还去广东省妇女劳动教养所和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深入访谈了部分外来女工。
三、调查结果
通过一年多的调查,我们发现在非公有制企业中普遍存在着职工合法权益难以保障的情况,特别是外来女工的权益受损尤甚:
1、超时加班。调查结果发现,加班已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劳动法》规定“对于用人单位来说,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实际上,企业主要求加班时,一般都没考虑到1小时、3小时的限制性的规定,而是完全根据生产任务的需要来加班。43.9%的人经常加班,52.4%的人偶尔加班,不加班的只有3.7%。而且加班时间一般比较长,都在三四个小时,甚至还有一天36个小时的。我们问到“在现在工作的企业中,你曾经一天工作最长的时间是几个小时?”结果是平均值为13.0351,标准差为0.1213,最小值为7,最大值是36小时。一天只有24小时,为什么会出现36小时呢?有的女工对一天的工作时间的理解可能是连续一次的工作时间,这就是说:有女工曾经不休息连续干过36小时。
不仅如此,问到“你上个月休息了几天?”一个月至少有四周,按照中国目前的双休日制度,至少有八天的休息,但是结果显示休息8天或8天以上的只有17.9%,5—7天的17.2%,4天的25.9%,4天以下的占了39.1%。显然大部分外来女工只是休息了应该休息天数的一半。
2、拖欠工资和克扣工资。最近半年,有过被拖欠工资的占了16.3%;有过被克扣工资的占了17.8%。可见,尽管国家有关部门三申五令的不许任意拖欠工人的工资和克扣工人的工资,但是这两种现象还是相当严重的。
3、不依法签合同。劳动合同是确立劳资双方权责关系的形式。我国经济合同法规定,订立或变更经济合同应采用书面形式,一旦发生纠纷就有据可查了。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很多工厂以工人流动性大为由,不与女工签订劳动合同,而女工往往没有意识到要签劳动合同,或者往往与工厂只是一种口头协议,而未签订书面协议,这样很容易吃亏。调查发现,只有59.2%的调查对象与企业签正式合同;没有签的高达40.8%。这说明外来女工的契约意识还是比较淡薄的。
4、“押金”与“押证”。“押金”、“押证”问题是外来女工权益受损较为普遍的问题。尽管国家三令五申不许扣押金或押放证件,但是许多企业还是存在这种现象,有的还比较严重。许多工厂企业招工,先要“押金”、“押证”,收取名目繁多的费用,有的称培训费,有的称工作服费,有的称生产发展基金,有的甚至是不知名的。这些“押金”有的是无偿交纳的,有的则是到时会归还。我们在东莞的某电镀厂调查时就发现,该厂进厂时收五十元、一百元不等的押金,工资也多月不发,许多工人发觉工厂的条件太差想要转厂时,工厂就以工作不满半年或一年为由,不退回押金也不发工资来限制工人转厂。
调查问卷在问到“您进企业时是否要押金?”时,回答“要”的比例高达48.4%。要押金的数额不一,进企业押50元以下的有5.3%,押50—100元的占44.6%,押100元以上的49.1%。在问到“您进企业时是否要押证”时,女工们回答“要”的也有35.6%。
5、不办必要的社会保险。《劳动法》对所有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和福利等方面作出明确的规定以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一些企业在执行这些法规的时候存在打折扣的现象。调查结果如下:
表1: 企业为外来女工提供社会保险的情况
回答情况工伤保险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
有50.8 40.849.8
没有 36.0 42.437.6
不清楚13.1 16.812.5
从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基本上只有一半的外来女工才享受到应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不仅如此,许多女工对自身的权利也不清楚,不知道是否享受了应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
6、侵犯人身权利。外来女工中有过“被搜查”经历的比例也很高,占了16.0%,有过“被管理人员打”经历的占了4.5%,而有过“被关押”经历的也占了1.7%。“被搜查”、“被管理人员打”、“被关押”是严重侵犯女工人身权利的表现。但是,不少工厂竟然无视国家的法律存在,也无视大众媒介的舆论监督,屡屡侵害女工的人身权益。有的对违反厂规的女工进行体罚,有的怀疑女工偷东西就随意搜身(注:如1999年4月15日广州市黄浦区怀远加工厂怀疑上夜班的60多名女工偷产品,竟强迫她们脱掉裤子接受检查(参见广东省妇联:《关于流动人口中打工妹情况的汇报》(内部资料));2001年7月30日深圳龙岗区韩资企业宝源厂56名女工被怀疑偷拿原料遭到厂内管理人员强行罚站、逐一搜身(参见《羊城晚报》2001年8月25日A3版);2001年9月28日,深圳宝安区松岗镇山门村一工业区内的广田贴合纸业厂15名女工因为厂方遗失5000元而遭到“脱衣搜身”(参见《羊城晚报》2001年9月30日A4版);还如珠海瑞进电子有限公司职工在连续工作近20小时的情况下,趁下午10分钟的休息时间,在工作间打瞌睡,结果100多个工人被老板罚跪,坚持不跪的工人遭到打骂(参见杨丽琼:《应加强“打工族”权益的保障》,《农村发展论丛》1996年第3期)。)。
四、非公有制企业外来女工权益受损原因分析
(一)特殊的“三方结构”关系决定了外来女工的弱势地位
“三方结构”关系是指劳资双方与当地社会三方所构成的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资方处于强势地位。其原因是资本稀缺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因而资本处于强势地位,劳动力处于弱势地位,劳动力依附于资本。另外当地社会往往由于要引资而缺乏积极制约资本的动力,这就更使得外来女工的弱势地位得不到支持。
对于工作、工资、劳动安全、生活、厂方管理方面的不满意,不少的外来女工能忍即忍,怕丢失她们的工作。但有为数不少的人“以脚投票”,流动到另一家厂。在珠江三角洲,外来工的流动率是比较高的,但对企业来说,外来女工走后,还有一大堆的后备军,他根本不怕你走。何况辞工以后再找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企业有限,而找工的女劳动力无限。就算流动到另一家企业,情况也可能差不多,没有太大的改观。然而工人的主动流失过度频繁,也会对企业不利,因为有一半左右的工人进厂前后经过了程度不等的培训。为了避免工人“跳槽”,企业采取了各种办法,主要的有扣押金,做够一定期限再返还;延长工资发放期限,每月只发生活费,累积到年底发齐;扣押身份证等使工人失去行动自由(如果外出时遇到当地“治安队”检查,就要被关押或罚款)。可是如果是企业想辞退工人,外来工就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尽管政府一再强调企业招工要签订约束劳资双方的劳动合同,但在我们调查中签订劳动合同的数量和质量都是令人担忧的,所签订的合同也基本是老板说了算,或者只是走形式,没有实际效力。同时也可看到,非公有制企业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政府原则上不得干涉其生产。因此这种监控能力是相当弱的,不像以前的国有企业,直接的行政命令就可以随便干涉企业的管理,这也使得当地政府在执法时困难重重。
(二)外来女工的社会支持体系薄弱
珠江三角洲的外来女工,由于在流动过程中失去了在原有家乡中初级关系的保护,又难于为新环境中的社会保障所接纳,故大部分人是处在保障缺位的状况。从调查中我们也可看出,外来女工所依赖的社会力量主要还是自己的私人关系。在她们的生存和权益保障中,这些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提供支持,而正式、制度化的组织的支持力度是相当小的。我们也从相关的部门了解到,制度实施的支持系统是十分薄弱的。据有关的资料反映,目前广东有劳动保障检察员1589名,与在职工人的比例为1∶20000,远低于国家、劳动部1∶8000的要求。执法人员的配置很大程度是按当地居民的人数为标准,但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外来人员远远多于当地居民的人数,有3倍、4倍甚至是10倍之多。显然,这种制度性的支持就难于到位。尽管国家和省市政府的法律法规都体现了平等,并且多有强调妇女的权益,但是正是由于这样的制度性障碍,使得法律的落实遇到很多困难。另外外来女工所依靠的这种非正式的支持体系由于本身力量单薄而难以与资本的力量相抗衡,因而处于不利地位。作为外来人,她们不但难以进入流入地社区的保护,而且往往受到当地的歧视。
(三)外来女工的自身素质的缺乏
外来女工权益受损很大一部分与自身素质有关。限于自身文化素质较低等,加上信息的不对称性,她们除了不知道应享有的合法权益外,一旦当权益受损时还不知道寻求制度的支持与保护,也不知道去哪里寻求支持与保护。因而她们往往接受资方苛刻的用工条件,有时还维护资方的不合法要求。在调查过程中,几乎所有外来女工都先用很防备的目光看着我们,然后说一通“赞美”工厂、“赞美”老板的好话。只有当一个人忍不住说出了事情真相时,她们才会围上来七嘴八舌地述说恶劣的生存状况。这就往往在无意中“助纣为虐”,纵容了无良老板。当外来女工受伤时,她们的要求只是希望企业不要把她们当作旷工处理,不扣除或克扣她们的工资她们就万分感激。她们丝毫不知道,按国家有关规定,厂方应负责她全部的医疗费用,而且按工伤进行补偿。正是由于外来女工不了解女工的各种权利与义务,不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她们也不懂得维护。即使有外来的支持与帮助,由于她们“谨慎怕事”,也使得这些支持与帮助发生不了多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