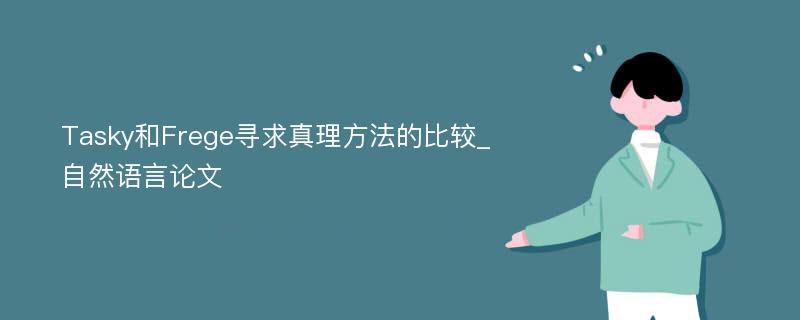
塔斯基与弗雷格的求真方法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基论文,方法论文,弗雷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81-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42X(2001)02-0062-06
自从世界上有了逻辑,求真的问题就提出来了。作为哲学和逻辑学的重大理论问题,真的涵义和所指不可避免地为现代逻辑学家所反复地探讨和论争。(注:参见金岳霖.金岳霖文集(第三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783~841;王路.论“真”与“真理”.中国社会科学,1996.6.本文所使用的“真”一词取西方哲学所探讨的“truth”或“wahrheit”之含义,与国内哲学界所使用的“真理”一词的含义有所区别。)波兰学者塔斯基(Tarski,A)和德国学者弗雷格(Frege,G)关于真的理论是现代逻辑领域颇有代表性的成果,本文拟就他们求真的方法作一比较。
一
1931年3月, 塔斯基用波兰文写作了《形式化语言中的真这个概念》,全文洋洋十万字,作者开头即明确指出:“本文几乎只探讨一个问题——关于真的定义。这篇文章的任务是参照一种给定的语言,建立一个实质上适当(materially adequate)、形式上正确的( formally correct)关于‘真句子’这个词的定义。”[1]他还用斜体表示强调这两句话。塔斯基的具体工作大致上由“前提”和“核心”两部分组成。
首先,作为分析问题的前提,他细致地考察了日常自然语言中真这一概念。他认为,我们日常所使用的自然语言,一方面预设普通的逻辑规律在其中有效,另一方面它在语义上又是封闭的,其中既包括“语言表达式”,又包括“真”、“假”等等“指称语句表达式的表达式”,这种语言系统无疑混淆了语言的层次性,因而语义悖论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断言:“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使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不说,尝试为‘真句子’这个表达式构造一个正确的语义定义遇到了很现实的困难。我们不知道有何种一般性方法会允许我们定义‘x 是个真句子’这类具体表达式的意义。”[1]他最终的结论是:“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1]。
其次,作为理论建构的核心工作,塔斯基致力于在形式语言中构造一个关于真句子的语义定义。在区分“对象语言”(object language)与“元语言”(meta language)两个不同层次的语言的基础上, 塔斯基提出了定义真的实质适当和形式正确条件。实质适当条件规定一个可接受的真之定义的内容限制,而形式正确条件则规定一个可接受的真之定义的形式规则和程序方面的要求。作为实质适当条件,塔斯基提出了约定T(Convention T),这是对真句子的一般表达方式的刻画[1]。
理解塔斯基的真之语义论,约定T是十分重要的内容。 这里有几个问题是值得强调的。
第一,约定T不是真的定义,而是真的显见形式, 是一个内容适当性条件。这种条件使得它的所有实例都必定被任何一种在内容上适当的关于真的定义所衍推(entail,即蕴含)。所以,约定T 所确定的不是“真”这个概念的内涵(即意义),而是它的外延(即它所特有的适用范围)。在塔斯基看来,一个实质适当、形式有效的真的定义必须蕴含约定T的所有实例。而约定T的每一个实例,都可看作真的部分定义。真之普遍定义便是这些部分定义的逻辑合取[2]。
第二,塔斯基认为,约定T 成立的必要条件是:①对象语言与元语言相区别;②元语言的阶高于对象语言。若不具备①, 则语句名称“x”和语句本身“p”会混淆。若不满足②, 则语句名称和语句本身就不对应[2]。
第三,既然约定T所确定的不是“真”的内涵,而是它的外延, 因此,塔斯基认为有必要运用数学上的递归方法,借助于“满足”这一中介概念间接地定义“真”。
基于以上思路,塔斯基给真下了定义。他说:“我们注意到,一旦获得了满足的一般定义,它也就自动地适用于那些不包含自由变量的特殊语句函项,即语句。最终可以看到,对于语句来说只可能有两种情形:或者语句被所有对象所满足,或者不被任何对象所满足。这样我们简单地通过下面的陈述就获得了真理和虚假的定义,那就是,语句是真的,如果它被所有对象所满足,语句是假的,如果情况相反[2]。 换一种说法,关于真的定义就是:x是真的,当且仅当x是一语句,类的每一无穷序列都满足x。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学术界对塔斯基真之语义论的某些批评并不是恰当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塔斯基的真之语义论是错误的,因为它仅从形式方面来考察真理,而排斥了真理的客观内容和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从语义上看,真与真理是两个概念。塔斯基所讨论的“truth”是“真”,而不是“真理”。 正如塔斯基在《形式化语言中的真这个概念》这篇文章中明确所说,该文“几乎只考虑一个问题——关于真的定义”。[1]事实上, 他所谓的“真”是在“真的”(作为谓词)这种意义上使用的。我国著名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在《知识论》中曾专门讨论过“真”与“真理”的区别。他说:“所谓真理和真命题不一样。真命题是一条一条的,或一丝一丝的,它是分开来说的,它不是真命题的总结构,它和真理不一样。”[3]多年来,国内学术界一直以“真理”一词翻译、 解释塔斯基探讨的“truth”一词,由此导致人们对“truth”产生一些误解。其次,从内容上看,塔斯基的真之语义论与认识论的真理概念也是有区别的。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真理作为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它是反映事物本质的知识结晶,是描绘世界总图景的理论体系。这种认识的成果也就是理论或思想,是观念性的东西,不仅需要用带规律性的真语句来表述,而且更多地表现为命题系统而不是单个的命题。但对什么是真语句,逻辑语义学和哲学认识论是运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进行研究的。当从逻辑语义学的角度问“什么是真”的时候,它所面对的是特定语言系统中的单个命题,具体地说,它要探究的是“一个命题(语句、句子或陈述)为真意味着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塔斯基关于真的定义并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定义,而是关于“在 L里为真”的定义。他写道,“被定义的概念之外延在本质上依赖于所考虑的那种特定语言。同样一个表达式可能在一种语言里是真的,而在另外一种语言里是假的或是无意义的表达式。这里根本就不会有对这个词项提出一种单独的普遍定义的问题。”[1]因此, 真之语义论和真理的认识论定义是根本不同的[4]。 认识这一点对于理解当代西方语言哲学的其他理论成果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二
现代逻辑大师弗雷格关于真的理论对哲学、逻辑学和科学领域的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弗雷格提出了自己对真这个概念的独到见解
历史上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在研究真这一问题时,一般是首先给出定义。符合论便是比较有影响的一种定义。根据符合论,一个命题符合它所陈述的事实,它就是真的;否则就是假的。亚里士多德关于“否定是的东西或肯定不是的东西为假,而肯定是的东西或否定不是的东西为真”的论断[5],即是真之符合论的典型表达。弗雷格否定符合论, 认为假如人们想以“如果一种概念与现实是一致的,那么它是真的”这种方式来得到关于真的定义,那他什么也得不到。因为若认为“概念与现实是一致的,则它是真的”,就必须先有一种预设,即在某一给定的情况下确定概念与现实是否一致。其他诸如“S是真的, 如果它有这般这般性质或者它与某物有那种那种关系”等各种解释的结果都是同样什么也得不到的,因为它也必须事先假定具有这种性质或那种关系是不是真的。因此,若想通过一条定义更清楚地说明应该把真理解成什么,那是徒劳的。真是基始和最简单的东西,不可能再还原为更简单的东西。真最重要的性质就是:它是一个基始概念,因而无法定义。
弗雷格认为,尽管真无法定义,也不能把真归结为语言与现实的一致,但人们必须从语言的角度去研究真,因为真之概念与生俱来是同语言有关的。
首先,弗雷格认为,真是一个谓词,与其他谓词相比,真这个概念的特性在于“每当表达出某种东西时,它总是被连带地表达出来了”[6],以至于不需用语言说出来。
其次,弗雷格认为,真这一谓词的独特性通过与美这个谓词的比较更进一步地反映了出来。美的东西有程度之分,我们可以发现两个对象是美的,并且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更美,真的东西没有程度之分,两个东西是真的,我们不能说一个比另一个更真。
第三,弗雷格还从形容词的角度考察了真。他说,表面看上去,真这个词在语言中是个形容词,但它与其他形容词相比具有很显然的差别。人们把真放在某个词的前面,是为了让人知道这个词是在它本来的未曲解的意义上使用的。比如说一块“真金”,并不是说金子具有“真的”这种性质,而是说这块金子含有它本来应具有的各种成份。
(二)弗雷格开启了独特的研究真的思路和方法
弗雷格是数理逻辑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不仅首先建立了初步自成体系的命题演算与谓词演算系统,而且把这些成果用于对语言特别是对真的分析。起始于弗雷格的逻辑与语言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使哲学研究发生革命性的变化,20世纪初西方哲学领域的“语言转向”即是表现之一。
第一,他致力于通过严格的形式语言的方法来研究真。他说,普通语言的不精确性和歧义性是进行逻辑分析的最主要的障碍,所以必须创立一种新工具。概念文字是以算术的公式语言为模型的,它与普通语言的关系如同显微镜与肉眼的关系,用这种语言进行推理和分析可以使我们最可靠地检验一串推理的有效性。因此,弗雷格抛弃了仅使用普通语言的方法,建立了一种形式语言,从而为逻辑的发展走上形式化道路并成为一门精确的科学奠定了基础,也为他对真进行精确的分析提供了工具。
第二,他致力于通过系统的逻辑演算的方法来研究真。弗雷格的逻辑演算是建立在他的形式语言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形式语言虽然能刻画一些推理规则,表达一些体现规律的公式,但与逻辑演算系统还有较大的差距。他说,“是只知道这些规则,还是也知道一些规则如何同时给出另外一些规则,显然是不同的。用后一种方式可以得到少数几条规律,这几条规律如果加上规则中包含的那些规律,则将一切(尽管尚未得到发展的)规律的内容都包括在内。……由于可提出的规律数量极大以致不能全部列举出来,因此只有通过寻找那些根据其力量将一切包括在内的规律才能达到完全性。”[6 ]弗雷格在这里表达了他建立逻辑演算系统的思想,即从少数几条规律(公理)和规则(推理规则)出发,推导出一切表达真的规律。
(三)弗雷格明确区分句子的意义与意谓,进而对句子提供了一种比较直观的语义解释
弗雷格在《论意义与意谓》这篇重要代表作中,对句子作了深入的独创性的研究。他从内容上把句子区分出意义和意谓,认为句子的意义是它的思想,句子的意谓是它的真值(即真或假)[2]。 句子的意义是第一层次的,意谓是第二层次的,句子的思想决定句子的真。这样,弗雷格就把对真的研究转化成了对句子思想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弗雷格所说的“思想”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思想”是不同的,他关于思想和句子、思想和表象、思想的否定、思想的结构和思想的普遍性的论述,形成了一个系统的整体,已经成为当代逻辑哲学和哲学逻辑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这个被弗雷格研究专家之一的D ·贝尔称之为“最持久最具有革命性的贡献”,至今仍释放出源源不断的能量[7]。 限于本文主题,这里不就“思想”作具体讨论。
弗雷格之所以要区分意义和意谓,与其逻辑观有直接的联系。他认为逻辑以真为对象,而真是相对思想而言的,思想又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因此,探究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和意谓成了逻辑的重要课题。弗雷格认为:“一个句子的意义是作为这样一种东西而出现的,借助于它能够考虑实真。”[6]总体上看, 弗雷格正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求真的:一是从意谓的角度直接求真;二是从意义的角度间接求真。(注:弗雷格: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王炳文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183,31,116,183。)
三
通过前面对塔斯基和弗雷格关于真的理论的阐述,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在求真的方法上既有许多共同点,又有较大的差异性。两者的相似或相通之处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们都认识到真这个概念在日常自然语言中的不可定义性。塔斯基认为,由于自然语言系统本身具有语义封闭性,并且该系统又预设普通的逻辑规律有效,因此,在日常语言里不仅难以无矛盾地使用真这个概念,更不用说为真构造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了。他指出:“倘若人们坚持日常语言与语义研究相联系的这种普遍性,那么为了理解上的一致,在这种语言中除了它的句子和其他表达式以外,我们还必须允许有些句子和表达式的名字,含有这些名字的句子,以及像‘真句子’、‘句子’、‘指谓’等诸如此类的语义表达式。然而,很有可能恰恰是日常语言的这种普遍性是引起像说谎者悖论或非自指词悖论等等语义悖论的主要根源。这些悖论好像提供了一个证明:在上述意义上是普遍的而且也是规范的逻辑定律所适用的日常语言必然是不一致的。……假如这些看法正确的话,那么与逻辑规律和日常语言的精神相符合的那种无矛盾地使用‘真句子’这个表达式的可能性似乎就有问题,因此对于那种试图给出这类表达式的正确表述的可能性也同样有问题。”[2]
弗雷格则明确表示,真作为一个基始性的概念,本身是根本无法定义的。所以,试图通过下定义的方式更清楚明白地规定究竟什么是真,那是徒劳无益的。在日常自然语言中,真这个词“总是被连带地表达”,以致于可以不必述说。弗雷格的这种观点对其他学者影响较大。由于肯定一个论断与说某个论断是真的具有同等作用,因此有人把弗雷格的这个思想推向极端,认为“是真的”这个谓词可以取消,这种观点就是“真之冗余论”(Redundancy Theory of Truth)。虽然我们没有理由断言弗雷格就是“真之冗余论”者,但它的观点与“真之冗余论”多少是有一些联系的,因为他认为,断定句的形式实际上就是我们藉以表达真的东西,只要说出一个断定句,就是肯定了某个思想是真的,而不论是否说出了“这是真的”。
其次,他们都明确地规定求真的论域或范围。塔斯基从否定在自然语言中构造真之定义的可能性出发,转向在形式语言的论域里讨论和定义真。如前所述,他认为既然日常自然语言是不分层次的,因此,这样的语言系统就不可能逻辑一致地给出真句子的定义。相反,满足一定条件的理想化的人工语言,它免受自然语言的“污染”,是一种语义开放的语言系统,在这里,语言可以分层,真这个概念可以无矛盾地被表达出来。在塔斯基那里,无论是借鉴希尔伯特元数学的称谓和思路,严格区分对象语言、元语言、元元语言……,实现语言分层;还是运用数学上的递归方法,迂回曲折地为“真”下定义,总体上都是在形式语言的系统里做文章。因此,我们不能不看到,在塔斯基的学术视野和理论框架内,求真是相对于特定的理想化的人工语言的,虽然他的思路和方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但其理论本身并不直接适用于日常自然语言。
弗雷格通过限制真的使用范围来讨论真,亦即把真看作是命题的真,把真的使用范围严格限定在有所断定的陈述句上,进而来描述和解释真。在弗雷格看来,研究真的首要前提是对“真”这一谓词的使用范围进行必要的限制,即先确定“真”的使用论域。按照弗雷格的思想,人们谈论真实际上是谈论句子的真,但并非所有的句子都能表达真。他说,“人们通常把真这一谓词用于句子;但是必须排除愿望句、疑问句、祈使句和命令句,只考虑断定句,即我们藉以传达事实、提出数学定律或自然律的句子。”[7]此外,真这一谓词并不是构成句子的语音系列, 而是对句子的意义的说明。我们称一个句子是真的,实质上是指其意义是真的。从逻辑上考虑,一个句子要包含有真正的思想或意义,必须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显然,只有断定句即命题才有这种性质,因此,也只有断定句才有真假。塔斯基与弗雷格的看法是一致的。塔斯基认为,“我们所理解的句子也就是语法中通常指的‘陈述句’……因为若干原因,把‘真的’这个词项用于句子是最为方便妥当的。”[3]
塔斯基和弗雷格得出“真之载体”(truth-bearers)是命题这个结论的意义十分深远。因为真之载体的讨论与逻辑对象的确定直接关联。按照通常的理解,逻辑研究推理,但推理不仅有形式结构方面的逻辑因素,也有心理及认识方面的非逻辑因素。逻辑研究的是有效推理的形式及其规律。在真之载体问题上排除了各种各样的非逻辑因素,明确命题是真之载体,这就从根本上确定了逻辑学科与非逻辑学科的划界标准。
最后,从他们对逻辑语义学的贡献来看。弗雷格以一阶逻辑为基础,断言真是不能定义的基始性概念,并把真看作是命题的真,进而区分出句子的意义与意谓;不仅如此,他还借助于现代逻辑的理论和方法,把对真的研究转化为对句子思想的研究,为句子提供了一种比较直观的语义解释。而塔斯基则在演绎的形式系统内证明了可以逻辑一致地引入真这一概念,进而开辟了现代真正意义上的逻辑语义学的研究方向。因为所谓句子的真,就是句子的一种最基础、最根本的意义,因而解决“真句子”这个语词的精确定义,也就是解决逻辑语义学的一个根本问题。
塔斯基与弗雷格之所以在求真方法上有不少相通之处,这与他们的哲学研究思路密切相关。不难看出,如下三个方面是两者共同的:第一,把语言(自然语言或人工语言)问题放到哲学研究的首要地位,试图通过语言的分析来澄清许多有争议的哲学概念和哲学问题;第二,致力于对句子的意义作出具体分析,并把真与意义联系起来考虑;第三,不仅从逻辑的观点看问题,而且自觉运用现代逻辑工具作为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
虽然弗雷格对真的特性作了多角度的刻画,并力图用逻辑方法与演算来描述或把握真,但总体而言他对真的探究只是对句子意义提供了一种比较直观的语义解释,因而离严格意义上的逻辑语义学的要求无疑是有距离的。
塔斯基的真之语义论作为真的形式化理论,不仅独具一格,而且自成系统,它在特定的逻辑框架内为真这个最基本、最核心的语义概念给出了“令人满意”的定义,从而奠定了现代逻辑语义学的坚实基础。与弗雷格相比,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性的巨大进步。
围绕着真这个概念来探讨句子的涵义与所指,进而形成意义理论,这是语言哲学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戴维森与达米特是当代语言哲学领域围绕真来讨论意义问题的典型代表。前者在实在论的思想背景下,提出了以真这一概念为基础的真之条件语义学,后者则高举反实在论的旗帜,围绕真与证实的关系来建构辨明条件语义学,双方的争论共同推动了语言哲学领域真之理论的深入研究。达米特的真之理论是从解读和阐发弗雷格的思想出发的,戴维森的真之条件语义学则基于塔斯基的真之语义论。弗雷格和塔斯基对后世不同的学术影响也间接地表明了他们在求真方法上的某些差异性。
[收稿日期] 2000-0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