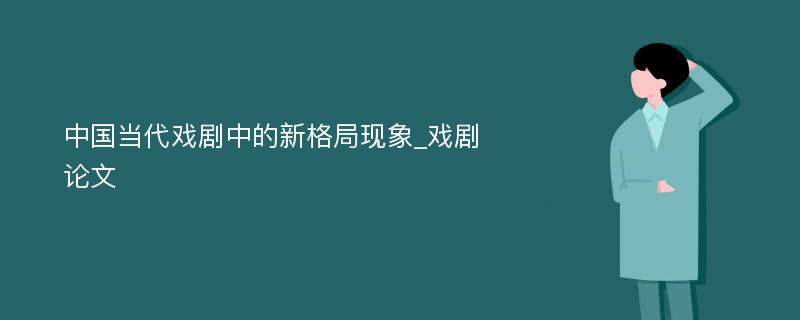
中国当代戏剧中的新模式化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模式论文,中国当代论文,戏剧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创作中的模式化和雷同化是个由来已久的问题,而在中国当代戏剧史上,这个问题却不是创造力不足和文学创作中不免多有继承与借鉴的问题,而是创作为政治服务、表现政治理念而形成固定的剧作模式的问题。当代戏剧史上的模式化是极为鲜明强烈的(注: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文章指出:“记得有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话剧舞台上只有三种剧本。工人剧本: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的斗争。农民剧本:入社和不入社的斗争。部队剧本:我军和敌人的军事斗争。这话说得虽有些刻薄,却也道出了公式概念统治舞台时期的一定情况。观众、批评家和剧作者自己都忍不住提出这样的问题:到底我们能不能写出不属于上面三个框子的第四种剧本呢?”(黎弘:《第四种剧本——评〈布谷鸟又叫了〉》,1957年6月11日《南京日报》)到了60年代,要求大写阶级斗争,又出现了模式化,例如当时写农村的戏,有人就编出顺口溜道:“队长犯错误,书记来帮助,贫农是依靠,根子在地富”,生动地描述出情节和人物关系的模式。文革时期只有八个样板戏的荒唐局面,从特定的角度看,也就是创作模式化的登峰造极的结果。),是经常的情况,曾是难以摆脱的。进入新时期后,思想解放,创作繁茂,有理由认为,创作模式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然而在90年代的农村题材戏剧中,我们又一次发现了模式化的现象,这就不能不引起重视,不能不进行认真地思考了。
1995年第三期的《剧本》月刊上刊登了河南剧作家冀振东的一个豫剧作品《红果,红了》(原名《风流小镇》)。在这之前,这个作品已经获得了1992-1993年曹禺戏剧文学奖。单单从这一个剧本来看,实在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但是《风流小镇》的出现仿佛登高一呼,跟进之作遍布全国,在此以后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面,一大批与这个剧本面目酷肖的作品,在重量级戏剧期刊上频频亮相,在各大奖项的角逐中受尽恩宠,“曹禺奖”对他们也是青眼有加。这些剧作都可以归到同一个题材类型底下:“农村题材现代戏”,从文献统计上来看,他们占这一时期发表在《剧本》月刊上同题材剧作的百分之六十,从获得荣誉情况上来看更是无可匹敌,也许是见怪不怪,到现在还没有人对这个剧作群进行定位描述,归纳其写作模式,并探讨其成因。笔者以为如同一个从DNA片断中可以推断出整个生物体的面貌与特性,对这类剧作的研究探讨,可以窥斑知豹,追问整个90年代乃至一直延续至今的剧本文学创作中的模式化平庸化的成因,并试图提出建设性意见。抱这样的意图,本文从文本出发而又回到文本,试图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归纳并评价这个剧作群的写作模式;第二,探讨其形成原因。
1
这个剧作模式是怎样的呢?让我们列举一批这样的作品来作分析。
《风流小镇》(豫剧,1995年第三期《剧本》),获得1992-1993年曹禺戏剧文学奖;
《啼笑冤家》(七场山歌剧,1994年第四期《剧本》);
《大青山》(四场话剧,1994年第七期《剧本》),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秧歌浪漫曲》(音乐剧,1995年第二期《剧本》);
《三醉酒》(现代评剧,1995年第八期《剧本》),获得1994曹禺戏剧文学奖;
《烧锅屯》(又名《补天岭下》,1996年第一期《剧本》);
《榨油坊风情》(大型萍乡采茶戏,1996年第三期《剧本》),获得1995曹禺戏剧文学奖;
《路魂》(现代戏曲,1996年第六期《剧本》);
《关东雪》(无场次现代吉剧,1996年第十期《剧本》),获得1997曹禺戏剧文学奖提名;
《李家沟的新鲜事》(无场次通俗喜剧,1997年第八期)。
先以《秧歌浪漫曲》、《路魂》为例分析这一剧作模式。
《秧歌浪漫曲》讲述一个发生在“现代北方农村”的故事:
花桥村有两个杰出的秧歌高手,李仁喜和金蝴蝶,曾经是一对情投意合的恋人,因为父母包办婚姻没有能够结合。时间推移,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乡亲们把辛苦血汗钱凑起来托付给李仁喜要他筹办秧歌会,而金蝴蝶的丈夫却在赌博中把金蝴蝶输给了别人。李仁喜不能坐视不理,便用筹办秧歌会的资金替金蝴蝶赎身,自己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金蝴蝶为了给自己的旧情人排忧解难,主动找到原来的买家要用自己换回秧歌会的资金。最后警方出面干涉,故事得到了皆大欢喜的结局。
《路魂》的故事发生在“当代”“一个叫旮旯沟的偏僻小山村”:
村长石柱和妇女主任山风曾经是一对情投意合的恋人,因为父母包办婚姻没有能够结合。时间推移,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石柱要带领众乡亲修路却没有足够资金,山风为了替旧情人排忧解难,毅然决然要嫁给一个有权有势的“韩主任”的外甥,以此换来足够的资金。最后,韩主任的大舅子周老贵赶来,阻止了这场悲剧的发生,并帮助村民解决了困难。
以上两个故事如果单独来看,还不失为有戏有情有意的好作品,可是两下一对比,就不难看出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两剧写法有所不同,但一种模式已经清晰可见。
如果用获得1994年曹禺戏剧文学奖的剧作《三醉酒》来印证一下,这一剧作模式就十分清楚了。
《三醉酒》的故事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的“关东偏僻的山村”:
村支书龙友和秀女曾经是一对情投意合的恋人,金德富运用手腕将他们强行拆散,自己将秀女据为己有。时间推移,到了改革开放的时期,龙友为了能够签下可以让村民发财致富的购买梅花鹿的合同,不得不向已经成为县银行主任的金德富求援,而金德富却因为秀女对龙友念念不忘而耿耿于怀,想方设法,不光要让龙友没钱签合同,而且要彻底摧毁龙友与秀女之间的感情。龙友与金德富斗志斗勇,秀女也挺身而出,最后挫败了金德富的阴谋,顺利签下了合同。
这个表面上似乎有所不同的故事,仍然没有脱离剧作模式,相对于《秧歌浪漫曲》和《路魂》,只不过在局部的处理上略加变化而已,上文所列举的剧作,大多属于这种情况,这里不再一一加以印证。
将剧作男女主人公用甲和乙来标志,就可以对这些剧本的叙事模式加以归纳总结:
1、甲乙曾是情投意合的恋人,过去因为外力的干涉,没有能够结合。
2、现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甲乙之一成为剧作中心事件(通常是致富事件)的责任人或主要承担者。同时,两人的爱情面临严峻考验,并且成为矛盾的焦点和解决矛盾的关键。
3、中心事件一定遇到障碍,而这一焦点问题的形成或解决总是与过去的爱情有关,因此过去的爱情线索一定在这个焦点问题上介入现实事件的线索,从而引起复杂的波澜。
4、矛盾最终得到皆大欢喜的解决,两人的感情得到升华。
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该剧作模式的实质在于:要安排两条故事线索(一条是有情人难聚首的感情线,另一条是以“发财致富”为主的现实线),让它们交织起来,造成戏剧纠葛,最后则让事业、爱情都得到满意的结局。
如果用一种更为谐趣的方法,可以用一首顺口溜来概括这一剧作模式:
过去爱情不幸福,
改革年代奔致富,
致富受了阻,
旧爱现身出,
波澜横生惊无险,
事业爱情两不误。
这个剧作模式的写作方式,是先用往事的三角恋情搭起人物关系框架,这个框架里,处于感情各端的几种人物又是当今现实生活的重要角色。戏剧主人公处在这个框架中,他既是感情纠葛的主体,又是解决现实问题的责任承担者,他一旦遇到困难,陷入危机,就必然引起人物关系框架的震荡,情感线和现实事件的线就必然纠葛起来,产生复杂激烈的矛盾冲突,整个故事模式便得以顺利展开。
从表面上看,这种模式既描写了现实(农村要致富),又写了人性(爱情婚姻问题),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然而问题在于,这是一种纯粹的写作技巧上的编织,几乎完全脱离了对于现实生活的观察思考和发掘。无论现实还是人性,都是从抽象的概念上接触的。真正的农村现实,我们仅从报纸电视的报道上看,就有大量的突出的问题,例如土地承包的政策的延续问题、粮食收购中的打白条问题,观念落后和文化低下的问题,封建残余问题……;而有关于爱情婚姻上值得注意和思考的问题也有许多许多,例如包办婚姻的问题,“换亲”的问题,强娶强嫁的问题,如果作更深思考,还可以发掘出引发爱情悲剧的根源,就是封建残余和文化落后的问题。我们并非主张写戏都要写成社会问题剧,也不是说致富和爱情不是农村的现实,但当我们看到大批剧作对负面的问题一概没有接触,一律只写具有正面意义的“致富问题”和“过去没实现的爱情”的问题,而对于这两个问题却都没有新的发现新的开掘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认为这是一种公式化概念化的写作了!这类剧作只是按照着同一种剧作模式变换着人物和场景,总是用两种线索的交织来造成戏剧性的波澜,与艺术创作的本质背道而驰,通常描绘出农村的致富和浪漫爱情交织的美好的虚幻的图景,和农村的普遍实际颇有距离。要想在这样一批剧作中找到深刻的创新的作品,是困难的事情。
2
从现在发表的大量作品的检索和扫描来看,这种模式的存在和它的局限性都是没有疑问的,它清晰地显现为一个新时期以后的当代戏剧史现象。作为戏剧史现象的研究,我们必须回答这样两个问题,第一,这个模式为什么会出现;第二,这个模式为什么兴盛几年之后就悄悄消失了。
要解答第一个问题,通常是把这个模式置放在文学史大背景下,对相关的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加以考察。而本文的做法略有不同:让我们用描述它的发生过程的方法加以回答。
8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戏剧创作的一个黄金时代,就“农村题材现代戏”来说,《狗儿爷涅槃》、《桑树坪纪事》可说是两大高峰,事实上,对于这两个剧作已经不能用题材来机械框定了,剧作家以其独到的眼光透视农民与农村生活,反思传统文化,甚至超越民族心理到人类灵魂的深度剖析。这样的剧作不是单凭编剧技巧就能够编织的。也不是简单的异军独起,而是在一系列有着同样眼光、同样意图的剧作的围绕下,众星捧月般出现在文学史中的。其他一系列剧作可能比这两个剧作略有逊色,但是同样秉承了文化与人性反思的传统,异彩纷呈,总的说来没有模式化的迹象。
从90年代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
倡导“主旋律”的指导方针的提出,这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是自然的,是现实的需要,这些都不难理解,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实现弘扬主旋律的方针,如果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从观念出发,从本本出发,对于“什么要写”,“什么不要写”给出明确的态度,归根到底,歌颂的赞美的要写,揭露的批判的不要写;正面的光明的要写,反面的灰暗的不要写,机械教条的创作精神就会改变创作的潮流,就容易造成概念化模式化的现象。
不过要形成一个这样模式化的创作局面还是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仅以中国最重要的戏剧刊物《剧本》月刊为例,观察1990年到1993年《剧本》发表的“农村题材现代戏”,它们可以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类是延续80年代创作精神的作品,第二类是急于跟上“主旋律”精神而不得法的作品,第三类是体现主旋律精神而逐渐得其门道的作品。从这三个类型剧作的消长中就可以清晰地标示这个发展的过程。
第一个类型可以发表在《剧本》1993年第七期月刊上的《这里曾经有座小庙》为例,成就不高,也没什么反响,如同流星滑落时的余晖闪耀,稍纵即逝。此后这类剧作虽然仍有零散的出现,如四川谭氏父子的川剧《山杠爷》,但是已经不能形成气候了。
第二个类型可以举《柯老二入党》(1991年第八期的《剧本》)、《来自滹沱河的报告》(1990年第十期的《剧本》)和《老宅》(1993年第三期的《剧本》)这三个剧本为例。
《柯老二入党》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农民在入党问题上遭遇重重阻碍,差点搞得妻离子叛,最终皆大欢喜,在村支书的帮忙下顺利入党。不难看出,这是一个迎合主旋律的作品,它的意图是表现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广大人民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始终保持着对于党和政府的忠贞和信任。问题在于这个故事本身,尽管抱着良好的创作意图,在编剧过程当中却脱离了实际:在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和气候之下,加入共产党根本不可能遭遇到剧本所描写的“误解”和“磨难”,同时,在艺术水准上,这个剧本也让人难以满意,所以总的来讲,这是一个“主题先行”的作品,无法得到肯定。
《来自滹沱河的报告》主要讲述了一个义务赡养孤寡老人的故事,批判以荣誉和名利为动机的所谓“好人好事”,歌颂了真正品格高尚的“平民”英雄。这样的人物生活中是有的,剧本的问题在于“主题先行”,为了写歌颂性题材,为了表现“主旋律”,就去找生活中的“好人”,把他们树为“英雄”。但这些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好人并非英雄,也不是代表时代前进趋势的“新人”,也不是有什么独特、深刻思想的人,因此,很难从人物内心挖掘出真正有写作价值的行为动机,不加拔高,戏就无甚可观,强行拔高成英雄则显得脱离实际。《来自滹沱河的报告》实际上是开了新时期以后重新兴盛的“好人好事剧”的先河。
《老宅》是一个水准较高,争议颇大的剧作。这个剧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某农村主妇和他的丈夫在解放前是地主家的佣人,受尽了屈辱和折磨。解放时地主逃往国外,夫妻两个分配到了地主家的老宅。改革开放的年代来到后,在国外身家百万的旧“东家”回乡,诚心悔过,并以优厚的条件想要换回自己的老宅,所有人都觉得可以接受,只有这个主妇坚持不同意,最后她死在了自己的老宅里面。死前高喊:“毛主席,毛主席!……您老人家在地底下都知道这些事吧!”这个剧本故事人物都好,只是故事主人公所坚持的信念与剧本主旨所宣扬的理念不合拍,看来作者既想歌颂政策的开放,又想表达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为了表现文艺政策所倡导的写作主题,勉为其难,以致出现了故事与主题脱节的情况。写来显得尴尬,甚至有一点滑稽。
这三个剧本尽管水准不一,却都反映出这个时期戏剧界的创作混乱,以及出现的困惑和迷茫。
第三个类型的剧本则小心翼翼的探索,在如何表现“主旋律”上逐渐摸到了路子。
由于“什么要写”,“什么不要写”已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剧作家在写“农村题材现代戏”的时候,可拱挑选的素材就变得非常有限了,尽管正面的光明的事情人物很多很多,但是戏剧需要冲突,需要矛盾,并不是领导作报告一样把好人好事念上一通就可以过关,从这一时期的剧作来看,经过选择筛选,越来越多的剧作家把写作的对象锁定在同样的有限的几样事物上面。
下面作一个简单文献统计:
列举1990年到1993年发表在《剧本》月刊上的“农村题材现代戏”12个,占这时期这类型剧作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中以描写男女情爱为主的有七个(《情与爱》、《三朵花闹婚》、《女大十八变》、《啊,乔老板》、《闹龙舟》、《村南柳》、《富有的女人》);描写寻求致富之路的剧本三个(《二月天》、《大地回声》、《水下村庄》);正面歌颂调解干部的一个(《爱洒人间》);描写洪灾的一个(《水淋淋的太阳》)。除去最后两个剧本属于特殊题材,其他的十二个剧本的写作素材是什么呢?正是上文提到的剧作模式仅有的两条线索:男女情爱和现实致富,同样的,对于这两个问题没有新的发现和开掘,只是在理念上抽象的描写现实和情爱,掩盖了真正的实际问题。
这其实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丢弃了透视社会生活的独特视角,丢弃了反思文化反思人性的现实取向,脱离实际的胡编乱造不能成立,就只能是平面地肤浅地描写现实生活,而生活中可以“入戏”的东西实在很少,于是最终剧作家们“集体无意识”地选择了这“两条线索”,这“两条线索”成为构成90年代中前期“农村题材现代戏”故事情节的最主要要素,在本文所描述的剧作模式之外的其他同类型作品,绝大多数所写的不外乎这两条线索而已,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作品。
剩下的问题就显得比较简单,那就是为什么最终形成的是“这一种”模式而不是其他模式呢?答案非常的明显,因为这是最有效率,也是最能够集中矛盾冲突,最能够出戏的一种编剧技法,同时,这样的编剧技法融合了情爱主题和现实问题,又能够最大程度的体现“时代精神”和“深刻的主题思想”。
我们可以看一看《富有的女人》(1990年《剧本》第二期)这个剧本,实际已经初具了本文所描述的“模式化剧作群”的雏形。主人公是致富发财的尖刀兵,掌握着整个村庄发财致富的关键,而同时她情感坎坷,围绕在她周围的几个男人分别扮演着红脸白脸各类角色,在她为事业奋斗的时候起着或好或坏的关键性作用。如果对比《风流小镇》,这个剧本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情节拖沓,故事松散,其内涵与主旨与《风流小镇》相差无几,所用篇幅几乎翻了一番。《风流小镇》将情感纠葛的主体和发财致富的主体合而为一,最大程度的集中了矛盾冲突,最有效率的组织了故事情节,而《富有的女人》苦心经营要将男女情爱与探索致富道路结合在一起,却因为人物众多,故事分散而显得处处用心却处处不着力,尽管这个剧本也获得了“全国优秀剧本奖”,也就是后来的“曹禺戏剧文学奖”,但和《风流小镇》对比起来,在编剧技巧上的不足是一目了然的。由此看来,从《富有的女人》到《风流小镇》是剧本文学内部模式选择的必然结果。当《风流小镇》以最有效率的方式组织有限的写作素材的时候,标志着“农村题材现代戏”最终艰难地找到一条似乎可以周旋于艺术与政策,周旋于得奖与好看之间的最佳路数。
这个剧作模式盛行一时,但是短短几年之后就销声匿迹,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恐怕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这些剧作家的写作目的是什么?显然不是为了艺术,恐怕也不是为了观众和票房,而是为了得奖。文艺政策为了鼓励剧作家写出符合主旋律的作品,用各式各样的奖项进行鼓励,与各种奖项密切相关的就是配套的福利政策和职称评定的体制。一个作品一旦获奖,主创人员除了获得可观的金钱上的奖励,还为自身职称的评定积累最有价值的资本,无论是剧作家、导演还是演员,都无法回避这个现实的问题,于是一台戏从剧本到导演到表演,所要迎合的最主要的是评奖的需要,艺术上的追求与创新和市场的观剧需要,反而成为次要的问题。自然而然,剧本创作所需要服从的就不再是艺术的规律和市场的规律而是评奖的规律。而评奖的规律比较轻松就可以摸熟摸透,而且相对简单地就可以加以模仿,于是有人创造出了一种上下讨好左右逢源的写作模式,其他人一哄而上加以模仿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从这个剧作模式来看,最初的几个作品的确可以让人眼前一亮,既符合了主旋律的需要,故事又编得紧凑,有较强的可看性,于是在各种评奖的活动中屡屡得奖。可是跟进的作品实在太多,这个剧作模式提供的创新空间又是相当的狭小,可想而知,这样一大批面目相似的作品是不可能一直受评奖评委的青睐的。由于再也不能得奖,于是这样的剧作模式就自然被淘汰了。
《李家沟的新鲜事》是新模式戏中发表时间最晚的一个,可以说是这个“剧作模式”消亡的标志。然而,我们一点也没有松了口气的感觉。就在这个“新模式”大行其道的时候,出现了可说是整个九十年代农村题材现代戏中最出色的作品:川剧《山杠爷》。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可以理直气壮地和“模式化剧作群”划清界限。遗憾的是,它虽然是真正的佳作,却决无《风流小镇》那样一呼百应的影响力。它仿佛落入了曲高和寡的境地,有人喝彩无人跟进。该剧作者谭氏父子则在获奖后大叹诞生过程太难的苦经:“写戏难,写现代戏更难……领导支持,专家帮助,群众努力,……写《山杠爷》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超越——艰难的超越。”(注:《艰难的超越》,《剧本》1996年第12期。)显然,《山杠爷》是寂寞的。这让我们意识到,新模式的迅速消亡无非是一种故事模式用滥以后被弃用而已。产生模式化的条件却仍然存在,写作素材的狭隘以及编剧眼光的平面化庸俗化不只这个“剧作群”所独有,而是戏剧创作的通病。因此只要需要,新的故事模式随时都可以被发明,概念化模式化的噩梦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对生于又死于90年代中期的“剧作模式”,我们决不能视为已经过去,应当重视它的警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