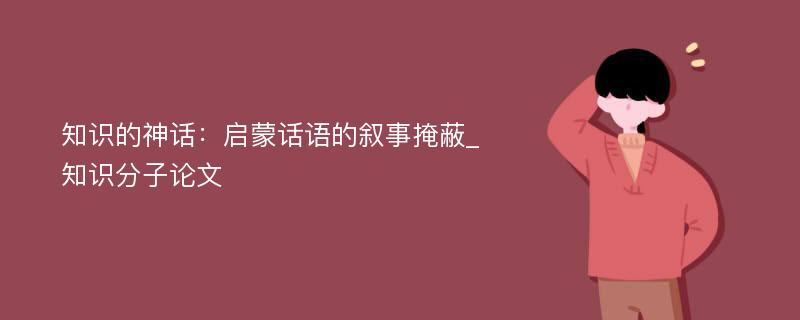
知识的神话:启蒙话语的叙事遮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神话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民性理论的先天缺陷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相继失败,向寻求中国富强的知识分子昭示了一个道理:在人民当惯了并继续当奴隶的国家里,政治革命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惟有从思想文化上唤醒人们的觉悟,才有可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于是,一场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应运而生,这就是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它将一批文化知识分子推上了历史的前台。启蒙的登台既是历史逻辑的发展,又是文化知识分子对社会职责担当的结果。尽管有论者强调“中国近现代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从根本上说是适应中国文化与时代的内在需求而产生和发展的”[1],但是西方理论在启蒙运动中还是充当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这就是国民性理论。中国启蒙的主题,研究者们一致认为是改造国民性,而据刘禾考证,流行于19世纪欧洲的国民性理论是梁启超等晚清知识分子通过日本而引入中国的。1889年至1903年梁启超写下大量文章,论述国民性问题成为中国向现代国家过渡的一大障碍。1911年前后出现的主要报章杂志,无论是进步还是保守,都不同程度地卷入有关国民性的讨论,它们使国民性理论在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和《我之爱国主义》将国民性问题与传统文化问题相提并论,把国民性当成中国传统的能指,让前者承担中国落后的一切罪名,从而使“国民性”的意义向国民劣根性滑动,成为不折不扣的贬义词。[2] 因此,即使承认中国文化内部蕴藏着启蒙的需求和动力,西方国民性理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广泛传播至少为中国启蒙运动提供了思路。
当中国知识分子通过日本接触到国民性理论时,它其实已通过传教士进入中国。以来华的北美传教士Arthur Smith(明恩溥)的《中国人气质》(今译《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为例,该书于1889年先以文章的形式登载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1890年在上海结集出版,据作者说它在中国和东方的洋人圈中广为传睹。它总结了中国人的26个气质特征,这些特征不管中国人怎么看,在明恩溥的眼中无疑是负面性的。他的写作目的是要发现“中国人的问题”,“关注究竟用什么方法来使人类中那么大一部分人取得进步”。他认为中国所需要的是人格和良心,“要改革中国,就一定要在素质方面追根溯源,一定要在实际上推崇良心”,而基督教文化可以满足中国的这种需要。[5] 从明氏关于中国变革的观点看,中国启蒙运动的思路确实与西方国民性理论有着相承关系。我们很难知晓当时这本书是否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而它通过日译本影响中国知识分子是毫无疑问的。鲁迅在留日期间看到其日译本《支那人气质》后,才开始认真思考经由文学改造国民性的途径,它构成了鲁迅国民性思想的主要来源。
明恩溥在华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的乡间传教,他对中国人特征的论证建立在对乡村生活和农民的观察上,他在该书引言中说,“一个外国人在一个中国城市呆上十年,他所知道的人们的家庭生活内容,还不如在中国乡村住上一年。家庭之外,我们必须把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生活的单元。因此,正是以一个中国乡村为立足点,这些文章才得以写成”。在他的另一本详述中国乡村的社会、文化结构的书《中国乡村生活》中,他同样认为“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4] 明恩溥虽然没有像1930年代的费孝通那样提出“乡土中国”以概括中国社会、文化特征,但是他已经明显指出了中国社会的乡土特征,而明恩溥对李景汉等社会学家的影响,也不能说“乡土中国”概念的提出与明恩溥无关。这正是明氏西方文化、生活背景使然。已经城市化、工业化的西方与尚停滞于农业时代的中国间的差别是一目了然的。在明氏的思路中存在着一个双级跳跃,当他把乡土特征等同于中国社会特征时,他也把一个中国乡村农民的素质当成整个中国人的素质。在明氏这里,中国与西方的对立暗暗演变为乡土与城市的对立。尽管我们很难在明氏与中国启蒙运动将农民定为批判的主要对象间建立直接联系,但是受《中国人气质》一书很大影响的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一开始就指向了农民。而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学国民性叙事的典范,他影响了一个世纪的中国乡土作家。
二、启蒙的基础:知识的权力
不过,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长远影响的还是明氏的西方眼光,或者说是现代眼光。启蒙知识分子接受国民性理论必须以接受其中包含的西方眼光为前提。如前所述,西方看待中国的眼光建立在它自身的工业化、现代化基础上,以此为标准,它看到的肯定是中国的前现代性。也就是说,在中国语境中,现代性眼光指向的就是乡土。因此,接受国民性理论和西方文化影响的启蒙运动将中国农民当成启蒙的主要对象势属必然。但是,启蒙运动将西方眼光转化成自己的眼光是有条件的。在分析《阿Q正传》时,刘禾指出,如果小说上演的是中国国民性,那么就要追问,在这个国民性理论的中国版本里,“叙事中什么声音使得阿Q和国民性向批判敞开?批判者的意识从哪里来?”在阿Q死前画押的情节中,她认为,阿Q丧失地位,在于他未能掌握书写符号,而“叙事人无论批评、宽容或同情阿Q,前提就是他自己高高在上的作者和知识地位”。[2](P97) 知识,包括对西方知识的掌握,使叙述人成为具有批判能力或免受批判的主体。这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启蒙者身份的确认建立在掌握现代知识这一点自信上。《阿Q正传》的叙述人特殊之处在于,他既娴熟旧学,也通晓新学(或者说西学),但是他对新旧学都不满意,对《新青年》和胡适代表的新学的揶揄,可见他并不是一个西学的盲从者。刘禾认为,鲁迅对叙述人知识背景的设置所体现的是他对西方国民性理论既接受又拒斥的态度,《阿Q正传》是对明恩溥支那人气质理论的超越和改写,它否定了其中国人必须被西方人拯救的论断。但是只要西学构成了知识分子的知识背景,知识分子就不能逃脱西方眼光的控制。国民性理论作为西方建立其种族和文化优势、为西方征服东方提供进化论的理论依据,它以高高在上的优越姿态对待中国是毫无疑问的。那么,继承国民性理论,接受西方眼光的中国启蒙运动似乎也难以摆脱它对待中国农民的超越态度。
以上论述,与其说证明了中国启蒙运动与西方国民性理论间的密切联系,不如说显示了启蒙话语依持的现代性价值所隐含的知识-权力关系,将它与西方传教士话语放置在一起,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这点。福柯认为,知识是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主体可以占有一席之地,以便谈论它在自己的话语中所涉及的对象”[5],因此,“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的建立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6] 谁掌握了国民性理论,谁就获得了话语实践的主体位置,谁也获得了阐释对象的权力,而对象则被迫去适应话语要求。就启蒙话语讲,知识分子不仅能够置身国民性话语之外,还拥有言说他人的话语权。现代价值标尺之下,那些匍匐在土地上、最不引人注意的农民才从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深渊里裸露出来。
近些年来一般人都骂中国人自私,甚至举以与贫、愚、弱共列为四大病,俨然自私是中国人的定评;其实完全误会了。难道中国人从血里便带来自私吗?断不会有某民族先天性的格外自私的事!不过中国社会构造恰与西洋不同,从而养得的习惯也两样,试从上面种种的比较去看,不难明白的。中国人这种与西洋人相异的生活习惯,从来也不曾被人唤作自私,而逢到国际竞争剧烈的今天,顶需要国家意识、团体行为,而他(中国人)偏偏不会,于是大家就骂他自私了。自私可以说是“反社会的”,一个民族果真有这严重的病症怕早已不能在天地间存在。何以我们民族生命的扩大竟成了世界少有的广土众民的国家?何以我们民族生命的延续竟维持了四千年不断的历史?为此言者何其不假思索耶?[7]
农民在现代语境中被制造成中国前现代性的代表、被启蒙的对象。在此情境中他们只有被言说的自由,自然也就难逃被改写的命运。范家进在分析鲁迅小说时指出,既存在农民对民主革命的冷漠,也存在“知识分子和上层社会文化环境变革对他们质朴合理的生活欲求的冷漠、对他们具体生存环境的无能为力以及对他们真正精神需要的不同程度的无知、隔膜、冷漠、以至无关和‘逃避’”[8]。在执着的现代性追求下,农民成为现代性话语的牺牲者,他们所需求的就是不断的被启蒙,被现代化,而其他的需求利益根本难以进入启蒙者的视野。这就不难理解,在早知农民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绊脚石时候,为什么农民屡屡成为城市利益的牺牲者;为什么农民总是处于现代化的边缘,进展缓慢;为什么农村、农民总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被作为问题提出来。正如论者已经指出的,“拒绝对现代化的任何反思,其结果已经看到,就是对农民的牺牲,这种牺牲是首先把他们变成沉默的羔羊:替罪羊”[9]。当农民的利益需要被我们所忽略时,我们其实也就是对他作为人这个事实的缺乏尊重。这样说来,现代性价值应该在中国语境中得到检视,否则农民总是要被钉在前现代性的耻辱柱上,中国落后的账总是会算在农民的头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中国文化实质上就是农民文化,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是个农民社会改造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要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与农民人格”。[10]
三、启蒙的叙事遮蔽
我们还记得,闰土喊出的一声“老爷”,一直被我们当作封建礼教和等级观念规训下闰土麻木、沉默的例证。可是那一层挡在“我”与闰土间的“可悲的厚障壁”是被规训的闰土制造的,还是获得新身份的“我”呢?
作品显示了“我”与闰土间的隔膜,这种隔膜是“我”对自身身份的充分觉察,“我”相信外出求学谋生的经历已经使“我”大不同于闰土。这种身份阻止“我”沉湎于儿时琐碎的乐趣,也使“我”不知对闰土说什么。而闰土呢?他总是问起“我”,说明儿时的短暂快乐同样令他难以忘怀;他如期到来,说明他对“我”回来重温那种友好和睦的情感充满期望。但“我”在相貌和衣着上的表现,特别是“我”的沉默令他不知所措。今天的闰土和过去的闰土一样,相对“我”来说,他都是主家的一个帮工,他对“我”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对他的态度,他可能强烈地意识到“我”不再是那个“飞跑的去看”他的少年了,于是他也相应的选择了对我恭敬的称呼。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与闰土间的“障壁”其实是“我”一手制造的。“我”的知识分子身份成为“我”与故乡之间不可逾越的屏障。故乡被放到“我”的对立面,“我”既然选择作了现代性价值的代表,那故乡就成为一个要接受现代性审判的前现代性符号。
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张承志《黑骏马》中。叙述者“我”在对待索米亚被强奸这件事上,与草原牧人有根本的差异。“我”将这件事看得无比的重要,甚至可以用生命搏杀。“因为几年来读书的习惯渐渐陶冶了我另一种素质吧……我不能容忍奶奶习惯了的那种草原习惯和它的自然法律……渴望……追求更纯洁、更文明、更尊重人的美好、也更富有事业魅力的人生”。“我”这么说的时候,实际上“我”就成为文明、理想的代表,而且牧人则成了野蛮不开化的群体。知识不仅没有为理解劳动者的生活提供帮助,反而将加深两者间的隔膜。闰土的沉默无语,索米亚的警惕躲避,他们原本渴望诉说的心灵向知识者关闭,不自觉地遁入黑暗与隐秘。因此,知识与其说是要照亮乡土的晦暗,不如说是它首先在文化层面生成它的晦暗。
乡土、或者说是农民的无语,为知识者叙述他们留出了一个阔大的空间,他可以根据先在的知识理念来塑造他所认可的农民形象。如葛红兵指出,“阿Q是一个在启蒙偏见之下被塑造出来的人物,因而他作为一个农民身上的正面要素完全被低估了,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是这样一个身上正面要素被低估了的农民形象,其被当作反面典型加以认定的东西,依然有许多是值得我们要探讨的”[11]。知识分子在观看乡土世界时,他天生持有一个过滤框架,通过这个过滤框架的农民要遭受变形的待遇。以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农民女性黄久香形象为例,可以看到农民形象是怎样在知识分子叙述中变化换形的。在章永璘恢复性功能的前后,黄久香的形象是千差万别的。她对丧失了男性功能的章冷嘲热讽,极尽蔑视之能事,为了满足欲望,明目张胆地与人偷情。此时的黄鄙陋、浅薄,完全是肉欲的化身,叙述者以此来掩盖知识者的无能、嫉恨。当章恢复性功能后,黄淑娴,隐忍,对章的抛弃毫不怨恨,在分手前夜,黄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肉体,以之愉悦、温暖于章。此时,黄的形象从粗鄙的荡妇升华为宽厚广大的大地之母。然而这不过要减轻叙述者抛弃黄的负疚感,并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样的人道主题寻找出口。但是黄形象的变化并不能掩盖在章看来黄是作为肉体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她的脑子只能理解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灰色的事物、模糊的事物,对她来说太费解了”。恢复了性功能的章也恢复了思考写作的能力,在章不愿仅仅作为肉体而存在时,他与黄的关系就必须结束,因为他们缺乏理解的基础。可是黄当初愿意嫁给章,正是看中了他的知识分子身份,在他的身上有那些只追求肉欲满足的粗男人所未有的其他内涵。可见,黄是一个被知识任意贬低的形象。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十七年文学”中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形象。《我们夫妇之间》的男主人公、《刘三姐》中的秀才、《创业史》中刘淑良上大学的前夫,这些以知识为伍的人都成为道德上有问题的人物。而农民形象前所未有的光辉起来,他们不仅具有淳朴、勤劳的品质,更获得了智慧、意志坚定、大公无私、眼光远大的新素质。当然,“十七年文学”对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塑造本身就是对五四以来启蒙话语的反拨。除却政治话语强行推行这种转变外,“十七年文学”面对的社会状况已经大不同。被五四知识分子认为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障碍的农民却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他们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前进。除了政治话语的压制,这也是十七年文学叙述无法避开的事实,从这个角度说,启蒙话语对农民形象的塑造至少是有偏颇的。
启蒙叙述的目的是要重构农民的文化身份内涵。启蒙者相信,通过“张个性尊精神”的立人方式,能使“国人之自觉至……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这是启蒙的坚定信念。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提供出一个否定性的版本,企图引起被启蒙者的警觉和批判,除旧立新,重组文化身份的构成内涵。但是当启蒙者以“农民是麻木的、愚昧的、狭隘的”这样的肯定方式来对农民身份的内涵进行判定时,它的实际效果之一是无形中抬高了启蒙,抬高了知识,因为启蒙者之所以能够下判断,就因为判断正是建立在知识之上。这样,启蒙者无疑是在制造一个现代知识文化可以克敌制胜的神话。这种立人的思路似乎无懈可击。但是费孝通在《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两篇文章中指出,“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在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农民对现代知识文化、价值观念的接收是需要物质基础的,在农村的社会结构、农民的生存状况得不到改变的时候,这些东西是不能被他们真正掌握的。不识字,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确是农民愚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费孝通认为,农民不识字不是因为他们在学习能力上天生低人一等,而是在他们生活中文字是一项多余的工具。一方面,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在面对面的交流中,文字,甚至是语言都不一定是传情达意的恰当方式,表情、动作有时更有优势;另一方面,乡村生活周而复始,缺乏变化,无所谓新鲜事物。生活经验的积累无须以累积的方式进行,而是不断的重复,语言就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12] 由此,对农民现代品格的塑造是不能独独在精神上完成的。其实知识分子的自身经验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启蒙思想影响下,这些企图开启民智的知识分子最热衷的事业是教育。对还未被侵蚀的孩子进行现代教育,无疑是塑造新的国民性的可行途径。但现代小说向我们表明,这也不过是知识分子的理想罢了。《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倪焕之》中的倪焕之、《追求》中的张曼青、《二月》中的萧涧秋、《财主底儿女们》的蒋纯祖,这些深入乡村企图传播现代文明的知识分子最后无不破灭了他们的追求。以现代精神的力量来独战中国前现代的种种阻力,在这些现代知识分子身上尚不可能,更遑论在他们看来沉浸于前现代深渊中的农民。
我们说五四知识分子制造了一个知识的神话,不仅是指他们对知识力量无比的相信,还因为它在之后很长的时间里没有受到质疑,相反还在继续张大。这是指,当今的广大农民对于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观念的笃信。就今天的农民而言,他们根本的苦境在于贫穷,这导致了他们在一切方面的弱势地位。虽然读书一直是中国从古到今的改变命运的一种方式,但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不同在于,它不再对个人的出身,或者阶级所属做出要求。它向人们昭示:只要努力奋斗,有能力就能获得教育上的成功,从而理所当然地占据权力位置,并享有非同一般的物质报酬。文学同样也在传播加深这样的观念。这主要指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如贾平凹多数小说中贯穿的一个以他自己为原型的、通过考试上大学并成为城市知识分子的农家子弟形象,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刘震云的《塔铺》,李佩甫的《败节草》、《豌豆偷树》,关仁山的《红月亮照常升起》以及一些知青小说也涉及此,像史铁生的《插队的故事》等。但是真正像《败节草》中的李金魁那样的通过读书最后当上市长、掌得权力的农家子弟还是凤毛麟角,他们更多是高考的落榜者,《人生》中的高加林、关仁山《太极地》中的邱满子、《伤心粮食》中王立勤、《平原上的舞蹈》中的尧志邦、毕飞宇《平原》中的端方,他们都不得不重新接受回家种地的命运。布迪厄认为:“教育体系,对每个人提出了相似的要求,即他们要拥有教育体系所没有提供的东西。这些东西主要是由语言和文化能力以及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构成,而个人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只能由家庭教育在传承主导文化时创造出来。”[13] 然而课程的分类是遵循阶级权力划分,精英教育知识基本上是围绕主导阶级的文化和能力组织的。能提供配套家庭教育的必定是那些掌握或者获得相关文化资本的家庭。因此在布迪厄看来,由于早期教育中获得社会价值能力的机会的结构性的不平等,下等阶层家庭的学生,在学校体系中不容易获得成功。但是教育为每个人提供机会却是平等的,这样它就把结构性不平等转化成个人差异,教育上不成功的人往往被贴上无能或无知的标签。他们被排除在权力之外,辛勤劳苦地生活就都是理所当然的。而那些教育上获得成功的下等阶层学生,他们不仅要有超出平常的才智,还得付出更多努力。因此,所谓知识改变命运也不过是知识—权力机制制造出来的一个意识形态。接受了这样的观念,也就是承认现存的等级划分、权力关系、利益分配方式的合理性,那么农民改变命运的机会始终是些微的。因此,对他们来说,所谓知识改变命运不啻是个不可实现的神话。
四、启蒙的反思
“……不真实的陈述并非是神话合适的涵义。而且神话也不是非真实的陈述,因为神话可以构成真实的最高形式,虽然是伪装在隐喻之中。”[14] 这里所说“知识是神话”,正是从神话是“真实的最高形式”这个意义上来讲的。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启蒙的可行性是建立在对知识的信任上的。然而知识与权力间纠结缠绕的关系,使知识在启蒙过程中担当了这样的角色:不仅在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制造隔膜、划分等级,而且制造被歪曲的农民形象,进而变成意识形态。知识的这种作用没有能引起知识分子的自觉,相反变成了超稳定的、真理性的东西。这与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有关。有论者指出,五四以来的知识话语“在努力描绘文化现象或在提出解决现实困境的文化方案时,也体现了知识分子对自身在理论话语展开过程中所处的复杂关系及如何通过理论话语发挥社会批评的功能缺乏自觉”[15]。对启蒙话语的肯定意味着对知识身份的深信,它必形成新的遮蔽。
因此,启蒙话语的缺陷应得到知识分子的检讨。首先,启蒙话语所依持的国民性理论是西方为了证明自身民族、文化的优越性,进行殖民扩张的文化工具,用它来启示中国民众,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状况,其有效性本身就值得怀疑。其次,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并不会单单聚集在某类人的身上,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同样是传统所争夺的对象。贾平凹说,“当我已经不是农民,在西安这座城市成为中产阶级已二十多年,我的农民性并未彻底退去,心里明明白白地感到讨厌,但行为处世上不自觉泛起”[16]。传统的负担对知识分子来说也不是轻易可去除的。作为启蒙者他们同样应反省自身,而不应占据精神上的居高临下的位置。第三,启蒙的价值尺度,现代性,也不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往往只注重现代化的诉求,而经常忽略人的需求。因为要现代,我们可以一方面牺牲农民的利益,一方面又把农民的难以现代化归结到他们自身。农民成为了现代化煎锅上反复被翻转的小鱼。第四,正如福柯所揭示的,启蒙实践的是这样一套话语机制:“权力以符号学为工具,把‘精神’(头脑)当作可供铭写的物体表面,通过控制思想来征服肉体;……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不仅仅是关于个人与社会的理论,而且形成了一种关于精密、有效和经济的权力技术学。”[6](P113) 启蒙者和被启蒙者都被符号权力所扭曲,被启蒙者成为一个沉默的他者,被人言说的命运意味其生存经验将遭到排斥。启蒙者则偏离了他的初衷,他的言说被打上了蔑视人的印迹。但是对启蒙话语的检讨,并不说明不需要对我们文化中、民族性格中的不合理内容进行批判了。觉察到启蒙话语一厢情愿的言说方式的弊端,我们所考虑的应是一种以对话方式展开的启蒙。
标签:知识分子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神话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读书论文; 闰土论文; 现代性论文; 阿q正传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