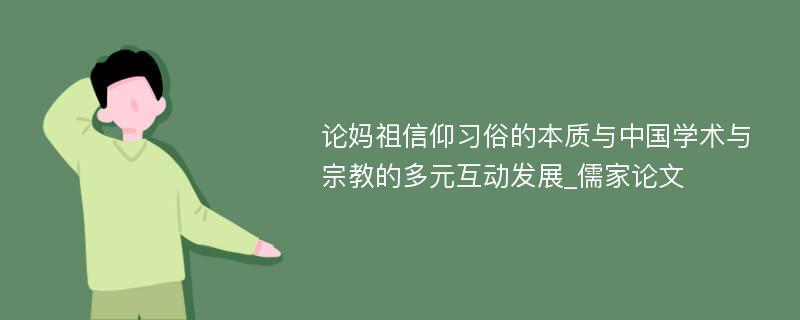
略论妈祖信俗的性质及中国学术与宗教的多元互化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妈祖论文,中国论文,宗教论文,性质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略评有关妈祖信俗的性质的歧见论争
关于妈祖信俗的宗教属性及社会性质问题,目前在学术界尚是观点分歧较多、争论较大的问题。例如:李露露《妈祖信仰》说:
妈祖是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海神,也是万能之神。但是,她属于什么宗教?具有什么性质呢?目前学术界有几种观点,一种认为属于佛教,一种认为属于道教,一种认为是佛教、道教和儒教的合一。从某些现象上看,三种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仔细推敲,她又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宗教,而是一种民间信仰,但她深受佛教、道教、巫教和儒家思想的影响。〔1〕其实,上述观点包括李露露的看法, 都未能正确全面地反映妈祖信俗的真相。依笔者浅见,妈祖信俗自产生之时起,就是一种不断超越地区、阶层、宗教乃至民族局限的多面体、多功能的信仰,因为不同宗教、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乃至不同种族的人,都先后投入参予这一信俗的创造与发展的历史潮流过程中,因而在不同的方面给妈祖打上自己的印记,同时又可把妈祖请入不同的宗教和不同性质的庙宇中。因此,我们可以就某一或某些庙宇的宗教及社会性质来具体分析它或它们供奉的妈祖的属性,但不可以把这样归纳出来的部分妈祖的性质当作全部妈祖的性质。例如:说妈祖只“是一种民间信仰”的观点,就是既不符合妈祖神象曾分别为儒道佛三教的殿宇接纳的事实,更不符合妈祖自宋迄清皆受地方官府以及中央朝廷的尊崇和引导的事实。其实,反映妈祖信俗的多面性和复杂性的各种例证,是十分多而且是不少学者都引述过的。但是,要正确认识这些例证及其蕴藏的结论,就必须同时对中国学术与宗教的多元混合发展的历史进程,有一较为全面正确的认识。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全体的认识与对局部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笔者认为,妈祖信俗之所以呈现出上述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是由先秦至唐宋,中国学术思想与宗教文化的多元互化发展的结果。我们既可以通过对整个历史进程的总体认识来给妈祖信俗一个正确的定位,亦可以通过对妈祖信俗之研究来矫正对历史进程的总体偏见。因此,研究妈祖信俗,不能只局限于妈祖出生以后的时代,而必须广泛联系妈祖以前的中国学术与宗教的发展史。
二、简述陈寅恪对儒道释三教关系的分析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指出:
……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数百年间,道教变迁传衍之始末及其与儒佛二家相关系之事实,尚有待于研究。此则吾国思想史上前系所遗之缺憾,更有俟于后贤之追补者也。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见旧唐书柒经籍志下)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集三教之学士,讲论于殿廷,是其一例。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2〕
以上之论,正确指出了“自晋迄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的基本事实。虽然,各教都有或明或暗,或主动或被动,或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异教某些成分,总之都有因互相影响而产生变化,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但是,三教的主体分别及鼎立是始终存在的。尽管历代都有人主张三教合一,甚至创立三教乃至多教合一的教派,但实际上大都是假的三教或多教合一——以旧的某一教为基础兼并其他教。现代有的学者在谈论儒释道三教合一时,往往惑于假象而不能说明以上实质。而陈寅恪的高明深刻之处,就在于既肯定三教始终分立的事实,同时又扼要地指出了三教互相影响变化的原因过程。他指出;
……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钜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如六朝大人夫号称旷达,而夷考其实,往往笃孝义之行,严家讳之禁。此皆儒家之教训,固无预于佛老之玄风者也。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六朝以后之道教,包罗至广,演变至繁,不似儒教之偏重政治社会制度,故思想上犹易融贯吸收。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其先导。……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3〕自宋代开始产生的妈祖信俗, 之所以形成前述三教皆参予其创造与发展的复杂局面,陈寅恪的正确观点可以说给我们提供了解秘的钥匙。反之,妈祖信俗也为我们理解陈寅恪理论的深义,提供了一系列的最佳典型例证。一方面,是来自印度但是至唐宋时已经相当中国化的佛教,通过参予源于中国的妈祖信俗的创造与发展,使自己变得更中国化和通俗化;而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则仍然在坚持本民族及本教地位的情况下,仿照和吸收了佛教及另一教的一些形式与方法,创造出具有一定的异教色彩,但又确是本国本教所崇奉的女神。下面,就分别对一些例子作专题讨论分析。
三、三教同予妈祖信俗例析
(一)儒家政教对妈祖的尊崇及祭礼
宋代新儒学乃儒学自魏晋衰落以后的大复兴,如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指出:“……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之世。”〔4 〕从宋初名相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便已揭开了以新儒学为主导的宋代政治学术新局面。故此,妈祖能从一个小岛渔民所崇拜的偶象,变为朝廷所钦定尊崇的保国安民的女神,主要就是得力于供儒家士大夫官僚们的大力倡导。属于儒家政教系统的拜神自有一套异于佛道二教的祭仪、祭品以及祭器。现征引有关文献证据举例略析如下:
(1)宋绍兴十四~三十年(1144—60), 陈宓撰“白湖顺济庙重建寝殿〔上梁文〕”云:
……伏原上梁之后,神人安妥,年谷顺成。无风鱼之灾,士有云龙之庆。春秋载祀,来千里之性牢,亿万斯年,报九重之宠命。〔5 〕今案:查陈宓传载《宋史》卷四零八,其人乃理学大师名儒朱熹之入室弟子,自少受朱熹器异。后历任地方及朝官,常兼任儒家官学及私学之职掌,在儒学界很有声望,遗著有《论语注义问答》、《春秋三传抄读》等。后被追赠为“直龙图阁”,故其集称《龙图陈公文集》。上引文中的“春秋载祀,来千里之牲牢”,表明对妈祖的祭礼是儒家传统的用家畜牺牲来献祭。
(2)宋绍熙三年(1192), 楼钥撰“兴化军莆田县顺济庙灵惠昭应崇福善利夫人对灵惠妃《制诰》”云:
敕:明神之词,率加以爵。妇人之爵,莫及于妃。倘非灵乡之著闻,岂得恩荣之特异。具某神壶彝素饬,庙食愈彰。居白湖而镇鲸海之滨,服朱衣而护鸡林之使。舟车所至,香火日严。告赐便蕃,既极小君之宠;祷祈昭答,遂超侯国之封。仍灵惠之旧称,示褒崇之新渥,其只朕命,益利吾民。〔6〕楼钥也是著名的儒家文士官僚, 其传载于《宋史》卷三九五。当朱熹以论事忤权臣韩侂胄而遭革职时,楼钥“言熹鸿儒硕学”,请皇帝“闵其耆老”而保留其修史及讲筵之席。今观上引楼氏为皇帝所撰封妈祖为“灵惠妃”的敕文,是站在儒家的政治宗教立场上,代表皇帝向妈祖神发出诰命的。目的是要妈祖继续为效忠皇命、保国安民而显灵。
(3)刘克庄《到任谒诸庙之一——谒圣妃庙》云:
某持节至广,广人事妃,无异于莆,盖妃之威灵远矣。某,妃之邑子也,属时虞,惕然恐惧。妃其显扶默相,使某上不辱君命,下不贻亲尤,它日有以见鲁卫之士。妃之赐。敢告。〔7 〕今案:刘克庄曾就学于名儒真德秀,观上引之祷祝文,向“圣妃”(妈祖)所求为使自己“上不辱君命,下不亲尤,它日有以见鲁卫之士。”纯从儒家的忠君孝亲传统观念出发,可谓儒家官僚士大夫个人拜妈祖的一个典型事例。
(4)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封《护国明天著天妃诏》云:
制曰:惟昔有国,祀为大事。……今遣正奉大夫宣慰使左副都元帅兼福建道市舶提举蒲师文,册尔为护国明著天妃。……尔其服兹新命,以孚祷祐我黎民;阴相我国家;则神之享祀有荣,永世无极矣!〔8〕
此诏令表明元室继承发展宋朝的政策,对天妃(妈祖)的进一步尊崇,仍是属于中国历代皇朝的祀神传统,目的依然是要神继续承担保国安民的责任。
(5)元大德七年(1294 )黄四如撰《圣墩顺济祖庙新建蕃釐殿记》末之诗云:
穆穆天子,前圣后圣,上昭下漏,靡神弗敬。洒泽龙宫,河图辉映……有齐季女,生也贤哲,岳钟渎聚。没也神灵,云飞电吐。……大哉乾元,坤顺合德,斯庙耽耽,千年血食。……〔9〕所谓“大哉乾元,坤顺合德”,是儒家《易经》的观点。“斯庙耽耽,千年血食”,更是儒家祭礼所肯定维持的传统牺牲血祭。类似之儒家颂诗甚多,如程端学于皇庆二年(1313)撰《灵慈庙记》之诗云:“鄞庙崔巍,百世血食。”〔10〕又延祐、至治间(1314—23)洪希文《题圣墩妃宫湄州屿诗》云:“升阶再拜荐脯藻,不以菲薄羞儒酸。”〔11〕虽是寒儒个人薄祭,也有肉制的“脯”这种儒家传统的祭品。
(6)至顺二年(1331)柳贯撰《敕赐天妃庙新祭器记》云:
……遣省臣率漕府官僚,以一元大武,致天子毖祀之命,荐于天妃。得吉卜而后行。……将祀之夕,会平章政事易释董阿公,入觐道吴,因请公莅荐裸,翼日公斋沭入庙,跪奠惟寅。观见尊斝笾豆,践列参差。……公奏事次,请更造天妃庙祭器如式,以昭神贶。……新制祭器为品十二……〔12〕
上文中的祭仪,祭品以及祭器,都是儒家传统那一套。所谓“一元大武”乃儒家所指献祭用的一头牛,典出《礼记·典礼》下云:“凡宗庙之礼,牛曰一元大武。”而“裸”、“奠”都是儒家的祭仪,指以酒食献祭。而“尊、斝”乃盛酒之祭器,“笾、豆”乃盛果品肉食之祭器。为天妃所新制的祭器共有十二品,可见其是按儒家有关礼制而设。
(7)至正十三年(1353 )周伯琦撰《台州路重建天妃庙碑》云:
……按礼曰:圣王之制祭祀也,禦大菑捍大患则祀之。又曰:有天下者祭百神。祈报之道,祀典所崇。惟天惟大,而海儗之,惟海大而神司之。尊以天妃,崇莫并焉。……〔13〕以上所引“礼曰”之文,原载于《礼记·祭法》。原文曰:
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禦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由此可见,由帝王宫府所倡导的妈祖祭祀,其主流本属于儒家政教的礼治体系的传统。
(二)道佛二教对妈祖信俗的参予和发展
道佛二教对于异教之神灵偶象,向来便有既排斥又吸纳的两种倾向,只是随着历史的推移,在帝王的兼容并蓄的主流政策调控下,宋元以后道佛二教互相吸纳、互相渗透日趋普遍,而且两教对儒家的关系也是如此。因此两教都也有把儒家神化的人物吸纳到本教的寺庙,或者直接参予或代替儒家官僚士大夫建造或管理有关寺庙。例如,关羽本为忠义化身之儒将而受历代帝王官府所代表的儒家礼教所推崇。〔14〕但相信传自隋天台智者大师推崇关羽为佛教的护法神之后,中国也就有很多佛教寺院把关羽请来充当守护神了。道教对关羽与佛教不同之处,就是可以把关羽作为单独崇拜的一尊神,既可在道观中单独设一关帝殿,也可单独建一属于道教的关帝庙。当然,也有本属于儒家的关圣庙而归道士或道徒管理。又如观音,有不少研究者都先入为主地只说观音是属于佛教的。但认真深入分析,便知宋元以来的观音主要分属三个系统:其一,是属于中国化的佛教观音,由原来的印度男性形象变为中国的女性形象。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终究仍在佛教的系统内。其二,是属于道教系统的。在道观中享有专殿供奉,具有原非印度佛教观音所有的神通和功能,如送子等。目前在香港,多有把佛及观音请进道观供奉的现象。在道观中的佛及观音,显然已不能说是佛教的,只能说是属于道教系统的。其三,是属于非佛非道的其他民间宗教系统,由非佛非道的其他民间宗教人士建立和掌管的庙堂供奉。例如,香港、澳门等地区的一些观音庙即属此类。
儒、道、佛三教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一个典型就表现在妈祖信俗的发展演变中。早在元代的史料,便有道佛二教之人参予儒家官僚主导的崇拜妈祖的活动工作中、由道士参予儒家主持的祭祀,这在《元史·祭祀志·岳镇海渎》中有明确记载。原文如下:
岳镇海渎代祀,自中统二年始。凡十有九处,分五道。……道遣使二人。集贤院奏遣汉官,翰林院奏遣蒙古官。……中统初,遣道士或副以汉官。至元二十八年正月,帝谓中书省臣言曰:“五岳四渎祠事,……宜遣重臣代朕祠之。汉人选名儒及道士习祠事者……〔15〕
虽然有关天妃的祭祀是另外记在《名山大川忠臣义士之祠》内,只说有关祭祀由“平江官漕司及本府官用柔毛酒醴便服行事”。〔16〕但依上引“岳镇海渎”之例,可推知妈祖天妃之祭祀,亦可以有非儒家官僚的宗教之人参予。因为正如元人程端学所说:“(对天妃的)岁时遣使致祭,牲币礼秩,与岳渎并隆,著在祀典。”〔17〕今试举若干例证于下:
(1)至元二十七年(1290)宋渤撰《顺济圣妃庙记略》云:
……宋咸淳中,三山陈珩提举华亭市舶,议徒新之。属其从事费榕经昼,礼致道师黄德文奉香火。……〔18〕
上文的“道师黄德文”当是被礼聘为掌管香火的道教大师。
(2)明成化十七年(1418)丘浚撰《天妃宫碑》云:
……京师旧有庙,在都城之异隅大通桥之西。景泰辛未,住持道士丘然源援引南京例,请升为宫。……〔19〕妈祖庙或天妃宫由道士掌管,至明代当为相当普遍的现象。自永乐七至十年之间(1409—12),已有道教中人所撰《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行世。〔20〕大陆现存的妈祖庙天后宫仍有少是由道教掌管的。〔21〕依笔者1994年往台湾考察所见,现时当地有关妈祖天后的庙宫大多由道教中人掌管。而李露露说:“台湾鹿耳门妈祖庙、赤嵌天后宫等处,均由僧人主持,世代相传。”〔22〕这大概只是根据一些旧文献记载而作的判断,至少目前鹿耳门的妈祖庙都是由道教或世俗之人掌管。并无憎人预事,则为本人亲访所知也。
(3)开庆元年(1259 )李丑父撰《灵惠妃庙记》有“守僧与祀”一语,〔23〕表明其时不但有佛教僧人为天妃守庙,而且参预了该庙对天妃的“血食”之祭祀。又泰定四年(1327)黄向撰《天妃庙迎神曲》云:“先是,因前代之旧,寓祠于报国寺庑下”。〔24〕至正十三年(1353)周伯琦撰《台州路重建天妃庙碑》云:“守者复奉神象旅寄天宁寺”,“时督工者,天宁寺沙门大明孜”。〔25 〕约至正十五年(1355)危素撰《河东大直沽天妃宫碑记》提及先后由吴僧庆福、 智本及福聚等人主持和维修扩建。〔26〕由僧人住持妈祖庙或天后宫,必然要面对一个矛盾问题,就是佛教的素食戒律与妈祖的牺牲血祭冲突。结果无非三种:其一,是容许矛盾存在,僧人自持素食,任由他人以血肉祭品拜神。其二,是僧人受妈祖的祭品影响,放弃素食之戒。其三,是妈祖受僧人的控制,只能享受素食之供品。至于其他与妈祖崇拜相关的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占卜打卦求签等方术,亦随之进入这类僧人住持的佛寺与妈祖庙,产生同样的矛盾共存或互化的情况。
(4)在澳门的妈祖庙及天后宫,情况也相当复杂。 如现在的妈祖阁庙,据说初名天妃庙。〔27〕该庙很早就由与普济禅院有关的一个宗派的和尚住持。〔28〕而且在现在中仍由普济禅院的方丈释机修兼管妈阁。又莲峰庙内设天后殿,〔29〕则是佛教兼容奉妈祖的另一方式。至于其他天后古庙、天后宫、关帝天后古庙以及望厦康真君庙内的天后圣母殿等等,〔30〕则是属于儒、道或其他民间宗教信仰系统的遗传。本文限于篇幅,就不一一详析了。
四、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妈祖信俗起于民间,而倡行于朝廷官府,主导于儒家礼祭,而分行于道佛以及其他民间宗教。因此,其源流演变是异常错综复杂,非一篇小文所能完全讲清。本文只是想研究一个基本的事实:有关妈祖的信俗历来就是任人参予,随人发展的,并无某人、某教予以专利垄断,更无所谓正邪真伪之争。因此,我们对于具体的妈祖或天后等等,只能根据其主持者及崇拜的方式等来具体分析判断其性质。决不能先入为主地断言妈祖是“非佛非道的神。”简而言之,在佛寺里的妈祖就是佛教的神,在道观里的妈祖就是道教的神,如此类推,当无误会。
(承姜伯勤先生提供《妈祖信仰之研究》,及郑炜明先生提供《妈祖信仰》予本人作研究参考,在此谨表谢意!)
注释:
〔1〕:见《妈祖信仰》41页,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年。
〔2〕:见《金明馆丛稿二篇》250—2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
〔3〕:见同上书251—252页。
〔4〕:见同上书245页。
〔5〕:转引自李献璋《妈祖信仰之研究》(资料篇)4—5页。 日本东京泰山文物社,1979年。
〔6〕:转引自同上书5页。
〔7〕:转引自同上书9页。
〔8〕:转引自同上书14页。
〔9〕:转引自同上书16页。
〔10〕:转引自同上书18页。
〔11〕:转引自同上书20页。
〔12〕:转引自同上书24页。
〔13〕:转引自同上书28页。
〔14〕:参考黄朴文《关公崇拜与儒学文化》, 载《齐鲁文化》1994年1期。
〔15〕:见《二十五史》第9册74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6〕:见同上书页。
〔17〕:转引自同(注五书)17页。
〔18〕:转引自同上书14页。
〔19〕:转引自同上书44页。
〔20〕:见同上书34—38页。
〔21〕:参见①书43—44页。
〔22〕:见同上书42页。
〔23〕:见同上⑤书10页。
〔24〕:见同上书21页。
〔25〕:见同上书28—29页。
〔26〕:参见同上书31页、同①书42页。
〔27〕:见郑炜明、黄启臣《澳门宗教》6页,澳门基金会, 1994年。
〔28〕:见同上书16—17页。
〔29〕〔30〕:见同上书7页。
标签:儒家论文; 妈祖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日本道教论文; 国学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道教论文; 陈寅恪论文; 佛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