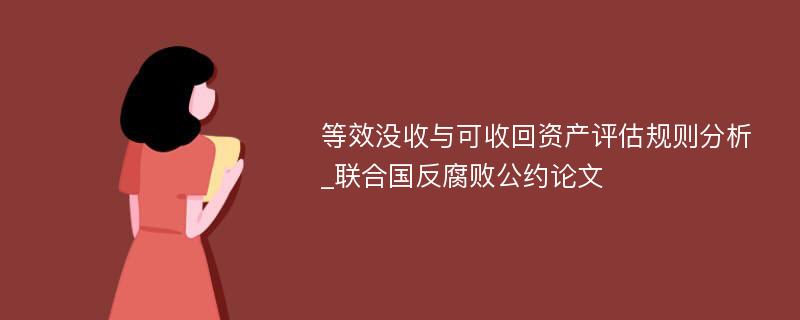
等值没收及可追缴资产评估规则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资产评估论文,规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1世纪初开始,世界各国的刑事没收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体现这一变革的最具代表性的立法有两项:一项是俄罗斯2003年对《刑法典》中没收财产刑的废除并代之以独立的没收措施,由此引起匈牙利、捷克、马其顿、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等一些原东欧国家的刑事没收制度发生连锁反应;另一项是英国《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它以数学的精确度调整刑事没收的对象、范围及规则,并为此指定了专门的法院审理刑事没收问题,由此促使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爱尔兰、牙买加、巴哈马、毛里求斯等一大批英美法系国家针对犯罪资产的没收推出特别立法。上述立法改革的趋势可以概括为:将刑事没收的标的和范围限定为犯罪资产的价值,力求实现刑事正义与民事正义的有机结合。 一、等值没收的形态、特点与性质 在刑事诉讼中,所谓等值没收是指没收的数额与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数额相对等,或者说,没收的数额以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数额为其上限。等值没收可以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态,一种是狭义的或者严格意义上的等值没收,即当犯罪所得被挥霍、转让、贬值或者灭失时,按照该犯罪所得的价值,以充抵的方式对犯罪人的个人财产实行没收。狭义等值没收的适用范围比较有限,仅表现为对已灭失犯罪所得的替代性追缴,在我国《刑法》第64条中被称为“责令退赔”。另一种是广义的或者一般意义上的等值没收,即以准确计算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数额为限度,对犯罪人的可支配财产实行没收,不问此种可支配财产是否直接来源于犯罪。广义等值没收将现代刑事没收制度的“比例性”或者“对称性”原则贯穿于始终,使得刑事没收紧紧与犯罪资产的数额挂钩,从而消除或者淡化了刑事处罚的功能。 狭义的等值没收(confisca per equivalente)①在一些国家的刑事立法中也被称为“等价物的没收”(forfeiture of value)②或者“折价款的没收”,例如,《德国刑法典》第74条C第1款规定:“如正犯或共犯可能知道将要没收行为时属于其所有或其享有处分权的物品,而于判决前用尽该物品,尤其是出售或耗损,或以其他方式致使无法没收该物的,法院可命令正犯或共犯交付与该物价值相当的折价款。”③这里所说的“折价款”指的正是不能直接予以没收的犯罪所得的变价款,此种折价往往适用于下列“直接没收不能”的情形: (1)犯罪所得,尤其是表现为特定物的犯罪所得(如:被窃取的汽车、文物等)已被挥霍、转让、藏匿或者以其他方式灭失。这是比较常见的情形,对此《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04-2条规定:“如果本法典第104-1条所列财产中的特定物,由于使用、变卖或其他原因在法院作出没收该物品的判决时已经不可能没收,则法院应作出判决,没收与该物品价值相当的金钱。”④ (2)犯罪所得表现为隐形收益或者说“财产节省”,⑤例如,因走私犯罪而偷逃的关税。正如一位意大利刑法专家所指出的,“在下列情况中确确实实不可能采取直接的没收措施:犯罪人的收益不是来自于获取某一财物,而是来自于对此类财物的节省,大部分财税犯罪就是如此,犯罪人在实施非法行为后获得的是不支付应缴纳税款的利益;此种节省由于不表现为直接获取某一看得见的财物,而表现为拒不承担在不犯罪情况下本应承担的费用,因而,无法成为没收的标的物”。⑥在此情况下,则对上述隐形收益实行等值没收。 (3)有关财物因犯罪而被获取后发生了贬值情况。从犯罪中获利的数额通常以有关经济利益取得时的价值为准,有时候,犯罪所得财物在使用过程中或者随着市场价格的波动可能发生贬值,例如:某人在2010年因受贿获得的某名牌手机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为6000元,而3年后同一品牌和型号市场价格仅为3000元,在没收犯罪所得时,除没收该手机外,可以对贬值部分实行等值没收。对此,《德国刑法典》第73条a规定:“如被追缴的物品的价值低于最初的取得物的价值,法院除命令追缴该物外,还命令追缴差价。”⑦ (4)犯罪所得与合法所得融合成难以分割的财产。例如:某人将抢劫获得的财产变现后,与其个人和家人的合法财产一起购置房产,在此种情况下,如果“应没收财产无法从其他财产中区分出来,或者将其区分出来存在超出合理限度的困难”,⑧在进行资产追缴和没收时,应对其抢劫所得财产进行估值,并可以对其个人拥有的存款进行等值没收,“没收价值最高可以达到混合于其中的犯罪所得的估计价值”。⑨ 广义的等值没收则是基于对各种不同形式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精准估值,计算出可追缴资产数额并将此数额确定为资产追缴的上限,采用钱款折算的方式实行的没收。它一方面参照了狭义等值没收的折算规则,另一方面,本着任何人不得从犯罪和违法行为中获利的原则和公平正义的精神,对所有产生于犯罪的财物、报酬、权益或者其他形式的经济利益,无论是否可以对其直接实行实物没收,均加以合理计算,以科学的量化标准规范追缴与没收活动。 “可追缴款额”(recoverable amount)是广义等值没收制度的一个基本概念,⑩它是指可追缴资产的价款数额,或者说,是与从犯罪活动中获取的或者同犯罪实施有关的财物相对等的钱款数额,《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1条将其表述为“与所得财物相当的价值”(property the value of which corresponds to that of such proceeds)。随着这一概念的确立,司法机关在对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进行追缴时,不仅对于已挥霍、损坏、灭失或转让的特定物,而且对于一切尚存的财物,包括可替代物,除作为证据使用外,均不必逐一地辨别和追踪犯罪所得的原物,只要根据有关物的价值确定可追缴款额即可,“在法庭签发任何没收令时,应当确定没收令签发时其所认为的没收令指定财产(金钱除外)的价值”。(11) 广义的等值没收,在吸收和借鉴狭义等值没收规则的基础上,创立了一整套缜密的规范体系,使得对犯罪资产的追缴与没收成为一项相对独立的制度,并表现出以下主要特点: 第一,使没收与犯罪所得的数额紧密挂钩,并受制于可追缴款额的上限,超出该上限的追缴与没收将被视为不公正的财产剥夺。由此凸显刑事没收的“适当性原则”,即没收的强度应当与非法获利的程度相对称。因而,在刑事诉讼中适用没收手段首先应当查清两个问题:一是被告人是否从有关犯罪中获利;二是被告人从有关犯罪中获利的程度及其数额。如果被告人没有从犯罪中获利或者获利数额微不足道,从诉讼成本的角度考虑,则不应作出没收裁决;刑事没收的范围也不应当超出被告人非法获利的范围。(12) 第二,等值没收紧紧围绕的是有关财物的来源和性质问题,不再具有刑事处罚的性质,可以在被告人逃匿或死亡的情况下适用,有着附带民事诉讼的色彩。司法机关通常采用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或者“优势证据”标准就有关财物是否与犯罪有关或来源非法问题作出认定,允许被告人及利害关系人参与相关的诉讼活动,以确保对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认定和估算符合公平原则,并平等保障被害人与善意第三人的权利。这样的权利保障机制自对财物执行冻结或扣押措施时起即可启动,一切与被冻结或扣押财产有利害关系的人均有权针对财产保全措施的适用依据以及扣押、冻结的数额提出异议,或者依照民事诉讼的程序申请司法审查。 第三,将对犯罪所得的实物没收转化为支付义务,此种支付义务的履行接受“司法之债”规则的调整,更加注重实际经济效果。采用货币尺度衡量和折算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数量将使资产扣押、冻结、追缴与没收更为精准和易于操作,使此种“司法之债”的执行更符合公平、公正原则。比如,如果某人根据没收令应当支付的钱款未予支付,则可以要求该人按照民事裁决债务利率的标准,就迟延期间尚未支付的款额支付利息。(13)一些国家的犯罪收益追缴法甚至允许当事人在一定条件下采用支付折价款的方式赎回被没收的财物。(14) 等值没收和罚金,从一定意义上讲,都属于“司法之债”,都要求犯罪人向司法机关支付特定数额的钱款,不同的是,等值没收要求支付的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折价款,而罚金则要求在犯罪获利范围之外支付一笔惩罚性的钱款。在等值没收的情况下,如果直接来源于犯罪行为的财物已被挥霍、损耗或转让,犯罪人有义务以自己的合法财产支付相对应的折价款,但是,随着对没收标的物及其数额的精准界定,“没收就失去了其惩罚性功能,而变成了一项修复性法律制裁”。(15)因此,就法律性质而言,等值没收已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没收财产刑,它对犯罪人合法财产的剥夺不得超越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范围,是对受到犯罪侵害的原有合法经济与财产状态的恢复,因而不再具有刑事处罚的性质。由于针对犯罪资产的等值没收不具有刑事处罚的性质,一些国家的相关立法明确规定对其不适用刑法的不溯及既往原则,例如,澳大利亚《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第14条规定:“本法适用于:(1)任何时间实施的犯罪(不论是否有人被定罪);和(2)任何时间被判决的犯罪,不论该犯罪或定罪发生在本法生效之前还是之后。”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等值没收也存在着比较严厉的一面,在一些情况下,严格执行等值没收也可能造成以犯罪人的全部合法财产折抵已被挥霍或损耗的犯罪所得的局面,甚至可能致使犯罪人为履行“司法之债”而倾家荡产。尤其在那些把没收犯罪资产作为保安处分加以适用的国家,等值没收有可能实际超出财产性保安处分的预防性功能而具有惩罚性,(16)“正是由于它较强的穿透性并且可能对与实施犯罪无关的财产也造成影响,人们一般认为它具有较为明显的制裁性质”。(17)因而,一些国家的刑事立法规定:如果等值没收超出了财产保安处分的预防功能并可能对有关人员的合法财产造成剥夺,一般只针对刑法典分则特别列举的某些犯罪(通常为贪利性犯罪和腐败犯罪)并且在对被告人定罪(包括通过辩诉交易定罪)之后适用;对于上述新引入的、针对特定犯罪适用等值没收的法律规定,需要考虑遵循不溯及既往的原则。(18) 二、可追缴资产的构成与确定 可追缴资产是刑事没收以及相关的扣押、冻结、查封措施的对象,并构成确定“可追缴款额”的基础。一般来说,可追缴资产由两大范畴组成:一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二是犯罪工具。 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许多国家的立法中被表述为“proceeds of crime”,即指“通过实施犯罪而直接或间接产生或者获得的任何财物”,包括由犯罪所得派生的收入或者其他利益,即所谓“利益收益”。(19)一些国家的刑事立法将犯罪所得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包括:(1)犯罪获利(profitto del reato),即从犯罪中直接获得的经济利益,无论该经济利益是由犯罪行为人获得的,还是由任何其他人获得的,例如,索贿犯罪的贿赂款受益人也可能是犯罪人的亲友或者任何第三人。(20)(2)犯罪报酬(prezzo del reato),即因实施犯罪行为而得到的酬金或奖励(例如:因泄露内幕信息而从受益方获得的钱款,因介绍贿赂而取得的佣金,等等),包括由他人得到报酬。(21)(3)犯罪产物(prodotto del reato),即犯罪人通过犯罪所制造、变造或者改造的物品,例如通过假冒商标犯罪制造的服装,使用有害原料生产的食品或药品,等等。(22) 犯罪工具是旨在为实施犯罪服务或者为犯罪提供便利的财物,它既可以是“被设计用于实施犯罪的专门物品”或者“它们的特征特别适合于作为故意犯罪的工具”的物品,(23)例如:为窃取商业秘密而安装的窃听设备或者用于谋杀的砍刀,也可以是被用于实施犯罪的普通物品,例如:用于购买毒品或者资助恐怖犯罪的资金。将犯罪工具列为可追缴资产通常以其属于犯罪人的个人财产为条件,如果被用于犯罪的财物“全部或部分地属于其他人而非犯罪人”,一般不对其实行没收,(24)但是,如果存在下列情形,则不受此条件的限制:(1)有关财物的权利人具有一定过错,“知道该物品的目的或用途与犯罪有关”、(25)曾经以应受谴责的方式共同参与使用,或者从他人行为中获取利益;(2)该财物有可能被继续用于实施犯罪;(3)出于人身或财产安全方面的考虑或者基于公序良俗方面的原因,没收具有绝对必要性。(26)除(1)所列情况外,物的合法所有人可以向犯罪人就被没收之物提出赔偿请求。 在可追缴资产中,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是最为主要并且最为复杂的范畴。就其构成而言,该范畴还包含一些特殊形态,之所以说“特殊”是因为,对于此类犯罪所得形态的认定,须把握某些特殊的条件。综合各国比较新近的没收立法,特别值得研究的犯罪所得特殊形态是“推定的犯罪所得”和“污点赠与”。 一般形态的犯罪所得均可证明与特定的犯罪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即在认定时需要证明有关财产来源于特定的犯罪。然而,对于推定的犯罪所得,在对其进行认定时,则无需证明有关财物与特定犯罪之间存在着联系,只需根据法律规定的条件,对被告人在特定时间段持有或者支付的财物作出来源非法的推定。在最近十几年中,不少国家关于追缴犯罪收益的立法开始注重对推定的犯罪所得实行没收,为相关推定的运用确立了一些法定条件。这些法定条件可归纳如下: 第一,法院认定被告人具有“犯罪生活方式”(criminal lifestyle)。这是英国《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创制的一项推定。一旦法院认定被告人具有“犯罪生活方式”,即其生活对犯罪收益具有依赖性,则可以推定该人在一定期限内获得的财产或者发生的开销均来自于犯罪收益并将其计入可追缴款额,无需证明犯罪收益与特定犯罪之间存在联系,该“一定期限”最长可为自被告人受追诉之日起向前回溯的6年的时间段。推定犯罪生活方式所依据的具体条件是:(1)被告人犯有犯罪收益法附表所列举的9类罪行之一,这9类罪行分别是:贩毒罪、洗钱罪、领导恐怖活动罪、贩卖人口罪、贩卖武器罪、走私罪、侵犯知识产权罪、组织卖淫活动罪、敲诈勒索罪;或者(2)被告人在6个月以上的时间中持续犯有任何罪行并且从中受益;或者(3)在现行刑事诉讼中被定罪的行为构成其犯罪活动进程的组成部分。(27) 第二,被告人被认定实施了特定的经济犯罪,且综合各种情形有理由推定其财产来源于犯罪。此种推定比较常见于毒品犯罪案件,例如,根据韩国《关于预防非法贩运毒品特别问题法律》的规定,在评估毒品犯罪的获利时,如果犯罪人在其持续实施毒品犯罪活动期间所取得的财产,相对于其根据法律和相关规章在相应期间的财产交易状况和支付状况,被发现明显超出,并且考虑到非法收益的数量以及取得财产的时间等各种情形,有合理根据认为所取得的财产来自于毒品犯罪的非法收益,有关财产应当被推定为与毒品犯罪相关的非法收益并对其予以没收。(28)不少英美法系国家法律均允许对毒品犯罪的犯罪收益实行推定,其模式与英国《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相似,但将“犯罪生活方式”改换为因贩毒行为而被定罪。(29)推定的此种法定条件也被一些国家扩展适用于某些严重犯罪活动,例如,匈牙利法律规定:行为人在参与有组织犯罪期间所获得的所有财产,在被证实来源合法之前,一律予以没收。(30)意大利2012年《反腐败法》规定:对于因贪污、索贿、受贿、介绍贿赂等行为而被定罪的人员,一律没收被判刑人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钱款、财物或其他利益,以及被判刑人享有的包括通过自然人或法人享有的或者以任何名义支配的、与其缴纳所得税时申报的收入不相符合或者与其经济活动不相符合的钱款、财物或其他利益。(31) 第三,被告人具有特定身份且不能对其财产的合法来源作出合理解释。此种推定的法定条件通常是针对有可能利用职权实施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设定的,例如,根据爱尔兰《2005年犯罪收益追缴(修正)法》的规定,如果被告人涉嫌腐败行为,对于其因腐败增加的财产,法官可签发“腐败致富没收令”(corrupt enrichment order),无需证明有关财产增加与特定腐败犯罪之间的联系。具体来说,认定涉嫌腐败行为以及“财产因腐败增加”须具备以下三项条件:(1)被告人可以因行使其公共职权使他人受益;(2)其他人已因被告人行使上述职权而受益;(3)被告人不能对其财产、经济资源、收入及其来源作出合理说明。(32)缅甸2013年《反腐败法》第53条也规定:对于公职人员,只有“能够提供确凿证据”证明有关财产“是合法途径获得的”,才可以将该财产归还本人。(33)实际上,这一法定推定条件正是参考《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2条提出的立法建议而制定,该建议提请各国考虑将“公职人员的资产显著增加,而本人无法以其合法收入作出合理解释”规定为犯罪。 以推定的方式认定犯罪所得及其数额是一种比较严厉的做法,为确保司法公正,法官在实行有关推定时应当遵守以下限度:(1)当存在相反证据,尤其是存在关于财物合法来源的证据时,应当放弃推定的适用。对此,加拿大马尼托巴省2004年《犯罪财产追缴法》(Criminal Property Forfeiture Act)第17.15条第1款规定:采用推定方式认定犯罪所得只适用于“不存在相反证据”的情况。(2)应当对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如果认为实行推定将有失公平和公正,则应当放弃推定的适用。在这方面,巴哈马2000年《犯罪收益追缴法》(Proceeds of Crime Act)第11条第4款规定:如果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认为实行推定显得不正当(is shown to be incorrect),则不得对被告人的任何财产或花费实行有关推定。(3)应当确保被告人等利害关系人的诉讼权利,在被告人逃匿情况下慎重适用或者不适用类推认定。根据开曼群岛《2008年犯罪收益追缴法》(The Proceeds of Crime Law,2008)第37条第2款的规定,在被告人逃匿的情况下,一般不依据关于“犯罪生活方式”的推定签发没收令,除非“总检察长采取了合理步骤与被告人进行了接触”。 犯罪所得的另一种特殊形态被称为污点赠与。污点赠与(tainted gifts)这一概念是由英国《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特别提出的,它是指被告人将犯罪所得财产“以明显低于当时该财产价值的对价移交给另一人”。(34)污点赠与概念的引入为刑事没收确立了这样一项原则:没收应当紧紧追踪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去向,不让任何人从犯罪中受益。刑事没收的属人特性因此而淡化,其“对物之诉”的特征则更为彰显。 在对污点赠与的认定问题上,各国相关立法的标准是一致的,即只考虑有关财物的接受者在受让时是否支付了合理对价,在没有支付对价或者所支付的对价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情况下,则应将所接受的、来源于犯罪的财物认定为污点赠与,不问受赠人是否具有“善意”,也就是说,不问受赠人是否知晓或者应该知晓有关财物的来源,而且也不问赠与人以无偿或明显低价方式转让财物的动机与目的。需要注意的是,污点赠与有偿转让有时候可能出现交叉的情况,这主要表现为低价转让来源于犯罪的财物,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考量“低价”的幅度,如果转让价与市场价之间的差价并不悬殊,在受让人具有善意的情况下,可以允许其保留被转让物,并应向司法机关适当支付差价;如果上述差价悬殊,所支付的对价“明显低于该财产利益的实际价值”,则应当将被转让的财物作为污点赠与予以没收。(35)也有的国家法律则干脆规定:如果受让人在转让时支付的对价低于市场价,其差价部分以“赠与”论。(36) 对于污点赠与,也可采用推定的方式予以认定,其前提条件是:对有关被告人在一定时段的财产、收入和花费可以推定为犯罪所得。在采用推定的方式认定污点赠与的情况下,无需证明被赠与的财物与特定犯罪之间存在联系,只要相关的赠与行为发生在特定的时间段,即可推定被赠与物属于污点赠与。例如,根据英国《2002年犯罪收益法》第77条(1)和(5)款的规定,如果法院认定被告人具有“犯罪生活方式”,那么,在现行诉讼开始前的6年期限内被告人所实行的任何赠与均可被判定为“污点赠与”,并构成追缴和没收的对象。 三、可追缴资产的数额计算 在对可追缴资产进行评估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估算犯罪所得财物的价值。这里所说的“价值”通常被理解为依据“市场价”(market value)对有关财物作出的估值,(37)或者表现为“公开拍卖销售的收入”。(38) (一)评估犯罪所得财物价值的时间点 评估犯罪所得财物的价值涉及两个不同的时间点,一个是司法机关在作出没收裁决时的时间,可称为“裁判时”,另一个是被告人因犯罪行为而获得有关财物的时间,可称为“获得时”。从各国立法和司法的情况看,一般要求司法机关按照犯罪所得在裁判时的价值认定可追缴资产的数额,例如,《荷兰刑法典》第36e条第4款规定:“法官认为属于非法所得的物品价值应当按照作出司法决定时的市场价值确定。”如果犯罪所得财物在裁判时的价值超过了获得时的价值,对超过部分应当作为产生于犯罪所得的收益加以没收,对此,《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1条第6款要求各国对于犯罪所得的升值部分也予没收,“其方式及程度与处置犯罪所得相同”。但是,如果犯罪所得财物在获得时的价值高于裁判时的价值,则应当按照获得时的价值确定可追缴资产的数额。因此,在估算犯罪所得财物的价值时,对于“裁判时”和“获得时”这两个时间点,应当本着“就高不就低”的原则进行选择,也就是说,应当选择犯罪所得财物价值较高的时点。(39)估算犯罪资产价值的“就高不就低”规则也得到我国的确认,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11日颁布的《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第1款规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数额,应当以实施掩饰、隐瞒行为时为准。收购或者代为销售财物的价格高于其实际价值的,以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价格计算。”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所谓“裁判时”不宜机械地理解为仅指法官作出没收裁决的时间,准确地说,在对犯罪所得采取了保全措施的情况下,它是指有关财物被查获时的时间,即犯罪所得财物受到扣押、冻结或查封的时间。在从扣押、冻结或查封到作出没收裁决期间,如果有关财物的价值发生了变化,比较公正的做法是以扣押、冻结或查封时的价值为准;对于被查获后发生的资产贬值部分,在评估犯罪所得价值时一般不再适用“就高不就低”的原则。资产冻结期间发生的增值或产生的孳息则添附于该资产,在法院裁决时与资产本金一并予以没收或者返还。(40)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各国刑事诉讼立法和实践中找到充分依据,例如,在刑事诉讼中允许当事人向司法机关提供“与被扣押物价值相当”的保证金,司法机关有权对不宜保管的物品进行折价处理,(41)而且,司法机关对犯罪资产销毁、废弃相当于没收,(42)等等。 (二)犯罪所得与犯罪被害人的财产损失之间的联系 另一个在评估可追缴资产的数额时需要特别加以考虑的要素是:犯罪所得与犯罪被害人的财产损失之间的联系。在许多情况下,犯罪所得与被害人遭受的财产损失是相互重合的,例如:在盗窃犯罪中,犯罪人通过盗窃行为所取得的财物恰恰构成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在有些情况下,被害人的财产损失也可能大于或者小于犯罪人的获利,例如:犯罪人窃取正在使用的输电线路电缆,除给国家带来电缆价值的直接损失外,还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间接经济损失,在此情况下,犯罪所得的数额小于被害人的财产损失;但也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即犯罪所得的数额大于被害人的财产损失,例如:犯罪人用价值100元的镀金饰品冒充24k纯金饰品诈骗被害人5000元,在此情况下,犯罪所得为5000元,被害人实际财产损失为4900元。因此,在根据被害人的财产损失评估犯罪所得的数额时,切忌简单行事,需要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和认定,为此,各国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了以下可供借鉴的规则。 1.已向被害人偿还的财产数额应当从可追缴款额中扣除 在作出没收裁决前,被告人向被害人退还财产,虽然一般不影响有关犯罪的成立及犯罪所得数额的认定,但直接影响没收数额的计算,“已经归还受害方的这部分收益”不得计入没收数额。(43)这里所说的退还,既包括被告人主动退还,也包括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使用被扣押、冻结的财产向被害人返还,或者被告人已经“根据民事判决”向被害人实行返还或者赔付,(44)或者“满足了因其行为而产生的民法上的请求权,或以可执行的方式通过合同使自己负有满足对方请求权的义务”。(45) 2.间接经济损失或第三方经济损失不计入可追缴资产数额 这里所说的“间接经济损失”是指除直接由犯罪人获取的财产利益外,被害人因犯罪遭受的其他经济损失,例如因就医用款被窃而导致病情加重并支出更高数额的医药费。所谓“第三方经济损失”是指除犯罪所得财物直接来源方以外的其他人员或机构遭受的经济损失,例如:受贿人因接受某企业行贿并为其谋取非法利益而致使国家遭受经济损失;这里的第三方可能构成有关犯罪的被害人,但不构成使犯罪人获得经济利益的财产来源方。被害人间接经济损失和第三方经济损失,虽然不纳入可追缴资产数额中计算,但却构成犯罪人赔偿的对象,而且,由此而产生的赔偿权优先于刑事没收和罚金,也就是说,“法院应当首先作出赔偿裁定,然后根据案情,考虑是否作出及在多大程度上作出没收令或罚金令是适当的”。(46) 3.为实施犯罪付出的费用一般不从可追缴资产数额中扣除 犯罪人为实施犯罪行为而付出的费用,包括以诈欺方式向被害人给付的财物,当是为犯罪活动服务、提供便利或者施放诱饵时,应当认为属于被用于实施犯罪或者为实施犯罪提供便利的工具,同样属于可追缴财物的范围。对此,新西兰《2009年犯罪收益追缴法》明确规定:在计算犯罪财产、所得或者获利的价值时,“与实施犯罪行为相关的费用和开支”不得加以扣除。(47)澳大利亚《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第126条也规定:因违法行为所产生的费用或者开支,不得从违法行为所获利益的价值中扣除。但是,作为例外情形,如果发生在犯罪过程中的某些支付是善意第三人“以诚信方式作为报酬取得的财产”,则应当从可追缴资产数额中予以扣除,(48)例如在实施某些经济犯罪过程中为划拨资金而向银行支付的汇费或者向税务机关缴纳的合法税费。 4.被害人在相关交易中的受益数额应当从可追缴资产数额中扣除 对于经济犯罪或贪利性犯罪,在认定和计算犯罪所得时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的形态,一种是“交易中犯罪”,另一种是“犯罪交易”。前一种犯罪发生在合法交易进程中,犯罪人与被害人在双务交易中互相负有给付义务,在此情况下,“在犯罪过程中被用来抵消有效民事权利请求的财产”,不应计入可追缴资产数额之内,(49)也就是说,应当从可追缴资产数额中减去被害人方面在交易中取得收益。例如,某甲通过贿赂活动从政府采购评审委员会获得一项中标额为1000万元的采购计划,行贿获利的净额应当为犯罪人所接受的1000万元采购价款减去被害人(政府机关)所采购物品的真实市场价格。而在后一种“犯罪交易”形态中,犯罪人所进行的整个交易均为违法行为,不产生任何合法、有效的民事请求权,例如:毒品买卖、合同诈骗等犯罪,交易的全部所得额均应计入可追缴资产的数额,“无需在整个所得与利润之间进行切分,”“不能采用企业的估价标准,尤其不能去区分收益和‘净利’,即犯罪人实际获得的盈利”。(50) 可追缴资产的数额在认定和计算时有着自己的上限,即从犯罪中获得的财产性利益的总和;同时,也有着自己的下限,在一些关于犯罪资产追缴的法律当中,这个下限被表述为被告人的“可支配款额”(available amount)。(51)所谓可支配款额,即指被告人在法院签发没收令时实际拥有的个人财产,不问该财产的来源和持有是否合法。从这个意义上,在追缴和没收犯罪资产,尤其在实行等值没收时,也可以没收犯罪者的个人全部财产。但是,在现代刑事没收制度中,这种对个人全部可支配财产的没收,就其性质而言,完全不同于传统刑法(如我国刑法)中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里所说的“可支配款额”必须低于“可追缴款额”,也就是说,只有当被告人所拥有的财产不足以涵盖本应依法追缴的财产数额时,才根据现实可能性减少追缴与没收的数额,将其限制在被告人实际拥有的财产范围内,因而,这是一种基于可追缴资产数额下限的没收,是对被告人或犯罪人的“克减”待遇,而不构成超越可追缴资产数额范围的财产性处罚。 可支配款额作为可追缴资产的下限,在计算时首先应扣除用于向被害人赔偿经济损失的数额,因为,正如前面所论证的,此种损害赔偿有着优先于没收的地位。随后还应当扣除其他一些需优先偿付的款额,例如:被告人在已开始的破产清算程序中应当清偿的优先债权等。(52)经过必要扣除后的可支配款额,无论最后剩下多少,均代表经过调整后的可追缴款额,对该款额的没收构成相关“司法之债”的消灭。如果可支配款额为零,可追缴款额则为犯罪所得的“名义款额”,即无实际没收可能的纸面数字,法院可以因此而撤销没收令。(53) 犯罪所得财产也可能由于某些法定原因而改变其性质,转变为持有人的合法财产,并且从可追缴资产的数额中扣除。这种使犯罪所得财产性质消灭的法定原因主要表现为时限,也就是说,为了避免已趋平稳的民事财产关系和社会秩序再经动荡,如果来源于犯罪行为的财产在经过一定期限后仍未受到追缴和没收,则不再被视为犯罪所得,并不再构成追缴与没收的对象。例如,挪威《刑法典》规定:“犯罪收益的没收期限不少于10年。”(54)英国《2002年犯罪收益法》第88条(1)款为追缴犯罪收益规定的时限为12年,自“该财产被获得时”计算。(55)澳大利亚《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则规定:如果来源于犯罪或者被用于犯罪的财产经过两轮的合法继承,也就是说,“当财产仍是犯罪的收益或工具时被死者作为遗产授予某人,该人去世后又将该遗产再授予第三人”,则“停止作为犯罪的收益或犯罪的工具”,不再构成没收的对象。(56) 四、没收程序中的权利保障 现代刑事没收制度,基于等值没收的理念,形成对犯罪资产的追踪、甄别、认定和剥夺,随着有关犯罪资产不断发生形态的变化以及在不同人员之间流转,等值没收的实现已不能仅仅依赖于对刑事被告人的定罪以及对其个人获利数额的认定,有时候需要查清其他问题,例如:可追缴资产的直接受益人是否为除被告人以外的其他人?可追缴资产是否与其他合法资产相互混合形成了新的财产形态?可追缴资产获取之后在估值方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可追缴资产是否被有偿或者无偿转让,有偿受让人是否属于善意第三人?犯罪被害人对于可追缴资产享有怎样的权利?在可追缴资产上是否也附着其他人的合法权利?等等。因而,对犯罪资产的追缴和没收已大大超出或者相对独立于对被告人的定罪和处罚问题,关系到方方面面的权利与利益,也事关民事公平与正义的实现。 现代刑事没收中的权利保障贯穿于整个相关进程当中,从对有关财物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开始,到对相关的没收问题作出司法裁决之时,均应当为利害关系人设置和提供相应的法律救济手段,允许其参与相关的诉讼活动并确保其诉讼权利。对可追缴资产的甄别、认定和估算自刑事扣押、冻结或查封措施采用之时就应当开始,并且对这类保全措施的适用发挥限制作用。如果有关财产被转移到境外或者处于境外,这种权利保障还将受到财产所在地法律制度和相关国际法规范的调整与维护,对犯罪资产的追踪、扣押、冻结、没收和处置以及相关的国际合作成功与否,还将取决于外国法和国际法关于当事人权利保障规则的适用。 刑事诉讼中对物的扣押、冻结主要基于三种目的:一是财产保全的目的,保障可能判处的财产性处罚或措施以及因犯罪而产生的民事赔偿裁决的执行;二是预防的目的,防范任何与犯罪有关的财物被动用并防止其继续产生引诱或者服务于犯罪的作用;三是举证的目的,防止作为犯罪证据的物品被销毁、转移、改变或者灭失。对可追缴财物的扣押、冻结主要是出于前两种目的而实行的,相关诉讼程序中的权利保障机制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由法官裁决适用对物的保全或预防措施。对物的扣押、冻结或查封涉及人的基本权利——财产权,因此现代刑事诉讼法制不再将其视为一般的“侦查行为”任由刑事侦查或检控机关自行采用,而是将对财产权的限制措施交由法官裁量适用。刑事侦查机关和检控机关只是作为提请法官适用上述财产强制措施的申请方。就连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有着较大权力的俄罗斯也确立了对财产保全措施的司法审查原则,要求侦查机关或检控机关在经检察长同意后,“向法院提出申请扣押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或依法对其行为负有财产责任的人的财产”。(57)一些国家法律即使允许司法警察或者检察官在紧急情况下决定采取扣押、冻结措施,也要求须在法定期限内得到法官确认,否则应解除相关保全措施。(58)根据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和犯罪资产追缴制度的不同,针对可追缴资产的扣押、冻结措施,包括英美法系法制所说的限制令(restraint orders或restraining ordes),既可由审理刑事案件的法官(法院)裁决适用,也可由负责预审法官(59)或初期侦查的法官裁决适用,(60)还可以由专门审理犯罪资产追缴事项的指定法院裁决适用。(61) 第二,与被扣押、冻结财物有关的人员享有知情权和请求权。确保与被扣押、冻结财物有关的人员知晓保全措施的适用情况,可以采用不同方式加以实现。有的国家法律将有关的通知程序安排在财产保全裁决作出之前,要求检察官在向法官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时应当将该申请也通知一切关系人,在一般情况下,只有当法官“确信申请所涉财产的所有人已经收到合理的关于申请的通知”时,才对相关的限制令申请进行审理。(62)有的国家则将通知程序安排在裁决之后,要求刑事侦查或检控机关将法官签发的财产保全令立即送达不动产的所有人、动产所有人或持有人、相关财产权利的债务人和债权人,在后一种情况下,为资产追缴目的而签发的财产保全令“自向债务人送达之时起生效”。(63)不少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允许当事人(主要是犯罪被害人)向法官提出扣押、冻结财物的申请,以确保自己因犯罪而失去的财产得到返还或者所遭受的财产损失得到赔偿;当事人关于扣押、冻结的请求,虽然是向刑事法官提出的,但通常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加以执行。(64)这些关于知情权和请求权的法律规范为刑事财产保全制度增添了民事公平公正的标准,使该制度的适用能够兼顾到各方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权益,自程序之初就将他们纳入到“没收参与人”的行列。(65) 第三,可应请求单独开展复查或变更保全措施的司法审查程序。相对于其他司法裁决而言,法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签发的扣押令或者限制令具有显著的可变性特点,即在作出没收裁决之前,可随时应请求对其进行复查或变更。对上述财产保全措施的复查或变更请求既可以由被告人提出,也可以由其他对被扣押、冻结的财物享有财产性利益的人员提出,还可以由犯罪被害人或者刑事检控机关提出。复查请求既可以基于被冻结或扣押的财物不属于可追缴资产、财物持有人属于没有从有关犯罪中获利的善意第三人等理由,要求将某些财物排除在保全措施适用范围之外,(66)也可以基于恢复受到犯罪侵害的合法所有权、保护第三人对可追缴资产享有的合法债权(如抵押权)等理由,要求从被扣押、冻结的财产中获得返还、赔偿、债务清偿,或者要求扩展财产保全措施的适用范围。(67)针对刑事保全措施的司法审查程序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可以在作出刑事判决之前的任何诉讼阶段提起,对于相关的司法审查裁决,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可以单独地提出上诉,甚至可以针对上诉审裁决单独地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68)对于检控方提出的关于扩展保全措施适用范围或者延长其适用期限的申请,法官还可以要求申请方承担损害赔偿或担负费用的责任。(69)在上述司法审查中,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的帮助,其他诉讼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也有权得到律师或者法律顾问的帮助和代理。 刑事没收裁决的作出可以出现在不同的程序中,一般来说,是由审理刑事案件的法官在刑事审判中与定罪处罚问题一并作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可以由审理犯罪资产追缴与没收案件的法官采用特别程序在刑事审判之前或者之后单独作出。在前一种情况下,定罪构成没收的基础,较为严格的刑事证据制度足以确保对可追缴资产及其数额的正确认定和估算;同时,除被告人以外的“没收参与人”也有权向审理刑事案件的法官提出并证明自己的权利主张,在资产追缴与没收问题上,“享有被告人享有的权利”。(70)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对犯罪资产的没收不以定罪为基础,而且可能存在被告人逃匿和死亡情形,因而,特别没收程序通常采用民事诉讼的程序规则和证明标准,以便最大限度地保护所有与没收标的物有利害关系的人的权益。同时,上述特别没收程序还设置了必要的纠错机制,如果曾经逃匿的被告人重返相关的诉讼程序且认为没收数额过大,可以在被定罪之日起的法定期限内申请变更没收令;(71)如果曾经逃匿的被告人在审判中被宣告无罪并向刑事法院申请撤销没收令,则法院必须撤销没收令。(72) 将刑事没收的范围限定于可追缴资产,这一广义等值没收观念的普及也为关于没收事宜的国际合作确立了更为严格的条件,被请求国在对请求国的没收裁决进行审查时将特别注意“是否存在合理根据认为有关财产来源于犯罪行为”,(73)并通过相应的诉讼程序听取有关各方的意见和主张,确保所有与没收标的物有关的人员享有平等的请求权。虽然承认与执行外国没收裁决具有刑事司法协助的性质,但我们看到,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比较常见的是采用民事诉讼的规则对外国没收裁决以及相关的资产保全请求进行司法审查,(74)有的国家甚至要求请求国直接作为原告采用民事执行程序(exequatur)向主管法院提出执行没收裁决的请求。(75)即使在外国的没收裁决已得到被请求国法院的承认或者被允许登记的情况下,一些国家法律仍允许对被没收的财产主张权益的人在一定期限内向被请求国法院申请获得司法救济,(76)如果审理此救济请求的法院查明申请人在请求国的没收程序中没有得到合法传唤或适当代理,或者其相关权利没有得到足够保障,则可以接受其司法救济请求,裁定从被没收的财产中扣除该申请人所主张的财产利益。 最后,笔者想特别提到的是,那种超出可追缴款额的范围“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裁决在大多数国家是不可能得到承认和执行的,因为此种没收裁决违背了等值没收的基本限度,可能构成对当事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合法财产的侵犯。在来源于犯罪或者与犯罪有关的可追缴资产已全额没收或者可追缴款额已清退的情况下,针对犯罪人其他财产的没收请求将被排除在国际合作范围之外。对此,一些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如果法院认为“没收令所针对的人已支付了相应数额,或未支付但以其他方式履行义务的情况下已经服刑完毕的,应当撤销对该没收令的登记”。(77) 五、结语 我国《刑法》第64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这里所说的“责令退赔”,不可与第36条提到的“赔偿经济损失”相混淆,应当理解为仅仅针对被挥霍或者已灭失的违法所得,因而构成“狭义等值没收”的表现形式。随着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引入,“依法应追缴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开始在我国刑事法律表述中与“没收”建立起直接的、具有排他性的联系,从而为“广义等值没收”的适用奠定了立法基础。然而,在关于可追缴资产的构成、确定与计算方面以及相关的权利保障问题上,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仍存在着严重的欠缺和一些随意性较强的认定标准,亟需研究和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法制成果和经验,创建一套科学的和统一的犯罪资产追缴与没收制度,并从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角度,“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78) 注释: ①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法律中,狭义的等价没收被称为“追征其价额”。参见李锡栋:“中国台湾地区没收不能时决定追征价额之标准”,载赵秉志主编:《刑罚体系结构的改革与完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4页。 ②《芬兰刑法典》(肖怡译)第10章第8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③《德国刑法典》(徐久生、庄敬华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④《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黄道秀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页。 ⑤荷兰《刑法典》第36e条第4款明确规定:“非法所得包括所节省的费用。”见《荷兰刑法典》(于志刚、龚馨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⑥Gian Luca Soana,La confisca per equivalente,Giuffre Editore,Milano,2013,p.6. ⑦同注③引书,第39页。 ⑧《匈牙利刑法典》(陈志军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7条C第1款b),第29页。 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1条第5款。 ⑩《英国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张磊等译)第7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11)《澳大利亚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张磊等译)第56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 (12)关于刑事没收的“适当性原则”可参阅《德国刑法典》第74条b和《奥地利联邦共和国刑法典》(徐久生译)第20条a第2款,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13)开曼群岛《2008年犯罪收益追缴法》(The Proceeds of Crime Law,2008)第21条。 (14)同注(11)引书,第79页。 (15)珀尔特·彼得主编:《匈牙利新〈刑法典〉述评》(第1-2卷),郭晓晶、宋晨晨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232页。 (16)在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刑法中,没收属于“财产性保安处分”,它是针对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危险性”而采取的预防措施,因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具有引诱和鼓励人们犯罪的“危险作用”,没收是对此种危险性的消除。 (17)Emanuele Nicosia,La confisca,le confische—Funzioni politico-crimiali,natura giuridica e problemi ricostruttivo-applicativi,G.Giatppichelli Editore-Torino,2012,p.16. (18)1995年2月9日,欧洲人权法院在Welch诉英国一案的判决中认定:英国法院于1988年8月24日对Welch判处的等值没收,由于可以转换为监禁刑,具有刑罚的性质,对此种构成刑事处罚的没收应当遵循《欧洲人权公约》第7条规定的不溯及既往原则。Se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9 February 1995,n.307/A.Welch v.United Kingdom. (19)《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条(五)和第31条第6款。我国《刑法》第191条将其表述为“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 (20)例如,匈牙利《刑法典》(2012年修订)第74条第2款规定:“在犯罪当中产生的、在犯罪过程中或以与犯罪相关联的方式被其他人所获得的财产也应被没收。”同注(15)引书,第235页。 (21)参见《葡萄牙刑法典》(陈志军译)第111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4页。 (22)上述关于犯罪所得的分类可参阅《最新意大利刑法典》(黄风译)第240条,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87页。 (23)《黑山刑法典》第75条第1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6页;《芬兰刑法典》(肖怡译)第10章第4条第2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24)《芬兰刑法典》第10章第6条第1款;同注(23)引书,第37页。 (25)同注⑤引书,第25页。 (26)《葡萄牙刑法典》第110条第2款,同注(21)引书,第53页。 (27)《英国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第10条、第75条(2)款(a)、(b)和(c),同注⑩引书。 (28)韩国《关于预防非法贩运毒品特别问题法律》(Act on Special Cases concerning the Prevention of Illegal Trafficking in Narcotics,etc.)第17条。 (29)例如:格林纳达《201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Proceeds of Crime Act,2012)第9条,巴哈马2000年《犯罪收益追缴法》(Proceeds of Crime Act)第11条,特立尼达和多巴《2000年犯罪收益追缴法》(the Proceeds of Crime Act,2000)第6条,等等。 (30)《匈牙利刑法典》第77条B第4款和第5款,同注⑧引书,第29页。 (31)《意大利反腐败法》(黄风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13年版,第91页。 (32)爱尔兰《2005年犯罪收益追缴(修正)法》[Proceeds of Crime(Amendment) Act 2005]第16B条。 (33)李晨阳、全洪涛主编:《缅甸法律法规汇编(2008-2013年)》,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年版,第439页。 (34)同注⑩引书,第66页。 (35)《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刑法典》(王立志译)第77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页。 (36)毛里求斯《2011年资产追缴法》(Asset Recovery Act 2011)第2条关于术语“gift”的解释。 (37)《英国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第79条(2)款,同注⑩引书,第66页。 (38)《荷兰刑法典》第36e条第4款,同注⑤引书,第28页。 (39)《英国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第80条(2)款,同注⑩引书,第67页。 (40)《英国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第296条,同注⑩引书,第232页。 (41)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2014年修订本)第260条和第319条。 (42)《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宗玉琨译)第442条第1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43)《芬兰刑法典》第10章第2条第3款,同注(23)引书,第35页。 (44)《英国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第308条(3)款(a)项,同注⑩引书,第238页。 (45)《奥地利联邦共和国刑法典》(徐久生译)第20条a第1款,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46)《加拿大刑事法典》(卞建林等译)第727.3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3页。 (47)新西兰《2009年犯罪收益追缴法》[Criminal Proceeds(Recovery) Act 2009]第6条第3款。 (48)匈牙利《刑法典》(2012年修订)第74条第5款b)项,同注(15)引书,第235页。 (49)匈牙利《刑法典》第74条第5款a)项,同注(15)引书,第235页。 (50)参见意大利最高法院2012年2月22日第20976号判决,转引自Gian Luca Soana,La confisca per equivalente,Giuffre Editore,Milano,2013,第31页。 (51)开曼群岛《2008年犯罪收益追缴法》第18条(1)款。 (52)《英国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第288条(1)款,同注10引书,第224页。 (53)《英国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第174条,同注⑩引书,第147页。 (54)《挪威一般公民刑法典》(马松建译)第70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55)《英国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第288条,同注⑩引书,第224页。 (56)同注(11)引书,第232页。 (57)《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黄道秀译)第115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58)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2014年修订本)第321条第3款-2和第3款-3。 (59)《法国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罗结珍译)第97条,国际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398页。 (60)《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黄风译)第321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页。 (61)新西兰《2009年犯罪收益追缴法》第20条。 (62)《澳大利亚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第26条,同注(11)引书,第23页。 (63)韩国《关于预防非法贩运毒品特别问题法律》第37条、第39条和第40条。 (64)《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317条第3款,同注(60)引书,第111页。 (65)关于“没收参与人”的概念,参见《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31条,同注(42)引书,第293页。 (66)《澳大利亚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第29条,同注(11)引书;新西兰《2009年犯罪收益追缴法》第30条。 (67)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99条,同注(59)引书,第398页;新西兰《2009年犯罪收益追缴法》第31条和第33条。 (68)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2014年修订本)第322条-2和第325条。 (69)参见新西兰《2009年犯罪收益追缴法》第29条。 (70)《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33条,同注(42)引书,第293页。 (71)根据开曼群岛《2008年犯罪收益追缴法》第38条的规定,该期限为28日。 (72)《英国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第30条,同注⑩引书,第28页。 (73)塞尔维亚《扣押和没收犯罪所得法(Law on Seizure and Confiscation of the Proceeds from Crime)》第54条第2款。 (74)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695-9-15条,引自司法部司法协助与外事司编译:《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立法资料汇编(一)》,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05页。 (75)哥伦比亚是采取此制度的国家之一,参见Contributed ed by Sáchica & Sáchica Abogados Colombia-Law & Practice,转引自http://www.chambersandpartners.com/partners.com/global/firm/343740/sáchica-sáchica-abogados,2015年1月28日访问。 (76)例如根据新西兰《2009年犯罪收益追缴法》第143条和第148条的规定,上述司法救济申请应当自外国没收裁决登记之日起6个月内向新西兰高等法院提出。 (77)马来西亚《2002年刑事司法互助法》第32条第2款,载《马来西亚刑法》(杨振发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4页。 (78)见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四部分(五)。标签: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论文; 法律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刑事犯罪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