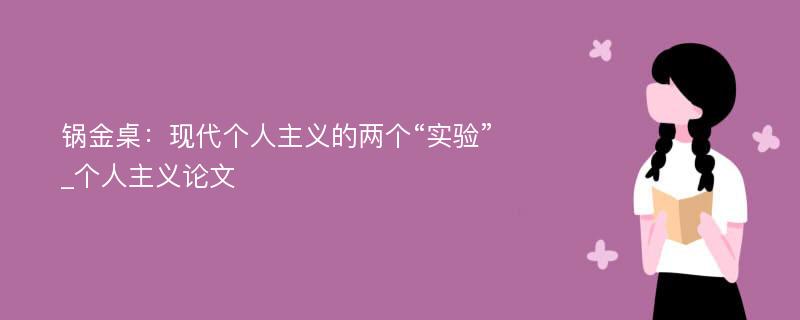
瓦罐与金表——现代个人主义的两个“试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表论文,瓦罐论文,个人主义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643(2009)01-0094-06
1.0“荒岛文学”与个人主义
鹦鹉重复着鲁宾逊的自问:“可怜的鲁宾逊!你在什么地方呀?你到什么地方去呀?你怎么到这儿来啦?”(笛福,1959:127)
这声诘问自18世纪西方现代小说兴起之日起,一直延续至今,询问着每个流放于现代社会、赢得自由却又难返故园的现代个体。这个问题就来自西方现代小说先驱笛福,特别是《鲁宾逊漂流记》和《摩尔·弗兰德斯》这两部堪称姊妹篇的小说,它们讲述着相似的故事:一个失去了过去和未来的孤立个体(男或女),脱离了传统社会关系的保护,被置于孤立无援的悲惨状况之中——险恶的自然环境或者社会环境,他们的生活注定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斗争,他们完全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寻求生存、征服命运。
自此“荒岛”成了个体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生存状态的隐喻,而“荒岛文学”则成了西方小说史上人性的试验场,从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斯蒂文森的《金银岛》,戈尔丁的《蝇王》,到狄更斯的《雾都孤儿》等等,主人公被从社会关系的大网中剥离出来,或者被抛入孤岛,或者流落于完全陌生的、充满恶意的大都市;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脱离了文明的束缚,他们的生存、身份乃至本质将主要依靠自己的行为来确定,个体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承受着来自生存极境的考验。这一极境考验,既可能凸现个体在社会关系的安全网中不曾被激发的巨大潜力,也可能暴露在文明遮蔽下不易察觉的人性真实。
17世纪以来,西欧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不断冲击着旧有的阶级、家族和行业关系,人们固有的群体归属和稳定的社会身份已不复存在。被从人身依附和土地束缚中解放的个体必须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和人生意义。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和新教——尤其是其中的加尔文教和清教的普及,引发了个人主义的出现。
英国学者斯蒂芬·卢克斯(Steven Lukes)在《个人主义》一书中梳理了现代个人主义的基本观念,它包括:人的尊严——单个的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内在价值或尊严;自主——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属于自己,并不受制于它所不能控制的力量或原因;隐私——公共领域中的私生活概念,在这个领域中,个人不受或不应受到别人的干涉,能够做和想他所中意的任何事情;自我发展——拥有卓越的自我,成为自我的精华,乃是人类发展的最高使命;抽象的个人——社会生活的所有形式都是个人的创造,只能认为是实现个人目的手段;政治个人主义;经济个人主义,它相信尽可能让个人得到自由的自我发展,以此来实现社会进步,主张经济自由和私有财产;宗教个人主义,它认为个人信仰不需要中介,他对自己的精神命运负主要责任,并有权利和义务以自己的方式直接建立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而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是一种契约或协议关系。(斯蒂文·卢克斯,2001)
事实上这些观念已经渗透到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塑造了每个现代个体。个人主义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个人主义的原则把人从社会母体中剥离出来,赋予了他不断膨胀的权利和满足欲望的理由,使自我成为一切的裁判者;另一方面,它也为遭到长期压抑的人类思想提供了新的驰骋空间,鼓舞着个体满怀尊严,能够独自面对人生的斗争并追求幸福。
伊恩·瓦特(Ian Watt)认为小说的兴起与现代个人主义思想的兴起密切相关,认为小说表达了特定个人在特定时间、地点的特定经验,而现代小说的兴起恰恰有赖于以个人主义为其特征的现代社会的建立,反过来小说又是现代个人首先亮相的文化舞台,它是“最充分地反映了这种个人主义的、富于革新性的重定方向的文学形式”。(伊恩·瓦特,1992:6)
本文力图从小说的源头考察个人主义在文学世界中的表达和遭遇,因为“笛福的哲学观念与17世纪英国的经验主义者极为相似,他在表现个人主义成分方面比以往任何作家更加彻底,他的作品独特地反映了各种形式的个人主义与小说的兴起之间的联系”。(Watt,1967:62)孤立的个体在笛福创造的艺术世界中所经历的一系列遭遇,使我们看到这两个个人主义的“试验”既标定了个人主义所能创造的辉煌或者说达到的个人能力的极限,也引发了我们对个人主义的疑问和困惑,而笛福对孤立的个人的关注,则开启了现代小说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追现代小说之本,溯现代个人主义之源,无疑会加深我们对当下现代个体生存困境的认识。
2.0个人主义的两个试验
对一个有闲暇阅读小说的读者来说,无论荒岛求生还是犯罪生涯,都是陌生而又充满刺激的想象空间。对作家来说,这是一个安全而又逼真的冒险游戏,惟其安全,想象力才敢于脱离生存本能的基本考虑,惟其冒险得逼真,才更富创作的吸引力和挑战性。
笛福搭好了人物活动的舞台,也为读者想象力的活动给出了基本图示:风险、海难、荒岛、孤独——《鲁宾逊漂流记》;犯罪的母亲、被抛弃的孤儿,既可能招致危险又可能是原始资本的女性美貌,充满诱惑和欺诈的、商品交易主导的男权社会——《摩尔·弗兰德斯》。
接着,作家召唤来一男一女给他们吹进了相似的灵魂:顽强的求生意志、热爱生活,充满行动力,决不多愁善感,有着简单的生活准则,粗浅的道德,遭遇接二连三的打击决不灰心,同时他们又都像商人笛福一样精明而讲求实际。
在小说想象的起点,我们就可以看到其中蕴含着新兴的个人主义观念:对自我发展的强烈渴望,经济个人主义动机。虽出生于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鲁宾逊却一心一意要到海外去,百折不挠:“我的倒霉的命运却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逼着我不肯回头”,“使我不顾自己冷静的理智的劝告”,不顾尝试中的教训,“继续前进”(笛福,1959:11);摩尔则出生贫贱,是个被抛弃的孤儿,从小立愿一定要做个贵妇人。
笛福把这样两个人物抛在被茫茫海洋包围的“孤岛”上。生存的极境一方面构成了对主人公生存的永恒威胁,另一方面为他们“提供了实现现代文明三个相关趋势的最充分的机会,即经济的、社会的和理性的绝对个人自由”。(伊恩·瓦特,1992:89)让他们自发活动起来,观察他们的反应。
在荒岛上,“鲁宾逊享有摆脱社会羁绊的绝对自由——没有家庭纽带或公民义务干涉他的个人自主权。最关键的是,荒岛给了他经济人实现其目的所需要的完全地自由放任”(同上:90):没有占有者和竞争者的荒芜岛屿和土地,不需要工资的劳动力——土人星期五、被搭救了的水手及移民。而摩尔·弗兰德斯的孤儿出身,天生贫困的窘境,求生存的沉重负担,又是男权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女性,这些都使她获得了一个流浪贱民才能享有的、在道德上的自由:有足够的理由“作奸犯科”,同时免于那些来自道德戒律、敏感的良心或者感情纠葛的苛责,正像弗吉尼亚·吴尔夫为她辩解的:“那都是由她的不幸出身造成的结果”,“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她可以毫不犹豫地撒谎”,“她没有时间多去考虑自己的感情;撒一滴眼泪,短短一瞬间的灰心丧气,然后一切照常进行”。(弗吉尼亚·吴尔夫,2005:54-55)
前者面对的是自然的挑战,获得的是向上的自由,后者面对的是社会的挑战,获得的是向下的自由。
3.0鲁宾逊的瓦罐
吴尔夫提醒我们注意《鲁宾逊漂流记》中一再出现的那只瓦罐,强调它的泥土性和结实性,提醒我们“为了寻求关于透视中的这三大基本方位——上帝,人类,大自然——的信息,我们所做出的每次努力,都被冷冰冰的普通常识顶回来了”。(同上:204)因为小说内容里占支配地位的全是现实、实际、财产。瓦罐不仅凝聚了笛福对个人创造力的强烈自信,也是他文体风格和人生态度的象征。
这个瓦罐,是鲁宾逊在毫无经验和无人帮助的情况下独立创造出来的。制造陶器可说是达到了个人创造力的顶点,因为它远非表面上看得那么容易,根据Lydia H.Liu(Liu,1999)的考证分析,以当时西方的科技基础、鲁宾逊所处的环境和采用的方法、物质条件,鲁宾逊对于陶器的独立研制创造更像是科幻小说而非现实主义。陶器这个意象后来又出现过一次,当时鲁宾逊质疑上帝对于世事安排的公平性,他反驳自己道“我们都是陶工(上帝)手里的陶土,没有一样陶器可以向他说:‘你为什么把我做成这个样子’”。(笛福,1959:186)
鲁宾逊与陶器——上帝与人,这一也许并非有意的类比包含着鲁宾逊对自己伟大创造——以陶器为典型代表——的骄傲。试验的结果是振奋人心的,鲁宾逊不仅生存下来了,还独自重历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这一切如此平淡而真实,让现代读者们惊讶、兴奋,因为我们早已远离原始环境进入社会化大分工、经济专门化的时代,个人创造力从未如此充分而生动地展示过。自我发展和个人奋斗就是让这个普通德国商人后裔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创造奇迹的最重要原因,而竖在荒岛上的那个十字架,则为现代个人记录下它驯服带着恶意的自然,并使主人公成为自身命运主宰的整个辉煌历程。
在上岸第十一二天之后,鲁宾逊竖起了一个大十字架,用刀刻上日期。这个特别的计时装置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是他与那个不在场的人类社会保持联系的方式,因为只有在人类的群居中日期和日历才有意义。同时在基督教里,十字架标志着基督徒自受洗之后在基督那里得到的新生——正像鲁宾逊海难中被水浸没所象征的那样。小说中并没有暗示鲁宾逊的十字架与基督有什么关系,它更像是主人公对自己的纪念,纪念他在荒岛上获得的崭新的个体经验——强调他已经完全自给自足,成了自己世界的中心。他像是已被上帝选中创造着岛上的一切文明,掌管着这个小小的世界。
陶罐的泥土性和结实性也是笛福极力要达到的文体效果,这不仅源于笛福重实际的商人头脑,也是作家想要他的读者对这个虚构的“试验”笃信不疑的基础。在这两部作品的序言里,他都郑重地宣称自己只是作为捉刀人,编辑了现实生活中某个真实人物的日记或者回忆录,他完全依据事实而根本没有虚构。笛福为了加强作品的真实性,极力排除古典文学中的传奇色彩、英雄主义,注目普通人琐碎的日常生活,甚至经常采取科学实验中的计算与测量的方式来看待他的世界。
他没有简单地说他的围墙围了一块很大的空地,而是以土地测量员的精确告诉我们说空地有150码长,100码宽;他没有笼统地说花了很长时间才造好独木舟,而是精确地叙述说花了20天砍倒大树,14天去除树枝。那也不仅仅是棵苍天大树,而是下端直径5英尺10英寸,顶端4英尺11英寸,总长22英尺的大树。(笛福,1959:65)
笛福的语言具有数学式的明了,其散文简单、明确的特点体现了17世纪后期科学理性的新价值观念。他的文体在细节上反映了洛克的哲学:只满足于指示出他所描写的事物的第一性质——事物的体积、形状、外延和数量,尤其是数量,这些被认为是客观的,物体所固有的;而对事物的第二性质——它们的颜色、声音或者滋味——却很少注意,因为它们是跟主观感受有关的,某种意义上它是由主观决定的。因而小说主人公鲁滨逊对美似乎毫无感觉——加勒比地区的风光他很少投去一瞥。而美的理念形式,诸如英雄主义、卓越的美德在他的脑子里几乎从没出现过。
排除了这些感性的主观不确定因素,鲁宾逊的个人主义实验就赢得了科学实验般的说服力了吗?
4.0摩尔的金表
金表在《摩尔·弗兰德斯》中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意象,它将摩尔人生的两大关键词凝聚一身:黄金(交易)与时间(青春),同时还暗示了她企图实现的最深层次的欲望——改变命运成为贵妇人。
摩尔未出生时就有了原罪——他的母亲偷了三块上好的布料,像是作为惩罚,她成了孤儿,一无所有地流放在没有亲友的人世。不象鲁宾逊,在生存试验的起点,还有沉船的货物积存,大片虽未开发却很富饶的地产,作为生存的基本依靠。
她可以依靠的只有自身的美貌,于是以此为资本做了12年的情妇或妓女,结过5次婚,不断变幻自己的角色,适应各种不同的生存环境。这个女人不甘贫困,精明而富实际经验,坚毅独立——她依靠男人寻求经济的安全,但是只要有可能她就以男人为工具最大限度地获取自我独立。
到48岁的时候,摩尔的第五任丈夫被一次经济损失击垮,忧郁悲伤而死,不过摩尔却依然保持着她的生命活力,很快作出实际的判断,“现在我的美貌已经衰颓了”,“我很容易地看出剩下来的钱是不能维持我多久的”。(笛福,1982:173)
现在她意识到自己的生活角色和谋生手段必须发生一个大的转变,因为她已经失去了最原始也是唯一的资本:青春。
于是金表的意象出现了——金表是她成为一个正式小偷的标志,因为这是她经过“职业培训”后第一次作案的战利品。伊恩·瓦特也注意到了金表的细节:当时摩尔被英国流放到美洲殖民地,她送儿子一块金表作为纪念,随后自嘲说:“我的确没有告诉他这是我在伦敦一个会场上从一位太太身上偷来的”(伊恩·瓦特,1992),而实际上前文已经交代那次对金表的行窃并没有得手。他认为这是作家笛福在创作小说时的细节疏忽。
但是任何人在讲述自己的记忆时都一定包含虚构、不准确以致前后矛盾之处,有时还会出于某种(未必意识到的)目的而撒谎,而该小说的叙述视角正是第一人称自传性回忆,那么金表出处上的矛盾,更准确地说,不正是主人公摩尔本人的记忆含混吗?
摩尔最喜欢偷盗的就是太太们身上的金表。因为在她看来金表是一种贵妇人的身份象征,乃至偷窃时为了掩人耳目“我们总是打扮得很好的”,穿着“很讲究的衣服,身上也挂着一只表,和贵妇人的样子也不相上下”。(笛福,1982:193)这样偷金表除了要获取财富以外,也暗含着对取得一种社会身份的渴望。
送给儿子的金表究竟是偷的还是正当获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含混中暴露出:她可以得到金表还有财富,但是金表与财富所象征的那个身份地位,在心理上她并没有得到,至少她潜意识里对此是存疑的,以至于通过正常途径获得的金表她也无法确信它的来源。
金表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象征:交易。摩尔送儿子金表可不仅仅是为了纪念他们的重逢。此前她的儿子送她55个西班牙金币,并宣读遗嘱给她一块垦殖地;送出后她还以一贯的精明算计并极力辩解了一下:这只表的价值并不低于他那满皮袋的西班牙金币。她回家得意地告诉丈夫得到了多少金币和土地。这时候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她的丈夫突然举起双手感谢上帝,摩尔相信自此“他是个诚实的忏悔者,一个完全改过自新的人,上帝的恩惠从来没有使一个强盗,一个剪径,一个放荡的人变得比他更好”。(笛福,1982:309)看来,摩尔用来做交易的不仅有感情还有信仰。
金表连接的恰好是摩尔前后两部分的人生——也是小说的前后两部分,而且在内涵和结构上呈现出一种对称性:年轻时用青春(时间)换取金钱,年老色衰之后用盗窃来的金钱换取继续生存(时间)——小说结尾摩尔差不多70岁了,仍然身心俱健。交易是贯穿其间的生活方式。
个人主义在摩尔世界中的遭遇,从消极的方面说也是令人安慰的,因为我们看到“兴衰沉浮并未损害她(摩尔)的惬意的生命活力;我们的最严重的罪行,我们的最卑鄙的道德弱点,显然永远不会剥夺别人对我们的热爱,甚至不能剥夺我们的自尊。”(伊恩·瓦特,1992:145)
5.0无法结尾的个人主义神话
看来“神秘而有力的天数”,一心一意出海的冲动,直到小说结尾也没有放过已经62岁的鲁宾逊,他又出海了,回到一开始被他视为监狱的小岛。在那里又度过了惊险的10年——作者声称这些故事将由续集讲述。笛福后来果然又写了续书,不过看来就像007系列一样,除了让他死以外没办法让鲁宾逊退休,给小说一个自然而完整的结局。
摩尔·弗兰德斯和她的丈夫在小说结尾被安排重返英国,决定用余生“诚恳地忏悔我们以前所度的罪恶生涯”(笛福,1982:312)——一种单调而沉闷的生活,不过更像是打发读者不再追问下去的托词。
这两部小说都面对着结局的困难,这并不简单的是一个创作问题。两个执著于个人主义的主人公自流落“荒岛”之后,虽然获得了完全的自由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却无法找到回归的路,找不到皈依,自然无法结局。这种结局并不是说一个明确的、终止性的结尾——诸如男女主人公终于结婚了或者主人公死了,它完全可以是开放的,有很多可能性的,但是结尾应该赋予小说整体一种指向性:或者指向自身,引发读者反观全篇,因发现现象间的联系或者现象背后的意义而获得一种整体感,就像我们回顾凌乱而偶然的生活时所作的那样;或者指向其外——给读者一个充分想象的空间,由小说设置的种种提示生发出去,带着想象去思考。但是现在,这两部小说的结尾,更像是对简单重复主人公冒险经历的疲倦:作者和读者都累了,它应该停止了。
对鲁宾逊和摩尔的个人主义奋斗威胁最大的,就是孤独的实际心理作用,这可能造成两个个人主义神话的解体。将个人经济利益放在首要地位的趋向,使得笛福极力将人与人的真诚关系,情感纽带驱逐到文本的边缘地带。为了保证个人主义试验的成功,为了给主人公赢得足够的自由,两部小说都极力压抑和排斥了一些重要因素,这在鲁宾逊和摩尔身上表现为一种完整人性的缺失,而正是这种缺失宣判了他们永无皈依的放逐,没有整体感地重复。
当鲁宾逊看到沙滩上有人的足迹时,他被吓坏了,立刻就对足迹的出现作出消极的解释,认为一定是魔鬼或者入侵者留下的。他从来没有乐观地想象那可能是天使或者另一个欧洲人的足迹,可能会搭救他,或者成为他的朋友。这种对他人的本能的消极、恐惧反应,让我们感觉鲁宾逊可能根本就不想返回人类社会,此刻所经历的孤独正是他的理想状态。
鲁宾逊从未对任何人表现出亲密真诚的情感,他用冷淡的语气、档案式的方式介绍自己的父母:他们的国籍、职业、出生地……,当他永远离开父母时也从未表现出一丝眷恋。与之鲜明对比的是星期五与父亲重逢时又叫又跳,活像发了疯似的。35年后鲁宾逊回到祖国,得知父母不在世,首先想到的是“家里没有给我留财产”,“我也完全找不到一点救济和资助”。他对爱情——最亲密的人类关系——只字未提,他是这样论述婚姻的,“我马马虎虎的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不久我妻子便去世了”。(笛福,1959:261)
但我们可以从小说结尾部分,通常被看作是鲁宾逊创业故事的补充部分,找到被笛福排斥的因素,德里达所谓的“增补的逻辑”。鲁宾逊自荒岛归来时,经济境况惨淡。他在海外冒险多年,必须得到可观的财富回报,才能完成他那个时代英雄人物的创业历程。就在山穷水尽之时,曾搭救过他的葡萄牙老船长,通知他在巴西的种植园增值了许多倍。27年的分离,老船长却一直对他忠诚、热情,并为他苦心经营。也就是说,是另一个人类成员最终成就了鲁宾逊的财富神话。老船长对他的这种真诚的人际关系,默默成就了小说中占主导地位的对个人主义创业的讴歌。
摩尔对深层情感的无能几乎与鲁宾逊是相同的。笛福为了使他的主人公保持完全而持续的自由、不断在社会中孤独地漂流下去,生硬地让每个能给她幸福的丈夫毫无说服力地死去。在每次男女关系结束之后,摩尔都会很快地结算出自己在经济上的收益与损失。哪怕是她声称最爱的人,她在难过的时候还不忘摸摸口袋看爱人给自己留了多少钱。她对自己的很多个孩子也是如此:或者付了钱把孩子送人养,或者与儿子做交易。在作为个人奋斗故事的补充部分,摩尔发财致富,达到了个人主义神话的顶点,而这又是由于一个对主人公忠诚无私、充满感情的人的妥善经营造成的。
生活首先是个做交易的地方——笛福小说中的世界是一个仅仅从为生存而斗争这个角度来定义的世界。物质导向的一个结果是,主人公把人类的每一个体都看作是被深深孤立的个人,其他人都被看作是可资利用的。比如摩尔的人际关系倾向于非常突兀的结束,不留一点感情。小说中出现了许多次要无名的人物,仅仅是用来发展情节然后就被抛弃了。人类生活的精神层面几乎被物质考虑遮蔽。人类可能找到超越生理与物质限制的观念,在笛福的观念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两个文本隐藏着二元对立的结构:个人/社会,理性/情感。占据主导同时也是作者极力宣扬的是个人(脱离社会关系)的奋斗,理性的不受(感情)羁绊的自由,个人主义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在人生幸福的追寻中大获全胜了。在文本的边缘这些被驱逐、受压抑的幽灵(与社会的关系,与他人的感情联系)却在暗地里成就了个人主义的成功,反过来也就在逻辑上解构了个人主义的神话:完全孤立的个人成功是不可能的。
6.0结语
这两部小说可说是关于现代个人主义的两个寓言,既测试了个人主义可能达到的成就,也蕴涵着深切的忧虑。自现代小说的源头就可以看到现代个体的生存困境:个人主体意识觉醒的同时,也被放逐于茫茫世界中的“孤岛”之上,身处于难以逃避的永恒矛盾之中——对自我的珍视与对回归家园的期盼,脱离母体后的自由与返回大地怀抱的渴望……正像因为得到智慧而被逐出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