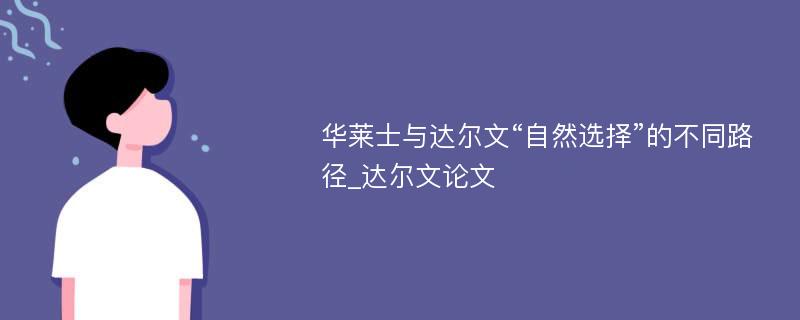
华莱士和达尔文不同的“自然选择”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达尔文论文,自然选择论文,之路论文,华莱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华莱士与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间的差异
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和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各自独立提出了以“自然选择”为机制的进化理论,他们是杰出的先锋思想家,他们之间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19世纪典型的博物学家,他们在偏远地区进行的广泛研究在他们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华莱士和达尔文各自都受到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人口论》(Principle of Population)的影响,他们都认识到动物和植物处于“生存竞争”中,并将这一点视为形成他们的进化理论的关键。
这些相似之处有时候会影响我们对达尔文和华莱士进化论的重大差异的评价。例如,在性别选择的雌性选择的重要性方面,华莱士与达尔文的观点完全不同。华莱士和达尔文的理论首次出版四十年之后,华莱士提出,“由于雄性的斗争而产生的性别选择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与达尔文不同,我认为不存在任何雌性的选择,科学观点的潮流是向着我的观点方向移动的”。当时,华莱士是正确的;科学观点确实是朝着华莱士的观点方向移动的。通过雌性选择实现的性别选择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成为进化论生物学界高度关注的主题[克罗宁2001,页167-170]。达尔文和华莱士在人工选择和驯化生物与野外进化之间的关联性上也持有不同观点。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在对通过自然选择实现的进化的“长篇论述”的开始部分论述了生物饲养的类推结论,尤其是鸽子的饲养。相反,华莱士对从饲养动物和植物中所推出的结论在自然界生物中的适用性表示怀疑[Shemer 2002,p.116]。
华莱士和达尔文之间的另一个重大分歧涉及杂交不育性是否可以通过自然选择的直接作用而进化,也就是说,杂交不育性本质上是否具有适应性?达尔文和华莱士一致认为,在分化的初始阶段,端始种之间进化的任何杂交不育性都不是杂交的部分不育性直接选择的结果,而是其他特征分化偶然产生的副产品。达尔文认为,所有杂交不育性和不可杂交性都是副产品;相反,华莱士认为在某些情况下,选择能够直接提高已经具有部分不育性的杂交的不育性。并且,华莱士觉得他将自然选择拓展到一个达尔文未曾涉及的领域。在华莱士的晚年,达尔文去世很长时间以后,华莱士在论述他对自然选择进化论的贡献的同时,将“维持自然选择提高杂交体不育性的能力”列为他对达尔文主义的拓展。[Johnson 2008,p.114]
另外,华莱士和达尔文在人类起源问题上的争论,也是许多华莱士的研究者们广泛关注的。华莱士的人类学思想主张自然选择不适用于人。对于这一问题,不同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史密斯和费奇曼相信,华莱士总是将自然选择视为一种服从于更深奥力量的规律。但是,长期存在的一种观点是,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某个时间,华莱士在人类智力和道德特征的进化问题上经历了急剧的观点转变,这一转变与他对唯灵论的接受以及对他的作品构成国内政治利用的动机有关。对于这一观点的代表有科特勒(Kottler)和斯洛顿(Slotten)。[Johnson 2008,p.124]
然而,华莱士和达尔文两人在世时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共同分享发现殊荣的自然选择理论本身也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华莱士的自然选择理论来源主要来自于野外考察,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则主要是基于对家养动物的观察。研究者们很早就关注到,华莱士与达尔文各自的“自然选择”理论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人口学家尼科尔森(Nicholson)在1960年就指出,华莱士倾向于认为环境确立了绝对的适应值衡量标准,一个物种中的所有成员都要接受检验。凡是不能通过这种标准检验的就要被淘汰,只有在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才可以发生进化[Nicholson1960,p.491]。鲍勒(Bowler)同意尼科尔森的观点,在1976年的文章中他也认为华莱士的论文忽视个体间的竞争,而强调环境对物种的选择压力[Bowler 1976,pp.17-19]。杜兰特(Durant)在1979年也指出,华莱士的选择单位相对于个体而言更多地发生在群体之间[Durant 1979,pp.41-45]。科特勒(Kottler)1985年和麦克尼尔(MacNair)1987年也批判华莱士用类似于群选择理论来解释通过自然选择而实现的进一步杂交不育性的进化。[Kottler 1985,p.384;MacNair 1987,pp.105-115]
到了近期,研究者们又给出了不同的看法,莱斯(Reiss)在2000年强调华莱士对自然选择的坚持和宏观考虑有着比达尔文更为彻底的优越性[Reiss 2000]。约翰森在2008年的华莱士前沿研究论文集中认为,有些学者批判华莱士利用天真的群体选择论述来解释通过自然选择而实现的进一步杂交不育性的进化是武断的。虽然,华莱士经常诉诸物种的利益,但是还并不清楚,他是将杂交不育性视为物种水平还是个体水平的适应。他引用克罗宁1991年的观点,华莱士和达尔文的作品中都充满“对物种有利”的说法,或许和当代生物学家谈到有机体的意愿而不提及它们有意识一样,只是一种捷径[Johnson 2008,p.117]。然而,无论华莱士自然选择理论的选择单位是什么,很多学者观察到了华莱士与达尔文对各自“自然选择”理论的微妙差别。那么导致华莱士与达尔文理论差别的原因何在?生物学史学家发甘(Fagan)最近采取的方法是,对华莱士和达尔文存在不同的出身经历和社会关系的,以及不同的博物学动机和理论兴趣的审视,能更好地理解两人在博物学实践中产生不同的习惯与方法。而这些不同的习惯与方法,又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华莱士在标本采集中对种与属层面的关注,以及达尔文相关工作中对个体细节的关注。当理解了华莱士和达尔文在博物学实践中对生物标本的不同的关注层面后,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两人在“自然选择”理论中所表现出的微妙差异。[Fagan 2007,p.601]
二、华莱士与达尔文出身及海外经历的不同
发甘发现,如果对二人的著作进行比较,会发现华莱士的著作中更多的是对种和属的关注,而达尔文的著作中对生物个体的描述更为突出。华莱士强调个体的群体特征,而达尔文强调并描述了不同个体间的细节特征。华莱士清楚地区分了群体与个体,而达尔文则相对模糊。这与他们之间“自然选择”理论之间差异的推论是相符合的。对于这种不同的关注倾向,发甘通过对二人的博物学实践进行详细的对比来寻找答案。二人虽然同为业余收集者而走上博物学之路,但却存在着诸多不同的背景。例如,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和出身的不同,决定了他们社会关系之间的差别。经济状况和理论上兴趣的不同也会导致博物学实践中侧重点的不同。在详细探讨二人博物学实践中的差别之前,我们首先有必要来关注二人的出身和航海经历。
达尔文的幸运出身广为人知,他的爷爷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 Darwin)是一个成功的医生,他的父亲也是位成功的医生,他的母亲出自著名的陶器商人韦奇伍德家族;达尔文曾被送到爱丁堡大学,继承家族学医的传统,但是他在手术台前感到恶心,不久就放弃了学医的打算。家人决定他应该在教堂谋得一个正式的职位,为此,他在1827年后期进入了剑桥基督学院。在那里他与植物学家约翰·亨斯罗(John Stevens Henslow)和地质学家亚当·塞治威克(Adam Sedgwick)等一批学者广泛接触。他与亨斯罗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已经读过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南美洲个人旅行记》(Personal Narrative of Travels in South America)的记述,而且憧憬着到热带地区研究博物学。到了1831年年末,来了一个机会。亨斯洛推荐他登上了英国海军派遣的一艘小船贝格尔号,这艘军舰的任务是去测量南美洲的海洋。船长费茨罗伊(Fitzroy)是皇亲国戚,需要找一位绅士作伴,以消除航海期间的枯燥,作为补偿,特地邀请一位博物学家,这样他也可以对到过的地方进行描述。达尔文由此获得了出海进行历时5年的游历机会[鲍勒1999,页195]。达尔文在这一时期的任务主要集中于地质学考察,查尔斯·赖尔(Charles Lyell)的《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正是他航行中研读的主要著作。他的这次出行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他的父亲还为达尔文支付了一笔可观费用。达尔文经济上稳定、社会关系广泛,以及众多的支持,为其博物学考察提供了广泛而自由的空间。船长费兹罗伊也从来不干预达尔文的博物学考察。与华莱士相比,达尔文甚至可以说有着自己的博物学团队的支持。他寄回英国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地雀,就是在鸟类学家古尔德(Gould)的帮助下进行分类鉴定的,达尔文也因此受到了启发。由于其在陆地上要经常骑马,他的标本采集工作很多也是依赖于他所雇佣的水手完成。[Fagan2007,p.612]
贝格尔号完成航行,抵达伦敦之后,达尔文开始了忙碌的工作,而他最初还是在地质学会阅读各种论文。对于物种概念的转变,多数现代史学家都相信是在他回到英国后发生的,而不是在他航海期间[鲍勒1999,页204]。这一点与华莱士的情况正好相反。
从某种程度上说,华莱士和达尔文互为镜像,达尔文的祖上来自于工人阶级,靠个人奋斗在上层社会立足,而华莱士来自于有特权的父母,但他们失去了财产,使孩子除了奋斗之外别无出路。华莱士的出身并不像他同时代人中绝大多数博物学家那样富裕,因此其早年生活也十分与众不同。达尔文读的是最好的学校,毕业时拥有一流的推荐信和可靠的经济来源,而华莱士则是自学成才,同时靠自己的双手辛勤工作才能养活自己。这种自我依赖部分原因来自于其父经济上的失败。在其早年,他的父亲在一次出版投资中,浪费了家中大部分的继承资产,而其余部分被诉讼所夺走。[米尔斯2010,页48]
华莱士的工人阶级背景也是他能够成为一个自力更生、足智多谋、现实的人的重要因素。没有这些特征,他在热带地区也不一定能够获得作为一位收集者的成功。1837年,华莱士十四岁,他作为一名测量员实习生成为他的哥哥威廉的学徒。在接下来六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的乡村遍布兄弟俩的足迹,华莱士很喜欢这样的生活,对于他所工作地区的自然历史越来越感兴趣。他摘抄了达尔文的《贝格尔航海日志》(The Voyage of the Beagle)中的文字。达尔文的这一著作对华莱士形成了早期影响,激起他独自旅行异域的欲望。
华莱士不断增长的科学兴趣使他开始涉猎地质学方面的著作,其中也包括查尔斯·赖尔所著的颇具影响力的《地质学原理》。这部著作在华莱士观点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们为华莱士提供了这一学科的一般背景,这一学科成为华莱士的生物地理学的组成部分,还因为这部著作支持均变说原则。均变说为通过自然选择而实现的进化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它强化了“变化是逐渐发生的,使自然选择有时间产生新物种”的观点。
华莱士将1840年到1843年这段时期视为他生命的转折点,在这段时期,他已经确定了其未来的路线。他对自然世界已经入迷,系统地获得了自我教育,已经获得了与他不断发展的理论前景互补的广泛、实际的技能基础,现在所需要的只是激起他行动的火花。这一火花将由亨利·沃尔特·贝茨(Henry Walter Bates)提供。
华莱士发现贝茨是一个与他志趣相投的人,他们兴趣相似,可以讨论各自的观点,尤其是关于进化的观点。莱斯特有一家非常好的订阅图书馆,正是在这家图书馆,华莱士阅读了三本非常有影响力的著作。洪堡的《南美洲个人旅行记》描述了他沿奥里诺科河的探险经历,这促使华莱士亲自体验热带地区的大自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华莱士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形成的关键;最后,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匿名发表的《宇宙自然历史的遗迹》和钱伯斯的《创世的自然史之遗迹》(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是一本畅销书,将进化观点(“物种问题”)带入一般论辩的范围,点燃了这两位年轻的自然主义者的想象力。
两人一同阅读了爱德华兹(Edwards)关于亚马逊昆虫的著作之后,决定去新大陆的丛林之中做昆虫的采集者。他们设法买到了船票并于1848年启程。他们的想法是捕捉昆虫然后把标本寄回伦敦,以便能得到继续采集昆虫的资金,甚至也许能为他们回国以后积攒些积蓄。贝茨到了巴西以后很快就病了,这在对抗药物几乎未用于热代疾病的危险年代来说并不是什么罕见的情况。华莱士只能自己出去采集,他也很快爱上了采集昆虫。他对他所遇到的当地土著人十分热情,在他的日记与著作中也充满了其与当地人的互动。因为最好的昆虫,即那些欧洲采集者所未见过的,只有在离文明最遥远的地方才能被找到,所以他在偏远的甚至无人烟的区域投入了好多时间。在这些年里,他往往生活于土著向导与当地定居者之中。这次探险的费用将通过出售他们的收集以及标本而获得。
华莱士在亚马逊河流域的收集工作持续了四年半的时间,他最大的成就是探索了尼格罗河上游和奥里诺科河源头,由此实现了他效仿他的偶像洪堡的理想。在这种恶劣条件下收集标本是一项艰苦、危险的工作。华莱士经受了热病的反复折磨、受到叮咬昆虫的攻击、并经历了濒临饿死的情况。华莱士没有像当时典型的欧洲探险者一样进行昂贵的探险,而是轻装旅行,没有挑夫随行。他和当地土著人一样生活。经过数年的昆虫动物皮毛采集后他于1852年准备启程回英格兰。当他到达码头的时候他发现绝大多数要寄往伦敦的标本在他在野外继续工作时都被官员扣留在了码头,因为他们觉得他从事的事无益,他们不懂为什么人人都想要看死的虫子。经过看上去繁琐的官僚形式和行贿,他最终说服当局给他送货。然而很快,灾难发生了;他的船,海伦号,着了火然后沉没了。他幸运地逃生,靠救生艇在海上漂浮了数天并幸存了下来,但他所采集的标本和他的笔记全都消失在大火和海洋之中。幸运的是他的代理人萨摩尔·斯蒂文森(Samuel Stevens)(帮他将寄回的昆虫在英格兰转卖的人)为货物上了保险,所以华莱士回国后并没有一贫如洗。
华莱士回到英国的时间很短,总共只有16个月左右,在此期间他安排了个人事务,准备进行下一次探险。几乎毫无疑问,他会回到丛林野外,因为他没有其他选择。在一段时间内华莱士暂时将东非视为一种可能,但是最终确定马来群岛更安全,这里相对来说收集工作做的较少,至少为了生物学研究而进行的收集工作较少。华莱士在马来群岛的八年时间为他的科学理论的建立以及他的生物地理学著作的许多主题提供了原材料。可以肯定,他是怀揣着远大的目标,即物种起源与变化的规律的目标来到马来群岛的,就像他在写给家人的一封信中所说,这封信可能是他对家人请求他回到文明世界的回复:
但是我在这里正在进行更为广泛、全面的研究——对动物与时间和空间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或者换言之,对它们的地理和地质分布以及其根源的研究。我已经决定要在印澳群岛解决这一问题,我必须尽可能去探索更多的岛屿,从更多的地区收集动物标本,以便能够得出任何确定的结论。[Raby2001,p.144]
像大多数那个时代的生物学家一样,他经常会考虑他的见闻如何能为进化机制提供新的洞悉。在他的南太平洋之旅中,在一场很可能是疟疾发作所导致的眩晕之后,他重新阅读了马尔萨斯的著作并浮现出一个新的想法。在1858年2月他寄往皇家学会一封信,委托生物学委员会当时的主席达尔文转交,宣布他所发现的生物学进化原理,即物种通过继承变异和幸存的适应性机制完成改变。就是后来著名的进化理论,自然选择理论。
捕捉昆虫以用阐明物种进化理论不是唯一吸引华莱士注意力的东西,在马来西亚的八年里,华莱士认识到本土的土著人正在被欧洲人所剥削。帝国主义的伪善,成为了他日后写作和政治工作的主题。华莱士1862年回到伦敦去建立他作为作家和昆虫学家的科学职业生涯。虽然他天性沉默寡言与达尔文的游刃有余不同,同时他对伦敦贵族化的科学圈又是个门外汉,但他很快结交了朋友,并且被允许加入重要的团体。他的出版记录增长到了多产的比例,他有很多文章在杂志中发表,也出版了很多著作。
虽然,19世纪的英国,科学是受到政府资助和鼓励的活动,但华莱士的早年经历是个例外,他的早年经济状况使得他长期生活在工人阶层和土著人之中。达尔文随贝格尔号的博物学考察和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随响尾蛇号的博物学工作一样都是受皇家海军支持的。但是与达尔文和赫胥黎不同,华莱士虽然也受过政府的些许资助,但他一直是一个要为经济问题费心思的博物学家。在他的南美和亚洲之行的12年里,他别无选择地与当地土著人相处在一起。[Rayher 1996,pp.167-168]
华莱士的经历与出身与他在科学史上的形象如影随形,他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在当时的英国阶级社会,他的出身没有社会地位,他后来成为科学界以及相关领域中卓越的知识分子,也是科学史上的奇闻之一。然而,在他去世后,他的形象又变得相对卑微,这一事实令人心酸,同时更耐人寻味。达尔文传记的作者这样描述,“华莱士来自另一个世界,他为标本讨价还价,以及他的社会主义出身都泄露了这点”。“华莱士这个社会主义者在亚马逊河与远东采集标本时,已经变成土著,他对那些野蛮人极其尊敬”。[戴斯蒙德、穆尔2011,页358,436]
三、华莱士与达尔文博物学实践中的差异
对比二人的出身与航海经历将会有利于接下来的探讨,达尔文为什么对生物个体标本的观察更为细致,而华莱士则更关注生物标本属和种层面的界定。达尔文的考察航行之初并未明确考察物种变化的方向,而是更多的以地质学考察为主,这从他对地质学的兴趣大过动物学与植物学以及日记中四倍于动物学的地质学记载就能看出。而且,他总是在马背上观察贝格尔号停靠的沿海地区的地貌与地质环境。他的兴趣首先在地质学上,其次才是动物学。当采集到标本时,他会用更多的时间观察标本的细节,却不能有更多的时间去采集它们。
而华莱士在海外博物学考察之前就受钱伯斯赖尔的影响已形成了物种变化的观念,并且确立了寻找物种变化的目标。可以说华莱士是第一个为寻找物种起源而进行海外博物学考察的博物学家。由于经济窘困,华莱士要靠采集为生,他不得不终日采集,无暇顾及个体标本的细节。达尔文由于生活富足,形成了雇佣他人采集标本的习惯。华莱士偶尔也会找人帮他,比如在马来群岛雇一两个人。达尔文自己观察得多,至于采集工作他可以交给别人去做。而华莱士采集标本强度要远远大于达尔文,这反映在两个方面:首先,华莱士的采集工作是全天候作业,没有时间限制,而贝格尔号上的生活只能让达尔文做短途沿岸旅行。其次,华莱士有严格的时间表,作息极其规律。达尔文贝格尔号上的生活则轻松随意得多。
华莱士用网捕甲虫和蝴蝶。较少捕鸟、哺乳爬行动物。如果对比华莱士和达尔文所采集的昆虫标本会发现,华莱士的标本大而艳丽,达尔文的标本则要平凡得多。华莱士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他的采集范围——标本要卖出好价钱。他会向斯蒂文森抱怨买家只关注艳丽漂亮的标本,而他的收集工作是十分认真详尽的。当然,经济压力也并不完全决定了华莱士的收集工作,他的理论兴趣中关于物种识别、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以及不同地域的物种组成之间的关系也是他采集生涯的重要导向。
达尔文对显微镜下细节的偏爱和单纯的采集动机使他没兴趣收集一系列相关的标本的副本。在给亨斯洛的信中,他曾经提到对两个标本的细节描述胜于六个标本的采集工作。细致入微的描述非华莱士所能及,他对标本的采集不仅仅是当时博物学的标准,他的理论兴趣与经济奖励使他更多地收集特别物种的整个系列的标本(例如天堂鸟系列和艳丽的鳞翅目)。华莱士对种与变种间的变化程度与实质区别的兴趣,也促使他收集多种多样的标本。华莱士每天要花五到六小时采集标本,还要花大量时间分门别类。与华莱士对鸟与昆虫的兴趣比,达尔文则更喜欢海洋无脊椎动物,他更注重观察描述标本的细节,达尔文对每个物种至多会采集两个标本。而华莱士大量疯狂采集,以区分出物种与物种间的差别,做出分类学上的定位。发甘认为两人这些博物学实践中习惯与方法上的差异,正是华莱士与达尔文对标本采集中个体与种群间关注不同的原因。从这样的对比中,我们再次看到了经济、社会和科学之间的相互交融。
博物学实践中习惯与方法上的不同,也导致两人在标本物质成果的数量和种类方面的差别。达尔文与同时代的博物学家相比算是收获颇多的,他一共向伦敦寄回了五千多件标本。达尔文的标本的特点是单一,而且更具随意性。而在华莱士一方,无论是标本的数量还是种类都多得惊人。在马来群岛的八年间,他收集了超过125000例标本。华莱士标本的特点是种类繁多,且在分类学上都有明显的定位,每一个种和属的标本都有众多的副本作为分类学上的参照。华莱士的博物学采集数量称得上疯狂,从中也可以管窥早期博物学家对于生态系统的掠夺式的破坏。
在写作方面,发甘同样关注到两人使用词语频率的不同。首先,在华莱士马来群岛考察期间的博物学相关文章中,只有一篇没有提及种以上的单位,当然他也偶尔零星会提及生物的个体。而达尔文在贝格尔号的博物学日志中则是,三分之一关注生物个体,四分之三提及个体,三分之二提及种或更广的单位。其次,华莱士一以贯之地描述他在物种上的工作,达尔文则不时报道新奇动物个体。虽然很难区分达尔文的个体与群体的差别,但至少可以肯定达尔文与种的层面无关。再次,华莱士写作中充满了“种的计量”,例如“13种鸟”、“194种昆虫”、“一个昆虫科中收集了1364个种”,另外像“新物种”、“漂亮的种”、“普通的种”这些词频繁出现。而达尔文的写作中则不突出种层面,或者说不关注种的划分。另外,他们在与种和个体相遇的时候,做出了不同表现。例如,华莱士收养小猩猩,将其称为“类婴儿”“婴儿种”,在它死后将它做为标本称为“年轻猩猩标本”。达尔文则不同,他没有特别注明他遇到的种,也不像华莱士那样对种的特征进行详尽的描述。最后,二人对待各自的强调实体态度也不一样。华莱士会抱怨一个种只有一个标本的情况,他需要一系列的标本来确定一个种,他总是强调种的特征属性。
华莱士12年的海外博物学考察期间,大部分时间与鸟及昆虫在一起,他对生物个体已经见怪不怪了。相应地,他对个体与群体以及每个层面的概念的划分是十分清晰的。而达尔文对个体与种间的区分则模糊得多,他经常在分类学意义上快速转换。由此可见,华莱士这样一个终日收集个体并把它们按群体或更大的单元分类的人是不可能混淆个体和群体概念的。达尔文因兴趣与时间分配等因素的不同,他每个物种标本只取一个或两个的方法使他混淆了群体与个体的描述。以少数个体代表群体或物种的做法使达尔文对不同层次范围间的划分变得模糊。[Fagan 2007,pp.605-625]
四、华莱士与达尔文经历与实践对比的启示
以华莱士和达尔文的出身经历以及博物学实践为基础的对比研究路径有着更广泛的意义,生物学史学家称其为综合路径,这种进路超越了以往所谓的“内史”与“外史”的进路。这种研究方法可以更好地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中得到他们不同的实践成果,这种比较进路也为研究其他博物学家提供了范例。即使在华莱士和达尔文后续的成就研究之中,例如华莱士的人类学理论、唯灵论、社会主义言论,达尔文的种族主义、资产阶级言论的研究中也能得到很好的应用。这种路径同时也为两人对待分类学理论方法、帝国主义政治和殖民主义的态度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和科学因素的起点。[Fagan 2007,p.626]
华莱士从一开始就是带着物种变化的假设投身到博物学实践之中,他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受赖尔和马尔萨斯影响,对生物地理学进行了深入研究。终于在1855年得出沙劳越律——《新物种所产生的相关规律》(On the Law Which Has Regulated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Species)。直到1858年发表了他的自然选择学说。虽然这一事件被后人重复了无数次但华莱士的理论还是被遮挡在了达尔文的阴影之中[Shemer 2002,p.3]。然而近年来,华莱士独立的自然选择理论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其自然选择理论中强调种群利益的特征已经成为了学界的共识,学者们在华莱士对性选择理论以及神创论的态度等方面都找到了有关印记。
这其中的例子之一是在性选择理论中,达尔文企图用拟人化的动物审美标准引入除自然选择之外的性选择进化机制,但是达尔文却没能对性选择“审美”偏好的起源给出合理解释。华莱士强烈反对达尔文提出的这一自然选择之外的进化机制。首先,性选择理论强调了同种生物个体间竞争,而华莱士认为自然选择是进化的唯一机制,同时他的自然选择理论关注的是生物种与属的层面。其次,华莱士还从自然选择理论反对神创论的角度提出,鸟类(及昆虫)有审美品位的观点是一种神人同形同性论,就像“作家说蜜蜂是伟大的数学家,蜂巢的建筑完全是为了满足蜜蜂的数学感觉”[Fichman 2004.pp.267-268]一样没有依据,他认为这很可能给神创论者反驳自然选择的理由——一切美感来自于神性,从而葬送掉自然选择理论对神创论的胜利成果。
另一反对神创论的例子还是来自于华莱士与达尔文在生殖隔离问题中的分歧,达尔文认为生殖隔离问题只是自然选择的附带产品,因为隔离机制的产生不利于生物个体的繁衍。但是神创论者们会认为物种也许是可以变化的,然而种与种之间的界限是不可逾越的,已经在上帝创造物种时划定了,生殖隔离问题正是神创论的有力证据。而华莱士则相信隔离机制受到了自然选择的作用,他的论点同样是不能给神创论者以任何理由插入“上帝之手”抢夺自然选择的领地[克罗宁2001,页538]。
对于华莱士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单位到底是什么,长期以来就有华莱士对变种生存的关注和达尔文对生物个体侧重的哲学和历史研究。关于华莱士的有曾经的代表性的评估是,他是个群选择者,被选择机制误导,或者二者皆有。发甘的研究显示,这其中的难点正如约翰森和克罗宁等人认为的那样,华莱士显然意识到了个体层面的自然选择。只有回到华莱士生物学本身才能找到答案。她认为华莱士对变种层面的关注,以及环境的关注使得他可以将群体与个体相结合起来,能够自圆其说,所以对华莱士的群选择论指责,还不能做出定论。[Fagan2007,p.629]
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约翰森和克罗宁等人也不建议简单地把华莱士列为群选择者。约翰森在讨论生殖隔离后的强化(学术界又其为称“华莱士效应”)时引用莱博维茨(Leibowitz)在汉密尔顿(Hamilton)的血缘淘汰等式的范围内形成了的理论处理为华莱士辩护。在这一等式中,如果关联性(R)乘以受体利益(B)的结果大于利他个体的成本(C),那么就会出现“利他现象”[Johnson2008,p.121]。而且,华莱士的研究泰斗查尔斯·斯密斯也不建议简单地给华莱士贴上群选择者的标签,他建议从更系统的视角来理解华莱士的做法:“看一下当代有关人类选择原理和盖亚假说①的大量著作,而这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为华莱士思想的遗迹。”[Smith 2004,p.3]这些学者对华莱士著作的深入发掘和重新解读,正如发甘对华莱士和达尔文的博物学实践的对比研究所揭示的那样,更加强调了华莱士进化之路的独立性,无需依存于达尔文的阴影之中。
注释:
①盖亚假说(Gaia hypothesis)是由英国大气学家拉伍洛克(James E.Lovelock)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的。后来经过他和美国生物学家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共同推进。盖亚假说的核心思想是认为地球是一个生命有机体。盖亚假说至少包含5个层次的含义:一是认为地球上的各种生物有效地调节着大气的温度和化学构成;二是地球上的各种生物体影响生物环境,而环境又反过来影响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过程,两者共同进化;三是各种生物与自然界之间主要由负反馈环连接,从而保持地球生态的稳定状态;四是认为大气能保持在稳定状态不仅取决于生物圈,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为了生物圈;五是认为各种生物调节其物质环境,以便创造各类生物优化的生存条件。
标签:达尔文论文; 华莱士论文; 自然选择论文; 博物学论文; 植物标本论文; 工作选择论文; 地质学论文; 进化论论文; 科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