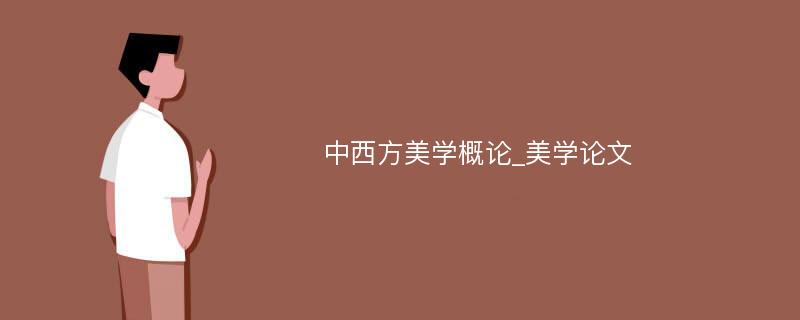
中西美学的会通要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要略论文,美学论文,中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地看,20世纪的中国美学始终处于风风雨雨的文化转型时期。这一时期尽管受到社会动乱、偏激思潮和专制型意识形态的多次阻滞与干扰,但总体上还是维系着由传统向现代、由锢闭向开放、由稳态向动态、由守望向创新的逐步演进态势。相应地,历尽百年沧桑的中国美学流变,也彰显出类似的特征。而且,从其发轫之初,就是在新旧之学的鼓荡互动和中西美学的碰撞磨合中,着力探寻着融会贯通与创新超越的可能途径。
一 文化碰撞中生成的美学形态
文化作为人类生活方式与生活环境的总和,包含着诸多社会决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全方位地影响着人的存在、思维、 行为、交往、自我表达、情感流露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等等。在每个文化之内, 这些因素起码具有双重效能。 它们一方面表现为霍尔(StuartHall)所谓的“趋同场”(site of the convergence), 另一方面则构成特殊的“防护网”(saftety net)。 前者促使每个民族根据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选择原则,于不断深入强化自身体验和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将各种导向社会谋生与环境适应的差异行为转化为相对一致的模式。后者则在团体包容及其相互间的边界规定、文化传播与社会文化心理等领域,兼顾着防御保护和隔绝疏离的作用。在这种“场”和“网”中成长起来的人们,会对自己的文化特质产生必然性的偏爱,会把它们当作悠久而亲近的住宅家园一样加以精心呵护。因为一旦失去这些东西,人们就会觉得整个世界变得毫无生气、苦不堪言。不过,若把这种偏爱推向极端,那就无法客观地认识自己文化的真实面目,更遑论批判或补正其内含的不足与缺憾了。结果,这“场”和“网”会演变为抱残守缺的屏障,趋于消极的守恒状态,最终会像各类有机体一样,难以超越自身的生命跨度,会随着自身活力的衰退而坠入施本格勒所言的文化周期性,即从朝气蓬勃的青年期,经由强健有力的壮年期,最终沦落到到渐趋崩溃的老朽期。
不过,文化的这一衰变沉浮过程,未必就像施本格勒所说的那样绝对,那样周期性地万劫不复。相反,其可能新生或复兴的契机,往往存在于它自身同异质文化的碰撞中。高能物理实验表明,两个粒子在加速器的作用下对撞,会产生数倍于原有能量的增值效应。跨文化研究发现,两种异质文化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时空背景下发生碰撞,也会激起火花四溅的景象与互动性的磨合,进而导向文化的变革、发展乃至创新。这其中的缘由,首先在于打乱或冲破了原来的文化“趋同场”和“防护网”。这样,会激活人们的文化批判意识(critical consciousness)和文化比较的敏感性(comparative sensibility), 会促使人们走出已往习惯性适应的旧巢,借助异质文化的光点或文化碰撞的火花,在反思和比照中重新审视自己文化的利弊与可塑性(makeability), 并且根据自身的需要,在寻求尽可能迅速摆脱困境之方式的同时,有选择地从其他文化系统中汲取营养或可资利用的成分,进而与自己文化中的相关部分加以重新熔铸,组成自己的文化特质。其次,重在沟通、建设而非干预、征服的文化碰撞,会通过开放而平等的对话交流,拆掉文化各个部分之间的壁垒,超越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楚河汉界”,使隔绝转化为互通、分离转化为融合、冲突转化为共存,“一分为二”的边界转化为“合二而一”的边缘。这一边缘具有强大的放射性和贯通力,“是文化种种对立二元之间或多元之间相互对话和交流、不断生发出新气象的地带,也是一个开放的和多元共存的地带。这个‘文化的边缘’就像文化的‘核子’,不同要素在这儿接触和融合,滋生出新的东西,并迅速向周边扩散,有效地改变着人们的意识和文化本身。”(注:滕守尧:《文化的边缘》,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
从学科的一般规定性上讲,“无中生有”的中国近现代美学,正是中西文化碰撞与创造性磨合的产物,或者说是诞生于中西文化之“边缘”地带的“新婴”。宏观上,其理论基础主要源于德国的古典主义美学和中国的儒道释思想,其理论形态也表现出相互别异但又彼此联系的特点。根据目前的研究结果,有的学者主要从文艺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将其宏观地归结为功利主义和超功利主义美学形态。(注:聂振斌:《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20页。 )也有的学者更多地是从艺术哲学的角度出发,将其划分为古典和谐型与新兴崇高型美学形态。(注:陈伟:《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70页。)当然,我们也可以从相对微观的风格、旨趣和理论导向出发,将其细分为以王国维为代表的意境诗学,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美育学,以朱光潜为代表的静穆美学,以宗白华为代表的体验美学,以蔡仪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哲学美学等等。它们中间有的侧重于探讨艺术创造的合规律性(如意境说、古雅说和典型论),有的侧重于论述启蒙教育的合目的性(如美育说和趣味说),有的侧重于思索人格的修养和人生的艺术化(如距离说和审美境界说),有的则侧重于揭示艺术欣赏与审美体验的本质特征(如审美层次说和积淀说)。但从跨文化研究的角度去审视,这些宏观与微观的美学形态,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中西融合的共性。
二 中西美学互动的三种模式
1、片断性的因借发挥
20世纪以降,中国内忧外患,许多有良知、有抱负、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康有为语),均以各自可能的方式探寻着救亡图存的文化革新之道。此时的“西学东渐”或文化转型,已从原来所偏重的文化器物层面(如船坚炮利)进而转向文化制度层面(如教育制度)和文化观念层面(如科学、哲学、美学、文学艺术)。虽然“旧学”(中)与“新学”(西)之争仍在继续,但“青山遮不住”,前者势运日衰,后者精进如斯,蔚然已成显学。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学无中西”(王国维语)和“别求新声于夷邦”(鲁迅语)之类的呼声日见高涨,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想理念通过译介像潮水般涌入华土。在当时的中国美学和文艺界,这一趋势也构成了一道热闹的风景线。不少从事美学译介或文艺研究的学者,出于文化革新或社会改良的愿望,怀抱“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方策,一方面批判守旧,一方面积极引进,在紧锣密鼓中“你方唱罢我登场”。
这便是中国美学在学科意义上的初创阶段。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开山之师们不大可能、也无暇顾及系统地了解和研究西方美学源远流长的全貌,而是根据社会文化需求、个人的兴致所好与理想追求,在西方美学理论思想史的横断面上,截取了一些影响较大的学说,如康德的“审美无利害说”、“优美与崇高说”、席勒的“审美游戏说”和美育论,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说”和“静观论”,尼采的“超人天才说”和“悲剧论”等等,继而联系中国文艺传统中的相关因素,借题发挥,大加张扬。这其中不乏片面的理解,机械的照搬,有意的夸大,概念的套释,牵强附会的取证,文本的误读和挪用,语境的错位和变形,而且在学术规范上也显得松散、随意、甚至杂乱无序。从学理上看,所有此类弊病显然是缺乏系统研究或片断性因借的必然结果。但从文化碰撞与文化选择的角度看,上述现象在一个急于救亡图存的社会环境里又显得那么自然而然、必不可免。
2、系统化的学科架构
“五四”新文化运动将中国美学研究推向新的台阶。特别是开创性的美育实践,不仅利用美学辅助文艺一同担负起民众启蒙教育乃至改造国民性的重任,而且在相关学者中间激发起建构美学学科体系的热情和努力,从而使系统化美学研究模式应运而生。该模式的主导宗旨在于参照和借用西方的科学研究方法,筛选和吸纳中国治学传统中的有效成分,由浅入深、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地梳理和厘清美学的历史沿革、文化背景、研究对象、基本范畴、理论形态、哲学基础等方方面面,进而确立其学科架构,完善其理论体系。这样不仅有利于消除和补正片断性美学研究的种种偏颇(如“就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论述方式),而且有利于深化艺术批评和文艺学研究,同时也促动了中国美学思想与部门艺术美学的系统研究,堪称中国近现代美学发展的逻辑必然。
国内建构现代美学体系的努力,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以吕澂、陈望道、范寿康、李安宅、朱光潜、蔡仪、傅统等人为代表的美学家,相继撰写出诸多部题为美学、美学概论、美学纲要、文艺心理学以及西方美学史之类的专著。他们抑或从知识的真、善、美三分法来界定美学学科的特征,抑或从学术、精神、价值和规范角度来分析美学的性质,抑或从主要的美感理论形态来组合美学的发展体系,抑或从艺术创造的合规律性出发来批判旧美学、建立新美学。虽然有的观点失之简略,有的地方稍嫌浅泛,有的结构难免雷同,有的学说显露出照搬或挪用的痕迹,有的论述也多少残存着机械或强辩的色彩,但总体上是在不断追求完善的过程中,系统地勾画出这门学科的基本特色及其方法原理。与此同时,系统化模式也有效地促进了中国艺术美学的体系化研究,从而为日后建立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体系莫定了基础。这方面的突出成果甚丰,譬如朱光潜的诗论,丰子恺的画论,邓以蛰的书法欣赏, 李泽厚、 刘纲纪、叶朗、敏泽等人的中国美学史……。从论述方法和体系结构上看,其中尽管不乏理论的因借,概念的嫁接,语义的转换,但基本上还是立足于中国的文化背景与思维传统,从纵横两方面展现出中华美学思想的发展经纬和独特风貌。
3、中西会通式的理论整合
从中西文化碰撞与磨合的夹缝中发展起来的美学,始终伴随着不同形式的中西美学比较过程。这种比较,需要跨文化研究的学术视野,平等的对话意识,学贯中西的学养和会通学理方法的能力。惟此,才有可能通过相关的理论整合而有所创建、有所超越。
所幸的是,中国近现代美学界的确涌现出这样一些特殊人才。其中众所公认的有朱光潜、丰子恺和宗白华等著名美学家。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一方面到海外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习得西方文化与美学的科学精神,也谙悉西方学理的要求及其规范,另一方面又都从小接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和传统的教育,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东方特有的妙悟智慧,同时也自觉地担负着创造中华新文化的历史使命和热衷于人生艺术化的理想追求。
就其成果而言,朱光潜早期所著的《文艺心理学》和《谈美》等书,总体上是以西方近现代重要美学理论为主干,利用语义转换、观念比较和取证于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以及诗歌范例的方式,从而有效地化解了外来学说的生疏与隔膜,譬如借助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情景交融”和“超然物外”说,分别诠释立普斯的“移情作用”和布劳的“心理距离”论。后来所著的《诗论》一书,则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会通中西学理和整合中西诗学理论基础上,通过科学的分析和对比中西诗歌的节奏、声韵、音波、情趣、意象、句法、韵法等要素,揭示了中西诗歌艺术的不同特征,其恰当的体例、严整的逻辑、缜密的求证和平实的结论,为创设中国现代诗学和中西比较诗学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迄今恐怕还无人超越这一成就。难怪著译作等身的朱先生声称自己一生仅写了这么一部书。相比之下,丰、宗二位先生更多地是从书画艺术的角度对中外美学进行比较研究。他们对中西绘画的审美理想、价值特征、创作规律和构成要素的相应功能等方面,都作了开创性的研究比较和理论归结,并对其发展方向提出了有意义的前瞻性展望,其学识和风范均为后学树立了榜样。
三 跨文化美学研究的学理要求
一个学科的发展水平,主要体现和落实在“述”与“作”的成果形式上。如果前者(“述”)侧重于转述和承传前人学说的话,那么后者(“作”)则要求超越前说和实现理论创新,即发前人之所未见与未言。从中西审美文化碰撞与磨合中发展起来的中国近现代美学,历经百年的跨文化互动与会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总体上处于“述”多于“作”的层面。因此,出于创新和超越的目的,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定位跨文化美学研究的这一有效途径。当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将涉及更高的学理要求。
1、跨文化美学的超越性
“跨文化”是一个外来术语。这个笼统的汉译名同时表示3 个不同的英文概念,即:cross—cultural 、 inter —cultural 和trans —cultural。这实际上包含着3种形态的跨文化研究方向。具体说来,这3个复合词是由同一词根“cultural”加上3个不同前缀“cross—”、“inter—”和“trans—”构成的。在这里,“cross —”主要包含着”横过”、“穿越”或“交叉”等意思,“cross—cultural ”一般表示“交叉文化或交叉文化地域”、“涉及多种文化或文化地域”;
“inter—”一般包含“在……中间”,“在……之间”,或“在……内”等意思,“inter—cultural”一般表示“不同文化间的”;“trans—”主要包含“横穿”、“通过”、“贯通”、“超越”、“胜过”、“转化”等意思,因此,“trans—cultural”通常表示“跨文化”、 “交叉文化”、“涉及多种文化”、“适合于多种文化”和“超越文化”。
跨文化研究的基本特性在于比较,也就是在两种以上的文化之间进行比较。这种比较的目的和范围是多样化的:抑或帮助解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社会交际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以期取得相互理解或真正沟通的效果;抑或总体性或局部性地探讨不同文化中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等领域的各自特征和可比较性;抑或研究不同文化中某个共同感兴趣的专题论述或相近时代两位历史人物的某一思想侧面等等。但在终极意义上,跨文化研究更多地是追求创造性的转化和可能的超越,也就是在文化(特别是理论)互动与整合的基础上进行会通与创新。譬如,在器物层面,梁思成开创的中(大屋顶)西(多层楼体)合璧式的现代建筑就是典型的例证。在观念层面,王国维的“境界说”,显然是以跨文化的研究方式会通康德的“精神说”、席勒的“审美王国论”、佛教的“境界”概念与中国传统的“意象”、“情景”和“自然”等艺术思想的结果。
所谓“跨文化美学”(trans—aesthetics), 本身就包含着“超越”(trans—)的内在目的性。它本身预示着一种科学方法, 一种在跨文化形态中进行系统和深入比较研究的方法,不仅涉及西方与东方,也涉及现代与传统。它旨在从可靠而翔实的历史和文化语境出发,对相关的理论和概念形态进行客观的比较或别异,进而探讨会通与整合的可能途径,最终追求独创性的超越或超越性的创新。这一过程容不得“短、平、快”的急功近利做法或华而不实的浮躁心理,而是需要学贯中西的学养和脚踏实地的、积厚而发的学风。与此同时,也需要重视下述几个方面的学理要求。
2、平等的对话原则
对话(dialogue)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历久弥新的交流方式。充满宽容、动态、开放和自由等特征的对话,是激活思想和实现真正沟通或相互了解的前提。孔子的论语与柏拉图的哲学,均是在对话的形式中展开的。另外,对话也是构成经纬式话语网络的重要机制。这种网络通常交织在天人之际、人人之间,以及读者与作者、读者与作品、作者与作者、作者与作品之间,具有明显的互动作用和由此引发的创新契机。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历史与现代,古人与今人,都会不同程度地被纳入对话的网络之中。这就是说,我们除了“究天人之际”,还需“通古今之变”,要与历史对话以知兴替或吸取教训,要与现实对话以知来者或善于应对。再者,在精神层面上,对话是一种“全新的意识和生活方式的‘隐喻’”,它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模式,拆除了表象与真实、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有限与无限、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等等二分式对立范畴之间的“界墙”,通过彼此之间的对话形成丰富的精神生活与“文化的边缘”,从而有助于建立真正的人伦关系和实现与他者的心灵沟通,同时也有助于滋养出相对纯洁的精神境界与审美趣味,进而转化为对高雅型审美文化的追求。这种追求在激发灵感和导向创新的同时,也“必将促成当代人精神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也会使当代艺术更加丰富多彩。对话精神如果得以实现,我们的文化就会一步步走向世界古哲们梦想的真、善、美一体的境界,成为人人向往的审美文化”(注:滕守尧:《文化的边缘》,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在跨文化研究中,对话精神特别需要一种真诚而开放的平等意识(sense of equal footing)。在这里,平等的意识主要是指参与对话的各方,在对话过程中都享有平等的地位,都否认片面的权威或对真理的独占,反对固执己见或差强人意的作法,同时摒弃文化偏袒或非此即彼的倾向,更不用说唯我独尊的话语霸权行为或随波逐流的从众心理了。在交谈中,对相关论题各抒己见,即便出现争论,也是善意的和建设性的,其争锋所至,只针对问题的所在,而不掺杂其他无关的负面因素。倘若得出结论,取得共识,那是万幸,皆大欢喜;倘若没有,那么对话双方可以自由地带着自己与他人的想法离开,经过进一步的反思以后,来日再会谈、再交流、再追问。在平等意识引导下,个人的见解和智慧与他人的见解和智慧互动,更多的问题与难题相遇,必然会使对话过程更富有活力、动态性和创新的可能。然而,在实际对话中,我们往往会陷入由自信与不自信所构成的连续统一体(continuum)内。 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上的自信无疑是一个积极因素。但自信过度者,经常会有意或无意地以权威自居,自以为真理在握,把对问题的解释权划归己有,其结果只能促使他人出局,消解对话的活力。相反地,缺乏自信者,则会在自己认为的权威面前出让话语权利,膜拜于对方的逻各斯(logos)脚下,结果沦为点头称是的人(yes—man)。这种现象在许多情况下是人为的产物。
当然, 平等的对话原则还要求对话者具有“自我反思”(self —reflection)的能力与“自觉批评”(conscientious criticism )的意识。前者不仅要求对他人的解读方式与释义结果进行反思,而且要求对自己的解读方式和释义结果进行反思。同样,后者要求对自己理解上的偏见进行批评和消解,而且要求对研究对象可能存在的缺失加以揭示和评判。诚如倡导中西比较哲学研究的学者拉巨(P.T.Raju)所建议的那样:“在历史长河中,东西方直接或间接的相互接触和影响与日俱增,作为历史个体的人,现在没有一个纯然是东方的或西方的。当今时代需要我们对人类和宇宙的综合概念取得相互的理解与发展,因为整个世界越来越自觉地由部分走向彼此联结,不同的文化及其哲学也在相互撞击。……这就需要进行不偏不倚的或超越成见的研究比较,尤其是在有关人的问题上,要竭力保持一种绝无偏见的、不以自我为中心的和开放的心灵,……要积极开展自我反思与自我批评。笛卡尔要求哲学家在思考之前须先铲除所有偏见。培根建议要打破所有‘偶像’。——否则,我们评判他人的准则必将是主观的和暂时的,而非客观的或普遍有效的。”(注:P.R.Raju.Lectures on
Comparative Philosophy.( Poona:University of Poona Ganeshkhind,1970),pp.48—50.)
3、多维度的诠释意识
在遵循平等对话原则的同时,多维度或多层面的诠释意识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其中首先涉及“无限的交流意志”(will
to boundlesscommunication)。这种交流,旨在取得相互的理解和真知灼见, 旨在发掘世界与人生的深层含义,旨在重构人格和完善人性。按雅斯贝尔斯的话说,它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心灵的交感”,必须是开放、热烈、坦诚和深刻的。它要求我们不仅要与周围显豁易见的、习以为常的或者人人都接受的事物相交流,而且要与棘手的、有争议的、对其一知半解的以及为我们的意识和能力所限制的事物相交流。这既是人类之间的交流,又是对符号或密码加以接受和领会的交流,是为达到最高境界而必须付出的永无休止的努力。事实证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乃至人与解释学所说的各种“文本”,在思想、情感、知识等方面的交流是无止境的。一次邂逅、一次知遇、一次凝照、一次解读(特别是跨文化的文本解读),只能获得初步印象,了解某个侧面,看到序列中的部分环节,解释篇章中的部分含义。但是,这却不断刺激和强化人的交流欲望。人类的本性也果真奇妙,对未知的彼岸世界总是充满无限的追慕之情。于是,从古至今,先贤时哲演示了一幕幕“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人生实践系列剧。
其次,还包括“批评的循环”(the critical circle)观念。 实践证明,我们对某一文本的理解与释义,之所以持有现在的看法,是因为有证据在,而且可以证明。然而,每当发现新的和相反的证据时,我们乐于改变原先的看法。可是,在这一刻到来之前,我们尚无理由不相信我们所相信的东西。不断地发现旧释义的不妥当性,不断地建立起新的释义,这便是他所谓的“批评的循环”的要旨所在。我们从事跨文化研究,本质上也是一种开放性而平等的对话过程。在此过程中,有必要以“批评的循环”方式来解读文本。因为,这种循环诚如海德格尔所言,是构成一切理解的基础。用我们的话说,它是提高对话质量的动力。
另外,诠释意识也关系到“视界的融合”这一重要的辅助因素。按照伽达默尔的有关说法,对文本的历史理解既不是主观的但又不是不可能的,因为文本不只是过去的一篇东西而已,它只要被人阅读,就会继续产生含义。然而,文本是受语境制约的,是以一种兴趣视界、即读者内心引入文本的语境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种释义语境严格说来属于解释者所认为的语境,是受他置身其中的传统限定的,而本文一般又是这一传统的组成部分。这样,对于过去的理解自然要受到对当前情境的理解的影响,对于文本的释义也自然受到自己的历史情境和某种利害关系的制约。这样一来,释义者受语境束缚的视界,因其开放性和灵活性而得以扩大,从而将当前的视界与过去的视界包容在一起,由此产生出一个新的视界。就是说,“这种融合包含了一种当前视界的扩展,因为据说历史研究常常就是去消除某种偏见并诱发宽容。另外,这种融合还包含对过去视界的一种凝聚,从而使仅属暗示的东西成为那一视界的明确因素。”(注:霍埃:《批评的循环》,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页。)其结果,我们面对过去的文本,会“思接千载”, 会联系现实,也会跨越一种文化语境而进入到另一种文化的语境,从而开辟出有利于创新的跨文化边缘地带。
4、点面相济的比较方法
真正科学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是全面而系统的。反之,仅局限于类似概念(点)的比较而忽视其相关文化背景和理论体系流变(面)的研究。常见的所谓比较,概括起来大概有自以为是的“相互攀比”式、“对号入座”式、即兴强制式、旁证点缀式等数种随意而简单的做法。从事比较研究的英国学者劳埃德(G.E.R.Lloyd)将其称为“零碎法”(piecemeal approach),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鸡零狗碎的比较研究方法。他根据自己多年研究中国和希腊文明的经验,恳切地告诫说:“把中国与希腊哲学中的单个学说或概念逐一进行排列,直接进行比较和对比,就好像它们都在讲述同样的问题似的,这种做法虽然不会引致什么灾难,但显然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们不能先从希腊哲学方面入手,譬如说,先从中挑选出一些特别著名的理论学说或概念,然后再着手从中国思想中寻找其对应的东西,因为这种作法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好像这类对应的学说与概念在先前早有结论似的。”(注:G.E.R.Lloyd.Adversaries and Authorit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3.)无疑, 这是一种带有简单攀比色彩的“张冠李戴”式做法,是难以得出科学性的结论的。其实,触及一个学说或概念,必然会牵动潜隐其背后的一大片文化,特别是观念层面的文化因素。因此,仅限于狭义的文本语境(点)而不计广义的历史文化背景(面),单就个别学说或概念进行比较的做法,难免会失之偏颇,有画地为牢之嫌。这就需要点面结合,要把单个学说或概念的比较研究,放在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具体的文本语境的“大平台”上操作。此外,在系统而深入研究比较的过程中,不忽视“形同”,更重视“质异”,不为表面或语义转换所形成的相似性所迷惑,而要“入乎其内”地寻根探源,“出乎其外”地反思比较。要知道,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异”或“差异性”(differences)的实际意义, 经常大于“同”或“相似性”(similarities)的实际意义。这是因为“异”的内涵张力,不仅为比较提供了场所,而且为思维拓宽了空间,也为对话、交流和创新构成了有利的契机。由此得出的结果,通常不是从诸多异同中提炼出一个圆融万相的类似“月印万川”式的真理性说法,而是多种可能的、具有不同启发意义的真理性说法。另则,还必须明确比较研究的基本宗旨。即:它不在于推导或抽绎出某个独一无二、贯通一切的真理,也不在于建构出某种绝对正确的知识,而在于为人们探寻真理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基础或思维空间,以便充分利用现有的人类精神资源来更好地理解万事万物。
5、独立的学术意识
没有独立的学术意识,上述学理要求就可能落空。质而言之,这种意识以追求真理为终极目的,要求排除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以客观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从事学术研究。相应地,“畏圣人之言”与“存而不论”等陈腐思想,理应为不断追问和分析批判所取代。因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对真理的探求,始终伴随着从遮蔽走向澄明的过程。
值得强调的是,独立的学术意识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是合学术规律性而非合实用目的性的,是兼容所用科学学说而非囿于任何教条阈限的,是提倡自由平等的讨论而反对权威迷信或武断独裁的。这些原本并非问题的常识,有时在特定的政治生态中反倒成了问题。对此,聂振斌先生在总结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发展的经验教训时,将这一问题提到了学理的高度进行了历史而客观地分析。他在强调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学说及其科学方法论的同时,深刻地揭露了时而困扰正常学术研究的某些怪现象。譬如,“有人对马克思主义真理不感兴趣,唯一令他感兴趣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因此一个严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在他那里变成几条极其抽象的教条,或者把个别词句变成随处可贴的标签,用以打人、吓人、捆绑别人的手脚。在学术领域谁想尝试新方法,另辟途径,立刻就会被扣上不坚持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马克思主义在他们那里已经不是可亲近、可信赖、可发展的真理,而变成一种僵死的、令人可怕的东西。这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与具体科学研究已经不是指导被指导的关系,而变成了束缚与反束缚的矛盾。”(注:聂振斌:《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8页。)这一批评委实入木三分,并从反面提醒人们培养独立的学术意识的必要性。
另外,独立的学术意识也需要严格的学术规范作保障。古人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真正的学者应当诚心正意地格物致知,而不是靠巧滑的心机或剽窃的手段博取虚名。尤其是在跨文化美学的著述中,要言之有据,谁说的就是谁说的,不可借用语言或语义转换这一过程,有意不注明资料出处而掠人之美、贪天之功。在国内外学术界,这些小聪明难逃法眼,为学者所不齿。
总之,新世纪呼唤独立的学术意识,实事求是的学理精神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同时期望中国的美学工作者率先垂范,在真正创新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步伐。
标签:美学论文; 跨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语境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