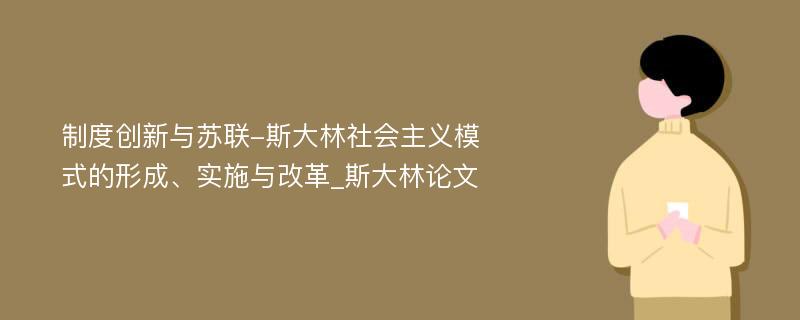
制度创新与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实行和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苏联论文,制度创新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看,上个世纪20~30年代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乃是针 对新经济政策的一次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它有力地促进了30~40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形成后,社会主义还应不停地进行制度创新,如此才能促 进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但是,苏联的整个历史发展表明,在后斯大林时代,苏联社会 长期处在继续发起制度创新与拒斥制度创新的矛盾对抗中,其结果是一再错失社会主义 制度创新的良机。最终,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在变革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时 ,苏联改革不但没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反而使几十年来的社会主义成果丧失殆 尽,导致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近来,笔者在学习党的十六大文件过程中,从制度创 新的角度重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历程,重点是学习和体会最近13年来中国社会主 义改革开放的经验。然后又从这个角度出发,深入总结苏联演变的历史经验教训,产生 了一些新的认识,形成本文,希望引起学界同仁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一 制度创新与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释义
社会制度是对一定经济基础及建立于其上的上层建筑的统称。在阶级社会,一定的社 会制度就是统治阶级为了确立和维护其统治地位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其中的 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人类社会总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 运动中向前发展,随着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革命,社会制度必然随之发生 变迁。生产关系是衡量一定社会制度的属性的核心要素,根据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人 类社会可以划分为五种社会制度,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必然要不断地发生制度变 迁。其中,促进社会进步,代表着生产力发展方向的制度变迁就是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不同社会制度间的更替。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 的替代,是人类历史上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重大制度创新。另一种是同一制度内的不同 的制度实践形式的变革。本文研究的是后一种形式的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创新包含两方 面的含义:其一是构造新的制度实践形式;其二是新旧两种制度实践形式的更替。于是 ,根据新制度实践形式的形成途径和新旧两种制度实践形式更替形式的差别,制度创新 可以分为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和民间自发型制度创新。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是由中央 政府主动发起的针对原有社会制度实践形式的社会变革;民间自发型制度创新,是由民 间力量联合发起的,针对中央政府执行的现有制度实践形式的社会变革。它有时被称为 需求诱发型制度创新。形象地讲,前者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后者是“自下而上的革 命”。
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社会主义制度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它克服了资本 主义制度的内在弊端,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社会制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制 度就可以停止制度创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社会主义制度仍然要不断 地进行体制变革,进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这样,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在全球最终完全 替代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进入其更高的阶段——共产主义制度。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恩格斯说过,“我认 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 它看成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这 可以看作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经典阐述。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时, 邓小平也提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 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 ”(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其实,所谓社会主义改革,就是政府主导型 的社会主义制度创新。
从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角度看,20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史恰恰是一部丰富的制度创新 史。苏俄(苏联)新经济政策替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替 代新经济政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形式替代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等,都可以看作 是成功的社会主义制度创新。
二 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对新经济政策的替代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
新经济政策如今已是一个特定的历史名词。它指的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停止 执行后,在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建立前,苏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形式。 新经济政策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废除了战时共产主义的一些做法,形成了多种经济并存和 一系列带有商品经济特点的经济体制,因此使苏联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在实 行新经济政策过程中,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变革并没能与经济体制的变革同步。
因此,新经济政策其实是一种不完全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形式,它存在重要的缺 陷。在经济上,新经济政策内部存在着商品经济与计划管理的冲突。比如,在粮食收购 领域,政府通过收购的办法从农民手中收购粮食,却又对粮食进行严格限价。农民有出 售粮食与否的自由,但若要售粮则必须按照政府定价出售。这样,农民为了规避政府的 定价,随时都可能拒售粮食。这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埋下了致命的病根。在政治上,带 有商品经济特点的新经济政策,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民主政治的呵护。频繁的政治斗争和 文化斗争,使国家根本不可能朝着建构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不同派别在政治上和文化 上的殊死搏斗,其结果只能是新的中央集权的出现。实行商品经济所需要的法治精神、 民主机制、平等交易和诚实信用原则在这里都不存在。集权体制随时可以践踏市场规律 ,运用行政手段葬送新经济政策的经济体制。严格讲,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仅仅停留于经 济体制的层面,与其相配套的社会上层建筑根本没有形成。这决定了新经济政策的社会 制度实践形式的脆弱性。尽管它毫无疑问地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和对在俄国 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贡献,但由于列宁去世过早,很多与新经济政策有关的问题,他还 来不及考虑。正是由于这一点,新经济政策才难以拒斥针对它的新的制度创新。
于是,在1928~1929年,新经济政策的实行连续引发了两次粮食危机后,当联共(布) 中央决定执行“非常措施”使用暴力从农村强行征粮时,坚持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力量并 没能阻止之。这种力量的主要代表人——布哈林,甚至还投票表示赞成(注:在1927年 召开联共(布)十五大时,大会否决了采用暴力剥夺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但是,在紧接 着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同意实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 第107条:对从事粮食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的分子予以严惩,本人交法庭判罪,粮食由 国家没收。就是说,包括布哈林在内的联共(布)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同意执行“非常措施 ”强行征粮。参阅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第463~465页。)。
在“非常措施”的执行引起了农村阶级对抗的激化后,布哈林等人开始维护新经济政 策,但他们的努力是孱弱无力的。“非常措施”的执行,引发了社会骚乱,却缓解了粮 食危机。随着局势的恶化,联共(布)中央逐渐被推向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或者彻底放 弃强行征粮,向富农妥协,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或者加速农村的集体化,打破富农对 商品粮的垄断,这意味着抛弃新经济政策。选择前者,有可能使党威信扫地,最终甚至 会导致无产阶级政权的丧失,因为连续两年的强行征粮已引起了强烈的阶级仇恨。在这 种处境下,布哈林选择了后者,其主张不过是向富农妥协,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这可 能会危及无产阶级政权。斯大林选择了前者,这种选择是对新经济政策的否定,但它能 巩固已经动摇的无产阶级政权。当斯大林获得这场斗争的全面胜利后,联共(布)“抛弃 ”新经济政策是毫不奇怪的。
可以说,执行“非常措施”,乃是联共(布)及其中央政府迈出对新经济政策进行制度 创新的第一步,尽管当时他们可能是不自觉的。在反省执行“非常措施”的后果时,斯 大林提出了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方针。本来,在粮食危机爆发时,新经济政策应该还拥有 通过自我调节克服社会危机的能力。但“非常措施”的执行,彻底断送了新经济政策进 行自我调节的机会。在斯大林击败布哈林后,新经济政策与党的新工作路线相对立,它 只能成为变革的对象。由此,苏联社会正式踏上了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之路,苏联—斯 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应运而生。
剖析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替代新经济政策的过程,比较二者的体制特征,可以 扼要地认清这场社会变革的特点和性质。
第一,这次社会变革是由中央政府主动发起的。首先,斯大林本人有一套抛弃新经济 政策的理论主张(注:在理论上,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作了否定,逐步形成了一套与新 经济政策对立的经济理论。关于农业经济,斯大林认为,小农经济是“最没有保障、最 原始、最不发达”的经济,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决不能无止境地即过于长期地建立 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立在规模最大的联合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 的小商品农民经济的基础上。”(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36、218页。)他主张 ,苏联农业的惟一出路是“利用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采用集约耕作的科学方法的大农庄 。别的出路是没有的。”(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61页。)关于计划经济体制 的建构和实行问题,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 觉组织所代替”的论点,斯大林推论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最统一最集中的经济,社会 主义经济是按计划进行的。”“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想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 指令性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都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内 将来发展的方向。”(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22页;第10卷,第280页。))。鉴 于斯大林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这些主张遂成为党和中央政府的工作路线,最终 转化为中央政府的政府行为。于是,苏联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行动,在全国发起农业集 体化。通过颁布法令,重组经济管理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指令性计 划制定、实行和监督体制。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高度集中的管理,彻底实现了全国 工农业生产和流通分配体制的变革。曾经繁荣一时的国家资本主义工商业消失殆尽,整 个苏联工业成为清一色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工业。农业则从“小生产者的海洋”,迅速转 变为以集体农庄为主的社会主义农业。
第二,新经济政策的社会制度实践形式与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具有很多重大差 别。新经济政策实行的是相对分散的商品经济,中央政府对社会生活进行了一定的宏观 调控,但社会生活仍然有较大的自由空间。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行,则由联 共(布)及其领导的中央政府对社会进行高度集中的管理。在经济上,苏联建立了单一的 生产资料公有制,运用行政手段在工农业生产和流通领域全面贯彻指令性计划。在政治 上,苏联实行了高度集权的一党领导制,执政党内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联盟中央对各 加盟共和国进行强有力的领导。在联共(布)内部,中央政治局及其日常办事机构书记处 成了实际权力核心,斯大林本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文化上,苏联通过政治批判构 造起了高度集中的意识形态,社会指导思想高度一元化。在新经济政策与苏联—斯大林 社会主义模式的对比中,前者属于不成熟的、相对分散的社会制度实践形式,后者则是 较为成熟的、高度集权的社会制度实践形式。
第三,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诞生和实行,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创造了不 可低估的成就,同时也向全世界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凭借苏联—斯大林 社会主义模式的作用,在资本主义遭遇世界大危机的时候,苏联指令性计划经济在全球 一枝独秀。国家的经济实力快速增长,用十多年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一二百年的现 代化历程,很快成为欧洲第一、全球第二的工业强国。在法西斯德国横行欧洲的时候, 凭借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备战优势和战时动员优势,苏联终于化劣势为优势, 最终打败了德国,拯救了人类文明。这些成就都是烙在人类历史上的客观存在,根本就 不需要列举数字去印证。简单说,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对新经济政策的替代,客 观上创造了伟大的经济成就,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这次社会变革,不但创建了新的制度 实践形式,而且以其伟大成就吻合了“制度创新”的字面含义——不是退步,而是创新 !
总的讲,新经济政策和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形式。它 们都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般性,都承认以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实行无 产阶级专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等。但是它们在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形式上却存 在着重大差别。列宁在评价新经济政策时曾说,“新经济政策并没有改变工人国家的实 质,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58 2页。)依据这一思路,我们也可以说,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对新经济政策的替代 ,并没有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但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
从制度变迁的类型看,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对新经济政策的替代,是一次成功 的中央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它对于制度变迁研究,具有永恒的魅力。
三 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是发起制度创新与拒斥制度创新的历 史进程
一定社会制度的实践形式一旦形成,它就具有拒斥制度创新的能力,必然会设法通过 各种努力争取延续。而且,这种社会制度实践形式越是成熟,其拒斥制度创新的力量也 越强大。这种现象在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身上得到了充分展现。后斯大林时代 的苏联史,恰恰就是变革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与固守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 的矛盾对抗,是继续发起制度创新与拒斥制度创新的历史进程。
战后初期,苏联社会只有继续实行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选择。在这个时候, 对斯大林模式进行变革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主要是出于三方面原因。其一,苏联社会急 需医治战争创伤。既然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被事实证明为高效的发展模式,在急 需战后重建时,人们根本没有理由弃之不用。其二,战争结束不久,“冷战”拉开了序 幕,苏联再度面临“谁战胜谁”的问题。于是,刚刚经过大战洗礼的苏联人民,为了尽 快恢复国民经济,在战后新的条件下站稳脚跟,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遏制与挑战,需要 继续实行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其三,斯大林仍然在世,鉴于斯大林的无上权威 ,变革斯大林模式就很难设想。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苏联失去最高领袖。3月6日,马林科夫被任命为苏联部 长会议主席,苏联从此进入马林科夫执政的新时期。马林科夫上台后,曾试图对苏联— 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稍加变革。1953年3月9日,在斯大林追悼会上,他提出要对斯大林 模式进行局部变革的动议,随后又领导了“医生间谍案”的平反,宣称苏联今后要“用 尽一切办法来加速轻工业的发展”。但事实上,马林科夫执政后随即失去了党的领导权 ,他根本无力去实施自己的主张。在与赫鲁晓夫的较量中,他甚至受到了后者的戏弄, 时而被指责为因循守旧,时而被指责为离经叛道。这段历史只是表明:最高权威的突然 消失,引发了政治高层的权力斗争,社会变革的话题无从谈起。
1955年2月,马林科夫被解除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苏联进入赫鲁晓夫时期。在 这个时期,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模式进行了喧嚣一时的改革,但这场改革是不成熟的。赫 鲁晓夫在理论上的浅薄和政策上的主观随意性,造成了党政工作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和社 会生活等方面的混乱。在批判斯大林时,赫鲁晓夫只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品质进行攻击, 并没有对斯大林模式的制度缺陷作出深刻批评(注: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 上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开始攻击斯大林。1961年10月,在 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再次公开地攻击斯大林,刻意把大会的注意力引向清算斯大 林的“罪行”。但仔细推敲可见,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行为,其实主要是为了打击对 手和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作为党的第一书记他对苏联—斯大林模式的高度集权政治体 制却是偏爱的。)。在经济体制的改革上,赫鲁晓夫领导改组了机器拖拉机站,取消义 务交售制,把中央管理的企业下放到地方,把以中央管理为主改变为以地方管理为主等 。这些做法对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确形成了一定冲击,但苏联指令性计划经济 体制的基本特征仍然存在,而且在改革过程中反反复复,改了以后又改过来。在政治体 制的改革上,赫鲁晓夫领导苏联在州和边疆区设立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改造苏联党和 国家的干部制度,削弱内务部的职权。这些行动只是对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作了 肤浅的调整,并没有触动斯大林模式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内涵——实行权力高度集中 于中央的一党制,反而削弱了党的领导。所以,赫鲁晓夫的改革只是主观上企图对斯大 林模式进行局部改造,而实际上斯大林模式并没有发生改变。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综合国力达到了顶峰,但很快盛极而衰。此时,苏联社会发 展不平衡的弊病已完全暴露,全面变革斯大林模式已经是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但在勃 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里,苏联针对斯大林模式的改革浅尝辄止,还逐渐恢复了一些被赫 鲁晓夫废除掉的做法。在经济领域,勃列日涅夫领导了所谓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三 次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没有触及斯大 林模式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而且还很快就销声匿迹。在政治领域,党的权力高度集中 在政治局和书记处,勃列日涅夫本人逐渐集党政大权于一身,斯大林时期的做法得到了 沿袭。时任政治局委员的契尔年科曾经说过:“党的一些部门和主管部门的领导人往往 因急于解决问题而撇开苏维埃,对完全属于苏维埃管辖的问题作出决定,而某些苏维埃 领导人也习惯于把直接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问题送交党的领导。”(注:江流、陈之 骅主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页。)可见,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决策机制与斯大林时期的决策机制如出一辙,苏联仍然实行着苏 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
在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执政的两个短暂时期内,苏联虽有变革斯大林模式的设想, 但真正变革的行为并没有出现。制度创新的话题与这两个时期根本无缘。安德罗波夫上 台后—反勃列日涅夫时期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习气,迈出了励精图治的步伐,为苏联 社会注入了难得的朝气,让人们看到希望。但安德罗波夫不久就去世,改革还来不及进 行,全社会仍然继续实行着斯大林模式。契尔年科执政时期,老迈的领导层昏庸保守, 根本就没有社会变革的冲动。
从对历史的回顾中,可以抽象出几点认识。
首先,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历史,充满着继续发起制度创新与拒斥制度创新的矛盾。 无论是赫鲁晓夫时期,或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领导人在不同程度上和出于不同的政 治考虑,都曾经有过发起制度创新的要求和变革斯大林模式的设想和行为,但他们在经 济上未能也不愿意打破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在政治上则迷恋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 式赋予的无上权威。于是,苏联社会只能在“改革”旗号下容忍着继续发起制度创新与 拒斥制度创新的矛盾冲突。
其次,修修补补的局部变革不能完成制度创新的使命。赫鲁晓夫粗浅紊乱的改革,勃 列日涅夫对改革的浅尝辄止,都没有促成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形式。真正意义上的制 度创新,无论是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还是民间自发型的制度创新,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 涅夫时期都没能出现。其中,勃列日涅夫后期的行为,甚至是用政权的力量去拒斥制度 创新。
最后,苏共一再错失对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变革的时机。面对社会变革的 客观要求,苏共及其领导的中央政府,不但不能自觉地主动发起制度创新,反而还以政 权的力量去拒斥制度创新。于是,各种变革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冲动不断地被 强行压抑,最终可能会凝集成反抗现政权的力量,使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 积重难返。
四 8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不但未能促成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反而导致 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他认识到苏联仍然实行着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事实,这 为发起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奠定了基础。他曾回顾说,“苏共二十大后结束了斯大林模式 一个最负面的特点——大规模的迫害。但同时却保留这一模式‘旧有的灵魂’原封未动 ——党的垄断权力,而实际上是少数政治局委员们的权力。”(注:[俄]戈尔巴乔夫: 《“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56页 。)那时,如果苏联能合理地变革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仍有机会实现自身的制度创新 。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的社会环境仍然有利于实行社会主义改革。此时,尽管苏 联社会出现沉重的积弊,到了不得不变革斯大林模式的时候,但是凭借历史上苏联社会 创造的雄厚物质基础,苏共仍然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机器,拥有堪与美国竞争的综合国力 ,特别是军事和科技实力。在经济上,苏联的许多主要指标都已经与美国接近。据统计 :1980年苏联的国民收入是美国的67%,工业产值是美国的80%强,农业产值是美国的85 %。在科学技术方面,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载人宇宙飞船遨游太空,空间技术和核力 量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有些方面甚至还处于领先地位。在民心向背方面,苏共中央在 广大党员和群众中仍然拥有号召力,大多数苏联人期望社会主义能够继续进行制度创新 。这为戈尔巴乔夫领导苏联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事实上,在1986年,苏联 曾经再度获得了较快发展,是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增长了4.1%,工业产值增长了4.9%。在 这种情况下,如果苏联领导者能够在巩固政权的基础上有条不紊地推进改革,社会主义 在苏联仍然是大有前途的。
但是,戈尔巴乔夫等人逐渐迷失了改革的方向,混淆了社会主义的共性和苏联—斯大 林社会主义模式的个性,在变革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同时,抛弃了社会主义基 本原则。在改革遇到阻力时,也就是在遇到拒斥制度创新力量的对抗时,戈尔巴乔夫错 误地向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开刀。他倡导并推动了所谓的公开性和民主化。很快,苏联的 舆论导向发生转变,社会改革的主题从变革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转变为颠覆社 会主义制度和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权。而且,这种社会潮流很快在党中央内部找到代言人 和领头人物。形形色色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力量蜂拥而起,戈尔巴乔夫则在其中随波逐 流。不可否认,此时戈尔巴乔夫已经不再关注共产党的前途和命运,只是醉心于占据总 统宝座去巩固自己的权势。于是,苏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很快失去了管理国家的权力 ,总统委员会成了苏联新的权力核心(注:1990年3月14日,第三次苏联人民非常代表大 会决定删去苏联宪法中保障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第6条,决定将党和国家分开,使国家不 再从属于任何政党,并宣布实行总统制。)。共产党的领导已经不复存在,马克思主义 的指导思想地位已经丧失。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名存实亡。对于坚 定的共产党人而言,首要的任务已经从推进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转变为挽救行将崩溃 的社会主义制度。
1991年“8·19”事件可以看作共产党人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后努力。但是,广大共 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在这场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冷漠,深刻地说明:苏联共产党在失去了对 苏维埃和中央政府的领导权后,已经完全无力平息社会危机,无力拯救社会主义制度。 这也说明:苏联的改革不仅断送了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机会,而且彻底断送了社会主义 制度。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结束。苏共在领导 发起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的过程中,轻易地让出政权,中央政府随之丧失了这场社会变 革的领导权。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继续创新,沦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
斯大林时期成功地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经验以及后斯大林时期未能继续进行新一 轮的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直到最终因错误的改革路线而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崩溃的教 训,分别从正反两方面说明:执政的共产党一定要自觉地发起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而 且还要牢牢地掌握着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的领导权,否则社会主义改革随时都可能改变 性质。
标签:斯大林论文; 制度创新论文; 赫鲁晓夫改革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新经济政策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斯大林全集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