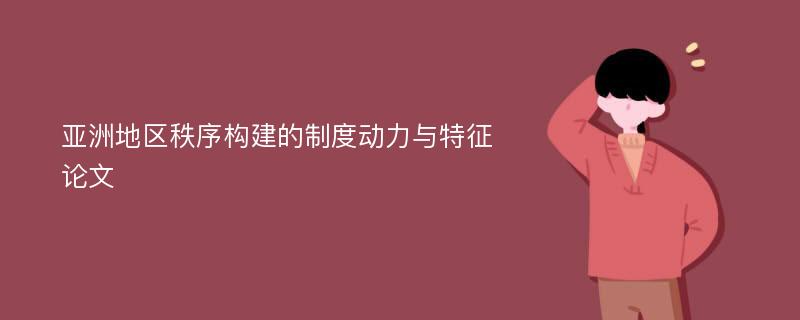
亚洲地区秩序构建的制度动力与特征*
马荣久
【内容提要】 以地区性国际组织、多边机制等为代表的地区制度框架的成长,反映演进中亚洲地区体系的一个显著变化。地区制度框架下的互动推动国家之间构建起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关系性逻辑和理念,并对于地区力量相对变化做出包容性回应。与此同时,各方对于主权和平等、软制度和弱约束、自主性与开放性的强烈诉求,成为亚洲地区秩序构建的重要动力和显著特征。亚洲地区秩序以及国家间关系的未来图景,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地区是否持续构建起有效运作的组织和机制。在国家日益崛起的进程中,中国在地区制度框架下的外交政策和行为应以明确的秩序理念为前提,以明确的国家角色为核心,从而为塑造地区和全球秩序贡献力量。
【关键词】 亚洲地区秩序;地区制度框架;国际组织;周边外交
引 言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其“世界秩序”论述中指出,秩序反映了一个地区或一种文明对它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正安排和实力分布的本质所持的理念。而地区秩序关乎在某一具体的地理区域应用秩序理念。具体来看,地区秩序建立在两个因素之上:一套广为接受的互动规则,明确规定了允许采取行动的界限;一种权力的均势,保障各方的自我克制并免于屈从。① Henry Kissinger,World Order:Reflections on the Character of Nations and the Course of History,New York:Penguin Press,2014,p.9. 可以认为,指导行为体互动的共享的理念和规则、相对稳定的权力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行为体互动关系中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Predictability and Stability),② Randall L.Schweller,“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Order Revisited:A Review Essa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6,No.1,2001,p.171. 是构成地区秩序必不可少的要素。
秩序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际问题研究的终极目标。国际组织学者试图理解国际政治秩序如何以及何时被创立、维持、变革和抛弃。③ James G.March and Johan P.Olsen,“The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4,1998,p.943. 正如相关研究指出的,各种形式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指向“模式化行动”(Patterned Practices)、提供一套具有内聚力的“观念和信念”(Ideas and Beliefs),④ Kalevi J.Holsti,Taming the Sovereigns:Institutional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21. 塑造“相对稳定的预期和共享的规范”,⑤ Thomas Biersteker and Cynthia Weber,eds.,State Sovereignty as Social Construc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59. 从而有助于秩序的建立和维系。对于国际制度,研究认为,国际社会存在不同层次的制度安排;诸如主权、外交和国际法等基本制度(Fundamental Institutions)构建了国际社会和秩序的基础,而国际组织的重要性在于为基本制度的变化提供了手段和驱动力。⑥ Tonny Brems Knudsen and Cornelia Navari,ed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Anarchical Society: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World Order,Switzerland:Palgrave Macmillan,2019,pp.23-50. 进一步来看,国际社会的基本制度与主要以国际组织所代表的次要制度(Secondary Institutions)是相互构成性(Mutually Constitutive)的关系,这就意味着不考虑基本制度的逻辑与运行就无法适当地理解国际组织和机制,反之亦然;相应地,国际组织处于国际秩序的中心位置。① Tonny Brems Knudsen and Cornelia Navari,ed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Anarchical Society: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World Order,Switzerland:Palgrave Macmillan,2019,p.15.
研究结果显示,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并不相关,或者仅弱相关。事实上,目前我国企业高管薪酬出现了两种极端的现象:一方面是高管薪酬奇高,超过合理的价位;另一方面,企业绩效提升了,高管的激励却严重不足。激励不足和激励过当并存,十分容易混淆是非,最终造成“眉毛胡子一把抓”。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化和地区化的日益深入发展,亚洲地区体系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地区多边制度框架的扩展。在地区经济一体化领域,“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建立和发展,汇聚了有关各方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的共同预期,反映并推进了相互依存与合作共赢的地区新态势;近年来“区域经济全面伙伴关系”(RCEP)的构建以及在此框架下的谈判进程,代表了地区贸易自由化安排的新举措。在地区发展领域,“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应时而生,成为有关各方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进行多边合作的制度化安排。在地区安全领域,“东盟地区论坛”(ARF)以其运行过程中独具特色的“东盟方式”,“一轨”“二轨”的相辅相成开启了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六方会谈”(SPT)“上海合作组织”(SCO)等在应对地区热点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中发挥作用。
难以否认,在制度框架的构建与扩展进程中,域外大国的战略调整、地区领导权问题、地区内国家双边关系的发展态势等时常会带来压力和挑战。但一系列地区性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已经在亚洲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等诸多领域成长起来,并推动构建一个日益“制度化”的跨国互动关系网络。有关的国际组织和机制为亚洲地区国家之间开展互动关系提供了目标和议程、规则和理念,并在其运行过程中显示出明显的地区特色,成为亚洲演进中的地区体系和转型中的地区秩序的推动力量。
在亚洲地区多边制度框架建立和延展的进程中,国家之间日益广泛和深入的制度联系、共享的偏好和规范等,显示出有关各方能够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自主地安排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包括“强主权”“软制度”以及“弱约束”在内的相关安排适应了地区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反映了地区自主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新的地区权力中心的出现和回归,地区内国家、尤其是地区大国日益增强的提供制度框架等地区公共产品的能力,正在显著提升地区秩序构建进程中的自主性。
因循“国际制度是建构和维持国际秩序的决定性变量”② 门洪华:《地区秩序建构的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7期,第6页。 的逻辑,本文认为,以地区性国际组织、地区和次地区多边机制为代表的制度框架的演进,承载着亚洲地区秩序的创立、谈判和维系。由此,若要洞察和理解亚洲地区正在出现的秩序图景及其发展取向,一个重要的分析路径在于思考有关地区多边制度框架创立与运行中的特征问题,并说明它们如何用于解释地区秩序构建的动力。
一、地区制度框架下的合作理念
地区秩序的形成和维持,首先要求国家之间形成一个追求基本目标的共同利益观念。亚洲地区制度框架的构建,既是该地区有关各方共同利益观念的汇聚,也是共同利益观念的传播、扩散以及作用的发挥,从而有助于塑造地区新秩序。
冷战时期,由于不同阵营的对峙和意识形态的分野,亚洲地区基本上是以地缘战略、军事防卫为主导的、支离破碎的体系;冷战的终结以及随之而来的地区内有关各方政治关系的缓和,推动行为体互动中原先以“制衡和防范”为重心的议程转变,使得地区范围内寻求经贸乃至安全领域的合作与共赢成为可能。在此背景下,以“亚太经合组织”“东盟+x”“上海合作组织”等为代表的地区性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的产生和延展,反映并推进了作为地区秩序基础的新理念。
重要的是,亚洲地区性国际组织和一系列制度性安排在其参与者之间构建起新的关系性逻辑和动力,其核心是多边基础上的合作而非意识形态的分野或者“冷战式”的防范与对抗。所谓“合作”,从静态的角度来讲,它可以“被定义为一组关系,这组关系不是建立在压制或强迫之上的,而是以成员的共同意志为合法基础的”。①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543页。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合作意味着有关各方谈判的过程,即通过政策协调过程,行为者将它们的行为调整到适应其他行为者现行的或可预料的偏好上。②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1页。
其次,地区制度框架的形成、变迁与大国战略和竞争存在密切关系。正如已有研究指出的,大国竞争为区域合作制度安排提供动力,大国竞争策略塑造区域合作制度安排的形式和变迁路径。③ 刘均胜、沈铭辉:《亚太区域合作制度的演进:大国竞争的视角》,《太平洋学报》2012年第9期,第61—62页。 一方面,有关各方在制度框架下的互动,经常伴随着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的竞争;另一方面,地区制度框架的延展,也在建构权力竞争的方式,这尤其体现为竞争性多边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在冷战后的亚洲地区,竞争性多边主义已在地区安全和地区经济等领域显示其存在和价值。比如,以美国为中心的军事同盟和“轴辐”关系一度主导了地区安全模式,但亚洲国家在“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ICA)等地区制度框架下积极倡导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为核心内容的亚洲安全观。类似地,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不遗余力地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以谋求继续主导贸易规则的制定;作为回应,亚洲国家积极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谈判。可以认为,以机制转换和制度创建为核心的竞争性多边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了冷战之后亚洲地区权力转移的图景,它同时适应了地区权力结构的变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地区国家的利益,因此将继续在地区秩序的演进中发挥重要作用。
图5示,与CON组相比,OPC组、IGF-1组和OPC+IGF-1组LC3-Ⅱ相对表达量分别为10.32±0.31、1.02±0.20和5.73±0.11,F值分别为5 083.113、524.294和583.542,均P<0.001,OPC与IGF-1主效应均有统计学意义,两者联合有拮抗效应;p62相对表达量分别为0.64±0.02、1.03±0.02和0.87±0.01,F值分别为1017.038、257.225和162.558,均P<0.001,OPC与IGF-1主效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两者联合有拮抗效应。说明OPC通过抑制 PI3K/AKT 信号通路诱导TU686细胞发生自噬。
当代亚洲地区制度框架的构建,能够反映各行为体对自身国家利益和地区共享利益的诉求,对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以及应对外部挑战的需要。正如我们看到的,东南亚各国通过“东盟”制度框架下的互动,不但通过内部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整合以获得集体力量,而且在定义地区互动规则和规范、塑造目标和结构等领域发挥出自身的影响。在地区秩序的构建中,它们并不是被动地搭中美两国的便车,而是努力通过东盟外长会议、外长扩大会议与“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机制构成的网络,来规范大国互动的进程和方向,谋求建立符合自己利益和特性的地区新秩序。① Evelyn Goh,“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2,No.3,2007,pp.113-157.
进一步来看,亚洲地区性国际组织和机制在建立之后进一步促进了各成员方之间的合作。由于对相对获益的关切,某个国家参与还是放弃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将部分取决于它对其他国家意图的判断。而在判断其他国家意图的预期形成过程中,制度框架具有重要作用。制度安排不但能够在不同程度上约束成员国的行为,而且也“使得国家行为更可预期、对彼此行为的预期更为有效”。① William T.Tow and Brendan Taylor,eds.,Bilateralism,Multilateralism and Asia-Pacific Security:Contending Cooperation,London:Routledge Press,2013,p.158. 当一国通过制度框架下的互动能够确定其他国家的意图、并认为相关的收益有助于自己的生存、安全与经济发展时,该国会积极参与到制度框架下的合作中。在实际层面,作为东亚地区的大国,中国和日本共同参与“区域经济全面伙伴关系”“中日韩三边合作机制”等地区制度框架下的互动,有助于双方累积互信,培育积极的相互认知,推动彼此之间的政策协调。类似地,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后,“上海合作组织”为包括中印关系、印巴关系等八个成员国间关系的发展合作开辟通道。尽管有关各方的双边关系中不乏问题和挑战,但地区制度框架下的互动、合作具有内生性特征。
又过了一个月,粒粒已经攒够了一笔钱,手上还有程颐送过来的10000积分里程,加一点钱,应该可以换购到一张去西藏的机票。可是,出发之前,她忽然想念那块大青石。
某种程度上正是得益于“软制度”和“弱约束”,在地区多边制度框架下的互动中“进程导向”的作用方式(Process-oriented Approaches)更好地保障了国家间关系的平稳发展,推进了相互依存和彼此融合,并能更为有效地塑造地区秩序。所谓“进程导向”,乃是指有关各方首先就原则性问题达成一致,然后让事态不断演化和渐进。显然,“进程”是相对于“结构”而言的,如果说后者意味着“制度是一定权力结构下战略设计的产物”,那前者强调的是“基于现有地区规范和实践、不断向前推进的协商性过程”;而建立和维持“进程”相比实现经济共同体或安全共同体等长期目标更为重要。③ Amitav Acharya,“Ideas,Identity,and Institution-building:from the‘ASEAN Way’to the‘Asia-Pacific way’?”The Pacific Review,Vol.10,No.3,1997,p.324. 以南海地区行为规范和地区秩序的生成为例,可以认为,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弱约束”特征并不意味着地区机制构建的“软肋”,而是为有关各方真正致力于解决问题开拓了空间。进一步来看,鉴于南海地区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尤其是一时难以有效解决的主权争议,“进程导向”的作用方式有利于“南海行为准则”的成熟落地。
二、地区制度框架下的权力转移
冷战后亚洲地区各种力量的消长以及力量对比的变化、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地区权力中心的回归,显示出亚洲地区体系下“权力转移”的前景。在此进程中,以地区性国际组织、多边和“少边”(Mini-lateral)机制为代表的制度框架的演进,为不对称权力结构中的不同国家实现外交政策诉求提供了路径和选择,为约束权力、同时也为权力的合法化提供了平台,显示出其有能力对于国家间实力的不对称以及力量对比变化作出包容性回应。
首先,地区制度框架是地区体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显示着地区权力分配的状况。基于此,地区国际组织和机制能够成为地区内国家实施外交战略、发挥自身作用和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依托,而且在此背景下的互动能够缓解有关国家在不对称权力结构中的不安全感,减少权力转移进程中的不确定性及其消极后果。
在东南亚,由于殖民经历且身处复杂的地缘环境,地区内国家通常对外界信任度较低,怀疑外部大国的意图。冷战后,东南亚国家积极构建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制度安排,从而在地区稳定与权力平衡的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方面,东南亚国家在“东盟地区论坛”“东盟+3”和“东亚峰会”等多边制度框架下始终处于“驾驶员”的席位,在互动规范和规则、议程设置等领域发挥了引领作用,“小马拉大车”,由此在不对称的地区权力结构中赢得有利地位。另一方面,多边制度框架发挥“绑定”(Binding)和“驯服”(Taming)的作用,即将中美等大国纳入协商和对话之网,约束它们在共同规则的框架内负责任地运用其权力,与此同时,它们为大国间围绕地区秩序问题的持续对话和谈判提供平台和场所。① Evelyn Goh,“Institutions and the Great Power Bargain in East Asia:ASEAN's Limited‘Brokerage’Rol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11,No.3,2011,pp.373—401.
冷战后的中亚,苏联解体使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安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变化曾导致中亚地区被认为会出现“权力真空”,即新一轮“大国博弈”(Great Game)② Alexander Cooley,Great Games,Local Rules:the New Great Power Contest in Central Asi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3. 的开始。然而,在中俄等国推动下建立起来的“上海合作组织”为该地区权力的平稳转移提供了支撑,为地区协调与合作搭建起了平台。借助“上海合作组织”,中亚中小国家不但更好地维护了自身的独立,避免了外部大国的直接干预,而且在制度框架下的互动中,中亚国家的偏好和优先目标能够成为塑造地区合作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如何在中亚地区互动,给中俄大国关系带来考验。而由于“上海合作组织”的构建,中俄在中亚携手合作的双边关系有了制度保障。
执教老师提问层层深入,逻辑性强,有效地引导学生理解文本主旨和结构。在此基础上,教师对该文的标题进行提问。展示型问题为参阅型问题作铺垫,学生在参阅型和评估型问题上能够分析问题和表达观点。教师先是对文本中人物收礼的基本信息进行提问,再进行一般送礼物的讨论,最后延伸到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礼物赠送问题。例如:
显然,对于亚洲地区的权力转移进程而言,多边制度框架的建立和延展已经在发挥显著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制度可以凸显或限制国家权力”。① 约翰·伊肯伯里:《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1页。 在制度框架下的互动中,各成员方的权力和影响力得以实现再次分配,尤其是大国的权力和影响力将受到规范和规则的约束;同样重要的是,多边制度框架推动权力的行使具有合法性的特征,并且建构权力竞争的方式,这与传统的主要依靠权力制衡来维持的地区秩序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当代亚洲地区各种力量消长以及力量对比变化,尤其是地区大国崛起的背景下,多边制度框架因其承载的“合法化”功能,将权力转化为“权威”(Authority),② Martin Wight,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Three Traditions,Leicester: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1,p.99. 所以将继续成为塑造权力转移和地区秩序的关键推手。
三、地区制度框架下的弱约束
亚洲地区相关国家之间日益广泛和深入的制度框架下的互动,显示出行为体对于主权和平等、“软制度”和“弱约束”的强烈诉求,由此构成了亚洲地区秩序演进中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和特征。
本质上,主权也是国家经过协商而达成的一种关系,国家希望以此获得他国对自己独立与主权地位的承认。冷战结束后,尽管亚洲地区国家间积极寻求合作与共赢,但主权原则依然构成了各种形式的互动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可以说,亚洲地区体系远不是超国家机构主导的国际体系,构成地区体系的基本单位仍然是积极恪守主权原则的国家行为体,而地区国际组织所获得的“授予性权威”(Delegated authority)① 研究认为,国际组织的“权威”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即授予性权威、理性—合法权威、道义性权威和专家权威;参阅迈克尔·巴尼特、玛莎·芬尼莫尔:《为世界定规则:全球政治中的国际组织》,薄燕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35页。 目前看来则相对有限。在上述背景下,亚洲地区制度框架的演进与国家行为体及其主权诉求存在密切的联系,并经由国家行为体实际的或预期的需求和偏好所塑造。有如相关研究指出的,该地区制度框架尚处于这样的发展阶段,即“最好还是把它理解为国家权力和目标的延续和交汇,而不是客观力量的产物”。② Michael J Green and Bates Gill,eds.,Asia's New Multilateralism:Cooperation,Competition,and the Search for Commun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p.3. 与此同时,主权国家利益以及建立在主权原则基础上国家间的平等地位在制度框架下的互动进程中通常得到了特别的尊重。就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国虽发挥重要作用,但难以主导或者自如地领导亚洲地区机构;而诸如东南亚地区的中小国家,现在扮演着“拉大车”的角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亚洲现在是历史上唯一这样的地区:强国生活在弱国的世界中,而且弱国领导强国。”③ Amitav Acharya,ASEAN can Survive Great-power Rivalry in Asia,4 October 2015,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5/10/04/asean-can-survive-great-power-rivalry-in-asia/,访 问 日期:2018年11月20日。
除了“强主权”的深刻影响,亚洲地区由于各国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差异性大、发展阶段不同、经济水平不一,所以制度框架下的互动不是建立在欧盟式的或者北约式的、具有强约束力的规则和实施机制之上,而是具有亚洲地区特性的“软制度”“弱约束”和“舒适度”。“软制度”和“弱约束”通常意味着制度框架下最小规模的官僚结构设置,(在决策过程中)对共识的偏好而不是强调多数表决,在合作的最初阶段尽量规避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绑定性的义务等。④ Muthaah Alagappa,ed.,Asian Security Order: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226. 制度框架下的互动注意兼顾各方“舒适度”,即“协商,而不是强加于人”;“作出某一项决定,有的国家原则上没有困难,但觉得不舒服。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其他人可以等一等,等大家都感觉舒服时再去做。”⑤ 吴建民:《东亚特性正在形成》,2005年11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11/15/content_3781172.htm,访问日期:2018年6月5日。 在具体国际组织和机制的实际运行层面,上述特征得到较为充分地体现。作为冷战后亚太地区范围内第一个致力于应对安全问题的机制,“东盟地区论坛”坚持按照“东盟方式”(ASEAN Way)运行,不急于推进“冲突解决”(Conflict Resolution)等高阶目标,而是遵循协商一致、最小制度化与循序渐进原则。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不同,“东盟地区论坛”的信任措施没有监督机制的介入和约束,各方自愿遵守,措施没有法律约束力。① 魏玲:《小行为体与国际制度——亚信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与亚洲安全》,《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5期,第91页。 与之类似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平稳运行倚重的是“共识”,而不是“否决权”,即不论国家大小或承担会费的多少,“所有成员国一律平等,在相互理解及尊重每一个成员国意见的基础上寻求共识;在利益一致的领域逐步采取联合行动。”②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http://chn.sectsco.org/documents/,访问日期:2018年2月10日。
可以认为,亚洲地区性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不仅提供了推动有关国家参与合作的动力,而且当国家成为国际组织或国际机制的成员后,它们之间可能会更好地发展合作关系。正是得益于一系列地区性组织和多边机制催生的积极效应,合作共赢的理念和行动成为演进中的亚洲地区秩序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特征。
四、地区制度框架下的自主性
事实上,对于蔬菜类这一整体的营养评价很难用非好既坏的“二元论”方式评价,生蔬菜和熟蔬菜的营养价值应从不同角度来衡量,不同的蔬菜也应区别对待。
在柏林墙倒塌之时,亚太地区第一个经济合作官方论坛开启。此后,“亚太经合组织”致力于促进地区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并推动了在开放贸易和经济技术领域的合作关系。“东南亚国家联盟”建立之后,在一度被称谓“东方巴尔干”的东南亚地区逐步构建了以其为中心的对话与合作安排,摆脱了过去主导各方互动关系中的猜忌与纷争。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东盟+”制度框架的延展,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国家构建友好与合作关系、拓展综合利益以及应对共同关切就有了平台和依托。“上海五国”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建立后,成员国在平等参与和协商的基础上,不仅以合作的方式解决了历史遗留的争议边界问题,而且这一框架继续支撑各方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宗教激进主义以及维护边境地区稳定等领域进行政策协调。这样一来,在存在不同文明背景、多个新生国家的中亚地区,国际组织帮助汇聚了共识,培育并传播了合作理念。
地区秩序构建进程中自主性的回归,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重塑包括美国在内的域外大国的态度与政策。冷战时期,美国凭借其军事同盟关系和“轴辐”模式在亚洲地区的制度框架领域占据支配地位;冷战后,美国对于亚洲地区多边制度框架的成长不乏怀疑和观望,其态度是忽冷忽热,其行为是瞻前顾后。对于“东盟+3”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地区一体化努力,美国政府虽然没有阻止或干预,但对相关事态的发展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尽管并不满意东盟国家在“东盟地区论坛”中的领导地位以及“东盟方式”的低效或无效,美国还是参加了该机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2005年“东亚峰会”(EAS)开创以来,美国并不寻求正式加入,直到2009年美国成为“东亚峰会”成员国;作为前提条件,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正如相关研究指出的,“美国政府的决定至少反映其对地区事态的承认,即华盛顿历来只关注它在亚太地区的排他性战略伙伴关系而忽视地区多边组织,这与地区现实不相匹配,因而在其处理方式上需要更多地顾及地区性的主导规范”。② Rosemary Foot,Saadia Pekkanen and John Ravenhill,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683.
第一,注重整合营销和品牌营销。“互联网+”背景下各自为战式的营销已无法达到营销效果的,乡村旅游应注重整合区域性的乡村旅游资源,统一包装形象、统一整合产品、统一规划线路,打造村庄整体的“乡村旅游名片”,或是区域性乡村旅游目的地的综合感知,[4]塑造乡村旅游品牌。最终实现资源共享、形象整合和市场一体化基础上的整体化营销。
亚洲地区制度框架构建进程中的自主性,深刻显示于新兴大国的角色定位与角色实践。正如相关研究指出的,当东盟于1997年邀请中日韩对话时,中国从一开始就表现得非常积极。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对东盟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东亚区域主体性”的认知。因此,中国对推动东亚合作表现得非常认真和务实。① 张蕴岭:《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的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期,第12页。 与此同时,中国主张地区国际组织和机制的构建和运行应当是开放的、包容的,而不是封闭式、排他性的“俱乐部模式”。正如中国领导人在首届“东亚峰会”上所强调的,“要大力推进由本地区国家参加、具有本地区特色、符合本地区要求的区域合作”,“也要考虑和照顾区域外国家在本地区的合理利益,增进这些国家对东亚合作的理解与支持”。② 温家宝:《坚持开放包容,实现互利共赢》,2005年12月14日,http://ww 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dyfheas_682566/zyjh_682576/t226426.shtml,访问日期:2018年1月20日。 当然,中国不只是积极参与已有的地区国际组织和机制,而是更加自信地推动创设地区性制度框架与合作机制,发起、组织和协调多边行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在中国的首倡和推动下建立起来的,这让亚洲在地区多边金融机构中拥有自主权和决定权。当前,中国积极与地区国家携手合作,共同推动“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这显示出亚洲国家在地区贸易领域构建制度框架的自主性,并会使自身在全球贸易规则制定进程中拥有一定的制度性话语权。
多边制度框架的建立和扩展,承载着亚洲地区秩序构建进程中的自主性回归。然而,这一回归并没有导向排他性、封闭性的地区制度框架,而是包容的、开放的互动体系。这种包容、开放的特征首先体现在成员资格(Membership)认定方面,成长中的亚洲地区国际组织不是“俱乐部”模式,即通常并不为此设定明确的地理范围以及候选成员国的政策调整等方面的加入门槛。其次,正是在包容开放的制度框架下,亚洲国家能够同时收获经济全球化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益处;“接受地区秩序建构必受外来力量影响的现实,愿意在非歧视原则的基础上与非成员国之间分享地区利益,同时又致力于确保地区秩序建构的主体性。”③ 门洪华:《地区秩序建构的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7期,第22页。 可以说,自主性与开放性的统一,构成亚洲地区秩序演进中的显著特征和发展取向。
结 语
地区秩序的形成和维系有赖于地区国际社会、尤其是在主权国家之间确立起共享的互动理念、规则和制度框架。冷战结束之后的亚洲,合作与共赢的理念、权力和平转移的趋势、各方互动关系的日益“制度化”等逐渐成为地区秩序构建进程中的显著特征。一系列地区性制度框架的建立和延展,承载上述秩序理念以及软制度与弱约束、自主性与开放性等特征,同时将这些秩序理念和特征限定在国家间的固定安排上,由此塑造着地区国家间的核心关系以及关于相互关系的彼此预期。从这个意义上说,演进中的亚洲地区体系以及国家间关系的未来图景——合作抑或对抗,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地区是否持续构建起有效运作的制度框架。
明媚的阳光散落在校园,小树吮吸着这美味的营养,几片黄色的叶子散落在林间,蝴蝶在阳光中穿梭、追逐、打闹、嬉戏着,珍惜着它们一年中最后也是最美的时光。隐约中,可以听见朗朗的读书声随着微风轻轻拂过大地。因为是秋天,阳光显得更为和煦,许多人开心地在操场上锻炼身体。他们有的大声喊着口号跑耐力赛,有的三五成群做着游戏……个个精神抖擞、精力充沛。
地区秩序和全球秩序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亚洲地区秩序的演进可能同时孕育了全球秩序的变化。基于此,新兴国家应当善于依托国际组织、多边机制成为塑造地区和国际秩序的积极力量。对于中国而言,构建亚洲地区制度框架,推进合作的议程,塑造互动规则和地区秩序,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为此,中国在地区制度领域的外交政策和行为应以明确的秩序理念为前提;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秩序理念为前提,多边外交将难以持续、有效地发挥作用,力量的增长将失去目标和方向。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多边外交政策和行为应以明确的国家角色为核心,即在地区发展、自由贸易、合作安全等领域成为制度框架的构建者、合作议程的设置者、共享理念的倡导者。在此基础上,中国能够与周边地区以及更为广泛的国际社会建立有共识的稳定关系,实现自身的和平发展,推动地区乃至全球层面的权力和平转移。
“说什么呢?威尔很厉害。”克里斯蒂娜耸了耸肩,“再说,我终于知道怎么可以不输了,他教我找到了自己的弱点,我以后只要阻止别人打我的下巴就好了。”
【作者简介】 马荣久,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山东青岛 邮编:266200)
【DOI】 10.13549/j.cnki.cn11-3959/d.2019.03.004
【中图分类号】 D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9)03-0059-12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推进周边地区制度框架构建的策略研究”(项目批准号:17BGJ056)和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一带一路’与地区制度框架构建研究”(项目批准号:16CZZJ01)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8-10-22】
【责任编辑:张颖】
标签:亚洲地区秩序论文; 地区制度框架论文; 国际组织论文; 周边外交论文;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