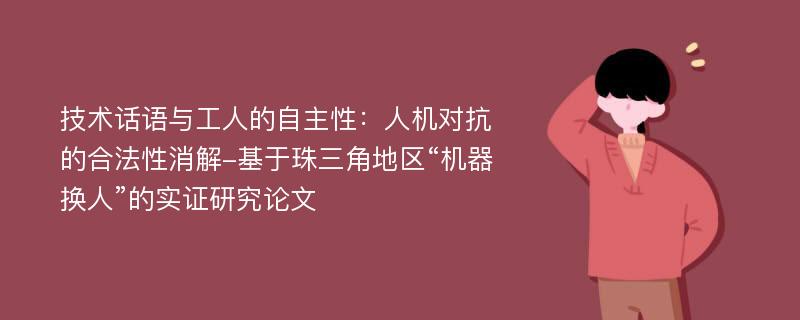
主持人语: 以信息化、自动化、网络化、智能化装备提升传统产业,推动技术红利替代人口红利,实现经济持续、高质量增长成为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毫无疑问,“机器换人”会改善劳动条件,提高生产效率和企业效益,但是从人类技术进步的历程来看,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会给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关系带来冲击。例如,1811年在英国发生的“卢德运动”就是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而激发的工人抗争。虽然这并不意味每一次技术进步都必然带来社会冲突,但却提醒我们在关注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后果的时候,也要关注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后果。从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关系的角度来看,社会后果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进步必然会从传统产业“挤”出一部分劳动力,“挤”出过程中的劳动关系和这部分人的再就业问题;二是技术进步必然会改变工人之间的关系、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对重新建构劳动关系提出新要求。本专题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产业升级实践为案例,围绕“新技术运用的社会后果”这一主题展开讨论。《技术话语与工人的自主性:人机对抗的合法性消解——基于珠三角地区“机器换人”的实证研究》分析了新技术的合法性建构、新技术推广的策略运用以及新技术对工人的市场选择空间的拓展,试图说明新技术的社会后果取决于政府发展理性、企业经济理性、工人社会理性三者的契合性。《技术赋权如何消解新业态中新生代劳动者的集体性行为》从技术赋权的视角,对移动互联网技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权利的影响,技术赋权带来的职业转换成本变化,以及新技术对劳动机遇和生活期盼的影响展开分析路径,认为新技术改变了传统集体行为的空间和基础。《“机器换人”对工人工资影响的异质性效应:基于中国的经验》运用大规模权威调查数据,检验了“机器换人”对工人工资的影响,探讨其背后的机制,发现“机器换人”对不同技术能力工人工资的影响存在不平等效应:“机器换人”带来的“就业替代效应”导致部分中低技术工人的工资降低,被迫离职;但提高了企业对高技能的需求,促使工人“再技能化”,导致高技术工人的人力资本回报和谈判能力上升。三篇文章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展开了讨论,不乏大胆的探索和新意。不过“新技术运用的社会后果”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话题,相信会引起学术的百家争鸣,若能达到如此效果,本专题的价值将远超文章本身。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蔡禾)
技术话语与工人的自主性:人机对抗的合法性消解
——基于珠三角地区“机器换人”的实证研究
邓智平
[摘 要] 尽管“机器换人”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但鲜有工人对“机器换人”进行抵制。文章针对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的实证调查发现,“机器换人”之所以未能引发“卢德运动”的原因在于国家、企业与工人三方合力作用的结果。国家对技术即进步的话语塑造,让技术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政治合法性,消解了工人对抗机器的道德合法性。企业普遍面临劳动力短缺,“机器换人”对工人的替代性有限,且通过柔性管理策略,以及转岗、保留岗位等方式悄悄地完成了机器换人。作为行动主体的工人,一方面认同国家技术即进步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则由于自身的流动性、就业选择的多样性增加等对“机器换人”产生的后果持乐观态度。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消解了工人抗争的社会经济基础。
[关键词] “机器换人”;劳动关系;抵制;人工智能
一、“机器换人”会引发工人的抵制吗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大力推进“机器换人”,许多传统制造企业开始引进自动化生产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升级,地方党委政府也纷纷出台政策对企业“机器换人”进行支持。2012年浙江省提出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全面推进“机器换人”。2014年1月,广东省东莞市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扶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资助企业推行‘机器换人’”,2014年8月又发布《东莞市“机器换人”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中国制造2025》的出台,更是将“机器换人”和智能制造推向了高潮。2016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财政部联合印发了《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到2020年形成较为完善的机器人产业体系。2013年起,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应用市场,2014年销量达到5.7万台,同比增长56%,占全球销量的1/4,但目前我国制造业机器人密度仍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15年我国每万名工人使用工业机器人数量为36,全球为66[1]。可以预见,未来随着国内工业机器人需求量的增加以及国产品牌的崛起,工业机器人的发展还将加速[2]。
“机器换人”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制造业工人下岗失业或转岗换岗。如浙江省自2013年起在4年多时间里,已累计减少普通劳动工人近200万人[3]。2014年9月至2015年12月,广东省东莞市制造业和加工贸易企业累计申报“机器换人”专项资金项目共 1262个,总投资达 103.84亿元,估算可减少用工 71253人[4]。另据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报告(2015—2016)显示:广东制造业企业的就业人数,在2013至2014年间下降了2.2%,2014至2015年间下降了6.3%;湖北制造业企业的就业人数,在2014至2015年间下降了3.3%。2014至2015年,广东就业下降企业占比为 52%,湖北为45%[5]。从全国来看,我国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在2012年达到2.3241亿人的峰值后开始逐年减少,2017年减少到 2.1824亿人,2017年比2012年减少1417万人。不仅如此,其下降速度还呈现越来越快的趋势[6]。
众所周知,在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由于机器生产对手工劳动的替代,导致大批手工业者破产、工人失业和工资下跌,当时工人把机器视为失业和贫困的根源,于是大肆捣毁机器,并以此作为发泄不满、反对企业主、争取改善劳动条件的手段,这就是著名的“卢德运动”。“卢德运动”于1811年在诺丁汉形成高潮,并迅速向整个英格兰蔓延,许多工厂和机器被破坏,英国政府被迫出动军警对付工人,并在1813年专门颁布《捣毁机器惩治法》,规定可用死刑惩治破坏机器的工人,由此可见工人对“机器换人”的抵制之强烈。
“机器换人”曾经引发了劳动关系领域的深刻变革,但有趣的是,当今中国的“机器换人”似乎并没有引发与当年英国类似的“卢德运动”。在大量的宣传报道和学术研究中,更多的是对产业转型升级和智能化制造的欢呼,以及企业推进“机器换人”的原因、困难和成效等的描述,鲜有关于工人对“机器换人”抵制的内容① 当然,偶尔也有工厂因为“机器换人”引发劳资纠纷。如 2014年浙江一家企业在引入一套高科技设备后,拟裁员50名,对裁员抱有抵制情绪的员工采取了不合作态度,一度严重阻碍了公司的生产活动。参见曹大友、郑梦:《机器换人,企业HR准备好了吗?》,《企业管理》2018年第9期。 。这个问题引起了笔者的研究兴趣,这也是本文拟研究的问题,即中国的“机器换人”为什么没有引发工人大规模的抵制?或者说“机器换人”就一定会引发工人的大规模抵制吗?笔者尝试利用调查资料,从国家、企业和工人三方视角来分析工人对“机器换人”的态度。
从多学科远程会诊、溶栓取栓、评估随访,到监护教育、大数据科研,将智慧医疗融入脑卒中救治。他们组织全市体系,力求脑卒中救治同质化、标准化。
二、技术变革中的人机对抗
(一)技术变迁与劳动关系
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会对劳动关系产生巨大冲击,并引发学界的广泛讨论。在工业革命早期,经典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随着机器大工业对传统手工业的替代,工人逐渐沦为机器的附庸,机器的使用使得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和监督更加充分,从而加剧了工人与机器关系的恶化[7],并导致了如“卢德运动”等工人抵制机器的事件发生。此后,布雷弗曼指出,以泰勒制为代表的流水线生产导致“概念与执行”的分离,工人被去技能化而变成“纯粹的机械工作的人”[8]。爱德华兹认为,在技术革命背景下,虽然资本对工人的控制策略已经从简单的直接控制转变为更加复杂的技术性控制,但工人也不是被动接受劳动控制,工作场所中其实充满了竞争和斗争[9]。布若威则强调不可忽视工人的主体性,他通过分析“赶工游戏”、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国家等机制,证明了劳动过程中工人的“同意”是如何产生的,并认为工人自发的同意与资本的强制共同塑造了生产行为,“同意的组织对诱发劳动者在将劳动力转化为劳动的过程中具有合作意愿是必需的”[10]。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加速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基于现实的失业问题以及对技术快速发展的恐惧,一批西方知识分子开始抛弃技术乐观主义的态度,重新审视技术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产生了以批评和反抗技术为主要特点的社会思潮,即“新卢德运动”或“新卢德主义”,这一思潮至今仍具有广泛影响[11]。可见,在学术传统中,工人对机器的抵抗以及资方如何通过策略消解这种抵抗始终是学者关注的核心议题。
2017年9月教育部“双一流”方案公布,中国传媒大学 “新闻传播学”“戏剧与影视学”两个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对中国传媒大学来说,建校以来的办学实践,在人文学科领域形成了以新闻传播学、戏剧与影视学为领先,传媒领域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特色和优势。要把一流学科建设作为高水平传媒大学建设的中心工程,引领创新,就要围绕主干学科,强化办学特色,建设若干一流学科,扩大国际影响力,带动学校进入世界同类高校前列。
(二)中国的“机器换人”及其后果
当前中国学界对“机器换人”的研究主要围绕其定义、原因、影响、困难及对策建议等方面进行论述。
学生将图文相结合,尝试从细胞核各部分结构和功能回答问题,如“细胞核内有DNA,能控制生命活动”“核膜能将细胞核与细胞质分开且进行物质交换”,等等。
综上所述,不同病因致颈部浅表淋巴结肿大患者应用高频超声诊断能够对其病情进行定性判断,具有较高应用价值,为了提高诊断准确度,应该对患者的淋巴结内部血流模式、大小、与周围分解以及形态、分区等进行综合评估。
首先,在“机器换人”的定义方面,有学者认为,“机器换人”是指在信息化、智能化、自动化、现代化技术应用背景下,企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与产业升级过程中增加使用机器设备的行动,其含义较宽泛,包含“人工智能机器人”对劳动力的替代[12]。许辉则认为“机器换人”本质上是企业通过自动化、信息化改革来促进生产方式革命,意味着我国产业发展模式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13]。“机器换人”主要是指企业增加机器的使用从而提升生产设备的自动化程度,实质是通过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实现对劳动力的替代,与以往历次工业技术革命把机器作为帮助人提高生产效率的工具而存在不同,当今制造业“机器换人”却直接把机器变成劳动力[14]。因此,机器对劳动力的替代更加直接,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更加广泛和深远。
其次,对于当前企业“机器换人”的原因,学界普遍认为是由于国内劳动力的短缺和用工成本的上涨[15],制造企业“机器换人”既有招工难等被动型原因,也有减少工伤改善劳动条件、优化工艺技术流程、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优质率等主动型原因[16]。不同企业推动“机器换人”的原因不同,处于市场领先地位、盈利能力较强的企业主要是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善产品质量等拉力因素,处于市场落后地位、盈利能力较弱的企业主要是降低人工和生产经营成本等推力因素。东莞市“机器换人”的调查发现,企业推动“机器换人”的主要动力在于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劳动力成本、改善产品质量、降低职业健康和安全风险,获得政府针对企业机器换人的财政补贴只是很小作用[17]。
再次,学界对“机器换人”的影响结论不一。有学者发现技术进步会促进生产率的提升,拉动经济增长[18],降低用工及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减少生产事故[19],带动工作质量、劳动权利、社会保障和劳资对话等社会升级[20]。但也有相反的观点,认为“机器换人”会冲击劳动力市场,导致体力劳动工人、低技术工人过剩,出现结构性失业[21],以及带来就业极化① Goos,M.et al,“Jobs polarization in Europe”Amercican Economic Review 2009,99(2):5-63;Graetz,G.&G.Michaels,“Robots at work:the impact on Productivity and jobs”,Technical Report,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LSE.2015;Michaels,G.et al,“Has ICT polarized skill demand?Evidence from eleven countries over twenty-five years”,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4,96(1):60-77. 现象等;“机器换人”导致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份额降低和资本收入份额增加,不同劳动力的工资更加不平等,进而加剧整个社会的收入不平等[22]。总体来看,学者们更多的是研究“机器换人”对就业规模、就业结构、就业质量以及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影响[23],较少研究“机器换人”对劳动关系的影响。
最后,学界认为“机器换人”会带来以下问题:技术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对构成雇主和雇员的挑战,雇主面临着机器成本过高、使用维护机器的人才不足、机器设备国产化水平低、政策优惠知晓率低和门槛高等问题[24],雇员尤其是中低端雇员则面临着的就业冲击和技能提档升级等问题[25]。为此,学者提出了诸如政府产业政策扶持[26]、分步推进“机器换人”[27]、鼓励雇主提高雇员技能、通过失业援助和扩大公共教育来帮助失业工人找到新工作[28]、加强对工人的教育培训、实行全民基本收入政策、对机器人征税等建议[29]。诸如此类建议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对企业“机器换人”进行补贴和优惠;做好公共就业服务、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等预防失业性措施;社会保障托底,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等补救性措施。
工人没有想过要去破坏机器,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破坏机器有什么用,有问题直接找老板。“机器换人”成为社会发展的趋势,表明中国越来越强大了。(电子厂工人,19G05)
三、“机器换人”背景下的国家、企业、工人策略
(一)政治合法性:国家对“机器换人”的话语塑造
“机器换人”是被逼的,现在用工成本越来越高,每年都在涨,随着中西部经济崛起,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不错的工作,想招到熟练的操作工越来越不容易,所以我们干脆加大投入买机器,不用再年年为招工发愁。前年购买5台自动穿孔机,每台可以代替10个穿孔工人。(纺织企业负责人,18Q08)
从国家层面看,近年来世界主要制造业强国均不同程度地推行产业振兴计划,如美国的“再工业化”与“制造业回归”、日本的“机器人新战略”、德国的工业4.0等,力图抢占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必须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其中最重要且契合实际的发展路径就是推动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方式由劳动投入为主向智能制造转变[32]。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出台《关于推进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2013年)、《中国制造 2025》(2015年)、《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2016 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7年)、《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2018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强调“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一系列官方文件的出台,昭示着党和政府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机器换人”的决心,一些文件甚至明确提出2030年我国要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二氧化碳综合利用存在潜在收益。二氧化碳化工产业、二氧化碳生物利用技术已成为国内外二氧化碳利用的研究热点,部分化工利用技术已进入产业化,预示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从地方层面看,各级地方党委政府,特别是东南沿海等制造业发达地区,纷纷出台政策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例如,广东省2014年出台《关于推动新一轮技术改造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并设立专项资金,组织企业开展广东省级企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设备更新“机器人应用”项目申报工作;2015年出台 《广东省工业转型升级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年)》提出 2015至 2017年三年累计推动195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机器换人”,使制造业智能化水平明显提升。广东省内的东莞、佛山等制造业大市也纷纷出钱出政策支持企业推进“机器换人”,例如,东莞市从2014年起设立“机器换人”专项资金,为企业“机器换人”提供补贴。政府对于开展“机器换人”的考虑,时任广东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徐少华的话比较有代表性,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表示:现在提出产业转型升级,我们不能再把劳动力的低廉作为招商引资的优惠工具,也不宜再用劳动力的低廉来作为发展产业的一个招牌。新问题要用新思维去解决,比如用工荒的问题,劳动力不够可以找机器人。所以在广东珠三角,特别是佛山、东莞这些城市,已经大量掀起“机器换人”的计划,大量的智能机器人已经开始运用到很多生产线当中,一方面是这些企业本身的转型,另一方面也为发展智能机器人带来一个巨大的商机。我们欢迎全国各地研究智能机器人的研究院来广东发展,欢迎制造机器人的企业到广东投资,也欢迎更多的企业使用机械手、机器人[33]。
事实上,企业实施“机器换人”并非是近两年才开始的,部分企业负责人反映所在企业早在2010年左右就已经开始着手引入自动化生产线。而什么时候、什么岗位要使用机器人都是经过理性的成本核算后的结果。企业负责人普遍表示,企业一般只是部分使用工业机器人、机器臂等自动化设备,仍保留了较多的人工岗位,一方面由于这些岗位机器目前替代不了,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岗位使用人工的成本更低。针对被机器人取代的工人,企业通常采取以下策略:一是内部转岗策略。企业购买工业机器人后,也不会把这一生产线上的工人直接辞退,而是通过公司内部转岗的方式就地安排到新的工作岗位。对大部分工人而言,只要还有工作就无所谓,换岗位被视为是正常的事情。二是仍旧保留工人原生产岗位,由于工人的流动性大,工人辞职后该岗位则不再招人。无论是工人转岗后导致转入岗位工人增多、人均工作量减少,还是自动化设备引入后导致该岗位工人工作量较少,直接后果就是工人的加班时间减少了。工人加班时间减少则加班工资下降,最终导致这部分工人的总工资受影响,这种情况下,工人通常主动辞职换下一家单位。在此过程中,企业通过对劳动过程的柔性控制,消解工人与资方的直接对抗,悄悄地实现机器对工人的替代。
综上所述,当前关于中国“机器换人”的研究总体上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次,缺少理论的深度,一些“机器换人”对就业影响的相关研究也缺少劳动关系的视角,工人在“机器换人”过程中的主体性和权益较少地被考虑。不可否认,尽管在一些企业中工人也因“机器换人”获得了额外的培训和技能提升机会,但“机器换人”确实导致了工人各种形式的去技能化和被替代[30],可为什么当今中国的产业工人没有去抵制呢?本文通过搜集“机器换人”的相关政策文件、媒体报道等文献材料,同时在2018年和2019年对广东省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开展“机器换人”的企业、工人进行深度访谈,共访谈企业负责人18个,访谈工人20人,这些资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实证支撑。
其次,对交易中的客户进行风险监控和风险提示。在此阶段可以运用大数据的资源及技术手段对客户的资金链条、交易情况、还款情况及违约情况等动态变化进行实时掌握,以降低客户贷款中及贷款后的金融风险。此外,也可以随时提醒客户违约后的严重后果,让其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
(二)柔和型控制:“机器换人”与企业管理策略
“机器换人”最直接的实施者还是企业,因此“机器换人”本质上是一种雇主策略,是精确的理性算计的结果。企业开展“机器换人”诱因是劳动力供给不足、用工成本上升。早在2004年,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就开始出现“民工荒”,并迅速波及全国。与此同时,农民工工资逐年上涨,2006—2015年的十年间,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了近一倍。2015年,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为4216元/月(635 美元),是美国的 20%(3099 美元),高于马来西亚(538 美元)、泰国(438 美元)、越南(206 美元)、印度(136美元)等新兴市场国家[35]。这些数据表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结束,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基本丧失。“招工难、招工贵,只好用机器换人”是不少企业主的心声。“机器换人”不仅解决了招工难和招工贵的问题,同时还确保了生产的稳定性。
自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科学和技术上的优越性震惊了中国,早期的中国喊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期望在不改变既有制度的情况下通过学习西方技术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新中国成立后,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社会公众都相信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打造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邓小平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因此,科学与技术的进步被认为是中国国家现代化的象征。郑永年把中国社会精英和社会公众对技术的推崇称之为“技术民族主义”的文化倾向[31]。尽管“技术民族主义”倾向这一判断值得商榷,但无疑中国在国家战略上确实十分重视技术的发展。国家对技术的推崇,使得技术在中国获得了政治合法性,也得到了社会公众的承认。
当然,想要在真正意义上开展生态循环经济活动,企业需要投入相应成本,不仅要投入维护生态环境的技术和成本,而且还要积极修复因为经济发展而被破坏的环境。通过综合利用各种因素,从而打破传统的“表象”理念,实现经济效益与保护环境的结合。
“机器换人”最大的好处就是稳定,现在人很难招,而且不能吃苦,一不顺心就走了,人员流动性很大,人一走生产就要受到影响。(包装企业负责人,18Q03)
虽然“机器换人”看上去很美,但购买机器的成本高昂,后期维护费用也不少,除了替代人工的设备之外,往往还涉及更多生产设备的改进或更新,甚至整个生产流程的改造,一次性投入比较高,成本回收周期长。因此,企业一般会经过仔细核算成本收益后才会考虑。
引入机器人的价钱,相当于可代替工人的月薪乘以12,再乘以1.5到5倍左右。目前普工的月薪大约为4000元,所以用机器换人的价格约在5万到25万之间。只有企业认为“机器换人”是划算的,才会去购买机器。(冲压企业负责人,18Q11)
从社会层面看,尽管新闻媒体有争论“机器换人”、人工智能是否会带来失业危机,公众也一度对人工智能的到来进行了讨论。然而,无论新闻媒体还是个体,鲜有出现反对“机器换人”的声音,对《中国制造2025》战略也普遍持欢欣鼓舞的态度。中国人对技术和机器的反思总体上远远不如西方发达国家。工人对机器的破坏和抵制基本被“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带来的政治合法性所消解,对工人而言,技术进步是必然的趋势。尽管有个别学者调查发现,中部地区有些工业园区的企业因“机器换人”裁员,导致当地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冲击工厂的行为,有的还暗中破坏企业生产[34],但笔者在对珠三角的调研中,工人破坏机器的现象鲜有发生,工人普遍认可官方转型升级的话语。
其次,除了机器人难以真正取代人之外,被替代的是工人不愿意干的工作。在技术比较落后的时期,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比较恶劣,工人要么从事脏苦累的体力劳动,要么在流水线从事高强度的重复劳动① 调研中,有工人笑称“自己就是机器人,在工厂,不管你做的是什么,最终都会变成机器人”。 。随着农民工的代际转换[39],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对物质和精神的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越来越不愿意从事单调枯燥的重复劳动,更不愿意从事搬运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焊接等环境污染强的岗位。机器替代的人工岗位主要是劳动强度大、工作条件差、风险高、程序化、重复性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并不为工人所喜欢。调研发现,目前“机器换人”主要用在轻纺、电子、化工等传统产业,特别是高危行业与工种,有毒有害生产车间是优先实行“机器换人”的领域,这既有利于保障工人人身安全,也符合产业升级的内存要求。因此,工人对此持欢迎态度,觉得这些工作就应该被机器所替代。
(三)选择性替代:工人的自主性及其选择
不可否认,“机器换人”会对工人的就业和劳动权益产生冲击。但是在劳动力短缺的大结构条件下,对工人的冲击总体不大,且受冲击的工人并非没有新的选择。即使在大力推行“机器换人”的东莞,普工、技工等用工缺口依然较大[36]。在此背景下,工人的自主选择依旧很多,并不需要以破坏机器来对抗“机器换人”带来的负向影响。
首先,就工人主体而言,部分工人本身不可替代,“机器换人”只是选择性地替代了部分岗位。据调查发现,目前全国只有8%的企业使用了机器人,其中广东为10%,湖北为6%,44%的企业使用了自动化设备,自动化设备价值占设备价值总额的17%[37]。也就是说,目前“机器换人”并没有全面推开和普及,特别是一些资金不足、订单不稳定的企业并没有急于推进“机器换人”,所以总体上这次“机器换人”行动并未造成大规模的劳动力失业[38]。特别是由于机器人技术发展还不够成熟,比如有企业反映,机械手抓不住“又重又脆弱”的陶瓷,机器人难以处理鼠标滚轮嵌入的动作,自动运输机爬不上角度太大的斜坡等等,因此短期内机器人并不可能完全取代人,许多工业生产程序还需要人手工操作。机器人从引入生产到完美使用之间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第一、宋代福建银矿开采全国第一,福建境内普及面甚广,闽东亦占一定比例,然闽东亦因交通系统尚不完善,人口相对较少等未得到全面开发。到了明代,随着白银货币化大势,闽东银矿再度迎来大开采,成为福建第一。为闽东区域开发吸引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等,实现资源优化组合,形成内引外联之势,促成白银文化背景和氛围的出现。
数控程序仿真功能[7],针对一些非宏普通程序,不需要检查碰撞等复杂工况的条件下,能够很好地对数控车加工程序进行仿真验证,相对一些大型仿真软件,能够避免过于复杂的后置设置[8],并且在自动比较分析时可以在任意方向进行余量分析。兼容Fanuc和Siemens仿真系统,运用灵活,通用性强。
在工厂干太无聊了,每天都是重复同一个动作,也见不到什么人,现在使用机器人来做那些工作挺好的。特别是那些脏活累活,譬如搬运、打包、贴商标、码垛等工作,最好全部用机器人代替。(家电企业工人,18F02)
最后,工人有新的就业选择,而且在替代时能获得补偿。“机器换人”导致简单体力劳动人员被替代的同时,也增加了大量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例如,为保障机器的正常运转,需要懂机器人编程、安全、机械、机电等人才。调研发现,一般5台机器人需要一名技术服务人员。不仅如此,随着产业的高端化特别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会相应地带动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增加。此外,近几年网约车、外卖骑手等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兴起,也为工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因此,工人并不担心自己被机器替换掉,反而发生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一些在企业工作时间较长的员工希望老板把自己炒掉,然后获得一笔补偿费。
我在这厂工作十多年了,现在厂里搞“机器换人”,我巴不得老板把我炒掉,然后每年赔一个月工资给我,这样我拿着几万块钱可以去做别的,回家做点小生意也行,去找别的工作也行……不担心找不到工作,只是找不到工资高的工作。(电子企业工人,19M09)
对于留下来的人,企业则会为其提供新的培训和技能提升机会,甚至增加工资福利。留下来的工人也表示,自己会努力提升自我能力,适应新的社会发展要求。既有的一些研究也发现,工人对“机器换人”的适应度与工人的学习态度、自信心强度、受教育程度、政策的落实度和工资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多数(约七成)工人有信心应对机器人可能带来的冲击,认为机器人的普及能减轻工作强度,并且愿意通过学习和提升技能水平来提高薪酬待遇水平[40]。总体而言,工人对“机器换人”后自己的前景是比较乐观的。当工人有其他选择并对未来持乐观态度时,工人就不太可能采取对抗性的行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我们开展“机器换人”已经两年多了,以前是600个人左右,现在是300人,省了一半的人,这样,公司就有能力去提高留下来人的工资,也会对留下来的工人进行培训,使他们学会与机器相处。(模具企业负责人,19Q03)
四、结论与讨论
(一)基本结论
当前中国“机器换人”主要是企业和政府积极推动的结果,工人在“机器换人”的决策中是缺位的,处于被动适应的地位,但劳动关系的三方主体即政府、企业、工人之间并没有发生直接的博弈和冲突,更没有引发工人的大规模抵制,社会总体比较和谐稳定。“机器换人”没有引发中国的“卢德运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从政府角度看,政府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竞争力,把“机器换人”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扎实推进,“机器换人”在中国社会获得了政治合法性,技术即进步的话语体系塑造消解了工人对技术的反思和反抗,破坏机器的行为缺乏法律和道德的合法性。第二,从企业角度看,“机器换人”是在劳动力供给不足、人口红利枯竭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企业推进“机器换人”并不会对工人就业产生大规模的冲击。企业出于减少工伤、提高生产效率、改善生产条件的“机器换人”,有利于改善工人的劳动环境,实现产业升级带动社会升级。同时,企业通过转岗、保留岗位等柔性治理策略,消除了与工人的直接对抗,“机器换人”带来的就业替代效应在渐进过程中悄悄完成。第三,从工人角度看,机器替代的岗位主要是劳动强度大、工作条件差、风险高、程序化、重复性的工作,即工人不愿从事的工作。同时,技术进步为创造新的工作岗位、提高生产率及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提供了机会① 世界银行集团:《2019世界发展报告:工作性质的变革》,第2页。 。如机器人维护,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平台经济等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兴起,为工人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增加了工人的选择。“机器换人”对劳动力就业的破坏效应小于“创造效应”[41],因而未造成大规模失业。
从更深层次原因看,伴随着生产自动化的推进,劳动力的代际更替和产业的升级换代也逐步完成,劳动者与机器之间形成了共生均衡关系。不同于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生产力的进步与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呈现出不同步状态,机器设备的应用构成了对工人阶级的挤压,两者之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对立和冲突关系,再加上社会化大生产不发达、产业系统吸纳劳动力的空间有限,使得被机器替换的工人无法再就业。同时,机器换人始终是企业的理性选择,企业需要综合考量政策支持、投资成本与收益、劳动力成本等多种因素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并非自动化生产越多和雇佣劳动力越少就会导致企业总成本越低,因此当前工人也没有面临“机器换人”就失业的生存危机。在这个意义上,“机器换人”在中国、在珠三角地区能够有序推进,契合了企业、政府和劳动者三方共同的理性诉求,即企业需要平衡投入和产出的经济理性,地方政府需要贯彻创新驱动战略的发展理性,新生代工人则追求良好劳动环境的社会理性。
(二)趋势研判
总体来看,在“机器换人”普及率并不高的当前,“机器换人”似乎是一个政企劳三方共赢的行为。从积极方面来看,“机器换人”带来了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和生产成本的下降,也改善了工人的劳动环境和增加了工人技能提升的机会,并提高了整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和生产竞争力。从更高层面来看,“机器换人”适应了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将人类从繁重的劳动过程中解放出来,迎合了人类对于机器人时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想象和期待。但是,我们也不能对此过于乐观。因为从长远来看,随着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和成本的降低,未来“机器换人”的覆盖面将更加广泛、更加彻底,一旦到达临界点,即因新技术而引发的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所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不能有效消化“机器换人”所替代的劳动力时,将会出现何种后果尚不得知。正如美国科普作家马丁·福特在《机器人时代》里写的:“我们要承认一个严峻的现实:目前的大部分工作被机器人取代只是时间问题。”[42]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机器换人”的破坏效应不容小觑。比如,对劳动就业的冲击,大规模的生产自动化可能会导致劳动者的大规模失业;对社会关系的影响,机器是局部替代还是全面替代,是替代简单生产还是替代复杂劳动,这种技术的走向随着生产自动化走向纵深,对人类社会关系产生怎样的后果,还有待实践观察。因此,这些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警示,相关政府部门、企业应尽早作出应对措施。2019年5月,国务院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的成立就标志着国家对新时代就业工作复杂形势的未雨绸缪。
(三)政策建议
尽管“机器换人”是政府主动作为、企业主动选择和劳动者适应配合的综合作用结果,但是也要警惕“机器换人”对劳动生产、对社会关系等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及早进行研判并作出有效应对:一是积极推进人机协同。“机器换人”并非将工人赶出劳动生产过程,而是寻求更高效率和更低成本的人机协同,未来要积极推进自动化生成和技能工人培育相结合,形成更加紧密的人机配套,使得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和自动化设备的日常运行维护能够兼容协同,从而实现人与机器的和谐相处。二是加强社会政策托底。对于可能被“机器换人”替代掉的工人,政府和企业应加强公共就业援助和技能培训,做好失业和基本生活保障,特别是对年龄偏大的产业工人,应做好有序退出和底线民生保障工作;对于分流到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中就业的人员,应逐步分类规范非典型劳动关系,维护从业人员的劳动权益。
[参考文献]
[1]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印发《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EB/OL].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8/c4746362/content.tml,2016-03-21.
[2]中国工业机器人发展现状[EB/OL].http://www.sohu.com/a/168244330_212888,2017-08-30.
[3]李海州.机器换人 人怎么办[N].舟山日报,2017-06-09.
[4]路平.“机器换人”换来高质量就业[N].中国劳动保障报,2016-03-02.
[5][35][37]CEES研究团队.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报告(2015-2016)[J].宏观质量研究,2017(2).
[6]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110.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1-53.
[8]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M].方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79.
[9]Edwards,Richard.Contested Terrain: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NewYork:Basic Books,1979:33-35.
[10]迈克尔·布若威.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M].李荣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3-50.
[11]陈红兵.新卢德主义述评[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3).
[12][16][38]张艳华.制造业“机器换人”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基于北京市6家企业的案例研究[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8(4).
[13][20]许辉.“世界工厂”模式的终结——对“机器换人”的劳工社会学考察[J].社会发展研究,2019(1).
[14]刘晓,徐珍珍.“机器换人”与职业教育发展:挑战与应对[J].教育发展研究,2015(21).
[15]陈昌平,罗琼.中国制造业基于成本控制的“机器换人”问题研究[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6(6).
[17][30]Naubahar Sharif,Yu Huang.Industrial Automation in China’s“Workshop of the World”[J].The China Journal,2019(81).
[18]Acemoglu,Daron.Technical Change,Inequality,and the Labor Market[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2(1).
[19]谢晓波,许垚,孟寅敏.“机器换人”之永康先行经验[J].浙江经济,2013(18).
[21]于冬梅,朱成喜.“机器换人”的困境与出路研究[J].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2016(2).
[22][41]Autor,D.H.Why are there still so many jobs?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workplace automa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5(3).
[23]吴锦宇,葛乙九.“机器换人”背景下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思考[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
[24]赵建.珠三角“机器换人”背后的利益博弈[J].决策,2016(4).
[25]张阳,张力跃.“机器换人”冲击新生代农民工[N].中国教育报,2017-04-04.
[26]林昌华.中国实施“机器换人”战略促进产业转型研究[J].中国发展,2015(3).
[27][34]聂洪辉,朱源.“机器换人”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与社会稳定的影响[J].广西社会科学,2017(4).
[28]Matthias Oschinski,Rosalie Wyonch..Future Shock?The Impact of Automation on Canada's Labour Market[EB/OL].https://ssrn.com/abstract=2934610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2934610,2019-09-16.
[29]曹静,周亚林.人工智能对经济的影响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2018(1).
[31]郑永年.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M].邱道隆,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14:27-35.
[32]戴伟,许桂华.工业4.0背景下融资租赁的约束机制与模式创新——基于“机器换人”的视角[J].财会月刊,2018(5).
[33]徐豪.广东常务副省长:东莞已开始大规模机器换人计划[EB/OL].http://news.anhuinews.com/system/2015/03/24/006727696.shtml,2015-03-24.
[36]乔金亮.“机器换人”难解农民工荒[N].经济日报,2017-03-24.
[39]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和城乡融合关系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1(3).
[40]何展鸿,韩宝国.“机器换人”的适应性研究——基于佛山市传统产业的工人调查[J].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1).
[42]马丁·福特.机器人时代:技术、工作与经济的未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25.
[作者简介] 邓智平,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现代化战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社会学博士,广东广州 510618
[中图分类号] C9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19)05-0001-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技术赋权与互联网时代的劳动关系转型研究”(18BSH076)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戴庆瑄]
标签:“机器换人”论文; 劳动关系论文; 抵制论文; 人工智能论文;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现代化战略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