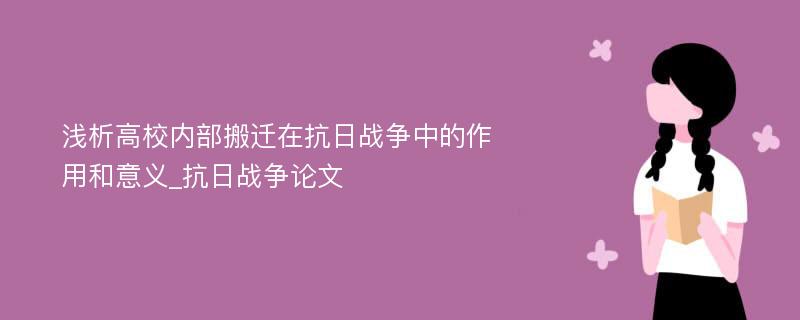
浅析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作用和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校内论文,意义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战时期,我国高校向西南、西北及粤赣闽浙等省山区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迁徙。高校内迁对中国抗战的胜利、开展抗日民主运动、恢复和发展战时高等教育、推动落后地区教育文化乃至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
一、高校内迁,保存了中国教育文化的基本力量,支持了长期抗战。
抗战爆发后,日寇为从根本上摧毁中国,对我国高校进行了有计划、长时期、大规模摧残和破坏。顾毓毓说:“此次战争中,蒙受损失最大者为高等教育机关,敌人轰炸破坏,亦以高等教育机关为主要目标”[①]据统计,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8月底,我国108所高校,91所遭到破坏,10所遭完全毁坏,25所因战争而陷于停顿;教职员减少了17%,学生减少了50%;高等教育机关直接财产损失(包括校舍、图书、仪器设备)达3360余万元。“此项教育机关,关系我国文化之发展。此项损失,实为中华文化之浩劫”[②]。
为了从这场浩劫中抢救和保存我国教育文化的命脉,坚持抗战,众多高校进行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搬迁。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于1938年1月被迫迁往昆明。师生分水陆两路出发。陆路由男生和部分教师组成湘黔滇旅行团,穿越丛山峻岭,行程3500里,耗时68天。当他们到达昆明时,闻一多的胡子有近尺长,曾昭伦满身长了虱子。其实,内迁中比这更为艰难的学校不在少数。浙江大学二年间被迫5次迁移,行经浙、赣、湘、桂、黔5省,行程5000余里。河南大学在1944年5月的迁移中遇敌,10余人丧生,20多人被俘。唐山土木工程学院在1938年迁至桂林时遇日机轰炸,全部仪器、行李被毁。由于战局动荡不定,许多高校一迁再迁,据不完全统计,迁校3次以上的约19所,其中4次的有唐山土木工程学院、私立东吴大学、私立之江大学等8所,5次的有浙江大学、私立铭贤学院2所,6次的有河南大学、江西省立医专等3所,7次的有中山大学、山西大学等5所,广东文理学院高达8次。据统计,在抗战期间,因战争影响而迁移的高校约106所(含抗战以后新建的学校),搬迁次数共计300余次[③]。
经过广大师生的努力,一所所高校终于迁移到较为安全的内地,大批珍贵的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免遭劫难,如浙大内迁时将极珍贵的218箱文澜阁《四库全书》安全带出。学校迁到内地者,大都恢复上课,“据教育部统计,……战事后迁入后方复课者七十七校。[④]”
二、内迁高校的广大师生积极参加抗日斗争,以各种形式从事抗日
救亡活动。
抗战期间,国统区青年掀起了“百万从军”活动,其中许多人是内迁学校的学生。1943年12月,在四川省三台县的东北大学发起了志愿从军运动,引发了当地学生的从军热。不少高校师生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如中山大学许多师生参加了东江抗日游击纵队,浙江大学许多学生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浙闽赣抗日武装斗争。复旦大学、西北工学院等校师生纷纷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河南大学的抗日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1937年冬,河大举办了抗日游击战术训练班,范文澜、嵇文甫等教授担任教员,许多学生参加了训练。在南召县,在中共号召下,以河大同学为基本力量组成了抗日自卫战时服务团。1938年初夏,服务团改称战时教育工作团,后来大部分团员参加了抗日武装。南召县的李青店,因此被人们称为“小延安”。
内迁学校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以各种形式为抗战服务。各医学院 或大学的医学院系为救护伤病员、培训战争急需的医药和护理人员做了大量工作。河南大学抗战后奉命承办重伤医院。台儿庄战役时,医学院组织救护队为伤员送水、换药,抢救伤员1.8万余次;后随军入湖南,收容伤员500余人[⑤]。苏州医学院医科将医院设备、器材、药品等运至扬州,组成第七重伤医院,随军转移到湘西,救护了大量伤员。江西省立医专为解决战时急需的医疗和护理人员,增设了高级药剂职业科,开办了战时救护训练班、护产助理员训练班,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空军援华作战,需要大量译员。于是西南联大外语系开办了培训班,许多外语系学生受训后担任了译员工作。内迁后的国立艺专和私立上海美专一改以往忽视社会生活、轻视乡土文化的倾向,以艺术为武器,进行义展、义卖、义演等抗日救亡活动。
广大在校师生则开展丰富多彩的抗日救亡活动。1942年,日军进犯赣东,中正大学成立了以校长胡先骕为名誉团长,目录学家姚名达为团长的战地服务团,慰问前线将士,救护伤员。服务团后不幸与敌遭遇,姚名达和一名团员牺牲。中山大学在云南徵江期间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形式多样。徵江地处边陲,消息闭塞,于是中大在县府门口的空房里设立了书报室,让民众阅览抗日快报;在街头和校门口开办宣传栏,以诗歌、漫画、杂文等文艺形式宣传抗日。学生们还组织许多进步社团,如民风剧团、粤声音乐社、青年生活社等,深入村寨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一时间,徵江形成了抗日救亡的新气象。河南大学学生自编了《抗日三字经》,深入农村,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农民做抗日宣传,召集他们学唱抗日救亡歌曲等。
内迁高校师生直接或间接参加抗日斗争,是教育界、学生界对民族抗日最直接、最有力的支持,谱写了学界抗日的光辉篇章。
三、内迁高校是抗战中后期国统区抗日民主斗争的先锋和中坚。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厉行独裁,压制民主,掠夺民生。在教育界则推行“战时教育须作平时看”的文化专制主义教育方针;在高校实行所谓“导师制”,建立国民党区党部、三青团和训导处三位一体的法西斯管理体制,安插特务,对师生实行严厉统制。这一切,激起广大师生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具有民主斗争优良传统的高校师生毅然揭起国统区抗日民主斗争的大旗,走在运动的最前列,成为斗争的生力军。其中,以1942年初的倒孔祥熙风潮和1944年成都高校的反迫害、争自由风潮影响最大。
在“五·四”纪念日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宣扬“民主”、“科学”,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是高校从事抗日民主斗争的普遍形式。特别是西南联大,荟集了一大批民主运动的斗士和追求进步的师生,每逢“五·四”都要举办各种纪念活动,斗争矛头往往直指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参加者常有昆明其它大学及文教界的机关团体,规模盛大,有时达3000余人。在重庆的复旦大学是西南地区又一学生运动中心和民主斗争的堡垒。“皖南事变”后,中共在复旦建立了“核心小组”以领导学校的民主斗争。著名学者和教育家陈望道主持的新闻学系则是全校民主力量的中坚。学校许多进步教授先后受到周恩来等人的邀见。浙大是西南地区民主运动的又一堡垒,被国民党视为眼中钉。浙大一些进步师生如浙大训导长、教授费巩等即惨遭国民党特务的逮捕和杀害。1944年12月,国民党政府电令解散浙大,要学生全体从军,教职员中年岁合格者也从军,以图除之而后快,但遭到浙大师生坚决反对。中山大学是粤北民主斗争的中心,河南大学则是北方学界抗日民主运动的堡垒。内迁高校为国统区的抗日民主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内迁高校在抗战时期,立志教育救国,艰苦奋斗,在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首先,高校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了较显著成绩。如前所说,抗战之初我国高校受到惨重破坏,学校和师生数锐减。当时,国民党政府就高校内迁、调整、新建及收留战区失学学生、允许流亡师生转学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内迁学校也克服重重困难,尽快医治战争创伤。经过二、三年的努力,高校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学生数在1939年超过了战前,达4.44万人,学校数在1940年超过了战前,达113所。到1945年,高校数增至141所,学生数达8.35万,比战前增加了1倍[⑥]。内迁高校在院系规模、师生人数、教学科研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有些学校还达到了较高水平,如浙大、联大、厦大、武大、中央大学等。
其次,内迁高校在极其简陋、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和发扬优良的校风、学风,取得了令人骄傲的办学成绩。内迁高校除少数迁往城市外,多数迁往经济文化落后、自然条件极差的小城或农村。不少学校的校舍是茅草屋或铁皮房,阴冷潮湿,冬寒、夏热,也有借庙宇寺观和租民房的。到抗战中后期,国民党统治日趋腐败,物价暴涨,广大师生常常食不裹腹,衣不御寒;办学经费和教学科研设备严重短缺。可是,苦难磨灭不了师生的兴学抗战意志,反而坚定了救亡图存信念。南开大学在遭到日寇毁灭性轰炸后,校长张伯岺慨然向新闻界声言:“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物质,而南开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⑦]”浙大校长竺可桢说:“将欲抗顽虏,复失壤,兴旧邦,其必由学乎![⑧]”他提出以“求是”为校训。浙大每学期课时数均超过教育部规定的要求,科学研究则以炭炉代酒精,以陶杯代营养钵,以竹管引水。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却孕育出大批杰出人才,如物理学家李政道,取得了许多科研成果。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参观浙大后,对其在如此条件下取得如此出色的办学成就惊叹不已,盛赞其为“东方剑桥”。西南联大著名化学家、负责人之一杨石先先生回顾这段历史时感慨地说:“联大经历了怎样一个历史时期啊!科学人才和革命志士同时涌现,给联大历史带来了殊荣”,联大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是“因为师生们都关心祖国的前途命运,……看不到对祖国明天丧失信心的情景。当时的条件很差,但恶劣的环境磨砺了大家的意志。同学们怀着中兴之志刻苦读书,许多人的论文是在茶馆里完成的”[⑨]。河南大学几度搬迁,校产损失殆尽,学生有时只能在屋檐下、树下学习;1945年医学院的毕业考试是冒着敌人机枪的扫射进行的。重庆大学在敌机的轰炸下,挖掘防空洞,建立地下实验室,坚持教学科研。国立艺专在艰难的办学环境中,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艺术人才,如赵无极、吴冠中,等等。
五、高校大批内迁带动和促进了落后地区教育文化乃至社会的发展。
最突出的表现是抗战时期和战后,西南、西北各省、两广及闽浙赣等内迁高校集中的省份新办高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抗战时期,我国新办高校56所,上述地区就有43所,占总数的3/4强;若除去外省市在当地创办的(如江苏战时在四川创办了5所学校,战后迁回江苏)则为34所,占3/5强[⑩]。高校的内迁和内地高校的兴办使我国教育中心发生大转移。由原来以平津沪宁汉杭厦穗为中心的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向以重庆、成都、昆明、贵阳、桂林、西安为中心的西南、西北地区及粤北、赣中南、闽西、浙南等地转移。这大大改变了这些地区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落后的局面。如西北地区战前仅有3所高校,而抗战期间就新建了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农业专科学校等5所高校,这些高校基本上是由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组成的西北联大分化而出的。江西战前仅有2所高校,抗战期间在赣中南创建了7所高校,从而根本改变了江西在华东地区高教落后的地位。新办高校在专业设置上大都考虑到地方实际,侧重师范、农、医、工科类,这就直接推动了当地教育、文化、卫生、经济等事业的发展。
高校内迁及大批文化界精英涌入内地,大大提高了内地高校的师资水平和办学质量。昆明、桂林、贵阳等地是战时著名的文化城,许多文教、科技人才荟集于此。当地大学纷纷聘请他们执教或讲学,一时学校人才济济,声誉迅速扩大。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利用燕大、金陵、齐鲁、东吴等6所大学及其部分院系借用该校校园之机,同它们联合办学,学习它们的办学经验,引进人才,聘请名家到校执教、讲学,终于使自己在办学规模、教研水平上有了很大提高,院系增加,学生数也由战前的335人增至1945年的1300余人,并先后创办了6个研究所、室,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11)。
内迁高校还主动帮助内地改变教育、文化、经济等方面的落后面貌,开展各种社会服务,为当地培养人才。中山大学在徵江期间,农学院对当地农业生产进行调查研究;医学院结合实际开办门诊,下乡考察地方疾病;师范学院师生在当地中小学兼课,开办民众识字班,招收未入学的学龄儿童读书,并在县城开商店、饭店,帮助当地办合作社。西北联大坚持“培养人才与服务社会并行”的原则,为陕南培养了大批人才。金陵大学内迁后,农学院增设了植物病虫害系,在仁寿、温江、新乡等地开辟农业推广区,开办短期培训班。
内迁高校对内地教育、文化、经济发展所起的影响和作用并不限于抗战时期,它是持久的、深远的。
内迁高校与中华民族的抗日大业相始终。内迁高校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抗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教育史中最为灾难深重、但又光辉难忘的一页。
注释:
①②顾毓琇:“抗战以来我国教育文化之损失”,转引自《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1957年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第28、32页。
③⑩统计数字根据季啸风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中国高等学校变迁》一书的资料得出。注③的统计数据还参考了彭友德的《近代江西高等教育沿革纪略》一文,见《江西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④白桃:《抗战三年来的中国教育》,转引自《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第41页。
⑤王敬:《抗日救亡运动在河南大学》,《史学月刊》1985年第6期,第80页。
⑥郑登云编著:《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第254页。
⑦梁吉生:《张伯岺》,《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70页。
⑧余章瑞:《竺可桢》,《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第2卷,第14页。
⑨王言俊:《杨石先》,《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第2卷,第229、218页。
(11)《中国高等学校变迁》,第9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