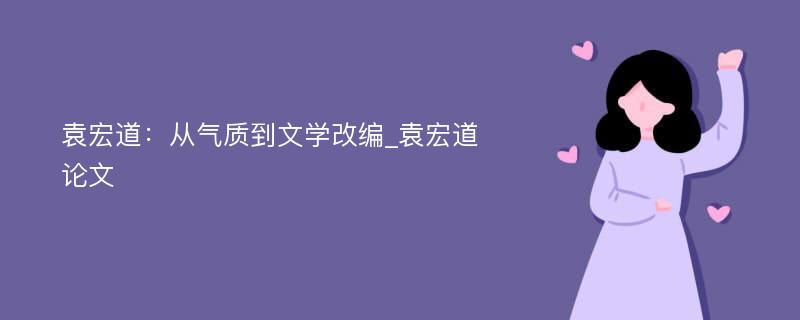
袁宏道:从性情到文学的自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情论文,文学论文,袁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22X(2000)01-0071-06
有的学者尝言,袁宏道的文论“是性情的,也是文学的,是中郎其人的风格,也是其文的风格”(注:田素兰:《袁中郎文学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版,第141页。)。此论十分确当。袁氏文论的主要概念,都首先关联着他的人生价值观念,而如“趣”、“韵”等,则几乎纯是他用以表述其人生价值取向的范畴。本文以袁宏道性情的自适为研究的切入点,来把握其沉沦与超越的人生价值取向及其与袁宏道文论的内在关联。
一、自适——沉沦与超越的二重路向
袁宏道的一生,是不停地追求自适的一生。他时时难禁“好适之心”(《汤义仍》,《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本文所引袁氏言论均出此书,以下仅注篇名),屡屡激赏“适世”之人(《徐汉明》),频频称道“闲适”为“世间第一便宜事”(《识伯修遗墨后》),常常欲造“自适之极”(《徐汉明》)。袁宏道的自适,就是顺适自我性情的一己之“乐”:“有一分,乐一分”,“极人间之乐”、“太上之乐”(注:此数语依次见于《家报》、《管东溟》、《徐渔浦》。)。这种顺乎一己之性情的快乐的自适,就是袁宏道人生价值的核心。由此出发,形成了袁宏道沉沦与超越的人生价值取向。
这两种不同的人生价值取向的形成,又基于一个普遍性的前提,即人的存在的双重性这一客观命定:一方面,人是个体的生命存在,不可能完全脱离其生物类属的本然性,因此,在人的意识结构中,潜藏着自我顺适其非理性的感性情欲的本能冲动。另一方面,人又是社会性的群体存在,体现着社会理性的普遍规定性,所以,在人的意识结构中,又必然存在着大量的理性内容。非理性的本然感性情欲和理性意识既相互排斥又互为作用,二者之间的对立互动统一于个体的意识结构,又体现在个体存在之中。正是这种人的存在的双重性使袁宏道分别选择了沉沦与超越的二重人生价值取向,而这种选择又得助于袁宏道禅学思想的强力推动。袁宏道的禅学思想,从一开始就潜隐着狂禅的非理性与反理性和精神解脱的宗教理性的二维倾向。从前者出发,袁宏道“淫僻畏仁义,行止羞罔两”(《赠李子髯》),强烈渴望纵情适欲;从后者出发,他又自言“我亦冥心求佛果,十年梦落虎溪东”(《游二圣禅林检藏有述》),真心希求宗教境界中的精神超脱。由于狂禅的巨大张力,袁宏道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本然性情欲有了自我顺适的强烈要求;渴求打破“自我”的理性约束,让“本我”的本然感性情欲越出潜意识层面,并在现实世界中顽强地确认与表现自己。作为一种人生价值取向,这种渴求所指向的目标,就是在物欲生活中的沉沦;这种情欲的自适,就是沉沦的自适。但是,作为一个娶妻生子事父、考举做官食禄、写诗作文佞佛的文人士子,袁宏道的个人性情又较多地存在着理性的成分,因此,他就不能在实际的行事中像所谓“无闻无识真人”和无室无家的匠人那样,不顾礼法的规范而无所顾忌地放纵自己的本然情欲(见《叙小修诗》、《碧晖上人修净室引》),命运注定他必须接受社会理性的普遍规范。唯其如此,他的情欲的自适就不可能在现实中顺畅地进行,而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表现为强烈的愿望。然而,袁宏道对自适的渴望并未就此止步,他偏要在理性的荆棘丛中重新开辟一条自适的通途。不过,慧根不浅、极欲自适而又好懒、怕累、易厌的袁宏道却没有像道学鸿儒那样选取在日用伦常中体证天道的道德超越模式,而是在更多地存在于其理性意识的宗教理性中开出了一条超越的精神自适之路,以求取万劫不坏的永恒真乐:“跳入清凉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聂化南》)如此,即形成了袁宏道的超越的人生价值取向;而这种精神的自适,即为超越的自适。
袁宏道把文学创作也当成了他的自适方式。他屡屡自言以诗文为戏(见《徐崇白》、《张幼于》),就是把写诗作文当作“去此无可度日者”(《黄平倩》)的遣情适意的手段;他极力提倡“独抒情灵”、“任性而发”(《叙小修诗》)、“率性而行”(《识张幼于箴铭后》),就是主张在文学创作中顺适己意、自由自在地放任个体性情。袁宏道的文论,毫无掩蔽地展示了他的沉沦与超越的二重自适路向。
二、沉沦的自适——自然性灵论
病态的晚明是狂禅思潮风行的时代,作为狂禅的“明星”,袁宏道亦毫不矫情地自许为不让天下(见《张幼于》)。袁宏道的狂禅,就是远绍洪州—临济一路“随缘禅”的“居士”狂禅(注:袁宏道多次对洪州—临济禅学大加赞赏。见《为寒灰书册》、《德山麈潭》等。)。他断然宣称“毛孔骨节,无处非佛,……贪嗔慈忍,无念非佛”(《与仙人论性书》),坚决认为“艳歌娇舞,无处非定”(《徐冏卿》),公然叫嚷“但辨此心,天下事何不可为”(《聂化南》)。这种狂禅的内在理路,就是洪州一脉的“作用是性”的致思模式,即以用为体,本体消融在作用中,佛性消解在“平常心”中,所以说“平常心是道”(《景德传灯录》)。袁宏道尽管说无处非佛、无念非佛,却是把“佛”消解于“贪嗔慈忍”的自然心性中,遂使作为被体证客体的佛性本体与作为生命个体的体证主体等而为一,“佛”仅成为一个毫无自性的名号,它再也不能作为普遍理性的宗教形上本体对作为“作用”的个体情欲有所约束和抑制了。佛性消解的结果,就是对“息妄”、“守心”、“去染”、“灭欲”的佛法教理的完全彻底的抛弃,就是对在“佛”的名号下贪著“艳歌娇舞”的情欲享乐的毫无保留的肯定,就是对以本然的“此心”遍行“天下事”的无端诸行的不加分辨的褒扬。概言之,就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自主性、本然性、非理性和反理性的无所顾忌的放任,就是对一己之沉沦的自适的一无拘束的放纵。
正是由于狂禅的强力推动,袁宏道的沉沦的自适极度张扬着个体生命存在的自主性、本然性、非理性和反理性。袁宏道的狂禅把佛性本体完全等同于本然的生命主体,在佛的名号下确立了自适主体的自主性原则。由此,袁宏道便胆敢放言:“当率行胸怀,极人间之乐,奈何低眉事人,苦牛马之所难,貌妾妇之所羞乎?”(《管东溟》)不要如牛马妾妇那样低眉事人,要高昂自适的主体,放纵其本然性,以获取适欲的快乐。他公然宣称“我好色”(《别石篑》),明白承认“弟往时有青娥之癖”(《李湘洲编修》),一度推崇“入拥座间红”为“人间第一佳事”(《龚惟长先生》),表露出强烈的好色欲望。除好色之外,袁宏道还十分好货,他曾对其姊夫毛太初说:“人生三十岁,何可使囊无余钱,囤无余米,居无高堂广厦,到口无肥酒大肉也!”(《毛太初》)如此等等,皆属本然性的身口享乐:“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鲜……一快活也。”(《龚惟长先生》)这种本然性的身口享乐即为非理性的感性快乐。此非理性亦为袁宏道的狂禅所肯定:“看来世间,毕竟没有理,只是事……又有何法可修、何悟可顿耶?”(《陈志寰》)他认定“礼法仇狂士”(《哭龙君诗》),“六籍信刍狗”(《孤山》),官场即“地狱”(《罗隐南》),均是其自适的障碍与滞累,极为显露地表现出他的沉沦的自适的反理性特征。
个体生命存在的这些特性,也随着沉沦的自适在文学领域的推衍而全面地表现在袁宏道的本于自然之旨而以“性灵”、“真”、“趣”等概念为标识的前期文论即自然性灵论中。首先,袁宏道的自然性灵论挺立了创作主体的自主性:“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从自己胸臆流出”(《叙小修诗》);“独抒己见,信心而言”(《叙梅子马王程稿》);“率性而行”(《识张幼于箴铭后》),“任性而发”(《叙小修诗》)。“性灵”、“胸臆”、“心”、“性”,都是创作主体自己的、独立的个人性情。袁宏道要求创作主体在创作活动中空所依傍,特立独行,极度强化了创作主体的自主性原则。他认为只有坚持这一原则,创作主体才能“不依傍半个古人”而“顶天立地”(《张幼于》)。其次,袁宏道的自然性灵论张扬着创作主体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本然性。他说:“无闻无识真人所作……任性而发,尚能通之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叙小修诗》)“无闻无识真人”之“性”,是尚未受到理性的“污染”与“蔽障”的“天然之性”(《识张幼于箴铭后》),亦即个体生命的本然存在;而“喜怒哀乐嗜好情欲”,即为本然性的情感意欲。这种情欲的快乐,即袁宏道的狂禅所张扬的食、色、衣、居的身口享乐,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他的诗文创作中。即如好色一端,在袁集中就有随检即得的“浪歌”、“艳歌”为证。再次,袁宏道的自然性灵论强调了创作主体作为本然的生命存在的非理性和反理性。袁宏道所肯定的创作主体是“无闻无识”的“真人”,所谓“闻识”,泛指道理、知识、闻见,包括儒学的名教义理礼法纲常等社会理性规范及产生于社会理性之域的、广义的人文经验知识。“真”,排弃了这些理性的“闻识”,明显地表露出它的非理性特质。这种非理性也表现在袁宏道所标举的“趣”概念中。他认为,“趣”是尚未为理性所规范的“童子”、“赤子”自得的“自在”,即非理性的心理感受,它发生于非理性的本然感性心理层面,排除了知性的参与,所以说“趣得之学问者浅”。“趣”的非理性又势必导向反理性。“趣”,始终抗拒着理性的束缚(以上袁宏道论“趣”之语均见《叙陈正甫会心集》)。概括地说,袁宏道的自然性灵论所张扬的创作主体的上述特性,就是主张创作主体在创作活动中“信心而言”、“率性而行”、“任性而发”,自由自在地顺适和表现自然性情,毫无滞碍地进行他的沉沦的自适。
三、超越的自适——人文性灵论
然而,袁宏道自然性灵论张扬沉沦的自适的叫喊不久即告消歇。他的前期文论即本于自然之旨而以“性灵”、“真”、“趣”等概念为标识的自然性灵论,到万历三十年(1602)就开始转向立足于理性之基而以“淡”、“韵”、“质”等概念为标识的人文性灵论,这一转向,究其实质就是从自然到理性的转向;这一转向的深刻内在原因,就是袁宏道的沉沦的自适向超越的自适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又紧密地联系着袁宏道禅学倾向的重大转移。
由于人的存在的理性规定,袁宏道的沉沦的自适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顺畅地进行,而必然遭到来自现实社会各方面种种理性的重重约束和层层抑制。生活在这一充满理性的此岸世界中,恰似“形体作奴仆,礼法成枷钮”(《贺家池》),正是“弥天都是网,何处有闲身”(《偶成》),怎能获得情欲自适的快活?但是,生性通脱、渴望自在的袁宏道却不肯由于其沉沦的自适在现实中的受挫而就此终止对自适的追求。不过,在理性之网的重重约束中,袁宏道不得不开辟一条超越的自适之路,这就是横贯其宗教理性园地而“直抵佛位”的精神超越之路。尽管袁宏道在年少时就有了“冥心求佛果”的夙愿,但由于考举、做官、适欲的强烈诱惑而一直“事佛心难定”(《偶成》)。到了中年,由于自适的受挫,也由于一向隐然存在的“贪生畏死”的“石火电光”之忧(《兰亭记》、《冯琢庵师》),袁宏道便感到有认真事佛的必要了:“因思浮生倏忽,真如电火……不如且料理未后一着为吃紧,余俱闲事也。”(《龚惟长先生》)“料理未后一着”,就是“发性命之玄机,究生死之根源”(《徐渔浦》),潜心释氏“性命之学”,追寻存在的终极意义,以图直抵彼岸极乐净土,入住精神的永恒家园。这样,理性环境的外部逼迫与畏怖生死的内在隐忧就同时从内外两向驱使袁宏道选择了宗教解脱的超越自适之路。
与沉沦的自适的本然性、非理性和反理性而指向现实的物欲世界不同的是,袁宏道的超越的自适有着理性、超越性及其所指向的精神性等特点。在本质上,这种自适所肯定的理性,就是宗教理性;这一肯定标志着袁宏道的禅学倾向从狂禅向禅净合一的重大转移(注:袁宏道后期佛论皆以净土为宗。其中,《西方合论》为主张禅净合一的名篇(《袁宏道集笺校》附录一)。)。与作为其前期禅学主要倾向的狂禅之消解普遍性的宗教形上本体不同,袁宏道的净禅合一的后期禅学重建了佛土净妙境界这一宗教形上本体。作为普遍的宗教理体。这一形上本体广大无边,遍入一切处,是三界六道一切众生的普遍本质规定。它既为一切个体众生往生佛土提供了宗教的形上担保,也有着规范个体行为、抑制个体私欲的普遍效用。它实际上是佛法教理的形上客体化。因此,众生要往生净土,个体的特殊存在要契合本体的普遍存在,就必须按此佛法教理严格地修行持戒。禅学倾向转变后袁宏道深明此理:“古德教人持戒,即是向上事。”(《李龙湖》)盖修持乃为“士大夫一道保命符子”(《答陶石篑》)。以这种肯定宗教理性的修持观反思其“言心言性”而“不肯修行”的狂禅,袁宏道不免深自悔恨而始知其为“虚头惑见”、“久久为魔所摄”的“毛道所谈之禅”,“所谓驴橛马椿也”(《李龙湖》、《答陶石篑》)。袁宏道不仅从学理上肯定修持,而且践行其事:既“渐学断肉”(《答顾绍芾秀才书》),又不近女色(《李湘洲编修》)。袁宏道的超越的自适对宗教理性的肯定也暗含着对儒学社会道德理性的某种程度的间接肯定,这是因为释教与儒学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之点:二者同为理性之学,都肯定着人的普遍理性本质(在释为佛性,在儒为天命之性);二者都预设了普遍的形上本体(在释为真如、佛土,在儒为天理、天道),又各有其规矩法度(在释为修行布施,在儒为主庄敬、重功夫)以抑制个体情欲(儒释皆主“去欲”、“灭欲”);二者又均主个体的内在精神超越。正是由于儒、释之间的这些相似点的存在,又受到宋代以降“三教合一”论的影响,袁宏道才有充足理由以释氏“高明玄旷清虚淡远”的“生死性命”之旨会通“朝闻道、夕死可”的“孔氏学脉”,肯定儒学之理即社会道德理性(《寿存斋张公七十序》、《为寒灰书册》)。由上可知袁宏道的超越的自适对理性的肯定,这种肯定即意示着此种自适的超越性和精神性。作为宗教本体的佛土净妙境界,是高悬于个体存在之上的形上普遍理性存在,因此,往生净土,就意味着普遍理性存在对个体存在及其本然性的超越。同时,这种宗教终极境界的形上性、普遍性也表明着它的超于有形色界的“形如虚空”、“如梦如幻”的精神性本质;所谓清净佛土不过是这种精神性的对象化和实体化,而往生净土的快活亦只是精神性的自适而已。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就出发点和终极目标来说,袁宏道的超越的自适与沉沦的自适又有着两个共同的根本特点。一是自私性。与他的沉沦的自适一样,超越的自适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都是为了获取个体的自身快乐,但又不同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圣学体道模式,作为宗教的精神解脱,它无疑具有释氏“为己”之学的根本特征,即“遗弃人伦事物之常”的“自私”性(注:朱熹、王阳明对佛学“自私”的批评,见《朱文公文集》,卷三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45页。)。二是粗俗性。袁宏道的沉沦的自适作为物欲的享乐,其粗俗性固不待言。而其超越的自适不仅亦以处于潜意识层面的本然情欲冲动为原初动力,而且此本然情欲的超越的“升华”所指向的终极目标,不用说不同于“万物一体”的圣学境界,即作为宗教境界,亦有异于清净虚空的真如禅境,而只是“黄金铺地”、“百味饮食,自然盈满”的净土“极乐世界”(《无量寿经》)。究其实质,就是财货物色的贪著欲望的宗教实体化。这本是下层信众所追求的粗俗境界,它成为文人士夫袁宏道的“超越”自适的终极追求颇值得深思:这不仅表明着袁宏道的“超越”的自适的粗俗性,而且往深层看,亦映现出袁宏道个人人格乃至晚明士人群体人格的世俗面貌,这意味着“高尚其志”的古典人文精神在晚明时代的严重失落。
袁宏道的超越的自适,连同它的种种特性,全面地反映在他的以“淡”、“韵”、“质”等概念为标识的后期文论中。由于袁宏道的后期文论肯定着人(创作主体)的理性本质和人文修养而有异于他的自然性灵论,所以可称之为人文性灵论。先看其“淡”、“韵”之论。《叙呙氏家绳集》云:“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灵也……元亮以之。”以“淡”为极至境界的“真性灵”,不同于“无闻无识真人”的自然性灵,而本应是文人士夫的淡泊之性,即陶渊明式的超然物外、淡泊名利的“出处志节”与高尚情怀。这种“淡”,应是文人士夫所特有的超越的精神境界,与所谓“学道之韵”有着相近的性质。袁宏道又把“学道之韵”视为所谓“贤回”、“与点”之“乐”(《寿存斋张公七十序》)。前者本为学习儒家之道而达到的超越的终极境界,后者则应是在这一超越境界中个体所体验到的精神愉悦,二者不相分离。从表层上看,有类于宋明理学所乐道的“寻孔颜乐处”。这是一种人文的境界,其中无疑融入了诸多理性的内容。从体验的主体维度看,个体存在必须摆脱本然自我之囿,由非理性之域进入理性之域;他必须在社会理性的人文环境中获得深厚的人文修养,才能由本然存在的“自然境界”进入到“万物一体”的“天人境界”,从而获得“体道”的精神愉悦。袁宏道于此亦不无所见:“大都士之有韵者,理必入微。”(同上)而从终极存在的维度看,这一境界所预设的形上本体是一种超乎个体存在的普遍理体(天道),它既作为终极境界为个体体验提供了形上担保,又作为人的本质规定而具有约束和抑制个体存在的普遍效用。从表面上看,“淡”、“韵”作为人文境界以及在此境界中个体所获得的精神快乐,与袁宏道趋向佛土的超越自适在理性、超越性和精神性方面确实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然而,从新儒学理和普遍接受的角度看,所谓“学道之韵”和“贤回”、“与点”之“乐”,本该是“寻孔颜乐处”的道德终极境界,可是袁宏道却把它完全等同于释氏“高明玄旷清虚淡远”之旨,并以之为“大解脱之场”,就把这一本属圣学的道德境界转换成了其后期禅学所主的佛土净妙境界,而将圣学“万物一体”的体道之乐一降而成为“跳入清凉佛土”的“快活”,从而满足了其超越的自适向文论领域全面推衍的迫切需求。这自然是套用了盛行于明代禅门的“会通三教”的浅薄做法,本无足论,不过在这里却泄露了袁宏道的“超越”自适的自私性和粗俗性。再看袁宏道关于“质”的论断(见《行素园释引》),其基
本精神也在于对理性的强调。他说:“物之传者必以质……文章亦耳。”“质”即文学文本的内在价值。创作主体必须经过“敝精神而学之”、“博学详说”的艰苦过程,然后才能在“机境偶触”的灵感状态中以其所蓄之学“会诸心”,从而使其文本获得“质”的内在价值。学习的内容,即所谓“学”、“说”以及“廉洛之理”,包括儒家的义理之学及其他广泛的人文经验知识;学习的目的,是在于积累深厚的人文修养以成就文人的“性灵”。十分清楚,“质”的定性,只能是一种文化价值,属于社会理性的范畴。总而言之,以“淡”、“韵”、“质”为标识的袁宏道后期文论,作为肯定理性与人文修养的人文性灵论,它的要旨就是立足于人的存在的理性之基而主张以理性、超越性和精神性为特征的超越的自适。袁宏道的人文性灵论,是他的超越的自适在文学领域的合乎逻辑的全面引伸。
袁宏道把文学活动当成了他的自适方式,他把追求自适的精神贯注于文学思想之中,使他的性情自适的双重路向及其种种特性一齐延伸和全面表现在他的前后期文论当中。袁宏道的性情的自适既规定了其前后期文论的不同特点,又规定了其整个文论的根本特征。由其自适的自私性和粗俗性来看,袁宏道文论的根本特征表现在迥异于传统文论的两个重要方面:
(1)袁宏道性情自适的自私性深刻影响了他的整个文论,使其所关注的焦点始终局限在个体存在的范围。他的文论的主题,只是倡言一己性情的自适,而极少涉及广泛的社会人生。这表明了袁宏道文论与重视美刺传统、主张礼乐教化、关怀现实人生、强调文道合一的传统政教文论之间的重大差别。(2)袁宏道性情自适的粗俗性也严重影响了他的整个文论,使其全部话语始终围绕着一己身心的自适这一快乐主义命题,而不是关联着建构审美意境的美学主题。这又反映着袁宏道文论与标举兴象风神、崇尚审美意趣、追求审美境界、注重审美超越的传统审美诗论之间的重要差异。
收稿日期:1999-0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