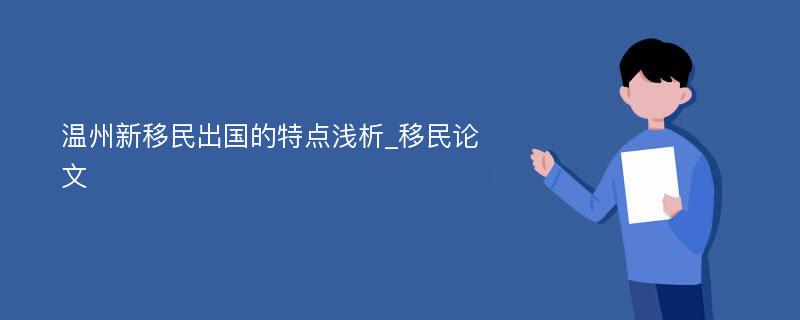
温州新移民出国特点简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温州论文,新移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4.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925(2006)01-0026-05
温州是全国知名的侨乡之一,拥有海外侨胞40多万,遍布世界65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温州新移民人数迅速膨胀,引起学者们的不断关注。本文拟在前人积累的材料基础上重点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新移民出国的特点,并与建国前两次移民高潮(一战后至20年代初;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作一对比。
温州侨乡涵盖今鹿城、瓯海两区,文成、瑞安、乐清、苍南、平阳、泰顺、洞头、永嘉等八县。其中,文成、瑞安、永嘉三县是侨胞比较集中的区域。本文主要采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数据,虽不是最新的,但至少可以看出其发展的态势。
一、出国高潮持续时间特别长,人数不断攀升
与先前的出国比较,温州新移民出国,从时间上考察持续时间特别长,第一次高潮从1918~1923年,前后六年时间;第二次从1929~1937年,历经九年;第三次从1979年至今,持续不衰。人数也不断攀升,始终保持成倍增长的势头。如,文成县玉壶区前两次高潮中共出国约1100余人,到1984年底统计也只有4659人[1],1997年的数据表明,玉壶镇在海外有13000多人[2],与国内人口的比例约1∶1.5;瑞安桂峰乡在前两次高潮中约200人次出国,1995年有华侨1689人[3];丽岙镇华侨出国始于1929年,在第二次高潮中共出国303人,到1997年底,全镇共有9399人侨居海外[4],单1997年就有1420人[5];永嘉七都镇人出国始于1934年,1937年出国二人,到1978年出国918人,1979~1993年移居海外者达3462人,平均每年230.8人[6]。另据温州市公安局提供的资料统计(表一),1982~1994年出国人数共计75556人,如果包括非法手段出境的,人数就更多了。可见百姓出国热情之高。
表一 1982~1994年温州市公安局批准发照人数统计表
年份批准发照人数
年份
批准发照人数
1982~19834508
1989
7526
19844751
1990
8607
19855035
1991
7957
19864207
1992
8759
19877435
1993
7292
19884306
1994
5173
——资料来源:《温州华侨史》,第104页
二、移民本源不断扩大,结构发生很大变化
过去,移民本源集中在几个特定区域,如前面的玉壶、桂峰、丽岙、七都等。现在,随着社会的进步,移民意识打破封闭的状态,开始向四周蔓延、渗透,越来越多的人走出了国门。以瑞安各乡镇为例,全市44个乡镇皆有人出国。(见表二)
表二 瑞安各乡镇侨居国外华侨、华人数(1995年12月)
乡镇 丽岙 仙岩 城关 桂峰 枫岭 塘下 罗凤 湖岭
永安
人数 6248 4535 2916 1689 1385 1232 715
478467
乡镇 马屿 鲍田 东岩 汀田 莘塍 高楼 飞云 桐浦 平阳坑
人数 361
290
285
240
219
201
169
169157
乡镇 场桥 营前 碧山 林垟 芳庄 荆谷 去周 海安
陶山
人数 155
154
142
133
121
999790 79
乡镇 梅屿 仙降 江溪 宁益 上望 龙湖 曹村 林溪
篁社
人数
696662585451474541
乡镇 梅头 鹿木 潘岱 金川 阁巷 潮基 大南 顺泰
人数
3433302625203 2
——资料来源:《温州华侨史》,第105页
出国人员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知识结构、身份结构等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年龄结构看,过去人们出国以谋生为主,基本上是清一色的青壮年。现在随着出国目的的多样性,出国人员的年龄呈现多层次。以瑞安市白门乡1979~1988年出国的华侨年龄为例(见表三),当时15岁以下儿童和40岁以上中老年人占到出国总人数的17.34%。
表三 1979~1988年瑞安市白门乡出国华侨年龄结构调查表
年龄 10岁以下 11-15岁16-20岁
21-25岁
26-30岁 31-35岁
人数 20
29 505339
33
年龄 36-40岁
40岁以上 外国出生
年代不明
总计
人数 18
15 6052
369
——资料来源:《温州华侨史》,第107~108页
从性别上看,过去出国闯荡的为清一色男子。现代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走出国门闯荡世界。1979~1988年白门乡共迁居海外338人,其中对偶家庭73人[7],即使不计算家庭子女和单身出国中的女性,女性出国占了当时总人数的21.6%,超过1/5。她们中很多人和男子一样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如:旅美画家陈雪薇,其作品受到了纽约州科学馆馆长格拉姆雷博士的盛赞,并受到里根总统和克林顿总统夫妇的礼遇;加拿大语言听力康复协会会员、加拿大中国笔会副会长张翎,被誉为“移民文学的探索者”;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常务理事、西班牙华人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王少媚,全球汉诗总会欧洲诗人协会副会长、瓦伦西亚中文学校校长王熙都,西班牙华侨华人妇女联合会秘书长、马德里中文学校教导主任黄小捷,美国营养学会会员、国际新潮保健品专家、美国FDA(食品药物管理局)法规专家潘萍微,西班牙中国佛教妙法协会会长、南部华侨华人协会副会长颜月华等都是新时期出国女性中的佼佼者。
从知识结构看,由于普遍实行九年义务制教育以及出国留学热潮的推动,大大提高了华侨华人的知识水平。据《海外温州人》(上册)、《闯天下的温州人》(下卷)记载的100多位海外名人中,有明确学历的、出国前拥有大专或本科学历的24人,拥有硕士学历的三人,拥有博士学历一人,占总数1/4,都是新时期出国的。其他出国人员大多数也在国内接受过程度不同的教育,很多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们中有三人在国外完成大学学业,一人进修硕士学位,六人完成博士学位。
从身份结构看,过去出国谋生的多是山区农民和破产的手工业者。进入新时期以来,出国已不仅仅是一条谋生的道路了,逐渐成为人们施展自己才华,实现自己理想和抱负,寻求人生更大价值的手段了。出国成为一种时尚。上至国家干部,中括教师、老板,下到农民、普通工人和职员,概莫能外。从《海外温州人》(上册)、《闯天下的温州人》(下卷)统计看,新时期出国的名人中有国家机关干部六人,国营企事业单位部门负责人(包括工矿、银行、文联)12人,商人、企业家17人,教师(包括大学、中学教师和校长)九人,医生二人,律师一人,出国留学生五人,共计52人,占两书新时期出国人数的一半以上,其中有些人还曾是人大代表、劳模等。
三、移民目的趋向多样化
建国前,浙南山区“九山半水半分田”,许多生活在浙南山区的老百姓普遍面临无田可耕,无地可种的困境,加上天灾人祸,他们的生活贫穷。瑞安、瓯海的部分山区海拔都在300~800米,人们多以种植番薯为生。当地流传一句谚语:“山头人三件宝:火笼当棉袄,竹篾当灯草,番薯干吃到老。”死守这方土地无疑没有活路,只有走出去,才可能有新的生机,这是当地人的普遍共识。现在,人们生活水平已有了很大提高,对外国的了解也逐步加深,人们的愿望发生了变化。虽然仍然有农民为谋生而出国,但比重在降低。在官方资料中,温州已全部摘掉“贫困县”的帽子,大部分人已达到温饱水平。许多人趋之若鹜地出国,存在几种情况:
(一)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和更高的社会地位。主要发生在著名的侨乡,是由于所谓的“相对失落感”造成的。首先,虽然这些山区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由于先天的条件限制,那里的生产水平和单纯的生产收入都不会很高,与相对比较发达的城镇中心区的居民水平还是有相当差距的。同时,与同地区家有华侨的居民相比,生活水平也会有很大的差别。有华侨的人家不断输入外汇,对家乡、家庭的贡献也大,本人和家人更有“面子”。于是,外国的高工资成了吸引他们的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动因。
(二)为了寻求就业机会和更好地发挥自身的才华,并得到相应的认同。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一部分有一定学历的留学生身上。他们通常对自己的能力有相当高的估计,对自身的价值有较高的期待,但当现实无法达到要求时,他们通常会选择留学海外,作为实现人生目标的一个跳板。一方面,进可以留在国外工作,甚至完成移民,过着比国内优越的生活;退可以拿外国的文凭回中国找工作,一般也能找到很不错的工作。另一方面,外企更加完善的人才选拔机制和好的工作环境,也是吸引他们的一个原因。在温州,关系非常重要,制约了人才自身可发展的空间,对此,高学历、高追求的人心理不愿接受,因此,出国留学成了他们摆脱这种困境的一块“垫脚石”。
(三)为了给孩子寻求一种出路。“望子成龙”是天下每个父母或多或少的期待。在温州现有的教育状况和升学体制下,不少有实力的家长纷纷选择让孩子去外地读书,其中就不乏选择去国外。分三种情况:一是有些父母认为外国的教育比中国的好,升学机会多,孩子将来比较能有出息;二是有些父母不愿意孩子学得太辛苦,面对过重的升学压力而选择送孩子出国念书,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高考和中考的孩子身上;三是发生在一些成绩差的孩子身上,他们在升学考中发挥不好,没有达到父母的预想,父母认为与其让孩子去读差的学校还不如送孩子出国。他们中间有些父母选择直接留学,有的则是把孩子托付亲戚先带出去,到国外是打工还是继续学业,那是后话。无论是打工还是留学,对父母来说以为是找到了一条他们自认为对孩子最好的出路。
(四)部分人单纯羡慕或追求国外整体生活环境,包括城市环境、生活方式、教育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等,想到国外定居。他们通常都有雄厚的资本,生活无忧,更追求生活的舒适和高品质。有的全家三口花100万元移民加拿大,有些通过涉外婚姻达到这个目的。老华侨们都有一份深厚的故乡情结,即使不能落叶归根,也希望子女能回家乡寻找另一半。据说在温州的大学生毕业招聘会上,许多老华侨既是在招工也是在招“儿媳”。一方面,儿媳是家乡人,沟通不是问题,同时对下一代而言,可以保持一种中国人、温州人的教育;另一方面,又可以让她们在自己的事业里帮忙,和儿子相互帮助,可谓“一举两得”。
四、出国途径和手段多样化
过去,人们出国并不需要任何手续,只要凑足旅费,能够登上去国外的轮船就行了。当然,这少不了专门牵线搭桥的人,当时称之为“包客”。他们会根据航程远近收取不同价格的“包银”,买通外国船员,将出国者藏于货轮的底舱。他们可以说是现代“蛇头”的前身和雏形。只是这些人由于没有政府限制,活动起来更加自由、安全,甚至会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有部分人是作为劳工输出的。一战后,西欧各国的经济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百废待兴,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于是,他们把目光放在了在自己殖民半殖民统治之下的国家,以各种欺骗手段来吸引贫困不堪的民众,使他们心甘情愿地踏上生死未卜的征途。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爆发经济危机的时候,为了转嫁危机,各国纷纷加强了对殖民地剥削和掠夺,雇佣廉价华工到这些地方从事艰难困苦的工作,以牟取暴利。
还有一些人主要是做“洋工”,在洋人的工厂、商行或家里工作并跟随雇主出国。这是极少的一部分。
今日,世界各国加强了对流动人口和移民的管理和限制,移民变得更加困难。人们不断高涨的出国愿望和现实的制约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因此,派生出了千变万化的出国途径和手段。
(一)以家庭团聚、继承财产为名出国,出现在大多数的移民家族中。第一代和第二代的老华侨们经过多年的在外拼搏,已经取得了一定的业绩,站稳了脚跟,他们纷纷把自己的妻儿老小接往国外,一来举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二来在生活和事业上多了一份助力和照应。这种移民申请多数会被通过,是最安全、有效的出国方式。
(二)以探亲、劳务输出、留学进修、旅游等为名,滞留他国。这些人一般都有一定的海外关系或具有一定的知识和技术,他们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利用自身的一些条件,谋求到合理的出国机会。在到达国外后,利用种种可能的情况,滞留国外,等待时机,取得合法的居留资格。这条道路应用越来越广泛。其中,尤以劳务输出最多。中国人的人情特别多,小到亲朋邻里,大到一村一镇,人与人之间都普遍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如:宗族关系、姻亲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朋友关系等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人际关系网。正所谓“人情比天大”。特别是在农村,人人最看重的是情面,一般人家有要求都不好剥人家的“面子”。因此,任何人只要和在国外的人扯上一点关系,你就等于有了出国的机会。这批人一般不会有过高的知识水平,生活也不会太好,无法以探亲、留学或旅游的名义出去,只能用劳务输出为借口。同时,在原本宗族关系非常严格的农村,人们的出国顺序不再象过去一样完全执著于宗族关系的亲疏。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大多数人有这种需求时,还是会遵循宗族关系行事的,这是为了安抚人心,以示公允的做法。
(三)利用中国的地理位置,以做生意为手段,进入与中国接壤的周边国家,先在该国立住脚跟,再转道去其他国家。特别是去东欧的一些国家,利用欧盟的优势,由东到西,无论是交通还是签证方面都比较方便。因此,近年来前往东欧的温州商人越来越多。近年来,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快、加深,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与融合进一步加强,不久的将来,欧盟各成员国之间会象西欧一些国家一样,往来自由,无须任何手续。这样,选择这条道路的人必将越来越多。
(四)偷渡。听到最多,也是很多人采用的一种手段。尽管多数人都知道这么做的危险性,但是对外国强烈的向往使他们对这些危险视而不见甚至甘之如饴,使偷渡之风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据统计,1989~2000年,温州市公安机关共破获偷渡案件400余起,打击处理“蛇头”487名,查获参与偷渡人员3200余名[8]。
五、目的国和谋生手段大大拓展
在目的国的选择上,新移民表现出比老移民更大的选择性和更理性的选择,一部分移民的活动显得更加有计划性,不再盲从。
一战后,温州人主要移居日本。民国11年(1922)春统计,“新从浙江温州、处州两地来日之劳工突然增加至5000余人,散处各地。”[9] 选择日本的重要原因是,温州到日本的海程是到几个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中最短的,可以大大节省旅费,对贫困的人具有最大的诱惑力,也是最实际的。中日两国自古就有密切的联系,两者的风俗和生活习惯有很多相近和相似的地方,比较容易适应。温州和日本同处海边,在饮食上也有许多共同之处。据说,温州话和日语在语调和一些音节上比较相近。这些足以构成他们选择去日本谋生的因素。
20年代末第二次移民高潮时,出于对日本1923年大规模屠杀中国劳工心有余悸,许多人转向了东南亚和西欧。这种变化,可以从瑞安桂峰乡出国的华侨流向中看出,1918~1923年,共出国82人,其中前往日本的80人,占97.56%,1929~1937年,共出国102人,去西欧的和日本的分别为67人和31人,分别占总人数的65.69%和30.39%,去西欧的人数超过了去日本的一倍多[10]。选择去东南亚的人们,理由和当初去日本的差不多,主要还是路途近,风险小,加上资本主义国家的致力开发,也为他们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去西欧则主要是看中了它们发达的经济和相邻的地理位置,便于流动和扩大谋生范围。
新时期,虽然仍有不少人沿着前辈的道路继续前进,但有许多人开始另辟蹊径,去打造自己的天空。因为走前人的老路固然有人提携和照应,但“人满为患”,竞争激烈,选择开辟处女地,虽然比较辛苦,但发展潜力很大。与30年代集中在日本、意大利、法国、荷兰、德国、美国等几大国相比,现在的温州人已经扩大到了西班牙、英国、挪威、冰岛、匈牙利、南斯拉夫、巴拿马、阿根廷、新西兰、加蓬、贝宁等65个国家和地区,遍布六大洲,可以说到处都有温州人的身影。
温州华侨华人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以什么方式手段谋生,生活处境如何?
二战前,华侨的生活处境基本相似,处于一种初级水平,只能勉强维持在温饱线上下。这是因为当时出国者多为没什么技术和知识的农民,加上言语不同(特别是在西欧的华侨),没有太多的人会雇佣他们,也没有太多适合他们的工作,因此,他们所能从事的都是一些苦力劳动或者是拿着“青田石雕”沿途叫卖等等出卖体力的劳动。后来,也有部分人在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开始从事一些小商小贩的工作(特别是在第二阶段),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比那些人好过一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依然在温饱的生死线上徘徊,并随时会受到不公的待遇,甚至是生命的威胁。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人有能力自己开办手工作坊,过上相对正常的生活。
新时期出国的华侨要比他们的前辈幸运得多,随着中国的强大和世人对人权意识的提高,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至少不必再为生命受到威胁而担心,同时有了同乡和前辈的帮助,只要你肯努力,基本上是能站住脚的。加上国内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一部分人出国已不象过去那样赤手空拳打天下,他们有一定的积蓄,对于出国作什么也有了明确的目标,甚至已有了相当的资本。很多人一去就自己做起了老板,或者先到别人那里取经再自己出来闯天下。总之,职业范围不断扩大,涉及方方面面,不再拘泥于餐饮和皮革行业,开始向一些高新技术领域进发,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经济学家、国际金融博士林建海,诺华(Novartis)生物制药集团公司高级医学顾问王家骅,伦敦大学分子病理系高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夏初临等等。
六、结语
温州人出国现象的种种变化,有学者说,大批的移民解决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大量的侨汇帮助侨乡脱离了贫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和收入水平,帮助政府加强了公共设施和文教设施。同时,他们把温州的商品推向市场,把国外的技术带回温州,大大推动了温州与世界接轨的步伐等等。但我们从近几年温州现状的变化看,繁荣的背后隐藏着不少不安的、不稳定的因素:大规模的出国潮带来了本地人口的大量流失,加上涌向祖国四面八方的温州商人,外来人口的数量已经持平甚至超过了本地人口。同时,本土高学历人才的流失,也是温州发展的一大制约。另外,华侨投入家乡建设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相对于他们的所有财产而言),他们寄回家乡的大笔侨汇都被家人用于了“炫耀性消费”,或者投资一些商业行为,如投资房地产,炒得温州的房价节节高,鹿城区的房价都已在每平方米万元上下。这么多资金没有用来投资再生产,温州到现在还在靠家庭小作坊发展,缺乏大规模有竞争力的企业,近两年在浙江的排名下降,不能不说是制约温州经济快速长远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炫耀性消费”只能更加刺激青年人向外闯的欲望,使他们无心农事,荒芜田地,浪费资源,却没有任何助力。
对比新旧时期出国潮的变化有助于我们分析和思考问题,对出国问题应从两面看,应消除出国潮带来的负面影响,积极加以正面引导。
标签:移民论文; 温州论文; 华侨论文; 移民欧洲论文; 日本生活论文; 温州房价论文; 温州房地产论文; 国外工作论文; 温州银行论文; 温州中心论文;
